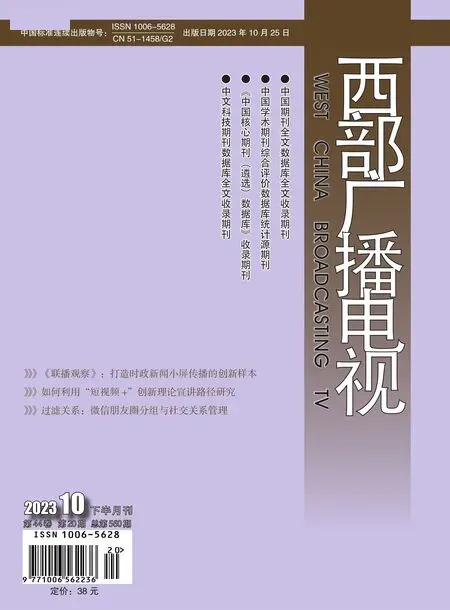文化場域視野下陸豐正字戲傳播研究
周美星
(作者單位:廣西民族大學傳媒學院)
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傳并視為其文化遺產組成部分的各種傳統文化表現形式,以及與傳統文化表現形式相關的實物和場所[1]。它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一個國家和民族歷史文化成就的重要標志,有“中華文化的瑰寶”之稱。黨的十九大以來,非遺傳播在弘揚與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提高我國文化自信和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
陸豐正字戲,又名正音戲,也有南下大戲之稱,以中州音韻官話(正音)唱念,系南戲遺響,距今已有近900年的歷史,被中外戲劇界的專家學者譽為“中國戲劇活化石”。正字戲以其豐富的文化內涵為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助力鄉村振興奉獻了力量。正字戲的保護、傳承、傳播工作仍在繼續,如何在新語境下做好非遺傳播成了陸豐正字戲劇團必須面對的一大問題。
目前,學界對陸豐正字戲的研究并不多,大多集中在其溯源考證、價值闡述上,而從傳播學視角出發考察正字戲的研究較少。從理論和現實層面來看,正字戲的傳播研究非常有意義。因此,本文立足于新時代背景和鄉村振興戰略,借助場域理論分析陸豐正字戲的傳播現狀,探討新語境下非遺傳播的文化場域構建,以期為當地非遺傳播實踐提供理論依據,使當地非遺煥發光彩,助力鄉村振興。
1 相關理論概述
1.1 場域
場域一詞源于物理學概念,后被法國著名社會學家布爾迪厄用來闡釋社會中的其他問題。在布爾迪厄的解釋里,場域就是“在各種位置之間存在的客觀關系的一個網絡或是一個構型”[2]36。根據這個概念可以知曉,場域主要是指一個系統的社會網絡中每個人所居的位置而形成的聯結,位置的不同決定了聯結所形成的網絡不同。這個網絡不是物理空間學意義上的概念,而是由人的社會屬性來決定,最終這個建構起來的場域擁有自己的運行邏輯和框架。在布爾迪厄看來,場域不是一個靜態、固定、永恒不變的空間概念,而是動態、有力量、活躍、不斷改變的,是開放性的。
1.2 文化場域
文化場域是特定文化背景下的人與人的社會關系、人的價值觀、生活方式等因素構成的社會精神化的網絡結構,它作為社會場域的重要部分,包括不同的價值取向、認知方式和行為習慣。個人作為同一文化場域中的行動者,會逐漸形成一致的道德觀念與言行方式,且更容易發揮場域的力量。相對于外部的經濟場域和社會場域,文化場域整體及其內部的各個子系統保持相對自治并激烈爭奪資源的狀態,根據擁有資本的富有程度或來自外部經濟、社會場域中的資本權力決定自身所處的支配或被支配位置[3]。
2 陸豐正字戲傳播的文化場域構建
慣習、資本是由場域中的主體(或稱行動者)在實踐過程中所統一于場域之中的,這幾個元素是布爾迪厄場域理論的核心概念。研究陸豐正字戲傳播文化場域的構建應以這幾個元素為切入點。
2.1 文化慣習
慣習是一套持久存在的、可變更的性情傾向系統[2]47。它以一種潛移默化的力量影響著人的喜好與選擇。有相同習慣的群體會更容易構建同一個場域,并且能積極發揮群體能動性,將群體構建成一個符合自身利益的系統。
陸豐處于粵東狹長的海岸上,屬潮汕文化圈,自古奉承多神信仰,佛、道、儒文化根深蒂固。各村落的慶典長年不斷,滋養了包括正字戲、白字戲、西秦戲在內的幾百個戲班。長期浸潤在傳統文化氛圍的陸豐人一直保留著聽戲的習慣,這使得正字戲能夠在當地開辟一個傳播市場。正字戲本身的戲曲特色、精彩劇目又符合當地群眾的文化喜好。如精品劇目《三國戲》取材于《三國演義》,其好惡符合陸豐人民的價值觀,深受陸豐地區人民的喜愛。因此,慣習作為一套與當地文化傳統有所牽連的較為穩定的傾向系統,是陸豐正字戲構建文化傳播場域的一大基礎,也是非遺傳播路徑探索的重要參考因素。
2.2 資本
布爾迪厄將資本的概念從經濟領域拓展至文化領域,將其分為經濟、文化、社會、符號四種類型[4]。在他看來,不同類型之間存在著相互轉化的機會。比如,當文化部分的資本積累由量變到質變,就有可能實現文化到政治、經濟方面的轉化。而文化資本之所以成為場域內外激烈爭奪的對象,在于經其轉換而成的社會、經濟勢力,可以在文化之外的其他場域發生直接作用[3]。
作為一種具有高度審美屬性的地方非物質文化遺產,正字戲傳播所要構建的文化場域存在于陸豐這個大的場域系統之中。其資本主要來自文化、政治和經濟幾方面。一方面,正字戲的文化資本使它獲得了政治、經濟的支持。陸豐正字戲現有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傳承人彭美英女士,她先后發表的多篇論文與著、編、出版的5本正字戲圖書是該領域的藝術教科書。此外,正字戲的演職人員隊伍愈發壯大,正字戲發展的中堅力量已經形成。另一方面,國家的重視、當地政府出臺的系列政策和鄉賢的幫助又為非遺的保護、發展、傳播提供了有力保障。如當地政府讓劇團積極參與各種擂臺賽、文化節活動,目的就在于提高非遺的傳播力。
3 正字戲的傳播局限
3.1 文化創新性發展動力不足
陸豐正字戲劇團于2012年轉為國家公益一類事業單位,劇團內部人員由先前的師徒制、合同制變成國家編制人員。如此轉變,一方面使得劇團歸入國家管理,擁有了更強大的資金支撐和更專業的制度管理,保障了正字戲在新時代具有招納賢才的基本物質條件。另一方面,制度化的統一管理也導致劇團人員傳播主動性退減,多為被動式傳播,創新性發展動力不充足。這是當前正字戲劇團發展與傳播亟待解決的問題。
3.2 缺乏核心戲迷群體
在陸豐,除了使用官話的正字戲,還有用福佬話演出的白字戲、栩栩如生的皮影戲、甲子英歌舞等非物質文化遺產。就戲曲方面,正字戲因使用語言與當地方言不同,所以比起傳統的白字戲在戲迷忠誠度和聚合度這一方面要遜色很多。戲迷是戲曲非遺傳承保護中一股不容小覷的力量,其不足也反映出正字戲在傳播方面需要正視的問題。
3.3 文旅深度融合能力不足
縱觀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大趨勢,文旅深度融合是非遺傳播的一大核心力量。但從陸豐正字戲發展的現狀來看,正字戲劇團的長期發展策略中缺少系統、專業的文旅深度融合設計。造成這一問題的原因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劇團的傳播觀念較保守,內部缺乏專業的傳播人才,傳播策略被動。比如正字戲劇團與中小學的合作大多囿于政府的任務指標,開放化、現代化的研學制度還未見雛形。二是廣東省陸豐市對當地優秀傳統文化的資源整合還處于探索階段,系統的“文化+”模式還未形成。
4 正字戲在文化場域中的傳播策略
正字戲在文化場域的傳播,一方面要繼續借助官方力量,為非遺傳播提供更多平臺,拓寬正字戲與國家政策、時代發展趨勢相適應的傳播渠道;另一方面也要秉承開放、共享的心態,歡迎更多群體加入傳播實踐,形成一條更具活力、創造力的傳播機制,使非遺傳播煥發生機,助力非遺的傳承與保護。
4.1 續構:持續打造文化傳播新空間
“空間”一詞是自然和社會科學研究過程中被廣泛應用的概念。20世紀中期,以列斐伏爾為代表的西方哲學家開始將空間理論運用到社會領域。在他看來,空間是一種集體創造出來或細化出來的社會空間,或者稱為“社會空間化”。文化傳播空間是在一定文化共同體內構建的社會空間,其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塑造與傳承有著重要作用[5]。正字戲扎根陸豐鄉村,扎根基層與民眾,若想要擴大傳播力、提高其在群眾心中的藝術地位,還需要持續打造新文化傳播空間。除了劇團所在的傳承基地和惠民演出廣場外,正字戲還要深入了解當地群眾的文化心理特點和審美傾向,選擇一些符合當地民情、文化特殊性的空間作為傳播的重要場域。由于空間具有一定的穩定性,群眾在接受了一段時間后,也會形成比較固定的空間記憶和認同心理。
4.2 嵌入:融合鄉村振興戰略,創作系列精品劇目
一是融入鄉村示范帶建設活動。鄉村振興是黨的十九大提出的一個偉大戰略目標,其中文化振興是鄉村振興的鑄魂工程。作為當地的優秀傳統文化,正字戲要牢牢把握這個機會,積極參加擂臺賽、文化節等活動,與當地政府配合、打造一套全面、靈活、可行性強的非遺推廣計劃[6]。同時,在保證演出數量達到基本傳播面的基礎上,正字戲還應扎根群眾,勤勞構思,創作出符合時代特點、振奮人心,能助力鄉村文化振興的精品劇目。如近年劇團的原創現代劇《黃厝寮》,講述了陸豐人民歷險克難保護周恩來同志轉移至黃厝寮養病,最后勝利渡海的感人故事,在演出后取得了群眾的一致好評。劇團以傳統的方式對這段人人傳頌的歷史故事進行精彩演繹,完美地詮釋了魚水情深的黨群關系,大力地弘揚了紅色革命精神,唱響了蕩氣回腸的英雄壯歌。此類精品劇目的創作不僅加深了群眾對紅色革命文化的認同,也促進了群眾對當地優秀傳統文化的理解。
二是積極打造“非遺強市”。陸豐市正處在示范帶建設發展階段,正字戲要善于利用鄉村振興這個大舞臺,從多方面拓展自己的傳播渠道,為當地經濟振興提供發展動力。比如,正字戲可以積極融入陸豐首次在省內推出的“鄉村文化集市”品牌,發揮自己的文化資源優勢,創新文化產品和服務,成為鄉村振興示范帶建設中讓資源變資產、資產變資金的一分子。
4.3 互動:尋找核心趣緣群體
趣緣群體是指人們因為共同的興趣、愛好而聯結成的社會群體。傳統的趣緣群體是以地緣關系為紐帶的,隨著時代的發展,傳統的聚合形態和聯結方式被打破,因共同興趣愛好聯結的網絡趣緣群體破土而出,并開始替代傳統社區發揮情感聯結功能[7]。非遺傳播離不開核心趣緣群體的加持,換言之,陸豐正字戲的傳播需要穩定、忠實的戲迷群體。正字戲戲迷的聚合源于對正字戲的興趣與熱愛,他們的群集互動性更強,對其傳承、傳播發揮著重要作用。一方面,戲迷可以在一定基礎上給予劇團以真實反饋,他們的意見和認可能為劇團注入生命力、創造力,給予正字戲傳承人和演員以信心、鼓舞,帶動劇團實現創新性發展;另一方面,戲迷會積極、主動地在人際傳播中做正字戲的宣傳者、普及者。鑒于此,陸豐正字戲應以本地為核心范圍,由此向外輻射尋找戲迷,與核心趣緣群體建立聯系,形成互動場域。通過互動場域內先向戲迷傳播、雙方交流,再由戲迷主動傳播的方式推動非遺傳播。比如,同處汕尾的西秦戲戲迷遠近聞名,對西秦戲的傳播有正面影響,正字戲可以借鑒其互動方法。
4.4 推動:打造“非遺+旅游”模式
“非遺+旅游”是指活化非遺與開發旅游相結合的產物[8]。非遺旅游的發展不僅為旅游業發展注入了新活力,而且為活化非遺開辟了新道路。陸豐是蘇維埃革命政權的創建地,同時有廣東強省的時代強音助力,加之近期正在打造多項示范帶項目,正字戲要充分借此機會,利用“非遺+旅游”的方式為自己開辟一條新的傳播路徑。比如,正字戲的服飾、妝造、唱腔、劇目等都是可以發展為文化產業的獨特資源,正字戲可以在“非遺+旅游”的框架下開設自己的文化體驗館,設計一些面向外來游客的體驗項目,通過沉浸式的參與方式來增強其對非遺的欣賞與理解[9]。同時,劇團應創新發展,成立自己的非遺品牌,打造周邊產品。正字戲可以借鑒陸豐皮影戲成立皮影戲動漫公司的做法,尋找適合自己的產業化道路。如此一來,通過市場的機制把非遺資源轉化為文化產業,可以為陸豐正字戲的發展與傳播提供經濟支持,推動正字戲文化傳播場域的構建。
5 結語
非遺傳播要積極嵌入國家制度體系中,運用多方力量將傳播力發揮到最大。在致力于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提升文化自信的時代背景下不斷構建新的文化場域,促進原有文化場域更新、發展,這是陸豐正字戲傳播的一大路徑。同時,作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陸豐正字戲也要保持自己的先進生命力,實現創新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唯有此,才能不斷增強非遺傳播的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