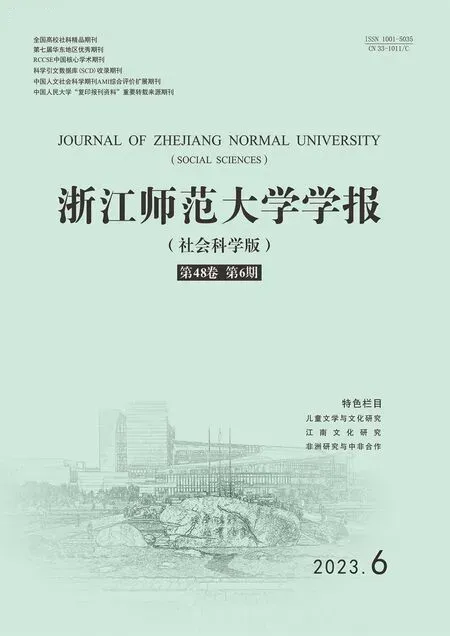時代曲與救亡歌
——白先勇小說影視化過程中的音樂修辭
俞巧珍
(浙江師范大學 國際文化與社會發展學院,浙江 金華 321004)
引 言
音樂修辭原指巴洛克時代(1600—1750)興起于德國的一種音樂詩學,是將修辭學原理與樂曲表達聯系在一起的音樂分析方法,其宗旨就是借助修辭原則進行音樂創作研究,“將修辭術語和修辭方法嚴格地運用到音樂創作和音樂分析中,是巴洛克時期德國音樂創作和理論著述中的典型現象”。[1]根據修辭文本的不同,音樂修辭話語通常分為兩類:一是以樂譜為中心的作曲法研究;①二是對音樂實踐文本的探討,即除樂譜作品外,還包含對音樂表演(演奏、演唱、配音、修飾等)過程的分析。②本質上,這是音樂詩學從將音樂作為一個文本、專注內部創造的技術特性,向將音樂作為一種語境、關注與外部再造的想象活動之間關聯對話的發展過程。
在美學意義上,修辭始終與“敘事”緊密相連,也可以說,敘事方式是展現修辭的手段。那么影視音樂就頗具典型性。
影視音樂作為一種“聲音語”,③在影視分析過程中常常被忽略。電影學者專注于影視表現中形式與結構的關系,探究影片的建構技術以闡釋影片的主旨,其中包含布景、燈光、剪輯等技術性要素,甚少考慮到音樂。“主要的規則是,如果提到了音樂,也只是以順帶簡評的形式,而且音樂往往被說成不過是畫面所表現的內容的簡單重復。”[2]216原因在于音樂本身是相當抽象、純粹的形式,“要務實地去談音樂的內容,有時是相當困難的事”。[2]216不過,“有歌詞時,音樂本身的意義就比較清晰……音樂與影像配合時,意義就更容易傳達”。[2]224
關于音樂在影像中的功能,不同的音樂理論家與影評人有不同的看法。C·M·愛森斯坦、B·H·普多夫金認為電影音樂有自己的意義和尊嚴,保羅·羅莎(Paul Rotha)甚至主張音樂有時應主導影像,當然也有導演認為音樂不過是影像的說明工具。實際上,由于導演和音樂家的合作方式不一而足,音樂的作用也伴隨著呈現形式的不同而千差萬別。有時音樂是序曲,代表著電影整體的精神和氛圍;有時音樂是暗示和隱喻,預示著人物情感、內心活動與故事結局;有時音樂是表演的旁白和補救,增衍電影的層次。以上論斷說明了一些問題,即音樂修辭與影視敘事之間的對應可以建立在諸多不同的水平面上,基本上,音樂支持、構造著影視敘事的維度。
有鑒于此,本文選取《孤戀花》(1985,導演林清介)、《一把青》(2015,導演曹瑞原)、《金大班的最后一夜》(1984,導演白景瑞)為樣本,探討音樂修辭如何與影視敘事相聯系,特別是,在顯性的影視結構中音樂作為一種與影像平等的符碼,同時也作為修辭性敘事的主體與手段,如何將影視表現中零碎的視聽信息與故事達成敘事性的統一與連貫,從而建構起隱性的音樂景觀在“表意”層面的功能。選取以上三部影視作品,一方面是其中典型的“音樂性”,《孤戀花》《一把青》直接以音樂名為題,《金大班的最后一夜》雖未以音樂為題眼,但由于金兆麗工作場合的特殊性,音樂依然是電影語境中反復出現的重要信號;另一方面,這三部作品皆改編自白先勇小說集《臺北人》。關于小說《臺北人》的討論,學界常奉歐陽子提出的“今昔對比”論為圭臬。其核心觀點是,1949前后隨國民黨撤退去臺的大陸人,在“客居臺北”的歲月中,始終無法斬斷“過去”,常有“不勝今昔之愴然感”。[3]4
從生存空間到生活狀態的“懷舊”,的確是白先勇透過《臺北人》中形形色色的人物所試圖傳達的重要話題。但需要指出的是,白先勇的“懷舊”,并不局限于臺北人的“回望”姿態,而是“回望”中有融入、“懷舊”中有接納,他表達的種種人生的“不盡意”,實際也并不僅局限于由大陸赴臺的“外省人”,而是展現了他在“中華民族”視野下對個體、對環境、對歷史的更深廣的悲憫和關懷。
我們可以從影視作品中看到,以上小說在影視化過程中,劇本和表演都表現出對小說主題相當出色的適切性,而音樂的介入更喚起了不同時代的觀(聽)眾對于“臺北人”人生狀態中脆弱、浮動、不確定的一面的理解與共鳴,從而提示我們應該在“今昔對比”的強烈反差之外關注到“在地時空”中一些共同問題的呼應和對話:兩岸底層女性相互映照的情感與精神困境、跨越省籍界限的普通人對溫暖家園的向往以及其中夾雜的諸多難以盡訴的“祖國”情懷,等等。或許這樣才更接近白先勇所描繪的世態,同時也呈現出導演在演繹故事的諸多間隙中試圖詮釋“游離”身份的現代意義空間的努力。
一、“有情之曲”:女性命運中“愛”的隱喻
我們知道,音樂作為一種話語方式,是借助聲響的波動和刺激來表達音樂家對現實世界的深層思索的,而那些被聽到的“音符”,塑造著聽眾對現實世界的感覺——包括圖景想象和認知建構,從而搭建起音樂文本與具象現實之間“隱含的類比”(an implied analogy)關系。據統計,在影片《孤戀花》《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一把青》中,涉及的樂曲大致如下。
一是臺灣民歌,如《孤戀花》《寒雨曲》(來自影片《孤戀花》,導演林清介)、《港都夜雨》《綠島小夜曲》(來自影片《金大班的最后一夜》,導演白景瑞)。
二是20世紀三四十年代流行樂,如《戀之火》《小親親》《滿場飛》《夜來香》(來自影片《金大班的最后一夜》,導演白景瑞)、《一把青》(來自影視劇《一把青》,導演曹瑞原)。
三是抗戰歌曲,如《西子姑娘》《松花江上》《長城謠》(來自影視劇《一把青》,導演曹瑞原)。
我們并不單純考量以上音樂作品的藝術價值,而是試圖從“藝術作品”的角度來衡量音樂如何在感性的藝術創作中借用修辭幻象促成了理性觀念的表達。從以上音樂文本中,我們大致也可看出,導演在音樂的選擇上,首先跨越了“大陸—臺灣”的空間界限,兩岸音樂文化共同成為影視人物情感和命運的表達途徑。換句話說,影視音樂在“歷史綿延”的維度上,進一步承載了更多更深入的關于人生、關于世界的復雜性等音樂文本之上的命題。
原則上,《孤戀花》和《一把青》都是既講故事,也講音樂的電影。所有關于音樂的細節都細膩地傳達著人物命運的流轉。兩支樂曲作為主題曲,都在影視中多次出現,是兩部劇作的靈魂所在,充滿了難以言說的命定意味。要了解這兩首樂曲,首先要了解其中的歌詞。歌曲《孤戀花》由臺北著名歌謠作詞家周添旺作詞、④楊三郎作曲,⑤以閩南語民歌的方式呈現:
風微微,風微微,孤單悶悶在池邊/水蓮花,滿滿是,靜靜等待露水滴/啊……
阮是思念郎君伊/暗相思/無講起/要講驚兄心懷疑
月光暝,月光暝,夜夜思君到深更/人消瘦,無元氣,為君唱出斷腸詩/啊……
蝴蝶弄花也有時/孤單阮/薄命花/親像瓊花無后暝
月斜西,月斜西,真情思君君不知/青春欉,誰人愛,變成落葉相思栽/啊……
追想郎君的情愛/獻笑容/暗悲研/期待陽春花再開
白先勇說,光是《孤戀花》的歌名,就讓他喜愛不已。他曾在一酒家偶遇楊三郎演奏此曲,酒女唱得哀婉凄惻,喚起了他心目中的“五寶”“娟娟”等人物形象。
《孤戀花》以一位由上海流落臺北的遲暮酒家女阿六(即電影中的云芳,又號總司令)的回憶性敘事為線索,講述她人生中親歷的兩位同為酒家女的親密女友五寶、娟娟在不同時代、不同生存空間里驚人相似的悲劇命運。五寶在上海萬春樓遭遇流氓華三,被華三以鴉片控制虐待,以至服毒自盡;而臺北五月花酒家的娟娟,因長相酷似五寶受到阿六格外照拂憐惜,但也未能逃脫“黑窩主”柯老雄的糾纏虐待。小說將兩則悲劇分別放置于戰爭前后、上海與臺北兩個不同時空,似乎仍有“今昔對比”之意,但實在很難用歐陽子所定義的“今昔對比”來完整概括。
與《游園驚夢》等小說中不斷回望大陸生活的姿態不同,《孤戀花》更深層的表達,首先是白先勇對彼時生活的那片土地上的人及其相關文化的親近、認同與關懷。如果說白先勇通過閩南語民歌將關注的焦點由兩岸生活空間的比較轉移到對兩岸底層女性命運遭際的共同關注,并在此意義上與難以回歸的“過去式”時空達成某種和解,那么影片將上海酒家女“五寶”直接置換成日據時期的臺北酒家女白玉,事實上就是將故事的焦點完全轉移到了臺灣。
電影中,樂曲《孤戀花》是日據時期臺灣樂師林三郎為酒家女白玉而作;但除了這未能善終的愛情之外,電影又以此為線索鋪展了更多層面的“愛”。林三郎對白玉的愛情、云芳對娟娟的愛護、云芳與林三郎對白玉的思念等,種種“愛”的情感都跨越時空與省籍界限;需要指出的是,從云芳的角度來說,無論她對五寶(白玉)還是對娟娟的“愛”,都頗有些女性主義的意味,但又沒能夠拯救她們。
影片最后,娟娟成了精神病人被關進醫院,《孤戀花》的歌聲幽幽回蕩在云芳、林三郎、娟娟幼子身后,詠嘆著《臺北人》中被“今昔對比”的視野遮蔽的臺灣底層女性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幾乎貫穿始終的悲劇命運。
而《一把青》的篇名則出自20世紀40年代聞名上海的電影明星兼女中音歌手白光為電影《血染海棠紅》演唱的《東山一把青》:
東山哪一把青,西山哪一把青,郎有心來姐有心,郎呀咱倆好成親。
今朝呀鮮花好,明朝呀落花飄,飄到哪里不知道,郎呀尋花要趁早。
今朝呀走東門,明朝呀走西門,好像那山水往下流,郎呀流到幾時方罷休。
用歐陽子的話說,《一把青》是白先勇在《臺北人》中將“今昔對比”之主題演繹得最明顯、直接、透徹的一部作品。《一把青》講述一位嫁給空軍飛行員的女中學生朱青,在遭遇丈夫郭軫陣亡的人生變故后,生活方式、人物性情上的巨大變化。過去的朱青,自然、樸素、純潔、拘謹;而失去郭軫之后,朱青變得矯作、世俗、華麗、浪蕩。她曾視愛情為生活的全部,卻在郭軫死后過著“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無論是在小說中還是在曹瑞原導演的影視劇中,樂曲《一把青》都是線索、伴奏,同時也是靈魂,是朱青三個人生階段的隱喻。
從美國受訓回來的空軍飛行員郭軫,將練習機低飛到朱青所在的金陵女中上空示愛,浪漫、熱烈又大膽。不過亂世的愛情,正如枝頭飄零的花朵,“飄到哪里不知道”,在時代風云中有著身不由己的宿命。郭軫死后,朱青一改往日的拘謹,她衣履風流,混跡于空軍新生社,“專喜歡空軍里的小伙子”,與小顧“眉來眼去”。可當小顧出事,朱青的表現卻淡然到讓師娘覺得“已經找不出什么話來開導她了”。事實上,從失去郭軫的那天開始,朱青不僅從此埋葬了愛情,同時也封鎖了所有鮮活人生的可能:“我也死了,可是我還有知覺呢。”[4]30
單從調式來說,《一把青》顯得比《孤戀花》更輕盈。音樂節奏輕慢推進,以輕巧的琴音描述美麗“愛情”的開始,但顯然這是一個關于“失散”的故事。歌曲在漫不經心中寄放著一絲潦倒,與流連于空軍新生社的朱青對一切的“不經意”遙相呼應。《一把青》的旋律伴隨朱青出現在臺北的不同場合,重重疊疊,都在虛幻中傳達著朱青以“流離放任”來遮蔽她對愛情的執著、對失散的結局深切悲痛又無可奈何的生命形態。
值得一提的是師娘,她也有深情,但她看透戰爭時代的種種“不確定”,以一以貫之的“平靜”面對喪夫喪子的境遇,這種“平靜”在音樂的烘托下給朱青這個角色注入了更立體的意蘊。換句話說,師娘之于朱青,或許是一種啟蒙的寓意。
“失散”作為《一把青》的重要命題,不僅僅是朱青面臨的問題,也是被迫卷入戰爭的所有人的主題曲。只不過當事人的心情、人性中的脆弱和孤獨、活著的勇氣,在時代洪流里都微不足道。
關于娟娟和朱青,音樂本來應該是她們的救贖,最終兩人各自選取自己的依歸。《孤戀花》的基調是冷暗,猶如難以舒展的冬日雨夜,娟娟始終戰戰兢兢,以《孤戀花》自我回應,用閩南語方言暗自表達歌女飄零凄迷的身世,是一種沉浸著生命痛苦的美學;《一把青》也講飄零,但似乎表現著一種超然式的情緒處理,音樂中頗帶著一些與生死離別之間的距離,盡管朱青這個角色本身被緊緊包裹在死亡、回憶和忘卻等種種厚重的主題中,亂世深情,如花開花落,回轉的意味甚濃。
不過,《金大班的最后一夜》并非以音樂命名,在小說中也只有《小親親》一閃而過。但由于金兆麗舞女的身份,影片中多次出現了以《小親親》為代表的“舞廳流行曲”,因為音樂表現是影片敘事中的重要事件。作為舞廳伴奏,圍繞著金兆麗的音樂既是聽覺的、感覺的,也是視覺的。音樂與人物之間彌漫的曖昧輕浮如空氣消磨著她的日常生活,不著痕跡,又隱隱賦予作品中人物潛在的生命力。《小親親》由音樂家黎錦光⑥作詞曲,徐小鳳演唱,全曲如下:
你呀你,你是我的小親親/為什么你總對我冷冰冰/我要問一問/請你說分明/你對我呀可真心。
你呀你,你是我的小親親/為什么你總對我冷冰冰/我要問一問/請你說分明/你對我呀可有情。
你不說分明/當你假呀假殷勤/你的話我不聽/你不說分明/當你假呀假惺惺/你的情我不領。
你呀你,你是我的小親親/只要你不再對我冷冰冰/你也要像我一樣用真情/免我早晚心不定。
和小說一樣,影片也從美人遲暮的金大班決定“老大嫁作商人婦”切入。作為夜總會常用曲目,音樂《小親親》響起時金兆麗的工作場景就被精確建構。在此,音樂看起來是作為故事背景的一部分出現在與金兆麗有關的影像敘事中的。相對于其他信息,《小親親》的音樂主旨清晰地預示了金兆麗及其人生該如何被理解、被定位。《小親親》的字里行間,表達的是卷入戀愛中的年輕姑娘深情、哀怨、患得患失的心情——也是年輕時的金大班曾冒出過的“許多傻念頭”之記錄。隨著音樂低回婉轉的旋律,引發金兆麗對青春時代與盛月如之間那一段交織著美好和殘酷的往事追憶,以化解現實時空中因青春消逝而失去獲得愛情可能的哀傷。
電影在敘事過程中借助音樂旋律打破了時間界限,在過去與現在的時空間來回切換,既是金大班在想象的時空中對過去時光、當下時光乃至未來時光的表述,也是身處風月場中的金大班對于愛與幸福的追求在想象時空與現實時空中的并置。二十年前與盛月如的幸福愛情,始終是金兆麗不斷緬懷的吉光片羽,她不得不在“下嫁陳發榮”的現實時空中不斷修繕過去以填補當下及未來人生的遺憾。導演處理這種虛實并行的電影語言時,也虛實交織地使用了音樂,在一個個看似漫不經心的場景中展現金兆麗的真摯。
《小親親》與《一把青》同寄一調,編曲簡單而有層次,流淌著“愛”的不經意,也共同指向“愛”的不完全,結尾充滿余韻。應該說,三部影視劇在闡釋小說的過程中,同名音樂成為影視表達的基礎鏡像,隱喻著女主人公在各自生命歷程中在愛與希望的保存、找尋和延續的命題上共同遭受的困境,因此“今昔對比”的命題,并不單純指向大陸—臺灣的地理空間,更指向現實生活中女性心理經驗和生命狀態的更深層面目:她們曾是美麗的、純真的、優雅的,卻不得不寂寞地、身心俱疲地幽隱在人間。她們遭受了許多艱難的時刻,積攢了很多的失望,甚至被凌虐至發了瘋。在此過程中,“愛”的命題有著多重關聯,包括艱辛的成長、浪漫又短暫的婚姻、難以跨越的階級、對衰老的無奈和恐懼以及死亡的難以預料等,無論是娟娟、朱青還是金兆麗,她們每個人生命中零碎的片段都夾雜著諸多復雜的層面——在很大程度上,這也是離亂時代普羅大眾的縮影,具有相當的普遍性。影像未能一一訴說的,音樂都做到了。
二、“時代之音”:流離歲月里“家”的尋覓
對于影視音樂而言,修辭結構常常是一個綜合性的由一首以上的曲目相互組織、共同作用而形成的有機整體。也就是說,影視中所有音樂曲目的集合體現出導演對不同層次音樂修辭活動的綜合構思。在影片《孤戀花》中,很顯然音樂《孤戀花》是整部影片音樂結構中的基礎性結構。但除此之外,影片也有意地使用別的音樂材料,以相似素材的旋律輪廓和節奏處理,從不同側面解析影片《孤戀花》的深刻主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影片中出現的另一首臺灣民歌《寒雨曲》。《寒雨曲》于1944年由日本作曲家服部良一⑦譜曲、香港音樂人陳蝶衣⑧填詞、潘秀瓊錄唱,是典型的日曲填詞歌曲,⑨也是藍調歌曲。⑩全曲如下:
吹過了一霎的風/帶來一陣濛濛的寒雨/雨中的山上是一片翠綠/只怕是轉眼春又去。
雨呀雨/你不要阻擋了他的來時路/我朝朝暮暮盼望著有情侶。
藍調歌曲被稱為黑人的“苦難之歌”,是所有黑人在黑暗舊時代下的苦難過往與疲憊心靈的見證。因而《寒雨曲》出現在娟娟的酒肆演唱場景中,也隱隱昭示了她迷蒙的傷感和惆悵。我們可以通過娟娟對阿六的傾訴得知,她發了瘋的母親被父親鎖在豬籠里,她偷偷去送飯卻被母親咬傷;父親醉酒后強暴了她,又在她懷孕后天天將她拎到鄰居面前示眾,罵她:“偷人,偷人!”對此情形,阿六的感想是:“我輕輕地摩著她那瘦棱棱的背脊,我覺得好像在撫弄著一只讓人丟到垃圾堆上,奄奄一息的小病貓一般。”[5]123
娟娟從蘇澳鄉下流落到臺北當酒家女,這種飄零的身世,與被販賣到美國的黑奴處境并無二致。這使得年代如此久遠的民歌出現在影片中也毫無突兀之感,可見導演在音樂素材選用和處理上的煞費苦心。
伴隨著哀婉的單聲部旋律,我們可以看到,在那個傳統意義上被視為故鄉的空間里,娟娟并未得到過絲毫持久穩定的有關“故鄉”的溫情回憶。她深陷柯老雄的暴力虐待,并不單純因為軟弱,一定程度上也源于她對某種強大力量的期待與依賴的本能。關于阿六讓她“小心”的提醒,她也只是“凄涼地笑一下”,十分無奈地說:“沒法子喲,總司令。”“說完她一絲不掛只兜著個奶罩便坐到窗臺上去,佝起背,縮起一只腳,拿著瓶紫紅的蔻丹涂起她的腳指甲來;嘴里還有一搭沒一搭地哼著《思想起》《三生無奈》,一些凄酸的哭調。”[5]126
這個場景與朱青在小顧飛行失事后的表現極其相似:“原來朱青正坐在窗臺上,穿了一身粉紅色的綢睡衣,撈起了褲管蹺起腳,在腳指甲上涂蔻丹,一頭的發卷子也沒有卸下來……朱青不停地笑著,嘴里翻來滾去嚷著她常愛唱的那首《東山一把青》。”[4]40郭軫死后,朱青有過“家”的溫情嗎?歐陽子曾指出,朱青在麻將桌上習慣性反復哼唱的歌曲,反映的正是今日朱青“得樂且樂”的人生態度。
如果說,朱青以“快意人生”來表達對沒有郭軫的“家”的深深失落,那么身為酒家女的娟娟卻始終處在“離家”而“無家”的空洞中。《思想起》是早期流行于臺灣南部恒春一帶的閩南語民歌,又叫《恒春調》。傳說兩百多年前清朝曾派大量官兵和移民,渡海開發臺灣,這些遠離家鄉的人們,用當地流行的曲調填詞,表現他們對家鄉的思念,故而得名。
冬天過了是春天/百花含蕊當要開/阿娘生做真正美/想無機會來相隨。
《三聲無奈》也是日曲填詞歌曲,是日據時期臺灣民眾借相思、失戀的情緒來表達被殖民語境下愁悶、壓抑的精神狀態。可以說,在《寒雨曲》《思想起》《三聲無奈》《東山一把青》中,共同隱藏著身世飄零、無家可歸之“異曲同工”之意。
從音樂修辭層面而言,《寒雨曲》《思想起》《三聲無奈》等民歌的音勢效果是模糊的,甚至并未完整連續地出現,僅以音色“點染”。這些歌曲與主題曲《孤戀花》一起,將影片所謂“無家”之“境”的主題展示到極致。
“某種意義上,人是鄉愁的動物,他為自己一次又一次地被拋棄而哀愁。個體從自然、子宮、家庭、故鄉以及文化母體中脫離出去,又總是在孤絕中尋找回家的道路。”[6]43在臺灣電影中,回家的道路呈現出一種“在家而無家、無家而尋家的特征”。[7]娟娟和朱青都在經歷“無家”的巨大痛楚中看透了曲折人生的虛無感,但金兆麗看起來卻有所不同。失去盛月如二十多年后,她早已看清愛情婚姻的真相,卻仍然一步一步認認真真為自己謀求以安穩為首要前提的“家”。在影片《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中,除了被歐陽子視為“俗詞艷曲”的《小親親》,還使用了《港都夜雨》《綠島小夜曲》等樂曲伴奏。《港都夜雨》極少見地描繪了臺灣本地男性的生存實景:
今夜又是風雨微微異鄉的都市/路燈青青照著水滴引阮心悲意。
青春男兒不知自己要行叨位去/啊……漂流萬里/港都夜雨寂寞暝。
想起當時站在船邊講甲糖蜜甜/真正稀微你我情意煞來拆分離。
不知何時會來相見前情斷半字/啊……海風野味/港都夜雨落袂離。
海風冷冷吹痛胸前漂浪的旅行/為了女性費了半生海面做家庭。
我的心情為你犧牲你那袂分明/啊……漂流萬里。
被任黛黛挖苦為“還在苦海普度眾生”的金大班,實際也獲得過輪船大副秦雄的一片癡心,不過從“家”的意義上來說,秦雄卻要她再等五年,迫使她最終放棄秦雄下嫁陳發榮。影片中,陳發榮帶金大班參觀陽明山別墅,并表示愿意過戶到她名下以表誠意。她意味深長地感嘆:總算有個落腳之處。相較之下,在“尋家”的過程中,金兆麗雖不斷回望大陸時期那段純美的愛情,但她更積極地追求生活的安定以抵抗青春逐漸消逝的焦慮。在此過程中,臺灣的輪廓開始變得明晰起來。導演借助《綠島小夜曲》娓娓道來的深情,無疑召喚了在臺灣尋覓自我身份與安穩生活的人對臺灣這片土地的認同。
從金兆麗的立場來說,《綠島小夜曲》傳達的首先是情感上對臺灣的確認。導演致力表現的大陸時期金兆麗的個人成長經驗,在功能上的確回應了“今昔對比”的議題。但不可回避的是,這種經驗的回顧不是為了“懷鄉”,而是為了使之成為啟發她自身以及相同職業與階層的女性形成在地生存經驗的知識之源。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呼應了20世紀50年代赴臺女作家在回望大陸悠遠的文化歷史、生活趣味的同時,提出的“此處心安即是家”的異地生存命題。
歐陽子說:“《臺北人》中的許多人物,不但‘不能’擺脫過去,更令人憐憫的,他們‘不肯’放棄過去,他們死命攀住‘現在仍是過去’的幻覺,企圖在‘抓回了過去’的自欺中,尋得生活的意義。”[3]7如今看來,這種說法就很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很顯然,在小說《孤戀花》《一把青》和《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中,關于“臺北人”的生活樣態,作者捕捉到了更多更為個人化和私密化的經驗,而這些經驗在影視化過程中,如果我們從意識形態角度介入,即可看出在既定的言說體系之下,“臺北人”實際上面臨著地理媒介之外的更細密的表征——通常的族群、階級區別消弭于性別、家園等更為具體的話語敘事之中。民間音樂,特別是帶著濃厚藍調歌曲色彩的日曲填詞歌曲的使用,除了再現一種感傷凄美的情緒氛圍之外,也以個體人生為媒介追溯了沉痛的被殖民史和戰爭史。換句話說,盡管白先勇不斷地在小說中感嘆“今昔相對”的境遇,臺灣在很多時候被不同程度地放置在“他者”的位置,但是,他并未將大陸與臺灣、今時與往日對立,而是在充分表達了“臺北人”異地生存的流落感之外,挖掘了同為“臺北人”生存的艱難與辛酸,從而建構起不同身份背景的“臺北人”(本省籍和外省人)在臺灣找尋更大的主體自我的經驗歷程——某種意義上講,“中國人”才是他們最大的共同身份。在此過程中,音樂就成為將個人的生命際遇、情感記憶以及兩岸的歷史記憶很好地并置在一起的重要符碼,也是在小說與影視之間、地緣身份與社會身份之間達成一種多重聲部敘事的精神進階。
三、“救亡之聲”:抗日戰爭延長線上“國”的寓言
關于音樂是否具有社會實用功能的問題,音樂學家們在很長的時間里一直爭論不休。許多浪漫主義者秉持“藝術對推動社會進步起重要作用”的觀點,認為藝術在某種意義上是“社會公眾意識的表達”;也有音樂理論家認為“藝術是美而不是功利性”,“真正的美不可能有所圖”。[6]43但形式美的展示,事實上只有以特定社會、個人的情感或人文情懷為依托才能獲得藝術生命的豐厚與深邃。如果說《孤戀花》在某種意義上也可視為日據臺灣的象征,那么《一把青》在很大程度上則體現了1949年以后赴臺軍民的主體寓言。關于《一把青》,曹瑞原在其導演的同名影視劇中,對人物設置、故事情節以及敘述空間都做了較大范圍的調整和改動,特別是,對朱青及空軍大隊各色人物命運背后的歷史和時代做了深入且正面的探索。
前面說過,白先勇的小說文本《一把青》中并沒有正面描寫戰爭,而是側重表達“喪夫”這一人生變故帶給朱青的命運轉折。由于《一把青》的背景涉及中國近現代史上抗日戰爭與國共內戰兩次重大戰事,在短篇小說中不可能把戰爭敘述作為重點加以展開,曹瑞原則在動態的影像空間對戰爭進行了深入具體的敘述,而音樂也成為這種敘述的重要指涉。除《東山一把青》外,曹瑞原在電視劇中還另選了三首戰時流行樂《西子姑娘》《松花江上》和《長城謠》,作為戰爭敘事的載體。
《西子姑娘》發行于1946年,彼時為抗戰勝利后一年,空軍復原南京,“航空委員會”更名“空軍總司令部”,為提振空軍士氣,激勵斗志,由傅清石作詞,劉雪庵譜曲,先選中陳燕婷主唱,后又由周璇、姚莉在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分別灌錄,作為空軍軍歌。全曲如下:
柳線搖風曉氣清,頻頻吹送機聲,春光旖旎不勝情,我如小燕君便似飛鷹;
輕度關山千萬里,一朝際會風云,至高無上是飛行,殷勤期盼莫負好青春;
鐵鳥威鳴震大荒,為君親換征裳,叮嚀無限記心房,柔情千縷搖曳白云鄉;
天馬行空聲勢壯,逍遙山色湖光,鵬程萬里任飛翔,人間天上比翼羨鴛鴦;
春水粼粼春意濃,浣紗溪映花紅,相思不斷筧橋東,幾番期待凝碧望天空;
一瞥飛鴻云陣動,歸程爭乘長風,萬花叢里接英雄,六橋三竺籠罩凱歌中。
《西子姑娘》出現在赴臺之后朱青與小顧的感情線上。小說中白先勇賦予朱青與小顧的關系頗多曖昧不明的色彩,而在曹瑞原鏡頭下,朱青對小顧的感情更為決絕,或者說,是小顧單方面承擔了對失去郭軫之后的朱青的愛戀。其中邵志堅接手犧牲學長遺眷的行為似乎成為一個暗示和隱喻,推動著小顧以照顧郭軫遺孀的名義靠近朱青,卻被朱青一再拒絕。
《西子姑娘》將飛行員對日常溫情的期待和“報效國家”的國族想象有機連接,小顧自然也是懷有如此心愿的,但直到他接受最后一次飛行任務前,兩者都未能達成。由此還引發另一個問題,即國民黨當局彼時偏激的戰爭宣傳,導致他們的軍事命令都缺乏正面意義,致使軍人尷尬地處在一種虛無主義遮蔽下的身份焦慮中。對此,曹瑞原借用空軍大隊長江偉成、副隊長邵志堅以及樊處長在不同場合發表的關于國民黨內戰的觀感和言論加以闡述:“自己的村子炸多了,就回不了家了。”作為軍人,無論是郭軫、江偉成、邵志堅、樊處長還是小顧,都清晰地看到,打仗的意義在于保家衛國——“多打下幾架日本鬼子的飛機”,而不是“多炸幾個自己的村子”。但作為國民黨治下的軍人,他們的人生不得不凝固于戰敗赴臺后的國民黨所建構的“國家危機”謊言中,從而不可避免地陷入某種身份價值的矛盾性和空洞性。換句話說,《西子姑娘》承載著國民黨空軍對個體人生、對民族國家的萬縷長情,但這種溫情和正面的國族想象被定義在了1945年以前。
《西子姑娘》之外,曹瑞原還在劇中使用了兩首抗戰歌曲《松花江上》《長城謠》。《松花江上》是抗戰時期《流亡三部曲》之一,發行于1936年,由張寒暉填詞譜曲。彼時已是在“九一八”事變五年之后,東北大地早已失去往日平靜。大批東北民眾有家難歸,流亡關內:
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礦,還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還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九一八,從那個悲慘的時候
脫離了我的家鄉,拋棄了那無盡的寶藏
流浪,流浪,整日價在關內流浪
哪年,哪月,才能回到我那可愛的故鄉;
哪年,哪月,才能收回我那無盡的寶藏;
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時候才能歡聚一堂。
1936年歲末,此曲在西安中學首次公演,此后在東北軍中廣為傳唱,它悲憤凄涼、如泣如訴,唱出了亡國的血淚、民族的悲傷,激起了廣大軍民強烈的抗日熱情。[7]
《長城謠》發行于1937年“七七”事變之后,由潘孑農填詞、劉雪庵作曲,周小燕演唱。原準備作為電影《關山萬里》的插曲,不過由于“八一三”淞滬會戰爆發,電影剛開機試拍就夭折。而樂曲卻因民族危亡的現實引發了民眾巨大的情感共鳴:
萬里長城萬里長,長城外面是故鄉
高粱肥,大豆香,遍地黃金少災殃
自從大難平地起,奸淫擄掠苦難當
苦難當,奔他方,骨肉離散父母喪
沒齒難忘仇和恨,日夜只想回故鄉
大家拼命打回去,哪怕倭寇逞豪強
萬里長城萬里長,長城外面是故鄉
四萬萬同胞心一條,新的長城萬里長
“萬里長城是中華民族凝聚力的象征,也是中華民族抵御外侮、剛強不屈精神的表現,歌曲以長城內外的富庶和日寇侵略的災難作對比,號召大家打回老家,建造新的長城。”[8]這兩首救亡歌曲,記錄了十四年抗戰期間流離失所的廣大民眾的悲憤和哀傷。但抗戰結束了,顛沛流離的命運遠未結束。這兩首歌曲出現在曹瑞原劇中的場景是:國民黨敗退臺灣之后,墨婷的地理老師在授課時說到東北,突然拋下粉筆唱起“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悲憤不能自抑。
這是很有意思的鏡頭。在影視音樂的實際運用中,有一種重要的形式是“音畫并行”,即音樂本身已經具備相對獨立、完整的主題表達,與影視畫面不形成天然固有的“自然”關系,因而影視表達中一個相當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在相互獨立的聲音和畫面之間建構起一座橋梁——認知與經驗,從而形成一種聲畫融合并行的方式。如果沒有音樂的介入,墨婷上學的畫面就只是表達一種外省人的臺灣生活視象,而缺少縱深的維度。
從敘事空間的角度而言,影視視象可分為畫內空間與畫外空間,音樂看起來是畫外空間的表達,卻暗示了人物內心的聲音,喚醒了1937年以來中國人難以擺脫的與戰爭相伴隨的日常生活記憶。在《松花江上》與《長城謠》的音樂節奏中,我們清楚地意識到,對于無數作為“外省人”的普通人而言,海峽對岸的“故鄉”是作為一種永久性的情感空間而存在的——實際上歐陽子“今昔對比”論的核心意義也在于此。“歸鄉”的渴望是自抗日戰爭以來循著流行音樂軌跡留在千千萬萬因戰爭離家的人們內心深處無比深刻的、可辨識的情感單位,凸顯出在臺灣的生存空間里更為豐富的敘事層次。
《一把青》以國民黨空軍及其眷屬的遭遇和命運為主要故事藍本,除朱青外,《一把青》中的人物都數度追憶大陸,并廣泛涉及遷臺民眾的在臺生活經歷。這些“臺北人”雖然身在臺灣,卻始終無法忽視自身的歷史和文化經驗——他們內心深處強烈的民族歸屬感和清晰的國家認同,都在戰時流行音樂中獲得了深深的共鳴。曹瑞原導演的《一把青》,借助音樂在一定程度上還原了戰爭給民眾帶來的傷痕體驗,對民眾記憶中的歷史現場進行了正面描述,批判了20世紀50年代以來國民黨威權統治和“白色恐怖”的政治氛圍,也揭示了“國族認同”走向惡質化的歷史事實及其帶給民眾的集體創傷。
結 語
從修辭視角來討論音樂,是對音樂分析、音樂表演等音樂研究與實踐工作空間的拓展。而關于音樂在影視中的修辭功能的分析,更進一步證實“修辭”是一個“有用”的概念,而不僅僅是一種理論視野。特別是,在我們沿著音樂的線索回顧與反思民族歷史的過程中,音樂修辭更可作為一種重要的影視表達的姿態來考量:音樂話語中的隱喻、重復、象征、呼應等形式承載著諸多影視無法用語言(臺詞)陳述的現實社會情感與心理狀態。
1987年以后,臺灣影視劇的創作語境開始松動,寫實主義傳統得到進一步深化,日據時期的民眾經驗敘事得以呈現出更細微的面貌,也促使一些影視劇跳出“大力宣傳和忠實執行當局政策”的藩籬,拓展了民族歷史書寫的疆域。由于影視導演們各自關懷的視角不同,不同族群的歷史記憶和生命體驗衍生出了各異的身份訴求。白先勇的小說顯然是對外省人離散記憶的深度挖掘,“回望的鄉愁”的確也是表征“游離”他鄉的外省人“中國情結”的典型載體。1949年國民黨敗退臺灣是中國現代歷史上影響最為深遠的一次集體遷徙,盡管遷徙之地仍在中國境內,但此后深重的“游離”感確實也是生存在兩岸政治夾縫中的臺灣“外省人”身份認同的新印記。而這種國土內的“流亡”狀態本身,早在日據時期就已漸次浮現。影視劇《孤戀花》《金大班的最后一夜》對臺灣鄉土音樂特別是閩南語民歌、日曲填詞歌曲的交互引用,除了借用音樂表達電影人物具體而微的情緒情感之外,更呈現了臺灣民眾文化意識中所夾雜的歷史想象和家園建構的復雜性;而《一把青》中空軍軍歌、抗戰歌曲的再現,也寓示著劇作的敘述話語,溢出了小說中傳達出的時代洪流中個體生命的喪失感和無力感,而試圖呈現出白先勇在《臺北人》中反復訴說的那種獨特的“家”的焦慮——這當然與臺灣社會一直以來的現實處境有著莫大的關系。國民黨當局長期將政黨沖突放置在“抗日戰爭”的延長線上,白先勇對這種狀態的洞察,被導演借用音樂的形式策略性地放置在影視敘事的肌理中。應該說,三部作品對兩岸音樂的使用,一定程度上稀釋了長期以來學界對《臺北人》中地理文化空間沖突感的關注和解讀,影片本身在尊重小說對個體生命體驗書寫的基礎上,借助音樂敘事,使觀眾在音樂體驗中,捕獲到了更為寬廣深厚的“中華民族”這一身份立場。
注釋:
①德國作曲家布爾邁斯特在《音樂詩學》中提出,音樂修辭原則是一種作曲教學方法,通過規則—實例—模仿,使學生掌握修辭規則,從而增加音樂表達能力;同時音樂修辭原則又構成一套音樂分析理論,大大推動了音樂理論的發展。參見Joachim Burmeister, Musical Poetics, lienito V. Rivera tran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②不同時代的音樂理論家對音樂修辭原則有不同的考量,總體上我們看到“音樂修辭”的概念是動態發展的。從一開始借用修辭學理論探討作曲技法等音樂的形式結構,到后期關注修辭原則在音樂表達與實踐中的修飾性作用,是一個逐漸“枝繁葉茂”的過程。
③從語言修辭的理念來看,修辭應包括聲音語、文字語和態勢語。引申到音樂層面,即可看到音樂活動中包含了聲音語與態勢語。
④周添旺(1910—1988),臺灣早期著名歌謠作詞家,臺北萬華人。6歲開始習漢語,1933年為《逍遙鄉》譜曲,曾任古倫美亞唱片公司文藝部主任、歌樂唱片公司文藝部負責人。詞作有韻味、富詩意。代表作有《月夜愁》《河邊春夢》《孤戀花》《秋風夜雨》等。
⑤楊三郎(1919—1989),臺灣作曲家,原名楊我成,生于臺北永和,后遷居臺北大稻埕。從小喜愛音樂,對小號情有獨鐘。1937年赴日本學習音樂,師從清水茂雄,并改名楊三郎。1940年轉赴中國大陸,在各地舞廳、夜總會擔任樂師。1945年返臺,1947年,經呂泉生建議、由那卡諾作詞、楊三郎作曲的《望你早歸》走紅臺灣歌壇,楊三郎因此揚名。1948年在臺北中山堂舉辦個人歌謠發表會,并結識作詞家周添旺,先后合作諸多名曲。1951年創作臺灣名曲《港都夜雨》。1952年與好友那卡諾、白明華、白鳥全書等人籌建“黑貓歌舞團”,活躍到1965年。曲作旋律優美、情感細膩,既有臺灣鄉土風格,又融合了日本音樂與爵士樂特點。代表作有《秋風夜雨》《孤戀花》《春風歌聲》《黃昏故鄉》等。
⑥黎錦光(1907—1993),中國早期著名流行音樂家,湖南湘潭人。1927年到上海,加入其兄長黎錦暉任團長的中華歌舞團,成為“黎派”歌曲重要傳人。與陳歌辛一道被認為是中國流行音樂成熟期的最杰出代表,被譽為“歌王”與“歌仙”。1939年任百代唱片公司音樂編輯,為上海各電影公司作曲。其中1946年為電影《鶯飛人間》作的插曲《滿場飛》《夜來香》《香格里拉》流傳甚廣。《夜來香》曾被日本作曲家服部良一翻譯成日文,流傳日本。
⑦服部良一(1907—1993),日本著名作曲家。1907年10月1日生于大阪,曾就讀大阪實踐商業學校、大阪音樂學院鋼琴科。曾在BK管弦樂團等處任職。創作歌曲2 000余首,并有管弦樂代表作《薩克管協奏曲》《水與煙的對話》等。1959年任日本作曲家協會理事長,1978年任日本作曲家協會會長,并獲日本政府三等文化勛章。
⑧陳蝶衣,原名陳哲勛,1908年生于浙江,后隨父遷往上海。15歲進報館作練習生,1933年創辦《明星日報》,并于創刊號發起舉辦“電影皇后”選舉活動。此后又陸續擔任《萬象》《春秋》《大報》等多家刊物編輯、主編。是活躍于上海報界的知名文化人。1944年,因電影《鳳凰于飛》導演方沛霖邀請,為影片撰寫了11首歌詞,經陳歌辛、黎錦光、姚敏、李厚襄、梁樂音等五位作曲家譜曲、周璇演唱,在歌壇、影壇引起轟動。由此開啟陳蝶衣電影歌曲詞作家之路。1946年,為電影《鶯飛人間》作詞《香格里拉》,由黎錦光譜曲,歐陽于飛演唱,歐陽于飛以此曲紅遍華人社會。1947年以陳式為筆名為歌舞片《花外流鶯》《歌女之歌》作詞12首。1952年,陳蝶衣移居香港,歌詞創作進入輝煌時期。香港時期代表作品有《南屏晚鐘》《情人的眼淚》《寒雨曲》《我有一段情》等。
⑨20世紀50年代的臺灣歌壇,根據創作方式的不同,閩南語流行歌曲分為兩大類:創作歌曲和日曲填詞歌曲。日曲填詞歌曲指的是用日本歌曲的曲調或加以改編的日本歌曲調,歌詞被直譯為閩南語或填上新詞,具有濃郁的日本風格。
⑩藍調音樂,又叫布魯斯。起源于美國黑人奴隸的勞動號子和哀歌。他們哀悼與法律的沖突、傾訴對愛的失望以及對種種不公的抗爭,表達了美國黑人苦難生存的命運。從藝術角度說,藍調通常有著自我情感宣泄的原創性與及時性,注重演奏、演唱者的靈魂與音樂的相通,這種相通與演唱者的即興發揮密切相關。因而藍調音樂既是悲苦愁悶的、憂郁的,又具有平靜祥和、自由自在的情緒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