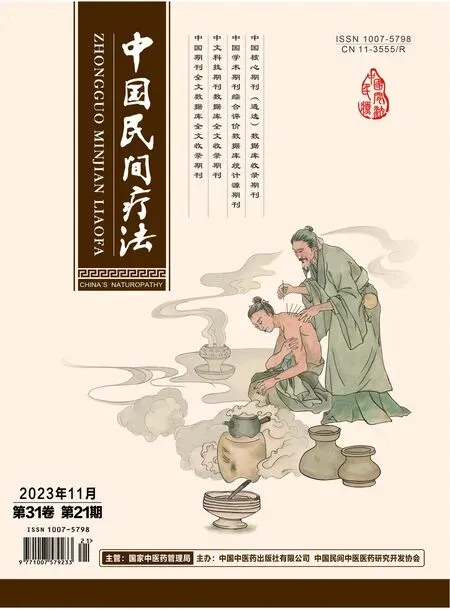豐廣魁運用己椒藶黃丸治療痰飲病經驗※
王英超,杜 青,馬先軍,孫 娜,萬芳村,楊曉明
(南京中醫藥大學連云港附屬醫院,江蘇 連云港 222000)
痰飲病是指體內水液運化輸布失常,水飲停聚于某些部位的一類疾病,臨床表現為咳嗽、喘滿、痞悶、嘔吐、眩暈、心悸、短氣、疼痛、水腫、小便不利等,其含義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痰飲是諸多飲證的總稱,既包括痰飲、溢飲、懸飲、支飲4類,也包括水氣病。張仲景在《金匱要略》中始將痰飲作為病名,其中《金匱要略·痰飲咳嗽病脈證并治》專門論述了痰飲致病的諸多證候,并介紹了21首經方的應用經驗[1]。
豐廣魁教授,主任中醫師,博士研究生導師,江蘇省名中醫,第2批全國優秀中醫臨床人才,第6、7批全國老中醫藥專家學術經驗繼承工作指導老師。豐廣魁教授學宗仲景,博采眾家,從事中醫臨床、教學、科研工作30余年,其臨證診病精于辨證,工于遣方,尤善運用經方。筆者常跟隨豐廣魁教授臨床診病,現將其運用己椒藶黃丸治療痰飲病經驗介紹如下。
1 痰飲病的病因病機
人體水液的運化、輸布、排泄主要依賴肺通調水道、脾運化水濕、腎蒸化水液及三焦的氣化作用。肺、脾、腎三臟相輔相成,共同主導水液的代謝,三焦司一身之氣化,為水液升降出入的通道,氣化則水行。如果三焦氣機不暢,失于宣通,或肺、脾、腎功能失調,水液運化失常,則會變生痰飲,如《圣濟總錄·痰飲統論》記載:“三焦調適,氣脈平勻,則能宣通水液,行入于經,化而為血,溉灌周身;三焦氣澀,脈道閉塞,則水飲停滯,不得宣行,聚成痰飲。”外感寒濕、飲食不當、情志失調、勞欲太過、體虛久病均可引起肺失通調,脾失轉輸,腎失蒸化,三焦氣化失常,導致水液停積,四處流竄,波及五臟,變生諸癥。痰飲病總屬陽虛陰盛、本虛標實證,臨床多見寒飲證,但筆者根據臨床實踐觀察發現,飲熱互結證亦不少見,國醫大師周仲瑛、李士懋在學習前人經驗的基礎上,證之于臨床,亦認為確有飲熱互結證[2-3]。豐廣魁教授認為痰飲病飲熱互結證的主要病因如下:先有寒飲,日久不愈,郁而化熱;或素有寒飲,復感外邪,化熱入里,與飲相結;或感受溫熱之邪,致三焦氣機不暢,水飲內停,飲熱兼見;或素體陽盛,胃熱消渴,飲水過多,運化失常,停而為飲,飲熱互結;或情志失調,氣機逆亂,氣脈阻滯,飲停化熱。飲熱之邪可流竄上下,無處不至,在內可損傷五臟六腑,在外可波及四肢百骸,諸癥蜂起,纏綿難愈。痰飲流于四肢,可見肢體水腫、疼痛;上犯清竅,可見頭暈目眩;上犯胸肺,可見胸悶咳喘、咳唾引痛、痰白質黏;阻滯中焦,可見腹部脹滿、瀝瀝有聲。
豐廣魁教授認為,臨床治療痰飲病,需辨明病位和病機,對于痰飲病飲熱互結證兼見腹部脹滿、口舌干燥、二便不利者,宜使用己椒藶黃丸治療。
2 己椒藶黃丸的方藥解析
己椒藶黃丸出自《金匱要略·痰飲咳嗽病脈證并治》曰:“腹滿,口干舌燥,此腸間有水氣,己椒藶黃丸主之。”該方主治腸間飲熱成實之痰飲。方中防己苦寒降泄,利水消腫,祛風清熱,為治療飲熱證水腫、疼痛之要藥,《名醫別錄》稱:“防己……療水腫、風腫,去膀胱熱,傷寒,寒熱邪氣……通腠理,利九竅。”椒目為花椒干燥成熟的種子,味苦、辛,性寒,具有利水消腫、降逆平喘之功,《金匱要略心典》謂:“椒目治腹滿,去十二種水氣。”豐廣魁教授認為椒目是治療痰飲病飲熱互結證的良藥;葶藶子苦泄辛散,瀉肺平喘,利水消腫,善治喘咳及胸腹水腫;大黃蕩滌腸胃,清熱利濕。防己、椒目、葶藶子利水消腫,使飲熱之邪從小便出,大黃泄熱推飲,使之從大便而下,全方共奏滌飲泄熱、前后分消之效。現代藥理學研究提示,防己、椒目、葶藶子、大黃具有抗炎、鎮痛、利尿、鎮咳平喘、強心等作用,已被廣泛應用于消化系統、心血管系統、呼吸系統及其他系統疾病的治療中[4-9]。
3 己椒藶黃丸的臨床應用
豐廣魁教授根據己椒藶黃丸的方證特點,結合現代研究,將其廣泛應用于具有飲熱特征的痰飲病的治療中,包括腹腔積液、胸腔積液、心力衰竭、心包積液、腎炎水腫、肺源性心臟病等。如治胸腔積液,可依證酌加桑白皮利水消腫、瀉肺平喘,加瓜蔞清熱滌痰、寬胸散結,加枳殼、苦杏仁理氣降逆,加茯苓、冬瓜皮、薏苡仁健脾利濕,加澤瀉、豬苓、車前子利水滲濕,加旋覆花降氣化痰、行水。如治肝硬化腹水,可依證酌加白術、蒼術培土制水,加黃芪扶正益氣,其中白術和黃芪用量宜大,加白芍養陰柔肝,加三七、桃仁、莪術活血化瘀消癥,加益母草、澤蘭活血利水,加土鱉蟲通絡消癥,加牡蠣和鱉甲軟堅散結。如治心力衰竭,可依證酌加黃芪補中益氣,加人參大補元氣,加附子、干姜溫補陽氣,加桂枝助陽化氣,加麥冬、五味子養陰益氣,加茯苓、薏苡仁健脾滲濕(用量宜大),加大腹皮利水消腫,加陳皮、砂仁行氣利水。
4 臨證特色
4.1 明悉體質,辨體施藥;動態調整,固護正氣 個人體質與先天稟賦和后天影響密切相關,不同性別及年齡段存在不同的體質特點,不同的體質狀況決定不同的疾病發生、傳變和轉歸[10]。《傷寒心法要訣》指出:“六經為病盡傷寒,氣同病異豈期然,推其形藏原非一,因從類化故多端。”體質有寒熱虛實之別,藥性有寒熱溫涼之異,藥味有酸苦甘辛咸之差,因此醫者治療痰飲病須知曉體質宜忌,要注意愈病而不傷正,需結合具體病證的特點,動態調整,固護正氣。豐廣魁教授認為,醫者診治痰飲病既要詳辨入微,又要統觀全局[11]。其一,醫者需要參考患者體質確定治法治則,己椒藶黃丸一般適用于偏熱偏實體質,如果患者確有虛象,可酌情考慮先攻后補或攻補兼施,但需注意中病即止,如程門雪先生所述:“體虛者,清熱化飲之中須顧其虛……體實者,清熱化飲之中兼治其實……熱雖同而體之虛實不同也。”其二,醫者需要根據患者體質決定用藥劑量。如張仲景在論述十棗湯時提及“強人服一錢匕,羸人服半錢”,明確闡述服藥劑量應因人而異,并囑咐藥后若瀉下,需喝粥以調養胃氣。對于己椒藶黃丸之證,豐廣魁教授認為同樣可參此法,需要根據患者體質結合病情調整服藥頻次、服藥劑量、藥物比例或改變劑型等,以求祛邪護正。其三,醫者可根據患者體質預測痰飲病的轉歸和預后,并指導患者善后調理及養生。體實患者服用己椒藶黃丸后,多見邪祛正安、舌脈平和,注意節制飲食、勞逸結合即可;體虛者仍需注意調補肺、脾、腎,以固其本。
4.2 首選原方,用藥精簡;因勢利導,給邪出路 豐廣魁教授常言,醫者在臨證過程中應準確辨證,用藥精簡,有的放矢[12]。豐廣魁教授倡導首選原方治療痰飲病,原方藥味雖少,但往往能夠奏效。因勢利導、給邪出路是經方醫學重要的治則之一,在痰飲病的治療過程中,豐廣魁教授也同樣強調此點。痰飲病飲熱互結證的邪氣出路主要在于通利二便。國醫大師周仲瑛認為,古人雖有“治飲不在利小便,而在通陽化氣,氣行則水行”的論點,但是分利小便之法亦有利于加速分消水飲之邪[2]。此外,仲景痰飲諸方多次使用防己、葶藶子、大黃、芒硝,可見其意在因勢利導,給邪以出路。
5 典型病例
患者,女,82歲,2021年1月15日初診。主訴:胸悶氣喘伴四肢水腫兩個月。患者兩個月前逐漸出現胸悶氣喘伴四肢水腫,未予重視,近來癥狀加重,并逐漸出現腹部脹滿,于我院住院治療。入院胸腹部CT 顯示有心包積液、胸腔積液、大量腹腔積液。患者經治療后病情平穩,雙上肢水腫、胸悶氣喘好轉,但其余癥狀改善不明顯,復查CT 較治療前無明顯變化。2021年1月10日曾行腹腔穿刺術,術后保留引流管,每日可引流出約600 m L淡黃色液體,經多次化驗,腹水性質仍難以明確,遂請豐廣魁教授會診。刻下癥:患者精神尚可,四肢水腫,尤以雙下肢為甚,左側肢體活動不利,胸悶氣喘,活動后加重,腹部脹滿,口干,身熱喜涼,雙目有神,面色暗黃,聲高有力,納可,夜寐不安,小便調,大便秘結,舌淡暗,苔黃膩,脈弦滑。既往有腦梗死、冠心病、心房顫動、心功能不全、高血壓病、2型糖尿病等病史。否認藥物、食物過敏史。西醫診斷:慢性心力衰竭,胸腔積液,腹腔積液,腦梗死后遺癥。中醫診斷:痰飲病。證候診斷:飲熱互結證。中醫治法:滌飲泄熱,前后分消。處方:己椒藶黃丸。方藥組成:防己12 g,椒目6 g,葶藶子15 g(包煎),大黃6 g(后下)。兩劑,每日1劑,水煎,分早晚溫服。
2021年1月18日二診:患者服上方后,雙下肢水腫較前改善,腹腔引流液較前減少,其余癥狀及舌脈同前。藥已中病,初見成效,故上方改椒目6 g 為澤蘭10 g。方藥組成:防己10 g,葶藶子9 g(包煎),大黃9 g(后下),澤蘭10 g。兩劑,煎服法同前。
2021年1月21日三診:患者服上方1劑后,腹瀉10余次,瀉后肢體水腫、胸悶氣喘、腹部脹滿等癥狀明顯減輕,每日僅引流出約50 m L 的腹水。刻下癥:雙下肢水腫明顯改善,稍感胸悶氣喘,活動后加重,腹部較前松軟,大便溏,每日2~3 次,舌脈同前。效不更方,己椒藶黃丸繼續投之。方藥組成:防己12 g,椒目6 g,葶藶子15 g(包煎),大黃5 g(后下)。4劑,煎服法同前。囑拔除腹腔引流管。
2021年1月24日四診:患者肢體水腫完全消退,并能下床進行簡單康復鍛煉,活動后稍有胸悶氣喘,但能耐受,稍覺口干,時有汗出,腹軟,小便調,大便溏,每日2~3次,舌淡暗,苔薄黃,脈弦滑。復查CT 提示胸腔積液和腹腔積液明顯減少。飲熱之邪尚未根除,當乘勝追擊,以防病復。方藥組成:防己10 g,椒目6 g,葶藶子15 g(包煎),大黃3 g(后下),煅牡蠣15 g(先煎)。3劑,煎服法同前。
2021年2 月6 日患者恢復良好,病情平穩而出院。2021年3月23日患者復診,一般情況良好,肢體無水腫,腹軟。
按語:本案患者雖高齡多疾,患病日久,但其精神尚可,飲食如常,身熱喜涼,聲高有力,脈弦滑,平素體質偏熱屬實。四診合參,診斷為痰飲病飲熱互結證。言其治法,則當滌飲泄熱,前后分消,因勢利導,給邪以出路,予以己椒藶黃丸治療。初診時,豐廣魁教授指出患者服藥后應以大便溏或少量腹瀉為度,因患者年老多病而大黃藥性峻猛,故大黃僅用6 g。二診時,因藥房缺少椒目,臨時改椒目為澤蘭利水消腫,因初診治療過程中,未見患者出現腹瀉,故將大黃劑量增加為9 g。患者服藥后腹瀉10余次,但瀉后并無不適感,亦未見虛弱之象,且諸癥隨之消減,說明藥證相符,正氣未損。患者已高齡,卻被投以大黃,服藥后腹瀉多次,諸癥漸消而未生變故,可見豐廣魁教授用藥既符合“有是證用是藥”之旨,又不悖于此處經文之義。三診時,藥已奏效,繼續守方治療,將防己、葶藶子加量以增強利水消腫之功,大黃減量以防腹瀉過多而傷正氣。四診時,諸癥明顯改善,但飲熱之邪仍未根除,故守方續服,因患者時有汗出,故加煅牡蠣以收斂固澀。
6 小結
豐廣魁教授善用經方治療內科雜病。臨床醫師治療痰飲病飲熱證時,不可固守“溫藥和之”的治法,應當根據患者體質特點和病證分析正邪盛衰,精準選方用藥。己椒藶黃丸是治療痰飲病飲熱互結證的代表方,豐廣魁教授謹守病機,首選原方治療,取得良效,值得臨床推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