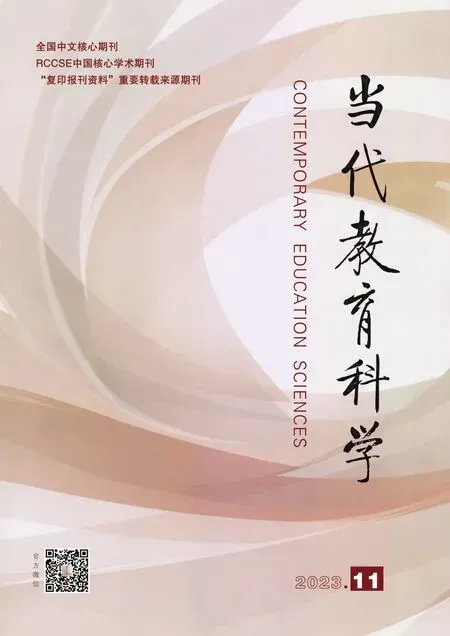兒童友好視角的教學空間建構
● 吳亮奎 楊藝寧
兒童友好是指兒童生活在一個健康舒適、溫馨有愛、不受歧視、基本權利得到保障的空間環境中,重視對兒童的人本關懷,主張釋放“兒童天性”。1989 年,聯合國大會通過了《兒童權利公約》,該公約圍繞兒童問題提出三個核心概念,即保障兒童優先、鼓勵兒童參與、維護兒童平等(聯合國大會第44/25 號決議)。這三個核心概念為我們思考如何對兒童友好提供了一個框架。根據空間社會學理論,教學空間可分為物質空間、精神空間和社會空間三層次。從兒童友好視角出發再認識教學空間三層次,有助于重新反思教學空間中存在的兒童成長問題。
一、兒童友好視角的教學空間問題表現
列斐伏爾的“空間三元辯證法”使空間得以重組,教學空間作為教書育人的場所,絕非是單向度的物質構成物,還是包含價值的精神聚集地以及人際關系編織的社會交往所。兒童是教學空間中的主體,主要活動都鐫刻著空間的痕跡,教學空間應服務于兒童活動。但從兒童友好視角審視當下的教學空間卻發現,空間設置缺少對兒童的友好,兒童主體性沒有被充分重視,兒童的自由天性和好奇心沒有受到足夠保護。下面從物質空間、精神空間和社會空間三個層次對教學空間問題展開分析。
(一)物質空間的界隔
物質空間是第一空間,是具有實在性的物象,不僅能夠被測量,而且能夠被改造和利用。教學空間展現的物理形態包括構成教室的一切客觀質料,如建構教室輪廓的門與窗,填充教室內部的講臺與桌椅等。
1.被忽視的配套設備
在當下教學空間中,填充內部的配套設備存在較多問題,主要表現為與兒童成長需求不匹配、空間分布不合理。首先,不同年級的兒童在生理上具有較大差異,身高差距明顯,即使是相同年齡的兒童,由于性別差別其身體尺度也具有差異。但學校不夠重視兒童的發展需求,采用統一化的配套設備。不同年級配備高度一致的課桌椅,這導致兒童在學習中產生不同程度的不適感。小個子兒童在寫字時會努力配合“過高”的課桌椅,從而產生疲勞感;高個子兒童會努力遷就“過低”的課桌椅,進而出現彎腰駝背。其次,大班額的教學空間所陳列的課桌椅數量多,擠壓兒童的通行空間,不方便靠墻就坐的兒童來回走動。人們對配套設備的忽視使兒童成長缺少足夠的空間彈性,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兒童的身體發育。
2.被固定的活動范圍
被固定的活動范圍主要體現在明確的功能劃分區和“目的性”的門窗使用。目前的教學空間大致可分為教學區、學習區和生活區。教學區以教師為主體,以講臺為中心向四周輻射。講臺是教室中知識與權力相結合的一種存在符號,教師在講臺上完成知識傳授、作業批改等大部分教學活動,可以站在講臺上睥睨兒童,將兒童的一舉一動盡收眼底,也可以走下講臺實施教學手段。教學區是教師的專屬領地,是監控兒童的最佳場所,卻不允許被兒童侵犯。學習區以兒童為主體,以“一人一座”的秧田式座位排布賦予兒童固定且狹小的私人領域,卻隨時可能被侵犯。教師可以根據兒童的行為表現調換座位,也可以命令兒童離開座位。生活區是以教師為主導的兒童使用區,包括衛生角、植物角、圖書角等,兒童幾乎只能在特定時間或教師允許下才能使用。在教學過程中,為了限制兒童的視覺流向,教學空間中的門窗呈遮蔽狀態;在自習過程中,為了方便教育管理者的突擊檢查,教學空間是敞亮的四方天地。一個是眺望門窗外的兒童,一個是監視門窗內的教師。當前者長期處于“他能被觀看,但他不能觀看”[1]的空間環境時,外在的好動被規訓為內在的紀律。門窗外也許不再有監視的教師,門窗內卻仍是“聽話”的兒童。固化的活動范圍使兒童的好奇心和求知體驗的主導權可能在悄悄湮滅。
(二)精神空間的阻隔
精神空間是第二空間,其表征傾向于語詞指號系統。每個教學空間在本質上并無差別,在使用功能上相差無幾,卻因內在的裝飾物、符號、標語等附件所傳達的不同語義而產生“真實”差別。教學精神空間中存在雙向約束過程。一方面,班級規章制度、評獎評優標準等符號的制定是教師單邊控制的結果,用來約束兒童的參與行為;另一方面,規則、標準等都具有自身獨特的語義,能在潛移默化中向兒童傳遞行為規范和價值期望,進而約束兒童的表現行為。
1.被控制的班級規章
班規是語詞指號系統的一種,賦予教學空間不同的色彩。班規不僅制約兒童的參與行為,而且影響兒童的精神空間。一方面,班規僅是由教師制定、傳達、監督,兒童了解、接受、遵守。教師缺乏對兒童的信任,很少放權讓兒童全程參與班規制定。尤其是對低學段兒童,教師更容易忽視其所具有的一定的自主性。另一方面,班規實施是教師主導用以規范兒童“在場”的過程。教師制定精致的班規,包括紀律標準、學習規范、用餐流程等,幾乎涉及方方面面。班規被簡單定義成用以維持時間、空間、活動、事件及秩序的操縱工具。教師習慣以成人視角為出發點,不能完全理解兒童行為,沒有對班規進行系統地指導和示范,讓處在由前運算階段向具體運算階段過渡的兒童難以真正理解班規的含義,導致兒童暫時達不到行為規范抽象概括出的幾個維度或只是程序化地淺表重復。這樣班規就失去了培養兒童養成良好行為的本真意義。
2.被桎梏的評價方式
被桎梏的評價方式是指評價主體與評價客體的單一性。評價的主導權掌握在教師手中,教師決定著評價標準與評價結果,即某種程度上評價主體的單一性導致了評價客體的單一性。在當下教學空間中,就評價主體而言,教師是主體,每位兒童只是教師評價的對象。但在面對眾多兒童時,教師多傾向于直接根據兒童的外顯行為區分好壞,很少做全局性、深層次的價值判斷與選擇。以教師一人為主體的評價,其評價結果往往摻雜著主觀成分。就評價客體而言,教師所選擇的“好孩子”評價標準與學習情況有關,兒童學習成績優秀與否仍然是主流的評價標準。教學空間的“教”與“學”是主要活動,因此學之所長便是評之所指。學優生自然而然能得到教師的高度評價,且這種高度評價是長期存在的。學習欠佳的兒童需要依靠其他特長來博取教師青睞,然而在以學為主的教學空間中,學習之外的特長只能短暫地發揮作用,使得這類兒童得到的高度評價也只是暫時性的。將“好孩子”桎梏在“學優生”的牢籠中,導致學習欠佳但另有特長的兒童漸漸在教學空間中淪為邊緣,這使原本各有千秋的兒童漸趨同質。
(三)社會空間的疏隔
“生產的社會關系具有一種社會存在,以至于也擁有了一種空間存在;即生產的社會關系把自身投射到某個空間上,當它們在生產這個空間的同時,也把自身銘刻于其中。”[2]社會空間是第三空間,包含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以及對這些關系的理解。教學空間中存在兩種重要的關系結構:一種是師生關系,包括教師與學生個體或群體的關系;另一種是生生關系,包括學生個體與群體,群體與群體間的關系。
1.師生關系的貌合神離
師生關系是教學空間中重要的社會關系,“作為異質性的既相互依存又對立的兩極,師生關系同時也是學校教育活動過程中一對最基本的矛盾。”[3]在教師擁有絕對權力主導的教學空間中,師生雙方處于一種“知和而和”的互動狀態,表現為“規范的和”與“拓殖的和”。“規范的和”是指兒童行為保持與教師塑造的規范一致,實現配合式的師生和諧。這些兒童往往處于教學空間中心區域,享有優質的空間資源,獲得的是教師的高關注、高期望。但他們往往占據教學空間權力的制高點,只能小心翼翼地配合教師的各種指令,嚴格遵守秩序,個人行動受限。“拓殖的和”是指兒童行為不配合教師塑造的規范,但通過一種表面馴服的形式出現,實現妥協式的師生和諧。這些兒童處于教學空間的邊緣區域,游離在教師視線之外,受教師關注較少或在與教師互動中不能得到及時反饋。較于中心區域的兒童,他們在教學空間中較少受到教師全方位監控,游走于各種權力力量控制的縫隙,構建一個可以容忍的世界。“拓殖策略,并不能使學生們完全擺脫權力的控制,只是在權力的層層包裹之下給自己一個既能夠發展自我,又能夠獲得權力體制中的利益的中間狀態”[4]。教學空間中的師生關系維系著表面有序的交互,實際上正以“權力之網”將原本“雙主體”轉變為“主客體”。通過“教師壓制——兒童服從”來規避空間向度下沖突的醞釀,努力形成貌合神離的師生關系。
2.生生關系的若即若離
教學空間被編碼成差異空間,因此生生關系便處于一種“若即若離”的互動狀態,體現為同質群體間的“即”與異質群體間的“離”。同質群體間的“即”是指擁有相同地位和身份的兒童彼此間關系和睦,如擁有絕對位置與特權身份的學優生之間、處于邊緣位置且存在感較低的學困生之間都能構建起互幫互助的良好關系。異質群體間的“離”是指擁有不同地位和身份的兒童彼此間關系疏離,如學優生與學困生之間難以構建平等相助的人際關系。在當下教學空間中,教師利用“優勢互補”原則安排學優生與學困生做同桌,希望通過合作學習讓學困生養成良好的學習習慣,以此拉進兩類異質群體間的距離。但實際上,由于學優生的“缺場”,“教師所設想的‘互補’關系并沒有轉化為‘互助’關系,而是被學生重構為‘幫助—受助’的單向關系。”“不少成績相對落后的學生在被問及是否得到過同桌或四人小組中成績較好的學生幫助時,都提到曾遭遇對方‘不耐煩’‘不理我’的態度。”[5]兩類異質群體正處于平而不等的教學社會空間地位,尤其是對弱勢兒童而言,長期的同伴冷落與拒絕將會帶來社會交往的不自信。
二、兒童友好視角的教學空間問題歸因
當下學校生活中教學空間的問題何以發生,教學空間為何在物質層面、精神層面和社會層面表現出對兒童的不友好?以下將從學校管理方式、兒童的主體差異、教學生活中的權力分配三個角度進行歸因。
(一)效率至上導致兒童成長的物質空間失宜
在教學物質空間的建構上,學校堅持效率至上,將兒童需求置后。其一,學校追求運作效率。學校場域是特殊的,為了正常運行,教學物質空間的改造被局限在寒暑假期間。在被規定的較短時間內,建造追求高效。學校負責人會用統一化、固定化的標準采購填充教學空間的質料,他們重視其價格和質量,忽視型號的多樣化。因此,由不同年齡兒童成長差異性所帶來的兒童需求問題難以在兼顧效率的同時一齊被重視。其二,學校追求空間效率,即空間利用率。班級授課制仍是現有學校的主要授課形式,班級兒童數量多,課桌椅數量亦多。不可避免地,由課桌椅所構成的學習區占據了教學物質空間的大部分面積。又為了追求“麻雀雖小,五臟俱全”的完備,剩下的物質空間被劃分為教學區和生活區,擠壓兒童的通行空間,造成兒童通行不便。其三,學校追求時間效率。由于課業壓力較大,教師希望提高時間利用率,讓兒童能在有限時間里完成更多的學習任務,掌控教學物質空間的使用權。拖課、訂正作業等教學活動讓原本屬于兒童自由支配的課間被壓縮,讓原本在生活區游戲的兒童被迫回歸學習區。兒童活動的時間和空間受到教師和作息表的限制,在什么時間什么地點該做什么被嚴格規定。教學空間雖是以兒童為主體的場所,但在兒童優先與效率至上的博弈中,學校更傾向于選擇后者。
(二)主體差異導致兒童成長的精神空間失落
兒童作為“尚未完全發展”的人,本身具有人的復雜性;教師作為“完全發展”的人,本身具有人的有限性。教師是無法完全理解兒童的,“這意味著教師理解兒童是一個只有起點而無終點的過程”[6]。在教學精神空間的建構上,兩者主體差異性的存在使教師對兒童的認知或多或少存在偏差。“教師往往沒有充分認識到學生活動的目的性,把學生視為一種只知接受和被動改變的對象。”[7]一方面,在教師眼中,兒童是認知有限的受教育對象,處于某種欠缺狀態,容易忽視學生的內在主動性。因此,教師不相信兒童有能力參與,進而不認可兒童有權利參與,逐漸將自己引導者、組織者的角色轉變為主導者,將應然的安全監督轉化為實然的實時監控,使兒童缺少獨立積累經驗的機會。另一方面,教師對兒童行為認知存在“人焉知魚之樂”的迷茫。教師作為成人,帶有強烈的成人色彩,難以深入理解兒童的內心世界,這所帶來的是教師以為的應知和兒童實際的未知之間的矛盾,教師以為的應做和兒童實際的未做之間的矛盾。作為兒童群體的“局外人”,守著成人的標尺,比較兒童行為與這套標尺之間的距離,以此來評價兒童的發展狀況,造成兒童成長的精神空間失落。
(三)權力控制導致兒童成長的社會空間失真
教育的分層與選拔必然導致權力控制,“成功”和“失敗”的標簽被教育的權力控制所把握。在教學社會空間的建構上,師生間的關系受其所附著的權力的影響。教學社會空間中的權力與差異相聯結。權力處于差異的上位,控制著賦予價值的尺度,劃出不同差異的界限。差異是權力得以維系的手段,通過生產差異才能分配等級,有權者才得以繼續保持自己的權威。這不僅直接影響師生之間的主體平等,而且間接挑戰生生之間的主體平等。權力控制的主體是教師,客體是兒童。“某個群體把自己的知識變成‘所有人的知識’的能力與該群體在更廣泛政治經濟領域內的權力有關系。”[8]教師是社會的代言人,對兒童進行規范意識形態的輸出。兒童是空白的受教者,處于他律到自律的過渡階段,表現出對外在權威絕對尊重和順從。在兒童心中,教師是神圣的;在教師心中,兒童是可控的。教師便擁有了教學空間權力的主導權。就權力控制的過程來看,教師獲得了權力資本之后,會在教學空間中生成差異地位以保持自己的權威,并將這種策略移植到生生交往之中。通過座位排布、考核評價、職務賦權等手段制造生生之間的差異。其結果是,權力控制策略使得“教師的”與“學生的”在教學空間中被一分為二,且前者擁有對后者的絕對領導力。屈于教師權力之下的兒童有兩種選擇:一是順從權力的規范者,二是反抗權力的拓殖者。兩種選擇在本質上如出一轍,都是對權力運作的無奈回應。兒童群體也被一分為二,學優生與學困生,有能力的與無能力的……前者是有權者,后者是邊緣人。同樣地,兒童之間的有權者不斷生產差異,拒絕靠近邊緣人,使得教學社會空間分類化、排他化。同質兒童得以聚集,異質兒童相互排斥。權力控制下產生差異,由此生成的異質群體發生碰撞,導致兒童成長的社會空間失真。
三、兒童友好視角的教學空間優化
教學是基于兒童、為了兒童、指向社會的活動。基于兒童的教學要改善物質空間,為了兒童的教學要創造兒童的精神空間,指向社會的教學要維護主體平等的社會空間。
(一)改善物質空間,保障兒童優先
在物質基礎層面,“物為人所用”才變得有價值,因此用之需求性、用之時間性、用之合理性都應遵循兒童優先的理念。首先,“物”的存在能夠滿足兒童的使用需求。在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中,生理和安全的需要是最原始,也是最需要滿足的層級。兒童成長速度快,個體與個體之間具有較大的差異性。學校應提前做好規劃,根據兒童身體發展特點制定多層次的建設標準,注重為不同年級的兒童配置規格不同或可調節的教學設備,保障兒童能在舒適的物質空間中學習。其次,“物”的存在能夠有時間被兒童使用。一種生機勃勃、穩定和諧、健康向上的環境氛圍,本身就具有廣泛的教育功能。教室中的每一寸空間,如生活區中的植物角、圖書角等都有其存在的意義。教師應認識到除學習區外其他物理空間所附著的育人作用,將使用主導權歸還兒童。同時也應杜絕“時空的暴力切割”,合理安排教學進度,給予兒童充足的課余時間,鼓勵兒童在教學物理空間中自由活動,尊重兒童的私人領域和游戲空間。最后,“物”的存在能夠被合理地利用。合理安排課桌椅的數量,調整排布方式,留出能讓兒童順暢走動的過道;合理使用門與窗,發揮其采光的本質作用,也可利用其透視性,使更多旁觀者自然監督兒童的安全。但監督并非監視,門與窗不應被化作監視體系下的“全景監控”,使兒童成為“顯微鏡”下的“被看者”。
(二)共創精神空間,鼓勵兒童參與
“空間不僅是人類生存的殼,而是經由人的主觀活動生產出來的,同時它又反過來制約和影響著人,生產了空間并存身其中的人與空間是一種雙向互動的辯證關系。”[9]教學精神空間是三維空間中最具建構性和生成性的,這也決定了教學精神空間的創造必須是由師生共同參與的。共創精神空間應是以實現兒童參與為目標的“共通、共享、共處”的過程。首先,“共通”要求教師真正俯下身去傾聽兒童內心的聲音,與兒童交往時以信任為前提。“圣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道德經》49 章),兒童作為人的存在就意味著教師不可能完全理解或精準理解兒童,師生間的主體差異性不可能完全磨滅。教師應無“常心”,不強以一己之心付諸于兒童,盡可能實現對兒童最大程度的接納、信任、寬容與諒解。其次,在“共通”的基礎上,師生應該“共享”班規、評價標準等符號的制定與實施過程,賦予兒童參與權。Riggio 將兒童的參與描述為一個全球目標,“貫穿于多種對兒童友好的模式,編織著不同的體驗。”[10]兒童不僅僅是教育對象,更是成長中的人。兒童有屬于兒童的思維方式,即使不成熟,也值得被信任。重視兒童的想法,遵照人人有事做的原則,激勵兒童發揮潛能。一位領路人比一位監督者更有可能引導兒童逐步走向完滿。最后,精神空間的創造應以“共處”為結果。“關系既是選擇者又是被擇者,既是施動者又是受動者”[11],空間精神符號不是一方控制另一方的產物,而是師生雙方彼此尊重和有責任意識的體現。當兒童認同并有意愿遵守時,外部規范才能內化為自身品質。懸置一切有限活動,達到師生間的純全真性。鼓勵兒童參與,促使精神空間成為兒童發展皈依。
(三)重構社會空間,維護兒童平等
“空間生產主體在各方面都有平等地位和機會”[12],重構社會空間既要維護師生主體平等,也要維護生生主體平等。首先,重新審視權力運作策略。克利夫頓與羅伯茲在韋伯著名的權威三類型說基礎上,提出了教師權威的四個層面。其中,法定的權威與傳統的權威源于教育制度,而感召的權威與專業的權威則源于教師的個人因素。“當教師缺乏從事這門職業的起碼的知識技能時,便不能稱之為‘知識權威’;當教師缺乏應有的師德時,便不能稱之為‘人格權威’;若兩者兼缺,則教師在學生面前便不再是‘個人權威’,而僅僅是‘制度權威’了。”[13]教師應不斷擴充專業學識,培養良好師德,提升人格魅力,用內在的精神氣質吸引兒童,而不僅僅依靠外在權力馴服兒童。其次,教師需要認清自身角色定位。教師是兒童學習的引導者、兒童經驗的改造者、兒童學習的參與者以及兒童思維的開發者,但不是主導兒童一切的專制獨裁者。師與生不是“主體—客體”的“人—物”關系,而是平等的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教師應有一種“空杯”心態,放下對兒童的戒備之心,相互溝通,相互信任,以主體間性模式賦予師生關系新內核。最后,教師應該引導兒童正確交往。“在課堂上,學生之間的關系比任何其他因素對學生學習的成績、社會化和發展的影響都更強有力。”[14]兒童是會察言觀色的,教師對教學空間中每位兒童的態度也影響兒童之間的交往。教師應保障兒童能共享教學空間資源,營造溫馨和睦的學習環境,不偏不倚,合理賦權,警惕兒童權力所滋生的差異力量。鼓勵兒童進行積極平等地人際交往,發展他們豐富的內心世界和團結協作的良好品質,讓最純粹的兒童回歸最純粹的教學社會空間。
綜上所述,兒童友好視角有助于探析教學空間中曾被成人教育者所忽視的問題。只有兒童在教學三維空間中受到理解與重視,才能真正挑戰他們邊緣性和暫時性的地位,才能真正解決教學三維空間存在的矛盾和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