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沉淪》看郁達夫東渡日本的心態之變
李小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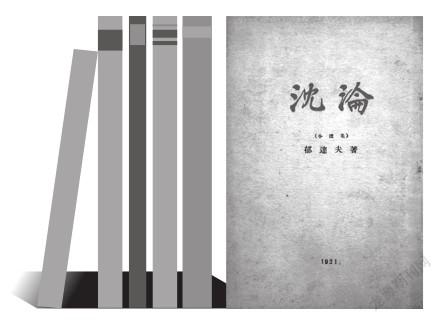
1913年,郁達夫跟隨兄長東渡日本。這位從小生活于富春江畔的青年才子,對于這次去國遠行,不安惶惑中依然充滿期待。然而,羈旅他鄉十年之后,郁達夫登上回國的船,心態與十年前大相徑庭:
我走近船舷,向我后面所別來的國土一看,只見得一條黑線,隱隱的浮在東方的蒼茫的夜色里。我心里只叫著說:“日本呀日本,我去了。我死了也不再回到你這里來了。但是我受了故國社會的壓迫,不得不自殺的時候,最后浮上我的腦子里來的,怕就是你這島國哩!”(參見《郁達夫全集》第3卷,浙江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P4)
此時的郁達夫,已經由十年前去國時的勇士變成了歸國時的歧路徘徊者。我們不禁會問:郁達夫在日本到底經歷了什么,讓他的心態發生如此巨大的改變?也許,這一切,還需從他的短篇小說《沉淪》說起。
郁達夫抵達日本之時,呈現在他面前的是一個充滿了摩登與現代氣息的大都會。連同日本街頭形形色色行人的服裝,交流的語言,都帶有濃郁的西化味道。這對于一位來自20世紀前半期鄉土中國的知識分子來說,震撼是不言而喻的。然而,最初的新奇與興奮過后,接踵而至的卻是深深的失落以及無所適存的焦慮。
郁達夫作為“創造社”的發起人之一和最重要的小說家,1921年出版了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部短篇小說集《沉淪》,其中的同名小說一經發表,引起了文壇強烈的反響。小說中的主人公“他”,是郁達夫結合自己在日本留學生活的經歷,塑造的帶有典型性特征的人物形象。這是一個在異質文化夾縫中求生存的青年知識分子。小說中的“他”,出生于富春江畔的一個小城市,三歲時失去了父親。他的哥哥從日本的W大學畢業之后,回到北京的法務部當差,負擔起了一家人的日常開支。我們從小說對“他”少年時生活的回顧中可以看出,“他”沿襲士大夫的正規渠道,從書塾開始傳統文化的啟蒙。后來“他”雖然開始接受學校教育,并最終考入一所杭州城外的教會學校,但因無法忍受教會學校的專制與保守,便中途輟學回家,在父兄留下的小書齋中讀書度日。由此可見,“他”來日本之前,接受了完備的中國傳統文化的教育。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思想觀念、處世準則、道德標準等諸種因素,都沉淀在“他”的文化心理結構中,規約著人生價值取向和生活方式。日本之行,徹底向“他”打開了認識世界的另一扇窗戶。開放的異域文化不斷沖擊著“他”業已形成的世界觀、價值觀和人生觀。這種沖擊成了主人公痛苦的根源。
不可否認,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后,中國的有識之士已經意識到了西方社會驚人的發展速度,甲午中日戰爭又使國人重新認識了日本。然而,遠距離的觀望、想象與親眼看見、親身體會畢竟不可同日而語。郁達夫初到日本,面對繁榮的現代都市,產生了巨大的心理落差。我們因此就能理解《沉淪》中主人公時時感受到“孤冷得可憐”的緣由。兩國的差距,以及這種差距帶來的巨大的認同危機,使主人公在精神和心理上處于一種緊張焦灼、無所適存的狀態,因此,他整日沉浸于自怨自艾、自尊自戀又自我貶損的復雜情緒之中。
小說的最后,主人公以蹈海自殺的方式獲得了解脫。然而,我們細究造成主人公人生悲劇的原因,除了當時積貧積弱的中國社會現實外,更深層次的原因恐怕還是異質文化的沖突所造成的個體生命的無法承受之痛。小說中的主人公,成長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時代。此時的中國,是需要以西方的科學、民主、自由的思想來啟蒙的中國,也是需要通過振興民族精神、民族文化來抵御列強入侵,挽救民族危亡的中國。一方面,以“他”為代表的知識分子來到日本,面對日益強盛的工業化的日本,對比還處于前工業時代的中國,他們對開放的西方文明無疑是信任的。另一方面,他們對沉淀于自己文化心理結構深層的中國傳統文化,有著天然的依戀親和之情,他們依然寄希望于通過振興民族文化來挽救民族危亡。開放的西方文明與封閉的傳統文化的博弈與矛盾,成為造成主人公內心沖突和復雜心理的文化根源。
郁達夫前期小說中最醒目、最具文學價值的人物形象,就是對“生則于世無補、死亦于人無損的零余者”。《沉淪》中的“他”、《南遷》里的伊人、《銀灰色的死》中的Y都是此類形象的代表。處于20世紀前期內憂外患中國社會的知識分子,“五四”雖然喚醒了他們沉睡的靈魂,可他們走出家門、國門之后,卻面臨著覺醒后無路可走的窘境。備嘗艱辛之后,他們感到寂寞和苦悶,他們渴望被救贖,寄希望于愛情,然而生在異國他鄉的弱國子民,想要獲得愛情就是一種奢望。于是,他們開始放縱自己沉溺于欲望的發泄之中,然而如同飛蛾撲火一樣,短暫的滿足之后,他們無一例外地沉淪于更深的黑暗。
小說《沉淪》發表之后毀譽參半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小說中有大量“露骨的率真”的書寫。然而,郁達夫關于情欲的書寫不是為了博人眼球,也不是為了讓自己的小說成為暢銷書。他筆下“性的苦悶”與“生的苦悶”交織在一起,主人公在靈與肉的沖突中徘徊于沉淪的邊緣,又時時發出渴望被拯救的靈魂之音。
《沉淪》中的“他”甫一出場,就是一個體弱多病、憂郁寡言的青年形象。他時常沉浸在苦悶的情緒中無法自拔。他的苦悶,既有現實的原因,又有精神的因素。現實的原因在于生活環境惡劣:來日本后與兄長不合,兄長不再資助他,生活沒有了物質基礎;精神的原因便是日本同學對他的輕視、疏遠加劇了他的孤獨,他期望祖國趕緊強大起來,然而,他又很清楚祖國不可能一夕之間舊貌換新顏。于是,他渴望愛情,渴望有一個能夠安慰他的“伊人”,“若有一個婦人,無論她是美是丑,能真心真意的愛我,我也愿意為她死的。”然而,伊人可遇而不可求,于是他只能通過偷看房東女兒洗澡,在葦草叢里竊聽男女的私語,或者喝酒后狎妓獲得滿足。
郁達夫在日本求學期間,廣泛閱讀了盧梭、施蒂納、尼采、柏格森、弗洛伊德等人的著作。這些西方近現代社會的文化巨人對人的感性生命與欲望的肯定,對他產生了深刻影響。因此,郁達夫對于《沉淪》中“他”身體最真實、最自然的情欲需求,采取的是肯定的態度。他試圖通過對這種赤裸裸的生理與情感的暴露作為反抗傳統禮教的工具,以此對“存天理,滅人欲”的傳統文化的倫理道德準則予以反擊。郁達夫在對“零余者”“生的苦悶”的表象書寫中,隱藏著對于他們靈與肉劇烈沖突的深層探究與表達。《沉淪》中“他”痛苦的根源,在于“他”不甘陷入肉欲的沉淪之中,“他”試圖通過閱讀、翻譯華茲華斯的詩歌,在大自然中尋求安慰來獲得拯救。雖然“他”的種種努力最終功虧一簣,但對郁達夫而言,他正是通過“零余者”的毀滅讓我們看到“靈肉沖突”的巨大力量,借此表達他對于“靈肉一致”生活欲望與追求的肯定,繼而完成對國人現代人格的構建。
初登文壇,郁達夫受19世紀歐洲浪漫主義文學的影響甚深,同時,日本“私小說”以及現代主義小說的某些藝術表現手法,也被他共時地吸收,轉化在自己的小說創作中,因此,他前期的小說有著非常濃烈的主觀抒情性。郁達夫認為,一部好的文學作品,里面需要充滿“情調”,讀者只要受到這種情調的感染,不管文字是否優美,就是一部好的作品。同為“創造社”成員的郭沫若,將《沉淪》的美學追求歸納為“主情主義”。的確,《沉淪》在發表之初受到無數青年人喜愛的原因之一,就是小說中這種萬物皆著“我”之情的書寫,這種內心情感的自然流露,往往能夠引發讀者的共鳴。總體而言,《沉淪》的抒情特征主要表現為如下三個方面。
其一,《沉淪》對身處異國他鄉、孤憤敏感的“零余者”形象的塑造,灌注了強烈的情感。小說中夾雜著大量的日記,日記體形式的介入,有利于作者在小說的第三人稱“他”和第一人稱“我”之間的轉換,更好地將主人公孤憤、憂郁、苦悶的心境赤裸裸地體現出來。小說雖然寫“他”的故事,但這個“他”經常給人一種錯覺,“他”分明就是“我”啊!郁達夫對這個既希冀以異域之光拯救古老的中國又缺乏行動的勇氣和力量的異域留學生形象的塑造,如此真實感人的原因,正是因為灌注了自己最真實真切的異域體驗與感受。
其二,郁達夫在《沉淪》中有不少篇幅的風景描寫,這些風景不是單純作為一種自然物象存在于小說中,而是一種“人格化”自然。郁達夫對自然風景細致、真實的描摹中,人物的情感汩汩而出,風景與人物的心情、心境完美地交織在一起,產生了一種“一切景語皆情語”的藝術效果。這也使郁達夫的異域書寫形成了意蘊豐富的敘述張力和魅力。
其三,與小說抒情性的特征相適應,《沉淪》的結構與敘事方式相對較為散漫。郁達夫似乎不太注重小說結構的經營,小說的情節經常隨情緒的變化而發展,或如枝蔓橫生,又如水隨山形,小說自有一種天然去雕飾的瀟灑氣度。他的異域書寫,有意或無意地契合了“五四”時期對新型小說文體的呼喚。
作為中國現代文學的先驅,郁達夫與魯迅、周作人以及“創造社”的同仁們一樣,在歷史巨變時期走出國門,期望尋求挽救國家、民族危亡的途徑。他身處異域,依然心系中國。以《沉淪》為代表的小說中的異域書寫,中國從來沒有缺席。他以熾熱的情感塑造出在異國他鄉飽受摧殘和欺辱卻求告無門,郁郁寡歡之際向祖國尋求寄托卻陷入更深迷茫的弱國子民形象。這些郁郁寡歡、形單影只的角色在歷史和文學的長廊中永存,成為站在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的一類知識分子的真實寫照。這一形象建構的意義在于,郁達夫通過此類人物形象不僅直面自己的精神困境,同時也對整個“五四”時期知識分子的精神世界做了探索。經由《沉淪》,我們深刻意識到個體命運與祖國命運緊密相連,因此,也就不難理解,郁達夫何以會在40年代再次遠赴異國他鄉,積極從事抗日救亡工作直至獻出生命。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責任感與西方文化影響下形成的個性解放精神,不僅表現于他的文學創作中,也貫穿于他生命的始終。
(作者系西北民族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學部教授、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