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鄒韜奮觀察比較的美蘇兩國
王茹花 張寶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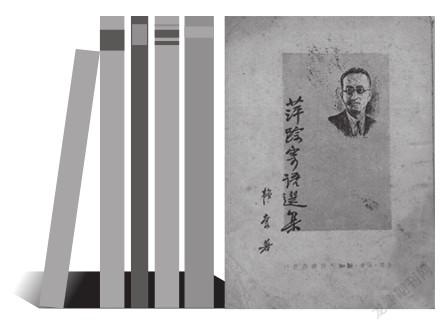
隨著20世紀30年代經濟危機爆發,曾經備受追捧的資本主義制度設計大幅失去了吸引力。與此同時,經過十月革命洗禮的蘇聯,在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之后,取得了顯著的經濟和政治成就,從世界各國中脫穎而出。當時的中國處于內憂外患的夾縫之中,民族的前途和出路問題成了中國知識界的關注焦點。鄒韜奮就是在這樣的時代語境中踏上了赴外之旅。他因公開批判國民黨的黑暗統治而被列入逮捕名單,便于1933年7月前往歐洲。以新聞記者的身份走訪英、法、德等國之后,他于1934年11月到達蘇聯,而后于1935年5月再到美國,8月離開美國回到中國。這期間,他將自己在歐洲和蘇聯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想皆以新聞報道的方式記錄下來,后經整理編成了《萍蹤寄語》,又于1937年憑借記憶完成了《萍蹤憶語》,記錄了他在美國的經歷和感受。鄒韜奮盡管在美國只逗留三個月,在蘇聯僅住了兩個月,但他憑著新聞記者的敏銳眼光,準確把握住了兩個國家的發展態勢。對比閱讀集中書寫蘇聯的《萍蹤寄語(三集)》和集中書寫美國的《萍蹤憶語》,我們不僅可以感受到鄒韜奮對美蘇兩個大國及其不同社會制度的態度,而且可以明了他作為先進知識分子表達中國現實關懷意識的曲折路徑。
鄒韜奮視察美國期間,見識了世界上最富有的都市——紐約,查訪了統治全美經濟生活的金融大本營——華爾街,體驗了當時最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物質文明,也了解了貌似民主和平等的社會制度。但是,他深入探尋之后發現,這個看似光鮮亮麗的“金圓帝國”只是虛有其表而已。它標榜民主和平等,但種族歧視盛行。除了種族壓迫,階級剝削也愈演愈烈。美國的階級分化,正如鄒韜奮所描述的那般窘迫:
所可比較的是這些闊人家的享用和在貧民窟所瞥見的凄苦狀況,一是天堂,一是地獄。這兩方面的人,一方面是靠著剝削他人血汗所獲得的利潤;一方面是靠著出賣勞力來勉強過活。
鄒韜奮筆下的美國社會,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那就是“少數富人的天堂和多數窮人的地獄”。繁榮是那些中飽私囊的資產階級眼中的繁榮,而要了解真實的美國,卻得深入社會最底層,了解底層人民的生活狀態。我們閱讀鄒韜奮的文字,可以充分感受到最底層人民受盡剝削和壓榨之后的窮苦和悲慘,了解這個“金圓帝國”繁華背后的狼狽和落魄。用杜甫的詩句“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來概括美國的社會慘狀,恐怕最為合適不過。鄒韜奮在《萍蹤寄語(三集)》的“弁言”中就一針見血地指出,資本主義社會已經陷入了“生產力的進步和生產工具私有的社會制度不相容”的尷尬境地。
蘇聯之行卻帶給鄒韜奮另一番體會。他初登“西比爾”號前往列寧格勒,發現船上雖有等級艙之分,但不限制各等級艙之間的來往,船上設備人人皆可利用,環境相對寬松許多。到蘇聯之后,他參觀了設備齊全的中央文化休養公園,為完善醫療設備而專設的夜間療養院,為解放家庭對婦女的束縛而設的托兒所和幼稚園,為工人及平民提供休閑娛樂的休養勝地克里米亞……作者所到之處,均可見證蘇聯漸趨完善的社會福利制度。除了社會福利,蘇聯的工會制度、農業生產、教育狀況等也讓鄒韜奮頗為心儀。他注意到,工人擁有自己的工會,生產資料屬于全體工人所有,工作時間合理;集體農場非常普遍,無論是貧民還是富農,都需參加集體生產;蘇聯重視培養青年一代,不僅因材施教,開發學生全面發展的潛能,而且著力實現教育大眾化和公平化。
在鄒韜奮看來,蘇聯盡管依然無法徹底根除沙俄時代滋生的社會弊端,但整個國家發展勢頭強勁,日新月異,處處充滿了生機勃勃的景象。勤勞的工人和農民,活潑積極的青少年,蒸蒸日上的工農業,處處洋溢自由和平等的氣息。這是一個人人平等、人人共享的國家,是一個正在積極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國家,是一個前途光明、呈現欣欣向榮景象的國家,是真正將民主、平等、自由等理念有效付諸行動的國家。
鄒韜奮筆下的美國,空有繁華的外表,雖為“金圓帝國”,但資產階級依舊極力剝削貧苦工人和農民,社會貧富差距巨大,社會矛盾尖銳;而蘇聯的經濟、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建設進展迅速,一改往日封建落后的面貌,正在成為世界上欣欣向榮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和美國都是當時在世界上擁有舉足輕重地位的大國,但是為何作者看待兩者的態度如此迥然不同,進而構建出近乎對立的異國形象呢?
九一八事變后,在嚴酷的階級斗爭和中國革命實踐的教育下,鄒韜奮接觸到了馬克思主義,政治覺悟迅速提高,開始從民主主義者到共產主義者轉變。他游歷歐洲期間,實地考察了一些漸趨沒落的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帶著對資本主義的這種消極心態,他來到了新興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蘇聯之行給作者留下了一段還算不錯的旅途記憶。抱著對社會主義的向往和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作者又來到了新興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闡釋學中有一術語,叫“前理解”。也就是說,由于受到某些主觀或者客觀因素的影響,人們在真正接觸到一些事物之前,就已經對其形成一種先入為主的印象。鄒韜奮未到達美國之前,就已經見證了老牌資本主義的沒落和新興社會主義國家的崛起,所以,在他的印象中,美國作為資本主義國家同樣難以避免衰落的命運,而社會主義的崛起已然成為一種不可阻擋的趨勢。
20世紀20年代末爆發的全球性經濟危機給美國等資本主義國家以沉重的打擊,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對于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制度開始持懷疑甚至否定的態度。20世紀30年代初,中國經濟因為受到大蕭條的牽連而日漸凋敝,再加上外有異族入侵,內亂不斷,人民的生活水深火熱,中華民族危在旦夕。像鄒韜奮這樣的先進知識分子不僅對國民政府感到失望,而且為國家命運和民族前途感到深深擔憂。他真切希望可以尋找到一條救國救民、富國強兵的道路,讓整個中華民族從壓迫和剝削中解放出來。蘇聯成功的革命實踐和社會主義建設成就猶如一盞黑暗中的明燈,重新點亮了他心中的希望。
鄒韜奮的文字浮面所寫的是他在美蘇的見聞,但是細讀文本我們可以發現,他在敘寫這兩個客體的同時,常常聯想國內諸事,并分別做一番饒有趣味的評說。比如,他在述及觀看《列寧的三歌》的感受時說,列寧的后繼者們“努力使社會主義一日千里,不負列寧的付托……我同時不禁聯想到有的國家里在革命領袖死后,便無惡不作,弄得喪權辱國、民不聊生,老實跑到反革命的路上去,卻靦然不以為恥的后繼者們”。諸如此類的議論,無不表明他作為先進知識分子的深切現實關懷意識。
在《萍蹤寄語》初集的“弁言”里,鄒韜奮曾提出過兩個問題:“第一個是世界的大勢怎樣?第二個是中華民族的出路怎樣?”美國和蘇聯就像兩面相對而立的鏡子,鄒韜奮立于兩者中間,分別通過兩面鏡子打量著,思忖著,抉擇著。可以說,看似是流亡歐美和蘇聯的旅行,其實于他而言,是一場身負嚴肅使命的解惑之旅。鄒韜奮在《憶語》的“弁言”里寫道:
世界上有三個泱泱大國:一個是美國,一個是蘇聯,一個是中國。……它們對現在和將來的世界大勢,都有著左右的力量!
也就是說,“世界大勢”影響著“中華民族的出路”的選擇,而“中華民族的出路”則在一定程度上引導著“世界的大勢”。歸根結底,“中華民族的出路”才是亟待解決的問題。
如果說在《萍蹤寄語(三集)》中,鄒韜奮親身感受了政權獨立、人民幸福的蘇聯后由人及己,時時感慨國內的悲慘現實,那在《萍蹤憶語》一書中,他已不再停留在思想批判的層面,而是流露出了更加明朗的態度。在從倫敦開往紐約的輪船上,鄒韜奮同一位“老印度”交談后發表感慨道:
我們看到歐美各國的一般人的生活,拿回來和中國人的生活比較比較,沒有不感覺到大多數中國人的生活簡直不是人的生活。……我們要鏟除剝削多數人而造成少數人享用的不平等制度,樹立功勞共享的平等制度。
在寫到美國青年時,作者更是集中表達了改變中國現實的迫切愿望:“這一群孩子們……對于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都有深切的興趣和懇摯的同情”,他們覺得中國“一旦翻過身來,給世界的前進動力,不知道要偉大到什么地步!”這種熱望讓他感覺既興奮又慚愧。興奮的是在這樣一個遍布剝削、壓迫和歧視的資本主義國家,還有一群進步青年和他一樣關注著中國的前途。然而,中國當局者卻軟弱無能,任祖國的國土被異族蹂躪踐踏。這讓他感到萬般慚愧,進一步堅定了他積極參與中國革命實踐的決心。
鄒韜奮認為,“法西斯的風行和備戰的狂熱”盡管是“歐洲最近的實際情勢”,但這只是日暮窮途的資本主義最后的掙扎。明確了“世界的大勢”,緊接著就是考慮“中華民族的出路”。中國是受帝國主義壓迫和剝削的民族,所以,最重要的就是開展爭取民族解放的斗爭,而要開展斗爭,就必須考慮中心力量和斗爭策略這兩個問題。對此,鄒韜奮也給出了自己的見解。依他看來,中國決不能依附于帝國主義,依靠他們的代理人和寄生蟲,而是要靠中國自己的勤勞大眾,因為只有“這樣的中心力量才有努力爭斗的決心和勇氣”。解決了中心力量的問題,接下來就是斗爭方略的問題了。他認為,民眾團結一心,奮起反抗,才是正途。這樣做,中國不僅能獲得自身民族的解放,還能造福于其他民族,就像蘇聯的革命實踐和社會主義建設為中國指出了一條充滿希望的道路一樣。
《萍蹤寄語(三集)》和《萍蹤憶語》雖屬報告文學,理應有很強的客觀性,但是,再強的客觀敘述也免不了摻雜作者的主觀情感。何況,鄒韜奮生活在動亂的20世紀30年代,不是一名普通的新聞記者,而是背負著特殊的時代使命。他業已形成的價值取向,自然而然會導致他對新聞材料做進一步的篩選和編輯。就此而言,兩部作品構建出的對比鮮明的美蘇形象,就成了鄒韜奮客觀敘述和主觀情感合力的產物。他寫作的用意非常明顯,只有弄清當時世界的大勢,才能思考中國在世界如何自處的問題。因此,觀察異國、書寫異國,也成了鄒韜奮思考中國問題、表達現實關切的重要策略。正是通過這樣的策略性書寫,他彰顯了作為現代進步知識分子的責任感和使命感。
(作者簡介:王茹花,西北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講師;張寶林,西北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