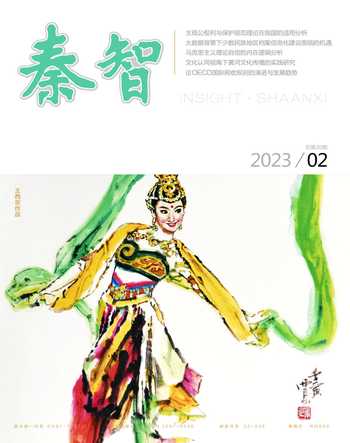檢察公益訴訟下未成年人保護(hù)的調(diào)查研究
[摘要]近年來,涉及未成年人的法律問題時(shí)有爭論,如未成年人刑事責(zé)任年齡問題、未成年人文身問題、未成年人受侵害問題等,涉及到未成年人犯罪和未成年人保護(hù)。實(shí)際上,后者對前者的預(yù)防極為重要,而未成年人檢察公益訴訟制度對未成年人保護(hù)又有了強(qiáng)有力的推動和兜底作用。未成年人檢察公益訴訟存在線索收集途徑有限、檢察監(jiān)督效力不足及起訴難等問題,本文主要對上述存在的問題進(jìn)行分析并提出相應(yīng)的建議。
[關(guān)鍵詞]檢察機(jī)關(guān);未成人保護(hù);檢察公益訴訟
一、未成年人檢察公益訴訟概述
202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hù)法》規(guī)定,在對未成年人合法權(quán)益的保護(hù)中,檢察機(jī)關(guān)有兩個(gè)特殊的權(quán)利。一是對涉及未成年人的訴訟活動進(jìn)行監(jiān)督,二是對涉及未成年人合法權(quán)益的案件,檢察機(jī)關(guān)也有權(quán)提起訴訟。但在這之前甚至目前,以下兩個(gè)問題處于爭議之中:公共利益和未成年人合法權(quán)益是否屬于包容關(guān)系?檢察機(jī)關(guān)又何以扮演未成年人合法權(quán)益“保護(hù)傘”的角色?
(一)公益訴訟與未成年人合法權(quán)益的保護(hù)
公益訴訟即相關(guān)主體針對損害公共利益的行為提起民事或行政訴訟。公共利益起源于古希臘,它是與個(gè)人利益相對的,是全體社會成員的總目標(biāo),其對秩序的構(gòu)建和維護(hù)具有重要意義,有助于推動依法治國,實(shí)現(xiàn)和諧社會的目標(biāo)。[1]
而未成年人的合法權(quán)益是否屬于公共利益?有學(xué)者將未成年人與國家聯(lián)系起來。如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長關(guān)乎國家和民族的未來和希望,國家是未成年人的“監(jiān)護(hù)人”,保護(hù)未成年人是國家的“義務(wù)”,“孩子”的利益就是“母親”的利益。[2]筆者贊同上述觀點(diǎn),但在本文意通過未成年人犯罪的特征,來論證未成年人合法權(quán)益屬于公共利益。
相比于成年人犯罪,未成年人的認(rèn)識能力處于成長狀態(tài),外在的不良環(huán)境對其影響遠(yuǎn)大于成年人,改善外在環(huán)境能夠使未成年人群體獲得良好的成長環(huán)境,有利于從小形成向上的價(jià)值觀,避免走上違法犯罪的道路。筆者通過對未成年人犯的自身、家庭、社會、學(xué)校等多方調(diào)查發(fā)現(xiàn),未成年人犯有著以下一種或多種特征:紋身、出入法律禁止未成年人進(jìn)入的場所、存在抽煙、喝酒的不良行為;監(jiān)護(hù)缺位或者不到位;學(xué)校對未成年人的教育不到位等。上述未成年犯的共同特征中,涉及家庭監(jiān)護(hù)、學(xué)校教育、市場監(jiān)管。如果削弱上述特征的負(fù)面,加強(qiáng)特征的積極面,如嚴(yán)格監(jiān)管酒店、酒吧等經(jīng)營場所,接觸不良行為的渠道減少,改善未成年人成長、生活環(huán)境,避免形成負(fù)面價(jià)值觀,減少他們的犯罪行為,這不僅有利于未成年人的成長,還有利于促進(jìn)家庭的和諧、社會秩序的穩(wěn)定,從而維護(hù)公共利益,而未成年人檢察公益訴訟恰恰是在上述家庭、學(xué)校、社會等領(lǐng)域進(jìn)行保護(hù)的。
(二)檢察機(jī)關(guān)與未成年人公益訴訟
對于檢察機(jī)關(guān)何以作為提起公益訴訟的主體?筆者認(rèn)為有以下原因:第一,憲法賦予了檢察機(jī)關(guān)的監(jiān)督職能,檢察機(jī)關(guān)對涉及未成年人保護(hù)的訴訟活動有監(jiān)督的權(quán)利。而且,對保護(hù)未成年人合法權(quán)益負(fù)有義務(wù)、職責(zé)的主體行為需要被監(jiān)督或者承擔(dān)不履行帶來的后果來約束和推動。故檢察機(jī)關(guān)有監(jiān)督權(quán)且監(jiān)督不可或缺。第二,檢察機(jī)關(guān)對涉及未成年人合法權(quán)益的案件有權(quán)提起公益訴訟。雖然根據(jù)傳統(tǒng)的訴訟原理,檢察機(jī)關(guān)沒有實(shí)體權(quán)利不能有訴訟程序上的權(quán)利。但隨著訴訟信托的發(fā)展,到現(xiàn)在的訴訟二元論,即使沒有實(shí)體權(quán)利的當(dāng)事人也可以行使程序上的權(quán)利。并且,根據(jù)國家監(jiān)護(hù)理論,國家是未成年人的最終監(jiān)護(hù)人,檢察機(jī)關(guān)作為是國家的訴訟代表,也有權(quán)對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權(quán)益行為提起訴訟[3]。
二、未成年人檢察公益訴訟運(yùn)行現(xiàn)狀的調(diào)查結(jié)果
本文旨在為未成年人檢察公益訴訟的發(fā)展盡綿薄之力,故主要通過對其出現(xiàn)的問題提出建議。在調(diào)查過程中,其出現(xiàn)的問題主要為以下:第一,訴前問題:“侵害合法權(quán)益”的界定不明確、案件線索難以發(fā)現(xiàn)、訴前程序有時(shí)會限制了檢察機(jī)關(guān)保護(hù)的及時(shí)性;第二,訴中及訴后問題:監(jiān)督效力不足以及訴訟與損害賠償?shù)你暯印?/p>
三、未成年人檢察公益訴訟的五個(gè)問題的思考及完善
(一)對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權(quán)益”的界定問題
何為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權(quán)益”,決定著未成年人檢察公益訴訟的受案范圍。學(xué)界對此主要持兩種觀點(diǎn),即實(shí)害性與危險(xiǎn)性,即是否有實(shí)際侵害結(jié)果與是否可能會出現(xiàn)侵害結(jié)果。筆者認(rèn)為應(yīng)當(dāng)采用危險(xiǎn)性這一觀點(diǎn),因?yàn)槲闯赡耆藢ξkU(xiǎn)源的認(rèn)識能力有天然缺陷,甚至對于危險(xiǎn)充滿著好奇心,需要他人提前“鏟除”危險(xiǎn),方不至于落入“虎口”。所以,對于涉及社會、學(xué)校、家庭、網(wǎng)絡(luò)等領(lǐng)域內(nèi)的潛在侵害,應(yīng)當(dāng)在未成年人檢察公益訴訟的受案范圍內(nèi)。如教科書內(nèi)容是否符合優(yōu)秀價(jià)值觀;另外學(xué)校監(jiān)控設(shè)備安裝情況也應(yīng)包括在內(nèi)。學(xué)校內(nèi)的侵權(quán)時(shí)有發(fā)生,監(jiān)控便于未成年人受侵害證據(jù)的取得,并且會降低潛在的不法主體實(shí)施侵權(quán)的可能,是與保護(hù)未成年人合法權(quán)益有直接或間接關(guān)聯(lián)的。
(二)未成年人檢察公益訴訟中的案件線索發(fā)現(xiàn)問題
首先,要普及未成年人檢察公益訴訟相關(guān)的法律知識,如在學(xué)校教育學(xué)生有關(guān)保護(hù)自己合法權(quán)益的法律知識。知法才能促進(jìn)守法,未成年人檢察公益訴訟的概念于2020年出臺的未保法中以法律的形式正式提出,現(xiàn)屬于起步階段,有些法律人都對此概念都有所陌生,更何況作為線索提供方的公民。其次,案件線索的取得方式應(yīng)當(dāng)線上線下相結(jié)合。線上開通線索收集渠道,如官方網(wǎng)站、微博等;線下線索收集場所要具有固定性、便民性,保證不隨意變更場所、接近居民區(qū)。其中,學(xué)校是收集線索的最佳場所。在調(diào)查過程中,了解到一起家庭內(nèi)部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權(quán)益的案件,小林從幼兒園時(shí)起即遭受父親的性侵害,但小林一直不敢報(bào)警,直到案發(fā),小林的初中老師在某次談話中得知小林受到其父侵害,在對小林做心理建設(shè)后,鼓勵(lì)并陪著小林去報(bào)警。由于家庭侵權(quán)的透明性弱、家丑不可外揚(yáng)的傳統(tǒng)倫理性強(qiáng),加之未成年人生活能力尚弱,離不開家庭,導(dǎo)致家庭侵權(quán)具有隱蔽性。上述案件如果沒有這位老師,檢察機(jī)關(guān)是很難發(fā)現(xiàn)小林父親的侵害行為。學(xué)校不僅是未成年人的聚集地,還具有位置上距家庭遠(yuǎn),家校共育中可知曉未成年人家庭情況的優(yōu)勢,因此學(xué)校是檢察機(jī)關(guān)發(fā)現(xiàn)線索的最好地方,故可以在學(xué)校設(shè)立未成年人合法權(quán)益保護(hù)員,面向在校未成年人收集線索并向檢察機(jī)關(guān)提供,增多案件線索收集的數(shù)量。
(三)有關(guān)未成年人檢察公益訴訟的前置程序問題
在未成年人合法權(quán)益受到或可能受到侵害時(shí),只有在公民或民政等相關(guān)部門缺席的情況下,檢察機(jī)關(guān)才作為遞補(bǔ)原告向法院提起公益訴訟。這一前置程序設(shè)置旨在檢察監(jiān)督職能優(yōu)先,通過督促、支持起訴,或者發(fā)出檢察建議,充分發(fā)揮各方主體的能動性。但是前置程序是否必須存在?筆者認(rèn)為,在同一主體再次被類似侵害或者以相似的作為或者不作為去侵害他人的案件中,不需要上述前置程序。因?yàn)槭状伟l(fā)生侵權(quán)行為或者遭受侵權(quán)時(shí),檢察機(jī)關(guān)已經(jīng)對負(fù)有職責(zé)、義務(wù)的主體發(fā)出了檢察建議或者督促起訴等,故侵權(quán)再次發(fā)生,表明前置主體的能動性較弱。根據(jù)“一事不再理”,基于同一主體且相似的案件,經(jīng)檢察機(jī)關(guān)監(jiān)督仍不作為或者繼續(xù)侵權(quán)的,檢察機(jī)關(guān)可以直接起訴,不受上述前置程序的限制。
(四)未成年人檢察公益訴訟的損害賠償問題
當(dāng)未成年人合法權(quán)益受到侵害時(shí),檢察機(jī)關(guān)向法院提起行政或民事公益訴訟。被告是行政機(jī)關(guān)或民事侵權(quán)人,檢察機(jī)關(guān)的訴訟請求常為要求行政機(jī)關(guān)積極作為或要求更換監(jiān)護(hù)人、民事侵權(quán)人停止侵害等,這樣未成年人的將來的合法權(quán)益會受到保護(hù),但未成年人因侵權(quán)行為造成的損失如何賠償?這個(gè)問題,筆者認(rèn)為有兩種方式解決,第一種就是由檢察機(jī)關(guān)在訴訟請求中加入損害賠償內(nèi)容;第二種則是判決書擴(kuò)張[4],未成年人檢察公益訴訟的判決書可以作為后續(xù)未成年人提起相關(guān)聯(lián)訴訟的證據(jù)。如果第一種情況沒發(fā)生,未成年方只能通過個(gè)人提起訴訟來實(shí)現(xiàn)。如當(dāng)某道路多發(fā)交通事故時(shí),檢察公益訴訟制度僅請求法院判決相關(guān)部門履行好職能,對于未成年人的損害賠償多是自行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法院判決相關(guān)部門承擔(dān)賠償責(zé)任。但是這時(shí)不僅交通部門及原告要舉證并且質(zhì)證,而且法院還要查清道路交通部門的職責(zé)以及過錯(cuò)責(zé)任,增加了法院負(fù)擔(dān)。故采用第二種方式,即判決的既判力擴(kuò)張,法院就可依該未成年人檢察公益訴訟的判決內(nèi)容來認(rèn)定交通部門是否存在過錯(cuò),不需再次由原被告雙方舉證、質(zhì)證。
(五)關(guān)于“訴中、訴后監(jiān)督”問題
在未成年人檢察公益訴訟中,存在監(jiān)督效果不足的問題,如何增強(qiáng)監(jiān)督,筆者有以下二點(diǎn)建議。第一,通過前置起訴主體提起未成年人檢察公益訴訟時(shí)的報(bào)告制度來增強(qiáng)檢察機(jī)關(guān)的訴中監(jiān)督效果。訴中監(jiān)督是為了防止前置起訴主體規(guī)避檢察建議等,隨意訴訟。在巴西一些公益訴訟案件中,如果其他主體提起訴訟時(shí)沒有通知檢察院,那么其進(jìn)行的程序是完全無效的[5]。這項(xiàng)報(bào)告制度可以不僅解決了以下問題,即其他主體既不想積極履行又不想被檢察機(jī)關(guān)督促、建議,因而直接自己主動起訴,把起訴主動權(quán)握于自己手中,通過訴訟請求的削弱以及證據(jù)的不足等來懶作為、濫訴訟。另外,在檢察機(jī)關(guān)收到報(bào)告后,還可使檢察機(jī)關(guān)及時(shí)地支持、參與訴訟,即使整個(gè)訴訟過程得到監(jiān)督,又起助力作用,如協(xié)助調(diào)查證據(jù)、合理建議訴訟請求等。第二,訴后監(jiān)督是檢察機(jī)關(guān)發(fā)出檢察建議或者提起訴訟后的監(jiān)督。實(shí)踐中,檢察機(jī)關(guān)向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權(quán)益的主體發(fā)出檢察建議、提起訴訟后,難以對涉案主體做到實(shí)時(shí)監(jiān)督,如有些酒吧等案件結(jié)束幾天后,會再允許未成年人進(jìn)入,甚至招聘未成年人售酒、坐臺,而檢察機(jī)關(guān)受到時(shí)間、人力、物力限制,檢察建議或訴訟效果會隨時(shí)間呈下降趨勢。這時(shí)應(yīng)對被監(jiān)督主體施加外部壓力,如檢察機(jī)關(guān)對案件回訪制度,即對未成年人檢察公益訴訟的案件進(jìn)行登記,由檢察機(jī)關(guān)相關(guān)部門不定期回訪調(diào)查被監(jiān)督主體的履行情況。回訪方式可以分為自行和委托回訪。自行回訪指檢察機(jī)關(guān)直接對涉案的行政機(jī)關(guān)不定期調(diào)查回訪,制作回訪報(bào)告;委托回訪指委托被告所在地的村居委、社會工作人員、負(fù)責(zé)監(jiān)管的行政機(jī)關(guān)通過電話、實(shí)地走訪對與涉案主體有關(guān)的人員進(jìn)行回訪調(diào)查并形成報(bào)告,回訪結(jié)果需向檢察機(jī)關(guān)報(bào)告。檢察機(jī)關(guān)根據(jù)上述回訪報(bào)告做出以下決定:被監(jiān)督主體不再實(shí)施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權(quán)益的行為,做出結(jié)案決定;被監(jiān)督主體再次實(shí)施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權(quán)益的行為,做出直接起訴或者發(fā)出檢察建議、督促起訴等決定。另外,檢察機(jī)關(guān)在辦理案件時(shí),在向案件當(dāng)事人普及相關(guān)法律知識的同時(shí),可告知他們便利的線索收集機(jī)構(gòu)及案件回訪部門的聯(lián)系方式,對他們進(jìn)行回訪或者接受他們的舉報(bào)線索,保障涉案未成年人的后期合法權(quán)益。
四、結(jié)語
本文中,由于筆者發(fā)現(xiàn)、分析及解決問題的能力不足,提出的問題及建議會存在錯(cuò)誤,但希冀為未成年人檢察公益訴訟盡綿薄之力。同時(shí),在通過調(diào)查過程中發(fā)現(xiàn),未成年人檢察公益訴訟起步初期已取得顯著成效,這既顯示出該制度的適用性,有效性,又彰顯了政府、家庭、學(xué)校、網(wǎng)絡(luò)等力量的凝聚和強(qiáng)有力的支持。相信在多方力量的支持下,該制度的發(fā)展趨勢將持續(xù)穩(wěn)中向好,更好地保護(hù)未成年人的合法權(quán)益。
參考文獻(xiàn):
[1]胡鴻高.論公共利益的法律界定——從要素解釋的路徑[J].中國法學(xué),2008(04):56-67.
[2]姚建龍.國家親權(quán)理論與少年司法——以美國少年司法為中心的研究[J].法學(xué)雜志,2008(03):92-95.
[3]謝偉.德國環(huán)境團(tuán)體訴訟制度的發(fā)展及其啟示[J].法學(xué)評論,2013,31(02):110-115.
[4]王玉輝.論日本消費(fèi)者團(tuán)體訴訟的限定性適用[J].河南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版),2012,39(05):121-125.
[5]劉學(xué)在.巴西檢察機(jī)關(guān)提起民事公益訴訟制度初探[J].人民檢察,2010(21):69-73.
基金項(xiàng)目:青海民族大學(xué)創(chuàng)新項(xiàng)目,項(xiàng)目名稱:檢察公益訴訟下未成年人保護(hù)的調(diào)查研究(項(xiàng)目編號04M2022047)
作者簡介:李淑萍(1997.10-),女,漢族,山東臨沂人,碩士研究生在讀,研究方向:刑事訴訟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