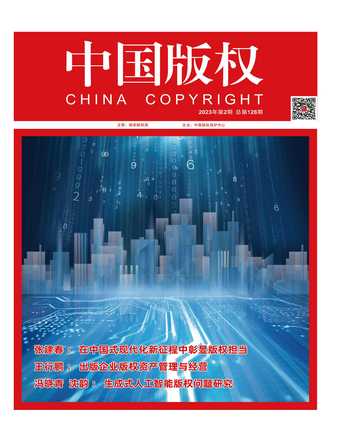晚清時期版權保護制度的探索與施行
王學深
關鍵詞:晚清;版權;報刊;著作權
自明代中后期以來,隨著經濟和技術的發展,我國刻書業取得了長足的進步,推進了文化知識的傳播和書籍市場的繁榮。不過,明清時期的中國作為書籍刊印大國,圖書向來可以翻印,士人階層也缺乏書籍版權意識。然而近代受“西學東漸”的影響,自19世紀晚期開始,關于圖書版權的思想逐漸傳播,并在“新政”施行以后形成了近代版權保護制度,對圖書、譯著版權加以保護,禁止他人翻刻。以林樂知為例,他是晚清時期較早呼吁并申請版權保護的西方傳教士。林樂知所著的《中東戰紀本末》一書在晚清多次再版.為此他特意致函美國駐上海領事向蘇松太道提出抗議,要求禁止翻印此書并予以版權保護,此事被朱維錚視為“近代中國有記錄的第一樁涉外版權官司”。
與之同時,林樂知在晚清呼吁和宣傳版權思想。如在論述何謂版權問題時,林樂知言及“西方各國有著一新書創一新法者,皆可得文憑以為專利而著新書所得者名日版權”。他介紹了美、英、德、法、奧、瑞、俄、挪、比、秘、愛等國版權施行期限,進而與當時國內的情況做以對比,其言“今中國不愿入版權之同盟,殊不知版權者,所以報著書之苦心,亦與產業無異也。凡已滿期之書盡可翻印,若昨日發行,今日即已為人所抄襲,是盜也。且彼處著書之人,又何以獎勵之,而俾有進步乎!”正是在這種大背景下,自19世紀末開始,近代報刊陸續刊登和宣傳版權問題,并逐漸形成了近代版權保護制度,最終在1910年頒行了《大清著作權律》為保護版權的正式律法。
一、近代報刊中關于版權思想的傳播
19世紀末,日本對近代中國版權觀念和制度的形成影響較大,也為后來版權施行于中國提供了借鑒。曾出使日本的黃遵憲就在其所著的《日本國志》中介紹了版權制度,其文日“凡欲以著作及翻譯之圖書刻板者,先以草稿繕呈本局(圖書局)。本局察其有益于世給予執照,名曰版權,許于三十年間自專其利,他人不得翻刻盜賣”。此后,在近代報刊中也多有涉及介紹日本版權制度和論述版權應施行于中國的文章。如在《東洋經濟新報》發表的《論布版權制度于中國》一文就認為,版權是保護知識的基礎,提出了“保護著述者之權利,以酬其著輯之勞,為最要矣”的觀點,進而在樹立起版權觀念后,則版權將成為“供給智識之原動力”。正是在版權制度的保護下,清政府才可以引進和翻譯更多西學著作,從而對推動維新變革有所助益。作為對這篇文章的回應,在1899年第13期的《清議報》上刊載了《讀經濟新報布版權于中國論》一篇,對版權制度施行于中國給出了肯定性的結論。該文作者認為,版權制度于中國自古所無,是由英美傳教士最先將其思想傳布于中國。在這期間,廣學會的譯書工作為版權意識的傳播起到了開風氣之先的作用,其言“英米之宣教師,有為我譯書者,其名曰廣學會,實為行版權之嚆矢。今者同學會譯著出版之書,坊賈無敢翻印者,此亦可以見其制度之實可行矣”。進而,作者在文章中具體提出了版權制度應率先嚴格施行于京師和通商口岸的想法,使著者和譯者權益得以保護,有利于著書和翻譯事業的蓬勃發展,推動先進思想的引進和傳播,其言“吾竊以為此版權制度,但于京師及通商各口岸嚴行之,而于內地則稍寬之,亦未始不可也。蓋推原譯書之意,于其一方,當保護著者之權利,使之功勞相償,以動其業”。
此后,在1901年第14期的《南洋七日報》中轉發了《蘇報》刊登的《版權宜歸重公會說》一文,進一步宣傳版權保護思想。在該文開篇,作者就肯定了版權制度對“文明開化”的積極作用,其文載“吾聞泰西各國,啟維新之秘錀,植開化之始基,印文明之跡于腦筋,除錮閉之萌于臟腑,而版權之例,與有功焉”。作者認為版權制度是國民所賴以自立,國家所恃自強的重要憑借,并專門向國人介紹了英國近代版權制度的完善過程。在談及當時中國的版權狀況時,作者不僅做了對比,而且認為無版權保護制度施行,將對正確知識的傳播大有阻礙。
實際上,晚清社會上書籍翻印之事甚為普遍,而各新式學堂所用課本成了重災區。據《大公報》的報道,蘇州城內有書籍刊刻的坊賈,“專以翻刻書籍侵占版權為事,如南洋公學之《蒙學課本》初二三編、格致讀本,以及其余風行之書無不翻刻,減價蒙混出售”。這種情況不僅會造成新知識的引入與傳播日漸困難,而且對所傳播內容的準確性也造成影響。故而,在《版權宜歸重公會說》中,作者就對當時的濫行翻印的情況評價到“我中國于版權之例,向未明定章程,志士或著一新書,譯一新籍,甫經出版,翻者踵起,甚至改頭換面,錯訛百出,徒求有利于己,罔顧有害于人,其貽誤學者正匪淺鮮也”。有鑒于此,作者提出了施行版權制度,改革當時弊狀的辦法,其一國家制定專門章程,其二創設版權公會。特別是針對第二點,作者認為由版權公會厘定的版本更加準確,可薈萃著作之才,可改換錯諸弊端,最終對新政推行有所幫助,成為“開化之始基”。
隨著版權意識的傳播和探索的逐漸深入,當時既有對在中國施行版權制度持否定態度者,又有對版權制度持積極擁護者,前者以張百熙為代表,后者以廉泉為典型。
二、管學大臣張百熙對版權保護制度的疑慮
正是在19世紀末報刊逐漸宣傳確立版權保護制度的大背景下,國人對版權問題日漸重視,特別是在“新政”推行后,不僅士人階層對版權問題展開討論,而且官方也日漸重視版權問題。不過,在清政府內部有不少官員表達了對設立版權的憂慮和反對意見。1902年,當時清政府和美國正在商定《通商行船續訂條約》,而在條約文內雙方即有約定版權的內容一條。其大意為美國有版權保護定例,“嗣后美人如在中國鐫印書籍、圖畫或譯印華文,自系專為華人所用,應由中國極力保護,并自注冊日起限期十年,準在中國得享專利,不準他人翻印”。然而,此事為日本所知,故而照會清政府也要求在中日新訂條約中議定版權保護制度事宜。為此,時任管學大臣的張百熙特致書日本使臣內田康哉,表達了中國不宜施行版權制度的看法。
在電文中,張百熙指出當時中國能通外國學問者人數較少,而每翻譯一部著作則需要花費重金,即“如英國出一書值十元,敝國用上等譯員譯之費數千元,再加刷印千部又數千元,是譯出變賣已不如英國原售價值之賤矣”。正因如此,他認為當時翻譯之事為官方所操持,“故翻譯外書以圖利,為敝國賣書人必不能辦之事”,故而張百熙認為在當時的條件下,中國尚不足以設立版權制度,不僅無益,反而有害,其言“若如此辦法,書籍一不流通,則學問日見否塞,雖立版權久之,而外國書無人過問,彼此受害甚多”。特別是張百熙認為,于條約內加入版權一事,無疑對尚處于萌芽狀態的新式學堂不僅沒有幫助,而且有扼殺之慮,其言“今日中國學堂甫立,才有萌芽,無端一線生機又被遏絕,何異勸人培養而先絕資糧!”不過,張百熙在此電文中只談及了因引進和翻譯花費甚多,而不應施行版權制度的理由,而沒有論及譯成之書的翻印問題,故而在一定程度上有避重就輕之嫌。
與之同時,為了避免在訂約中涉及版權事宜,張百熙還曾特意致電前兩江總督劉坤一表達了其時不宜施行版權制度的看法,并期望劉坤一設法維持。然而,劉坤一在覆電張百熙文中雖然對張百熙所慮表示理解,但也闡明了“以中國語文著作書籍及地圖,應得一律保護。其東文原書及東文由中國自譯,或采取東文另行編輯者,不在版權之列”的觀點,但也轉告了張之洞意圖“將日本用中文編輯之書,亦準華人重加編訂”的想法。劉坤一同意將張百熙所慮轉達給正在商談條約的呂海寰和盛宣懷二人。與劉坤一所述類似,經過商定,呂、盛二人覆電張百熙告知當前商談的結果,即“東西書皆可聽我翻譯,惟彼人專為我中國特著之書,先已自譯及自印售者不得翻印,即我翻刻必究之意”,o清晰地闡明了條約內已無法避免版權條文的事實。
張百熙對版權制度的疑慮,隨著《大公報》《選報》《鷺江報》等近代報刊的轉錄,引起了當時官方和知識界廣泛的關注。對于版權保護事宜,在1902—1903年的報刊中多有反對的聲音,而尤以反對日本訂約中有關版權同盟一事為甚。在1902年春季的《浙江新政交儆報》中,有作者發表了《交涉芻言:版權平議》一文,其言“以維新三十余年多通西書之國,而近時論者尚嘆失策,何況吾國正如蒙稚之時,有不受其遏抑而關礙發達之機,使本國有志者譯書之事幾于熄耶?”甚至是日本國人也有反對版權同盟之論者。在《論版權同盟》一文中作者言及“我邦自一千五六百年以前,所有學問及文明德化均賴中國輸入,至近來三百年間,中國文明之來我國進步兀猛,德川將軍時代漢學各家于中國各種書籍,無不供其翻譯,受益實非淺鮮。明治維新近三四十年間,泰西文明輸入我國,始若不過略見一日之長,現當中國派人翻譯我邦書籍,即儼然自詡”,明確表達了反對以中日圖書交流行版權之事的看法。
甚至在施行保護版權規定之后,也有地方大員依舊對版權保護持否定意見者。據《大公報》 1904年3月1日報道,有督臣電文致函商部及大學堂申請撤銷版權,而其觀點是版權阻礙圖書銷路,為“奸商”把持,其言“中國編印書籍原為開通風氣,豈可給其版權以隘銷路。近來書賈屢有稟請者,跡近壟斷,有關開化,請貴部嗣后遇有此等事宜一概批駁,以杜奸商把持。”但是隨著條約商定進程的深入,雖然以張百熙為代表的清廷內部不乏官員發出了對施行版權制度的反對聲音,但是卻已呈無法扭轉之勢。在政府內部以廉泉、嚴復為代表的官員紛紛上疏管學大臣,要求給予刊行圖書版權保護,杜絕翻印,以期更好地推動新學教育和知識傳播。
三、戶部郎中廉泉對施行版權制度的支持
雖然在清政府內有如張百熙發出疑慮的聲音,但是也有像戶部郎中廉泉等堅定地支持版權制度設立與施行者。廉泉在1903年初接連上疏管學大臣張百熙,表達了對后者堅持暫緩施行版權態度的不認同。廉泉請求仿行日本版權制度,給各省府州縣學堂所用教科書授予版權,其言“今京師大學蓋與日本文部名異而實同,謂宜仿照日本規制,凡編譯教科書者胥吏呈送,京師大學堂詳鑒而審定之。……今日東西各國法律皆重版權,擬請嚴定規制,凡書經大學堂鑒定準與通行者,無論官私局所概不得翻印以重版權”。特別是廉泉本人和舉人俞復、副貢生丁寶書于1902年6月間在上海成立了文明書局,又在京師和天津成立分局,不僅編印小學教科書,而且對西學著作多有翻譯發行之舉。為此,廉泉對于版權制度的擁護既有官員對大趨勢下推行新法的支持,又夾雜著出版商人維護自身商業利益的考量。故而他請求“敢援日本文部檢定之制,東西各國版權之律,屆時恭呈鑒定遵飭印行,以利學堂而杜翻印前者”,而文明書局已經將編成的《蒙學讀本七編》等書上疏請求版權保護。
不僅如此,廉泉還上疏稟明北洋大臣袁世凱請求保護文明書局發行圖書的版權,禁止翻印,并獲得后者的支持。為推動版權事宜,袁世凱不僅將其圖書從上海運至北京的輪船招商局船運費概行全免,而且為文明書局版權事咨文各省督撫,言及“至該局編譯印行之書,無論官私局所概禁翻印以保版權,并候分咨各省督撫院,轉行遵照抄由批發”。正是因為有了袁世凱的支持和推動,廉泉所主持的文明書局在當時的報刊中刊發緊急告示,以強調保護發行圖書版權,杜絕翻印事宜。其文告日:
凡本局編譯印行之書已蒙北洋大臣咨行各省官私局所,概禁翻印以保版權在案,倘仍有人易名翻版或抽印匯刻等情,一經察出定當稟官懲辦,以其翻刻之書全數充公為該地方學堂之用,并請官科罰,為該地方學堂經費。如本局未及察知,有人得其翻刻實據,寄示本局并能述其印刷之所,能為扣留全書作見證者,本局查明稟官懲辦后,以其書銀之半充公,以其半酬告發之人,恐未周知,特此布聞。——上海北京天津文明書局廣告。
正是在版權勢在必行和力行新政大臣的支持下,在1903年以后推行版權保護逐漸形成共識,對所出版的圖書呈請版權保護成了一種新常態。如文明書局編成并發行的《蒙學讀本七編》《理財學綱要初》等書即已得到官方的保護,“業經呈蒙審定頒發圖章以重版權而杜冒印”;已經編成,即將出版納入學堂課本書目的,如《植物學教科書》《國民體育學》《實用教育學》《教育新論》《教育新史》等教材則“飭知各行省定為課本,一體通行在案”;而即將付梓的日本大學教科書《理財學》《西史通釋》也在加速印刷,呈請審定頒行。可以說,以文明書局作為當時的代表,其所刊印的教科書和宣介東西方近代化的著作得到了官方的版權保護。正因如此,廉泉在《上管學大臣論版權事》一疏中論述到,“嗣后凡文明書局所出各書,擬請由管學大臣明定版權,許以專利,并咨行天下大小學堂。各省官私局所概不得私行翻印,或截取割裂以滋遺誤而干例禁,則學術有所統歸,而人才日以奮迅矣。伏望迅斷施行,學界幸甚!天下幸甚!”
與廉泉觀點類似,嚴復也表達了對施行版權制度的支持,提出了“版權廢興,非細故也”的論斷。1903年5月繼廉泉之后,嚴復上疏管學大臣張百熙指出,今日雖然刊行的圖書人人得以刻售于普及教育有益,但從長久來看則實有所損于學界。嚴復認為著書立說,翻譯西學書籍都需要耗費人的巨大精力,“竭二三十年之思索探討而后成之”,若書成“乃奪其版權,徒為書賈之利,則辛苦之事誰復為之?”這實際上損害了剛剛起步的維新之法,以致最終的結果是“彼外省官商書坊,狃于目前之利,便爭翻刻以毀版權。版權則固毀矣,然恐不出旬月,必至無書之可翻也”。
中國政府今欲中國人民在美國境內得獲版權之利益,是以允許凡專備為中國人民所用之書籍、地圖、印件、鐫件者,或譯成華文之書籍,系經美國人民所著作或為美國人民之物業者,由中國政府援照所允保護商標之法及章程,極力保護十年,以注冊之日為始。俾其在中國境內有印售此等書籍、地圖、鐫件,或譯本之專利,除以上所指明各書籍地圖等件不準照樣翻印外,其余均不得享此版權之利益。又彼此言明不論美國人所著何項書籍、地圖,可聽華人任便自行翻譯華文刊印售賣。凡美國人民或中國人民為書籍報紙等件之主筆,或業主,或發售之人,如各該件有礙中國治安者,不得以此欺邀免,應各按律例懲辦。
在條約簽訂后不久,美國使臣還照會清政府外務部稱“此次新訂商約載有專條。嗣后中國國家將如何妥為保護,使著作者享有版權利益,不致被人侵害請,將保護條例詳細示覆”。稍后在中日《通商行船續約》中第五條款也有關于版權保護制度的約定。可以說,以管學大臣復函廉泉為起點,又以中美新訂條約正式加入保護版權一項為標志,中國近代版權保護制度開始施行,民間保護版權意識日漸普及。
五、清政府關于版權保護的立法
雖然隨著版權意識的普及和保護版權措施的推進,民間書局濫行翻印的情況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但是清朝對內尚未頒布明文律法以禁止和懲治侵犯版權的行為。隨著版權意識的逐漸深入,清政府不斷探索編訂保護版權的明文條例。1904年,清廷命商部負責試行編修了《版權律》草案,張元濟還曾參與到晚清《版權律》和《出版條例》修訂的工作中,并提出了不少修訂意見。他對編訂條例草稿中的第19、49兩條尤為關注。對第19條,張元濟認為授予版權之書應該予以保護,既不可翻印,也不可翻譯,其言“按有版權之書籍,非特不能翻印,抑且不能翻譯。中國科學未興,亟待于外國之輸入。現在學堂所用課本,其稍深者大抵譯自東西書籍”。但是,張元濟也提出在現擬草稿中,對研習洋文書籍給予版權的規定實乃自我增加阻力,以“實際之利權,易彼虛名之保護”,應予以改定。而對草稿第49條“翻印仿制”項,張元濟也提出了個人觀點,其言“中國幅員如此廣大,原著作者之耳目豈能一一周知。且倒填年月,為中國慣行之事。此端一開,必有無窮糾葛。鄙見如原著作者自行呈控,亦應照章科罰,編書局擬增入第二十四條之數語,極應補入”。
不過,由于商部試行編訂的《版權律》內容較為粗糙,并未呈請施行,但其內容大致以“書籍、圖畫、演述、雕刻以及屬于文藝學術之物皆得予以版權,著作人在世之年及沒后三十年享有之”為內容。而其主體原則也為后來頒行律法所繼承和借鑒。1908年,雖然民政部編成的《大清報律》第39條中規定“凡報中附刊之作,他日足以成書者,得享有版權之保護”,對于報刊文章的匯集成書版權有了明確的法律條文保護,但是原有的《版權律》依舊擱置,沒有新的進展。直到1910年經過再次籌備和修訂,民政部奏請擬定《著作權律》,承繼之前的《版權律》以為拓展和完善。最后,經資政院對著作權律議案決議并請旨允準后,《大清著作權律》于公元1910年12月18日正式頒布。
這部晚清的律法在很大程度上參照了日本對于版權保護的規定修纂而成,包括給予版權之范圍,版權之期限等均有相似之處,但無論如何,《大清著作權律》的頒布既是“新政”后從現行規定向立法的飛躍,又是從傳統圖書版權概念擴大到著作物權的轉變。在《大清著作權律》開篇就闡明了著作權范圍,文載“凡稱著作物而專有重制之利益者,日著作權。稱著作物者,文藝、圖畫、帖本、照片、雕刻、模型皆是”。《大清著作權律》依次對權利期限、呈報義務、權利限制做出了明確的規定,特別是在第33、34兩條中分別規定“凡既經呈報注冊給照之著作,他人不得翻印仿制,及用各種假冒方法,以侵損其著作權”“接受他人著作時,不得就原著加以割裂、改竄及變匿姓名或更換名目發行”。這些規定是承繼了自1903年以來實際施行的保護版權規定,并給予了相應的擴充與完善,只不過這一律法在頒行后僅一年,清王朝即走向終點。雖然《大清著作權律》施行時間很短,但它是自19世紀末以來國人探索近代版權制度的一項重要成果,也是中國官方版權制度正式確立的標志,而中國人對于近代版權觀念與制度的追尋腳步在繼續前行。
結語
晚清以來受“西風東漸”的影響,有識之士在追求近代化的過程中日益重視圖書版權保護問題。不僅有如黃遵憲、林樂知等晚清中外人士介紹版權制度于先,而且依托近代報刊為平臺,版權問題的討論、思想的傳播與制度的施行漸次展開。雖然如管學大臣張百熙和部分地方督撫對于在中國施行版權制度有所疑慮,認為版權保護會阻礙新學的推廣,故暫持否定態度,但是以廉泉、嚴復為代表的官員則呈積極支持之勢。隨著張百熙肯定性的復函廉泉施行版權制度所請,加之袁世凱的支持,以及呂海寰和盛宣懷在與美國訂約中對版權保護一項較為認可,故而自1903年以后清政府雖然沒有頒布《版權律》或正式律例以作規范,但事實性地開始施行版權保護制度。一方面傳播了版權思想,使得著作權人紛紛呈請版權保護,另一方面嚴查濫行翻印書籍事宜,使版權保護呈常規化態勢。經過了一段時間的擱置之后,自1908年清政府再次重啟對于版權律的編纂與修訂工作,并最終在1910年12月18日正式頒行了經過擴充和完善后的《大清著作權律》。雖然這一律法僅施行短短的一年時間,但是它卻是晚清以來有識之士孜孜以求,推動近代化改良的成果之一,更是中國近代版權制度正式確立的標志。
(作者單位:中國政法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