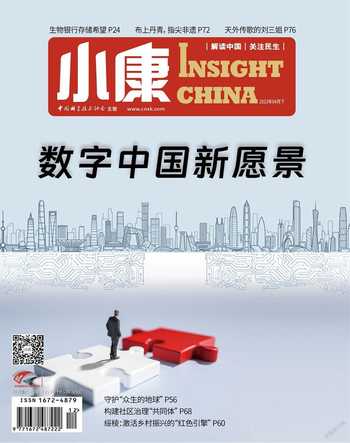搶占數字能源新賽道
袁凱

數字化浪潮席卷而來,傳統能源行業如何實現 “蛻變”?
新一輪科技革命與產業革命正加速興起。數字化技術與能源行業的高度融合,使得能源數字化成為未來發展的必然趨勢。當提起傳統能源產業,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很可能是工作環境煙塵繚繞,機器聲響徹礦區,工人們灰頭土臉,在一片灰霾中艱難工作。不過,隨著數字化浪潮席卷傳統能源行業,這樣的場景逐漸成為歷史。
2023年以來,我國加快推進能源領域數字化轉型。今年2月發布的《數字中國建設整體布局規劃》中明確提出,培育壯大數字經濟核心產業,研究制定推動數字產業高質量發展的措施,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數字產業集群。推動數字技術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在能源等重點領域,加快數字技術創新應用。
3月31日,國家能源局發布的《關于加快推進能源數字化智能化發展的若干意見》明確,到2030年,能源系統各環節數字化智能化創新應用體系初步構筑,數據要素潛能充分激活,一批制約能源數字化智能化發展的共性關鍵技術取得突破,能源系統智能感知與智能調控體系加快形成,能源數字化智能化新模式新業態持續涌現。
可以預見,未來能源數字化將實現跨越式發展,一張數字化智能化的能源藍圖將徐徐展開。
前景廣闊
發展數字能源,即利用數字技術,引導能量有序流動,構筑更高效、更清潔、更經濟、更安全的現代能源體系。
其實,數字技術在能源行業早有應用。權威數據顯示,早在2017年,數字技術在能源領域的市場規模已經達到520億美元,約占全球數字技術應用市場的44%。在這520億美元中,有46%即240億美元,來自化石能源電廠的運行管理,包括利用傳感器、數字采集和解析提高電廠效率。有35%即180億美元,來自建設智能電表。而隨著全球能源轉型進程的進一步加快,大數據、機器學習、人工智能、云計算、區塊鏈等技術將與能源行業產生更多關聯。
企查查數據顯示,2021年,我國新增數字能源、光伏、新能源、能源管理系統相關企業5.67萬家,同比增長154.93%,其中,新增企業名稱中含有“數字能源”的現存企業93家,是2020年的8.45倍。
當前各大公司也正加速進入數字能源產業。一方面,以華為、中興通訊、工業富聯等為代表的科技型企業紛紛通過設立獨立部門或子公司形式入局數字能源領域;另一方面,傳統能源企業也相繼組建數字化公司,加快能源數字化轉型。目前,國家電網、南方電網、中國石化、國家能源集團、中國能建、國家電投等一批能源央企已紛紛組建了專門的數字化公司。
科技的不斷進步,為數字能源發展提供源頭活水。全聯新能源商會專家委員會主席、中國科學院院士李燦認為:“要通過大力推進新能源先進技術、大規模新型儲能技術、綠色氫能技術、碳捕集利用與封存技術和先進核能技術攻關,為新能源發展提供關鍵技術支撐。”
在技術應用方面,智慧礦山、虛擬電廠、智能光伏、電化學儲能等數字科技已經讓傳統能源企業嘗到甜頭。國家電投內蒙古公司北露天煤礦所使用的純電驅礦用卡車是分散式風電示范項目中的一環。據北露天煤礦礦長劉敬玉介紹,風機每年將貢獻超過1166萬千瓦時清潔電能,配備靈活調節的電化學儲能系統,用于新能源礦卡充電,每年可節約標煤3562.74噸、單臺礦卡67000升柴油,減少二氧化碳排放9586.16噸。而這,只是整個數字煤礦的冰山一角。
窺一斑而知全豹。碳達峰、碳中和目標驅動下,智能化、低碳化成為未來兩大確定性發展趨勢,智能化需要數字化技術,低碳化更離不開電子電力技術,全球能源產業正從資源依賴型走向技術驅動型。如此,一個融合了數字技術和電子電力技術的產業——數字能源,前景廣闊。
短板明顯
國家能源集團建成了“智能礦山”“智能化工”等多個無人化、少人化的智能生產體系。南方電網公司的AI虛擬數字安監工程師,實現了對經營區域所有縣級區域氣象災害的全天候監測預警。中國石油化工集團推進智能油氣田、智能工廠與智能管網建設,研發出公司級智能化管線管理系統。
無可否認,數字能源在大力推進生產環節智能化提質增效方面效果顯著,但在業務與數字技術深度融合等方面還面臨著許多挑戰。
以煤礦為例,現在離真正的“智能礦山”還很遠。“礦山無人化作業是一項系統工程,也是礦山智能化的發展目標。” 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礦業大學(北京)校長葛世榮這樣說。在煤礦智能化建設中,礦山的安全化、無人化作業被視為5G等新興技術最適合切入的環節,但礦業環境對設備及操作要求嚴苛。對此,葛世榮認為,礦山智能化應借助5G、工業互聯網、人工智能、大數據、數字孿生等新一代ICT(信息通信技術),更好地實現數據泛在高速接入、裝備實時控制、圖像視頻智能分析、災害監測預警、機電裝備故障診斷等功能,最終構建礦山產運銷儲用全流程透明化系統。但葛世榮也坦言,目前智能化開采還存在感知能力不夠強、裝備可靠性不夠高、終端計算速度不夠快、信息互通性不夠強、人機交互性不夠好等諸多問題。
特雷西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崔文彬則認為,數字能源目前短板明顯。以數字油田為例,各油田投身于自建系統,形成了體量巨大的系統數據,但依舊存在數字基礎設施部署不足、感知設備數量有限、數據資產目錄尚未建立等問題。
更需要注意的則是技術壁壘與“卡脖子”風險。崔文彬表示:“油藏數字孿生作為一門綜合性交叉學科,是數學、物理、計算機、軟件等多學科的融合,需要多年實踐經驗積累,無法在短期內掌握,從而使該行業形成較高的技術壁壘。”此外,目前我國70%以上的高端裝備和95%以上的核心技術仍依賴進口,在數字孿生賦能數字油田發展的新階段,繼續依賴國外技術將會面臨“卡脖子”風險。
電化學儲能東風將至
在能源需求與環境問題的雙重壓力下,電化學儲能技術逐漸處在了數字能源的風口浪尖。顧名思義,電化學儲能是將電能轉化為化學能并儲存起來,然后在需要時再將化學能轉化為電能釋放出來,從而實現能源的高效利用和可持續發展。
當前,是我國實現碳達峰目標的關鍵期和窗口期,也是新型儲能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國內儲能產業呈現蓬勃發展的態勢。
華為數字能源首席科學家劉云峰認為,隨著新能源裝機和發電電量在電力系統中的比例不斷提升,新能源場站必須通過和不同形式的儲能技術相結合,共同維持未來新型電力系統的穩定運行。未來新能源的大發展,需要有合理的市場機制來牽引商業模式,推進配套新能源發電儲能產業的發展,從而提升新能源在電力系統中占比的理論上限。需要促進電化學儲能在內的儲能技術進一步發展,從而提升新能源產業在未來新型電力系統電源中的比例。以國家電網青海共和華潤電站項目為例,其電化學儲能系統既具備暫態支撐電網的能力,又具備分鐘至小時級的調峰調頻能力。
2022年是全球儲能市場爆發的元年,新型儲能是近兩年的熱門詞。面對百花齊放的儲能技術,海辰儲能聯合創始人、總經理王鵬程認為,技術沒有絕對的好壞,它們都有各自的長短板,但電化學儲能是產業化最成熟、技術最成熟、安全最可控且降本邏輯最清晰的一個賽道。他預計,未來8到10年,電化學儲能一定是新型儲能最成熟的商業模式。
在王鵬程看來,真正理想的新能源要從能源供應是否充足、成本是否夠低和產業化路徑是否成熟三方面來看。在未來的能源結構里,光能和風能會是最成熟的模式,它們與電化學儲能的結合在5年內有機會做到比火電成本更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