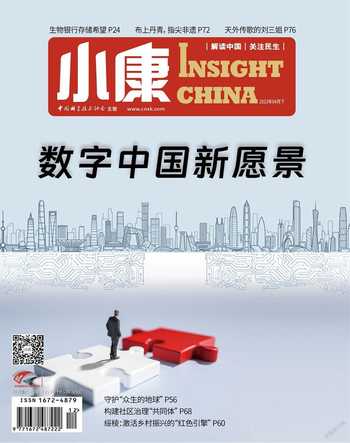中國鄉村的數字蝶變
劉彥華

用數字賦能打造“金飯碗”、著力破解鄉村振興中的重點難點問題,已經成為一股熱潮,在神州大地持續涌動。
數字鄉村是鄉村振興的戰略方向之一,也是建設數字中國的重要內容。近年來,在《數字鄉村發展戰略綱要》《數字鄉村發展行動計劃(2022—2025年)》《數字農業農村發展規劃(2019—2025年)》等一系列政策的引導下,全國各地積極響應,越來越多的農村地區讓5G成為“新幫手”、直播成為“新農活”、數據成為“新農資”……用數字賦能打造“金飯碗”、著力破解鄉村振興中的重點難點問題,已經成為一股熱潮,在神州大地持續涌動。
開局態勢良好
“寶寶們,歡迎大家來到我們的直播間。我們遠安的羊肚菌朵大肉厚、香味濃郁,這些都是剛剛從地里摘下來的,只要60元一斤,搶到就是賺到……”3月19日,湖北遠安舉行首屆電商采摘節,10余名助農主播走進羊肚菌種植基地,面對鏡頭,自信大方地直播推介家鄉的農產品。
這樣的場景,如今在全國各地常常上演。
2017年,圍繞重要農產品全產業鏈大數據建設,國家公布了13個試點縣區,建設了近100個數字農業試點項目。2020年,中央網信辦等七部門聯合印發《關于開展國家數字鄉村試點工作的通知》,部署開展國家數字鄉村試點工作。接著,農業農村部又發起了“互聯網+”農產品出村進城工程試點,覆蓋了110個特色農產品優勢縣。緊隨其后,各地陸續出臺各種政策措施,華為、騰訊、阿里云、京東等互聯網和科技巨頭企業紛紛入局,全力推進數字鄉村建設。
如今,如何以數字化手段賦能鄉村發展,很多地方已在先行先試中找到了答案:從直播電商有效拓寬農產品銷路,到智慧農業平臺通過遙感巡田、農作物生長監測、精細化管理助力農作物品質與產量雙提升,再到技術專家遠程識別病蟲害、在線診斷“疑難雜癥”,數字技術貫穿鄉村產業種植、收獲、加工、生產、銷售等各個環節,不僅大大促進了農業技術革新和生產力提高,更是催生了鄉村生產生活模式的深刻變化。
一是鄉村數字基礎設施不斷夯實。過去十年,我國移動通信從“4G并跑”到“5G引領”,實現“縣縣通5G、村村通寬帶”。數據顯示,截至2022年6月,我國農村互聯網普及率達到58.8%,與“十三五”初期相比,城鄉互聯網普及率差距縮小近15個百分點。
二是農業產業數字化進程加快。數字育種探索起步,智能農機裝備研發應用取得重要進展,智慧大田農場建設多點突破,畜禽養殖數字化與規模化、標準化同步推進,數字技術支撐的多種漁業養殖模式相繼投入生產,2021年全國農業生產信息化率達25.4%,其中畜禽養殖信息化率達34.0%。
三是鄉村數字經濟新業態新模式不斷涌現。農村電商繼續保持鄉村數字經濟“領頭羊”地位,全國農村網絡零售額2022年已達2.17萬億元;在各種數字技術的支持下,農村普惠金融發展成果喜人,“草莓貸”“咖啡貸”等各種特色農業貸款產品層出不窮,截至2022年末,已有多家國有大行涉農貸款余額超萬億元,涉農貸款增速超20%。
四是鄉村數字化治理效能持續提升。近年來,我國網上政務服務不斷健全,基本實現了省、市、縣、鄉、村五級全覆蓋,全國六類涉農政務服務事項綜合在線辦事率達68.2%,利用信息化手段開展服務的村級綜合服務站點行政村覆蓋率達到86%。
此外,數字創業創新的火種在農業農村點燃。2021 年我國返鄉入鄉創業人員達1120 萬人,其中一半以上采用了互聯網技術。
以數字技術來推動農業農村生產方式、生活方式、治理方式創新,不僅能提高農業產業效能,還能優化城鄉與區域要素流動和配置。由農業農村部信息中心牽頭編制的《中國數字鄉村發展報告(2022年)》對我國數字鄉村建設的進展予以高度肯定,指出,各地區各部門全面落實黨中央、國務院關于實施數字鄉村發展戰略的決策部署,積極出臺配套政策措施,制定完善實施方案,全方位推進,“總的來看,數字鄉村發展取得階段性成效,實現了‘十四五’良好開局。”
凝聚共識,直迎挑戰
雖然我國數字鄉村建設發展取得一定成果,但也面臨諸多挑戰。北京大學新農村發展研究院與阿里研究院高度關注數字鄉村建設,早在前幾年便成立了項目組,聯合發布《縣域數字鄉村指數報告》。據其2022年最新報告,項目組以2019年各區縣農業GDP占比大于3%為參照系,選取全國范圍內2481個縣域進行研究,并將縣域數字鄉村各領域指標的發展水平從高到低分為五等。結果顯示,超六成的縣域處于中低水平,且“東部較高、中部次之、西部和東北較低”分布格局依然明顯,東部地區的縣域數字鄉村發展處于較高水平及以上的比例為67.6%,中部地區為50.1%,而東北和西部地區分別為4.8%和12.2%。
另外,北京大學新農村發展研究院與阿里研究院特別指出,我國數字鄉村建設在基礎設施、鄉村經濟數字化、治理數字化等不同領域的表現差距較大,基礎設施進入了發展較高及高水平階段(大于60分)的縣占比達86%,且東西部差距較小,而鄉村經濟數字化、治理數字化、生活數字化發展處于同等階段的縣占比分別只有17%、28和21%。基于同一縣域數字鄉村不同領域發展存在不平衡、不協調的現狀,項目組還將這2481個縣域分為了五個類型,即“低數字基礎設施-低經濟數字化-低治理數字化-低生活數字化”(四低型)、“高數字基礎設施-高經濟數字化-高治理數字化-高生活數字化”(四高型)、“低數字基礎設施-低經濟數字化-高治理數字化-低生活數字化”(治理突出型)、“高數字基礎設施-低經濟數字化-高治理數字化-高生活數字化”(經濟短板型)、“高數字基礎設施-低經濟數字化-低治理數字化-低生活數字化”(基礎設施領先型)。結果顯示,上述五個類型的縣域占比分別為 20.3%、17.1%、10.6%、8.2% 和 7.5%。
“雖然縣域數字鄉村發展取得一定成果,但也面臨經濟數字化水平偏低、區域差異大、數字鴻溝與經濟鴻溝交疊、新業態惠民不夠、體制機制亟待完善等挑戰。”基于對數字鄉村建設中短板和問題的思考,項目主持人、北京大學新農村發展研究院院長黃季焜建議,一要明確縣域數字鄉村整體及各領域發展的階段性目標、重點任務及發展路線圖,持續完善數字鄉村建設的體制機制。二要采取更具包容性和公平性的區域發展策略,加大對數字鄉村發展滯后地區,特別是西部和東北地區以及脫貧摘帽縣的政策支持力度和社會幫扶力度。三要立足縣域發展實際需求,堅持突出重點和補足短板并重的原則,加強不同支持政策間的協調與銜接。例如,對于縣域數字鄉村發展“四低型”,需完善長短期發展規劃、穩抓穩打,加強潛力挖掘和優勢領域培育。而對于“四高型”,則需夯實發展基礎、筑牢優勢領域、強化創新升級、積極發揮引領作用。四要持續推進數字鄉村試點并開展試點成效評估,深入總結前期試點經驗與不足,不斷創新數字鄉村發展模式。
無獨有偶,4月初,中國社科院發布了最新的《數字經濟藍皮書:中國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報告(2022)》,其中的子報告《數字經濟助力鄉村振興:現實路徑、具體實踐及政策建議》同樣關注到了我國數字鄉村建設中存在的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單薄、數字人才培育缺乏、數據分享體系以及相關法律法規保障方面較為薄弱等問題,直言“學術界已經初步達成共識,數字鄉村發展的根本保障是政府在前期投入的基礎設施建設和提供的相關政策支持,客觀條件是以數據為生產要素來降低成本和信息不對稱程度,外在表現是通過平臺經濟實現農民的自我‘造血’功能,核心功能是由信息技術進步帶來經濟活動信息化,從而實現兩者間的相互促進和互利共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