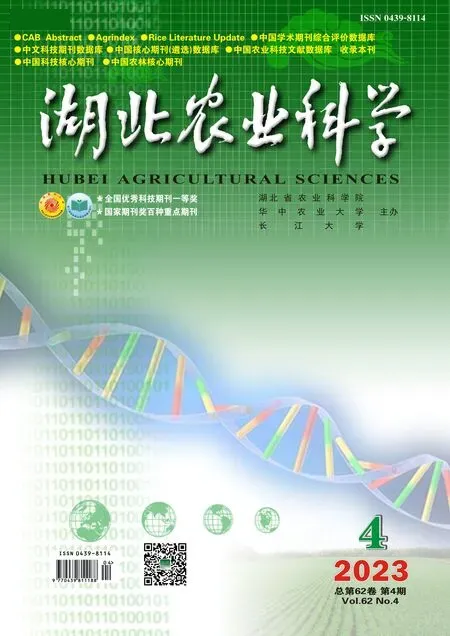基于LMDI和脫鉤模型的黃河流域農業用水驅動因素研究
馮晨,孔千慧
(河海大學商學院,南京 211100)
黃河流經青海、四川、甘肅、寧夏、內蒙古、陜西、河南、山西、山東9 省(區),橫跨三大階梯,是連接青藏高原、黃土高原、華北平原的生態廊道,構成中國重要的生態屏障,其經濟與生態地位不容忽視。黨的十八大以來,黃河流域在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治理方面作出重要貢獻。然而,黃河獨特的地形及生態環境特點導致75%左右地區地處干旱半干旱地帶,水資源匱乏,時空分配不均,流域內生態環境脆弱,水土流失嚴重,出現水源性缺水和水質性缺水雙重“水危機”。與此同時,黃河流域以灌溉農業為主,生產灌溉技術落后,水資源利用粗放,農戶節水意識不強,加之全球氣候變暖,進一步加劇了農業缺水態勢,嚴重制約了農業可持續發展。2019 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在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座談會上強調,黃河流域要堅持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堅持生態優先、綠色發展,以水而定、量水而行[1]。這意味著黃河流域要將水資源作為剛性約束,以水定產,合理管控,推動農業生產方式和居民生活方式由粗放向節約集約轉變,促進水資源集約利用與可持續發展[2]。
學者們圍繞黃河流域高質量發展及水資源問題開展諸多研究。在黃河流域生態保護與高質量發展研究層面,已有的研究成果主要是針對黃河流域城市群建設、產業升級轉型、人地耦合等的研究。王錚等[3]基于黃河流域區域發展優勢,討論了黃河流域經濟帶建成的可能性。任保平等[4]對黃河流域地級市經濟增長、產業發展與生態環境的綜合水平及三者耦合協調度進行分析。陳富良等[5]對黃河流域制造業發展的動力及路徑進行了探究。在黃河流域農業用水研究層面,研究重點主要集中在流域水資源承載力、水資源配置、農業用水效率與節水潛力的評價及測量。付俊怡[6]、崔永正等[7]利用超效率SBM模型對黃河流域農業用水效率進行了測量,并探析了流域各省的節水潛力。楊騫等[8]將投入導向的SBM-DDF 模型與全局參比的Luenberger 生產率指數相結合,測算了黃河流域農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張慧等[9]對黃河流域及流域各省的綜合農業水資源利用效率進行了對比分析。在農業用水驅動因素研究層面,現有文獻主要集中于全國或某些區域尺度對農業用水影響因素的研究。Geng等[10]和張玲玲等[11]運用超效率數據包絡分析方法計算了中國各地區農業用水效率以及空間異質性對用水效率的貢獻程度。張陳俊等[12]、盛前等[13]、劉曉東等[14]分別運用LMDI 模型對中國、長江經濟帶、河北省農業用水量變化的驅動因素進行了分析。李靜等[15]基于MinDW 模型探究了中國農業的用水效率及其影響因素及驅動機制。
現有研究在黃河流域高質量發展的內涵要義、發展路徑以及黃河流域農業水資源利用效率、農業用水影響因素等方面取得了豐富的成果,但尚未見對黃河流域農業用水影響因素的詳細報道。本研究聚焦黃河流域9 省(區),利用LMDI 分解模型對黃河流域各省(區)農業用水影響因素及驅動機制進行分析,探究農業用水優化路徑,為沿黃各省提供切實可行的水資源建議,以期緩解流域農業缺水態勢,助推黃河流域生態保護與高質量發展。
1 研究方法與數據來源
1.1 模型構建
指數分解法(Index decomposition analysis,簡稱IDA)目前常被運用于水資源研究。Ang等[16,17]將指數分解法分為拉氏指數分解法和迪氏指數分解法,結果顯示對數均值迪氏指數分解法(Logarithmic mean Divisia index,LMDI)是最優的分解方法,本研究采用該方法分析黃河流域9 省(區)農業用水量變化。
首先,依據Kaya 恒等式將農業總用水量(FW)分解如下。
式中,FW表示農業總用水量,單位為億m3;I表示地區農業產值,單位為億元;RP表示地區農村人口規模,單位為萬人;P表示地區人口規模,單位為萬人。
T=FW/I為技術效應,表示單位農業增加值耗水量;J=I/RP為經濟效應,表示人均農業產值;L=RP/P為城鎮化效應,表示農村人口占區域總人口的比重;P為地區的人口效應。農業總用水量(FW)的計算見式(2)。
ΔT、ΔJ、ΔL、ΔP分別為技術效應、經濟效應、城鎮化效應、人口效應變化量對農業用水變化量的貢獻值,從t-1到t期,技術效應、經濟效應、城鎮化效應、人口效應變化量的計算見式(3)至式(6)。
在加法分解模式下,農業用水量變化量ΔFW的計算見式(7)。
1.2 衡量標準
運用LMDI 模型對農業用水驅動因素進行分解,若分解效應為正,說明該項因素促進農業用水量的增長,為耗水因素;若分解效應為負,說明該項因素抑制農業用水量的增長,為節水因素。技術效應、經濟效應、城鎮化效應和人口效應的分解值之和代表當期跨度的農業用水總量,若總和為正,說明當期農業用水總量增加,總和為負,說明當期農業用水總量減少。
1.3 Tapio 脫鉤模型
脫鉤模型常被用于闡述經濟發展與能源資源環境消耗的內在關系,也常被用于探析經濟增長與水資源消耗的關系。OCDE 脫鉤指數法和Tapio 脫鉤模型是脫鉤分析中常用的模型[18]。Tapio 脫鉤模型因其在基期選擇和脫鉤類型上較OCDE 脫鉤指數法更優,故本研究選用Tapio 脫鉤模型構建農業用水與經濟增長的脫鉤關系,計算方法如式(8)所示。
式中,e表示脫鉤彈性;FW表示農業總用水量,單位為億m3;I表示地區農業產值,單位為億元。根據彈性系數劃分的各種脫鉤狀態見表1。

表1 脫鉤狀態分解
1.4 數據來源
選取2006—2019 年作為研究期,所用黃河流域農業用水量、農業產值、農村人口數、地區人口總數等原始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中國水資源公報》、各省《水資源公報》以及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部分分析所需數據根據核算得到。
2 實證結果與分析
2.1 分解因素效應的時間差異
基于LMDI 模型,對2006—2019 年黃河流域9省(區)的農業用水的面板數據進行分析,結果見表2。結果顯示,經濟效應和人口效應為正值,表明經濟效應和人口效應促進農業用水量的增長,為耗水因素;除2017 年技術效應為正值,其他年份技術效應和城鎮化效應均為負值,說明技術效應和城鎮化效應基本能夠抑制農業用水量的增長,為節水因素。黃河流域農業用水量變化波動較大,其中,技術效應波動最不穩定且變化最大,且除2015—2017年,其他年份技術效應對農業用水量的抑制作用均強于城鎮化效應,表明農業節水技術的提升能夠有效降低水資源消耗,但是傳統粗放型的農業灌溉方式向現代節水技術的演變依然需要較長時間的科技創新投入及政策推廣。城鎮化效應均為負值,表明隨著農村人口不斷涌入城市,城鎮化水平提升,能夠有效抑制農業用水量的增長。經濟效應和人口效應總體上分別呈減弱、加強的趨勢,且經濟效應的絕對值總體高于人口效應、城鎮化效應和技術效應,是流域農業用水量上升的第一助推因素,表明黃河流域經濟發展尚未擺脫水資源的束縛。2012—2014 年總效應出現顯著的下跌趨勢,產生該變化的主要原因是2012 年《關于實行最嚴格水資源管理制度的意見》的出臺,多地為緩解水資源短缺及水污染嚴峻等問題嚴格控制水資源的開發和利用。2016—2019年,農業用水量總效應逐漸趨于平緩。
2.2 分解因素效應的區域差異
為進一步探討各地區農業用水及其驅動因素的時空特征,分別計算得出黃河流域9 省(區)2006—2019 年農業用水量變化驅動因素,各省用水量變化的總效應和分解因素效應見表3。

表3 黃河流域各區域2006—2019 年農業用水量LMDI分解結果 (單位:億m3)
從總效應變化來看,青海、甘肅、寧夏、內蒙古、陜西、山東6 個省(區)用水量出現下降,表明這6 個省(區)農業用水總體得到有效抑制,四川、山西、河南3 個省份用水量出現上升,農業用水尚未得到有效抑制。各省(區)中,對農業用水促進作用和抑制作用最大的省份分別是四川和山東,用水變化量分別達32.71 億m3和-18.11 億m3,說明流域各省(區)用水量存在較大差異。2006—2019年,黃河流域9省(區)總效應變化較大,其中四川總效應變化最為曲折,青海最為平緩。經濟效應對農業用水的促進作用占據主導地位,其中四川省的經濟效應對農業用水的促進作用最大,青海省的經濟效應對農業用水的促進作用最小。這進一步說明青海省、四川省的農業用水量與兩地的經濟發展水平密切相關。
從技術效應來看,黃河流域9 省(區)的技術效應基本均為負值,說明技術效應能夠有效抑制農業用水量的增長,其中技術效應對抑制四川、甘肅、寧夏、內蒙古、河南、山東的農業用水消耗的作用明顯,對青海、山西作用不明顯,表明青海、山西兩省農業節水能力有限,水資源利用效率低,節水潛力有待開發。技術效應絕對值最大值(內蒙古,172.43 億m3)是最小值(山西,32.30 億m3)的5.3倍,表明節水技術水平存在較大的省際差異。流域內技術效應對農業用水的作用總體波動較大,表明黃河流域總體節水技術不夠先進,節水設備投入不夠穩定,節水效果受外部的影響較大。2010—2011年,除山西和山東外,黃河流域各省(區)節水技術均有提升,產生該變化的主要原因可能是2010 年《中國城市節水2010 年技術進步發展規劃》的出臺[19],對水資源節約使用提出一系列政策指示。
從經濟效應來看,流域農業用水量變化與經濟增長密切關聯,農業產值的提升需要投入更多的生產要素,水資源是主要投入要素之一,因此對水資源的需求量增加。經濟效應最大值(四川,239.89 億m3)是最小值(青海,39.19 億m3)的6.1倍,說明各省(區)經濟增長對農業用水量上升的影響存在較大的省際差異,主要與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有關。流域較多省(區)經濟效應在2010—2017 年逐步減弱,說明隨著第二、第三產業的發展,農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逐漸回落,農業用水量隨之減少,導致經濟效應對農業用水的促進作用逐漸減弱。流域各省(區)經濟效應在2017—2019 年總體呈上升趨勢,產生該變化的原因可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的出臺,在農業經濟發展方面提出了新的目標和規劃,農業用水量回升,經濟效應對農業用水量的促進作用增強。
從人口效應來看,除個別地區個別年份外黃河流域9 省(區)人口效應均為正值,說明人口數量的提升能夠帶動經濟規模的擴大,從而促進農業用水量的增長。相較于經濟效應,人口效應對農業用水量變化產生的影響較小,人口規模效應的最大值(山東,12.84 億m3)是最小值(甘肅,1.92 億m3)的6.7倍,說明東西部人口流動水平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關。2006—2019年,青海、寧夏、內蒙古、山西、山東人口效應均為正值,四川、甘肅、陜西、河南人口效應由負轉正,說明這幾個省份人口流入現象明顯。
從城鎮化效應來看,黃河流域9 省(區)城鎮化效應均為負值,說明城鎮化效應對農業用水量的上升起到抑制作用。人口從經濟欠發達的農村地區流動到經濟發達的城鎮地區,水資源消耗結構改變,對農業用水量增長產生顯著的負向影響。四川、內蒙古、河南、山東城鎮化效應對減少農業用水量的作用較為明顯,青海、甘肅、寧夏、陜西、山西不明顯,總體呈東高西低的態勢,自然條件對黃河流域城鎮化空間分異的作用依然存在[20]。
2.3 對農業用水經濟驅動因素的進一步分析
由表2 可知,農業用水的4 個驅動因素中,經濟效應的累計效應最大,在一定程度上說明農業產值的增長促進了農業用水量的變化。為進一步探究黃河流域農業產值對農業用水量變化的影響,以人均農村農業產值和農業用水為研究對象,在LMDI 分析的基礎上,引入脫鉤模型中的Tapio 指標,準確考察黃河流域9 省(區)農業用水量對農業產值提高的反應程度。依據公式(8),測算出2006—2019 年黃河流域九省(區)農業用水與人均農村農業產值增加的脫鉤指標e(FW,I),再根據e(FW,I)的數值,參照表1,得到對應的脫鉤狀態,整理后如表4 所示。

表4 黃河流域9 省(區)農業用水與經濟發展的脫鉤關系
從脫鉤狀態上看,黃河流域9 省(區)由于各自的經濟發展、地理位置以及資源稟賦的不同,在水資源利用與經濟增長的脫鉤態勢方面存在差異。總體上看,黃河流域9 省(區)均實現了農業用水與經濟增長的脫鉤,且絕大多數省(區)處于強脫鉤狀態。相對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農業用水量表現出相對不變或緩慢增加的發展態勢,兩者逐漸呈背離趨勢。青海、甘肅、寧夏、內蒙古、陜西、山東為強脫鉤,既達到了經濟的正增長,又實現了農業用水的負增長,是最理想的一種脫鉤狀態,強脫鉤狀態顯著的省(區)中,寧夏的脫鉤指數最高,其次是山東和陜西。四川、山西和河南為弱脫鉤,在保證經濟增長的前提條件下,實現了農業用水的低速增長,是較理想的一種脫鉤狀態[21],說明山西、四川和河南在農業用水與經濟增長的協調關系仍然面臨一定的壓力,農業用水與經濟增長的協調關系還需進一步改善。
3 小結與建議
3.1 小結
本研究基于2006—2019 年黃河流域9 省(區)的農業面板數據,運用LMDI 方法將農業用水驅動因素分解為技術效應、經濟效應、城鎮化效應、人口效應4 個驅動效應,以時間和區域分別進行測算,探究每種效應對農業用水量的響應程度,最后引入Tapio脫鉤彈性指標,進一步分析LMDI 中對農業用水量影響程度最大的經濟效應與農業用水量的響應關系,得到以下結論。
1)從總體上來看,技術效應、城鎮化效應均為負值,說明技術效應、城鎮化效應抑制農業用水量的增加,為節水因素,通過改善節水技術、提高城鎮化水平,將有效促進農業用水量的減少;經濟效應、人口效應為正值,說明經濟效應、人口效應促進農業用水量的增加,為耗水因素,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人口規模的不斷擴大將促進農業用水量的提升。
2)從區域上來看,黃河流域9 省(區)分解因素效應具有較大差異。各省(區)中,技術效應和城鎮化效應均促進農業用水量下降,且技術效應的促進作用強于城鎮化效應,實現農業用水量下降仍有賴于農業節水技術的提高;經濟效應和人口效應均助推農業用水量上升,其中經濟效應占主導地位。四川、甘肅、寧夏、內蒙古、河南、山東技術效應抑制作用明顯,青海、陜西、山西作用不明顯。四川、內蒙古、河南、山東城鎮化效應抑制作用明顯,青海、甘肅、寧夏、陜西、山西城鎮化效應作用不明顯。
3)從脫鉤指標來看,2006—2019年,黃河流域9省(區)均實現農業用水與經濟增長的脫鉤,即農業用水的增長速度低于經濟增長的速度。青海、甘肅、寧夏、內蒙古、陜西、山東6 個省(區)為強脫鉤,四川、山西、河南3 個省份為弱脫鉤。
3.2 建議
基于以上研究,為了緩解黃河流域9 省(區)農業用水壓力,推動高質量發展提出以下建議。
1)提高農業節水技術。黃河流域水資源利用較為粗放,農業用水效率低,推進節水灌溉技術對緩解黃河水資源供需矛盾、推動水資源高效利用、助推高質量發展具有積極作用。各省(區)需進一步加大節水灌溉技術推廣,實施高效節水灌溉工程,減少耗水農業,推廣應用節水技術。尤其是青海、陜西、山西3省,應加快推進節水技術和設備投入,加快農田水利設施提檔升級,促進農業節水科技成果轉化,加強農業節水增效。
2)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城鎮化水平的提升能夠有效抑制農業用水量的增加,黃河流域應不斷探索符合自身條件的城鎮化發展之路,青海應發揮生態環境優勢,不斷形成服務自然的開發格局;甘肅應以蘭西城市群為主體,結合自然條件,適度推進遷移性城鎮化,完善生態補償機制,發展縣域經濟;寧夏、陜西、山西應處理好生態環境保護與資源開發的關系,以蘭西、關中、晉中、呼包鄂和寧夏城市群為載體,發揮歷史文化比較優勢,加快構建以文旅為重點的現代服務業體系,加強西安市的培育。
3)優化人口空間分布。人口從農村向城市流動,雖促進了農業用水量的下降,但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城鎮用水量的提升。針對此,一方面,需要不斷形成協調聯動的城鄉區域發展體系,實現城鄉優勢互補,釋放城鎮人口壓力;另一方面,需要不斷發揮沿黃城市群和中心城市的引領作用,提升對農村區域的輻射和影響,以城市帶動農村,促進城鄉協調發展,引導人口合理流動。
4)推動農業水資源利用與經濟協調發展。黃河流域9 省(區)已基本實現農業用水與經濟發展的脫鉤,在青海、甘肅、寧夏、內蒙古、陜西、山東6 個強脫鉤省(區)中,內蒙古適配指數最差,推動水資源節約集約利用勢在必行。四川、山西和河南需提高農業灌溉技術,提升灌溉利用效率,實現經濟發展的同時降低水資源消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