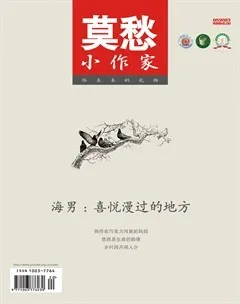江城春日
安慶城倚江而建,江雨霏霏,潮打城還,故稱江城。舊安慶城山頭星羅,高坡棋布,有“九頭十三坡”之稱,故又稱山城。九頭,即高井頭、橫壩頭、衛山頭……十三坡,即朱家坡、任家坡、登云坡、卸甲坡……九與十三,皆是虛數,言山頭坡嶺之多。
時光流水,春隨浪至。年后,江水盈盈,風兒輕吻,堤岸楊柳繡口輕張,一時盡皆吐穗,遠近一片嫩綠,映得大江也溫柔了幾許。天朗氣清,沿江而行,江上征帆去棹,往來如梭,甚是熱鬧。
少時住在縣城農村,土墻瓦灶,消息閉塞,每日與小伙伴在村前羊腸粗細的河里摸魚抓蝦、嬉戲打鬧,以為人間樂事。一天,父親忽說要帶我和姐姐去安慶游玩,我歡喜得在河里亂蹦,泥水濺了身邊的侉佬滿臉。侉佬像個泥猴,一點兒不惱,陽光下臉上堆滿了笑,笑得諂媚、討好、嫉妒。
次日,父親帶我和姐姐去了高井頭的江毛水餃,點了一屜熱氣騰騰的小籠包子,正吃得滿嘴流油,忽聽“嗚——”一聲長鳴。父親說,是汽笛聲,該有江輪靠岸了。于是我和姐姐包子也不吃了,吵著要看大輪船。父親牽著我和姐姐的手,一路小跑到江邊。
多么遼闊的長江呀,倒映著藍天,渺渺茫茫,江水淌到天邊去了。一艘客輪靠在碼頭,比樓房還高,旅客正排隊從輪船上走下來。我和姐姐看得目瞪口呆,我們做夢也不能想到,世間竟還有這么排場壯美的場景。我更不能料到,多年后自己將在這夢幻的地方工作和生活。回家后,村里沸騰了好幾天,男女老少皆來問訊,侉佬天沒亮透就趴在窗腳喊我,一定要我說明白長江比村前的小河寬多少,長多少。我努著嘴,找來扁擔、草耙子、洋叉、竹篙、耙鋤、糞瓢等一切能用的農具,笨手拙腳地向他比畫自己看到的大江。
三十來年過去,往事斑駁,侉佬跺著腳罵我吹牛的聲音猶在耳畔。眼前的江水嫵媚、文靜、溫柔,似一江醉人的酒,可回溯過往,百十年前的江面,也曾刀槍耀日、硝煙彌漫,所幸戰火終于熄滅在時光的長河中,唯有留在史書里的傷痕,不時牽扯得我們心上一顫。
穿過馬路,沿坡而上,前面便是水師營,因當年曾國藩水師駐扎此地辦公而得名。時至今日,水師與營房的影子也沒有了,紅紅綠綠的塑料盆桶擠滿街巷,盆桶里盡是泥鰍、魚蝦、老鱉,攤販人人身穿皮衣,腳穿膠靴,與水師倒也契合。行人往來匆匆,路畔,一位老人騎在小竹椅上,左手握一卷膠條,右手拿桿焊槍,正低頭修補一個裂開長口的大紅盆。那焊槍連著一只小汽罐,老人的左腳不停地踩踏機關,槍嘴噴出藍色火焰,膠條遇火,瞬時像煮熟的面條,軟了,化了,嗞嗞叫著,隨裂口游走,百足蟲一樣,死死粘在裂口上,與紅盆融成一體。
一會兒,紅盆修好了,老人吁口氣,站起身來,一絲不易覺察的微笑漾在嘴角。五塊錢。老人伸出枯枝一樣的手,對修盆的攤販比畫道。攤販遞過錢來,問:液化氣灶、電風扇、抽水機能修嗎?修著哩,修著哩。老人接過錢,就手將汽罐竹椅拎上支在一旁的自行車。我今年才八十三,再修個十多年沒問題。老人笑著,抬腳跨上自行車,順坡而下,轉瞬消失在人流里。
不遠處,太陽穿過浩浩江水,正鱗光閃閃而來,江面似籠上了一層紅彤彤的輕紗。幾只黃鸝唱著清脆驚喜的歌,追逐在楊柳堤岸。而江水依然脈脈無語,嫻靜如初。
程建華:安徽省作家協會會員,潛山市作家協會主席,作品散見于多家報刊。
編輯? ? 沈不言? ?786559681@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