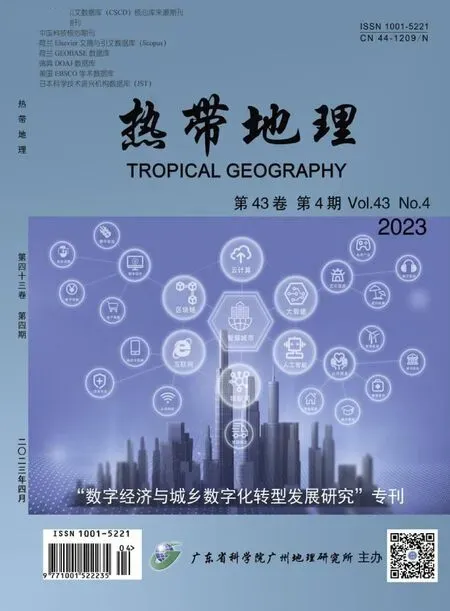金融聯系視角下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網絡空間結構及其影響因素
汪 菲,羅 皓,王長建,葉玉瑤,張虹鷗,林曉潔,陳 靜
(1.廣州新華學院 資源與城鄉規劃學院,廣州 510520;2.廣東省科學院廣州地理研究所,廣東省地理空間信息技術與應用公共實驗室/廣東省遙感與地理信息系統應用重點實驗室,廣州 510070;3.粵港澳大灣區戰略研究院,廣州 510070;4.廣東工業大學 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廣州 510090)
隨著全球化和信息化交互推進,世界經濟的“地點空間”正在被“流的空間”所代替(陸大道,2017)。不同類型企業及其企業內部(Intra-firm)、企業之間(Inter-firm)、企業之外(Extra-firm)的“流”被用來探討城市間不同功能聯系(馬海濤,2020;黃曉東 等,2021)。Taylor 及其領導的全球化與世界城市研究網絡(Globalization and World City Research Network, GaWC)是目前世界城市網絡(World City Network, WCN)研究的主流之一,著眼于金融、廣告、法律、會計、管理咨詢等高級生產性服務業(Advanced Producer Services, APS)在全球的分布,運用高級生產性服務企業總部及其分支機構空間分布數據衡量城市在世界中的連通性及其功能(Taylor, 2001, 2005; Taylor et al., 2002),主要刻畫以西方為主的發達國家經濟力量主導下的世界城市網絡(薛德升 等,2018)。伴隨著服務經濟的快速發展,APS對塑造空間結構與功能聯系格局的意義愈發凸顯,是區域內部協調發展的強大動力(Zhao et al., 2014; Zhang et al., 2016)。金融業是APS 中最具代表性的行業部門(李小建,2006a),金融服務網絡在空間上表現為節點與鏈接的復合式空間系統(Bardoscia et al., 2021;武巍 等,2005)。銀行相比保險、證券等具有運行系統成熟、空間分布廣泛等特點(李小建 等,2006b;賀燦飛 等,2013),能較好地表征城市網絡空間結構(尹俊 等,2011)。對于銀行業而言,構建以數據為中心的現代金融服務體系,是當前數字經濟的時代要求。數字化轉型背景下,由實體銀行網點鏈接的城市網絡結構,可以相對直觀地表征城市之間的金融聯系,是對資金流所構建的銀行間/城市間真實金融聯系的有益補充。國內基于銀行網點構建的城市網絡在尺度上具有多樣性,大多以全國尺度為主(尹俊 等,2011;馬學廣 等,2017;趙金麗 等,2018)。構建城市網絡的銀行網點主要圍繞多個銀行企業或針對國有銀行(李小建 等,2006b;賀燦飛 等,2013)、地方性銀行(李瑋 等,2013)、外資銀行(劉丙章等,2021)等單一類型探究銀行(金融)網絡結構及其形成機制。如尹俊等(2011)通過利用銀行、證券、保險等63家企業總部分支機構在國內的地理分布,揭示了以北京為核心的環渤海、以上海為核心的長三角、以深圳和廣州為核心的珠三角的中國城市網絡空間結構;馬學廣等(2017)以33家國內外銀行網點數據,區分國有銀行、股份制銀行和外資銀行等不同類型的金融聯系,揭示了以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成渝和長江中游等5個城市群為核心的中國城市網絡化空間聯系結構;張杰等(2022)借助193家銀行、236家保險、133家證券、128 家基金和149 家期貨等金融企業數據和聯鎖網絡模型,揭示了中國城市間金融網絡的空間演化;季菲菲等(2014)以長三角地區城市商業銀行分布數據為基礎,揭示了長三角地區金融機構網絡分布格局;武前波等(2021)以浙江省19家國內銀行的總部分支數據,利用聯鎖網絡模型和社會網絡分析揭示浙江省城鎮網絡空間的結構特征;潘蘇等(2019)以福布斯2000強的APS企業和制造業前40位的跨國企業為基礎,揭示了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網絡結構呈現出“以香港為中心”向“以香港、深圳、廣州等為多中心”演化的趨勢;在關注銀行網點的對內金融聯系的同時,相關研究進一步拓展銀行網點的對外金融聯系,薛德升等(2018)以中資商業銀行的總部分支數據為基礎,揭示了其連接下的世界城市網絡格局的演變,彌補了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經濟動力影響下的世界城市網絡的研究不足。總體而言,當前基于銀行企業的網絡構建大多以城市尺度居多,區縣尺度研究相對匱乏;同時,銀行企業的類型較為單一,綜合所有銀行類型的研究相對較少。
粵港澳大灣區作為國家戰略區域,2020年GDP累計115 191.5億元,廣州、深圳、珠海、香港及澳門的第三產業比例達50%以上,高速的經濟發展刺激著對銀行服務的需求。中共中央 國務院(2019)印發《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明確提出要發揮香港在金融領域的帶動作用,發展與完善廣州、深圳及澳門的金融服務體系及資本市場,支持部分港澳的外資銀行在廣州南沙、深圳前海等重要自貿區設置分支,促進金融市場聯通。然而當前粵港澳大灣區的要素整合正處于起步階段,金融網絡的聯系效率還有待提高(巴曙松 等,2019;王長建 等,2022a)。因此,本文基于粵港澳大灣區國有商業銀行、全國性股份制銀行、港澳銀行及外資銀行、城市商業銀行等26家銀行的網點數據,運用聯鎖網絡模型刻畫區域內部各區縣的金融聯系,并挖掘各類銀行對網絡中不同節點聯系量的貢獻差別,以期豐富APS金融聯系視角下縣域尺度銀行網絡研究,對于促進粵港澳大灣區內部的多尺度金融協同發展提供決策參考。
1 研究方法與數據來源
1.1 研究方法
1.1.1 聯鎖網絡模型 將聯鎖網絡模型中的企業網絡向城市網絡的轉換思想具體應用到銀行網點(倪鵬飛 等,2011;薛德升 等,2018;王長建 等,2022b),并進行圖解(圖1),包括2 個關鍵問題:1)等級問題。即不同等級銀行網點之間所產生的聯系程度存在差異,通常情況下銀行總部以金融資本流量對各級分支起統籌和支配作用,往往比同等級分支間的聯系流量大,如地區A、C、D之間通過銀行a 所產生的聯系中,地區A 憑借該銀行總部優勢取得較大的關聯性。當然總部或高層級分支所起的支配或帶動作用還取決于接收端的銀行網點等級,如地區D 的銀行d等級較低,通過該銀行與地區B 產生的聯系較弱。2)存在問題。即便自身銀行企業或網點數量較多、等級較高,當其他地區不存在該類銀行時,聯系便無法形成,如銀行e、f僅在地區D布局,使該地區無法與其他地區產生密切的聯系。在上述2個問題的基礎上,將不同級別銀行網點間的企業聯系映射到地區空間,即可得到金融聯系下的城市網絡,并且不同類型銀行差異性較大,對城市網絡結構特征產生差異化影響。

圖1 銀行網點與城市網絡的映射關系Fig.1 Mapp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ank branches and urban networks
利用聯鎖網絡模型計算各區縣之間的聯系強度,以建立基于銀行網點的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網絡,按銀行機構的總行、區域性總部、一級分行、二級分行、支行及儲蓄所/營業廳5個級別(不包括ATM 與自助銀行),由高到低依次賦權為5~1 分(薛德升 等,2018)。香港、澳門地區的部分銀行網點雖然名稱為分行,但主要按街道單位布置,服務功能與支行較為接近,因而按支行賦權,部分地區性網點則按區域性總部賦權。計算j銀行網點在i地區的服務價值Vij(Kogut et al., 2001):
式中:h表示網點的級別;ωh為網點級別的權重;nij,h表示h級j銀行網點在i地區的個數。計算整理得到大灣區銀行網點的金融服務價值矩陣,并計算j銀行網點在兩地區之間的單位鏈接值rabj:
式中:Vaj和Vbj分別表示j銀行網點在地區a、地區b的服務價值。將a、b地區之間所有銀行單位的鏈接值相加,即可得到兩地區間的鏈接值rab及地區自身的總鏈接值Na:
1.1.2 社會網絡分析方法 社會網絡分析是挖掘網絡特征的常用方法,以各區縣為節點,以地區間銀行網點的金融聯系為線,對粵港澳大灣區的金融聯系網絡特征進行識別,包括整體網絡及個體網絡特征分析2部分:
1)整體網絡特征。通過聚類系數和平均路徑長度2個指數反映,前者能體現網絡內部聯系的聚合程度,系數越高意味著金融網絡的凝聚力越強,反之則越弱;后者指網絡中任意2個節點間產生聯系必須通過的路徑數均值,長度越短意味著金融網絡中各節點間聯系越便捷,通過效率越高,反之則越低。利用實際的聚類系數及平均路徑長度,與Ucinet生成相同節點數的隨機網絡的對應指數進行對比,檢驗網絡是否具備小世界性(Kogut et al.,2001),公式為:
式中:Q為小世界熵;Cactual和Lactual分別為實際網絡中的聚類系數和平均路徑長度;Crandom和Lrandom分別為隨機網絡中的聚類系數及平均路徑長度;Q>1時,意味著網絡具備小世界性。
2)個體網絡特征。通過點度中心度、中間中心度、接近中心度3個指數反映。點度中心度指某地區與其他地區的直接聯系情況,度數越大的節點表明其在金融聯系中的“話語權”越強,反映節點在網絡中的等級性或影響力;中間中心度指某地區出現在各地區最短路徑上的頻率,即作為地區間聯系“中間人”的次數,度數越大表明該節點的金融聯系通過能力越強,反映節點在網絡中的中介性或資源控制能力;接近中心度指某地區與其他地區的聯系距離,度數越大表明該節點的平均最短距離越小,受其他節點的限制越弱,用來衡量節點在網絡中金融聯系的接近性或便捷程度。
此外,將借助Ucinet軟件的結構洞、塊模型等功能模塊對粵港澳大灣區金融聯系網絡結構作進一步分析。
1.1.3 地理加權回歸模型 地理加權回歸模型(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 GWR)是對經典回歸方法——最小二乘法(OLS)的改進,該模型的特點是參數估計值隨著地理位置的變化而調整,能反映自變量存在空間自相關性時不同局地的詳細情況,彌補最小二乘法無法反饋局部空間異質性的不足(Brunsdon et al., 1996, 1998; Fothering‐ham et al., 1998),計算方式為:
式中:yi為因變量;(ui,vi)為i地區的地理中心坐標;βn(ui,vi)為連續函數β(ui,vi)在i地區的值;xin為i地區的第n個自變量;εi為隨機誤差項。
1.2 數據處理與來源
本研究范圍涵蓋粵港澳大灣區“9+2”城市的各個區縣(圖2),為避免行政劃分差異導致聯系網絡的銜接不合理,對部分城市的處理方式為:1)參考東莞市園區統籌片區聯動協調發展工作推進會的戰略部署(東莞市城鄉規劃局,2017)和《中山市域組團發展規劃(2017—2035 年)》(中山市城鄉規劃局,2018)的空間發展格局分區并結合實際情況,將東莞劃分為城區片區、松山湖片區、濱海片區、水鄉新城片區、東部產業園片區和東南臨深片區等6大片區,將中山劃分為中心組團、東北組團、西北組團、東部組團、南部組團等5個組團;2)香港地區按傳統劃分為香港港島、香港九龍、香港新界(包括離島區);3)由于澳門的行政區劃面積較小,銀行網點規模不大,對整體網絡銜接的合理性影響弱,故不再細化地區。由于本文著重研究粵港澳大灣區內部的金融聯系情況,參考“2020 年中國銀行業100 強榜單”(中國銀行業協會,2021)選取該范圍內布局相對較多的銀行企業為研究對象,由于農村商業銀行跨城市設置數量少,對跨城市網絡形成的意義較小,暫不將其列入研究范疇;外資銀行方面,選擇總部在香港或澳門地區的銀行企業,以及具有代表性的全球性銀行。采用各地區截至2021年7月以前的網點信息,其中中資銀行、港澳銀行及外資銀行網點數據通過各銀行的官方網站爬取(表1)。

表1 銀行選取Table1 Bank list

圖2 研究區域Fig.2 Research area
2 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網絡空間結構
2.1 城市網絡的空間格局
根據上述26家銀行在各區縣的網點數量,通過聯鎖網絡模型建立兩兩之間的聯系矩陣,分別討論城市和區縣不同尺度下的網絡空間特征。
1)城市尺度的網絡結構特征。粵港澳大灣區整體形成廣州-深圳、廣州-佛山兩大金融聯系高地(圖3)。廣州、深圳和佛山的鏈接量占粵港澳大灣區總鏈接量的50%左右,是大灣區內部金融聯系的關鍵節點城市,其他城市的鏈接量占粵港澳大灣區總鏈接量的比例差異較小。香港和澳門兩大國際性城市與其他各城市間的鏈接量尚且不大,未來港澳與珠三角城市群的金融聯系有待進一步增強。

圖3 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網絡拓撲結構Fig.3 Topology of the urban network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2)區縣尺度的網絡結構特征。粵港澳大灣區形成環珠江口集聚的金融聯系高能量區,并呈現向外圍地區逐漸放射狀態(圖4):第一等級城市聯系表現為沿著珠江口兩側形成“人”字形網絡,節點間聯系十分密切,構成粵港澳大灣區金融聯系網絡的基本框架;第二等級城市聯系向珠江東岸集聚明顯大于珠江西岸,東莞城區片區及濱海片區、中山中心組團、惠州惠城等組成網絡的次級節點,香港地區及江門蓬江、新會也以一定的聯系規模接入網絡;第三、第四等級城市聯系網絡向東北-西南方向擴張,除肇慶封開、德慶等節點外,其余節點均已加入金融聯系網絡。整體上,從第三、四、五等級城市聯系的擴張可以看出,城市網絡的鏈接數量隨著聯系等級降低而迅速增加,在空間上珠江東岸的整體鏈接水平較珠江西岸高,存在等級擴張的地理連續性或漸進性。

圖4 不同等級的城市聯系網絡形態Fig.4 Different urban network forms
2.2 不同銀行類別的城市網絡結構
不同類型銀行所產生的網絡聯系大小存在差異,涉及節點數量及連通量由高到低依次為國有銀行、股份制銀行、城市商業銀行、外資銀行(圖5),具體表現為:1)國有商業銀行所形成的城市網絡奠定粵港澳大灣區整體網絡的基本輪廓,以廣州天河、廣州越秀及佛山南海、佛山順德、佛山禪城等為核心,這些節點因其設有省級或市級分行,方便地方政府對金融資源實施管控,進一步提升其金融集聚效應;2)深圳福田、深圳南山及廣州越秀、廣州天河等城市中央商務區大多為股份制銀行網絡的核心節點,與該類銀行實行資產負債比例管理模式、自負盈虧、對資本流通量要求較高有關,導致其區位選擇存在一定的資金指向性(李智山等,2014);3)香港港島、九龍、新界為港澳及外資銀行網絡的核心節點,港澳銀行及外資銀行在珠三角的分支機構僅分布在中心城區或者金融開放度較高的區域,與前兩類銀行所產生的聯系規模差距極大,從而導致香港、澳門在當前大灣區內部的金融聯系網絡中并不突出;4)廣州天河、珠海香洲以及東莞城區片區、東莞濱海片區為城市商業銀行網絡的核心節點,憑借廣州銀行、珠海華潤銀行、東莞銀行的總部及其分支同其他節點產生聯系,該類銀行在本城市內分布較為廣泛;而在異地城市,大部分布局在中心或較發達的城區(如深圳福田、南山等),符合該類銀行梯度式分布的一般特點(李瑋 等,2013)。

圖5 不同銀行類型的城市網絡結構Fig.5 Urban network structure of different bank types
從各類銀行所形成的城市網絡看,以外資市場為主導的香港和澳門同中資市場的珠三角各地的金融聯系主要通過國有銀行(尤其是中國銀行)建立,大部分股份制銀行以及外資銀行、城市商業銀行因資本、政策等方面的支撐有限,穿透市場壁壘的能力尚且較弱,對粵港澳三地的金融聯系貢獻并不突出。
2.3 城市網絡的結構特征
由于聯鎖網絡模型默認企業各等級分支之間普遍存在聯系,將導致地區間的鏈接值膨脹(Liu et al., 2013),為了使整體網絡特征更加清晰,需降低網絡中夸大、冗余程度,經過多次篩選與實驗,最終保留網絡中前68%的聯系對。
2.3.1 整體網絡特征 在篩選過的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網絡聯系矩陣基礎上,進行二值化處理,區縣間存在聯系的設定為1,反之為0,分別計算網絡實際的聚類系數及平均路徑長度。聚類系數為0.898,所有節點的聚類系數閾值為 [0.67, 1.00],說明整體網絡的集聚效應顯著,核心節點與其他節點的聯系極為密切;平均路徑長度為1.320,即網絡中節點間產生聯系僅需通過1~2個節點,說明粵港澳大灣區金融聯系網絡的通過效率高,聯系便捷。根據實際網絡和聯系密度為0.681 的隨機網絡的特征值進行計算,得到小世界熵為1.320,即實際網絡擁有更高的聚類系數和更短的聯系距離,具有小世界性,說明網絡中存在聚集性強、聯系密切的金融子群。
2.3.2 個體網絡特征 對各節點的中心性進行反比距離插值,以反映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網絡的節點中心性的空間結構(圖6)。整體上,粵港澳大灣區的點度中心性和接近中心性存在明顯的高低區間分化,而中間中心性較為集中,具體特征為:

圖6 城市網絡節點的中心性格局Fig.6 Centrality of nodes in urban network
1)等級性。點度中心度高值節點集中在廣州與佛山的交界地帶,如廣州天河、越秀及佛山南海、順德等區域,低值節點主要在肇慶封開、德慶等區域,整體表現出珠江東岸的網絡等級性強于珠江西岸,若干低值節點被高值節點包圍的空間特征,如東莞水鄉新城片區及深圳光明、坪山等近年正處于發展規劃階段的新區,這種現象在等級性強的珠江東岸較為明顯。佛山南海、順德憑借龐大的國有銀行網絡聯系,節點等級性強于深圳福田、南山等金融業發達區域,是由于這些節點在國內銀行業市場化改革確立階段(1994-2002年)屬于佛山管轄的縣級市,該階段是國有銀行轉型競爭比較激烈的時期(賀燦飛 等,2013),以自身的行政區劃等級優勢及龐大的業務需求量吸引銀行設置市級分行、支行,從而在銀行網絡中處于權力地位。
2)中介性。由佛山南海、廣州天河、佛山順德中間中心度高值節點組成粵港澳大灣區金融聯系的核心中轉區,東莞濱海片區及深圳寶安、南山、福田組成金融聯系的珠江東岸樞紐走廊,其他零散節點如珠海香洲、惠州惠城等也存在一定的中介性,而江門、肇慶的部分區域由于網點數量不多,因而承擔中介節點的概率不高,與核心區域的中介性差異極大,整體網絡表現出強烈的極化態勢。佛山南海、廣州天河等節點憑借區域內所集聚的高級別銀行網點,同其他節點的聯系具有流量大、范圍廣的特點,是網絡中其他未產生直接金融聯系節點間的中轉樞紐,承擔著橋梁功能,這一地位為當地匯集了更多的金融資源。
3)接近性。接近中心度的空間分布格局與點度中心度相似,以廣佛交界為高值區,說明廣州天河、越秀及佛山南海、順德等權力節點同其他節點的網絡聯系距離較短,不需要通過多次中轉即可與其他節點產生金融聯系,受其他節點的限制程度低,網絡接近性強。從空間分布的平滑性看,接近中心度的平滑性要弱于點度中心度,說明粵港澳大灣區的接近性空間變化較等級性明顯,表現在江門鶴山、臺山及惠州龍門等節點與高值區的接近性差距較大。
綜合三類中心性特征可以發現,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網絡中形成2個區域性金融極核空間:一是中心性和接近性極高,聯動規模較大的廣佛核心區,包括廣州的天河、越秀及佛山的南海、順德、禪城等節點;二是中心性作用或橋梁功能較廣佛核心區稍弱的深圳核心區,包括深圳的福田、南山、羅湖等節點。在兩者影響下,使珠江東岸地區的整體中心性較強,而江門、肇慶的部分邊緣節點表現出較強的依賴性。
2.4 城市網絡的結構洞與板塊劃分
2.4.1 結構洞分析 結構洞是指節點間的非冗余聯系,通常用于判斷節點在網絡中是否具有競爭優勢及自身的獨立性,包括有效規模、效率和整體限制度3個指標(圖7)。整體而言,佛山南海、廣州天河、佛山順德、廣州越秀及深圳福田的有效規模大,效率較高,說明這些節點在金融聯系網絡中存在結構洞優勢,對大灣區整體的金融聯系具有深刻影響力及控制力,東莞松山湖片區、東部產業園片區及香港港島、九龍、新界等節點在城市商業銀行或港澳銀行及外資銀行網絡中充當資源控制與分配的“權力角色”,也具有較高的結構洞優勢。大部分地區的有效規模與效率表現比較一致,而深圳南山、中山中心組團的效率較同等級規模節點低,說明它們的金融聯系存在冗余要素,對網絡聯系的把控能力存在上升空間。從整體限制度看,大部分地區的限制度在0.114 以下,而邊緣空間的限制度較大,以深圳光明最高,說明這些地區在網絡中的金融聯系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權力節點。

圖7 城市網絡的結構洞水平Fig.7 Structural holes in urban network
2.4.2 凝聚子群分析 通過Ucinet 的CONCOR 方法,依據節點的網絡聯系情況進行子群劃分,計算子群內部及子群之間的密度矩陣,并按一定標準將密度矩陣轉換為像矩陣(圖8和表2)。子群Ⅰ與子群Ⅱ的內部聯系密度為1.000,即各節點間均存在聯系,前者包含廣州越秀、深圳福田等有效規模大、中介性與接近性強的節點,在各類銀行的城市網絡中占有一定地位,為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網絡的核心子群;后者整體的有效規模及效率較前者弱,包含深圳羅湖、廣州增城等節點,屬于金融聯系網絡的次級或過渡型子群。子群Ⅲ包含香港港島、九龍、新界以及廣州南沙等節點,板塊內部的聯系密度為0.382,節點間聯系較不緊密。子群Ⅳ既包括佛山南海、廣州天河2個權力節點,也包括深圳坪山、光明及肇慶鼎湖、廣寧等邊緣節點,板塊內的聯系密度為0.257,各個邊緣節點需要通過權力節點達成串聯。

圖8 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網絡板塊劃分Fig.8 Division of urban network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表2 城市網絡子群密度矩陣及像矩陣(R2=0.598)Table 2 Subgroup density matrix and image matrix of urban network
以密度均值(0.679)作為判斷臨界值,大于均值的賦值為1,否則為0,形成無向的二值型像矩陣(孫宇 等,2021)。從子群內部聯系看,子群Ⅰ和子群Ⅱ存在強烈的自反性,即內部金融聯系的集聚規模較大,“俱樂部”效應顯著,子群Ⅲ和子群Ⅳ則因內部金融聯系相對松散而不具備自反性。從子群間的關聯性看,子群Ⅰ、子群Ⅱ、子群Ⅲ相互之間聯系緊密,其中子群Ⅰ為粵港澳大灣區金融要素的主要傳導者,對區域金融行業發展及城市網絡構建的意義重大,子群Ⅳ雖然憑借佛山南海、廣州天河與其他3個板塊的節點產生關聯,但由于邊緣節點的接收能力有限,關聯程度不高,僅有子群Ⅰ與之產生高密度聯系,成為網絡中相對孤立的板塊。總之,粵港澳大灣區金融聯系主要依靠核心或次級核心板塊的節點發揮中介性,邊緣板塊中各節點間的聯系非常松散。
3 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網絡結構的影響因素
3.1 指標選取
銀行網點的布局決定著城市網絡的形態與結構,其區位選擇與區域的人口密度、經濟發展水平、產業結構、政府能力、設施水平等方面有關。結合現有研究,選取7項指標作為解釋變量(表3),其中,人口密度、經濟發展水平屬于影響金融發展與集聚的基本因素(賀燦飛 等,2013;姚曉明 等,2020),政府管控行為、交通便捷程度、社會消費水平、金融服務需求、對外開放程度能分別反映地方政府、基礎設施、地區社會和國際市場等主體對金融聯系的表現(張虎 等,2016;王艷華 等,2020)。以篩選前68%聯系對后各節點的總鏈接值為被解釋變量,通過GIS 中的GWR 工具計算各解釋變量對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網絡中不同節點的具體影響。需要說明的是,由于香港地區年鑒中未按片區分別統計相關指標,詳細數據難以獲得,在此將以整個香港地區作為分析單元。在運行GWR 模型前,首先,通過OLS檢驗所選取變量是否存在嚴重的多重共線性(VIF>10),除道路密度、人均年末本外幣存款余額的VIF接近臨界值外,各項變量的VIF 相對較低,不會導致模型回歸系數的標準誤差偏大。

表3 變量選取與指標說明Table 3 Variable selection and indicator description
3.2 實證結果分析
以核類型Adaptive 和AIC 帶寬方法運行GWR模型,得到整體模型的AICc 值為-68.936,小于OLS 模型的AICc 值(-65.850),且GWR 模型的擬合優度(R2=0.798)高于OLS模型(R2=0.764),說明GWR 模型的擬合性能更優,模型精確性更高。通過全局莫蘭指數(Moran'sI)對GWR 模型的標準化殘差的空間自相關性進行檢驗,得到Moran'sI=0.043,Z=0.985,在空間上表現出完美隨機分布,說明通過該模型得出的回歸系數具有較高的統計意義,各項變量回歸系數的空間分布具體情況見圖9所示。

圖9 變量回歸系數的空間分布Fig.9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egression coefficients of variables
1)與節點總鏈接量主要呈負相關的因素有人口密度、經濟發展水平及政府管控行為,即這些指標特征值越高,節點總鏈接量越低。人口密度對節點總鏈接的負向影響由沿海地市向灣區內部逐漸減弱,對珠江西岸的影響較東岸大,最高值在珠海香洲,最低值在惠州龍門;經濟發展水平的負向作用由東北向外圍增強,最高值在江門恩平,最低值在廣州花都,這2個變量之所以出現負相關,是因為人口密集區、經濟發達區的銀行的便民服務設施屬性得到基本滿足,使2種基礎性因素對節點的金融聯系影響削弱,尤其過度的人口集中所帶來的規模不經濟不利于聯系網絡的優化(張鵬 等,2019)。政府管控行為的負向作用由中心向外圍減弱,回歸系數最高值、最低值節點分別為中山東北組團、肇慶懷集,說明當前粵港澳大灣區的金融市場聯系對政府財政投入的依賴度較低,以鏈接量較高、金融活動頻繁的珠三角核心地市表現最為顯著,隨著向總鏈接量不高的外圍推進,該負向效應降低。
2)與節點總鏈接量主要呈正相關的因素有交通便捷程度、社會消費水平,即交通便捷程度、社會消費水平越高,銀行網點的聚集規模越大,同網絡中其他節點的金融聯系更密切。交通便捷程度對肇慶和環珠江口區域的影響程度較高,回歸系數最高值、最低值節點分別為珠海香洲、惠州龍門;社會消費水平對節點總鏈接的正相關性在整體空間上表現為珠江西岸高于珠江東岸,回歸系數最高值、最低值節點分別為江門恩平、香港地區。對于香港地區、深圳福田等中心性突出的部分節點而言,交通便捷程度所帶來的金融聯系增強效果會優于社會消費水平。
3)金融服務需求、對外開放程度與節點總鏈接量的空間關系復雜,同時存在正負相關,具有雙向效應。金融服務需求與節點總鏈接量除在江門恩平表現為微弱的正相關,大部分地區表現為負向相關,說明金融服務需求越高,節點的金融網絡聯系量越低,如廣州天河、越秀等社會服務水平較高的地區,居民和企業的金融服務需求得到滿足,再次反映大灣區銀行網點布局處于相對飽和狀態;從對外開放程度看,珠江東岸的開放程度較珠江西岸高,與之相對應的是東岸與金融聯系量表現為正相關;而西岸尤其是廣佛肇間的鄰接地區,與金融聯系量表現為負相關,說明珠江東岸(尤其香港、深圳南山等節點)能通過對外聯系獲得更多的金融投資或其他資源。
4 結論與討論
以APS中金融業聯系為切入點,借助聯鎖網絡模型中所蘊含的企業網絡向城市網絡轉換思想,將26家銀行總部和各級分支間的關系網絡進行映射變換,以構建區縣尺度下的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網絡,運用社會網絡分析和GWR 模型等方法,剖析粵港澳大灣區內部的城市網絡的結構特征及影響因素,主要結論為:
1)不同類型的銀行網點所揭示的城市網絡結構特征差異化顯著,相比于單一類型銀行刻畫的城市網絡,本文重點關注的國有商業銀行、全國性股份制銀行、城市商業銀行、港澳銀行及外資銀行等不同類型銀行所刻畫的城市網絡更具科學性。從城市尺度看,粵港澳大灣區的內部金融聯系整體形成廣州-深圳、廣州-佛山兩大核心區域的空間格局,香港、澳門與其他9個城市的金融聯系尚且不強;從區縣尺度看,在環珠江口形成網絡聯系的高能量區,珠江東岸的金融聯系水平整體較珠江西岸高,表現出等級擴張的地理漸進性。以各類型銀行的城市網絡挖掘整體網絡差異的成因,其中港澳銀行及外資銀行對大灣區內部金融聯系的貢獻度較低,以該類銀行為主導的香港、澳門與其他城市地區間表現為弱聯系,意味著現階段珠三角同港澳之間依舊存在資本流通的壁壘,未來粵港澳大灣區的金融協同建設需著重關注并增強資本之間的合作與流動。
2)整體網絡具有較高的聚類系數和較小的平均路徑長度,具有小世界性,集聚效應較為顯著。從個體網絡特征看,各節點的等級性和接近性存在高低區間過渡,均表現出以廣佛交界為高值區,且若干低值節點被高值節點包圍的空間特征,但相比之下,中介性方面極化傾向更加明顯。整個網絡形成2個區域性的金融極核空間——廣佛核心區與深圳核心區,以自身強大的等級性、接近性和良好的橋梁溝通能力,以及兩者的聯動輻射,促進珠江東岸整體中心性較強。
3)大部分地區的有效規模與效率表現比較一致,外圍空間的限制度較高。處于兩大極核空間的廣州天河和越秀、佛山南海和順德、深圳福田的有效規模、效率突出,在金融聯系網絡中存在結構洞優勢,而深圳南山、中山中心組團存在一定的有效規模,效率卻較同等級規模的節點低,金融聯系中存在冗余因素。整個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網絡通過具有自反性的核心或次級核心子群的部分節點傳導產生金融聯系,邊緣板塊中的大部分節點等級性不高,其內部相互之間以及同外部建立的金融聯系松散,是網絡中相對孤立的板塊。
4)人口密度、經濟發展水平、政府管控行為對金融網絡聯系量表現為負相關;交通便捷程度、社會消費水平與節點總鏈接量主要呈正相關,兩者的影響系數絕對值也大于其余因素;金融服務需求、對外開放程度與節點總鏈接量的關系復雜,同時存在正負相關,具有顯著的空間異質特征。綜合而言,珠江西岸由于金融聯系及各方面建設的程度較東岸低,因而與正相關變量具有較高的相關系數;珠江東岸社會經濟發展水平高,金融發展將逐漸轉向外部尋求機會,因而對外開放程度成為關鍵因素。
銀行作為金融業最為基礎且廣泛分布的行業代表,是未來粵港澳大灣區金融市場一體化建設的關鍵部分。盡管當前銀行網點數量能基本滿足服務需求,但從形成的城市網絡結構看,以中資銀行為主體的珠三角城市群和以外資銀行為主體的港澳地區的金融連通性尚且不高。因此,未來除了要提高邊緣地區的社會設施、經濟發展水平,以增強銀行業務服務能力外,應當更多地關注其經濟與政治屬性,即通過銀行的金融要素流動,推進粵港澳大灣區金融戰略建設的進程。要實現粵港澳大灣區金融市場互聯互通,一方面,可以推動中資銀行“走出去”,到香港地區和澳門地區投資設點,以借助兩者的國際大都市地位,增強區域同全球的外資聯系,進而提高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地位;另一方面,通過一些放寬措施,如降低總資本的門檻,取消持股比例限制等,推動外資銀行在珠三角上市融資。當2種資本性質銀行在對方金融市場的合理融入時,才能更好地調動金融產品、科技、人才等方面的流通與合作,實現資源整合,提高粵港澳大灣區金融網絡的結構合理性與聯系效率。
城市網絡本身存在尺度差異性,即不同空間尺度下城市網絡所呈現的格局特征不同(Fischer et al.,2006;林濤,2019),僅在一個分析尺度上成立的結論推廣到其他尺度時,容易得出不適的分析結論(劉云剛 等,2022)。因此,本文可能的邊際貢獻在于:1)以銀行為代表的APS 企業的區位選擇更傾向于在地方集聚,區縣尺度的金融關聯度對銀行網點的城市內部區位選擇更具指導意義。2)銀行網點的個體異質性所揭示的差異化城市網絡結構特征,對于不同類型銀行網點的利益訴求更具參考價值。但是,本文重點討論的是粵港澳大灣區內部的金融協同發展,更加強調金融合作,對于各類銀行之間的競合關系明顯研究不足,未來可以補充銀行之間的競合研究。香港確實是全球金融中心城市之一,香港的對外金融聯系能力水平突顯,但是香港的對內金融聯系強度確實值得進一步思考,未來應加強香港對內對外金融聯系的多尺度研究。同時,在粵港澳大灣區這個特殊區域內,也更應該注重不同制度下的銀行網絡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