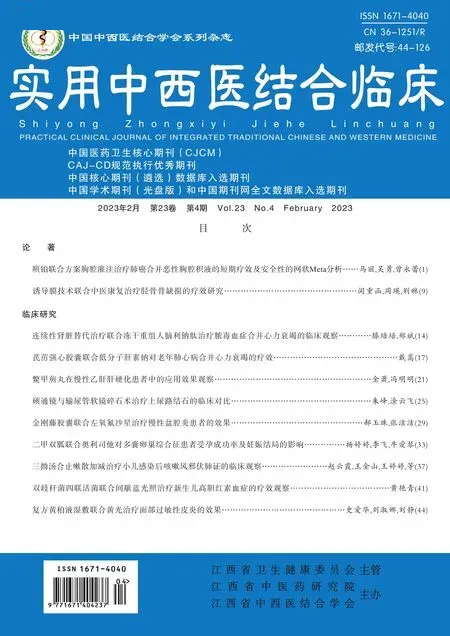濕疹外洗方聯合玉屏風顆粒治療小兒慢性濕疹濕熱浸淫證的臨床觀察
陳曉雙
(河南省平頂山市葉縣人民醫院 葉縣 467200)
濕疹是一種瘙癢性、炎癥性皮膚疾病,與遺傳、內分泌功能紊亂、變態反應等因素均有關[1]。該病多見于兒童中,以慢性炎癥性皮膚損害反復發作、高度瘙癢為主要特征,臨床表現為皮膚紅斑、丘疹、水皰、糜爛等癥狀,瘙癢劇烈,夜間更甚,對患兒睡眠造成嚴重影響,不利于患兒健康生長發育和身心健康[2~3]。有資料顯示,近10 年來兒童濕疹發病率增長了2~3 倍[4]。西醫針對該病尚無特效方法,主要通過口服抗組胺藥物或局部涂抹糖皮質類激素治療,雖有一定的效果,但長期服用會引發諸多不良反應,停藥后易復發,而局部涂抹則會產生色素沉著、皮膚萎縮等,故不宜長期使用。中醫學將該病歸屬于“濕瘡、浸淫瘡、奶癬”等范疇,多因濕、熱阻于皮膚所致,臨床以濕熱浸淫型最為常見,治療關鍵在于燥濕清熱。中醫藥治療小兒濕疹歷史悠久,且副作用小。本研究探討兒童慢性濕疹應用中藥濕疹外洗方聯合玉屏風顆粒治療的效果。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2020 年1 月至2022 年2 月我院收治的100 例慢性濕疹患兒,按照隨機數字表法分為對照組和觀察組各50 例。對照組男28 例,女22 例;年齡1~10 歲,平均(5.42±0.69)歲;病程4~20 d,平均(12.45±2.42)d;體質量7~40 kg,平均(20.24±2.40)kg。觀察組男30 例,女20 例;年齡1~9 歲,平均(5.29±0.71)歲;病程5~21 d,平均(12.50±2.36)d;體質量9~38 kg,平均(20.32±2.37)kg。兩組一般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本研究經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批準(倫理號:20190520001)。
1.2 診斷標準 西醫診斷標準[5]:皮損呈水泡、潮紅、丘疹、滲出等多種形態,自覺灼熱,劇烈瘙癢,皮損常對稱分布,以頭、面、四肢遠端等多見。中醫診斷標準[6]:辨證為濕熱浸淫,證見皮損潮紅灼熱,瘙癢無休,滲液流汁,伴身熱、心煩口渴,大便干,尿短赤;舌質紅,脈滑或數。
1.3 入組標準 納入標準:年齡6 個月至10 歲;符合上述診斷標準;初次患濕疹;入組前4 周未服用糖皮質激素類及免疫抑制劑;患兒家長知情簽署知情同意書。排除標準:因其他藥物過敏所致濕疹者;對本研究所使用藥物過敏者;近2 周內局部外用糖皮質激素者;合并嚴重內科疾病或嚴重感染者;合并其他皮膚疾病者。
1.4 治療方法 對照組予以爐甘石洗劑(國藥準字H20163477)治療,將洗劑搖勻,取適量涂于患處皮膚,3 次/d。觀察組予以濕疹外洗方聯合丹溪玉屏風顆粒(國藥準字Z31020395)治療,濕疹外洗方組成:馬齒莧15 g,黃柏、黃芩、補骨脂、側柏葉、防風、荊芥、蛇床子、白鮮皮、透骨草、白芷、地膚子各10 g,甘草(生)6 g。水煎煮,取汁200 ml,往藥汁中導入40℃溫水稀釋至500 ml,待水溫降至患兒可耐受時,將無菌紗布塊放入稀釋液中浸潤,敷于患兒濕疹部位,15~20 min/次,2 次/d。開水沖服玉屏風顆粒,5 g/次,3 次/d。兩組均連續治療4 周。
1.5 觀察指標(1)臨床療效。瘙癢消失,皮疹消退,皮膚恢復正常為治愈;皮膚恢復范圍≥70%,瘙癢明顯減輕,自覺癥狀明顯好轉為顯效;皮膚恢復范圍30%~69%,瘙癢減輕,自覺癥狀緩解為有效;未達上述標準為無效。治愈、顯效、有效計入總有效。(2)中醫證候積分。根據患兒癥狀由無到重對患兒皮損潮紅灼熱、瘙癢無休、滲液流汁、心煩口渴、大便干、尿短赤等6 項癥狀分別計0~3 分,于治療前、治療4周后評估。(3)血清學指標。于治療前、治療4 周后采集患兒空腹靜脈血10 ml,檢測免疫球蛋白E(IgE)及白介素-2(IL-2)、白介素-6(IL-6)水平,前者采用散射比濁法檢測,后兩者采用酶聯免疫吸附法檢測。(4)濕疹面積及嚴重度。采用濕疹面積及嚴重度指數評分法(EASI)評分評估。濕疹面積:將全身劃分為軀干、頸部及上、下肢,按照無皮損、皮損<10%、皮損為10%~19%、皮損為20%~49%、皮損為50%~69%、皮損為70%~89%、皮損為90%~100%分別計0~6 分;濕疹嚴重度:臨床表現為丘疹(I)、紅斑(E)、苔蘚化(L)、表皮剝脫(EX),每一項按照無、輕、中、重計0~3 分。EASI 分值計算:頭頸和上肢=(I+E+L+EX)×面積×0.2;軀干和下肢=(I+E+L+EX)×面積×0.3。EASI 總分為軀干、頸部及上、下肢EASI 分值之和。
1.6 統計學分析 采用SPSS22.0 統計學軟件進行數據分析,計量資料用(±s)表示,兩組間比較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用%表示,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P<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兩組臨床療效比較 觀察組臨床總有效率高于對照組(P<0.05)。見表1。

表1 兩組臨床療效比較[例(%)]
2.2 兩組治療前后中醫證候積分比較 觀察組治療后中醫證候積分低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表2 兩組治療前后中醫證候積分比較(分,±s)

表2 兩組治療前后中醫證候積分比較(分,±s)
2.3 兩組治療前后血清學指標和濕疹面積及嚴重度比較 觀察組治療后IgE、IL-2、IL-6 水平、EASI評分均低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3。
表3 兩組治療前后血清學指標和濕疹面積及嚴重度比較(±s)

表3 兩組治療前后血清學指標和濕疹面積及嚴重度比較(±s)
2.4 兩組不良反應發生情況比較 觀察組不良反應發生率低于對照組(P<0.05)。見表4。

表4 兩組不良反應發生情況比較[例(%)]
3 討論
中醫學中關于濕疹有眾多描述,《醫宗金鑒》有云:“此證由肝、脾二經濕熱,外受風邪,襲于皮膚……致遍身生瘡……令人煩躁、口渴、瘙癢,日輕夜重”,《外科正宗》中記載:“奶癬……生后頭面遍身發……睡臥不安,搔癢不絕”,以上均指出該病瘙癢難耐,影響睡眠,不利于患兒生長發育[7~8]。中醫學認為,該病無外乎先天和后天因素,先天因素通常是母親在孕期進食肥甘厚味之物,導致機體濕熱毒內蘊,通過胎盤遺毒于胎兒,而后天因素是由于小兒為稚陰稚陽之體,加之小兒脾胃虛弱,谷氣未充,喂養不當,損傷脾胃,脾失健運,水濕內停,濕熱邪毒蘊結于肌膚,故發為該病[9~10]。現代中醫學認為,目前兒童多進食肥甘厚味,飲食不加以節制,多暴飲暴食,久之濕熱內生,蘊結于肌膚,導致該病發生[11]。由此可見,該病主要證型為濕熱浸淫,治療應以清熱利濕為基本原則。
IgE 作為一種親細胞性抗體,在正常人體外周血中含量甚微,若機體出現各種變態反應性皮膚病時,其水平呈現上升趨勢,且其可通過Fc 段與肥大細胞結合,當機體再次受到抗原刺激后,結合在細胞表面的IgE 可與過敏原發生作用,進而使肥大細胞釋放組胺等物質,增加血管通透性,引起皮損,并出現瘙癢等癥狀[12]。炎癥反應與慢性濕疹的發病密切相關,在疾病發生、發展過程中,IL-2、IL-6 等致炎因子水平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本研究結果顯示,觀察組臨床總有效率高于對照組,治療后中醫證候積分,EASI 評分,IgE、IL-2、IL-6 水平,不良反應發生率低于對照組,說明濕熱浸淫型慢性濕疹患兒應用濕疹外洗方聯合玉屏風顆粒治療效果較佳,可有效減輕疾病嚴重程度。中藥外用在皮膚疾病治療中具有悠久的歷史,本研究所采用濕疹外洗方中的馬齒莧、黃柏、黃芩、側柏葉具有清熱解毒、清利濕熱之效;防風具有祛風除濕、止痛之效;蛇床子具有燥濕祛風止癢之效;白鮮皮具有祛風解毒、清熱燥濕、止癢之效;荊芥具有透疹止癢之效;透骨草具有散瘀止痛、祛風除濕之效;白芷具有止痛、散風除濕之效;地膚子具有祛風止癢、清熱利濕之效;補骨脂具有補脾之效;甘草調和諸藥。上述藥物聯合應用可顯著發揮清熱利濕、祛風解毒、止痛止癢之效。將上述藥方熬成藥汁敷于患兒濕疹部位,可促進局部血液循環,使外洗藥液直達病灶組織而發揮藥效,增強清熱利濕、祛風解毒、止痛止癢之效,從根本上解決病機,促進疾病恢復。藥理研究顯示,白鮮皮具有抗炎、提高機體應激能力、可抑制多種皮膚真菌的作用;蛇床子可使局部皮膚中肥大細胞對組胺的釋放受到抑制,并可通過調節機體Th1/Th2 比值,從而有效抑制組胺的釋放,進而起到抑制皮膚的被動過敏反應及對抗皮膚腫脹,此外其還具有顯著的抗炎作用;黃柏、黃芩具有抗炎、抗病原微生物等作用,其中黃芩還可具有抗變態反應的作用[13~14]。濕疹外洗方將藥物敷于患處,經皮吸收,舒適度好,患兒易于接受。同時服用玉屏風顆粒,其主要成分為黃芪、炒白術和防風,具有益氣、固表、止汗之效,主要應用于體虛易感外邪者,而小兒機體抵抗力較弱,易受外邪侵襲,予以此藥可增強患兒免疫力,發揮標本兼治的作用[15~16]。從安全性角度分析,觀察組不良反應發生率低于對照組,說明本方案治療具有較好的安全性。本研究采用內、外治相結合的方式治療慢性濕疹患兒,注重整體和辨證論治,標本兼顧,可加速疾病恢復進程。
綜上所述,濕熱浸淫型慢性濕疹患兒應用濕疹外洗方聯合玉屏風顆粒治療可減輕炎癥反應,利于改善濕疹嚴重程度及臨床癥狀,降低IgE 水平,是一種安全、理想的治療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