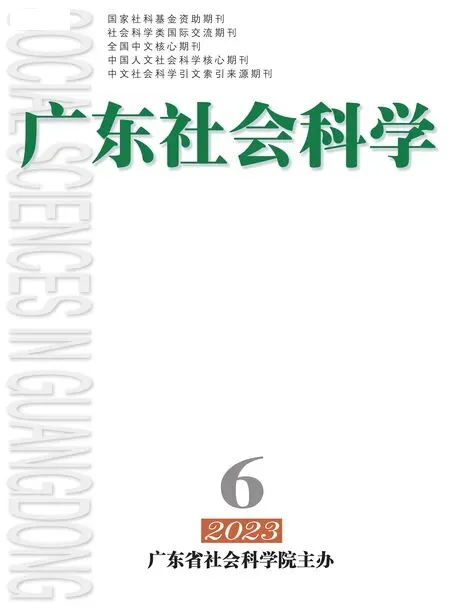道德普遍性是生物進化的產物嗎?
趙 斌 孫 燕
元倫理學家在關于何者構成道德以及道德認知的問題上存在著實質性分歧。康德主義者將“絕對命令”作為指導行動的最高原則,認為此原則與一切感覺、經驗、情緒或者文化無關;而進化論者和支持進化論的哲學家們則以經驗論的視角改變了對道德的傳統理解,主張人類社會一些固有的道德傾向和道德準則都是進化適應的結果。但是,道德相對主義的支持者強調不同文化和社會環境中所塑造的道德存在巨大差異,反對進化能夠產生單一的、普遍的道德評價標準。進化力量對道德究竟產生了何種影響?道德普遍性議題能否在道德相對主義的挑戰下得到辯護?圍繞這些問題,進化論者和哲學家們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分析總結這些爭論,有助于深入推進我們對生物進化與道德普遍性關系的研究。
一、進化論與道德相對主義
早期將達爾文進化理論應用于倫理學的觀點認為,進化過程能夠形成某種普遍規范意義上的道德。隨著進化倫理學的發展,道德普遍性(moral universality)的內涵由規范的、規則的普遍性,逐漸發展到對于道德潛能、道德范疇之普遍性的討論。
在查爾斯·達爾文(Charles Darwin)看來,一切智能生物及其種群都有發展出道德規范的可能,或者說道德普遍存在于生物界及其歷史中。他明確指出:“任何明顯具有社會本能的生物都將不可避免地獲得一種道德意識或良心,只要它的智力發展得與人類一樣好或幾乎一樣好。”①[英]達爾文:《人類的由來》,潘光旦、胡壽文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第149、150頁。達爾文沒有明確談及這種演化出來的道德意識是否具有普遍性,但他將人之道德視為自然選擇的結果,認為只要生物種群的智力水平和人類相當就可能進化出類似人類的道德規范。此外,達爾文仍然在傳統倫理學框架下尋求對道德規范及其普遍性的解釋,只不過他所說的普遍性不是基于理性的道德律,而是一種適應于種群、環境和文化的普遍性。邁克爾·魯斯(Michael Ruse)這樣描述達爾文主義的道德感:
我們人類天生就有一種社交合作的能力,也可以說本能。我認為這種能力在身體層面表現為一種道德感——一種真正的、特蕾莎修女式的利他主義!因此,基于純粹的自然主義,達爾文主義認為道德,或者更確切地說是一種道德感——一種對利他性和服從傾向的認可——是人類與生俱來的。這是自然選擇的結果,目的是讓我們在社會中一起工作或合作。②Stephen G.Post,Lynn G.Underwood,et al,Altruism and Altruistic Love:Science,Philosophy,and Religion in Di‐alogu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158.
在這里,道德被理解為進化適應的產物,其普遍性意味著一種合作本能的普遍性。在達爾文看來,獲得道德感的必然性與某人的文化偶然性不存在聯系,因為這種經由文化參與的道德感僅僅是民間習俗的產物。而達爾文的倫理學也并不認為道德僅僅源于某人的文化基礎,人的社會和生物本能都是必要的。所以說,在達爾文的理論中,道德感與社會本能有很大關系,或者說體現出社會生物學的色彩。
基于對社會本質的理解,赫伯特·斯賓塞(Herbert Spencer)“將社會視為實現功利主義的工具——一種源于‘生存斗爭’的交換和互利體系。此外,隨著時間的推移,人類社會的演變是現在所謂的生態、心理和社會經濟力量相互作用的結果,包括合作和競爭關系。”③Losco J, “Evolutionary ethics: An idea whose time has come?”, Politics and the Life Sciences, Vol. 22, No.1,2003,pp.64-66.因此,他認為道德規范的形成和遵守是為了促進社會穩定和個體生存。斯賓塞的道德觀點強調道德的實用性和個體性,他認為道德規范的形成乃基于社會進化和實踐經驗。斯賓塞并沒有提倡一種普遍適用的道德規范,而是強調倫理原則和道德戒律的確立應該以功利主義為基礎,并根據特定情況可能產生的結果適時調整,從而實現更好的生活。因此,斯賓塞的道德規范觀點帶有相對主義傾向,而不是絕對的普遍規范。但他同時強調,道德作為相對的普遍規范在人類社會中是廣泛存在的。
達爾文主義者威廉·薩姆納(William G.Sumner)是將進化論應用于社會研究另一代表。基于社會的多樣性,他將社會視為具有復雜性的有機實體,而社會進化是對生物進化的直接發展。在研究了不同文化的各種道德之后,他提出道德是相對的,是“風俗”的產物④Sumner W G,Folkways,Boston:Ginn&Company,1906,p.41.。對于薩姆納來說,他觀察到的全球文化中的各種道德規范證明了道德相對主義。類似于薩姆納,吉爾伯特·哈曼(Gilbert Harman)更關注特定文化中的“道德慣例”。在哈曼看來,自然主義者需要解釋自然世界的價值,道德相對主義①道德相對主義用于描述與不同民族及其特定文化的道德判斷差異有關的幾種哲學立場,具體有描述性道德相對主義、規范性道德相對主義和元倫理道德相對主義。(moral relativism)在這個問題上做得最好。對于自然主義的方法來說,道德相對主義就是最合理的②Harman G,Explaining value and other essays in moral philosoph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98.。通過使用“慣例”或“框架”的概念,哈曼的道德相對主義觀點表現為,道德意義上的對與錯、好與壞、正義與不正義、美德與罪惡等總是取決于“框架”的選擇,而非某種“絕對正確”。他進一步以推測的口吻指出,我們對他人的關心,也可以通過“慣例”來解釋。當其他人正在發展或已經發展出類似的關心和尊重,作為接受“慣例”的一部分,便會發展出對他人的關心和尊重③Harman G,Thomson J J,Moral relativism and moral objectivity,Oxford:blackwell,1996,p.26.。因此對哈曼來說,道德取決于擁有主觀欲望的行動者對“慣例”的接納,且不存在任何道德的約束,道德是否是進化的產物的問題并不重要。
那么,是否如哈曼所言不存在任何道德的約束呢?主張多元相對主義④元倫理相對主義的一種形式,按照黃百銳的解釋,道德觀點的正確性因社會而異,不同社會可能對相互沖突的道德觀點持有不同理解。的黃百銳(David B.Wong)期望建立一條完全自然主義的路徑。不同于哈曼,黃百銳承認道德存在“普遍約束”,如道德的功能、人類心理和人類合作的本質,任何道德都必須承認這些約束,因為它們是我們人性的一部分。他指出,今天任何可被作為道德的信念體系,都是一個漫長而復雜的進化(生物的和文化的)過程的產物。隨著社會環境的變化,用以調節人際關系的舊有習俗會消亡或轉變,新的習俗會出現⑤Wong D B,Natural moralities:A defense of pluralistic relativi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p.65.。人們普遍認為,相對主義只是將一個社會中被廣泛接受的道德規范視為該社會中道德陳述的真理條件的決定性因素。這種粗糙的、不加批判的約定俗成并不是多元相對主義的產物,因為道德規范是根據對道德的普遍約束被評價的⑥Wong D B,Natural moralities:A defense of pluralistic relativism,p.73.。但是,黃百銳依然認為各種道德規范之間和道德內部有足夠的多樣性,有足夠的差異和分歧,可以說道德最終是相對的,根本不存在唯一的、真正的道德。他通過討論道德矛盾心理,即認識到重要價值觀之間的嚴重沖突,理性的人在面對這些沖突時可能采取不同的道路,以及通過以權利為中心的道德與以種群為中心的道德論證了道德多樣性,強調了普遍存在的道德差異⑦Wong D B,Natural moralities:A defense of pluralistic relativism,p.250.。這種多元相對主義承認跨社會和社會內部道德的共性和差異。作為一種道德差異,道德矛盾存在于不同的道德傳統中,也存在于同一道德傳統中。特定類型的道德沖突涉及道德矛盾心理,按照黃百銳的觀點,道德矛盾心理的事實與道德的自然主義概念相結合,支持了沒有單一真正道德的結論⑧Wong D B,Natural moralities:A defense of pluralistic relativism,p.14.。
拋開社會文化方面的考量,尼爾·列維(Neil Levy)試圖從純粹生物學的角度為道德相對主義辯護,他并不認為這些生物學上的考量能夠消除相對主義,因為道德上的差異作為道德相對主義者觀點的核心,生物學的視角為那些重要的差異性留下了足夠的空間。列維強調道德與自然的、生物的約束之間存在著鴻溝①Levy N,Moral Relativism:A Short Introduction,Oxford:Oneworld,2002,p.137.,即不能簡單地從我們的生物學中讀出我們的價值觀。列維與哈曼的立場相似,也認為沒有單一的真正的道德,但列維的道德相對主義和黃百銳一樣認為進化對道德施加了特殊的約束,并且不認為這些約束阻礙了道德相對主義。他認為這些約束非常廣泛,仍然有很大的空間可以容納一種有趣的描述性相對主義,容納各種人類道德體系,每一個體系都足夠好地履行道德的進化功能②Levy N,Moral Relativism:A Short Introduction,p.134.。
進化心理學是為道德相對主義辯護的另一路徑。杰西·普林茨(Jesse Prinz)采用進化視角論證其道德相對主義觀點。他認為“道德規范是情緒規范:它們是由各種情緒所支撐的,特別是,道德規范是以道德情緒為基礎的。”③Walter Sinnott-Armstrong,Christian B.Miller,Moral Psychology,Cambridge:The MIT Press,2008,p.368.普林茨認為雖然“贊成”和“反對”這兩個詞有點過時了,但可以被視為兩類道德情緒的總稱:道德贊美情緒和道德譴責情緒。前者包括感激、尊重和正義,后者包括導向外部(other-directed)的情緒,如憤怒、蔑視、厭惡、怨恨和憤慨,以及導向自我(self-directed)的情緒,如內疚和羞恥。④Walter Sinnott-Armstrong,Christian B.Miller,Moral Psychology,p.368.具體來說,普林茨認為先天道德的證明缺乏證據,道德更像是一種由進化而來的副產品,像所有人類能力一樣,取決于特定的生物傾向。人類道德規則的形成,取決于兩個因素,其一是人類自身的心理能力,其二是情境。這些心理能力包括:⑴非道德情緒,情緒調節可以讓我們從固有的情緒中構建行為規范;⑵元情緒,即關于情緒的情緒,例如我們會因為生氣而感到內疚,二階情緒可以在重塑一階情緒中發揮因果作用;⑶觀點采擇,人類往往會表現出對第三方的關心,而動物不會,這可能是由于人類善于站在他人的角度思考;⑷非道德偏好和行為傾向,除了我們天生的情緒能力外,可能還有一些天生的社會行為有助于道德的形成。除了這四種心理機制之外,情境因素也會驅動道德規則的形成。所有文化都構建道德,這是因為在共同生活中,我們需要制定行為規則,并且需要以易于內化的方式傳播這些規則。
普林茨搭建起一個情緒如何影響道德規則形成的框架,認為道德確實源自于我們的人性能力,但還沒有證據表明人類大腦中有一個道德本體。道德的構建受社會文化影響,反過來也起著協調社會問題的功能。這個體系看起來像是柏拉圖的三駕馬車,道德像是那個稱之為理性的馭手,引導著情緒這匹烈馬。普林茨援引三個遞進的心理學證據來正面論證道德與情緒是關聯的:其一,道德判斷可以通過引發情緒來改變,這意味著情緒可以影響我們對道德問題的看法和評價;其二,情緒缺陷導致道德盲目,這意味著當我們的情緒受到干擾或扭曲時,可能會做出不符合道德規范的決策和行為;其三,情緒和道德判斷之間似乎存在概念上的聯系,這進一步加強了道德與情緒的相關性⑤Walter Sinnott-Armstrong,Christian B.Miller,Moral Psychology,p.369.。有基于此,普林茨在其后來作品中確立了道德相對主義的立場。在他看來,我們的價值觀只是已存的許多價值觀中的一部分,那些認為我們擁有道德真理的信念應該被審視。我們的價值觀就是情緒的價值觀,文化的歷史就是道德轉變的歷史。道德的靈活性并不意味著我們被迫接受一切皆可的道德虛無主義,它使我們擺脫了偏執和道德停滯,使我們能夠改進我們已有的道德觀念⑥Prinz J,Beyond Human Nature:How Culture and Experience Shape the Human Mind,New York:W.W.Norton&Company,2012,p.329.。
總之,在道德相對主義者看來,有關人性的生物學事實并不能給予充分的道德理由,使行動者去執行或不執行某項行為。行動者可以不理會其自然傾向自由地追蹤行動目標,即使這些傾向是生物學意義上的適應。這樣的觀點對一些進化論者來說是難以接受的,他們會認為道德是人類進化的產物,不能通過相對主義來解釋,尤其是對于人類沒有單一的真正道德的觀點。相對主義者的觀點明顯脫離了我們對達爾文倫理學的印象。在倫理問題上,達爾文似乎強調人類之間的相似性,而不是多樣性,并且生物性特征與文化特征很難在進化理論中進行嚴格區分。達爾文的理論隱含了一種可能的人類道德客觀性,即便不是真正的道德,但至少存在普遍的約束,而且這種普遍約束在本質上與相對主義是背離的。
二、進化論者對道德普遍性的辯護
關于進化論是否會導致道德相對主義的問題引起了巨大的爭論。例如,魯斯和愛德華·威爾遜(Edward O.Wilson)在研究倫理學和進化論時,就反對道德相對主義,主張圍繞人類本質和道德的進化觀點不會導致道德相對主義。為了證明生物學確實可以為倫理學提供有價值的洞見和理解,魯斯認為來自人類研究的證據表明,在所有文化差異之下,道德信念是一致的,這些一致性是先天的,而不是后天習得的①Matthew Nitecki,Doris Nitecki,Evolutionary Ethics,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3,p.148.。在魯斯看來,人類不同文化間的相似之處遠遠超過了彼此的差異。對達爾文主義者來說,道德的本質在于它是共享的,而不是相對的。
大多數相對主義者強調社會之間和社會內部的道德多樣性,他們的理由是,如果真的存在客觀的價值,那么為什么我們會觀察到如此多的相對性案例?魯斯通過援引突出道德一致性而非道德相對性的數據,開辟了一種可能的論證道路,認為是客觀價值觀促使人們走到一起。為此,魯斯強調進化倫理學家應強烈否認相對性,否則合作的普遍性就會被瓦解②Matthew Nitecki,Doris Nitecki,Evolutionary Ethics,p.158.。魯斯的基本觀點可以概括為:除非我們都參與其中,否則道德不會作為一種生物適應發揮作用;人類除了存在差異之外,還擁有共同的基本價值觀,以及合作的普適性。不過,即便如此,面對人類學研究所呈現的人類間文化差異的事實,任何自然主義倫理學都很難一蹴而就地解決道德相對主義問題。
當所有的矛頭指向文化(傳統、慣例、框架),生物學家們的態度讓這一問題的討論更加有趣。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認為遺傳規則是出于控制基因的目的而約束和指導行為,然而,人類的行為并不完全受生物規則的支配,還受到文化的支配。道金斯提出,人類社會具有驚人的多樣性,人類的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文化而不是基因決定的③[英]理查德·道金斯:《自私的基因》,盧允中等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第185頁。。與道德相對主義相似,道金斯認可社會之間和社會內部的道德多樣性,但道金斯并沒有接受相對主義。一方面,道金斯所指的道德變化是一種道德進步,他認為在漫長的時間尺度上,進步的趨勢是明確和延續的④Dawkins R,Ward L,The god delusion,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2006,pp.270-271.。這種道德進步的觀點顯然不符合道德相對主義,因為相對主義者若接受道德進步的觀點,那么他們就必須解釋道德進步是按照什么標準進行的,否則就違背了道金斯關于社會進步趨勢的觀察。另一方面,道金斯的觀點也不會導致道德相對主義,因為他認為存在道德普遍性的證據,以及關于對與錯的共識和共同的道德感。在道金斯看來,我們的是非觀來自我們的進化歷史,對不公平的敏感是人類與生俱來的,進化是人類具有道德感的原因。
不過,道金斯也曾認為親緣選擇和互惠利他模型不足以解釋文化進化和我們觀察到的巨大的文化差異,因而他使用了“模因”的概念來解釋人類文化之間的巨大差異。和基因一樣,模因也是復制因子。模因通過從一個大腦傳播到另一個大腦的過程,在模因池中自我傳播,這個過程在廣義上可以被稱為模仿①[英]理查德·道金斯:《自私的基因》,盧允中等譯,第222頁。。通過道金斯的模因理論,我們可以發現他認為道德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相對性,但這顯然不是道德相對主義。道金斯和達爾文一樣,通過觀察自然歷史的進程看到了道德的進步,而不是放大其中的差異。
另一位自然主義進化論者斯蒂芬·古爾德(Stephen J.Gould)也不認為自然主義方法的道德會導致道德相對主義。在討論進化論和道德時,古爾德主張自然對人類是漠不關心的,在他看來,我們根本無法從自然的事實中收集道德真理,但他并不認為這會導致一種“破壞性的”道德相對主義②Gould S J,Rocks of Ages:Science and Religion in the Fullness of Life,New York:Ballantine,1999,pp.203-204.。古爾德的早期觀點就曾指出,人類已經把自己看作為一種學習型動物,階級和文化的影響遠遠超過微弱的遺傳傾向。但是,在過去的十年里,人類還是被一種死灰復燃的生物決定論所淹沒③Gould S J,Ever Since Darwin:Reflections in Natural History,New York:W.W.Norton&Co,1977,p.237.。在古爾德看來,對于人類來說,文化的力量淹沒了基因的構成,人類無法直接擁有基因決定論者們所設想的遺傳性狀,也就是說,古爾德可能同樣認為人類受文化支配。當然,古爾德也認為文化多樣性是常態,人類的靈活性是理解和解釋人性最重要的東西,而不是由基因決定的特定人類特征,但這并不意味著古爾德導向道德相對主義。人類表型特征的進化已經停滯了至少5萬年,而人類具有的靈活性和適應性卻依然在發展,而且很難將特定的人類特征與特定的遺傳基礎相匹配。這一事實符合古爾德的間斷平衡理論。古爾德提出,基于“欲望、談判和互惠”的道德原則出現在許多不同時代的文化中,并顯示出它們的價值④Gould S J,Eight Little Piggies:Reflections in Natural History,New York:W.W.Norton&Co,1993,p.50.。在這里,古爾德所觀察到的某種道德原則的共性,即某些共性原則確實幫助了人類的更好發展,并因此具有了普遍性意義。
總之,進化論者往往會從進步⑤需要指出的是,古爾德雖反對進步的概念,但本文認為他并不排斥某些道德原則能有效推動群體發展的觀點。或某種發展過程的視角來看待道德的普遍性問題,主張生物性和文化性特征的共同作用才是推動道德起源和發展的肇因,這里也蘊含了將人類道德視為一種更普遍的生物現象的傾向,即在道德上對我們有益的事情對其他種類的生物也有益,其中一些物種能夠敏銳地察覺并適時地對環境中的特定特征做出反應,獲得巨大的益處,從而形成某種普遍形式的道德規范,這支撐了道德普遍性的觀點。
三、道德普遍性的生物、文化基礎
從進化角度對道德普遍性的辯護需要回答以下問題:首先,是什么讓道德上好的事物成為道德上的善(如何確立普遍的道德標準)?第二,為什么道德上的善無法簡單地還原為對我們基因有益的東西(如何建立直接的普遍適應解釋)?第三,自然的道德善究竟應該如何與道德上的“應當”相關聯(如何由觀察事實變為普遍規范)?對于這三個涉及普遍性的問題,在這一部分將展開分別討論。
(一)自然的道德善
約翰·科利爾(John Collier)和邁克爾·斯廷(Michael Stingl)主張一種自然主義的道德方法,稱其為進化道德實在論(EMR),其基本假設在于:生物體所處環境中存在某些自然的對該生物體有益的事物。這些事物先于生物體發育出任何檢測或響應它們的能力,被稱之為自然的道德善(natural moral goods)。①Stingl M,Collier J,Evolutionary Moral Realism,London:Routledge,2020,p.1.此基本假設包含兩個推論:其一,任何生物體都有機會接觸到自然的道德善;其二,從自然的道德善到自然道德需要一些條件,是進化適應的結果。那些能檢測和響應自然的道德善的能力被自然選擇并保留了下來,逐漸形成了人類的道德能力。
第一個問題在于,自然的道德善具體內涵是什么?EMR認為,自然的道德善是指在生物界中經常出現的一類結構特征,這些特征可能對環境中的有機體產生重大影響②Stingl M,Collier J,Evolutionary Moral Realism,p.2.。例如他人需要幫助的情況、公平競爭的情況,似乎是一種定期重復出現的結構性特征。因此,EMR 將人類道德視為更普遍的生物現象的一個特殊實例。“人類進化到能夠討論或爭論這些有益事物,而這種討論或爭論在文化和歷史上導致了精妙闡述的道德規范。”③Stingl M,Collier J,Evolutionary Moral Realism,p.3.第二個問題是,為什么它們是“善”的?EMR沒有給出正面的回答。但可以認為,自然的道德善除了指稱客觀存在于世界的某些結構特征外,還提供了一個簡潔的假設,即道德從一開始就是一種普遍的生物現象,在這之前,沒有什么神秘的實體或存在作為原因。第三個關鍵問題在于,推論二的具體實現方式是什么,即我們如何從EMR關于自然道德善的假設轉向人類道德準則的“應當”?以及自然道德善究竟如何與道德上的“應當”相關?EMR顯然采取了一種建構論和實在論的綜合解釋,自然的道德價值觀再加上語言和論證的能力。它一方面不否認人類的語言、思想和論證能力塑造了道德;另一方面,堅持自然的道德善先于人類的語言和論證能力出現。人類在社會關系和社會規則方面具有豐富的創造力,但隨著環境的變化和歷史的發展,這些創造力使我們偏離了基礎的自然的道德價值觀。
簡言之,EMR的論證始于一個實證假設,即自然的道德善經常出現在社會性物種和智能物種的環境中,這些道德環境的結構性特征與生物體道德特征的選擇有因果關系,無論這些特征是純粹的行為、本能、情緒還是認知。道德并非根源于具有生存價值的行為模式,也不是源自可能使人類相信某些事物在道德上是好或壞的心理能力。這一論斷雖然有待更為深入的推敲,但它開辟了探討道德普遍性問題的一條新路徑。
(二)道德是擴展適應的結果
先天論者存在一種傾向,認為道德的發生或生成源自我們大腦的某個模塊,美國心理學家勒達·科斯米德斯(Leda Cosmides)和約翰·托比(John Tooby)并沒有試圖證明存在單一連貫的道德模塊,而是認為道德推理的一個特定方面具有模塊化(Modularity)特征④Cosmides L, Tooby J, The adapted mind: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and the generation of cul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p.165.。
按照先天論的觀點,道德先天能力的模塊化可能是功能或解剖學意義上的。其中,功能意義上的模塊化是指處理特定領域特定信息的一種方式。模塊是信息封裝的,即它們無法直接訪問其他模塊中的信息。解剖學意義上的模塊化指的是位于大腦內的特定神經回路。在這兩種意義上,語言能力通常都被認為是模塊化的。大腦的特定區域產生用來處理語言的規則和標準,使得我們擁有語言能力的同時,又很容易受選擇性缺陷(selective deficits)的影響。如果道德能力能夠在功能和解剖學上均被證明是模塊化的,才能更好地支持道德先天論。因為我們在學習和發展認知能力時,常常會利用功能模塊化的通用認知資源(如感覺系統),而解剖學可以定位這些提供通用認知資源的模塊。然而,普林茨對先天論者的這種模塊化觀點表示質疑,指出這些大腦模塊只涉及情緒反應和推理能力,沒有強有力的證據表明在道德領域存在功能或解剖學上的模塊,先天論者必須尋找其他證據來支持他們的觀點①Walter Sinnott-Armstrong,Christian B.Miller,Moral Psychology,Cambridge:The MIT Press,2008,p.385.。這也引發了下面的話題,即道德能力是否被自然選擇所塑造的。
馬庫斯·阿爾文(Marcus Arvan)反對社會合作是道德認知的進化功能,或者說反對道德認知是社會合作的進化適應,他認為道德認知根本不是一種“生物能力”,而是我們通過個體理性和社會化過程學習的結果,這些過程將進化史上出于多種原因選擇的能力用于新穎的、親社會的用途②Johan De Smedt,Helen De Cruz,Empirically Engaged Evolutionary Ethics,Cham: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2021,p.90.。他的基本論點是道德認知涉及各種長期規劃能力,而這些能力不只適用于促進社會合作,也適用于破壞社會合作。阿爾文這里所談及的道德認知涉及三個基本能力,即心理時間旅行能力、換位思考能力以及風險規避能力。③Johan De Smedt,Helen De Cruz,Empirically Engaged Evolutionary Ethics,p.96.這三種能力都能找到神經生物學上的證據。大腦默認模式網絡(Default Mode Network,DMN)是指人類大腦中一組特定的神經元之間形成的一個網絡。這個網絡在人類大腦處于靜息狀態時最為活躍,而在執行任務時則相對較弱。DMN包括腹內側前額葉皮層(vmPFC)、背內側前額葉皮層(dmPFC)、顳頂聯合區(TPJ)等腦區,這些腦區在靜息狀態下會相互協調,形成一個內在的、自我參照的狀態。在阿爾文看來,DMN在最廣泛的意義上提供了長期規劃的能力,包括記憶、審慎的態度和情緒處理等,但這些能力并不是明顯的“道德”。這些能力在進化史上是出于非道德原因而被選擇的。例如,無論道德行為還是非道德行為都需要心理時間旅行能力。如果一個兒童通過獎勵和懲罰機制,認識到什么是道德的或不道德的,并學會以道德的方式關心他人的觀點和利益,那么他會對違反社會規范的行為產生擔憂,他需要回憶或預測他人可能對自己行為做出的反應,也就是進行心理時間旅行。然而,他也可以利用時間旅行的能力,通過想象不同的未來,以規避因違反規則所帶的風險。
總之,在阿爾文看來道德認知涉及的三種基本能力與社會合作無關,而只能寬泛地總結為與長期規劃能力相關。盡管不能將道德認知作為社會合作進化適應的證據,但DMN確實可以視為道德普遍性的生物基礎。至少,DMN的一些區域確實與道德敏感性相關,即監控和識別給定情境下道德相關細節的能力,例如,腹內側前額葉皮層處理風險和不確定性,參與從錯誤中學習和將道德判斷應用于自己的行為與情緒調節和決策能力有關;背內側前額葉皮層參與自我意識和理解他人心理狀態的能力;顳頂聯合區與自我意識、情景記憶、共情和寬恕有關,尤其在判斷他人意圖時發揮重要作用;扣帶回(CG)、眶額皮層(OFC)、舌回(LG)和杏仁核(amygdala)參與各種情緒處理、記憶和學習。④Johan De Smedt,Helen De Cruz,Empirically Engaged Evolutionary Ethics,pp.97-99.
可以肯定的是,進化歷史中這些特征的出現與道德認知能力的演化無關,并且至少有17個大腦區域涉及道德判斷和敏感性,也就是說,涉及道德認知的每個大腦區域都將賦予我們的祖先特定類型的適應性優勢。另外,在進化史中,涉及道德認知的不同能力出現在不同時期,有些甚至發生于高強度的社會合作活動之前。這些事實表明,道德認知所依賴的生物特征是分別進化而來的。但是,在后來的生物環境下,這些特征促進了群體的社會合作和個體的親社會特征的發展,使穩定的群體和大規模的社會成為可能,促進了生存適應性。在這個過程中,道德認知(即社會合作)是通過個體層面的理性能力和社會化來學習的。這些群體隨后發展、傳播和執行特定的規范,使個體社會化,從而發展出遵守道德原則的理性。所以,道德認知能力是一種擴展的生物適應。
(三)個體行為的傳播促使道德規范的形成
埃斯特爾·帕勞(Estelle Palao)也認為道德應被視為一種擴展適應(Exaptation),是文化進化在道德形成的過程中的二次適應(Secondary adaptation)①Johan De Smedt,Helen De Cruz,Empirically Engaged Evolutionary Ethics,p.112.。文化選擇壓力因社會群體和物種的不同而不同。經驗證明,人類以外的動物也有能力進行規范行為,并且它們也可能受到文化傳播過程的影響。有關動物行為的研究以前使用“社會規范”一詞,但現在更普遍地使用“文化”②Sapolsky R M,“Culture in Animals:The Case of a Non-human Primate Culture of Low Aggression and High Affil‐iation”,Social Forces,Vol.85,No.1,2006,p.218.。對于帕勞來說,“文化”被定義為“在個人或群體之間流傳的信息實體,通過這些信息的傳遞來實現文化的再生產”。這里的“文化”指的是“由某個群體或亞群體共享的信息或行為,是通過某種形式的社會學習從同類中獲得的”。
有必要澄清,帕勞這里所使用的“社會規范”概念借用了克里斯汀·安德魯斯(Kristin An‐drews)的動物社會規范(后簡稱社會規范),其內在的發生機制為:⑴種群成員表現出的某種行為模式;⑵某個體選擇遵從這種行為模式;⑶該個體期望全體種群成員同樣遵守該行為模式并制裁那些不遵守的其他個體③Andrews K, “Na?ve normativity: The social foundation of moral cognitio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Association,Vol.6,No.1,2019,pp.36–56.。這種理解很好地描述了動物在社會規范下運作的模式。形成這些行為模式可以通過社會性的學習或傳播而擴散。而他這里使用的“文化”概念則借用了格蘭特·拉姆齊(Grant Ramsey)的觀點,即,在個體或群體之間傳遞的信息,這些信息在其間流動并重復出現以及導致行為特征的持久變化。文化可以同時影響環境和基因,也可以被后二者所影響。例如母鼠舔舐幼崽的文化行為可以影響幼仔的表觀遺傳④Ramsey G,What is animal culture?,London:Routledge,2017,pp.348-351.。文化傳播的方式極為多樣,包括但不限于經由物理手段或制造品進行傳播。而且,動物行為學的觀點認為,特定行為只要持續存在于某物種的一個亞群中,就可以算作文化的證據。
關于社會規范、道德規范和文化規范的適用范圍,帕勞提出了兩種觀點。首先,社會規范通常被視為完全受環境或權威的支配,而道德規范通常具有更廣泛的適用性,并可以通過不同方式證明其合理性,是主要關于避免傷害或保護公平相關的規范⑤Johan De Smedt,Helen De Cruz,Empirically Engaged Evolutionary Ethics,p.116.。按照帕勞的觀點,將道德和習俗都視為“社會規范”并不會導致相對主義,因為可以存在一種在不同文化群體中表達方式有所不同的普遍道德原則,具體而抽象的普遍道德原則與其在任何特定歷史時期、文化背景或地理區域上的具體表現之間存在著重要差異。其次,帕勞還認為,任何對道德、傳統或文化規范的描述都首先是社會規范的一種形式①Johan De Smedt,Helen De Cruz,Empirically Engaged Evolutionary Ethics,p.117.。這些規范必須滿足社會規范的所有因素和基本要求,包括種群中的行為模式、個體選擇與行為的一致性、對他人遵守規范的期望以及對違反規范的抵制。當某種行為成為“文化”規范時,意味著社會行為模式通過行為信息的傳播而逐漸形成,并且由于規范的存在,種群在代代相傳中會發生持續的變化。
總之,共同的道德價值觀提高了群體在應對其環境時的基本生存效能,而道德規范的形成是文化發展所推動的社會組織演化的結果和集體過程。當然,盡管潛在的普遍原則和價值觀似乎是跨文化的,但對道德規范的表達、應用或細節處理取決于不同群體的歷史、地理和社會教育,特別是文化與歷史。因此,道德規范由于源于一般規范性行為,因而其基礎是普遍性的,但會有特定環境的不同表達。
四、結 語
基因文化協同進化(Gene-Culture Coevolution) 理論主張,道德的進化是由自然選擇直接推動的,道德行為因具有增加適應性的效果而推動了道德感和道德規范的協同進化。弗朗西斯科·阿亞拉(Francisco J.Ayala)認為,如果該觀點是正確的,就會產生一個普遍的道德體系,而不是今天不同文化之間存在的道德準則(moral codes) 的高度差異②Ayala F J, “The difference of being human: Morality”,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Vol.107,No.2,2010,p.9015.。但是,“人類生活是受規范制約的。從進化的觀點來看,……人類生活中充滿了各種各樣的規范,而道德規范只是其中的一個子集”。③徐向東:《道德生物增強與道德認知》,《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4期,第52頁。通過援引神經生物學領域的研究,不難發現大腦的默認模式網絡和大腦的模塊化特征可以作為辯護證據,支持道德普遍性有著生物基礎的觀點。道德行為和具體道德準則都經歷了生物進化和文化進化的塑造。道德行為及其所遵循的具體準則完全取決于促進行為產生的文化框架,在這里,行為的正當性可能是通過最基本的道德價值來確立的,即,存在某種人類共同認可的道德事實。在此基礎之上,又因不同社會地理區域或物種特有的文化發展走向,形成表達相同或相近道德價值的多樣化的具體規范及行為。總之,生物性特征使我們具備了一些基本的道德傾向和道德價值,而文化性特征則在不同的社會環境中塑造了具體的道德準則。通過將道德視為一種用于規范行為的擴展適應工具,能夠調和各種具體道德準則的多樣性與普遍性之間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