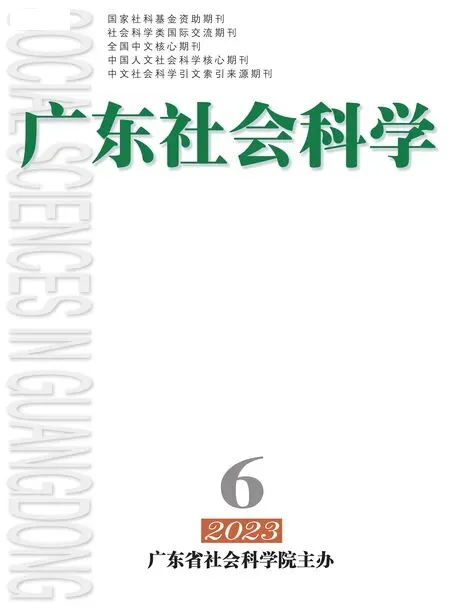地緣政治與利益沖突:桂系與兩廣事變*
賀江楓
1936年6月1日,國民黨西南執行部、西南政務委員會呈請南京國民政府領導全國抗日,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遂即通電響應、粵桂軍隊紛紛北上,國內局勢頓形緊張。兩廣事變爆發后,中央與兩廣大有兵戎相見之勢,陳布雷感嘆時局恐無法緩和矣。①陳布雷:《陳布雷從政日記(1936)》,1936年6月8日,香港:開源書局,2019年,第113—114頁。桂系作為兩廣事變的核心參與者,反蔣態度甚為積極,在鼓動陳濟棠共同反蔣的同時,更主動聯絡各地方實力派一致行動,即便7月9日余漢謀倒向蔣介石、粵局危急之時,桂系仍舊不忘勸說陳濟棠公開另立政府。②《黃旭初日記》,1936年7月12日,廣西壯族自治區博物館藏(下同,不再注明)。兩廣事變作為全面抗戰爆發前國民政府整合地方勢力的重要歷史轉折點,學界已有諸多精深研究,③代表性論著如:王英俊:《變局中地方軍人的生存邏輯:兩廣六一事變中的余漢謀》,《廣東社會科學》2022年第4期;白先勇、廖彥博:《悲歡離合四十年:白崇禧與蔣介石》,臺北:時報文化出版社,2020年;羅敏:《走向統一:西南與中央關系研究(1931—1936)》,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肖自力:《南京政府前期地方實力派的政治生存——以何鍵為中心》,《歷史研究》2014 年第3 期;肖自力:《陳濟棠》,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2年;鄧正兵:《陳濟棠與兩廣事變的發動——兼論兩廣事變的性質》,《學術研究》2002年第8期;施家順:《兩廣事變之研究》,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1992年。重點圍繞蔣介石處置事變的決策過程,陳濟棠、余漢謀、何鍵政治態度的變化等問題進行了全面的史實梳理,使得今人對事變歷史演變過程認知更為清晰。相對而言,作為事變的主要參與者之一,桂系的行為邏輯、態度變化,及其與各方的政治博弈仍有諸多尚待挖掘的空間。故而本文試圖全面展現桂系在事變過程中面臨的現實困境以及在和戰選擇過程中的猶疑與躊躇,進而管窺全面抗戰爆發前地方政治的復雜多元面相。
一、“和蔣”謀黔失敗
1931年寧粵和談結束后,廣州國民政府雖宣告取消,但西南作為半獨立的割據勢力仍舊長期存在,在其內部則形成以胡漢民為首的元老派、陳濟棠主導的廣東實力派,以及李宗仁、白崇禧掌控的桂系。元老派之唯一目的為開府廣東,對陳濟棠態度猶豫極為不滿。粵系以陳濟棠為領袖,對外均主張不可輕舉妄動。桂系則外部活動由李宗仁主導,內部事務純操諸白崇禧之手,省主席黃旭初惟李、白之命是從。粵桂一方面相互依存、形成犄角之勢,“廣西叛亂,使不得廣東之助,則必不成,惟反之,廣東有不軌行為,使不得廣西之同意,則必不敢動,兩者實有依存之關系在焉”,①《王叔陶呈蔣中正函》(1934 年5 月7 日),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檔案,典藏號002-080101-00033-001。(下文簡稱“蔣檔”,且本文所引蔣檔均源自臺北“國史館”,不再注明)。另一方面又各有政治盤算與利益考量,彼此提防牽制,白崇禧直言“只有自己努力為最可靠”。②《黃旭初日記》,1935年2月20日。待至1934年中央紅軍長征北上,國民黨中央軍以“剿共”為名順勢進入貴州,西南固有的地緣政治格局被打破,“往昔閩有十九路軍,黔有王家烈,滇有龍云,均遙通聲氣,而‘贛匪’復牽制中央,今則不然,情勢全非,‘贛匪’早告肅清,川黔次第底定”,③《關于最近西南情形之報告》(1935年8月30日),國民政府檔案,典藏號001-071100-00003-002,臺北“國史館”藏(本文所引國民政府檔案均源自臺北“國史館”,不再注明)。桂系面臨嚴峻的生存壓力。
廣西僻處邊陲,地方貧瘠,財政來源極為有限,主要依靠禁煙罰金等非稅收入。所謂禁煙罰金,又名煙土稅,廣西地理氣候雖不適宜于鴉片種植,但卻是滇黔煙土運銷廣東及港澳的必經之路,為開拓餉源,廣西設立禁煙監察處,規定凡販運滇黔鴉片入境,無論銷往何處,一律征收禁煙罰金。因滇黔煙土轉桂輸粵數量巨大,禁煙罰金成為桂系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④賀江楓:《財政困局下桂系的生存邏輯(1931—1936)》,《歷史研究》2023年第3期。1935中央軍以“剿共”為名迅速入黔后,王家烈地位朝不保夕,被迫辭去省主席職務,貴州原有的政治格局迅速被打破,桂系感受到來自中央的直接壓力。1935年2月5日蔣伯誠致電蔣介石,建議此后以黔制桂,禁止貴州煙土過境廣西,斷絕桂系經濟命脈。蔣介石對此深表認同,贊許蔣伯誠所陳黔事處置極有見地,但并未直接置桂于死地,而是主張加強中央軍薛岳的勢力,強調“惟目下步驟:第一、應先將薛岳所帶各師之缺額及軍實迅速補充完畢;第二、應趕筑湘黔公路;第三、應加派人員充實薛岳之幕僚,并酌加該部多少活動費,使之隨時有獨力應付環境之能力”。⑤《蔣伯誠致蔣中正電》(1935年2月5日),蔣檔,典藏號002-080200-00205-106。貴州轉向中央,不僅粵桂的生存空間進一步受到擠壓,并且廣西的經濟命脈亦將受制于人。廣西對此憂心忡忡,1935年2月5日財政廳廳長黃鐘岳向黃旭初不無憂慮地談到“貴州之煙土倘受妨礙,不能入桂,則本省之財政必大受影響”。①《黃旭初日記》,1935年2月5日。事態緊急,2月19日李宗仁自廣州返回南寧,召集桂系軍政干部多次會商應對貴州變局,②《黃旭初日記》,1935年2月9日、3月23日。借與蔣商量合作“剿共”之機,爭取貴州實際控制權,進而將經濟命脈掌握在自己手中,就成為桂系最核心的政治訴求之一。
為改變西南長達數年的割據狀態,瓦解粵桂聯盟,蔣介石此時也將交涉重心轉向桂系,強調先桂后粵,以黔制桂,逼桂就范。3月25日,蔣介石飛抵貴陽,致電李宗仁望其赴貴州面談。李宗仁考慮再三,決定派張定璠、劉斐謁蔣。蔣介石為表達合作誠意,決定對桂“以黔省府主席為緩和條件”。③《蔣介石日記》,1935年3月30日,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館藏(下同,不再注明)。3月31日蔣桂雙方會談,蔣表示出與桂合作的意愿,張定璠返邕后,向白崇禧建言“蔣之為人早晚時價不同,此事能從剿共軍事上先合作,亦一機會”。白崇禧與黃旭初考慮再三,決定派人“赴粵報告德鄰(李宗仁——引者注)取決”。④《黃旭初日記》,1935年4月4日。蔣介石為促使桂系態度轉變,決定暫緩對桂實施鴉片禁運。5月12日廣西駐貴陽代表王哲漁拜見新任貴州省主席吳忠信,吳表示黔省決無對桂軍事行動,承諾“至桂省特貨運輸照常辦理”。⑤王文隆主編:《吳忠信日記(1934—1936)》,1935年5月12日,香港:開源書局,2020年,第95頁。多方舉措之下,桂系態度逐步明朗。7月23日,吳忠信派韓德勤赴南寧與桂系會晤,隨后吳從韓德勤處得知“桂方請求將黔、湘兩省之一,歸其綏靖”,甚為興奮,“此等主張余兩月前曾向介公進言,未得要領,此次如能見諸事實,乃大局之幸”,當即致函蔣介石,促其贊成。⑥《吳忠信日記(1934—1936)》,1935年8月6日,第116—117頁。8月22日,李宗仁召集桂系核心成員商討應對時局方案,最終決定“和蔣”辦法:“將全國劃分為若干區,區設政治分會或政務委員會,粵桂黔為一區,將西南政務委員會改組,粵設一綏靖主任,桂黔設一綏靖主任”。⑦《黃旭初日記》,1935年8月22日。8月30日,李宗仁致電吳忠信,將各項訴求悉數開列,建議“最好請兄乘機赴川,與季寬兄(黃紹竑——引者注)向介公共策進行”。⑧《吳忠信致蔣中正電》(1935年8月30日),蔣檔,典藏號002-080200-00457-101。
蔣介石鑒于粵桂立場差異,認為“粵陳利于觀望遷延,李、白利于速轉速決,其立場確亦互異,兩機關存廢問題,尚非彼方必爭之焦點,如能從具體辦法著想,使桂事速先解決,則粵事自較易就范”,⑨《楊永泰擬具意見》(1935年9月6日),蔣檔,典藏號002-080200-00457-155。故而決定滿足桂系訴求,“如能提早實現,更佳,以免夜長夢多”。⑩《黃紹竑致蔣中正電》(1935年9月17日),蔣檔,典藏號002-080200-00457-237。9月20日,黃旭初從黃紹竑處得知,蔣介石已允桂系所請,同時黃紹竑建議李宗仁赴南京參加國民黨五全大會,“德鄰能出席五全代會,于蔣面子較好看”。?《黃旭初日記》,1935年9月20日。此后張定璠又致函黃旭初,告知中央對桂決策內幕,“蔣表示今非昔比,舊賬已算不清,桂若能和,猶增百萬兵云,但蔣對撤退駐黔中央軍一事,表示不能,謂此非對桂,實在控川”。?《黃旭初日記》,1935年9月30日。蔣桂互動日趨頻繁。11月11日,黃旭初與西南方面代表林云陔、劉紀文等共赴南京,14日黃旭初拜見蔣介石,“蔣表示滇黔桂分區事不成問題,雖曾以黔許龍,但總有方法可改”,黃極為興奮,為示誠意,當即“電報德鄰,促其來京”。①《黃旭初日記》,1935年11月14日。孰料李宗仁突然于11月17日致電黃旭初,決定不再赴京,負責與桂系和談的黃紹竑、吳忠信對此頗多責言,“今李忽來電不來,誠令余(吳忠信——引者注)左右為難。黃(黃旭初——引者注)系廣西主席,張(張定璠——引者注)系參謀長,說話尚不算數,廣西前程可想而知矣”。②《吳忠信日記(1934—1936)》,1935年11月18日,第145頁。客觀而言,中央與粵桂畢竟對立長達數年之久,桂系突然因現實利益考量被迫與中央和談,但彼此之間猜忌在所難免。因此,當11月李宗仁拒絕赴京后,蔣桂和談迅即有陷入僵局之危險。
為轉圜局勢,11月26日貴州省主席吳忠信召集桂系赴京代表黃旭初、王季文等人作最后討論,結果決定分頭行動,由吳忠信介紹王季文以私人名義與蔣再次面商,黃旭初回邕向李宗仁報告在京所得各方情況。黃旭初強調“對蔣有硬軟二法,今取軟法,欲巧取之”。③《黃旭初日記》,1935年11月26日;《吳忠信日記(1934—1936)》,1935年11月26日,第147頁。11月29日,吳忠信偕同王季文赴京與蔣會談,王季文向蔣提出桂系內部對時局走向的疑慮:放棄華北,日本是否中止?與日抗戰,以華南為根據地,是否可以持久,倘能持久,是否可得國際之援助及其內部之分化?與此同時,王季文提出和解的五項訴求:一、蔣胡陳李精神合作,對日抗戰;二、在華南秘密指定負責人員,商定對軍事、外交、內政合作方針;三、外交聯歐美,請胡接洽,暫時不必回國;四、分配陳李新任務;五、一中全會新政府之組織問題。④《黃旭初日記》,1935年11月29日。
面對桂系積極和解的態度,蔣介石將計就計,以桂制粵,因此,蔣對于王季文的各項要求,“滿口接納”,29日又請吳忠信轉告李宗仁,無論李此次來京與否,“均將滇黔桂名義發表,惟須想幾句話對付龍云”。⑤《黃旭初日記》,1935年11月29日。為拉攏桂系,蔣介石囑咐宋子文在經濟方面向廣西多所補助,黃旭初乃向宋子文建議:“(一)請準廣西發建設公債,囑滬銀行推銷。(二)中央銀行在桂設分行,其準備金須留桂。(三)中央應補助桂省財政”。⑥《黃旭初日記》,1935年11月30日。顯然中央給予的現實利益,桂系無法拒絕,蔣桂就合作初步達成三種方案:“一、桂方聯絡西南實力派促成統一,改革現在政治制度,改組政府,實行總統制度。二、桂方對粵方軍事積極行動,中央充分接濟桂方。三、桂方消極自保,中央給德鄰西南邊防名義,并物質上之補助”。⑦《桂方聯絡西南實力派促成統一改革》(1935 年11 月30 日),國民政府檔案,典藏號001-071100-00004-023。11月30日,黃旭初決定先回省向李宗仁匯報,如得同意,就通知王季文按照第二種方案,即中央以支持桂系的方式,對粵采取軍事行動,實現統一。諸人特別提醒黃旭初:陳濟棠為絕對反蔣者,“對季文此次行動頗有懷疑”,應特別留意。待黃旭初與李宗仁商洽完畢,“即請德鄰電蔣報告,表示與蔣相晤之地點”。⑧《黃旭初日記》,1935年11月30日。
此時賀龍、蕭克率領的紅軍第二、第六軍團進入貴州,國民黨在黔統治局面危急,1935年12月1日,蔣介石致電吳忠信,令其轉達廣西,希望桂軍能夠在旬日內派十二團兵力,李宗仁當日向駐滬代表黃建平表態全力出兵支持。⑨《李宗仁來電》(1935年12月1日),國民政府檔案,典藏號001-071100-00004-016。桂系“和蔣”謀黔的策略看似已成功在望,但彼此合作的基礎極為薄弱,尤其是蔣介石對于桂系渴求的貴州控制權無從兌現后,伴隨著政治局勢的變化及現實利益的沖突,雙方不可避免的再次走向對立。云南龍云同樣將貴州視為自己的勢力范圍,志在必得,1935年11月20日、21日龍云兩電陳布雷,強調貴州對于云南關系太重,“滇黔名雖兩省,實如一體,如此措施,雖只對黔,而滇亦不啻在內也”,堅決反對桂系主滇。①云南省檔案館編:《國民黨軍追堵紅軍長征檔案史料選編(云南部分)》,北京:檔案出版社,1987年,第604頁。陳布雷亦無可奈何,“滇省對桂系勢力北漸,常用惴惴,誠無兩全之解決策也”。②《陳布雷從政日記(1936)》,1936年1月23日,第17頁。如若云南因此反目,蔣介石以黔制桂、拆分粵桂的計劃也就無從實施。考慮到云南在西南諸省特殊的政治地位,蔣介石決定暫緩公布李宗仁滇黔桂綏靖主任的任命。12月7日,蔣介石召見桂系代表張任民,示意“綏靖名義可稍緩”。③《張任民等致李宗仁、白崇禧電》(1935年12月8日),蔣檔,典藏號002-080101-00034-005。李宗仁對此不置可否,“綏靖區域加滇,原非我方要求,京方既有為難,何不單提黔桂”。④《李宗仁、白崇禧致黃建平等電》(1935年12月8日),蔣檔,典藏號002-080101-00034-005。雙方僵持不下,12月25日王季文與楊永泰再次磋商,楊永泰有意安撫桂系,聲言“蔣自廿一年以后,中心政策志在和平,故不屑以武力解決西南”,王季文則不依不饒,強調“若蔣不承認桂之主張,及放棄以黔為堡壘,作攻桂之準備,是無誠信為國之表示”。⑤《王季文致李宗仁、白崇禧電》(1935年12月26日),蔣檔,典藏號002-080101-00034-006。
龍云鑒于貴州綏靖權遲遲未有定案,頗為介懷,1936年3月3日致電蔣介石,聲言粵桂正謀聯絡云南,共同對抗中央。⑥《龍云致蔣中正電》(1936年3月3日),蔣檔,典藏號002-080200-00469-032。龍云詞語之間重在迫使中央授其滇黔綏靖主任之職。蔣介石反復權衡之后,4月5日決定將貴州綏靖之權授予龍云,吳忠信聞悉此項消息,憤而請辭貴州省省主席,“緣蔣將發表滇龍之滇黔名義,余如不請假離黔,則將來對西南說話更難矣”,⑦《吳忠信日記(1934—1936)》,1936年4月19日,第190頁。蔣介石命令朱紹良繼任。此舉更加劇桂系對中央的惡感,4月28日白崇禧致電黃旭初,“吳忠信決辭黔主席,擬以素來仇我之朱紹良繼任”,鑒于“近日桐梓遵義自川運來軍實甚多,所有公所、學校均已儲滿,蔣決先取滇湘,以為對付西南張本”,主張“我應充分準備,使其知難而退”。⑧《黃旭初日記》,1936年4月28日。
二、被迫鋌而走險
桂系謀求貴州控制權難以實現,但廣西財政狀況在中央對西南不斷的滲透與壓制之下,難以為繼,伴隨著西南政局的變化,“以前元老派極端不愿與中央合作,實力派則愿合作,現則反是,實力派頗不愿合作,而元老派則愿合作”,若元老派“相率入京,西南半獨立局面自可根本解決”,⑨《關于最近西南情形之報告》(1935年8月30日),國民政府檔案,典藏號001-071100-00003-002。兩廣地方實力派與中央的矛盾迅趨激化,試圖以抗日為號召,掀起反蔣運動,進而改變其政治被動的局面。
為收撫廣西,蔣介石強調“對桂應以經濟與建設為重”⑩《蔣介石日記》,1936年2月19日、22日。,鴉片統制成為蔣介石鉗制桂系的有力工具。桂系面對蔣掐斷禁煙罰金的經濟命脈,幾乎無所憑借。廣西省財政極感困難,1936年3月已虧空1000萬元,廣西財政在中央打壓之下難以為繼。①《黃旭初日記》,1936年3月31日。雪上加霜的是,胡漢民等元老派面對蔣介石的拉攏,政治態度游移,“以前元老派尚希望西南局面有發展可能,至相當時期,取中央而代之,惟時至今日,知實力派志在利用元老為招牌,鞏固現有地盤,且于元老禮貌日衰,始唐紹儀之被逐,繼蕭佛成因受打擊離粵,最近胡漢民亦以不得志而去國,再三思維,故胡氏確有入京之意”。②《關于最近西南情形之報告》(1935年8月30日),國民政府檔案,典藏號001-071100-00003-002。1936年1月胡漢民自歐洲回國,16日李宗仁得知蔣介石極力拉攏胡赴京,斥責南京此舉猶如釜底抽薪,陳濟棠經李宗仁游說,決心挽留胡漢民,“罕有的親自前往香港迎接胡漢民,并將廣州八十幾個團體代表前往香港,發動了聲勢浩大的迎胡運動。胡來到廣州,街頭巷尾都懸掛著歡迎最賢明的革命領袖胡展堂先生的橫幅,這讓胡非常快慰”。③《西南三派ト反蔣運動(未定稿)》,1936年3月,帝國ノ対支外交政策関係一件,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2030162800。然而陳濟棠見胡漢民留粵,危機已解,態度又趨消極,2月10日胡漢民請王公度轉告白崇禧,“甚望劍生(白崇禧——引者注)到粵晤商”,④《黃旭初日記》,1936年2月10日。試圖聯桂以制陳。
客觀而言,西南三派雖均聲稱反對南京政府,但訴求卻各有不同,令李宗仁意想不到的是,陳濟棠同樣因地緣政治與現實利益的沖突,與中央關系愈發惡化。首先,廣東1935年幣制改革后,因投放紙幣過多,“導致港幣與廣州法幣的比值,從港幣100元等于廣州法幣141元,增至港幣100元等于廣州法幣155元”。⑤廣東省檔案館編:《民國廣州要聞錄》第二十冊,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83、195頁。收兌的大量銀元又遭中央抵制無從換取外匯,廣東金融秩序迅即陷入紊亂,“廣東金融問題,中央不特不予幫助,財部反多所為難,例如粵省擬以二千萬現洋購買港幣,財部亦囑匯豐銀行拒絕,粵省擬以洋米稅擔保向銀行借款,財部亦不允許”。⑥《楊德昭陳述陳濟棠對中央懷疑之點及意見》(1936 年6 月),國民政府檔案,典藏號001-071100-00004-015。其次,陳濟棠因福建綏靖權問題與蔣介石糾葛不斷。1936年3月,陳濟棠的胞弟陳維周曾親赴南京晤蔣,蔣試圖以福建為餌,誘使粵系合謀伐桂。李宗仁在回憶錄中也曾特別提及陳維周探悉蔣解決西南的三大原則:中央協助廣東出兵解決廣西李白、驅逐元老派、廣東維持原來局面。陳濟棠深知兩廣合作的重要,“中央既可授意廣東解決廣西,又何嘗不可反其道而行之?”認為這是陳濟棠發動六一事變最主要的動機。⑦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496—497頁。李宗仁所言雖道出蔣、陳矛盾焦點所在,但對陳濟棠態度反轉有所隱瞞。事實上,作為慣用手法,蔣介石違背前言,將福建綏靖權轉授予他人,任命張發奎為閩贛浙皖四省邊區“剿匪”總司令,當張發奎被任命為四省剿匪總司令入閩時,陳看到這一點,懷疑蔣介石沒有對日行動的計劃,卻打算對粵行動”。⑧《西南三派ト反蔣運動(未定稿)》,1936年3月,帝國ノ対支外交政策関係一件,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2030162800。
粵桂與中央因派系糾葛、經濟利益、地緣政治多重因素交互疊加,矛盾迅速激化。即如日方觀察:“胡漢民不顧中央殷切的勸請,回到廣州而并未入京,值此之際,粵漢、廣九兩鐵路聯絡問題、粵漢鐵路開通后的護路軍警及鐵路收入問題以及廣東拒絕在省內使用中央法幣和中央新鑄輔幣等問題接連出現,在軍、政、黨各方面的問題上雙方觀點相左,相持不下,這加劇了中央和兩廣之間關系的不穩定”,“中央與兩廣之間已處于一觸即發的狀態”,①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昭和期II第2部第5巻下,外務省,2008,頁1110-1111。兩廣掀起反蔣旗幟已勢所必然。2月26日陳濟棠向來廣州訪問的日本陸軍大將松井石根信誓旦旦地表示:“自1931年以來他一直試圖與蔣謀求妥協,到最后終于不能相互容忍,于是有了如今兩廣聯合,決意反蔣的狀況”。②《松井石根日記》,1936年2月26日,支那事変日誌回想305,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雖然陳濟棠與李宗仁、白崇禧因現實利益均欲反蔣,但粵桂在反蔣的方式、時間等問題上卻有較大分歧。陳濟棠認為如若反蔣,“除依靠兩廣的力量之外,別無他法”;李、白則要樂觀地多,主張兩廣與各方反蔣力量密切合作,兩廣的軍事、財政、經濟、交通實施一體化戰略,重點開展和英法等列強的良好外交關系。總之,“粵桂迅速聯合起來,形成反蔣抗日的核心”。然而陳濟棠審慎小心的性格,加以對李白的猜忌,使得雙方遲遲難以達成共識。
然而陳濟棠也有欲罷不能的現實考量,尤其是眾多粵系軍政官員為維護自身利益,亟愿維持割據自保的局面,“以為如果合作實現,則粵省黨政軍財等權必須交還中央,完成統一,而不能如前之任意支配,取舍由己,故仍戀戀,欲割據謀得分立之利”。③《關于最近西南情形之報告》(1935年8月30日),國民政府檔案,典藏號001-071100-00003-002。胡漢民更是積極鼓動陳濟棠盡速起事,“胡在廣州聯絡李白,并從事挑撥,其語各師長謂:伯南(陳濟棠——引者注)太老實無用,將來必上當,本人從前如何忠于蔣,結果仍不見容”。④《陳立夫致蔣中正電》(1936年3月26日),蔣檔,典藏號002-080200-00264-135。1936年3月19日李宗仁致電白崇禧,望其迅速趕赴廣州,強調此乃陳濟棠催促,共商反蔣計劃。鑒于過往陳濟棠舉事多系虎頭蛇尾,“明則利用其御用機關,大聲疾呼,甚或痛哭流涕,謂彼救國而人賣國,彼系真革命者而人系反革命者,以期博得國人同情,暗則召集將領開會謂中央如何如何將有事于西南,復密遣使節前往魯冀滇湘聯絡,以張大其聲勢,而脅中央,期在此種運用之下,使給予滿意之利益”。⑤《關于最近西南情形之報告》,(1935年8月30日),國民政府檔案,典藏號001-071100-00003-002。白崇禧等人多不以為意,未及數日,李宗仁又致函白崇禧,強調此次“伯南積極,欲以非法憲法為題倒蔣”,黃旭初直言“真覺可笑”。⑥《黃旭初日記》,1936年3月25日。4月17日,李宗仁再度向白崇禧表示“陳伯南確欲積極”,但桂系諸要員仍舊堅持己見,“我們皆以為未必”。5月9日,白崇禧、黃旭初等人共同研判陳濟棠反蔣決心問題,經過數日討論,桂系最終決定“應付時局之辦法,決先作思想戰”。⑦《黃旭初日記》,1936年4月17日、5月12日。與此同時,為預備起事,5月8日白崇禧與日本陸軍溝通,采購大批軍火,“鑒于當前局勢,首先,契約好的第一批野、山炮各四門、相應彈藥及教官,應努力在二個月后交付派遣;而第二次之后的野、山炮的預定發放日期也要明示;廣西軍隊的訓練及作戰計劃的決定,正在等待日本陸軍中央對上述野、山炮問題的答復”,至于貨款,日方答允易貨貿易,以桐油支付。⑧《白崇禧に兵器拂下の件》,1936 年5 月8 日,陸満密大日記,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1003124700。
歷史的演進總是充滿偶然性,5月12日胡漢民突發腦溢血去世,粵桂頓失憑借,與中央對峙數年之久的西南政局面臨嚴峻挑戰,此前負責與桂和談的吳忠信自信西南“已失主持中心,統一之局可望促成”。①《吳忠信日記(1934—1936)》,1936年5月29日,第201頁。5月14日,白崇禧、黃旭初等桂系要員以吊唁為名紛紛致穗,當天先后與陳濟棠、陳維周商談應付時局辦法,“其兄弟均甚固執”,雙方并未達成一致意見。16日,白崇禧再邀請粵系將領余漢謀、繆培南、張達,商討反蔣事宜。②《黃旭初日記》,1936年5月14日、15日、16日。5月20日,李宗仁亦從桂林飛粵,粵桂實力派人物齊聚廣州,蔣介石感到局勢緊張:“李白皆聚粵會議,對中央之方針,其必謀反抗,中央之計劃不能不預為之備”。③《蔣介石日記》,1936年5月21日。粵桂合謀再度反蔣已箭在弦上,兩廣事變的爆發只在朝夕之間。
三、和戰兩難
陳濟棠再起反蔣之心,但瞻前顧后、猶豫再三,桂系半信半疑,恰逢胡漢民突然離世,在李、白策動之下,最終粵桂合謀,以北上抗日為名掀起兩廣事變,然而此后日本態度強硬,各地方實力派亦未隨風而動,粵桂漸處和戰兩難境地,直至余漢謀倒向中央,粵局分崩離析,桂系意欲再度和蔣亦不可得。
就在胡漢民去世的同時,云南龍云、湖南何鍵態度曖昧,意欲相機而動。1936年3月,陳濟棠、李宗仁派遣代表張振毆、王乃昌赴滇,“商訂反對中央,及軍事攻守同盟計劃”,④《顧祝同致蔣中正電》(1936年4月8日),蔣檔,典藏號002-080200-00470-065。龍云語意模棱兩可。此后龍云突然明朗,5月28日,黃旭初獲悉龍云將與粵桂合作。至于何鍵,面對中央在湖南勢力的不斷拓展以及兩廣的策動,認為“料中央不敢對兩廣作戰(因兩廣用抗日招牌),希望保持均勢,借中自重”,⑤《陳誠與何健談話記錄》(1936年6月10日),蔣檔,典藏號002-080101-00035-006。并且湖南財政也因國民政府鴉片統制政策損失頗巨,根據此前蔣介石與何鍵達成的協議,“湘滇黔特貨稅款內分撥半數,并以湘產特稅全部歸湘,每月約可收入三十萬元,以之補助,尚虞不足,現因湘省為絕對禁種區域,湘產特稅無形消減,所恃滇黔經湘統撥半數又因稅率增高,來源驟減,實不足以維持”,⑥《內政部咨送黔貨內銷特貨稅各項辦法及有關文書》,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內政部檔案,檔案號:十二(1)/1048。故而向粵桂代表劉斐、陳維周聲言全力配合兩廣出兵⑦有關何鍵態度的演變過程,可參見肖自力的相關研究,本文僅側重展現桂系聯絡何鍵的動態過程。,雙方達成合作協議。而此時日軍又增兵華北,挑起事端,“逼宋與中央脫離關系,否則請其離開冀察”,⑧“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徐永昌日記》第三冊,1936 年5 月25 日,臺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第428—429頁。蔣介石倍感壓力,在兩廣看來,日軍有事于華北,正可借機掀起反蔣大旗。而日本此時對西南的策略重在擴展在兩廣的經濟權益,同時努力促使西南成為親日地方勢力,利用西南與南京的對立關系,來迫使國民政府改變對日政策,⑨《西南排日態度に関する件》,1936 年7 月7 日,陸満密大日記,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1003163400。尤其對于桂系極力拉攏。為避免胡漢民去世后,西南局勢崩塌,日本駐廣州領事館武官臼田寬三積極鼓動粵桂合作反蔣,強調機不可失,日本外務省官員石射豬太郎事后聞悉內幕,感嘆真令人意外。⑩伊藤隆、劉傑編:『石射豬太郎日記』,1936年6月9日,東京:中央公論社,1993年,頁75。
桂系抓緊策動陳濟棠反蔣,5月28日,白崇禧向陳濟棠羅列中央對西南生存空間的種種擠壓,強調非倒蔣無以挽救時局,桂系態度始終堅決,“伯南稍為之動,但猶豫不決”。①《香港來儉午電》(1936年5月28日),國民政府檔案,典藏號001-071100-00004-004。5月30日,白崇禧再度與陳濟棠會商,白咄咄逼人,如若“粵不開府,可在桂開,請李任潮領導兩粵,擔任財政”。陳思考再三,坦言目前所處困境,內部分反中央、服從中央兩派,在此情形之下,如若不反蔣起事,恐終將瓦解。此時廣東因財政金融問題,已呈混亂之象,“粵白銀中央不受,又不能沽與英美,其炮械商又催款,昨轉與日商接洽,儉港三井大班來省斡旋購銀事,刻在磋商中”,并且毫券急劇貶值,“粵軍官大購港紙及中交兩行大洋券,日來港紙及中交券價飛漲,面加六四,市面紛擾,人心浮動,流言四起”,②《香港來世電》(1936年5月31日),國民政府檔案,典藏號001-071100-00004-004。最終陳濟棠下定決心與桂共同舉事,向白崇禧表示“我非不愿倒蔣,但我內部意見未一致,不能不審慎將事,盼從詳計劃,粵桂決不分手”。③《香港來世電》(1936年5月31日),國民政府檔案,典藏號001-071100-00004-004。至此,兩廣就合作反蔣已完全達成共識,當天白崇禧返回南寧,向部屬斬釘截鐵的表示:“解決時局辦法在真抗日!”④《黃旭初日記》,1936年5月30日。
對于兩廣事變爆發的經過,陳濟棠、白崇禧在回憶錄中,諱莫如深,閉口不談,李宗仁則將責任全部推向陳濟棠,“陳濟棠意志堅決,勢在必行,無法挽回。然兩廣原屬一體,廣東一旦發動,廣西方面不論愿與不愿,也必被拖下水,廣西如果毅然參加,或許對陳濟棠的行動尚能有所糾正”。⑤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第498—499頁。廣西軍政要員劉斐認為桂系可謂兩廣事變主導者,“桂系則極力主張趁此時機反蔣,這時,陳濟棠若不共同反蔣,就會陷于孤立地位。他感到與其坐以待亡,不如和桂系一起反蔣,以便進可以爭取全國輿論的同情,擴大西南聲勢,進一步瓜分蔣介石的政權,退可以使蔣投鼠忌器,多少向西南讓點步,以便維持西南現狀”。⑥廣州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南天歲月——陳濟棠主粵時期見聞實錄》,廣州:廣州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63頁。事實上,無論是粵系主導,抑或桂系策動,均與史實有所距離。兩廣聯合反蔣初始是由陳濟棠主動提出,恰逢蔣桂矛盾激化,粵桂一拍即合,孰料此后陳濟棠態度猶豫、胡漢民去世,桂系感到非反蔣無以自存,再三鼓動,最終兩廣事變爆發。
1936年6月4日,白崇禧連致何鍵三電,首電希望湖南迅速響應,“否則我粵桂部隊接近長沙,湘省之榮譽頓減,且將蒙漢奸賣國之名”,強調桂軍已整裝待發,桂軍蘇祖馨部“秦團歌(5日)到黃沙河,主力繼進”;⑦《白崇禧致何鍵電》(1936年6月4日),國民政府檔案,典藏號001-071100-00004-002。次電詢問外間傳言是否屬實,“湘如不即表示,及努力公開宣傳,湘人對我誤會滋多,究竟如何,盼即明示”;⑧《白崇禧致何鍵支申電》(1936年6月4日),國民政府檔案,典藏號001-071100-00004-002。隨后白又向何鼓勁,主張應政治為主、軍事為輔,并將廣西民眾運動辦法告知,強調以抗日為名必然占據道義制高點,“有敢犯大不韙,反對或摧殘此種行動者,即為漢奸,為賣國,謅必為全國所共棄,我實立于不敗之地”,保證桂軍將按計劃行事,“此間部隊先頭本日已到黃沙河,趕到衡州,不誤”。⑨《白崇禧致何鍵支辰電》(1936年6月4日),國民政府檔案,典藏號001-071100-00004-002。
黃旭初自感近日桂系對何鍵之推動“煞費力氣”,6月5日何鍵代表李覺赴滇過邕,桂系得知“何顧忌甚多,實不敢聯絡粵桂,一齊發動”,鑒于“湘能動則影響最大”,6月6日桂系乃派軍事將領李品仙飛赴長沙,當面督促何鍵配合兩廣軍隊軍事行動。①《黃旭初日記》,1936年6月6日。與此同時,中央亦不斷向何鍵施加壓力,何鍵首鼠兩端,態度模棱兩可,對中央軍羅霖部“不愿開衡州,以免沖突”②《陳誠與何健談話記錄》(1936年6月10日),蔣檔,典藏號002-080101-00035-006。,又向李品仙表示“非俟我方兵到長沙,不肯明白宣布與西南一致”。③《黃旭初日記》,1936年6月9日。同時,何鍵致電龍云,試探云南態度,“湘處境困難,較甚他省,素仰老成謀國,乞示周行”。而龍云亦未如桂系所愿,主張“滇黔方面,暫事緘默”,并于6月9日建議滇湘一致行動,“愚見以為蕓樵(何健——引者注)如輕易牽就,愈致擴大,實中日人以華制華之計策,故縱有困難,亦應以國家為前提,以正義為依歸”。④云南省檔案館編:《國民黨軍追堵紅軍長征檔案史料選編(云南部分)》,第606—608頁。最終羅霖率中央軍一營抵達衡陽,占取先機,何鍵態度迅即明朗,完全倒向中央,黃旭初感嘆“我對湘推動之計劃遂完全失敗!”⑤《黃旭初日記》,1936年6月9日。兩廣期待的滇湘響應的局面,并未出現,6月10日桂系被迫中止派兵北上的計劃,“今到祁陽大營市之我軍停止前進,并宣傳中國軍隊不打中國軍隊”。⑥《黃旭初日記》,1936年6月10日。
更令兩廣感到意外的是,日本態度的急劇轉變。日軍華南策略本就重在以兩廣問題為要挾,迫使國民政府讓渡更多政治經濟權益,張群事后曾向蔣介石坦言,日方“主要目的似在實現華北政策,如對彼華北要求無相當妥協余地以資緩和,彼必乘粵事初定、桂局尚懸,中央尚多顧慮之際,加我以重大壓迫”;⑦《張群致蔣中正電》,1936年7月23日,蔣檔,典藏號002-090200-00018-079。此時日本正謀求與國民政府就國交調整展開談判,冀圖以“中日經濟提攜”為名,全面加強對華北的滲透與蠶食。面對華南日軍武官的策動,日本政府既不欲投入過多精力,更不希望對整體侵華政策形成阻礙。日本外務省認為兩廣事變是粵桂地方實力派利用國內日趨高漲的抗日情緒,以抗日為名掀起反蔣運動。如果成功,就徹底打倒蔣介石,倘若失敗,則借機尋求更為有利的條件與南京妥協。⑧伊藤隆、劉傑編:『石射豬太郎日記』,1936年6月9日,頁75。6月13日,日本駐廣州領事河相達夫正式向陳濟棠提出抗議,“西南當局的抗日是進行內爭的手段,對日本的國家名譽有所損毀,我方斷不能坐視不理,必須迅速停止抗日宣傳,鎮撫民眾的抗日運動”,同時河相亦警告李宗仁,勿以抗日為由掀起民眾運動,李當即表示接受,聲言目前轉變比較困難,“我方將逐次轉換”。⑨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昭和期II巻第2部第5巻下,頁1117—1118。
此后日本判斷兩廣局勢難以維持,“陳濟棠并未進軍,廣西勢力內部出現了反對征兵的動亂,中央逐漸集中兵力于湖南,廣西將全面崩潰”,⑩伊藤隆、劉傑編:『石射豬太郎日記』,1936年6月13、14日,頁77—79。日本陸軍態度逐漸明朗,直言“西南方面誤認為,高喊打倒蔣介石就可以對帝國的善意予取予求。其以抗日為名向南京方面發出通電,對帝國官員的抗議以不遜的態度回應,若擴散開來,將會有重燃全中國民眾抗日運動的風險,與帝國的期望背道而馳”,日本“有必要在此時以更進一步的強硬態度,以求西南方面反省”。?《西南排日態度に関する件》,1936 年7 月7 日,陸満密大日記,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1003163400。粵桂本擬按照福建事變時期十九路軍另立政府的做法,陳濟棠在日本壓力之下態度猶疑,計劃被迫暫緩。①《黃旭初日記》,1936年6月10日。此外,英國態度亦令兩廣大失所望,6月10日陳濟棠曾派代表前往香港,尋求英方援助,希望香港與廣東能夠本著自由開放的精神密切合作,建議談判盡速開始,并且香港殖民政府應鼓勵英國銀行向廣東提供兩千萬港幣的借款,避免因廣東金融秩序紊亂影響到他們自身的利益。②“Situation in China:proposed Cooperation between Canton and HongKong”,July 15,1936,FO371,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UK.然而,英國駐華使館為維護在華南利益,強調任何支持西南政權的行為都將使得英國被迫卷入與日本或者南京國民政府的糾紛,提示英國企業目前與兩廣進行經濟或商業上的往來都將是危險的行為。③“Sir H.Knatchbull-Hugessen to Mr.Eden”,September 18,1936,Ann Trotter editer,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Series E,Asia,1914-1939,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1996,p.288.
桂系仍舊寄望于華北宋哲元、韓復榘的響應,6月14日白崇禧派張任民赴廣州,向李宗仁轉達意見,“促宋韓抗日事公開發表”。④《黃旭初日記》,1936年6月14日、17日。然而韓、宋處于中央與日本夾縫之下,對于兩廣更多是虛言應付,徐永昌即有此種看法,“西南既各方拉攏,此亦敷衍而已”。⑤《徐永昌日記》第三冊,1936年6月22日,第436—437頁。兩廣卻因日漸陷入困境之中。首先,陳濟棠態度發生變化,派遣楊德昭密赴南京,向蔣轉達意見,“渠自信為在廣東擁護中央最忠誠之一人,除渠而外,恐另無他人,中央如有辦法,渠可使桂省就范”。⑥《楊德昭陳述陳濟棠對中央懷疑之點及意見》(1936 年6 月),國民政府檔案,典藏號001-071100-00004-015。桂系聞悉陳派人與寧方接洽,對陳頗多懷疑,“其決心如何,殊可顧慮,其人非講理智者,極難共事”。⑦《黃旭初日記》,1936年6月17日。其次,粵桂經濟秩序、軍事物資在中央封鎖之下愈發難以為繼。蔣指示孔祥熙“廣東向中華書局訂印之鈔幣,應即令該局停止印刷,并將其已印之鈔券截留為要”。⑧葉健青編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37冊,臺北:“國史館”,2009年,第210頁。廣西物資供應極度匱乏。多重壓力之下,與南京握手言和再次成為桂系的選項。
1936年6月23日,滇系要員胡郁蓀向重慶市長李宏錕私下談及:“健生馬電有悔意,望滇出任調停。伯南有副總統欲,與桂異夢。滇尚待時再作調人也”。⑨重慶市檔案館編:《兩廣六一事變后蔣介石與李宗仁等來往函電》,《歷史檔案》1987年第4期,第75頁。桂系急不可耐,希望能夠通過談判維持事變前之狀態,6月27日正式邀請盧燾,致電滇系將領李雁賓,“促龍云速發起調解”。⑩《黃旭初日記》,1936年6月27日。蔣介石對此頗為介懷,“滇龍似有挾兩廣以自重之心,乃欲以調人自居”,?《蔣介石日記》,1936年6月29日。對此置之不理。7月8日,白崇禧又致電黃紹竑,態度軟化,強調“一切當可詳商也”。?《白崇禧致黃紹竑電》(1936年7月8日),國民政府檔案,典藏號001-071100-00004-006。局勢發展顯然超出桂系判斷,7月9日余漢謀率部倒向中央,蔣介石態度強硬,7月10日命令桂系代表張定璠轉告桂方,“白崇禧應接受中央命令”。?葉健青編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37冊,第399頁。和戰之間,如何抉擇,顯然桂系已無更多可供猶豫的空間。
四、蔣桂握手言和
余漢謀倒戈,廣東局勢極度緊張,唇亡齒寒,粵危桂亦不保,7月10日黃旭初偕同劉斐前往廣州,當晚陳濟棠召集文武干部會商應對辦法,聽取劉斐“對于時局之分析及今后我應采取之方策”,陳雖原則采納,但已無實行之勇氣,“因陳掌握部隊已無信心”。次日,黃旭初再度與陳討論,最終決定“先組織第一、四集團聯軍總司令部及粵軍取內線作戰兩事”,同時粵桂就經濟合作達成一致意見,“(一)粵桂鈔票彼此收稅互相收受。(二)桂對粵匯款,粵行盡量接受,但須以一部現金作抵押”。7月13日,黃旭初返回南寧,當晚與白崇禧等再度商洽,仍不安心,乃決定次日再派李品仙至粵,以便促使“陳濟棠將可靠之軍隊集結掌握,速將現銀子彈運存西江,并詢其要我相助之兵力”。①《黃旭初日記》,1936年7月10日、11日、12日、13日。
未雨綢繆起見,桂系開始籌謀另辟局面,因李宗仁、白崇禧在國民黨內政治資歷、威望尚淺,為使得舉事更具合法性,二人遂把目光轉向北伐時期的重要將領李濟深,“不特李、白對之有深切之默契,即廣西一般將領對之亦有濃厚之感情”。②《王叔陶呈蔣中正函》(1934年5月7日),蔣檔,典藏號002-080101-00033-001。事實上,兩廣事變爆發前,李宗仁就曾與李濟深密商共同反蔣。1936年初李濟深曾派代表密赴莫斯科,與共產國際中國代表團商討建立抗日統一戰線的事宜,5月9日李濟深在致中共地下黨員胡鄂公的信函中,特別談到力促桂系聯蘇聯共,“弟擬日間再去密電一詢,催其究竟,想先生亦同意也,或者他尚須與白一商,故去電一并使白同商,或有較確實消息也”。③《李濟深致胡鄂公函》(1936年5月9日),西泠印社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重要文物——胡鄂公上款名人書札專場》,印刷品,2017年,第1933頁。兩廣事變爆發后,各國列強多持反對態度,而兩廣在中央封鎖打壓下,陷入多重困境,6月21日李任仁奉白崇禧指示再度拜見李濟深,向其表達了聯蘇聯共的意向與決心,“并盼此事急成,且如不能整個西南辦,必欲單獨先辦”,希望李濟深能夠負責此事。李濟深對桂系政治立場轉變頗為自信,希望胡鄂公迅速將情況轉告中共。④《李濟深致胡鄂公函》(1936年5月9日)、《李濟深致胡鄂公函》(1936年6月21日),西泠印社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重要文物——胡鄂公上款名人書札專場》,第1933、1934頁。6月26日,李濟深親赴南寧與桂系商討聯蘇聯共事宜。⑤《黃旭初日記》,1936年6月26日。30日,李濟深告知胡鄂公,“健生先生之意甚決,粵方究如何?弟意如一時無望,吾人或先從一方進行,以應時機”⑥《李濟深致胡鄂公函》(1936年6月30日),西泠印社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重要文物——胡鄂公上款名人書札專場》,第1935頁。7月9日余漢謀倒戈,局勢緊張,次日黃旭初赴粵途中,赴梧州與李濟深會晤,提出此后兩種應付時局辦法,“(甲)粵能自固,不至一時崩潰凈盡,并贊成組織政府,則目前難關較易渡過。(乙)如粵已無可救藥,則吾桂須單獨堅持,奮斗到底,此兩案均須請公為主持”。黃旭初希望李濟深能夠“擔任各黨各派之聯絡及國際路線之運用,及組府人選之準備”。⑦《黃旭初日記》,1936年7月13日。中共對于桂系急謀合作的動機亦有清醒認知,7月1日潘漢年向共產國際的報告,強調當前“陳濟棠、李宗仁和白崇禧都希望同我進行談判,但是眼下未必能達成具體的協議,因為他們都希望弄清楚有關蘇聯援助的可能性問題”。①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31—1937)》第15冊,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年,第220頁。
局勢進展迅速,7月16日,蔣介石命令余漢謀率三十六個團的兵力南下。韶關被余漢謀占領后,廣東浮動,白崇禧鼓動陳濟棠全力抵抗,“應以財以官以地盤,背城借一,否則一切皆他人所有,何所愛惜耶”,然而粵軍毫無斗志,②《黃旭初日記》,1936年7月15日、16日、17日。7月18日廣東海陸空軍皆倒向中央,陳濟棠宣布下野赴港,中央終獲得廣東的控制權。吳忠信興奮地表示“粵局底定之后,中國政治軍事已臻統一,此為多年來求之未達者”。③《吳忠信日記(1934—1936)》,1936年7月18日,第215頁。李宗仁此時感到廣西勢孤,決定與蔣言和,與李濟深合作的聯共之議遂被束之高閣。至于就任廣西綏靖正副主任與否,李、白再三考慮后,7月23日致電蔣介石,表示接受任命。然而南京內部主張趁機解決廣西者不乏其人,7月20日楊永泰向蔣建言:“粵事大體已告一段落,桂事似宜一氣呵成,軍事封鎖與政略分解,應同時并進,連日與季寬兄商討,認為德鄰絕難覺悟,只可側重健生用功,同時應準備健生亦不就范之釜底抽薪工作,為減輕桂民痛苦計,季寬頗愿挺身效勞,親赴廣州,就近運用,似季寬亦較有相當把握”。④《楊永泰致蔣中正電》(1936年7月20日),蔣檔,典藏號002-080200-00474-098。蔣介石亦有此意,7月25日更換任命,改調李宗仁為軍委會常委、白崇禧為浙江主席,調黃紹竑、李品仙為廣西綏靖正副主任,意圖激怒李白,黃旭初直斥此乃對桂用兵之張本。
李宗仁、白崇禧此時“對新職決不就,逼不得已,惟有一戰,否則固守,以待時勢之變化”,⑤云南省檔案館編:《國民黨軍追堵紅軍長征檔案史料選編(云南部分)》,第613頁。決定重啟與李濟深的合作。7月26日李、白邀請李濟深、原十九路軍將領蔡廷鍇等人到邕,并召集桂系將領夏威、廖磊等共同研討此后做法,決定成立抗日政府,并宣言桂省自治,脫離南京國民政府。⑥《黃旭初日記》,1936年7月26日。為壯大聲勢,桂系積極與國內各地方實力派聯絡。此時,張學良與中共在陜北已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達成共識,雙方形成事實上的合作關系,1936年7月張學良派中校參謀解如川(解方)去廣西,7月31日解如川與李、白等人會晤,表示“東北軍團體甚堅,且有解等前進分子在內領導,甚望彼此互促中國局勢之改觀”,雙方一拍即合。⑦《黃旭初日記》,1936年7月31日。隨后桂系派遣代表李寶璉前往陜西與張學良展開溝通,8月19日李報告“張學良對抗日意志極堅,決惟須一月后布置方就緒”。此外,四川態度亦甚積極,蓋其認為“響應兩廣,壯其聲勢,若不然,兩廣失敗,四川更無法對付蔣”。⑧全國政協文史資料文員會編:《機詐權變:蔣介石與各派系軍閥爭斗內幕》,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1年,第127頁。8月19日,劉湘開始與桂系直接秘密通電。雙方一致同意由川湘按照預定計劃攻取貴州,但劉湘不贊成聯蘇,只言倒蔣。與此同時,桂系加緊籌劃組建抗日政府,曾連續數日討論政治組織各法案,各方意見分歧。⑨《黃旭初日記》,1936年8月10日、19日、21日。8月16日夏威“以久不見決心行動,特由桂來催促”,最終當晚“即有決定”,桂系與各派反蔣人士達成共識。⑩《黃旭初日記》,1936年8月16日。
1936年8月23日,桂系致電張學良、劉湘,迅速聯合公開反蔣,8月24日李濟深、李宗仁、李任仁、黃旭初等人討論臨時政治組織名稱,“結果決定將委員會或臨時政府兩案電張學良、劉湘征詢意見,再行決定,并指定十一人起草國民抗日公約”。25日,李、白再電劉湘,促請發表聯合通電。然而最后時刻,張學良、劉湘態度猶疑,27日李寶璉自陜西返桂,“張漢卿口頭說必抗日,但發動須在一月后至三個月之間,以便作運用各方之準備,但如果西南倒蔣,則彼不參加,亦不反對,蔣對彼以馬氏回子監視之,其左右尚多藍衣社分子,其餉糈仍仰蔣之施與,內部矛盾不少”,28日桂系得知劉湘亦不愿公開出面。桂系密謀與川湘、東北軍合作組建抗日政府的計劃遂告流產,事實上即便黃旭初對組織聯合政府亦不看好,直言“國民救國綱領初讀其內容,僅系集合各方之主張,多不切實際”。①《黃旭初日記》,1936年8月23日、24日、25日、28日、29日。同時,廣西社會經濟秩序在南京政府的封鎖圍困之下,已呈朝不保夕之勢。為解決廣西問題,蔣介石命令陳誠迅速展開軍事部署,形成對桂大兵壓境之勢后,禁煙罰金徹底斷絕,并且廣西金融秩序亦呈紊亂狀態。南京政府更是利用外交、軍事等手段徹底隔絕廣西與外界的物資聯絡。廣西財政、經濟物資本就貧瘠,嚴密打壓之下,獨木難支,謀求各方響應,又功敗垂成,面對南京的政治攻勢,唯有就范之一途,誠如龍云所言:“桂甚倔強,未肯甘心,唯其經濟甚感困難,民怨沸騰,結果恐未必佳良”。②云南省檔案館編:《國民黨軍追堵紅軍長征檔案史料選編(云南部分)》,第614頁。
桂系與中央形成劍拔弩張之勢的同時,雙方之間私下仍舊信使往還。8月30日居正、程潛、朱培德、陳誠均致電桂系,希望來邕促成和談,李宗仁當即復電表示歡迎。③《黃旭初日記》,1936年8月30日。黃紹竑亦來電勸告李白,“你們此次之立場面子風頭皆十足,得好休時便罷休”。9月3日李宗仁、白崇禧、黃旭初等桂系要員就和戰問題徹夜商談,鑒于當前廣西經濟、政治的實際困難,決議言和。9月4日李宗仁再度召集白崇禧等人就和談條件磋商,最終決定廣西黨政依舊;中央向桂系提供巨額財政補貼,軍隊撤退至相當地點后,即通電就新職。9月4日,居正等人返回廣州,將桂系條件轉告于蔣介石,蔣當即應允,和談遂即達成,與中央對立數年的西南政權亦告終結。桂系作為獨立的地方政治勢力仍舊得以保存,陳誠對此頗多異議,抱怨“此次桂事曲折太多,徒耗精神財力,仍未徹底”。④《陳布雷從政日記(1936)》,1936年9月7日,第181頁。
余 論
1935年蔣介石成功改造貴州政局之后,桂系從地緣政治與現實利益的角度考慮,均面臨南京國民政府的嚴重擠壓。為改變被動局面,桂系試圖以臣服中央為代價,換取貴州的控制權。然而在龍云干預下,桂系爭取貴州綏靖權最終功敗垂成,廣西經濟陷入困境,加以中央對胡漢民的爭取,使得桂系愈感局勢危急。陳濟棠也因地緣政治與現實利益問題,再起反蔣之心。胡漢民突然逝世后,桂系以此為契機,對陳多所策動,最終粵桂合謀共同反蔣。兩廣事變爆發后,日本強烈反對,加以粵桂之間彼此猜忌,桂系為保存實力,試探與李濟深合作,尋求新的外援。但是余漢謀倒戈后,粵系土崩瓦解,李宗仁、白崇禧本欲與中央和解。蔣介石為徹底解決兩廣,故意撤換李、白二人。進退維谷之間,桂系再度與李濟深共商組織抗日政府事宜,意圖另立局面。但是廣西社會經濟在中央封鎖之下難以為繼,各方又毫無響應,最終桂系被迫接受和談,與南京國民政府分立數年的局面亦告終結。通過考察桂系與兩廣六一事變的復雜關系,可清晰窺知1930年代中國地方社會的復雜面相與各種政治潛流。
桂系作為國民黨統治時期持續時間最久、影響極為廣泛的地方政治勢力,一方面它與何鍵、閻錫山等其他地方實力派類似,擁有諸多政治共性,地盤與軍隊成為其關注的核心,為維持存在、保存實力,往往游走于各方政治勢力之間,政治態度具有較大的投機性與多變性。但另一方面桂系面對復雜的民國政治形勢與嚴峻的外在挑戰,之所以能夠長期屹立不倒,乃至數次對蔣介石權威形成嚴重挑戰,仍有其不同于其他地方實力派的諸多鮮明特質:一、桂系不愿偏居一隅,有更強的問鼎中央權力的意愿與政治行動能力,不僅兩廣事變期間桂系聯合各方力量意欲另組政府,并且1936年9月蔣桂和談初成,26日張任民就向李宗仁建議為應對即將實行的憲政,應進行副總統競選之準備①《黃旭初日記》,1936年9月26日。,由此可窺一斑。二、桂系雖是以地緣、學緣、業緣組織起來的地域政治團體,但對其團體的純潔性、穩定性與團結性極為重視。黃旭初事后總結兩廣事變教訓時,對于桂系的團結頗為自得,“發現我力量之偉大,精神團結不屈不懼,懾服敵方,兵員動員迅速多量”。②《黃旭初日記》,1936年10月12日。三、桂系部分將領對于國際局勢、時代潮流有一定認識,看到民族主義興起之下,抗日潮流不可阻擋,唯有順應時代要求,方能有所發展。因此當1935年李宗仁力主聯日之時,劉斐直言“中國與日本利害根本沖突,情感根本惡劣,我應根本認識彼此不能結合”,兩廣事變期間日本對桂態度的轉變,更讓桂系認識到聯日不足恃,1936年10月19日桂系要員分析抗日局勢,白崇禧直言“統一必須抗日,不攘外絕不能安內”。③《黃旭初日記》,1936年6月10日、10月19日。
更為重要的是,南京國民政府自1928年在完成形式上的統一后,在與各軍閥混戰,拓展中央控制范圍的同時,蔣介石受制于國內外復雜的政治局勢,往往難以通過軍事手段徹底解決地方勢力。蔣曾直言桂事解決時,“左右幕僚只短桂方之弱點,而不知我本身之弱點尤多”,試圖以財政補貼換取地方實力派的政治忠誠,以此維系中央的統一與權威。問題是廣西的政治與經濟結構仍舊如昔,桂系賴以存在的社會基礎并未受到根本改造,雖然因現實困境被迫向中央臣服,倘若中央政局出現劇烈變動或無力向廣西提供足夠財政補貼之時,又或桂系自身控制的區域與財賦力量轉趨強大后,雙方再次走向對立也就難以避免。西安事變爆發后,桂系又欲借勢行動,12月21日桂系與西安電臺直通,22日桂系商擬應付時局辦法,強調“南京政府須使之慢慢變質,逐漸參加抗日分子,如驟行崩潰,我之力量收拾不易”,并準備趁勢向南京提出改造西南政局方案,“以王伯群主黔政,并設法調滇黔綏靖副主任他往,由我薦人繼任”,只是西安事變迅速解決,此議乃臨時作罷。④《黃旭初日記》,1936年12月21日、22日。桂系仍舊是蔣介石在國民黨政權內部始終要面對的潛在挑戰者,直至其政權土崩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