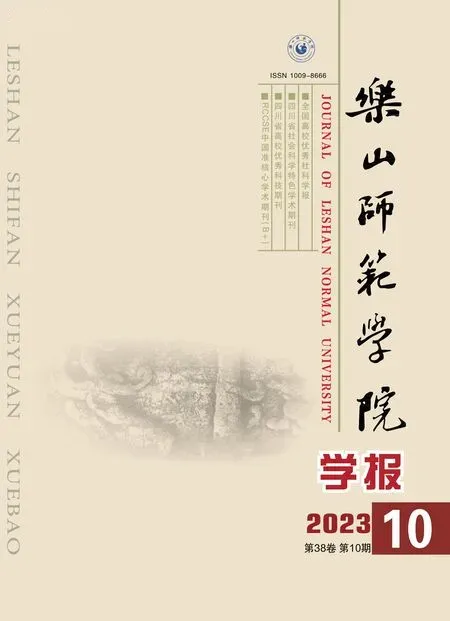“權知徐州軍州事”還是“權知徐州軍事”?
——蘇軾徐州所任職官說略
2023-05-13 10:46:36趙越
樂山師范學院學報
2023年10期
趙 越
(西南交通大學 人文學院,四川 成都 611756)
蘇軾在宋神宗時期于徐州任職時,在當時的滕縣(今山東滕州)寫下《滕縣公堂記》一文。該文在后世的傳抄刻印過程中,關于蘇軾職官方面的記載有“權知徐州軍州事”和“權知徐州軍事”兩種,而在學界已整理的《滕縣公堂記》中也存有這兩種不同的說法。因而有必要對“權知徐州軍州事”和“權知徐州軍事”的基本情況進行考察,把握兩種職官之間的關系,厘清蘇軾在徐州所任官職的情況,從而進一步推動對蘇軾徐州所任職官的認識。
一、蘇軾職官的現有記載
宋代文人蘇軾于熙寧十年(1077)前往徐州任職,在此期間寫下《徐州上皇帝書》《乞醫療病囚狀》《滕縣公堂記》等文章。細致閱讀蘇軾《滕縣公堂記》時會發現,學界目前已刊載了這篇文章的各類學術著作和古籍整理資料,關于他寫作此文時的職官有二說:一是記載為“權知徐州軍事”。例如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云:“元豐元年七月二十二日,尚書祠部員外郎直史館權知徐州軍事蘇軾記。”[1]377-378此外,張志烈、馬德富、周裕鍇所編《蘇軾全集校注》和李之亮所作《蘇軾文集編年箋注》也作如是說。二是“權知徐州軍州事”。這個說法亦見于孔凡禮的相關著作,他在《蘇軾年譜》中提及蘇軾到徐州任職的全稱為:“朝奉郎、尚書祠部員外郎、直史館、權知徐州軍州事、騎都尉。”[2]同一位學者的著作就有兩種不同的說法,而且只有一字之差,那么“權知徐州軍事”是否為“權知徐州軍州事”的簡稱,即兩者是否為同一種官職呢?……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