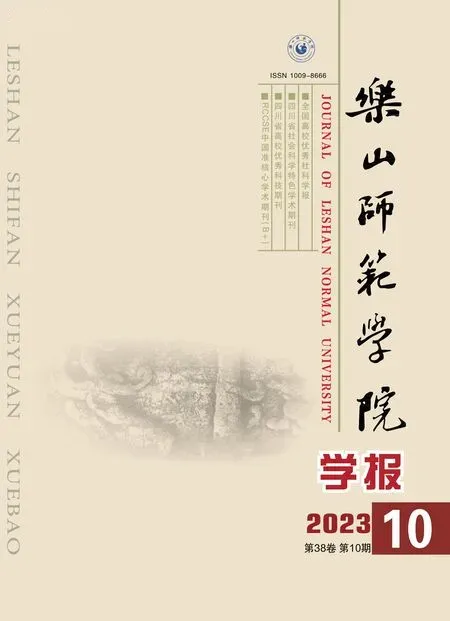杜甫詩歌的“以古入律”及詩史意義
2023-05-13 10:46:36華若男
樂山師范學院學報
2023年10期
華若男
(蘭州大學 文學院,甘肅 蘭州 730000)
杜甫“以古入律”承襲初唐“以古入律”風氣而來,又影響到了中唐時期的“以古入律”風尚,呈現出鮮明的時代與個人特色。對杜甫“以古入律”的關注從唐代就開始了,但它直到明清時期才成為完整的概念得到較為集中的闡釋。理論總結與創作實踐之間的錯位也從側面印證了杜甫“以古入律”之作歷久彌新的魅力。當前對杜甫“以古入律”的研究,多從聲律角度入手,其中尤以杜甫拗體律詩對古體詩的吸收借鑒研究為最,這自清人李兆元《律詩拗體》始便有了集中且詳細的論述。事實上杜詩在語言表達如句式、章法、用字以及創作精神、藝術風貌等方面對古詩同樣有許多繼承創新,但研究相對較少。前人多偏重于討論杜詩的“以古入七律”,對于其“以古入五律”則較少論及。同時,當前研究大多將目光集中在杜甫“以古入律”的形式層面,對其精神層面的發掘則稍顯不足。為此,本文將從杜律整體語言表達與精神實質入手,分析其“以古入律”的表現及詩史意義。
一、杜甫“以古入律”的概念界定
“以古入律”之風在唐代就已顯露,但它作為一個完整的概念直到明代才出現,明清時期得以廣泛運用,但在表述方式上存在多種“變體”,如“以古為律”“以歌行入律”“以古行律”“運古于律”“律體似歌行”等。其中,“以古為律”使用頻率最高,明代許學夷《詩源辨體》、鐘惺與譚元春合編《唐詩歸》,清乾隆帝《唐宋詩醇》、潘德輿《養一齋詩話》、浦起龍《讀杜心解》、楊倫《杜詩鏡詮》等書都采用了這一表述;……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