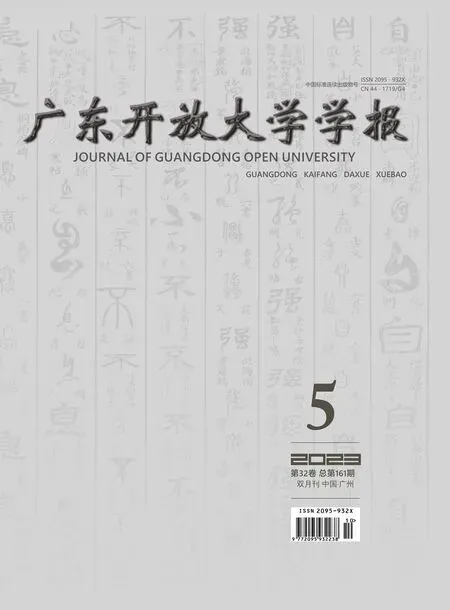“偷租”行為之定性
——財產犯罪的第三條解釋路徑
張澤龍
(西南政法大學,重慶,401120)
一、問題的提出
近年溜門撬鎖的“偷租”行為時有發生。所謂“偷租”行為是指行為人在戶主不知情的情況下,非法侵入他人空置住宅,并假冒房東將房屋出租給他人的行為。
“偷租”案件涵蓋多種行為,理論上可解釋空間較大,案件存在較大爭議。案件定性觀點梳理如下:
第一種觀點認為“偷租”行為不構成犯罪。該觀點認為,租客并不存在值得刑法保護的法益被侵害,僅是租賃合同效力存在瑕疵,戶主的房屋也并未因“偷租”行為產生不可恢復的實質損害,故不應當將“偷租”行為認定為犯罪[1]。
第二種觀點認為“偷租”行為構成盜竊罪。部分學者認為本案盜竊對象是不動產本身。行為人竊取空閑房屋的占有權,將房屋門鎖更換,意味著戶主在不采取救濟措施的情況下,事實上已經喪失對房屋的占有,而盜竊罪的核心是轉移占有,一旦財物的占有被轉移,就足以認定為盜竊罪,并不以被害人是否能夠救濟成功為阻卻事由。
部分學者認為盜竊對象是戶主的債權請求權[2]。該觀點認為“偷租”偷的是戶主的財產性利益,即戶主的債權請求權。房屋空閑并不代表戶主對于房屋不享受財產性利益,房屋事實上被出租所獲得的債權理應屬于戶主所有,不能因為戶主無從知曉房屋是否被出租就否定戶主的債權請求權。
部分學者援用“使用盜竊”的概念,認為本案的盜竊對象是房屋的使用權。該觀點認為,行為人雖然不具有非法占有房屋的目的,但是通過對房屋的非法使用謀取利益,屬于具有返還意思的可罰的使用盜竊[3]。
第三種觀點認為“偷租”行為成立詐騙罪。租客因行為人虛構事實、隱瞞真相,將本應當屬于戶主的租金錯誤交付給行為人,雖然租客本人并未產生財產損失,但是戶主存在財產損失。在本案中財產處分人與受害人并非同一人,屬于三角詐騙。
另有觀點認為本案屬于普通詐騙罪,受騙人為租戶。租客因行為人的欺騙行為產生錯誤認識,從而處分財物租賃房屋,租客本應當租賃的是權利無瑕疵的房屋,但卻因陷入認識錯誤而租賃了權利存在瑕疵的房屋。從表面上看租客并非存在財產損失,但實質上不能否認租客的財產損失,租客租賃的是事實上權力不完整的房屋,且該權利瑕疵嚴重影響租客的權利行使,應當認為行為人構成詐騙罪。
案件定性的矛盾爭點集中于盜竊罪與詐騙罪的對立。盜竊罪的核心是“轉移占有”,詐騙罪的核心是“基于認識錯誤處分財產并產生財產損失”。“偷租”行為的本質并不契合二罪核心。
“偷租”行為的牟利事實只能引起民事法律效果,不足以喚起刑罰制裁。但是,“偷租”行為的牟利事實是建立在“偷租”手段上的,牟利行為法益侵害性程度無法被解釋進刑法構成要件,并不意味著達到牟利效果的手段不能在刑法意義上被評價為值得打擊的非價值。“偷租”行為更符合故意毀壞財物罪的構成要件,無論是定性還是量刑皆有合理性。
二、現有解決路徑認定失準
(一)不動產不能成為盜竊罪的犯罪對象
無論是大陸法系還是英美法系,多個法治發達國家或地區的刑事立法與司法實踐都否定不動產盜竊的存在,將盜竊罪犯罪對象限定為動產,如德國、意大利、瑞士、法國、加拿大、美國部分州、我國臺灣地區等。上述國家和地區之所以將不動產排除出盜竊罪之犯罪對象,是因為對不動產的“盜竊”不滿足盜竊罪“轉移占有”的本質。
盜竊罪“轉移占有”的構成是“破壞原有占有關系——建立新的占有關系”。如果只能破壞原有占有關系而不可能建立新的占有關系則不構成盜竊罪,建立新的占有關系才是“轉移占有”的本質。在動產盜竊情形中,行為人通過盜竊行為破壞被害人原有的占有關系,建立了行為人對該動產的新的占有關系;在不動產“盜竊”情形中,誠如“不動產盜竊肯定說”所言,對不動產的“盜竊”會侵犯被害人對不動產占有的安寧權,但是此種侵害僅僅屬于“破壞原有占有關系”,而未成功建立新的占有關系。不動產登記取得制度和不能物理移動、無法人力簡單支配的特質,決定了不動產不會如動產般被輕易建立新的占有關系。建立新的占有關系意味著事實上或觀念上的控制支配,該控制支配的基本特征就是排他性。在不動產盜竊案件中,即使行為人搬入他人房屋,行為人在事實上或觀念上也不可能被認為實現了對房屋的排他性控制支配。
(二)基于法秩序統一性原理應當否定債權請求權被盜竊
財產性利益是否能夠被盜竊存在爭議。我國的通說觀點認為財產性利益是盜竊罪犯罪對象“財物”的下位概念,也即肯定財產性利益能夠被盜竊[4]。在“偷租”案中,有觀點認為行為人是對戶主財產性利益的盜竊,即盜竊了戶主的債權請求權。該觀點混淆了“房屋被侵權而產生的債權請求權”與“房屋租賃合同所產生的債權請求權”。“債”發生的主要原因包括合同、侵權、無因管理、不當得利等。在本案中租客與戶主之間不存在任何債權請求權產生基礎的事實,無法認定戶主存在對租客的債權請求權,不可能認定“偷租”行為是盜竊了戶主債權請求權。雖然存在一方不當得利,一方受損,但并不意味著受損方所受損害與不當所得利益是對應的同一利益,完全可能是基于不同事實而產生的不同利益。戶主受損后產生債權請求權的事實是其房屋被“偷租”,租客得利的事實是其善意的房租租賃行為。基于合同的相對性原理,債權請求權只在兩人之間存在,雖然戶主事實上存在被侵犯的財產利益,但并非債權請求權被侵犯,戶主根本不存在被盜竊的債權請求權,只存在因侵權行為產生的債權請求權。
(三)偷租行為不屬于“可罰的使用盜竊”
按照可罰的違法性理論,某種行為即使在形式上符合構成要件,并且不具有違法阻卻事由,但如果達不到可罰的違法性程度也不成立犯罪[5]。財產犯罪保護的不僅是財產的本權,還保護財產權利人對該財產的利用價值,可罰的使用盜竊本質上仍然是法益侵害的判斷,如果盜用行為達到了阻礙權利人利用財物價值的程度,如財物丟失、損毀,則具有可罰性。反之,如果僅僅是單純的盜用,未達到了阻礙權利人利用財物價值的程度,則不構成盜竊罪。故在“偷租”案中,不動產的特性也意味著“偷租”未達到阻礙權利人利用財物價值的程度,“偷租”行為人根本不可能造成不動產的丟失;戶主可以毫無障礙的恢復對房屋的各種權利,因此不應當認為“偷租”行為屬于“可罰的使用盜竊”。我國司法解釋中也可以體現這種觀點。司法解釋規定,偷開機動車后造成機動車損壞、丟失的,應當認定為盜竊罪。那么根據司法解釋精神,如果沒有造成機動車無法返還的,則不應當處罰。這也與“偷租”案相契合。
(四)詐騙罪適用存在缺陷
有論者認為,租客是刑事被害人。租客因行為人隱瞞真相、虛構事實,以正常市場價格租賃了權利瑕疵了房屋,應當認定該行為是詐騙罪。但如果認定“偷租”案構成詐騙罪,是對真正法益受損主體的認定偏差,會導致案件定性失準,且存在處罰漏洞,邏輯上難以自圓其說,也很難做到量刑合理。
就行為人欺騙租客的行為而言,租客雖然存在法益受損,其法益受損的程度無法進階認定為刑事法意義上的受損,僅通過民事法律關系調整即可。民法保護善意第三人,租金是合法的債務履行,即使產生債權債務的合同本身存在一定瑕疵,但民法仍對其予以充分背書。“偷租”案中租客支付對價,簽訂房屋租賃合同,也成功實現了合同所約定的利益,租客整體的財產秩序并未有明顯程度的惡化,因此無需評價為刑法意義上的被害人。
此外,認定案件被害人為租客,行為人構成詐騙罪,還存在明顯的處罰漏洞。首先,租客與行為人合謀租房的情況將以無罪論處。如果將案件事實修改為租客對于“偷租”知情,租客為了貪圖便宜主動與“偷租”者達成一致,在知道案件真實情況下主動租房,此時無法認定租客被“詐騙”,更無法認定租客存在財產損失,只能做無罪處理。其次,如果現實中發生僅僅溜門撬鎖自己居住不動產而不出租的情形,如按上述詐騙租客的意見處理,也是無法認定為犯罪的。
(五)三角詐騙援用困難
有論者指出,“本案中存在財產損失,只是財產受損人與受騙人并非一致,戶主顯然失去了對租金的所有權而遭受損失”。該觀點似乎從三角詐騙的角度來解釋受損主體錯位的問題,意圖以三角詐騙的解釋路徑實現對案件定性詐騙罪的合理解釋。該觀點認為,因為三角詐騙的核心概念是:受騙處分財物人與蒙受損失人即使不是同一人,也可成立詐騙罪[6]。其認為在“偷租”案件中,有人受騙,有人受損,且兩主體分離,因此完全符合三角詐騙的核心構造。
然而事實并非如此。三角詐騙的判斷涉及被騙者的處分意識、處分地位、處分權限[7],三角詐騙構造的提出是為了實現盜竊罪與詐騙罪的界分,具體來說是區分間接正犯形態的盜竊罪與詐騙罪。三角詐騙中受騙人不當處分了被害人的財物,出現受騙人與被害人的分離。在德國,盜竊罪被認為是他人損害型犯罪,而詐騙罪則被認為是自我損害型犯罪,由此出發,認定三角詐騙成立的核心在于,受騙者所做出的財產處分能否歸屬于財產的最終受害者,從而能夠將第三人(受騙者)的財產處分行為視為財產受害者的自我損害[8]。在“偷租”案中,無論如何解釋,租客處分的都是自己的財產。善意的租客履行正常的具有權力外觀的行為,不可能被認定為是處分戶主財產的行為,本案缺少“受騙人處分被害人財產”這一核心要素,從而導致了三角詐騙在本案中援用困難。
三、故意毀壞財物罪的解釋路徑
盜竊罪與詐騙罪之于本案的失準,必然要另尋他路實現刑法的合理規制。有論者“另辟蹊徑”,認為本案社會危害性較大,不應當將之如此出罪,若實屬無奈,當以非法侵入住宅罪兜底。非法侵入住宅罪保護的法益是人的居住安寧權,只有擾亂人的居住安寧的非法侵入住宅的行為才應當以該罪論處。換言之,即使從形式上看存在非法侵入住宅的行為,但實質上未侵犯人的居住安寧權,不能認定為該罪。“偷租”行為人所侵入的房屋都是長久無人居住的住宅,其才有機會假冒該戶的戶主進行“偷租”,“偷租”行為不滿足非法侵入住宅罪的構成要件。
本文認為,“偷租”行為本質上是財產犯罪,雖然盜竊罪與詐騙罪的適用存在問題,但是在財產犯罪的解釋路徑上仍然行得通,那就是將案件定性為故意毀壞財物罪。
(一)“毀壞”學理之簡描
在德國、日本,對于故意毀壞財物罪之“毀壞”的理解存在不同學說。按照“物質侵害說”的理解,“毀壞”是一種物理層面的損毀滅失,其將“毀壞”限定在物質層面,要求對財產的保護回歸物質本身,不應當是概括性的、主觀性的判斷。該學說從“毀壞”的核心語義出發,緊緊立足于對財物自身物理形態完整性的毀壞,有意淡化對財物權利人效用影響在評價中的成分,強調對財物本身的保護,關注毀壞的手段是否導致財物毀損、致其難以恢復原狀而不能發揮原有效用[9]。該說立足于刑法的明確性,意圖限制刑法打擊范圍。
但是,完全貫徹“物質侵害說”將會導致刑法對所有權的保護失利。隨著社會的發展,財物的作用不僅僅停留在物質表面,財產價值的發揮愈加注重財物的內在效用價值。如果故意毀壞財物罪僅停留在“物質損害”的判斷上,易使得許多妨害財產價值發揮的危害行為得不到懲治,因此留有較大處罰漏洞。許多情況下即使財物并不存在物質層面的損害,但是財物的價值確已喪失。如把吃飯用具浸泡在糞便中,即使該用具在物理層面不存在任何損壞,但確實不能再發揮其原有功能了。也正因如此,德國學者提出“狀態變更說”。該觀點認為,一切對他人財產造成不利變更的行為都屬于“毀壞”行為。根據該觀點,對于“毀壞”的理解不應當局限于物理意義和功能層面,只要是導致被害人整體財產秩序受損的一切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行為都應當是“毀壞”。日本理論中的“效用侵害說”與之相似,“效用侵害說”認為,一切對財物效用的侵害都屬于“毀壞”;該說較之德國的“狀態變更說”在打擊范圍上有所限縮,但是仍然關注的是對財產的概括性保護。
但是,上述對財物進行概括性保護的觀點也遭受了批判,認為其過分擴張“毀壞”的含義,擴大了刑法的打擊范圍,違背刑法謙抑性。
綜合上述兩種理論的缺陷,德國學者提出了“有形侵害說”。“有形侵害說”是一種階層式判斷理論,第一階層要求對財物施加“有形”的影響;第二階層要求對財物具有物理層面的損害或者效用層面的損害。該觀點遵循刑法的明確性原則,限縮了“毀壞”的認定,同時又使對于財物價值效用的損害不至逃脫刑法打擊,“有形侵害說”后來逐漸發展為德國的通說。
我國刑法學界對于“毀壞”經歷了重視“毀壞”的本真性、物理性理解到重視“毀壞”的概括性理解的過程。早期,由于故意毀壞財物罪在我國并不多發,學界和實務界對該罪并未給予太多關注,我國刑法教科書和其他財產犯罪專著都從表面上理解該罪,采取“物質侵害說”的觀點。因為社會經濟不斷發展,實踐中越來越多非典型的故意毀壞財物的行為發生,逐漸暴露了“物質侵害說”的缺陷;隨著德日刑法理論的引入,學界開始對故意毀壞財物罪有了法理意義上的討論。例如張明楷教授主張一般的“效用侵害說”,認為“毀壞不限于從物理上變更或者消滅財物的形體,而是包括使財物的效用喪失或者減少的一切行為”[10]。這是一種對“毀壞”較為寬泛的理解,不拘泥于物理意義;周光權教授則立足于功能妨害的視角,認為“即便沒有破壞實物,但對于財物的正常功能發揮有影響的,也是毀壞”[11]。
總之,我國現在刑法通說更加重視對財物的概括性保護,但又不同于德國的“狀態變更說”,我國理論限制了毀壞財物罪的構罪范圍,屬于折中說觀點,并為司法實踐所采(如朱某勇故意毀壞財物案①2002 年4 月29 日至5 月10 日,被告人朱某勇利用事先獲悉的賬號和密碼,侵人被害人陸某輝、趙某花夫婦在證券營業部開設的股票交易賬戶,然后篡改了密碼,并使用陸、趙夫婦的資金和股票,采取高進低出的方法進行股票交易。,法院便認定朱建勇構成故意毀壞財物罪)。我國刑法理論上存在的眾多折中說——如一般的效用侵害說、功能妨害說、有形影響說、損毀危險說等等——雖具體判斷上存在略微差異,但核心都是將“毀壞”理解為“形式+實質”的結合,既注重本真性理解又注重概括性理解。
(二)“偷租”滿足“毀壞”的實質解釋
“偷租”行為能否認定為故意毀壞財物罪的關鍵在于:“偷租”行為能否認定為“毀壞”。本文認為,“偷租”行為認定為“毀壞”不存在任何障礙。
Seyfort Ruegg 1977: David Seyfort Ruegg, The gotra, ekayāna and tathāgatagarbha theories of the Praj?āpāramitā according to Dharmamitra and Abhayākaragupta,Praj?āpāramitā and related systems (Studies in honor of E. Conze), Berkeley, 283-312.
從實質上看,法益侵害決定了構成要件的內容,法益實現的關聯性始終扣緊著行為規范的禁止范圍,一個無視于結果的行為規范概念上不可能存在[12]。財產犯罪保護的不僅是財產的本權,還保護財產權利人對該財產的利用價值,對故意毀壞財物罪實質理解不能限于對所有權的保護,必須作廣義理解——一切妨害財產權利人對財物行使利用價值的行為都可能是故意毀壞財物罪所要規制的行為,或者說,侵犯整體財產秩序,影響財產經濟價值的行為都能夠為“毀壞”所包含[13]。
“偷租”行為會導致房屋價值貶損。房屋使用得越久其價值越貶損,即使未對房屋進行物理性改造,“偷租”行為對房屋造成的價值貶損也會存在。基于社會一般觀念,未入住的毛坯房和已經入住的二手房在市場價格上存在較大差別,根據網站“房天下”近期的一篇報道,同一小區二手房房價為13000元/平,新房房價為19000元/平;如果是100平方米的房屋,二手房與新房價格差異為60萬元。并且曾經用于對公眾開放出租的房屋,其折價更加嚴重。現實發生的案例中,多數租客還存在改變房屋構造、重新裝修的情況,將非承重墻拆除或者增加新的墻面以改變房屋格局,這種物理性的改變對于不動產價格折損更大,對于房主財產法益的侵害更為嚴重。在民法的司法實踐中,租客某些行為導致房屋價值貶損是得到司法裁判認可的,租客對于租住的房屋具有妥善使用的義務,如果違反義務導致房屋價值不正常貶損,是需要進行損害賠償的。如(2016)京0107民初2574號判決、(2017)遼01民終2177號判決記載,因承租人存在過錯,致使房屋成了“兇宅”,給房屋交易帶來一定價格貶損,構成對戶主從財產權利的侵犯。雖然房屋沒有任何物理性的損害,但是法院認可租客對戶主具有賠償責任,由此也能證明租客不當使用房屋造成房屋價格貶損是為司法實踐認可的。
當然,之于刑法保護范圍擴張與罪刑法定原則限制的緊張關系,并非一切上述行為都能夠評價為“毀壞”行為,只有處于構成要件形式邊界內的行為才能評價為故意毀壞財物罪,因此在還需要從形式上對“毀壞”作邊界限制。
從形式上檢視,“偷租”行為仍在“毀壞”的語義輻射范圍內,將“偷租”行為解釋為故意毀壞財物罪的實行行為并未超出國民預測可能性,屬于符合罪刑法定原則的擴大解釋。為了現實中案件的周延處理,司法實踐不得不對構成要件的解釋進行擴大化,有時不得不脫離對構成要件本真的、最符合國民預測可能性的理解。此時該解釋結論雖有侵害國民自由嫌疑,但如果能夠實現妥當說理、規范論證,與反對觀點唇槍舌戰后仍能邏輯自洽,那么便能擺脫類推解釋的“追殺”,甚至成為推動國民預測可能性進步的解釋結論。國民預測可能性并非一成不變,其會隨著刑法理論與司法實踐的進步而進步。
對于“毀壞”的理解要從形式上對語義邊界進行限定。法律解釋要以一般的語言用法為基礎,因為法律是適用于所有人,進而涉及所有人,故而不能放棄最低限度的可理解性[14]。本案中“偷租”行為人是故意毀壞財物罪的間接正犯,能夠評價為“毀壞”的行為是“租客之入住對房屋所產生的物理性影響的行為”,“偷租”行為人通過對犯罪事實的支配,使偷租行為人的行為獲得“毀壞”的評價。間接正犯與直接正犯在本案的區分具有重要意義,間接與直接的區分決定行為方式的認定,也就決定“毀壞”能否解釋本案的行為。
認定本案間接正犯的意義是厘清“毀壞”行為之所在——租客對房屋施加物理性影響的行為是“偷租”案之“毀壞”行為。換言之,“偷租”行為人的“詐租”行為作為支配行為無法直接進入故意毀壞財物罪的構成要件,該行為很難解釋為對房屋施加了直接的、有形的、物理的影響;本案的直接實行行為(即直接體現“毀壞”的行為)是租客之入住對房屋所產生的物理性影響的行為。正如警察甲通過言語方式教唆單位的保潔乙對犯罪嫌疑人丙進行刑訊逼供的案件相同,警察甲的言語行為之所以能評價為刑訊逼供的行為,是因為其對案件事實具有支配作用,保潔乙的普通毆打行為就轉化為甲刑訊逼供的行為。善意的租客入住房屋,對房屋進行裝修改造,并且日久天長的加以利用,必然對房屋施加了有形影響,租客的日常生活行為由于“偷租”行為人對故意毀壞財物事實的支配,轉化成了“偷租”行為人對房屋“毀壞”行為。因此,無論是按照何種折中說,租客對房屋入住、改造、裝修等行為都能評價為具有物理性意義的行為,屬于對財物施加了足以降低其財產性價值或者效益、外觀的行為,能夠為“毀壞”的語義涵射,因此“偷租”行為仍處于“毀壞”的形式邊界內。
一個問題的結論需要顧及類似問題,不能顧此失彼。承認“偷租”行為構成故意毀壞財物罪是否意味著打開了潘多拉魔盒,即任何盜用、騙用行為是否都能評價為故意毀壞財物罪?
本案之所以能夠評價為故意毀壞財物罪,是因為存在于本案中的毀壞行為恰巧穿著盜用的外衣;換句話說,本案的“毀壞”是通過“盜用”行為實現的,形“盜”實“毀”;盜用行為與故意毀壞財物罪之間存在一個溝通管道,即對財物施加物理性、有形性之影響的作用力。盜用、騙用行為本身不會構成故意毀壞財物罪,但盜用、騙用行為會形成盜用、騙用狀態;在該狀態下,如果存在對財物施加物理性、有形性之影響的作用力,并且造成財物價值的貶損、滅失,那么仍然可以將該盜用、騙用行為評價為構成故意毀壞財物罪。
總之,“偷租”行為人擅自使用房屋的行為,能夠以故意毀壞財物罪加以規制。
筆者身邊有人反駁,如果認為采取故意毀壞財物罪的路徑規制“偷租”行為,由于本案行為人的行為具有社會危害性應當認定為犯罪,故通過認定房屋價值貶損從而構成故意毀壞財物罪具有合理性,但是這也意味著打開了一道閘門,即租客對于房屋的不當使用導致價值貶損都有可能會認定為故意毀壞財物罪。該做法過于侵害國民的自由,不當擴大故意毀壞財物罪的打擊范圍,使得租客時刻處于入罪的風險,不具有合理性。
上述觀點忽略了“偷租”類對不動產侵害的案件與租客租房的核心差異,即戶主是否知情。租客與戶主通過正當法律程序實現房屋租住,戶主對于租客入住其房屋是知情的,基于一般人的常識,戶主必然會認識到租客入住有可能導致房屋價值產生一定貶損,應當認為戶主存在“被害人承諾”,羅馬法諺有云“得承諾的行為不違法”。戶主的承諾能夠阻卻房屋因租客一定程度不當使用導致的價值貶損的法益侵害性。應當注意,“被害人承諾”要求經承諾實施的行為不得超出承諾的范圍,一經超出則不能阻卻行為的違法性。戶主對于租客的“被害人承諾”是有一定限度的,如果租客對房屋進行各自拆毀活動,導致房屋的價格貶損超過正常范圍,也應當認定為故意毀壞財物罪。
此外,在犯罪故意層面,行為人至少存在間接故意。行為人作為社會一般人,必然對于自己撬門出租他人房屋行為的社會意義有認識,無論租客改變房屋物理性結構,或是單純入住使房屋增加使用痕跡從而導致價值貶損,“偷租”行為人都是明知的,行為人對于房屋財產價值減損的結果明知且放任發生,至少存在故意毀壞財物罪的間接故意。
四、故意毀壞財物罪的適用優勢
(一)明晰受損法益性質、被害人與社會危害性
首先,大眾憑借樸素的法直覺會認為“偷租”行為侵害的是被害人的財產權。“偷租”行為是為了圖財,行為的方式是通過損害他人財產的方式不當得利,本案受到不法侵害的法益主要是財產法益,因此案件定性理應從財產犯罪把握。將本案認定為非法侵入住宅罪不僅對于構成要件做出不當解釋,還對案件事實做形式上的歸納,未能正確把握案件真正受到不法侵害的法益。其次,不同罪名的適用往往意味著對被害人地位歸屬有不同的價值判斷。如果認定案件是普通型詐騙罪,那么被害人就是租客;如果認定案件是盜竊罪,那么被害人就是戶主。“偷租”行為侵害的主要是戶主的權益。通過被害人的正確判斷,揭示案件主要社會危害性是行為人侵占損害不動產的行為,向社會宣誓侵害不動產行為是值得刑法打擊的,利于實現一般預防的效果。如果認為本案刑事被害人不是戶主而是租客,則代表刑法疏于評價被害人不動產被侵犯的行為。刑法具有規范指引功能與價值評價功能,對侵害行為的消極不評價則代表刑法認可該行為,代表刑法認為侵占不動產行為不具有刑法上的非價值,沒有社會危害性,這不僅會做出錯誤的價值引導,導致此類案件無法得到預防,而且對于已經發生的案件束手無策;即使意識到侵害不動產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必須予以刑法打擊,也會因同案異判而使司法實踐陷入進退兩難的局面。
(二)彌補處罰漏洞
本案不宜認定為詐騙罪的重要原因是詐騙罪無法全面的評價行為的社會危害性,甚至無法評價出行為主要的社會危害性,具有處罰漏洞。上文分析,定性為詐騙罪的處罰漏洞有兩種情形,第一種情形為行為人串通租客共同利用戶主房屋牟利,租客為了貪圖便宜主動與“偷租”者達成一致,在知道案件真實情況下主動租房,此時無法認定租客被“詐騙”,更無法認定租客存在財產損失。第二種情形是行為人單純的侵占不動產,對不動產造成破壞導致價值貶損的情形。此時由于也不存在被詐騙的被害人,也是無法通過詐騙罪規制的。上述兩種情形本質相同,都是不存在詐騙罪被害人,因此詐騙罪的規制路徑存在較大處罰漏洞。如果以故意毀壞財物罪論處,則可以妥善解決兩種情形。對于租客與“偷租”行為人合謀損害戶主財產利益的行為,利用共同犯罪的原理即可很好地解決。租客與行為人具有共同的犯罪行為、犯罪故意,可以輕易認定為故意毀壞財物罪的共同犯罪,并不存在理論上的障礙。對于單純危害不動產的行為,如上文分析,故意毀壞財物罪也不存在任何規制上的困難。
(三)法定刑與行為罪質相符
量刑是否合理是檢驗甚至指導定性是否準確的要素。即從量刑妥當性的基點出發,反過來考慮與我們裁量的相對妥當的刑罰相適應的構成要件是哪個,從而反過頭來考慮該定什么罪[16]。罪名和被害人的認定決定犯罪數額的認定,從本案看,如果定性為詐騙罪,無論是三角詐騙還是普通詐騙,那么該案犯罪數額都是租客交付的租金數額;如果定性為盜竊罪,根據犯罪對象的不同又存在不同犯罪數額的認定,認為犯罪對象是不動產的,犯罪數額就不動產的價格;認為犯罪對象是戶主的財產性利益的,犯罪數額為租客交付的租金數額。
我國刑法關于盜竊罪與詐騙罪的量刑略有差異但是大致相同,如果犯罪數額達到數十萬的,量刑動輒十年以上甚至無期徒刑。如果在“偷租”案中認定行為人盜竊的是不動產,由于不動產市場價格較高,可以輕易達到“數額特別巨大”的量刑檔次;即使是以租客的租金計算,犯罪數額仍然較高。實踐中“偷租”案所得不當利益多為50萬左右,因此被告人也會面臨較重的刑罰懲罰。“偷租”行為本質上并非社會危害性較大的犯罪行為。不動產的性質決定了“偷租”行為不會造成太大的損失,被害人的利益損失容易追償。而且實踐中案發率并不高,“偷租”得手的可能性比較低,預防必要性相對不大。如果僅因被害人不法獲利較多就判處較重刑罰,不符合罪刑相適應原則。將“偷租”行為認定為故意毀壞財物罪,在量刑上更為合理。根據我國刑法規定,故意毀壞財物罪最高刑為7年有期徒刑,一般為3年以下有期徒刑,以該法定刑規制“偷租”行為較為合理,符合“偷租”行為的社會危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