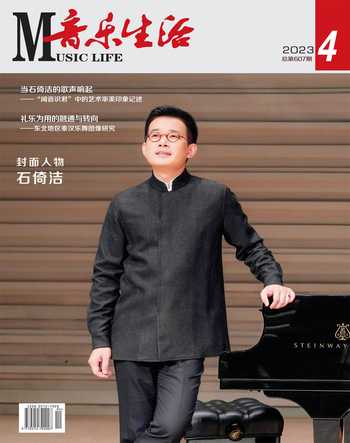雅韻高致人淡如菊
何靜
阿鏜老師再出新著——《我作曲的故事》,邀我作序,受寵若驚之余,不免有惴惴之感,然盛情似火難拒、友情似水長流,豈能拒其美意,于是心潮澎湃,提筆揮毫,愿為新作添幾分色。
初聞阿鏜老師大名是在十多年前,彼時剛畢業(yè)的我去了西部小城一所高校任教,意氣風發(fā)、躊躇滿志地要在西部聲樂教學上有所作為。初為人師,最初上手,我對男生各聲部曲目積累量有些捉襟見肘,除自我提升外,免不了討教恩師和同行,也會讓學生幫我推薦他們喜愛的聲樂作品。有一天,一位男學生興奮地拿來一首剛得來的新作品給我看,欣喜之情溢于言表。我拿過樂譜,看見上面寫著《烏夜啼》,作曲阿鏜,這是一個聞所未聞的名字,還以為是寫流行音樂的曲作者。鋼琴視奏后,我愈發(fā)興奮,頓覺其文質(zhì)兼美,既有中國古典與西方作曲技法,又寫得詩意、古典、精致。急忙上網(wǎng)查看,當時網(wǎng)上關(guān)于阿鏜的信息并不多,但也了解到阿鏜是一位十分優(yōu)秀的作曲家,寫過包括藝術(shù)歌曲和交響樂等大量的音樂作品。“樂莫樂兮新相知”,從此,阿鏜的名字就正式進入了我的音樂視野,他的幾首藝術(shù)歌曲也便收錄到了我個人聲樂教學曲目庫里,而內(nèi)心中也一直期望有朝一日能向阿鏜老師當面請教。
天遂人愿,2019 年12 月13-14 日,此時全國歌劇理論與創(chuàng)作研討會暨首屆優(yōu)秀歌劇評論征集比賽在山東藝術(shù)學院舉辦,作為獲獎?wù)撸液軜s幸地參加了這次盛會。由于第一天報到錯過了歡迎晚宴,所以第二天正式會議,我很早便來到會場,人群中我看見了一位面帶微笑、精神矍鑠,背著背包的慈祥老人,看見他和善地和與會專家聊天,并從包里取出他的唱片和論著與大家分享,又有一些老師上前向他求贈唱片,在他們互報家門中,得知他就是阿鏜老師。激動與驚喜之情難以言表,我立刻站起身,暗想一定不能錯過這個可以與阿鏜老師相識的好機會,便圍過去聆聽各位老師們交流,默默學習。這些老師大都是中國歌劇界理論與創(chuàng)作的“大咖”,怎奈人越聚越多,眼見唱片和書就要分享完了,我靈機一動,說“阿鏜老師您好,我唱過您的歌,能否也贈予我一張唱片。”阿鏜老師看著我露出驚喜的表情,回答道,“好呀,原來你唱過我的歌,那你就是知音。”于是他便將最后的兩張專輯和論著都贈予了我。那一刻的我感到十分快樂和驕傲,“人生交契無老少,論交何必先同調(diào)”,此前雖未曾與阿鏜老師謀面,但因為阿鏜老師的聲樂作品,我與阿鏜老師其實在相識之前“友誼橋梁”的主體結(jié)構(gòu)已然建成,只待時機成熟便可以順利竣工,“一句我唱過您的歌”,便是最好的問候。
這次會議后,我與阿鏜老師有了更多音樂上的溝通,他曾多次通過郵件、微信,無償贈予我他的聲樂作品集,并且允許他的音樂作品和文章在我的公眾號“在水一芳”上發(fā)表,豐富了我教學曲目的同時,也開闊了我的音樂文化視野。隨著交流的深入,我對阿鏜老師的創(chuàng)作和為人也有了更全面的認知。阿鏜老師早年曾赴美留學,學習小提琴演奏,后又拜名師潛心研究作曲理論與創(chuàng)作,深諳西方音樂作曲創(chuàng)作之道,將西方作曲技法與中國傳統(tǒng)音樂之美完美融合。在他的作品中,我們總能感受到東方與西方文化的碰撞,古典與現(xiàn)代藝術(shù)的審視,眾生與自我音樂的對話。他的創(chuàng)作既有古典主義的嚴謹亦有巴洛克時代的精致,既有浪漫主義的自由也有現(xiàn)代主義的理想,但你又不能把他的作品簡單地劃分為任何一種風格,我們可以從他的古詩詞藝術(shù)歌曲和《神雕俠侶》交響曲中窺見一斑,我想這得益于他對中國傳統(tǒng)詩詞歌賦、戲劇、小說、繪畫等音樂姊妹藝術(shù)的癡迷,這便使得他的音樂作品總是具有深邃的內(nèi)涵與藝術(shù)修養(yǎng),而藝術(shù)家們在藝術(shù)造詣上的終極比拼,恰恰都是那些“弦外之音”的比試。“繁音忽已闋,雅韻詘然清”,音樂即人生,我們可以在他的音樂作品中聽出屬于阿鏜獨有的創(chuàng)作標簽——“功底深、意境深、修養(yǎng)深”,所以阿鏜老師的音樂作品近些年得到越來越多專業(yè)人士及音樂愛好者的關(guān)注便在情理之中。
收到阿鏜老師的書稿《我作曲的故事》(以下簡稱《故事》)后,我一氣呵成,讀罷感慨良多。這本書以作曲家本人的視角,全面闡釋和解析了他音樂創(chuàng)作上的心路歷程,書中囊括了他已出版的全部音樂作品的緣起、創(chuàng)作、演出及業(yè)界評論,更附有珍貴的演出視頻網(wǎng)址等,書中講述的作品從阿鏜老師1969 年(或1970年)創(chuàng)作的第一部至今都有廣泛影響力的小提琴代表作《重見光明》到最新創(chuàng)作的小提琴教材,創(chuàng)作時間跨度長達50 年,這半個世紀以來,無論國際還是國內(nèi)的音樂創(chuàng)作和演出市場都發(fā)生了風云變幻的改變,讀者可以透過這些故事的講述,感受一個時代的社會背景以及音樂的創(chuàng)作環(huán)境,從這角度來說,《故事》不僅僅是阿鏜老師的個人作品集,也對中國當代音樂史做出了豐富詳實的補充。阿鏜老師的《故事》,不僅僅是他個人創(chuàng)作歷程的全方位總結(jié),更是中國當代音樂口述史的一部分,具有中國當代音樂史學研究價值。難能可貴的是,阿鏜老師對于自己音樂作品創(chuàng)作的每一個背后的故事敘述都十分詳實,他的語言真實細膩,情感真摯。在本書中匡正了一些以往錯誤的認知,比如關(guān)于阿鏜老師的早期小提琴作品《重見光明》的版權(quán)歸屬問題,我們透過他的講解,知道了整個創(chuàng)作的來龍去脈,理解了他的隱忍與無奈,也感受到了蘊含其中含而不露的善良與真實。值得欽佩的是對于他作品的評價,無論好壞他都會將各方評價真實坦誠地收錄進來,敢于正視自己的缺點,并努力將缺點轉(zhuǎn)化為優(yōu)點,彰顯出阿鏜老師的睿智與對自己作品的自信。當然,見微知著,通過他行為處事的風格可以推斷他對于音樂創(chuàng)作的態(tài)度。可以說,類似于阿鏜老師的新著在中國作曲家中還鮮有人出版,這本論著既可以當作雅俗共賞的故事,亦可以作為音樂院校作曲專業(yè)師生教材的補充。毫無疑問,新書的出版為研究和學習阿鏜老師音樂作品的學者提供了詳實寶貴的音樂史料。
阿鏜老師的音樂作品之所以吸引人,得益于他作品中不斷挑戰(zhàn)、不斷試錯的創(chuàng)新理念。藝術(shù)的核心往往不是復(fù)雜的技巧、艱澀的技法,而是新的表達方式。對于音樂,阿鏜有著天然的高度敏感,加之他不斷挑戰(zhàn)自我的性格與踏實勤奮的學習態(tài)度,決定了他作品的品質(zhì)和高度,這也是阿鏜老師作品可以一直得以傳唱的原因。阿鏜在音樂作品的選材上非常考究,無論是藝術(shù)歌曲還是交響樂,一定是能夠引起他思想高度共鳴的內(nèi)容,所以他的作品總給人詞曲合一之感。在他的音樂作品中,有兩類非常重要的音樂體裁,那就是《神雕俠侶》交響曲和他的宗教音樂。《神雕俠侶》的新在于形式和內(nèi)容,這種寫作首創(chuàng)了武俠題材交響樂。對作曲家需要提出更高的要求,因為宗教在其形成和發(fā)展過程中不斷汲取人類各種思想文化的養(yǎng)分,又與哲學、歷史、文學、倫理、詩歌、繪畫、建筑、雕塑等相互滲透、包容,而阿鏜老師創(chuàng)作的宗教音樂不僅限于一種宗教,而是包含基督教、佛教等,雖然他的宗教音樂因受眾群體對宗教的關(guān)注度還不夠,但卻不能否認其價值。“欲取鳴琴彈,恨無知音賞”,很多經(jīng)典的藝術(shù)作品不一定會在它誕生的時代綻放光芒,卻往往能超越藝術(shù)家們的生命而傳承下來,很多真正有價值的藝術(shù)作品往往需要更多時間的沉淀。
在我眼里,阿鏜老師對于音樂是絕對的“ 真愛”,是一位真正的“樂癡”。作曲在他的世界里不僅僅是他的職業(yè)、生存的仰仗,更是他一生的事業(yè)與理想,為了這個理想,他不辭辛苦、不斷試錯、不停積累、不懈努力,在學習與實踐中迅速成長。其實,樹立自己音樂作品的藝術(shù)個性是每一個藝術(shù)家都向往的,而想讓自己的作品在音樂的海洋中獨樹一幟,是作曲家們的畢生追求,作為小提琴演奏家的阿鏜,在小提琴演奏道路上順風順水的時候,毅然改弦更張潛心學習作曲,這不得不說需要十分的勇氣和熱愛。曾經(jīng)聽過這樣一句話:一個人總是喜歡做什么,說明他在這個方面一定有天賦的。阿鏜老師在學習音樂之始就有主動創(chuàng)作意識,對日后他潛心學習打好了基礎(chǔ)。而“癡情”的他,看起來特別像個“難得的傻子”,特別是在這個快節(jié)奏工業(yè)化時代已然影響到古典音樂領(lǐng)域的當下。
現(xiàn)如今搞作曲的人都有這樣一個秘而不宣的信條,那就是“能寫歌劇絕不寫藝術(shù)歌曲”,能寫流行音樂絕不寫古典歌曲,究其原因無外乎是無利可圖。是的,在當今這個時代,只寫藝術(shù)歌曲的作曲家恐怕會面臨生存危機,而阿鏜老師的創(chuàng)作從來都是將藝術(shù)理想放在首位,從他160 篇作曲故事中可以窺見,他這一路走來所經(jīng)歷的艱辛與不棄、委屈與倔強、隱忍與豁達、智慧與執(zhí)著,若不是一位對音樂有真愛的人,絕不會堅持這么久,專注這么多年。他的創(chuàng)作看起來任性卻真的在古典音樂日漸式微的當下,走出了一條帶有鮮明風格的作曲之路。作為中國人,阿鏜骨子里一直推崇和喜歡的中國古典文學特別是詩詞是他作曲的根基,所以就不難理解他為何堅持寫格調(diào)高雅卻賺不了錢的藝術(shù)歌曲。他迷戀金庸小說,欣賞金庸小說里的人物,只為實現(xiàn)自己的大俠夢,所以他甘愿蟄伏十載,花費大量時間認真學習作曲技法,并最終通過苦學苦練打通了他作曲的任督二脈。從這點來說,我越來越理解阿鏜老師雖已古稀,卻在他的笑容中露出童真笑容的原因,因為他的世界里,音樂便是他最在乎的東西,這種執(zhí)著與純真是他一直懷有的初心,不管歲月更迭,從未更改。
阿鏜老師是一位具有真性情的音樂家,沒有世俗的心機,唯有瀟灑的豪情,喜歡喝酒就斟滿,喜歡的詩句就譜寫。因為他最傾慕金庸筆下的大俠令狐沖,所以阿鏜對權(quán)力才色恬淡無欲,卻醉心于追求真善美,他為早逝的好朋友寫主題變奏曲,他為一幅感動他的畫作寫?yīng)氉嗲U\然,阿鏜老師的音樂學習之路道阻且長,求學經(jīng)歷也頗為坎坷,但無論做什么,阿鏜老師都會把作曲放在人生重要位置。理所當然的,“幸運”也總會與阿鏜老師相伴。阿鏜老師在新書中,多次提及自己的幸運,比如有人資助他出版專輯、開音樂會等。阿鏜在音樂創(chuàng)作和演出中,一直都有老師、朋友的提攜和幫助,但幸運的背后,其實離不開有心人的準備。所以,別人眼中阿鏜的駕輕就熟其實得益于他的勤奮,而勤奮對于他來說,不僅是天助、人助更像是一種自助。
阿鏜老師的音樂是他抒情的內(nèi)核,而阿鏜老師的《故事》是他精神世界的外延,祝賀阿鏜老師新書的出版,感謝阿鏜老師對晚輩的信任,感謝可以讀到這本書的你,文至此,是為序。
(責任編輯 李欣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