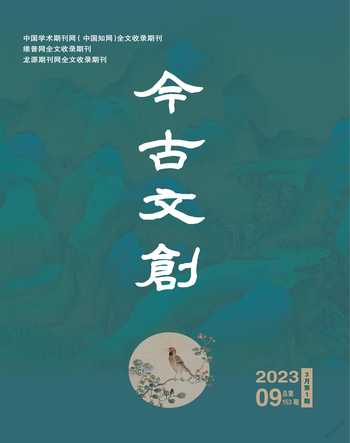《剪燈新話》與瞿佑的文藝觀
【摘要】瞿佑的短篇小說集《剪燈新話》摹寫元末的社會動亂以及文人命運,一個個短篇故事凝結著他豐富的人生閱歷及多方面的思想觀念,如懲惡勸善、因果報應的宿命觀,托言鬼怪、批判世道的鬼神觀,重視文華、炫才逞技的文學觀,重情重義、死生相隨的主情觀等,展示了瞿佑豐富的思想世界,表現了亂世文人的生存狀態,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
【關鍵詞】瞿佑;《剪燈新話》;亂世文人心態
【中圖分類號】I106?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3)09-0013-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09.004
瞿佑,字宗吉,號存齋、吟堂、樂全叟等,原籍山陽(今江蘇淮安),后徙居錢塘(浙江杭州)薦橋街。生于元至正元年(1341年),卒于宣德二年(1427年),享年87歲。瞿佑多才多藝,卻一生流落不遇,抑郁不得志。其創作的小說集《剪燈新話》記錄了一些瞿佑從好事者口中聽聞到的故事,遠不出百年,近止在數載,這些聞見經他加工創作,融匯了自身豐富的人生閱歷和思想感悟。因此,以《剪燈新話》為文本來反觀瞿佑的思想懷抱,從中探求瞿佑的宿命觀、鬼神觀、文學觀、主情觀等,對于《剪燈新話》和瞿佑研究的深化,無疑是很有意義的。
一、懲惡勸善,因果報應的宿命觀
元末明初是中國歷史上的大動亂時代,瞿佑遭此亂世,對戰亂災難和社會黑暗都有很大的感觸,所以其創作的《剪燈新話》一方面是想記錄社會動亂中發生的真實事件,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借一個個光怪陸離的故事來懲惡揚善。
瞿佑在《剪燈新話序》中表明自己創作的主旨是:“今余此編,雖于世教民彝,莫之或補,而勸善懲惡,哀窮悼屈,其亦庶乎言者無罪,聞者足以戒之一義云爾。”友人凌云翰為《剪燈新話》作的序中也說:“是編雖稗官之流。而勸善懲惡,動存鑒戒,不可謂無補于世。”懲惡勸善是瞿佑作為一個亂世文人的責任與擔當,而他實現懲惡揚善的方式之一就是宣揚佛教的因果報應思想。
佛教自產生之后,就與中國的社會和文化進行了長達數千年的融合,并滲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對中國古代小說創作的影響更是廣泛而深入,不但佛教故事成為明清小說的題材內容,而且許多佛家觀念也成了文學家創作的思維模式。
佛教對《剪燈新話》的影響,誠如葛兆光所言:“宗教與文學常常會不由自主地聯姻,前者刺激后者的想象,并提供大量神奇瑰麗的意象,因此,盡管文學家未必都是宗教的信徒,但仍然會受到宗教的影響,而一旦文學家受到宗教的影響,便往往會出現宗教式的思維、情感、意象不斷滲透文學領域的現象,使文學作品極為濃重地表現出這種與宗教有千絲萬縷聯系的感情色彩、意象群落。”
元代科舉廢除,儒生地位低微,知識分子的意志理想在亂世中旁落,尋不到仕進前途的瞿佑開始反觀儒家的文化觀念,主動接受佛教因果觀念的影響,以因果論世事,寓勸懲,探索新的價值觀念與文藝創作方法。
《三山福地志》中山東人元自實“生而質鈍,不通詩書”,但家產頗豐,他曾借給同鄉繆君二百兩銀作路費,因鄉黨相處之厚,未要求寫文券。“至正末,山東大亂,自實為群盜所劫,家計一空”,元自實于是前去投奔已經發跡的繆君,繆君卻因元自實無文券拒絕還錢。元自實走投無路之際動了殺繆君的念頭,后因心懷慈悲隱忍而歸,百般無奈之下投井自殺,幸至三山福地,得知事情的前因后果:他自己前世在職之時,因為文學自視甚高,不肯引薦后輩,故而今生懵懂不識字;前世以爵位自傲,不肯接納游士,故而今生漂泊無依。今生繆君此行不義,不出三年,時運變革,大禍將至。
《令狐生冥夢錄》中有個叫令狐生的人剛直不阿,不信神靈,其兇惡的鄰居烏老病死之后,因為家人廣做佛事竟然死而復生,令狐生因此賦詩以諷。后來地府聞知此詩,請令狐生至,令狐也得以趁機觀覽地獄,親眼目睹了那些生時作惡死后受到殘酷懲罰的陰森恐怖之象,看到了地獄中的因果報應。
《富貴發跡司志》中何友仁在富貴發跡司親耳聽見司主和判官講述因果報應的斷案過程;《永州野廟記》中畢應祥除妖去害,延壽一紀;《太虛司法傳》中馮大異因為正直被任命為太虛殿司法;《愛卿傳》中羅愛愛因為集孝順與節烈于一體,投胎轉世為男子,得以再續前緣。
瞿佑在《剪燈新話》中講述此類因果報應、輪回轉世的故事不在少數,通過這種因果循環的宿命觀來達到懲惡勸善的教化目的是瞿佑創作的重要思想特點,也體現出佛教已經成為一種文化積淀凝結在士人及民眾的心理結構中,影響到人們的行為方式和思想觀念。
二、托言鬼怪,批判世道的鬼神觀
《剪燈新話》收錄故事的時間范圍為元大德年間(1297—1307)至洪武七年(1374),其中一半以上的故事發生在元末最為動蕩的至正年間(1341—1370)。瞿佑正是在這段戰火中出生成長起來的,他親身經歷了避亂的波折與辛酸,這些苦難之下,他蘊蓄了豐富的情感和素材。明初,朱元璋為加強思想領域的控制,實行文禁,在嚴刑峻法的重壓面前,文人們為避免遭禍,于是學習唐人小說,借寫鬼怪神仙、閨情艷遇來委婉表達自己豐富的思想情志與對社會現實的不滿。瞿佑的《剪燈新話》中就有許多篇章順應時代潮流,借鬼神來批判世道,敘述戰亂給人民帶來的災難。
《水宮慶會錄》中,一位名叫余善文的白衣秀士,頗有才名,被廣利王邀請進南海龍宮為新建的宮殿撰寫上梁文,在宴會上余善文才驚四座,獲得眾神的一致好評,得到廣利王設宴重謝。《水宮慶會錄》作為《剪燈新話》的第一篇,有著深刻的隱喻含義。首先,余善文其實是擅長文學的瞿佑的自我真實寫照,文中全篇皆錄的上梁文也是作者著意表現自己的文學才賦;其次,對貧寒儒生禮遇有加的神仙廣利王則代表瞿佑對統治階級的殷切期望。《舊唐書》記載:“(天寶)十載正月,四海并封為王……義王府長史張九章祭南海廣利王。”從國家層面上推崇南海祭祀實際上是在宣揚王權君威,所以神仙廣利王一定程度上象征統治階級的護佑。元代知識分子地位極低,明代天下穩定后,朱元璋對知識分子的態度由開始的禮遇轉變為輕慢,甚至殺戮,《水宮慶會錄》中蘊含的深意不言自明。同時,廣利王來源于道教神仙譜系,瞿佑創造這一禮遇儒生的神仙形象也表明瞿佑的文藝創作受到道教鬼神觀的影響。《修文舍人傳》講述書生夏顏博學多聞,性氣英邁,然而名分甚薄,日不暇給,客死潤州,死后他的鬼魂來到人世與友人交談,告訴友人自己已經隸職冥司,并且詳細描述冥司的情形“黜陟必明,賞罰必公,昔日負君之賊,敗國之臣,受穹爵而享厚祿者,至此必受其殃;昔日積善之家,修德之士,阨下位而困窮途者,至此必蒙其福。”后來其友人在夏顏的勸說下,生病后不復治療,數日而終。文中夏顏的鬼魂講述的冥司情景與人間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友人寧可放棄生命也要前往陰間更是深刻地諷刺了現實的黑暗。《牡丹燈記》記敘奉化州判符君之女的棺木因為戰亂被臨時安放,后鬼魂寂寞,遂化為精怪害人的故事,黑暗的世道造成了鬼蜮橫行,又反過來損害世道,最終喬生延請高道開壇做法,將精怪驅捽而去。
明代洪武朝文字獄較多,瞿佑出于全身避禍的心理,借助道教神仙思想來勸善懲惡,批判黑暗的世道,表達對理想世界的向往。無論是佛教因果論還是道教鬼神觀,瞿佑的文藝創作都完成了知識分子的歷史責任。儒家提倡“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他并沒有抱守儒家思想一成不變,瞿佑在自己不得志時,也依舊從事自己的文字勸懲事業,他援佛道二家思想入于文學創作,體現了復雜圓融的文藝觀。
三、重視文華,炫才逞技的文學觀
瞿佑出生、生長于戰火之中,即便幾經輾轉流離,他都未曾放棄求學,這首先離不開生活環境的熏陶。瞿佑出生于明經世家,自幼便接受了正規的私塾教育,并且轉益多師,據《歸田詩話》記載,年少時曾從王叔載、其叔祖瞿士衡、祖姑丈楊仲弘等人學詩,且經常隨長輩拜會名家大儒,其才華獲得頗多贊譽稱賞。這樣的教育環境不僅使瞿佑在才學上有所進益,而且也形成了兼容并包的文學觀。
廣泛的唱和交游也增長了他的詩學才賦。少年時期瞿佑曾多次參加云間詩社的唱和活動,如楊維楨與凌云翰有香奩詩八首,瞿佑也和有香奩詩八首,凌云翰的詠雪、詠月詩,瞿佑也曾唱和過,在切磋唱和中,他的詩藝不斷精進。對此,瞿佑在《歸田詩話》中感激地說凌云翰的賜教、獎勸之功對自己有重要影響。瞿佑一生雖輾轉流離多地,但他也因此能夠不斷與當地的文人相互交流,博采眾長,錘煉詩藝,即便是在短篇小說集中,瞿佑也著力表現自己的詩才,炫耀文華。
第一,瞿佑的詩學才賦表現在《剪燈新話》中的詩詞韻語中。《剪燈新話》全書有二十一篇小說,其中插入的詩詞歌賦高達七十余首,甚至《水宮慶會錄》《聯芳樓記》《秋香亭記》等篇中韻語超過全篇字數的三分之一,其凸顯文學才賦的創作意圖顯而易見。這些詩詞韻語也極富藝術價值,首先,這些韻語眾體皆備。詞有《金縷詞》《木蘭花慢》《齊天樂》《沁園春》《臨江仙》《滿庭芳》等不同曲調;詩歌古體和近體皆全備,又分為四言詩、五言詩和七言詩等不同類型;駢賦對仗工整,音律和諧,這些韻語錯落在文言小說中,顯示出瞿佑的文采斐然。其次,這些韻語風格多樣。如《聯芳樓記》中的《竹枝曲》帶有清新的民歌意味,《水宮慶會錄》中的 “上梁文”語言典雅,對仗工穩,《天臺訪隱錄》中的詩詞淺易明白,各色的詩文風格與多樣的人物故事相得益彰。傳奇小說中詩詞韻語原本可有可無,除去之后并不影響基本故事情節的發展,但是瞿佑連篇累牘的穿插,或仿效前人,或自創新詩,使這些詩詞韻語成了故事情節的有機組成部分,如翠翠與金定重遇后不方便傾訴衷情,只能借詩詞隱晦達意,薛氏姐妹以詩詞與鄭生調情,推動故事情節發展。另外,一些原有的詩詞經瞿佑稍加改動,便能夠與小說意境相符,增添了小說的藝術魅力,如《鑒湖夜泛記》中成令言與織女的對話等,這些詩詞韻語都是瞿佑有意在炫耀自己的詩才文華。
第二,瞿佑的炫才意識還體現在他塑造的各色人物形象身上。瞿佑筆下的人物多是較有文化的階層,如《龍堂靈會錄》中以歌詩在吳地聞名的聞生,《華亭逢故人記》中富有文學的全、賈二子,《滕穆醉游聚景園記》中善于吟詠的滕生,《天臺訪隱錄》中粗通書史的徐逸,小說中“余善文”“成令言”的名字則更能直接透視出瞿佑的炫才心態。《三山福地志》中的主人公元自實是唯一一位愚懵不識字的人物,但他前世也是以文學自視甚高。小說中的女性形象亦是較有文化的階層,如吟詠不輟的薛氏姐妹、織女等形象,她們與男主人公志趣相投,詩詞唱和,成就了一段段可驚可嘆的佳話。
在文化環境的熏陶下,瞿佑培養起深厚的文學素養并以此為傲,他不遺余力地將自己的創作才賦表現在小說《剪燈新話》中,無論是寫作模式還是小說內容,都成功地展現出瞿佑的文學功力。文章中大量的詩詞歌賦,既能為小說語言添彩,又能塑造人物形象,推動故事情節發展。
四、重情重義,死生相隨的主情觀
元末雖遭戰亂,但社會環境相對自由、寬松,瞿佑也因此交友頗廣,對他影響最大的莫過于同為云間詩社成員的楊維楨。楊維楨名擅一時,寫詩主張性情說,認為詩歌創作要依情而出,這種性情說對經常互相唱和的瞿佑產生了極大的影響,表現在小說中即是有情便可以突破生死界限。
此外,楊維楨香艷的創作風格對瞿佑也頗有影響,瞿佑的作品中多青年男女悲歡離合的愛情故事,濃郁艷麗,反映出瞿佑尊情、重情,重視人的自然欲望的文藝觀念與創作風格。
《剪燈新話》中描寫愛情故事的篇幅較多,人與人相戀如《聯芳樓記》《渭塘奇遇記》《翠翠傳》《秋香亭記》,人與鬼怪遇合如《金鳳釵記》《滕穆醉游聚景園記》《愛卿傳》《綠衣人傳》,約占全書篇數的五分之二。
瞿佑在小說中正視人的自然欲望。《聯芳樓記》中蘇州薛姓富商之女蘭英、惠英姐妹在樓上玩耍時,看中船上的鄭生,便投下一雙荔枝表示愛慕之情,當夜,二女從樓上垂下一竹兜吊鄭生上樓,“相攜入寢,盡繾綣之意”。在這里,瞿佑并沒有把蘭英、惠英塑造成大戶人家的小姐一般恪守禮教規矩,而是敢于正視自己的欲望,大膽追求肉體上的歡愉。《金鳳釵記》中興娘則更為直率,半夜約會崔生并威脅其就寢,一系列坦蕩追求情欲的人物形象反映出瞿佑主情尚真的文學觀念。
瞿佑筆下的女子大膽追求愛情,為愛死生相隨。《渭塘奇遇記》中王生本是世族子弟,收租途中被一酒肆主的女兒相中,她見王生奇俊,便心生愛意,后相思成疾,最終魂逐王生入夢,“執手入室,極盡歡謔”。《翠翠傳》中劉翠翠與金定為愛舍棄生命,雙雙殉情。《滕穆醉游聚景園記》中衛芳華死后依然追求幸福,其魂魄與滕穆回鄉共度三年美好時光。《綠衣人傳》中綠衣人與趙源前世不能相守,今生以精魄之身也要再盡夫婦之情。這些女子都勇于追求自己的幸福,并且能夠為愛情突破生死界限,這種執著追求愛情的精神無不令人肅然起敬。
《剪燈新話》是一部情感豐富的作品,瞿佑的自序中說此書是要供自己閱讀,不做外傳,既是在這種前提下完成的作品,則更容易帶有個人抒情色彩。正視個人欲望,大膽追求愛情,為愛死生相隨,這種主情觀已經突破了傳統儒家學者“禮”的束縛,向“人”回歸,體現出瞿佑進步的創作觀念。作為熟讀圣賢書的文人,瞿佑雖然開始反觀儒家文化,向佛道二教尋求解脫之道,但他又沒有完全擺脫儒家倫理綱常的藩籬。如《渭塘奇遇記》的結尾,王生與酒肆女訂婚,明媒正娶,結為正式夫妻;《聯芳樓記》中雖然薛氏二女大膽追求鄭生,最終卻也沒有逃離禮法的規束,要求鄭生托人前去提親,三媒六禮,問名納采,完成婚禮的各項程序,為他們的愛情披上合法的外衣,這表現出瞿佑尊情重情的主情觀是戴著鐐銬在跳舞,無法真正超越當時的社會風尚,同時也反映出亂世中瞿佑真實的文藝創作觀念。
總之,瞿佑《剪燈新話》以元末動亂為時代背景,書寫兵火之余文人士子們的悲歡經歷,故事情節極幻極真,既真實地反映了瞿佑的亂世經歷,又光怪陸離地展現了其宿命論與因果論思想;既反映了其主情的進步觀念,又展示了其重文的情感態度。透過《剪燈新話》一個個短篇故事,展現出特定時代背景下瞿佑的生存狀態與思想世界,也體現出瞿佑反觀儒家思想,對佛道采取較為圓融態度的文藝創作觀念。
參考文獻:
[1]瞿佑.歸田詩話[M].明刻本.
[2]楊維楨.東維子文集[M].四部叢刊本.
[3]瞿佑.剪燈新話[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4]劉昫.舊唐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5:934.
[5]葛兆光.道教與中國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376.
[6]喬光輝.援道、釋以消儒——《剪燈新話》之《鑒湖夜泛記》主題解讀[J].明清小說研究,2021,(4):77-197.
作者簡介:
黃靜,女,山東臨沂人,青島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古代文學專業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