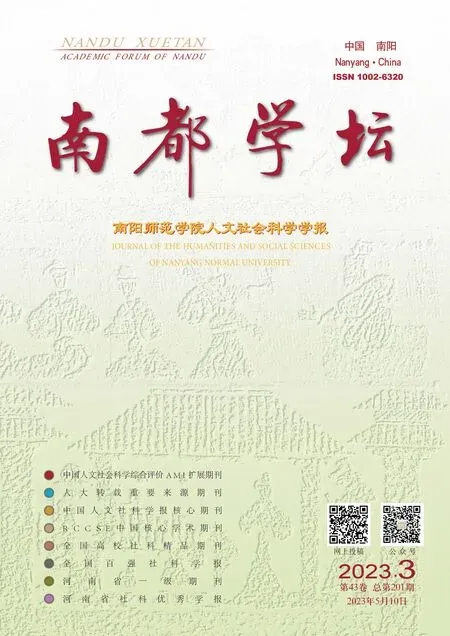“霍光故事”:霍光事跡的記憶與失憶
李 沈 陽
(濱州學院 黃河三角洲文化研究所,山東 濱州 256603)
漢武帝后元二年(前87)春,武帝病重,大司馬大將軍霍光等受遺詔輔佐少主昭帝。從那時起到漢宣帝地節二年(前68),霍光一度獨攬大權,是西漢中期政局中的關鍵人物。學術界涉及他的研究成果,集中在評價霍光的地位、考察霍光的影響和分析霍氏家族被滅族的原因三個問題上(1)第一個問題的相關成果詳見呂志毅《論霍光》,載《河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5年第1期;侯婕《昌邑王劉賀廢立史實考——兼論霍光的真實形象》,載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編《歷史文獻研究》第41輯,廣陵書社2018年版,第65-84頁;張國剛《霍光輔政:“昭宣中興”的功臣》,載《中國青年報》2018年2月14日,第5版;劉良亮《因循與變革:霍光主政時期對匈奴政策的演變》,載《甘肅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19年第2期;趙秋燕《西漢權臣霍光的軍事謀略探賾》,載《哈爾濱學院學報》2016年第7期。第二個問題的詳見江建忠《從霍光的政治行為看中國古代權臣的基本特征》,載《史林》1998年第4期;沈潛《霍光現象的警示》,載《炎黃春秋》2001年第3期;呂宗力《西漢繼體之君正當性論證雜議——以霍光廢劉賀為例》,載《史學集刊》2017年第1期。第三個問題的詳見蘇瑞卿《略論霍光滅族之禍》,載《煙臺師范學院學報(哲社版)》1995年第4期;鄧愛紅《西漢霍光家族悲劇的前因后果》,載《江西教育學院學報》1992年第2期;李峰《漢宣帝與霍光的權力博弈探析》,載《歷史教學(下半月刊)》2015年第12期;宋超:《“霍氏之禍,萌于驂乘”——宣帝與霍氏家族關系探討》,載《史學月刊》2000年第5期。。近年來隨著海昏侯墓的發掘,墓主劉賀被廢的原因再度引起學界熱議,而這又繞不開他與霍光的關系(2)此類成果較多,如廖伯源《昌邑王廢黜考》,載其所著《秦漢史論叢》,中華書局2008年版,第24-36頁;黃今言、溫樂平《劉賀廢貶的歷史考察》,載《江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2期;朱紹侯《易邑廢帝誨昏侯列賀經歷考辨》,載《南都學壇》2016年第4期;臧知非《劉賀立、廢的歷史分析》,載《史學月刊》2016年第9期;辛德勇《海昏侯劉賀》,三聯書店2016年版,第136頁;王子今《“海昏”名義補議》,載《南都學壇》2018年第5期。。
從縱向角度看,研究者對霍光的評價逐漸從消極趨向肯定,對霍氏家族滅亡原因的分析從簡單趨向復雜,而對霍光影響的總結則有待于深化。事實上,早在東漢前期,班固就在《漢書》中用“霍光故事”一詞概括其影響。《東觀漢記》《后漢紀》《后漢書》和《資治通鑒》等史籍也多使用此語,“霍光故事”成為考察霍光影響的專門術語。管見所及,律其林從直言諍友、針砭時弊和警諫于道三個方面概括了“霍光故事”在宋朝的運用[1],但他使用的“霍光故事”是自己的追述而不是宋代術語;蘇一博等在研究漢代“故事”時提及“霍光故事”在禮儀中的運用[2],其他研究者則極少著意。有鑒于此,本文對“霍光故事”進行解析,并以之為切入點探討漢代“故事”的共性,進而對中國古代“故事”的性質作一些思考。
一、霍光的生前與身后事跡
漢代“故事”名目繁多,或僅稱“故事”,或冠以職官,或冠以人名等。冠以人名的“故事”多與人物言行直接相關,這是形成“故事”的基礎。“霍光故事”的基礎即源自霍光的生前與身后故事。

后元二年(前87),漢昭帝即位時尚且年幼,皇位還不穩固。當時的輔政大臣雖然有幾位,但“政事一決于光”(4)辛德勇認為,此時霍光還無法隨心所欲,直到平定上官桀等人之后,才確立絕對權威,詳見其所著《建元與改元:西漢新莽年號研究》,中華書局2013年版,第195-196頁。,霍光也盡心輔政,大致保持天下太平,“昭帝既冠,遂委任光,訖十三年,百姓充實,四夷賓服”[3]2936,基本扭轉了漢武帝后期的頹勢局面,助推了昭宣中興的到來。其間,霍光還挫敗了奪取皇位的陰謀。此前漢武帝在位時,衛太子劉據、齊懷王劉閎和昌邑哀王劉髆已經去世,燕刺王劉旦和廣陵厲王劉胥因行為驕慢而被疏遠,漢武帝屬意的繼承人是昭帝,但劉旦并未放棄對皇位的追求。史載,漢昭帝即位后,劉旦探聽朝廷虛實,在得到朝廷賞賜后“怒曰:‘我當為帝,何賜也’”,“即與(宗室)劉澤謀為奸書,言少帝非武帝子,大臣所共立,天下宜共伐之”[3]2751-2753。劉旦的陰謀得到上官桀等人的支持。然而漢昭帝元鳳元年(前80),事情敗露,參與此事的上官桀、上官安和桑弘羊等人被滅族,劉旦和鄂邑長公主等人自殺。就輔佐昭帝和忠于昭帝兩方面而言,霍光確實如司馬光所評價的那樣對漢朝忠心耿耿:“霍光之輔漢室,可謂忠矣。”[4]
元平元年(前74)漢昭帝去世時,沒有子嗣,由誰繼承皇位再次考驗著霍光的政治判斷。本來,第一順位繼承人應是漢武帝唯一健在的兒子劉胥,他也一度得到群臣的支持,但霍光不這樣認為,他堅守著漢武帝的判斷,劉胥“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3]2937,他也不能用。在這種局面下,昭帝之侄——昌邑王劉賀成了最合適的人選。在征得上官太后的同意后,劉賀應召入朝,先被立為皇太子,隨后登基。劉賀在位僅僅27天,就因“行淫亂”[3]2765而被霍光聯合群臣奏請上官太后同意后廢除,他本人先是回到故地昌邑——王國被降為山陽郡,后被封為海昏侯。
劉賀被廢意味著皇位再次出現空缺。霍光召集群臣,商議皇位繼承者。這時,齊懷王和漢昭帝已絕嗣,廣陵厲王劉胥早已被漢武帝否定,燕刺王劉旦也因為謀反被誅殺,他們的兒子自然不能繼承皇位;現在又排除了昌邑哀王一支,漢武帝的近親之中,只有生活在民間的衛太子劉據之孫受到一致稱贊,于是霍光等奏報上官太后,漢武帝在世時,命令掖庭撫養和照顧曾孫劉病已,如今他已經18歲,不僅拜師學習《詩經》《論語》《孝經》,而且生活儉樸,慈仁愛人,可以作為昭帝的繼承者。此即宣帝。班固稱贊霍光“處廢置之際,臨大節而不可奪”[3]2967,擁立宣帝可謂例證。
漢宣帝即位后,沒有忘記霍光的擁立之功,把河北(治今山西芮城縣西)和東武陽(治今山東莘縣南)兩縣的1.7萬戶增封他作為食邑。然而他的家人還不滿足。漢宣帝冊封原先娶的妻子許平君為皇后,但霍光之妻想讓自己的小女兒霍成君為皇后,就指使女醫淳于衍毒殺許皇后,并勸霍光把女兒送入后宮,霍成君果然被立為皇后。從《漢書》本傳的記載來看,毒殺許皇后似乎不是霍光的本意。
漢宣帝地節二年(前68),輔政近20年的霍光去世,葬禮極為隆重,宣帝和上官太后親自吊喪,太中大夫與御史護喪,派軍隊送喪,賞賜葬品規格極高等。這還不夠,葬禮結束后,宣帝追思霍光的功勞,下詔免除他后代的賦役,其爵位和食邑不再遞減,世世代代不變。
言猶在耳。霍光去世兩年后,霍家便遭到滅族之災。其子霍禹被腰斬,侄孫霍云、霍山和女婿范明友自殺,其妻霍顯和女婿鄧廣漢被殺,其女霍成君廢處昭臺宮。此外,霍氏女眷的兄弟被處死,與霍氏有牽連的幾千家被滅族,不可謂不殘酷。
上述事跡中,有的是霍光主動抉擇的,有的則是他預想不到的。從此后歷史來看,時人對其事跡的選擇性運用——記憶和失憶卻出乎意料之外。
二、霍光事跡的甄選與“霍光故事”的形成
昭宣時期,霍光兼具權臣和外戚兩種身份,雖然漢宣帝即位后侍御史嚴延年就彈劾他“擅廢立,無人臣禮,不道”[3]3667,霍光更多時候還是以正面形象被后人記憶。從西漢末年開始,其生前事跡與身后發生的相關事件不斷被人援引,作為解決相似問題的參照。那些被援引的事跡以“霍光故事”的名義出現,形成“霍光故事”。
其一,“霍光故事”指霍光受賜食邑。漢平帝元始元年(1),王莽奏請太后王政君下詔,把他事先安排好的越裳氏進奉的白雉進獻宗廟,朝中大臣趁機強調王莽的策立平帝之功,認為“故大司馬霍光有安宗廟之功,益封三萬戶(5)按:《漢書》本傳稱霍光增封后,“與故所食凡二萬戶”,少于此處所言戶數。詳見《漢書》卷68《霍光傳》,第2947頁。,疇其爵邑,比蕭相國。莽宜如光故事”[3]4046。據《漢書》本傳記載,蕭何共食邑1萬戶,霍光共食邑2萬戶,最終,王莽增封召陵和新息兩縣的2.8萬戶,其后世免繳賦稅和徭役,爵位不變,封邑不會遞減,僅是食邑戶數就遠超蕭何和霍光。
其二,“霍光故事”指霍光之女嫁給宣帝。西漢末年,漢平帝在位時,王莽秉政,政治地位與霍光相似,因此“欲依霍光故事,以女配帝”。雖然太后不同意,王莽還是通過欺騙手段讓女兒進宮,借以抬高自己的地位[3]4009。當然,王莽依據的“霍光故事”,據《漢書·霍光傳》和《外戚傳(上)》記載,是霍光之妻霍顯的主意。漢宣帝本始三年(前71),霍顯聯絡宮廷女醫淳于衍害死皇后許平君,把霍成君送入皇宮,次年,霍成君被立為皇后。
其三,“霍光故事”指霍光備受哀榮。建武九年(33)春,輔佐光武帝建立東漢王朝的征虜將軍祭遵在軍中去世,光武帝悲痛不已,給予他像霍光一樣的高規格葬禮。祭遵的遺體被運到河南,光武帝詔令百官到舉行喪禮的地方集合,他本人則穿著喪服前往吊唁,哭得非常傷心。在返回城門經過送葬車隊時,他還止不住流淚,“親臨祠以太牢,儀如孝宣帝臨霍將軍故事”[5]。值得注意的是,“孝宣帝臨霍將軍故事”在《后漢紀》中表述為“孝宣帝臨霍光故事”[6],在《后漢書》中為“宣帝臨霍光故事”[7]741,對霍光稱呼的差異并不影響他們指的是同一件事。建武二十年(44),同樣追隨光武帝的開國功臣、大司馬吳漢去世,光武帝下詔哀悼,賜予“忠侯”謚號,而且“發北軍五校、輕車、介士送葬,如大將軍霍光故事”[7]684。安帝元初二年(115),太后鄧綏之兄鄧弘去世,“將葬,有司復奏發五營輕車騎士,禮儀如霍光故事”[7]615。直到魏晉時期,“霍光故事”的這層內涵仍被援引。曹魏嘉平三年(251)太傅司馬懿病逝,“天子素服臨吊,喪葬威儀依漢霍光故事,追贈相國、郡公”[8]20;前秦建元十一年(375)丞相王猛去世后,“謁者仆射監護喪事,葬禮一依漢大將軍霍光故事”[8]2933。
其四,“霍光故事”指霍光廢劉賀立宣帝一事。漢靈帝中平六年(189),靈帝去世,少帝劉辯即位。董卓入京后,權傾朝野,打算廢掉少帝,“欲依伊尹、霍光故事,更立陳留王”[7]2324。雖然有大臣反對,陳留王劉協還是被立為皇帝,即漢獻帝。“霍光故事”的這層內涵為權臣廢立天子提供了依據。曹魏嘉平六年(254),司馬師聯合朝中大臣上奏郭太后,認為曹芳不適合繼續當皇帝,“請依漢霍光故事,收帝璽綬”[9],曹芳被降為齊王。
在“霍光故事”的四層內涵中,第一層是最早記載的,見于《漢書》;第三層是被援引最多的,見于《東觀漢記》《后漢紀》和《后漢書》等;第四層是被援引最晚的,見于《后漢書》。從這些史籍作者的生活時代來看,《漢書》和《東觀漢記》的編撰者班固和劉珍等生活于東漢,《后漢紀》的編撰者袁宏生活于東晉,《后漢書》的編撰者范曄生活于南朝宋,《晉書》的編纂者房玄齡等生活于唐初,《資治通鑒》的編纂者司馬光生活于北宋。這意味著在東漢前期,漢代人即用“霍光故事”來稱呼特定的霍光事跡,而后世史家在追書時也多使用此語。
三、“霍光故事”所見漢代“故事”的共性
漢代之前,“故事”作為專有名詞已見諸史籍,如《商君書》的《墾令》要求秦國各級官吏嚴禁“博聞、辨慧、游居之事”,以免農民聽到奇談怪論,“則知農無從離其故事”;“知農不離其故事”[10],那么荒地就會得到開墾。但先秦典籍中出現“故事”的數量不多。從漢代開始,“故事”頻繁出現于簡牘、碑刻(6)竹簡如居延漢簡393.1A,木牘如尹灣漢墓簡牘YM6D5,碑刻如《太尉喬玄碑陰》等,分別見謝桂華、李均明、朱國炤《居延漢簡釋文合校》,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549頁;張顯成、周群麗《尹灣漢墓簡牘校理》,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37-39頁;嚴可均輯《全后漢文》卷77,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第776頁。和《東觀漢記》《后漢紀》等史籍中,并被時人廣泛運用于處理現實問題,體現出“故事”在漢代治國理政中的重要性。以“霍光故事”為切入點,可對漢代“故事”的共性進行分析。
第一,“霍光故事”體現了“故事”在社會運行中的作用。中國古人在治國理政時往往遵循一定的依據,如天象、律令、經典和“故事”等。據邢義田研究,故事與律令、經義是漢代政治活動中處理事務的三大依據[11]381。如上所述,無論西漢末年王莽增封食邑和把女兒嫁給平帝,還是東漢初年光武帝給予祭遵和吳漢高規格葬禮,乃至東漢末年董卓意欲廢掉少帝等,都援引“霍光故事”,以其不同內涵作為自己行動的依據。如果說引文中的“霍光故事”主要運用在禮儀(吉禮、兇禮)和政治領域,那么在祭祀、行政、軍事[12]和對外關系[13]等領域,同樣存在大量援引“故事”的情況。“故事”不僅為后人行事提供了依據,也提供了模式和程序,有利于問題的迅速解決。
第二,“霍光故事”折射出“故事”地位的模糊性。“故事”可以為解決相似問題提供依據,但后世在面臨相似問題時,非必遵循“故事”,是否遵循取決于事件參與者的主觀意愿。哀帝元壽元年(前2),丞相王嘉因封還哀帝賞賜董賢的詔書等事觸怒哀帝,哀帝讓他到廷尉詔獄。使者到了王嘉府上,掾史哭泣著給他和藥,王嘉不肯吃。主簿勸說道:“將相不對理陳冤,相踵以為故事,君侯宜引決。”[3]3501-3502王嘉不僅沒自殺,還把藥灑在地上,出門拜見使者接受了詔書,跟著去見廷尉,沒有遵循“將相不對理陳冤”的“故事”。前述鄧弘去世后,有司上奏按照“霍光故事”的規格送葬,鄧太后都一一拒絕,只許使用白篷車和兩名騎士,由鄧弘的門生拉著送葬,與有司奏請的五營輕車騎士規模相去甚遠,也沒有遵循“故事”。類似的情況還有很多。這就反映出漢代時的“故事”還不具備法律地位,不像律、令、科、比那樣屬于法律的組成形式(7)也有研究者認為“故事”屬于廣義的“比”,如中田薰說:“在漢代,比、科之外還編有‘故事’。由于‘故事’是指慣例,所以筆者想故事亦與比、科同樣,是適用律令的慣例集……可以說故事是廣義的‘比’之一。但因史料缺乏,不得其詳。”詳見中田薰《漢律令》,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中國古代法律文獻研究》第3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01-124頁。,也無法確保其權威性,它僅僅是處理相似問題的備選項。
第三,“霍光故事”佐證了“故事”形成主體的多樣性。漢代“故事”地位的模糊性與其形成主體的多樣性有關。從形成主體來看,人物、職官、習俗和年號等都可能成為“故事”,其中,人物包括皇帝,也包括官吏,正如邢義田指出的:“故事非必出自皇帝,臣僚的一言一行只要有人引為先例,也可以是故事。”[11]383皇帝言行形成“故事”的例子如竟寧元年(前33),漢元帝病重,傅昭儀和定陶王經常在身邊服侍,皇后和太子卻很少進宮探望。元帝病情加重,心緒不平,“數問尚書以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3]3377。元帝詢問的“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是指景帝前元七年(前150)“廢皇太子榮為臨江王”而“立膠東王徹為皇太子”[3]144之事。官吏言行形成“故事”的例子如“霍光故事”。形成主體的多樣性使“故事”難以像律令那樣,在等級分明的社會里適用于所有階層,這無疑會削弱“故事”的權威性,加劇“故事”地位的模糊性。
第四,“霍光故事”透露出“故事”在傳承中的去情境化。“故事”誕生于具體的情境,受當時各種因素的制約(8)從極端角度來說,在人生和人類發展的重大時刻,特殊環境下的無數偶然性制約著人的行為選擇,除非這些偶然性全部再現,否則,過去不會為現在提供什么啟示,正如政治思想家漢娜·阿倫特所言:“具體問題必須具體分析……對于就各種特殊情況作出判斷來說,沒有什么恒常的通行標準,也不存在什么特定無疑的規則。”詳見漢娜·阿倫特《反抗“平庸之惡”:〈責任與判斷〉中文修訂版》,陳聯營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3頁。。然而后世在提及“故事”時,受自身利益、立場等因素影響,把“故事”與具體情境剝離,即去情境化,對“故事”進行不同的解讀。王莽援引“霍光故事”以女配帝,主觀意圖是鞏固和強化自己的地位(“因以自重”),而史載當時的情境是:許皇后暴斃、霍成君入宮之事是霍顯一手謀劃,后來她“恐事敗,即具以實語光。光大驚,欲自發舉,不忍,猶與”[3]2952;董卓援引“伊尹、霍光故事”廢掉少帝,是想樹立自己的威望,所以尚書盧植提出反對意見:“以前太甲即位后朝政紊亂,漢昌邑王即位后犯有一千多條罪狀,所以伊尹和霍光才廢除他們的帝位。當今皇帝正處在年輕時候,沒有不當的行為,不能和他們相提并論。”[7]2324盧植所說劉賀在位期間“罪過千余”正是霍光廢除劉賀的具體情境,現在卻被董卓忽略掉了,“霍光故事”成了他達到個人目的的托詞。從這個角度上說,“故事”不僅被傳承,也被不斷地建構;被建構的“故事”不僅異于歷史,甚至是反歷史的,因為“歷史意識,就其本質而言,聚焦于事件的歷史性——它們發生于那時而不是現在,是從不同于現在的環境中發展而來”[14]4。
四、余論
就時間維度而言,治國理政的依據包括指向過去的經典和“故事”等,指向當時的律令、時令和天象等。“故事”的內容在很大程度上指向過去,對“故事”的重視亦即對過去的重視。過去的言行通過記錄和記憶而保存和傳承,匯入不斷累積且有待發掘的“資源”。一旦相似情境或事例再次出現,相應記錄就被激活,以“故事”的名義出現于時人言語中。那些被激活的言行就此成為“故事”,而那些未被激活的、甚至與激活的言行相反的言行,則處于失憶中,或者說被“邊緣化”,“當記憶并不反映我們的自我理解之時,我們就把它邊緣化了”[14]248,等待類似情境的出現。“霍光故事”的形成,體現了人們對霍光事跡的記憶和失憶,是漢代“故事”形成的一種模式,反映了漢代“故事”的諸多特征。
不同時期的治國理政會遵循不同的依據,同一依據在不同時期受到重視的程度也有差異。與先秦相比,漢代“故事”在漢宣帝時成為新增的治國理政依據,時任丞相魏相“明《易經》,有師法,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以為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三事”[3]3137,可見魏相曾整理漢代詔書并以之為“故事”[15]。也是在漢宣帝時,“故事”尤其是“漢武故事”被賦予祖宗權威含義,成為宣帝借此提升自身威望的工具[16],并被作為行政運作的基本方針。“霍光故事”就是在這個大的趨勢中進入時人視野,在漢平帝時期首次被援引,在東漢時與“呼韓邪故事”“石渠故事”和“元始中故事”一起成為被援引次數最多的四個“故事”之一[12]。
從中國法制史角度看,“故事”在漢代不是法律,也不屬于人類學者邁克爾·赫茲菲爾德(Michael Herzfeld)所說的“道德權威”(9)邁克爾·赫茲菲爾德指出:“在現實的行動中,作為一種靜態的形象,過往歷史的不可恢復和原初性往往起著重要作用。通過對行為的合法化確證,這種形象往往可以帶來某種永恒的道德權威。”詳見邁克爾·赫茲菲爾德《文化親昵》,納日碧力戈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159頁。,它僅僅為時人解決相似問題提供參照或者說選項,無論在制度規定還是時人觀念上,都不是必須遵守的,這使得“故事”在漢代社會中處于可能被遵循也可能被輕而易舉地否定的尷尬地位,因此它還有抬升的空間,一直到西晉、南朝時才確立其法律地位(10)《隋書·經籍志》載:“晉初,賈充、杜預,刪而定之,有律,有令,有故事。梁時,又取故事之宜于時者為《梁科》。”(詳見魏徵等《隋書》,中華書局1973年版,第974頁。)據此,“故事”在西晉初年與律、令并列,在南朝梁時單獨成卷,法律地位得到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