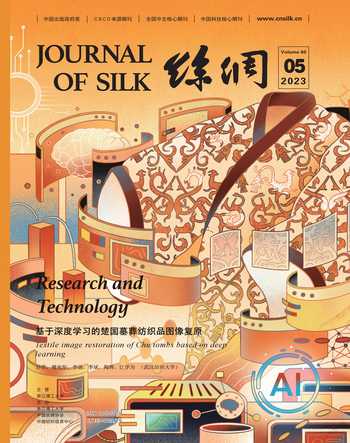薩珊王朝紡織品經典圖案研究與文化解讀



摘要: 公元3—7世紀,薩珊王朝通過圖案各異的紡織品打開了歐亞間的商業大門。借助頻繁的商貿、外交等渠道,薩珊王朝奢華的絲織品不僅遠銷各地,且對周邊的文化藝術產生了明顯影響,因此對其絲織品裝飾圖案進行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文化意義。文章依據薩珊王朝留存下來的織物為研究基礎,綜合文獻、考古及實物等多重證據為支持,考察了薩珊王朝絲織品上的聯珠動物紋、森穆夫圖案、三球式圖案及帝王登基與狩獵圖案。研究結果顯示,以上經典裝飾圖案的使用與流行背后受到了古波斯傳統文化、英雄崇拜及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影響。
關鍵詞: 薩珊王朝;絲織品;聯珠動物紋;森穆夫圖案;三球式圖案;帝王登基與狩獵圖案
中圖分類號: TS941.12; K876.9
文獻標志碼: B
文章編號: 1001-7003(2023)05-0120-07
引用頁碼: 051301
DOI: 10.3969/j.issn.1001-7003.2023.05.016
基金項目: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藝術學后期資助一般項目(19FYSB030)
作者簡介:
楊靜(1986),女,講師,博士,主要從事絲綢之路上的古代文化、藝術交流的研究。
薩珊王朝(Sassanid Empire,公元224—651年)是伊朗高原上繼阿契美尼德王朝(Achaemenid Dynasty,公元前550—前330年)之后最強大的王朝,建國者阿爾達希爾(Ardashir,公元224—240年)以宗族祖輩薩珊名字命名的薩珊王朝由此誕生。薩珊王朝當時的統治者首先通過復興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文化以期擺脫安息王朝時期受古希臘影響的設計與圖案;其次當時統治者對外來文化也持開放態度,因此,薩珊君主們創造了具有古波斯遺風的波斯藝術風格,并將其作為他們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這個開放且充滿創造力的時代,薩珊人創造的波斯圖案深刻地影響了歐亞地區裝飾藝術。在薩珊王朝的各類藝術中,絲織品不論從質地、顏色、圖案、設計等各方面均展示出了其紡織藝術的獨特之處。國家依靠絲織品上精美的設計與圖案打開了歐亞之間的商業大門,歐洲各地、土耳其、中國、日本、敘利亞、埃及及高加索等地發現的絲織品(或殘片)即為最好證明。隨著薩珊王朝國內不同城市間紡織工場的行業競爭,激發內部紡織行業新面料、花色的出現,這又為國家絲織品的對外貿易奠定了重要基礎。
關于薩珊王朝絲織品裝飾圖案的研究,學界已有不少討論。中國的學者多立足于中國出土且具有明顯薩珊裝飾風格的聯珠動物紋進行了深入的討論與分析,如獅紋[1]、聯珠大鹿紋[2]、狩獵紋[3]、森穆夫圖案等,以上研究成果側重于對某一特定裝飾圖案進行系統分析,研究內容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方面:首先是藝術層面的裝飾特點、藝術風格、造型演變等;其次是織造技藝;再次是與中國裝飾藝術的融合與改編。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以薩珊王朝的絲織品為研究主體,并結合同時期不同藝術門類所涉及的相關紡織圖像資料,重點分析了薩珊王朝絲織品上的幾款經典圖案,并予以解讀。
1 薩珊王朝的絲織品生產概況
公元3—7世紀的伊朗高原,絲綢織造業在伊朗各大城市中得到發展,特別是胡齊斯坦(Khuzestan)省的蘇薩(Susa)、舒什塔爾(Shushtar)、迪茲富勒(Dezful)、貢德沙布爾(Gundeshapur)及法爾斯省的法薩(Fasa)等地,不同城市生產的絲織品特色與種類也不盡相同。薩珊時期,各類優質絲織品的出現首先體現了統治者對該行業的支持,其次也是城市間行業良性競爭的結果。薩珊早期的伊朗商人不僅壟斷了從中國到羅馬的絲綢貿易權,還承擔了國內絲織品的大部分貿易。此外,薩珊王朝自身絲綢業的繁榮發展,不僅降低了早先對外國絲織品的高需求,也對羅馬帝國的絲綢生產與貿易活動造成了不良影響,以至于拜占庭的各大教堂被迫宣布法令,禁止使用來自薩珊王朝的絲織品。
沙普爾一世(Shapur Ⅰ,公元240—270年在位)戰勝羅馬后,國內經濟迅速恢復,還涌現出了新的職業與行業,羅馬和敘利亞的戰俘也參與了薩珊王朝各行業的生產活動。如名為頗希(Posi)的人即為一名羅馬戰俘的兒子,作為一位紡織技術精湛的織布工[4],他因擅長錦緞織造,還被晉升為胡齊斯坦省的紡織技術負責人,即所謂的工匠長(kirrōgbed)。沙普爾在位時,各個行業的生產環境也得到了改進,紡織行業得以復興。沙普爾二世(Shapur Ⅱ,公元309—379年在位)繼位之后,通過繼承阿契美尼德王朝的遺產及其本人良好的治國聲譽為國家帶來了大量財富,這為發展紡織行業奠定了重要基礎。他下令雇傭敘利亞和安條克(Antioch)的紡織技術人員,在薩珊不同地方參與并大力推廣先進的紡織技術,外來紡織技術人員的到來也進一步促進了紡織行業的發展。沙普爾二世在位時,皇家工場生產的迪巴(Diba)絲綢遠近聞名。薩珊的宮廷一方面向拜占庭、中亞出口生絲與絲織品;另一方面也將那些珍貴的絲織品作為外交禮物送至其他地區。公元6世紀以后,薩珊王朝的絲織品對周邊地區的紡織文化產生了明顯影響,拜占庭、中亞及中國的絲織品上就出現了薩珊王朝經典的紡織圖案。此外,隨著絲織品貿易進行的同時也促進了亞洲內部紡織技術的傳播。基于薩珊王朝絲織品的華麗與多樣設計,一些國家也對薩珊的絲織品進行了技術和設計方面的模仿、借鑒。薩珊王朝的紡織行業在國家的大力支持下,已經完成了從傳統的家庭式作坊向城市集中生產類型的轉變,并建立了相關的行業管理組織。而國內良好的公路網絡、道路安全與驛站的建設,也有助于將伊朗高原與歐亞大陸其他地區聯系起來,加快不同地域間紡織文化的交流與藝術的融合。
2 薩珊王朝典型的絲織品圖案
整體看薩珊王朝的各類藝術,包括紡織品上的裝飾藝術均反映出強烈的政治意圖與宗教象征意義。以紡織品為例,通過藝術主題和裝飾圖案等視覺形象清晰地反映出了社會階層的差異,如在皇室專用的絲織品上,一些圖案或是皇室權威的象征或是宗教信仰中某位神祇的物化化身,如雙翼、森穆夫圖案等。根據薩珊君主對于服裝的使用要求,絲綢是一種奢侈品,只有貴族才被允許使用,而君主和地位更高的貴族則可以穿錦緞制作的服裝[5]。君主送給朝臣的禮物同樣也反映出社會地位的差異,如國家重臣及軍事上的重要伙伴贈以裝飾華麗的榮譽長袍(khilat robe),這體現了君主的重視。薩珊王朝的藝術被認為是古波斯藝術的最后階段,其紡織藝術視覺語言的豐富、多變為以后伊斯蘭時代的紡織文化的繁榮奠定了至關重要的基礎。整體看,絲織品上顯著的裝飾圖案有以下幾種。
2.1 聯珠動物紋
雷奈·格魯塞(René Grousset)認為:薩珊王朝藝術具有雙重傾向,其一是用自然主義手法表現活的形體,其二是創造裝飾性圖樣和抽象的幾何圖案[6]。而在絲織品上的體現,有具象的動物圖案,風格化的植物圖案,還有幾何圖案及復合動植物圖案等。康馬泰(Compareti Matteo)博士認為典型的薩珊王朝織物裝飾圖案通常有三種:含有動物圖案,或獨立,或在行進隊列中;有一定的網格骨架;采用聯珠紋[7]。但實際上薩珊王朝紡織藝術的研究存在諸多避不開的困難,首先研究樣本的缺失;其次,盡管同期的金銀器、摩崖石刻等裝飾藝術可以為紡織藝術研究補充一些重要的參考資料,但這些補充的資料有些屬于薩珊晚期,其藝術形式已受域外的影響。關于動物圖案的織物,實物可參照一件織物殘片,該織物使用毛、棉制作,圖案為頸部系有飄帶行走的山羊(圖1(a))。對于動物與飄帶的結合,相關研究學者傾向于以下兩種釋讀,一是此動物用于皇室狩獵,二是某位神祇的象征。如瑣羅亞斯德教中的勝利之神和戰神(或軍神)韋雷特拉格納(Verethraghna/Vrθraγna)的化身之一就是山羊。飄帶作為薩珊王朝藝術的一個重要標志,還可見于印章、銀器、雕塑上的王冠與御馬的腿部。另外,動物身上的飄帶應該還與古波斯皇室專用的披帛有關,一般認為系有飄帶的動物為皇室專有。
聯珠紋作為歐亞大陸上廣為流傳的一種裝飾圖案,一直吸引著學者的廣泛關注。聯珠紋并非主題圖案,而是結構或骨架圖案,類似中國裝飾語境中的團窠紋。事實上,考古發現顯示,聯珠紋在阿契美尼德王朝之前的青銅器及金銀器中已有使用。目前對其文化內涵的解讀,并無定論。對聯珠紋的研究也是薩珊王朝裝飾研究的一大難題,尤其是在紡織品領域。因為聯珠紋在織物上的使用地域非常廣泛,除了伊朗的薩珊王朝外,同時期的拜占庭、中亞粟特、埃及、中國及高加索地區的織物上均有出現,甚至薩珊王朝結束之后的倭馬亞(Umayyad Caliphate)、塞爾柱克(Seljuq Empire)等王朝也在持續使用。因此在界定某些具有聯珠紋織物的歸屬地上存在不確定性。
盡管聯珠紋的使用流行于不同的時代與地域文化中,但薩珊王朝的聯珠紋珠粒較大,馬爾夏克(Marshak)[8]認為這種珠粒較大的聯珠紋為薩珊王朝聯珠紋,出現于公元550年之后,至公元600年才真正廣為流行。但從考古圖像資料看,早于7世紀的哈吉阿巴德遺址中出土的建筑雕飾(圖1(b))上,已有大顆聯珠紋與單體動物的結合使用,因此對大顆聯珠紋的使用時間可以往前推進一些。有一點可以肯定,即薩珊王朝的裝飾圖案對周邊的裝飾藝術產生了深刻而積極的影響。考古資料顯示聯珠紋還會使用在薩珊王朝貴族的府邸建筑雕飾、摩崖石刻、銀器及錢幣上等。因此有學者認為在伊斯蘭時代前的伊朗,聯珠紋的使用和生產僅限于薩珊王朝的灰泥雕塑,而非紡織品[9],但一件被鑒定為公元5—7世紀的織物片段(圖1(c))為聯珠紋在織物上的出現提供了重要參考,然對其制作的判定時間跨度較大,因此還需要更多的紡織實物加以證明。不過,織物上聯珠紋的集中使用時間為薩珊王朝晚期的判定已被學界越來越多的學者所認同。整體看,薩珊王朝的聯珠動物紋中的元素有:獨立的翼馬、有翼對馬、對羊、森穆夫等。
2.2 森穆夫圖案
森穆夫(Simurgh)圖案不僅見于紡織實物(圖2),也可見于伊朗西部的克爾曼沙赫市塔克-伊·布斯坦(Taq-e Bostan)石窟內的摩崖石刻上,庫思老二世(Khosrau Ⅱ,公元591—628年在位)的服裝上,森穆夫造型為狗頭、狗爪(或獅爪)、鷹翼、雀尾(或鼠尾或魚尾)、身有鱗片的混合動物。森穆夫的身上有時還會出現植物元素,其他圖像資料則顯示,有時森穆夫的身上還會出現植物元素及森穆夫與生命樹相結合的圖案。盡管森穆夫圖案的造型與文化內涵到目前為止依然爭議頗多,但多數學者認為這種復合型的動物造型與皇室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且將森穆夫與古波斯文化中法爾恩(Farn)聯系在一起,象征了財富與榮耀。
根據森穆夫的不同組成元素,學界也從不同的角度予以闡釋,于爾根斯邁爾教授與魯夫教授在《世界宗教百科全書》中指出“因為犬視被認為可以避開惡靈,因此狗在瑣羅亞斯德教教徒的葬俗中扮演著重要角色”[10],此外,狗還可驅趕惡魔,消除污染等。根據宗教教義的規定,在善的創造中,狗僅次于人;狗被視為生者和死者之間充當媒介的生靈[11]。在《阿維斯塔·萬迪達德》(Avestan Vendidad)中,不僅有一章節描述了狗的種類,還敘述了狗的各種美德。此外,狗(犬)在瑣羅亞斯德教信仰中有著“至善”本質,它們是諸善端動物的突出代表,必須得到人類全力保護,若虐待它們,就會受到嚴厲懲罰[12]。鷹翼造型改編自阿胡拉·馬茲達的雙翼造型,取其一半放在了森穆夫的身上。關于雀尾造型與印度古代文化有關,也受到了古波斯文化的影響,即荷浦·威爾奈斯(Hope Werness)所說的“在古老的伊朗,孔雀屹立于生命樹的旁邊……它扇形的尾巴象征著宇宙精神的輻射”[13]。孔雀在瑣羅亞斯德教教徒的心中也是圣鳥,是女神安娜希塔的象征。康馬泰博士認為“這種復合動物暗示了一個主權國家的聯合體,它在塔克-伊·布斯坦的出現暗示著帝王與伊朗東部的聯系”[14]。此外,森穆夫也出現在拜占庭的絲織品上,不過其使用弱化了它原有的象征意義,反而凸顯了其裝飾性。
依據筆者的研究,針對森穆夫擁有獅爪的理解可從獅子在伊朗文化中的地位談起,古波斯文化中,獅子被認為是勇氣、驕傲、權利、慷慨的象征,將獅爪與森穆夫結合在一起,可能是為了展示皇室的威嚴與慷慨。薩珊王朝之前,獅子被認為是密特拉(Mitthra)或太陽神的象征。也許薩珊王朝的藝術家們從古代的獅子圖像中,如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的獅子與公牛搏斗的圖像中找到了創作靈感。自阿契美尼德王朝開始一直到近代的愷加王朝,獵殺獅子的傳統或宮廷狩獵已成為君主與皇室權力與威嚴的集中展示,而獅子圖案背后的文化內涵也被伊斯蘭時代的各宮廷所沿用,這背后還與經典文學作品的推波助瀾有關。以上解讀也解釋了古波斯不同的藝術種類上均可看到獅子的身影,如火神廟、宮殿浮雕、器皿及珠寶裝飾中。邁赫達德·奇雅(Mehrdad Kia)教授認為“歷史學家塔巴里寫到,巴赫拉姆之所以成為薩珊王朝的君主,是因為他通過殺死獅子展示出了卓越的勇氣。”[15]塔克-伊·布斯坦摩崖石刻上,庫思老二世服飾上的森穆夫圖案屬薩珊晚期,因此如果對薩珊織物上的森穆夫圖案有更為理性認知的話,還需參照諸如壁畫、銀器與建筑雕飾等其他藝術類型和實物資料。
針對森穆夫圖案在歐亞大陸的傳播與部分程度的改編,影山悅子(Etsuko Kageyama)認為“森穆夫圖案源自薩珊王朝,并在整個中亞地區廣泛傳播”[16]。本文贊同影山悅子的說法,同時認為公元7世紀以來的森穆夫圖案在亞洲東部的出現可能更多的是受到了中亞粟特藝術的影響,如撒馬爾罕的阿弗拉西阿卜(Afrasiyab)大使廳壁畫上,有交波框架內填充獨立的森穆夫圖案,旁邊一位人物的服裝上則是團窠豬頭紋圖案。粟特藝術包含諸多薩珊王朝的藝術元素,已成為學界共識,特別是織物上的動物圖案更是受到了薩珊王朝紡織藝術的深刻影響,但二者在具體的使用上有所區別。從目前搜集的實物圖像資料看,具有森穆夫圖案的織物(包括銀器)出現時間較晚,雖然薩珊王朝的文化藝術具有強烈的輻射影響,但中古時期粟特人隨著絲路的繁盛獲取了大量財富,其藝術也隨之發展,所以不能排除粟特藝術的影響,而且同屬伊朗文化圈的一些裝飾圖案在最初來源的判定上本就錯綜復雜,需要大量的實物圖像加以佐證,因此其傳播路徑的溯源也存在一定困難。
2.3 三球式圖案
薩珊王朝的絲織品上,特別是與皇室環境有關的場景中,三球式圖案較為流行,它多出現于皇室人員的宮廷服裝或與皇室相關的織物上,但遺憾的是考古發掘中鮮有紡織實物,它們可見于銀器、石雕等藝術種類上。戈德曼[17]教授認為三球式圖案是唯一一種被薩珊王朝的宮廷和貴族采用的一種紡織裝飾圖案。參照其他圖像資料可知,除了服裝(圖3)與馬鞍毯外,三球式圖案還可見于巴赫拉姆二世、納斯爾及庫思老二世銀幣的祭壇上。如果立足于薩珊時期的紡織裝飾角度,較早有三球式圖案的服裝可見于公元4世紀的哈吉阿巴德壁畫上。在公元4—7世紀的薩珊銀器上,三球式圖案出現的頻率更高。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藏的一件銀器上,騎著駱駝的巴赫拉姆五世與阿扎迪在野外狩獵的場景中,巴赫拉姆與阿扎迪的服裝上、馬鞍上均有三球式圖案。在各大博物館的藏品中,三球式出現的場景均與皇室活動有關,如帝王狩獵、加冕宴飲及皇室婚禮等。塔克-伊·布斯坦的石窟最深處,頂部有題為《君權神授》的浮雕,其中阿胡拉·馬茲達的衣服和庫思老二世的半月形頭飾上均有三球式圖案,如圖3(b)(c)所示。研究薩珊王朝服裝上的三球式圖案,可看出它出現的位置具有強烈的指向性,或皇室服裝,或主神的服裝或宗教祭壇等。那么,對此圖案的出現與使用就需要從宗教層面對其進行解讀。
以瑣羅亞斯德教為國教的薩珊王朝,三球式圖案可能象征了靈光(Farr)來源或提供者,靈光作為古波斯文化中一個十分重要的觀念,在《亞什特》各篇中,靈光被尊奉為“凌駕于一切造物之上”的神明,這顯然是善神神主的象征,代表著馬茲達的神力、恩賜與庇佑[18]。靈光在古波斯的文化中,寓意權力和威嚴的降臨,有靈光籠罩和護佑的帝王既象征王權的合法性,也意味著國家的繁榮與昌盛。三球式圖案也是天狼星提什特里雅(Tishirya)的藝術化表現。從靈光再現的角度解釋了為什么三球式圖案的出現多與薩珊王朝的宮廷藝術或宗教藝術有關。站在藝術母題的角度,這個圖案則非常古老,它跨越了歐亞大陸,在不同時期,不同的宗教文化背景下均有使用[19]。目前的考古發現顯示,呈三角形排列的三球式圖案在公元前3100年的兩河文明藝術中已有使用,因此對它進行的解讀需要站在更加宏大的時空觀內。薩珊時期的藝術與宗教信仰緊密聯系在一起,所以在薩珊王朝這個特定的時間內,從宗教角度對其進行的解讀具有重要的參考意義和理論價值。不過到了薩珊末期及伊斯蘭時代的各政權中,三球式圖案的使用范圍愈加廣泛,它與植物圖案結合使用,或獨立使用,或變成四個點的造型等。
2.4 帝王登基與狩獵圖案
薩珊時期的帝王登基和狩獵圖案是經典的藝術主題或圖案,可見于不同藝術種類上,且此類主題的織物生產于皇室工場,其使用也有明確的指向性。主題圖案中的君主姿態、所用的武器及其他藝術元素均反映了帝王的榮耀及宗教信仰。不過據對現有資料的考察,狩獵圖在絲織品上的使用頻率不如銀盤。帝王登基圖可見于一件公元7—8世紀的薩米特(Samite)絲織品(圖4)上,它采用了斜紋緯重組織,從技術層面看,屬于經線加Z捻的中亞系統斜紋緯錦,不過其圖案則體現了薩珊時期的裝飾風格。因此,它可能由薩珊人生產,但也不排除是在伊朗定居的倭馬亞工匠或者其他地區工匠的仿制品。此外,織物上的紅色也體現出與薩珊王朝的聯系,因為紅色不僅被薩珊君主偏愛,也是阿契美尼德王朝皇室的專屬色彩。上述織物的主題圖案分為兩個部分,分別為庫思老二世登基圖和生命樹圖案,生命樹上有薩珊王朝常見的圖案,如葡萄、變體的雙翼圖案、蓮花和棕葉飾的復合圖案等。織物上使用君主肖像一直是古波斯文化中一個持續流行的藝術現象,到了薩珊時期,君主下令在宮廷服裝面料上設計的圖案,無論是自己的肖像,還是其他的圖案設計,背后具有特殊的政治目的。
帝王登基與狩獵圖案上可見雙翼王冠的造型,它是薩珊藝術中流行的藝術元素之一,雙翼在古波斯帝國被視為高貴的象征,不僅象征了神靈,背后還蘊含著強烈的王權意識。雙翼圖案可能改編自阿契美尼德王朝的雙翼太陽圓盤,瑣羅亞斯德教的主神馬茲達的形象也為雙翼造型。到了薩珊時期,馬茲達主神巨大的雙翼被薩珊的藝術家們提取出來并改編為對稱的雙翼造型,它還可見于泰西封6世紀的灰泥雕飾(圖5(a))及薩珊君主的錢幣與王冠(圖5(b))上,一些學者[20]認為雙翼王冠是戰神韋雷特拉格納的象征。不管從何種角度對其進行解讀,雙翼圖案的頻繁使用可見其在古波斯文化中的重要性,這背后避不開政治、經濟、宗教等層面的影響。在古波斯文化中,葡萄和生命樹是生育、不朽、吉祥、祝福的象征。庫思老坐于鋪有地毯的寶座上,君主的寶座兩旁各有一只羱羊,君主雙手各持一朵紅色蓮花,頭戴聯珠雙翼王冠,服裝為飾以羅塞蒂(Rosette,或譯為圓花飾)圖案的卡夫坦(Caftan)長袍。蓮花在阿契美尼德王朝文化中是王權的象征,在波斯波利斯遺址中,有君主或王子手持蓮花(圖6)的圖像(也有學者認為是石榴花)。織物上的帝王狩獵圖在薩珊王朝本土發現的不多,但可見于同時期的敘利亞、埃及、拜占庭及中亞等地。從搜集實物資料看,飾以帝王登基圖和狩獵圖的織物多采用薩米特技術,此類織物的價值可媲美黃金,因此除了供皇室成員使用外,還會作為外交禮物送至其他宮廷。
3 結 語
薩珊王朝的絲織行業因多樣的裝飾藝術不僅得到了本國權貴階層的喜歡,也隨貿易、外交等形式傳播至其他地區。薩珊王朝的紡織藝術作為伊朗古代絲織品生產和視覺藝術發展歷程中的重要一環,那些經典的裝飾圖案在伊朗的裝飾系統中,不僅起著承上啟下的重要作用,還為伊斯蘭信仰時代的裝飾藝術奠定了基調。伊朗高原上的狩獵圖案和三球式圖案甚至遠在阿契美尼德王朝建立之前或者在周邊更加古老的文化中已有較長的使用歷史,而今天它們依然得以沿用。織物上流行的聯珠動物紋、翼馬圖(翼馬是密特拉教傳統中勝利之神的象征)、森穆夫圖案、三球式圖案等,不僅在本土各類藝術門類中得以使用,亦得到了周邊文化的認同、模仿、改編與創新。立足于文化層面,薩珊王朝的視覺藝術中體現了顯著的宗教二元論、帝國構想、英雄崇拜及樸素的宇宙觀等思想,但其視覺系統的建立與完善也從周邊的文化中汲取了養分。隨著新政權的建立及絲路文化的繁盛,一些圖案隨貿易、外交等形式進入其他地區,那些薩珊王朝的經典圖案也隨之被拆解、部分挪用及重新組合等,變成了新的裝飾圖案,然而一些藝術元素、圖案及色彩傾向的前后繼承性或者使用慣性還能依稀可辨,這證明了古波斯文化的延續性與靈變性。
參考文獻:
[1]尚澤麗, 王樂. 唐代絲織品中的獅紋及其文化源流探究[J]. 絲綢, 2022, 59(6): 118-126.
SHANG Zeli, WANG Le. Research on the lion motif in the Tang Dynasty silks and its cultural origin[J]. Journal of Silk, 2022, 59(6): 118-126.
[2]許詩堯, 王樂. 吐魯番出土聯珠大鹿紋錦研究[J]. 東華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22, 22(2): 30-36.
XU Shiyao, WANG Le. The study on the samite with stag motif from Turfan[J]. Journal of Donghua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2022, 22(2): 30-36.
[3]孫志芹, 李細珍. 薩珊藝術東漸下狩獵紋錦藝術流變與織造技術特征[J]. 絲綢, 2021, 58(9): 100-109.
SUN Zhiqin, LI Xizhen. The evolution of empires hunting pattern brocade during the eastwardspread of Sasanian art and its weaving technical features[J]. Journal of Silk, 2021, 58(9): 100-109.
[4]TAHVILDARI N P, FARBOD F, MEHRPOUYAN A. A historical contextual analysis study of Persian silk fabric: (Pre-Islamic Period-Buyid Dynasty)[C]//Proceedings of Socioint 2017-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2017: 1136.
[5]CANEPA M P. The Two Eyes of The Earth: Art and Ritual of Kingship between Rome and Sasanian Iran[M].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9.
[6]雷奈·格魯塞. 近東與中東的文明[M]. 上海: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1981.
GROUSSET R. The Civilizations of the East: The Near and Middle East[M].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1981.
[7]康馬泰. 唐風吹拂撒馬爾罕[M].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17.
COMPARETI M. The Tang Wind Blow Samarqand[M]. Guilin: Lijiang Press, 2017.
[8]馬爾夏克. 突厥人、粟特人與娜娜女神[M].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16.
MARSHAK B. The Turks, The Sogdians & Goddess Nana[M]. Guilin: Lijiang Press, 2016.
[9]BROMBERG C A. Sasanian stucco influence: Sorrento and East-West[J]. Orientalia Lovaniensia Periodica, 1983, 14: 247-267.
[10]JUERGENSMEYER M, ROOF W C. Encyclopedia of Global Religion[M]. 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s, 2011.
[11]瑪麗·博伊斯. 伊朗瑣羅亞斯德教村落[M]. 北京: 中華書局, 2005.
BOYCE M. A Persian Stronghold of Zoroastrianism[M].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5.
[12]張小貴. 波斯多善犬: 古伊朗犬的神圣功能[J]. 世界歷史評論, 2021, 8(3): 43-59.
ZHANG Xiaogui. Many good dogs: The sacred function of the dog in ancient Persia[J]. The World History Review, 2021, 8(3): 43-59.
[13]WERNESS H B. The Continuum Encyclopedia of Animal Symbolism in World Art[M]. New York: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2007.
[14]COMPARETI M. Observations on the rock reliefs at Taq-i Bustan: A late Sasanian monument along the “Silk Road”[J]. The Silk Road, 2016, 14: 71-83.
[15]KIA M. The Persian Empire: A Historical Encyclopedia[M]. Santa Barbara: American Bibliographical Center-Clio Press, 2016.
[16]COMPARETI M, RAFFETTA P, SCARCIA G. Eran ud Aneran: Studies Presented to Boris Ilich Marshak on the Occasion of His 70th Birthday[M]. Venice: Libreria Editrice Cafoscarina, 2006.
[17]GOLDMAN B. The later pre-islamic riding costume[J]. Iranica Antiqua, 1993, 28(1): 218.
[18]元文琪. 二元神論: 古波斯宗教神話研究[M]. 北京: 商務印書館, 2018.
YUAN Wenqi. Dualism: A Study of Ancient Persian Religious Mythology[M].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8.
[19]楊靜. 從三球式圖案看古代歐亞文化的交融[J]. 中國美術研究, 2020(4): 159-167.
YANG Jing. On the integration of ancient Eurasian culture from the triple-ball pattern[J]. Research of Chinese Fine Arts, 2020(4): 159-167.
[20]STINE B. Using Imagesin Late Antiquity[M]. Oxford: Oxbow Books, 2014.
Abstract: Thanks to the superior geographical location, convenient trade along the Silk Road and high demand for luxury silk products between Europe and Asia, the silk fabrics of the Sasanian Empire were spread to surrounding regions. Though the silk industry of the Sasanian Empire had a certain scale with the strong support of the monarchs, and the textile decoration patterns were diverse, the author focuses on pearl roundels with animal patterns, simurgh patterns, triple ball patterns, enthroned king and hunting patterns in this article. Although the above-mentioned patterns were popular and spread far and wide in the Sasanian Empire, their initial use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more ancient Mesopotamian plain civilization, and some artistic elements can also be seen in the Achaemenid Dynasty. The monarchs of the Sasanian Empire hoped to get rid of the influence of Greek art and establish a unique local decoration system on the basis of ancient Persian traditional culture. Therefore, on the one hand, they advocated the revival of ancient Persian culture in order to establish cultural relations with ancient times. On the other hand, the final establishment of decorative patterns is also the result of the collision of cultural factors in different periods and regions. Thus,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study the decorative patterns of Sassanid silk fabrics.
The author took several classic textile decorative patterns of the Sasanian Empir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studied the four classic patterns with the help of evidence from philology, archaeology, and iconography. This paper aimed to analyze the modeling characteristics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s of several decorative patterns of the Sasanian Empir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ancient cultural blending and mutual learning. Research shows the decorative patterns and dazzling colors of the Sasanian Empire first inherited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ancient Persia. With an open cultural attitude, the monarchs also actively absorbed nutrients from the surrounding culture and modified them to some extent, making them unmistakably accord with Sasanian aesthetic. Secondly, those classic decorative patterns concentratedly reflect their religious beliefs, and their spread is also related to the advocacy of royal authority. To sum up, the decorative arts of the Sasanian Empire have a complex and obvious fusion tendency.
In this paper, several classic decorative patterns on Sassanid silk fabrics are discussed systematically and deeply, and their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is made according to their modeling characteristics. Due to the lack of physical textile samples of the Sasanian Empire and the large span of some samples, other types of art of the Sasanian Empire, such as architectural carvings, cliff carvings and silver coins, also provide important academic reference for this study. The study of the classical decorative patterns of the Sasanian Empire is not only conducive to the clarification of Central Asia and Byzantium,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age of the fabric excavated by archeology and the multicultural analysis of decorative art, but also provides important academic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expansion and improvement of the decorative systems of various regimes in the Islamic era.
Key words: Sassanid Empire; silk fabrics; pearl roundels with animal patterns; Simurgh patterns; triple ball patterns; enthroned king and hunting patter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