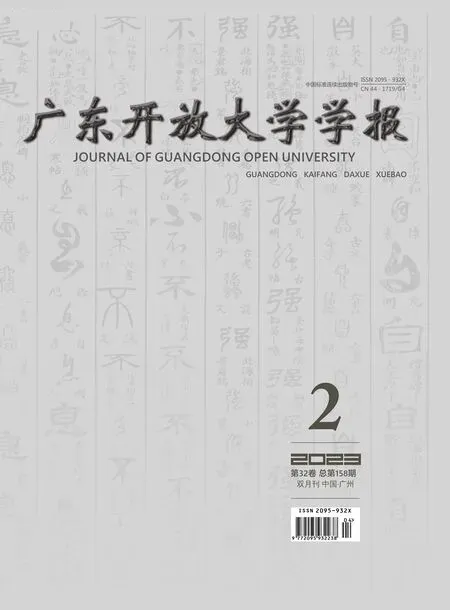近十年交互研究的發展脈絡與展望
——基于2011-2020年國內教育技術學期刊的內容分析和知識圖譜研究
尕藏草 馮紫欣
(1.西北民族大學,甘肅蘭州,730030;2.南昌大學,江西南昌,330031)
一、問題的提出
交互研究是教育技術學研究的重要領域。在教育技術學學科范疇下,無論是科學研究還是教學實踐,交互往往分為兩類,一類為人際關系型交互,指向同伴交互、師生交互、群體交互等;另一類為技術中介型交互,包括學習者與設備、學習平臺、教育軟件等之間的交互,以及學習者和由技術呈現的學習資源、學習環境之間的交互。穆爾(Moore)對遠程教育交互的劃分,就包括上述兩類,分為學習者與學習者、學習者與教師、學習者與遠程平臺內容、學習者與數字界面、教師與遠程平臺內容等[1]。陳麗、王志軍等對遠程教育教學交互的界定亦接近上述兩類[2]13-14[3]36-37。
隨著人工智能教育、教育大數據、教育元宇宙等新型技術的發展,技術中介型交互突破了以往人與機器(設備、界面環境)的交互,擴展為機器與機器、機器與環境、現實環境與虛擬環境、虛擬環境與虛擬環境等的交互。交互從兩個對象間的雙向影響和作用變成為一種人、物和環境之間互相發生的多邊影響、多項效應的作用。交互研究也必將面臨技術迭代、范式轉換的新時期。
本文通過對近十年(2011-2020)教育技術學交互研究的綜合分析,梳理交互研究的現狀、特征、發展趨勢和存在的問題,希望為交互研究在新型科學范式和技術社會興起下提供新思路和新視野。
二、研究設計
(一)內容抽樣
本文選擇《電化教育研究》《中國電化教育》《現代教育技術》《現代遠程教育研究》《遠程教育雜志》《中國遠程教育》和《開放教育研究》七種教育技術學學術期刊作為研究樣本,這七種學術期刊能夠綜合反映我國教育技術學交互研究的現狀。
在中國知網數據庫中,對上述七種期刊從2011至2020年間的論文進行關鍵詞高級模糊檢索,關鍵詞選擇“交互”“教學交互”“交互性”“互動”。剔除不相關論文后,有372篇論文成為本文的研究樣本。
(二)類目表設計
本研究內容類目總共分為兩級維度,一級維度包含6個類目。首先結合我國教育技術學交互研究和交互教學實踐,分為人際關系型交互(A)、技術中介型交互(B);其次參考其他學者的概念界定和分類[4-5],加入交互影響與分析(C)、交互過程與質量(D)、交互策略(E);最后,考慮到交互除了具備教學過程的屬性之外,還包括交互感知屬性,因此加入交互感知(F),共形成6個一級類目。再通過文獻分析和研究者的討論,將6個一級類目細分為22個二級類目(表1)。

表1 交互研究內容類目表
(三)信度效度分析
為了平衡編碼過程中編碼員主觀評判對研究信度的影響,首先對本研究的3位編碼員進行編碼培訓。當編碼員之間編碼一致性比較穩定后,開始編碼。
根據復合信度系數公式測算出三位編碼員的信度達到0.91,說明三位編碼員間編碼高度一致。
(四)Citespace知識圖譜分析
Citesspace是一款對相關專業領域研究文獻進行引文、關鍵詞、作者和機構之間社會網絡關系研究的開源軟件。本文輔助采用Citespace知識圖譜軟件對近十年交互研究文獻進行了關鍵詞、突現詞、作者、機構之間的關系分析,以補充和完善本文對文獻的量化研究。
三、近十年交互研究的總體發展
在我國教育技術學領域,第一篇專門討論“交互”的論文,是1999年發表在《電化教育研究》的《MPEG與現代教育技術》,MPEG是運動圖像壓縮編碼技術的國際標準,該文提到MPEG會使多媒體交互化,即當時興起的用戶可實時控制操作的交互電視[6]。第二篇為2000年發表在《電化教育研究》的《談計算機輔助教學軟件有關“交互”的幾個問題》[7],這兩篇最早的文章中的交互都指向人機交互,從控制論的輸入與輸出、控制與反饋的角度進行論述。早期的其他論文也是從此角度出發研究。隨著web2.0的發展,互聯網連接人和人的功能凸顯,社交媒介逐步普及,交互研究的視野逐步得到拓展,開始研究同伴交互、協作交互、師生交互等,交互研究成為教育技術學重要的研究領域。近十年,教育技術學領域交互研究的論文呈現平穩上升的趨勢,每年發文量均值為37.2(標準差為2.12),見圖1。

圖1 近十年交互研究發展趨勢圖
從表2可以看出,人際關系型交互、交互策略、交互影響與分析、交互過程與質量以及交互感知等五個維度的論文數,明顯高于技術中介型交互的部分。其中以人際關系型交互研究論文最多,達到78篇。

表2 近十年交互研究各主題論文數
橫向比較7種刊物的發文數,《電化教育研究》的交互類論文最多(79),接下來依次為《中國電化教育》(67)、《現代教育技術》(66)和中國遠程教育(58)。其他三類刊物發文量較少。但總體來說,對于每本期刊而言,每個季度都會刊載交互研究的最新成果(圖2)。

圖2 7 種期刊交互研究論文數比較
關于交互研究,雖然7種期刊在多數研究主題上的比例分布差別不大,但在少數研究主題上略顯差異。表3的結果表明,《電化教育研究》《遠程教育雜志》中人際關系型交互居多。《現代教育技術》和《中國電化教育》較多關注交互策略,而《中國遠程教育》和《開放教育研究》更加關注交互感知的研究。

表3 近十年7 種期刊交互研究主題分布狀況
四、近十年交互研究的主題分布
(一)人際關系型交互
人際關系型交互分為師生交互、生生交互、社區交互和群體交互四類,其中師生交互篇數最高,有26篇(33%)。在教育技術學領域,無論是在翻轉課堂、協作學習等以教師引導、學生主體的建構主義教學實踐研究中,還是在慕課、微課、在線學習、智慧課堂等依托數字技術的教育教學中,師生交互都是課堂教學的關鍵、也是影響學習效果的主要因素,因此也成為交互研究最重要的部分。
近十年我國社交媒介和移動網絡得以普及,因此網絡虛擬型學習社區交互,以及由網絡弱連接屬性驅動的群體交互,成為遠程教育、在線學習的新型交互研究領域。此類交互研究聚焦交互的關系種類、交互機制、影響因素及其對教學和學習的影響,多采用社會網絡分析、大數據挖掘等量化方法進行研究,部分研究也采用網絡民族志、話語分析等質性研究方法。生生交互是人際關系型交互中研究較少的二級維度,其中近一半篇數的文章聚焦同伴交互(8篇)(表4)。

表4 人際關系型交互研究的分布狀況
(二)技術中介型交互
本研究將外在化的機器、可視化的軟件界面和智能代理為主的人機交互,以及通過數字技術傳遞和呈現的學習資源、內容和人之間的交互都歸入技術中介型交互中。由表5可知,人與機器的交互、人與學習資源的交互是技術中介型交互中占比較多的研究。

表5 技術中介型交互研究的分布狀況
但總體來說,技術中介型交互研究占比較少。2010至2020年期間,數字技術更新迭代飛速發展,基于互聯網的教育教學興起,技術成為新型教育的基礎條件,反而降低了其可見性。研究的焦點開始向人際關系型交互,以及交互影響與分析、交互認知和交互質量轉變,因此人機交互研究較少。值得注意的是,與管理學、社會學、傳播學和計算機科學等學科當下對數據化、算法治理的研究熱度相比,在教育技術學領域以數據化和算法為基礎的人與教育智能代理交互的研究過少。智能代理(intelligent agent)是基于智能算法定期地收集學習者數據并執行服務的程序,如虛擬助手、虛擬助教、虛擬班主任等,僅有4篇論文涉及智能代理,包括從宏觀角度對智能虛擬助手的教育應用進行分析[8-9],以及對智能導學系統人機互動的跨學科文獻綜述等[10],缺乏微觀研究和應用類研究。
(三)交互影響與分析
交互影響與分析主要指專門對交互這一行為及其機制進行分析的研究,包括交互分析模式、交互分析方法、交互分析應用以及交互影響機制。其中研究最多的為交互分析應用(24篇),以交互分析具體工具的開發和應用類研究較多,如課堂互動工具[11]、互動觀察工具[12]、互動分析工具[13]、互動反饋系統工具[14]等。其次,有19篇論文研究交互影響機制,多關注交互的影響因素,如學習風格[15]、學業情緒[16]、人格特征[17]等心理影響因素,以及動畫[18]、語義圖示[19]、問題支架[20]等教學影響因素。交互分析模式共有12篇研究論文,多討論不同數字環境下交互的分析模型和機制,如互動雙編碼分析模型[21]、交互可視化分析機制[22]、交互分析模型[23-24]等。交互分析方法的研究,多以文獻分析、內容分析的方法進行對我國交互研究的總結和分類(表6)。

表6 交互影響與分析研究的分布狀況
(四)交互過程與質量
交互過程與質量分為交互質量與交互評價、交互過程監督和交互效果三個二級類目。其中交互效果研究的論文最多,共30篇,幾乎占比一半,此類研究采用實驗法、行動研究、基于設計的研究等方法,研究結果發現交互對數字化學習效果[25]、深度學習[26]、學習滿意度、學習自主性、學習效果[27]等有明顯效果。交互過程監督的論文不多,僅占2.42%,因為交互過程監督的數據采集和持續跟蹤稍有難度,另外,借助數字技術對交互過程進行可視化、數據化的技術應用目前有限,使得該領域研究成果較少(表7)。

表7 交互過程與質量研究的分布狀況
(五)交互策略
交互策略分為促進策略、干預策略和教學模式三個二級類目。其中,交互教學模式的文章數多達44篇,成為近十年研究的焦點,維度占比為65.7%,總體占比也達到11.8%。此類研究梳理和分析網絡教學交互的理論和邏輯基礎,從聯通主義、建構主義等理論出發建構教學交互理論模型[28-29]、異步交互模型[30]等,嘗試為遠程教育、在線學習的交互提供具備科學流程、策略指引和多元評價的交互模型。交互的促進和干預策略研究雖篇幅不多,但聚焦對深度交互、學生創造性協作能力方面的研究,達到一定的研究深度(表8)。

表8 交互策略研究的分布狀況
(六)交互感知
交互感知分為交互概念與交互理論、交互與認知、情感交互3個二級類目。交互概念與交互理論的研究有25篇,多是對教學交互概念辨析[2]12-16[3]36-40、有意義交互的解析[31]等交互概念的梳理和辨析,以及對社會交互理論、交互層次理論的綜述和分析[32-33]。交互與認知方面,聚焦交互與認知的相互影響,比如基于具身認知的情景交互研究、數字交互設計實現移情進而激發學習者產生元認知的研究等。情感交互雖然論文數很少(11篇),但鑒于大數據分析、社會網絡分析研究中對情感因素的重視傾向,未來研究情感交互的論文可能會增多(表9)。

表9 交互感知研究的分布狀況
五、基于Citespace的交互研究知識圖譜分析
本文將內容分析法采樣的372篇論文導入Citespace中,分析近十年交互研究論文中共現的關鍵詞、時間分布特征以及學術共同體中作者和機構的分布現狀,以補充和完善交互研究的內容分析。
(一)關鍵詞共現和聚類
Citespace對372篇論文關鍵詞頻次及中心性進行社會網絡分析后得出20個關鍵詞,如表10所示。中心性和頻次高的關鍵詞代表著一段時間內研究者共同關注的問題。

表10 高頻關鍵詞詞表
表10的關鍵詞體現了近十年交互研究的兩種取向,第一,關鍵詞共現的結果與內容分析結果一致,發現交互研究聚焦數字環境下的教學,關鍵詞依次為在線學習(35)、MOOC(13)、人機交互(9)、智慧教室(9)、遠程教育(8)、在線交互(8)、翻轉課堂(7)。第二,聚類的關鍵詞中依次出現教學交互、交互、交互性、互動,其中教學交互是頻次最高的關鍵詞,與內容分析結果一致。但同時也反映出5個關鍵詞雖涵義有交叉,但混用和交替使用的較多,需要更清晰地界定幾個概念間的本質區別和隸屬關系。
再以關鍵詞作為節點類型,以2011-2020的十年作為時間切片,對關鍵詞進行聚類分析后導出共現圖譜(圖3)。其中Q值(模塊值)為0.6775(大于0.3),S值(平均輪廓值)為0.9272(大于0.5),說明關鍵詞的節點結構比較顯著,關鍵詞聚類比較合理。

圖3 關鍵詞共現圖譜
聚類的前五個關鍵詞分別為在線學習、教學交互、交互、課堂互動和交互設計。但因為節點結構圖密度較低(0.0133),結構不嚴密,表明近十年交互研究雖然達到一定的廣度,但在具體分類和選題上的研究缺乏足夠的深度。
圖4為關鍵詞共現的時區視圖,是對關鍵詞在時間線上的特征捕捉。近十年,交互研究的選題與數字媒介技術的發展緊密相關。2012年“大數據”成為網絡關健詞,交互研究開始關注基于數據驅動的學習分析。2013年大規模在線開放課程(MOOC)快速崛起,關于MOOC的交互研究受到關注。2014年我國多省市開始進行翻轉課堂試點實踐,翻轉課堂的交互設計和應用逐漸增多。2015年虛擬現實設備得以市場普及推廣,虛擬現實創業公司爆發增長[34],虛擬現實的交互一度成為研究熱點。2017年,微信推出小程序,基于小程序的交互設計、開發和應用研究成為前沿。除上述技術發展的線索之外,從圖4可以看出,聯通主義從2014-2015年起成為交互研究的重要支撐理論。陳麗、王志軍的《聯通主義學習理論及其最新進展》被引量達375次。

圖4 關鍵詞共現時區視圖
Citespace的突現詞分析可通過短時間內關鍵詞的增強和衰弱,了解不同時期的研究前沿和趨勢。由圖5可知,2011至2020年間的交互研究共出現16個突現詞,突現值(strength)在1.2~2.9之間,凸顯差異不大。但16個突現詞在十年內的不同時期呈現出一定的錯位和時序。其中,持續時間為4年(2017-2020)的突現詞有深度學習、學習分析、微信,持續時間為3年的突現詞有遠程教育(2012-2014)、QQ群(2012-2014)、MOOC(2014-2016)、虛擬現實(2015-2017)、智慧教室(2018-2020)、混合學習(2018-2020)。16個突現詞的時間分布顯示出近十年交互研究的內容和研究對象逐漸多樣化。

圖5 2011-2020 年交互研究的16 個突現詞
(二)作者和機構共現
Citespace對作者機構的共現聚類分析,可以了解同一個研究領域中作者及其機構形成的合作團體。2011至2020年交互研究共有290個節點(作者機構),形成的合作網絡圖共包含183條邊,密度偏低(0.0044),說明機構間的聯系和合作并不緊密。
整體來說,存在較明顯的四個合作網絡,皆呈現出單一機構性。以陳麗、王志軍為主的作者多是以北京師范大學導師和學生構成的合作網絡。其他三個合作網絡中作者機構多為華中師范大學,但因為每個網絡聚焦不同的研究選題,因而形成分割的三個網絡。其中,萬力勇、趙呈領為主的合作網絡在2011、2012年發表的研究成果較多。
圖6中節點越大,作者發文數越高。陳麗2004年在《中國遠程教育》發表系列文章論述教學交互的本質、交互規律、交互質量評價等,掀起教育技術學領域交互研究的開始和發展。2011-2020年間陳麗、王志軍共同就交互理論、交互模型、國內外交互研究、交互研究方法等做了梳理和具體研究,推動了交互研究的持續發展。

圖6 2011-2020 年交互研究作者合作網絡分析
六、交互研究的展望
近十年教育技術學交互研究進入了蓬勃發展時期,從理論到交互模式、從交互策略到交互質量、從交互過程到交互感知,交互研究呈現出多元化、多視角、多層級的趨勢。研究方法也從早期的定性式經驗總結研究,發展到量化研究,以及量化質化結合的綜合方法應用上。但每一個研究范式和研究話語主導下的研究態勢,總是會在概念界定、理論來源和技術認知上具有一定的限定性。面向大數據、物聯網、元宇宙發展的未來技術社會,教育技術學需要重新審視交互的本質,拓展交互理論來源,為新的科學范式下繼續深入研究教育領域的交互提供新視角和動力。
(一)交互概念辨析
2004年陳麗的系列文章提出用“教學交互”替代“交互”,專指遠程教育中具有教育意義的交互現象,并以“遠程學習教學交互層次塔”作為理論核心,掀起教育技術學領域教學交互研究的熱朝,逐步形成了以陳麗、王志軍為主的教學交互研究的學術共同體。也逐步形成教育技術學交互研究的一種話語框架,主導了近二十年交互研究的聚焦點,但同時也限制了交互的其他維度和層級研究。
隨著移動網絡、物聯網、5G、人工智能、元宇宙等技術的發展和普及,數據化、算法化、智能化成為技術及其應用的普遍特征。在智慧教育、教育大數據、教育計算等領域,學習者、教育者、學習資源等皆被數據代理,被算法中介。人與數據、人與算法、數據與數據、數據與算法、算法與算法間的交互將會成為未來人機交互的新形式。元宇宙的興起將賽博格(cyberborg)從學術討論和社會想象推及到實際應用和實踐時,教育元宇宙帶來了新的以學生為主體的場景沉浸式學習,現實場景與虛擬場景、虛擬場景之間、過去場景和未來場景、肉身與數字身份疊加場景間的交互必定是賽博格時代交互研究的重點。因此,需要重新拓展和界定交互的概念,形成一種以“教學交互”為圓點,人際關系型交互、人機交互等不同形式交互,以及涵蓋場景交互、數據交互、算法交互等新型交互的放射性的概念群。
(二)交互理論的尋找與選擇
行為主義、認知主義、建構主義和聯通主義學習理論成為近十年交互研究的主要理論來源[35]。王志軍、陳麗也嘗試從哈貝馬斯交往行為理論論證教學交互的哲學基礎[36]。但哈貝馬斯的交往理性更多聚焦于資產階級政治公共領域,無法為教育技術學領域的交互研究提供充足的理論支撐。
21世紀是崛起的技術社會,技術正在重構和形塑著教育、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各類關系、實踐和研究。交互研究更需要以跨學科的視角豐富理論來源和理論支撐。如由法國社會學家拉圖爾構建的行動者網絡理論,在該理論中,行動者不一定是人,也可以是設備、界面、節點,甚至是理念或者現象。多元行動者將信息轉化、認識、表達、聯系,并加以傳播,形成交互,構成網絡。行動者網絡理論能夠更好地適應交互的多項化和復雜化的現象[37]。另外,回朔并審視90年代后期教育技術學領域交互研究中應用的控制論、系統論等以自動化反饋為主的交互研究,并借鑒計算機科學、哲學等領域對自動化反饋最新的研究,如“遞歸的自動化”[38]等,能為以智能算法和大數據分析為主的智能教育中的交互研究提供理論基礎。
面向迭代升級的技術社會,交互研究既要堅守近十年以教學交互為重點的研究目的,也要借鑒跨學科的視角重新研究多元變化的交互,才能更好地提升教育意義上的交互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