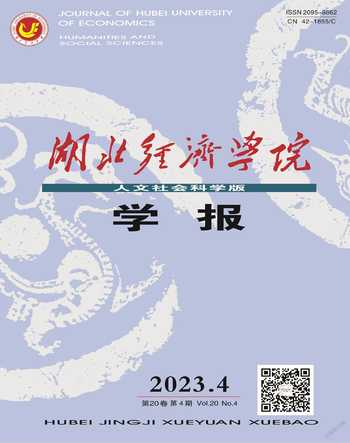鄉村振興視域下耕地流轉對甘肅河西地區農戶生計的影響研究
摘 要:耕地流轉在解決土地資源撂荒和促進農戶現代化發展的同時,對農戶生計產生了怎樣的影響是社會各界廣泛關注的問題。基于農戶調查數據,從生計策略轉型和經濟收入及其結構變化視角,就耕地流轉對耕地轉出農戶生計的影響進行了研究。結果表明:受耕地流轉影響農戶對家庭成員的具體生計活動安排做了不同程度的調整,生計多樣化指數有所降低;大部分農戶的生計策略類型發生了轉型,且呈現出向更高生計非農化類型轉型的趨勢;耕地流轉后除少部分以互換方式流轉耕地、流轉前耕地處于閑置狀態或耕地流轉后大規模搞養殖的農戶農業收入增加外,大部分農戶的農業收入減少了,而農戶家庭總收入卻普遍增加了,這主要是由非農收入的增加引起的。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改善耕地轉出農戶生計狀況的政策建議。
關鍵詞:耕地流轉;農戶生計;甘肅河西地區
一、引言
隨著我國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進城務工農民逐漸增多,耕地流轉成為了解決土地資源撂荒和促進農業現代化發展的重要舉措。農戶作為農村社會發展的主體和耕地流轉事件中的重要利益相關者。耕地流轉使農戶資源稟賦發生了較大改變,附著于耕地上的生計保障也隨之發生了變化。那么原本以耕地為生的農戶,在耕地轉出后,依賴何種方式或資源得以生存和發展呢?農戶的生計策略和收入結構發生了哪些變化?其經濟收入是增加了還是減少了呢?這些問題成為了鄉村振興視域下政界和學術界都高度關注的熱點問題。這些問題的研究對評價耕地流轉績效,提高耕地流轉農戶生計可持續性,推進全面鄉村振興等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已有學者從農戶視角對耕地流轉問題進行了研究,研究主題涉及農戶的耕地流轉意愿[1]、流轉行為模式[2]和流轉效率[3~5]等。關于耕地流轉對農戶生計影響的研究較少,已有的少量研究主要通過參與耕地流轉與未參與耕地流轉農戶生計現狀的對比,分析耕地流轉對農戶生計策略和生計可持續性或經濟收入的影響[6~7]。從農戶視角就耕地流轉對農戶生計策略和經濟收入的影響進行動態、綜合研究的文獻較為鮮見。事實上,以耕地為基本生存和發展資源的農戶,耕地流轉必然會引發其生計策略轉型,并以此為中介導致農戶的經濟收入及其結構發生變化。因此,從農戶生計策略轉型和經濟收入及其結構變化兩方面,就耕地流轉對農戶生計的影響開展研究十分可行且必要。
近年來,甘肅省把耕地流轉作為深化農村改革,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重要舉措。在這一政策的積極引導下,耕地流轉速度加快,流轉活力顯現[8]。甘肅河西地區是西北最主要的商品糧和經濟作物集中區。武威市涼州區農業資源豐富,是河西地區典型的農業大縣、強縣。本文以甘肅省武威市涼州區為例,以存在耕地轉出行為的農戶為研究對象,從生計策略和經濟收入及其結構變化兩方面就耕地流轉對農戶生計的影響進行研究,以期揭示耕地轉出對農戶生計的具體影響方式及其效應,為促進耕地流轉、推進農業現代化發展、保障糧食安全,提升耕地轉出農戶的自我發展能力和改善農戶生計狀況提供理論依據。
二、數據來源與研究方法
(一)數據來源
采用問卷調查、觀察法、小型座談會等參與式農村評估法(PRA)主要對存在耕地轉出行為的農戶開展調查,以獲取研究所需數據及信息。2020年底在甘肅省武威市涼州區西營鎮和高壩鎮進行了農戶耕地流轉情況的預調查。在預調查基礎上修改和完善調查問卷,并于2021年初采用分層隨機抽樣的方式,在涼州區范圍內選取了9個鄉鎮的27個行政村,以農戶為單位進行入戶調查。為確保調研工作的順利進行,并收集到更為準確的信息,在調查時聘請6名涼州區當地的大學生進行調查。每戶問卷調查時間約為0.5小時,共調查了152戶農戶家庭,收回有效問卷148份,問卷有效率為97.36%。
被訪問者的年齡介于18-72之間,平均年齡為55.08歲。被訪問者中男性占68.92%,女性占31.08%。被訪問農戶家庭的平均規模為4.48人/戶,人均可支配性收入為1.65萬元。63.81%的被訪者為戶主,對家庭各方面情況較為了解。將問卷的農戶統計特征與《涼州區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20)》中的統計數據對比,發現調查樣本基本反映了涼州區農戶的基本情況,具有較好的代表性和典型性。
調查內容包括:(1)農戶家庭基本情況,包括農戶家庭成員基本信息、當前農戶的生計策略和經濟收入等。(2)農地流轉影響,包括耕地流轉前農戶的生計策略,耕地流轉前后農戶農業收入、非農業收入和總收入的變化等。
(二)研究方法
1. 生計多樣化指數
生計多樣化指數指農戶家庭成員所從事的生計活動種類數,用于測量農戶生計活動的多樣化程度[9]。
2. 生計策略類型劃分
為深入分析耕地流轉前后農戶生計策略轉型情況,在借鑒已有農戶生計策略類型劃分研究成果的基礎上[10],結合涼州區農戶的生計活動特點和獲取的研究數據,根據非農收入占家庭總收入的比重結合農戶的具體生計活動方式和收入變化情況等,進行農戶生計策略類型劃分。具體劃分為:無非農收入的純農戶,非農收入占家庭總收入比例<50%的農兼戶,50%≤非農收入占家庭總收入比例<90%的兼農戶和非農收入占家庭總收入比例≥90%的非農戶四類。
三、耕地流轉對農戶生計影響的分析
(一)耕地流轉對農戶生計策略的影響
1. 耕地流轉對農戶生計活動安排的影響
耕地流轉前居于前三位的被訪農戶生計活動方式為種植、養殖和打工(表1),分別占總受訪戶的94.59%、47.30%和59.46%;從事工資性工作、經商、搞運輸和垃圾回收等活動的農戶占比相對較少,分別占總受訪戶總數的20.27%、12.16%、8.11%和1.35%。受訪戶生計多樣化指數的平均值為2.398。
耕地流轉后居于前三位的被訪農戶生計活動方式為打工、養殖和種植,分別占總受訪戶的65.57%、47.30%和35.14%;有農戶家庭成員從事工資性工作、經商、搞運輸和垃圾回收等活動,分別占總受訪戶總數25.00%、14.19%、8.11%和1.35%。受訪戶生計多樣化指數的平均值為1.986。
將耕地流轉前后農戶的具體生計活動安排對比分析,發現雖然耕地流轉前后被訪農戶均以種植、養殖和打工為主要生計活動方式,但具體占比有所變化。其中,從事種植業的農戶占比顯著下降,下降了59.45%;以務工、固定工作和經商方式謀生的農戶占比相較于耕地流轉前均有所上升,分別上升了6.11%、4.73%和2.03%;以搞運輸和其他如回收垃圾等方式謀生的農戶占比未發生變化。農戶生計多樣化指數有所降低,降低了0.412。
2. 耕地流轉對農戶生計策略轉型的影響
對受訪農戶耕地流轉前后的整體生計策略類型對比分析(表2),發現耕地流轉前屬于純農型、農兼型、兼農型和非農型生計策略類型的農戶分別占總受訪戶的22.30%、35.13%、36.49%和6.08%。耕地流轉后屬于純農型、農兼型、兼農型和非農型生計策略類型的農戶分別占總受訪戶的5.41%、24.32%、29.05%和41.22%。可見,受耕地流轉影響純農型、農兼型和兼農型生計策略類型的農戶占比均所有下降,分別下降了16.89%、10.81%、7.44%;而非農型生計策略類型農戶的占比則顯著上升,上升了35.14%。
對每戶農戶耕地流轉前后的具體生計策略類型對比分析(表3),發現共有39.86%的農戶在耕地流轉前后生計策略未發生轉型。其中,5.41%的農戶在耕地流轉前后均為純農型生計策略,17.56%的受訪戶在耕地流轉前后均為農兼型生計策略,10.81%的受訪戶在耕地流轉前后均為兼農型生計策略。但進一步分析以上農戶在耕地流轉前后的具體生計活動安排,則發現為彌補因耕地流轉造成的種植業收入減少的損失,這些農戶在耕地流轉后都不同程度地增加了養殖業或外出從事非農產業活動的時間和精力投入。這說明雖然這部分農戶的生計策略類型在耕地流轉前后未發生轉型,但農戶對家庭成員的具體種植業和養殖業活動或農業和非農生計活動安排還是做了一些調整,耕地流轉對上述農戶生計策略的影響依然存在。還有6.08%的農戶在耕地流轉前后均為非農型生計策略,這部分農戶在耕地流轉前已不主要依賴耕地生存和發展,耕地流轉對其生計策略的影響很小。
60.14%的農戶因耕地流轉生計策略發生了轉型。就具體轉型趨勢來看,6.76%的農戶生計策略由純農型向農兼型轉型;4.73%的農戶生計策略由純農型向兼農型轉型;5.41%的農戶生計策略由純農型向非農型轉型;13.51%的農戶生計策略由農兼型向兼農型轉型;4.05%的農戶由農兼型向非農型轉型;25.68%的農戶由兼農型向非農型轉型。可見,耕地流轉引發的農戶生計策略轉型較為普遍且呈現出向更高生計非農化類型轉型的趨勢。
(二)耕地流轉對農戶經濟收入的影響
當前被訪農戶的人均收入為1.65萬元,戶均收入為7.68萬元。其中,農業收入占農戶家庭總收入的30.75%,非農業收入占69.25%。耕地流轉使農戶的經濟收入及其結構發生了較大變化(表4)。
1. 耕地流轉對農戶農業收入的影響
共有19.59%的農戶認為耕地流轉后自家農業收入增加了。其中,2.03%的受訪戶認為耕地流轉后自家農業收入增加較多。進一步分析發現,這些農戶均采取了互換的方式進行了耕地流轉。究其原因,這部分農戶自有耕地數量較多,但土地細碎化程度較高,均值為16.67,這導致農戶耕作的成本較高而收益較低。通過互換方式流轉耕地使耕地能夠連片耕作,較好地滿足了規模化耕作要求,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農戶的耕作成本并提升了耕作效益。17.56%的受訪戶認為耕地流轉后自家農業收入略有增加。這部分農戶中有84.61%的受訪戶采取了出租的方式進行了耕地流轉,13.64%的農戶采取了互換的方式進行了耕地流轉,還有4.55%的受訪戶采取了入股的方式進行了耕地流轉。這些農戶的農業收入在耕地流轉后之所以略有增加,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一些農戶常年在外務工,耕地原本處于閑置狀態或免費交由自家親朋好友耕種,并無收入。現將耕地以出租或入股方式流轉后,可以得到一些流轉金或分紅,故農業收入略有增加;還有一些農戶將耕地轉出后,開始搞養殖或養殖規模較耕地流轉前有所擴大。雖然因耕地流轉這部分農戶的種植業收入降低了,但養殖業收入增加較多,使得總的農業收入沒有減少反而略有增加。
共有53.38%的農戶認為耕地流轉后自家農業收入減少了。其中,33.11%農戶認為耕地流轉后自家農業收入略有減少,20.27%的農戶認為耕地流轉后自家農業收入減少較多。分析這兩類農戶的耕地轉出率,發現耕地轉出后農業收入略有減少的農戶耕地轉出率為73.79%,接近被訪農戶耕地轉出率的平均值72.98%。而耕地轉出后農業收入減少較多的農戶耕地轉出率為91.07%,遠高于被訪農戶耕地轉出率的平均值。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耕地轉出率是影響農戶耕地轉出后農業收入變化的重要因素之一。深入訪談了解到這部分農戶農業收入減少的原因如下:有一些農戶將耕地全部轉出后,不再從事農業種植,也沒有搞養殖,自家農業收入因耕地流轉經歷了從有到無的巨大變化;有一些農戶因轉出耕地規模較大或轉出率較高,導致種植業收入減少了;還有一些農戶原本在自家耕地上種植飼草料以供養殖業發展所需,現因耕地流轉不得不購買飼草料進行養殖,導致其種植業收入沒有了,同時養殖業成本又增加了,總體的農業收入減少了。
27.03%的被訪戶認為耕地流轉后自家農業收入基本沒變。這是由于農業生產費時費力,加之購買化肥、種子和澆水等也需要一些支出,致使小規模的傳統種植在扣除了各項支出后,實際種植收入較少。現在雖然耕地流轉出去了,但原本自家耕地較少或轉出耕地較少,在耕地轉出后減少的農業種植收入與耕地流轉金大體相當。因此,在耕地轉出后這部分農戶的農業收入基本沒變。
2. 耕地流轉對農戶非農收入的影響
共有60.81%的受訪戶認為耕地流轉后自家非農收入增加了。其中,7.43%的受訪戶認為自家非農收入增加較多,53.38%的受訪戶認為略有增加。進一步分析發現,這兩部分農戶的耕地轉出率都較高,分別為89.45%和85.07%;當前的非農收入占比也比較高,分別為89.77%和82.23%。耕地轉出后,這些農戶將更多的時間和精力投入非農產業,甚至有的農戶常年在外從事非農生計活動,不用在農忙季節返鄉種地,相應的非農收入也隨之增加了。其中,非農收入增加幅度較大的這部分農戶中,有36.36%的農戶將耕地轉出后,開始經商,因此其非農收入增長幅度較大;剩余的63.64%的農戶家庭勞動力資源較為充足,將耕地轉出后,青壯年勞動力常年在外務工,因此其非農收入也增長較快。
39.19%的受訪戶認為耕地流轉后自家非農收入基本沒變。對比分析,發現這部分農戶的耕地流轉率相對較低,為53.88%;非農收入占比也相對較低,為47.69%。這部分農戶在耕地流轉后,仍有家庭成員從事種植業或養殖業等農業生產活動,處于農業和非農產業相兼的狀態,投入到非農產業的勞動力數量、時間和精力等未發生大的變化,故非農收入基本沒變。
沒有農戶認為耕地流轉后自家非農收入減少了。究其原因,耕地被全部或部分轉出后,迫于生計壓力,農戶不得不探尋新的生計策略或專職從事原有的非農生計活動以替代或補足因耕地流轉而減少的收入,并爭取更高的收入,以滿足家庭成員的各種開銷、維持原有的生活質量或不斷提高其生活質量。
3. 耕地流轉對農戶總收入的影響
共有61.49%的受訪戶認為耕地流轉后家庭總收入增加了。其中,6.08%的受訪戶認為自家總收入增加較多,55.41%的受訪戶認為自家總收入略有增加。對認為家庭總收入增加較多的農戶收入結構分析發現,33.33%的農戶認為自家農業收入增加較多,22.22%的農戶認為自家農業收入未發生變化,還有44.44%的農戶認為自家農業收入減少了;66.67%的農戶認為自家非農收入增加較多,33.33%的農戶認為自家非農收入未發生變化。對認為自家總收入略有增加的農戶收入結構分析發現,31.71%的農戶認為自家農業收入略有增加,34.17%的農戶認為自家農業收入基本沒變,28.05%的農戶認為自家農業收入略有減少,6.10%的農戶認為自家農業收入減少較多;4.83%的農戶認為自家非農收入增加較多,78.05%的農戶認為自家非農收入略有增加,17.07%的農戶認為自家非農收入基本沒變。可見,農戶家庭總收入的增加主要是由非農收入增加引起的。
共有24.33%的受訪戶認為耕地流轉后自家總收入減少了。其中,11.49%的受訪戶認為耕地流轉后自家總收入略有減少,12.84%的受訪戶認為耕地流轉后自家總收入減少較多。具體分析發現,認為耕地流轉后自家總收入略有減少的農戶中有94.12%的農戶認為自己農業收入略有減少,5.88%的農戶認為自己農業收入減少較多;88.24%的農戶認為自家非農收入基本沒變,11.76%的農戶認為自己非農收入略有增加。認為耕地流轉后自家總收入減少較多的所有農戶均認為自家農業收入出現了大幅下降;94.74%的農戶認為自家非農收入沒有發生變化,5.26%的農戶認為自家非農收入略有增加。可見,農戶家庭總收入的減少主要是由農業收入減少引起的。當非農收入沒變或略有增加不足以彌補因耕地流轉較少的農業收入減少時,會引起農戶總收入大幅減少。
14.19%的農戶認為耕地轉出后自家總收入基本沒變。這部分受訪戶中有47.62%的農戶認為自家農業收入在耕地流轉后保持基本不變,38.10%的農戶認為自家農業收入略有減少,14.28%的農戶認為自家農業收入減少較多;38.10%的農戶認為自家非農收入在耕地流轉后保持基本不變,57.14%的農戶認為耕地流轉后自家的非農收入略有增加,4.76%的農戶認為自家非農收入增加較多。
四、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促進農業現代化發展和改善農戶生計狀況是耕地流轉政策的初衷,兩者缺一不可。通過分析耕地流轉對河西地區農戶生計的影響,得出的主要結論如下。
1. 就耕地流轉對農戶生計策略的影響而言,受耕地流轉影響農戶對家庭成員的具體生計活動安排做了不同程度的調整,生計多樣化指數有所降低。大部分農戶的生計策略發生了轉型,且呈現出向更高生計非農化類型轉型的趨勢。
2. 就耕地流轉對農戶經濟收入及其結構的影響而言,耕地流轉后除少部分以互換方式流轉耕地、流轉前耕地處于閑置狀態或耕地流轉后大規模搞養殖的受訪戶農業收入增加外,大部分受訪戶農業收入減少了;而受訪戶的家庭總收入卻普遍增加了,這主要是由非農收入的增加引起的。
(二)建議
基于上述研究結論,建議從以下幾方面著手,以改善耕地轉出農戶的生計狀況,助力全面推進鄉村振興。
1. 加強教育和非農就業技能培訓,提升農戶的非農就業能力。河西地區的農戶轉出耕地后農戶主要以非農產業為生,只有提升農戶的非農就業能力,才能增強耕地轉出農戶生計的可持續性。首先,要通過短期的職業技能培訓,提升農戶自身的非農就業技能。其次,要通過加強對外交流,積極幫助農戶拓展非農就業渠道。最后,要通過提升義務教育的普及程度和延長義務教育年限,提高農戶子女的受教育水平,才能長遠而持久地提升農戶的非農就業能力,并為農業農村發展培養更多優秀人才。
2. 大力發展農村新產業和新業態,讓農戶在家門口富起來。在調查中了解到,一些農戶因需要在家照顧孩子和老人或自身年齡較大等不宜進城務工,耕地流轉前在家種地。現在耕地流轉出去了,實際處于無業、無收入的狀態,生活非常困頓無聊。當前急需充分利用和挖掘當地的土地、生態和文化等資源,推進農業與旅游、教育、文化和康養等產業深度融合,推動當地形成一批能夠彰顯地域特色、感受自然氣息的以“賣風景”“賣文化”“賣服務”和“賣體驗”為特點的新產業和新業態。這些新產業和新業態的形成既有利于盤活當地沉睡的資源,帶動耕地轉出農戶順利創業就業、增加農戶的經濟收入,又有利于挖掘鄉村價值、豐富城鄉居民生活,還有利于吸引更多的人留在農村、走進農村、了解農村、投身或投資農村發展,更好地推動美麗宜居鄉村建設,促進鄉村振興和城鄉融合發展。此外,新產業、新業態的發展也有利于老年人發揮余熱、充實生活,增強老年人的獲得感和幸福感。
3. 建立健全農村社會保障和養老服務體系,解決農戶的后顧之憂。從農戶生計策略轉型趨勢和收入變化來看,耕地流轉后耕地對農戶的就業和生存保障功能正在進一步減弱。此外,過去農村老年人一輩子生生不息地在田間勞作。耕地流轉后,農村老年人沒地可種了,也沒事可干了。如何充實又安心地度過晚年生活是很多農村家庭在耕地流轉后擔心的問題之一。因此,急需進一步建立健全農村社會保障和養老服務體系,以解決農戶的后顧之憂。首先,要在新型農村醫療與養老和最低生活保障等社會保障制度基礎上,推進城鄉社會保障制度并軌,使外出務工的農戶更好地融入其工作所在城市,使其在流得出的基礎上能夠留得住,讓城鄉居民共享經濟社會發展成果。其次,應統籌各種資源推進農村養老制度改革,在農村地區構建居家養老、社區養老、機構養老協同補充的多層級養老服務體系,針對不同的養老需求提供切實可行的養老服務,解決農村地區養老難的問題。讓耕地轉出家庭的老年人能夠安度晚年,讓中青年農戶能夠放心地外出從事非農產業或留鄉、返鄉創新創業。
參考文獻:
[1] 張忠明,錢文榮.不同兼業程度下的農戶土地流轉意愿研究——基于浙江的調查與實證[J].農業經濟問題,2014,35(3):19-24+110.
[2] 何欣,蔣濤,郭良燕,甘犁.中國農地流轉市場的發展與農戶流轉農地行為研究——基于2013-2015年29省的農戶調查數據[J].管理世界,2016(6):79-89.
[3] 陳海磊,史清華,顧海英.農戶土地流轉是有效率的嗎?——以山西為例[J].中國農村經濟,2014(7):61-71+96.
[4] 蓋慶恩,程名望,朱喜,史清華.土地流轉能夠影響農地資源配置效率嗎?——來自農村固定觀察點的證據[J]. 經濟學(季刊),2020,20(5):321-340.
[5] 曲朦,趙凱,周升強.耕地流轉對小麥生產效率的影響——基于農戶生計分化的調節效應分析[J].資源科學,2019,41(10):1911-1922.
[6] 蔣佳佳,張仕超,邵景安,王金亮.耕地流轉脅迫下農戶生計多元化選擇與可持續性水平——基于重慶市合川區188戶的調查數據[J]. 中國生態農業學報,2019,27(2):314-326.
[7] 柯煉,汪小勤,陳地強.土地流轉與農戶收入增長——基于收入結構的視角[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22,32(1):127-137.
[8] 史亞瓊.甘肅省農村土地流轉的特點及態勢[J]. 社科縱橫,2018,33(12):44-46.
[9] 閻建忠,吳瑩瑩,張鐿鋰,等.青藏高原東部樣帶農牧民生計的多樣化[J]. 地理學報,2009,64(2):221-233.
[10] 郭秀麗,周立華,陳勇,楊國靖,趙敏敏,王睿.典型沙漠化地區農戶生計資本對生計策略的影響——以內蒙古自治區杭錦旗為例[J].生態學報,2017,37(20):6963-6972.
基金項目:甘肅省高等學校創新能力提升項目“鄉村振興視域下河西地區農地流轉對農戶生計的影響研究”(2019A-087);甘肅省教育廳創新基金項目“甘肅農村養老與鄉村振興戰略:現實邏輯、耦合機制與發展路徑研究”(2021A-100)
作者簡介:郭秀麗(1982- ),女,甘肅涇川人,甘肅政法大學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為區域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