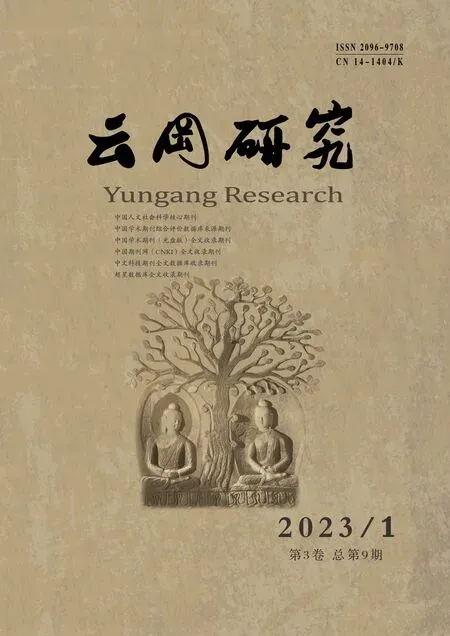《重修云岡石佛寺碑記》作者考證
——兼論順治元年修繕活動
李海林
(山西大同大學云岡學學院,大同 037009)
《重修云岡石佛寺碑記》記載的是順治元年(1644年)六月至順治三年(1646年)五月間對云岡石窟的修繕活動。碑文共485 字,內容分為三個部分,首先介紹了云岡石窟的概況,然后點明此次重修原因及時間,最后以偈詩來表達作者對佛法的感激。碑文如下:
云川東距九十里,為云岡之陽,有古剎焉。其奉佛,皆就岡石而莊嚴之。或偏袒而立,或跏趺而坐;或奇或偶,或大或小,居然祗樹園說法地也。是以種種菩提心,具此種種微妙相。猗歟,休哉!洵云川一靈巖也。爰考《云志》,建自后魏拓跋氏,垂今千百余年。彼以霸業之余運,神斤鬼斧,固不難使頑石成佛。惟是,自古山川因人而名,不為修葺,幾何不為鳩巢鼠穴耶?云岡以甲申三月,為闖寇過天星盤踞,屠人之肉,覆人之居,天日為晦,又何有于剎耶?余不揣螳螂,馳軍士千人,于五月朔十日,一舉而克復之。生縛過天星,寸磔以快云憤。使非慈云慧月之照,何以有此?因感佛土當凈之義,于是鳩工庀材重修,以董厥事。夫佛實無土,何以凈為?然有形累,正未免托土以居,石佛之謂也。此余所以恭承按都暨諸士大夫鼎新意也。況今上以神圣開天,崇儒重釋,度越往古;行舉天下,皆為清凈土、極樂國,豈僅區區三云哉?是役,始于甲申六月,迄于丙戌五月,凡兩年而役竣。其捐助姓氏,載之別勒。余謹齋沐作記,而復為之偈。偈曰:云西有石白磷磷,靈根盡化如來身;不垢不壞幾千春,念彼慧力生云人;刃不傷兮火不焚,何以報之剎維新;輝煌金碧自嶙峋,樂國永永無氛塵。[1](P54-55)
一、《重修云岡石佛寺碑記》作者
關于《重修云岡石佛寺碑記》作者,目前有以下兩種說法:《云岡石窟編年史》一書提到:“作者,《縣志》未載,事必有因。我疑其為姜瓖黨羽,可能是駐守左衛城的大同協鎮副將林世昌。”[2](P334)員小中先生在《云岡石窟銘文楹聯》一書中,因襲《云岡石窟編年史》觀點。[3](P111)大同地方史志學者姚斌先生認為該文作者“很可能是大同總兵姜瓖,或余黨所為”。[4](P139-146)由于研究側重點不同,以上結論均沒有深入分析碑文作者。筆者通過分析碑文,結合其它古籍史料記載,認為《重修云岡石佛寺碑記》的作者是姜瓖。姜瓖“陜西榆林人,世為明將。崇禎間,掛鎮朔將軍印,鎮守大同”。[5](P616)
(一)姜瓖投誠大順軍
碑文所載“云岡以甲申三月,為闖寇過天星盤踞”。“過天星”是明末農民起義中一些起義領袖經常會使用的諢號。《云中郡志》明確記載“崇禎十七年甲申春,闖難陡發,偽兵西來。三月初六日,兵過陽和,留住一宿。東行,鎮城所留偽總兵張天琳號過天星者,殺戮兇暴,居民重足兩閱月”。[6](P486-487)因此,碑文中的“過天星”就是明末農民起義將領張天琳。
順治元年(1644 年),李自成東進北京途中,不斷攻城掠池,三月進入大同。此時“兵民皆欲降,命城守不應。總兵朱三樂自刎,巡撫衛景瑗、督理糧儲戶部郎中徐有聲、朱家仕俱死之。文學李若葵闔家九人自縊。先題曰‘一門完節’。李自成入大同六日,殺代府宗室殆盡,留偽將張天琳守之。”[7](P1374)大同城被大順軍順利占領,并且由起義軍將領張天琳鎮守。而李自成入占大同,起關鍵作用的是大同總兵姜瓖。
針對農民起義軍不斷奪取政權一事,有寧愿誓死保存名節者,也有投機取巧看明朝大勢已去斷然投降者。大明王朝窮途末路江河日下,李自成大順政權如日東升,因此,鎮守大同總兵姜瓖認為農民軍拿下山西只是時間問題。大順政權雖然深受兵民歡迎,但李自成能夠順利奪取大同城,姜瓖功不可沒。李自成自順治元年(1644 年)初破太原,便攻寧武。當時,守關鎮臣周遇吉誓死抵抗,城破被殺。寧武一役,農民軍受創亦深。李自成認為“自此達燕京,尚有大同、宣府、居庸、陽和等鎮皆宿重兵,使盡如寧武連袂受戮矣,不若姑回陜休息,相機載舉。”[8](P738)寧武總兵周遇吉頑強抵抗,使李自成東進之路受到極大阻礙,心生怯意,因此,決定暫停東進。此時,“忽收得大同總兵姜瓖降表,自成喜甚。”[8](P738)屯有重兵的大同鎮不戰而降,宣府亦投降。因此,李自成一路向西,攻入北京。《甲申傳信錄》亦有詳細記載:
闖入西安,榆林總兵姜讓先趨降闖。而大同總兵姜瓖、陽和副總兵姜瑄皆讓弟也。闖將攻大同,讓先騎至城下,約瓖偽以觀兵設仗,出城迎闖,降之。瓖復入城,開門延賊,闖入即縛瓖,命斬之。而數其罪曰:“朝廷以要害重鎮寄若,若何首降?”瓖無辭。而闖將張天林曰:“將欲定京師,而殺首降非所以勸歸順也,不如釋之,以招將來之士。”自成從之。遂釋瓖,而使天林鎮大同,守之。瓖叩謝張。張曰:“國家創大業,招徠服遠之始,固應如是,何敢當謝。”[9](P493-494)
李闖王農民軍攻打大同時,大同鎮總兵姜瓖在其兄姜讓的授議下,以隆重的禮節出大同城投降李闖王。姜瓖本以為自己獻城能夠得到李自成的認可,但結果卻與愿違。李自成反而因為姜瓖叛明,想要殺掉他。后來因為有張天琳的勸說,姜瓖才得以幸免。隨后,李自成繼續北上,留下張天琳鎮守大同。
(二)姜瓖斬殺張天琳
隨著大順軍山海關戰役的失敗,姜瓖又叛變大順軍,刺殺張天琳,瓦解了農民軍駐防大同軍隊,“使李自成放棄北京后,固守山西的計劃轉眼就落了空”。[10](P268)據載:
及闖東出,敗于關門,西遁。清兵且入。瓖即單騎走陽和,假其弟瑄部兵數百,疾趨大同,欲入大同。聞吳兵將來,城守不欲啟,天林曰:“此獨瓖至,必酬向者勸王不殺德也。”命啟門內,瓖等部卒盡入,瓖入即縛天林,斬之。而守城以待清兵入,即以殺天林賜功鎮。[9](P494)
漢族地主中的許多人,大約從崇禎十六年(1643年)冬開始,已經看出明王朝氣數將盡。他們在這場社會大動蕩中倉皇四顧,尋求新的保護者,見李自成的大順軍如日東升,很自然地把保護自身利益的希望寄托于大順政權。然而,漢族地主們很快失望了。基本政策方面,李自成等大順政權的領導人仍然堅持維護農民階級的利益,對官紳實行追臟助餉,大大損害了這些人的利益。
1644 年,李自成大順軍在山海關戰役中的失敗和被迫放棄北京,在全國產生了巨大的反響。農民軍自從崇禎十四年(1641 年)以來幾乎是戰無不利,攻無不克,卻在一次關鍵性的戰役中遭到重大挫折,士氣大受影響。清軍旗開得勝,一舉拿下北京,邁出了多年夢寐以求的進取中原的第一步,自然興高采烈,信心大增。當山海關戰役大順軍失敗、北京陷落之際,各地官紳地主認為時機已到,紛紛叛變大順軍。
大同總兵姜瓖,自然打起了歸清的旗號。當過天星張天琳誓與清朝抵抗到底之時,姜瓖“即單騎走陽和,假其弟瑄部兵數百,疾趨大同”。張天琳沒有識破姜瓖的陰謀詭計,誤以為他會報答其救命之恩,在沒有任何防備打開城門之際,即被姜瓖生縛并斬殺,籍此向清廷邀功。
(三)碑文與史書記載的一致性
《重修云岡石佛寺碑記》作者以第一人稱寫到“余不揣螳螂,馳軍士千人,于五月朔十日,一舉而克復之。生縛過天星,寸磔以快云憤怒。使非慈云慧月之照,何以有此?”此正是清軍入犯之際,姜瓖叛變大順軍,從陽和借軍,趁張天琳不備而襲殺其之時。姜瓖逆殺張天琳時間,碑文中載為“五月朔十日”。雖然《甲申傳信錄》沒有明確時間記載,《云中郡志》卻載:“鎮城所留偽總兵張天琳號過天星者,殺戮兇暴,居民重足兩閱月,而國威東震。陽和軍民約與鎮城軍民內應,于是殺天琳及偽中軍張黑臉,恢復大同,時五月初十日也”。[6](P486-487)
碑文所記斬殺過天星一事與《續表忠記》《甲申傳信錄》《云中郡志》等史料所載內容及時間相一致。尤其碑文通過第一人稱“余”展開陳述,確定碑文作者系姜瓖無疑。事實上大順軍在大同留了上萬重兵,之所以姜瓖能夠叛變得逞,著名明史專家顧誠先生曾在《明末農民戰爭史》一書中提到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沒有解除明朝投降總兵姜瓖等人的兵權,二是防范不嚴。”[10](P277)
(四)《左云縣志》不載其名之原因
姜瓖叛變大順政權后,清廷命其佩征西前將軍印鎮守大同。雖然姜瓖是一鎮之首,但由于多爾袞不信任姜瓖,派和碩英親王阿濟格鎮守大同,顯然,架空了總兵姜瓖的權利。順治五年(1649 年)十二月初三日,大同總督、司道、餉司、知府各官,出城驗草,“大同總兵官姜瓖,閉門叛。”[11](卷41,戊戌條)姜瓖打起“反清復明”的旗號,與清軍對峙,很快在大同及山西其它地區掀起了反清之風。清廷命令英王率領諸多王公將士前往大同征討姜瓖,多爾袞也兩次親臨大同指揮打仗,雙方僵持了9 個月,最后,城中糧草將盡,兵民疾苦,姜瓖麾下總兵楊振威等人密謀造反,斬姜瓖首級并將其交付給清軍,打開城門迎降。
清軍進入大同城之后,多爾袞諭和碩英親王:“斬獻姜瓖之楊振威等二十三員及家屬并所屬兵六百名,俱著留養,仍帶來京。其余從逆之官吏兵民,盡行誅之。將大同城垣自垛徹去五尺。其城樓房舍、不得焚毀。”[11](卷46,戊午條)此番“姜逆”導致大同府生靈涂炭,遭受前所未有的破壞,不得不于順治六年(1649 年)東遷移至陽和衛(今陽高縣),改名為陽和府,大同縣遷至西安堡(今懷仁縣西安堡)。
姜瓖身為明朝將領,投降大順政權;張天琳對其有救命之恩,不思回報,反而將張天琳斬殺,投降清朝;多爾袞封其為大同鎮總兵,卻不被信任,權利被削弱,又反清復明。姜瓖背主忘恩,首鼠兩端,丟掉了家國大義,實在令人不齒。這也是《左云縣志》收錄碑文,不載其名的原因。
二、順治元年至三年云岡石窟修繕活動
對于云岡石窟的修繕活動,自北魏以來,歷經北齊、隋、唐,至遼大規模重修,可惜被金付之一炬,金在遼基礎上繼續修繕。及至明朝,大同成為明蒙交戰的前沿地帶,明廷特別注重軍事防御設施的修建,在大同地區修建了大量的防御工程,而云岡堡的修建在一定程度上更是造成對石窟的破壞。明末農民起義軍盤踞云岡,對云岡石窟更是造成了極大破壞。
(一)明代云岡石窟概況
明代對云岡石窟的文獻記載主要是云岡十寺,其它記載相對較少。云岡十寺修建于北魏時期,遼代在北魏基礎上在云岡石窟窟前修建了巨大的木構建筑,可惜于遼末遭到破壞。金太宗完顏晟執政后,又開始修復云岡十寺,推動了云岡石窟寺廟文化的進一步發展。據成化《山西通志》記載“石窟十寺,在大同府城西三十五里,后魏時建,始于神瑞,終于正光,凡七帝,歷百十有一年。其寺,一同升,二靈光,三鎮國,四護國,五崇福,六童子,七能仁,八華嚴,九天宮,十兜率。寺內有元載(魏)所修石佛二十龕。”[12](P77)由此可知,成化年間,云岡十寺存在。正德《大同府志》亦有相似記載。雖然正德《大同府志》有部分內容抄襲成化《山西通志》,但是,云岡石窟作為當時的名勝古跡,撰修者對其現狀應該有所了解,因此,至遲在正德年間,云岡十寺還在。
宿白先生在《〈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的發現與研究》一文中認為云岡十寺有可能毀于明中葉“‘卒無寧歲’的韃靼之役過程中。”[13](P103)云岡十寺具體毀于什么時候,沒有明確記載。但根據繪制于明萬歷三十一年(1603 年)的《宣大山西三鎮圖說》(圖1)中云岡堡圖說內容可知,此時云岡石窟窟前樓閣依然存在。不知是后期重修,還是一直存在。該書作者楊時寧(1537-1609 年),萬歷二十九年(1601 年)擔任宣大山西總督。在其擔任總督期間,修撰了該書。由于該書是進奉給皇帝看的,宣、大、山西地區各官吏俱認真審核。尤其是卷2的《大同鎮總圖》,楊時寧與大同巡撫張悌同纂,且成書后由分守冀北道兵備僉事李芳、分巡冀北兵備僉事陳所學、陽和兵備副使劉汝康共同校正,準確性更高,相較于其它涉及大同鎮的邊地圖書記述更為準確、詳細,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同時,吳伯與①伯與,字福生,宣城人。萬歷癸丑進士,除戶部主事,歷郎中、出為浙江布政司參議,遷廣東按察副使。的《游石佛寺》碑文中也有這樣的記載:“奇樹映樓閣以蔥蘢,丹膏并異卉而冥密。”[14](P106)《游石佛寺記》是吳伯與在萬歷四十七年(1619 年)與友人徐檀燕、王振宇同游云岡石佛寺所寫,刻于萬歷四十八年(1620 年)。據此可知,在萬歷四十八年,云岡石窟亦是奇樹映樓閣以蔥蘢。

圖1 《宣大山西三鎮圖說》(萬歷秘閣本)
明末農民戰爭,“云岡以甲申三月,為闖寇過天星盤踞,屠人之肉,覆人之居,天日為晦,又何有于剎耶?”云岡十寺被過天星所毀。宿白先生也曾提到崇禎十七年(1644年)明末恢復的云岡寺院又毀于闖將過天星之手。[13](P77)大同地方史志學者姚斌先生亦認為張天琳燒毀了重修于遼金時期的云岡十寺窟檐木構建筑。[4](P139-146)
(二)姜瓖修繕具體內容
姜瓖叛大順軍成功,繼續鎮守大同。其把斬殺過天星的功勞歸結為“使非慈云慧月之照,何以有此?”同時,經過明末農民戰爭的洗禮,云岡石窟籠罩在烏煙瘴氣之下,姜瓖“因感佛土當凈之義,于是鳩工庀材重修,以董厥事。”大力召集工人購買材料,重新修葺云岡石窟,試圖洗去大同佛門凈地的戾氣。當然,姜瓖修繕云岡石窟還有一個更深層次原因,即響應清廷的宗教政策,維護清廷的統治,向清廷表忠。滿清入關后,為鞏固政權,順治時期就制定了“黜邪崇正”的宗教政策。打壓旁門左道宗教信仰,對于中原流傳已久的佛、道二教,既肯定其為善去惡的積極作用,又強調其必須在官方力量的統管之下。正如碑文所言“況今上以神圣開天,崇儒重釋,度越往古;行舉天下,皆為清凈土、極樂國,豈僅區區三云哉?”
該次修繕活動從順治元年六月至順治三年五月,用時兩年。具體修繕內容,《重修云岡石佛寺碑記》中沒有詳細記載,只是末尾有姜瓖所做偈一首,偈云:“云西有石白磷磷,靈根盡化如來身;不垢不壞幾千春,念彼慧力生云人;刃不傷兮火不焚,何以報之剎維新;輝煌金碧自嶙峋,樂國永永無氛塵。”這首偈語不僅體現了姜瓖對石窟的一個認識,同時,也提到了唯有“輝煌金碧自嶙峋”,才能達到“何以報之剎維新”的目的。據此可推測,姜瓖的具體修繕活動應該包括能使石窟金碧輝煌、燦然一新的項目,諸如彩塑、金裝、補修等修繕內容。
此外,順治元年至順治三年,云岡石窟修繕活動還重修了第7、第8 窟窟前木構建筑。對于第7、8 窟窟前木構建筑,絕大多數研究者認為是順治八年佟養量所修。②參見姚斌:《明清時期對云岡石窟的保護與破壞》,《云岡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保護卷》,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139-146頁;云岡石窟文物研究所:《云岡保護五十年》,文物出版社,2005年;王恒:《云岡石窟詞典》,江蘇美術出版社,2012年。據《云岡日錄》載:“第三窟(第七窟)雖然壞了,但仍有一座樓閣立在那里。樓閣屋檐上方,懸掛著一塊匾額,上面書有‘西來第一山’五個大字,右側雕刻著‘順治四年歲次丁亥菊月之吉’一行字,左側雕刻著‘兵部尚書兼都御史馬國柱立’這一署名。”[15](P103)馬國柱“遼陽人,魁偉有大略,順治三年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在任二年,多善政,調江南總督。”[16](P360)其在山西任職總督時間是順治三年、四年。順治四年(1647年)秋七月,清廷“升宣大總督兵部右侍郎馬國柱,為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江南、江西、河南等處。”[11](卷33,戊午條)這塊匾額是總督馬國柱于順治四年九月離任之前為云岡石窟所立,并懸掛于第7窟樓閣屋檐上。
云岡石窟清代匾額目前已知的共有24塊,除了掛在山門院天王殿及山門兩側的5塊匾額,還有掛在第8 窟的“佛籟洞”及第7 窟的“西來第一山”木質匾額2塊,其余17 塊均掛在第5、6 窟。據此可知,無論是康熙御書的“莊嚴法相”還是總督兵馬侍郎佟養量的“大佛閣”抑或是“神靈默佑”“佛光普照”等眾多木質匾額,都是盡可能掛在第5、6窟。因此,如果云岡石窟第5、6、7、8窟窟前木構建筑都是總督佟養量于順治八年(1651年)所修,那么總督馬國柱所書匾額一定是掛在規模更大的第5、6窟,而不是規模狹小簡陋的第7窟。“西來第一山”匾額緣何掛在第7窟呢,原因只能是順治四年只有第7、8窟有窟前木構建筑,第5、6窟沒有。據此認為,順治元年至順治三年姜瓖修繕云岡石窟的活動還包括修繕第7、8窟窟前木構建筑。
云岡石窟第7、8 兩窟系雙窟,建筑形制相似,宿白先生曾推斷這兩窟是云岡十寺之一“護國寺”。第8 窟窟前木構建筑早在20 世紀初對云岡調查時,已經不復存在,只剩下第7 窟。《云岡石窟的考古學研究》載:“第8 窟的樓閣在東方文化研究所調查時,業已坍塌毀壞。”[17](P115)《云岡石窟詞典》也寫道:“第7、8 窟窟檐規模較小,且較為簡陋已經散架,其中第8 窟的窟檐多年不存。”[18](P170)《云岡保護五十年》亦載:“第8 窟原來應與第7 窟一樣,建有木結構的窟檐。”[19](P26)
結語
綜上所述,《重修云岡石佛寺碑記》作者為投降李自成農民軍、斬殺過天星張天琳、投降清朝及最后又舉起反清復明大旗的大同總兵姜瓖。姜瓖首鼠兩端,見風使舵,拋卻了國家大義,因此,光緒版《左云縣志》搜錄碑文,不載其名。這次修繕活動也為佟養量順治八年(1651年)的對云岡石窟的修繕奠定了扎實基礎,正是有了前期兩年的修繕,才使的佟養量于順治八年的修繕工程,縮短了維修時間。《重修云岡石佛寺碑記》所記是入清的第一次修繕活動,修繕時間兩年,修繕內容一是彩塑、金裝、補修石窟佛像,二是修建第7、8窟窟前木構建筑。考證《重修云岡石佛寺碑記》作者,探討其修繕內容,對于梳理云岡石窟保護史、發展史是不可或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