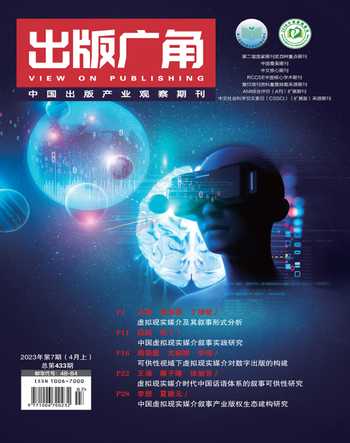可供性視域下虛擬現實媒介對數字出版的構建
周榮庭?尤麗娜?李珮
【摘要】研究基于可供性理論,檢視VRM與數字出版生態之間互動關系的認識論潛能,進一步探索數字出版生態中“生產—社交—移動”分析路徑,提出未來數字出版的發展應在生產可供性上積極擴展和繁榮內容生態,在社交可供性上形成社交化內容生態,在移動可供性上通過優化終端體驗構建虛擬現實媒介內容生成的場景生態,以推動數字出版產品和服務創新及產業可持續發展。
【關? 鍵? 詞】虛擬現實媒介;生產可供性;社交可供性;移動可供性;數字出版
【作者單位】周榮庭,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科學教育與傳播省級哲學社會科學重點實驗室;尤麗娜,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科技傳播系;李珮,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科技傳播系,沉浸式媒體技術文化和旅游部重點實驗室。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虛擬現實媒介敘事研究”(21&ZD326)階段性成果。
【中圖分類號】G237. 5【文獻標識碼】A【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23.07.003
在萬物皆媒的時代,虛擬現實媒介(virtual reality media,VRM)作為一種傳播媒介,拓展了人類的視覺、聽覺和觸覺,其“復現真實、臨場體感”[1]的特性為文化產業提供了描摹和體驗世界的強力工具。VRM技術歷經“跳躍式”發展和“降檻式”演進,已從尖端科學領域的應用拓展到人類的日常體驗[2]。在出版領域,VRM為數字出版提供了多元化、開放性的協作過程,不僅可以借助虛擬現實(virtualreality,VR)技術和工具創建三維模型、虛擬場景和交互式應用,而且在5G、區塊鏈與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等技術的加持下加速了智能化的融合進程[3]。
本文基于可供性視角探究VRM生成內容對數字出版的構建,系統研究其背后的“生產—社交—移動”關鍵理論問題,以優化內容生產關系,構建新的內容生產格局。
一、可供性與虛擬現實媒介
1.媒介環境下的可供性研究
可供性指在環境中可獲得的行動可能性,在重新界定環境與主體、技術與人關系的同時,也解釋了主體與環境的對應關系[4]。其中,媒介可供性就是傳播技術提供給人們用于開展行動的可能性,強調一種理解人與媒介、技術之間交互關系的視角[5]。
可供性理論研究分為媒介文化研究和結構功能研究兩種范式[6]。媒介文化范式可采取本體論、認識論兩條進路對可供性的定義、概念、屬性和演變歷程進行辨析[7-8]。從結構功能范式出發,可供性的框架圍繞技術、媒介在數字時代特定領域的功能、影響和價值展開探究,集中在話語重構、情感分析、媒介賦權、產業轉型和生態發展等多重視角。基于技術可供性的數字出版可嘗試構建用于體驗的VR文化空間、閱讀空間和娛樂空間,并向基于AI技術的VR出版形態發展[9]。從可供性視角出發,數字出版的建構可以依賴“生產—社交—移動”分析路徑,為VRM下的內容生產拓展資源空間和實現技術賦能。
2.虛擬現實媒介與可供性的耦合
VR最早由美國計算機科學家杰倫·拉尼爾(Jaron Lanier)于1984年正式提出,是一項運用計算機圖形技術、計算機仿真技術、AI技術、顯示技術、傳感技術及各種控制和接口設備等的集成技術。VR的媒介建構及對肉體的“自我超越”是人類媒介史中一以貫之的邏輯線索[10]。VR作為媒介的發展階段,依據其技術特性可分為VR1.0階段和VR2.0階段。
在VR1.0階段,虛擬現實具有模擬性、交互作用、人工現實、沉浸性、遙在、全身沉浸和網絡通信[11]7個特性,后來歸并為3I特性,即交互性(interactivity)、沉浸性(immersiveness)和構想性(imagination)[12]。其中,沉浸性指通過計算機構造的圖像讓人置身于一種虛擬環境中,帶給用戶身臨其境的感覺;構想性指虛擬環境可使用戶沉浸其中并獲取新的知識,提高對事物的理性認知和感性認識,從而使用戶深化概念或產生新的聯想;交互性指在計算機生成的虛擬環境中,人們可以利用一些傳感設備進行交互,仿佛置身于真實的世界中。
當前,VR已經邁入智能化的VR2.0階段。人工智能技術的滲透使得 VRM 具備“PIE”特征,即參與性(participation)、互通性(interconnection)和演變性(evolutionary)。參與性指通過多種方式促進用戶的積極參與,包括思考、互動、貢獻、反饋等,是一種兼有主動和被動參與的形式;互通性指兩個或多個系統或物品之間能夠相互傳遞信息或進行交流的能力,虛擬對象或環境與對應的真實對象或環境之間存在多模態數據互通;演變性指虛擬對象模型隨著物理對象的形態和狀態變化,實時或及時地進行同步更新,以及生命體和時變體模型可依據相應規律自行演化。
“可供性”是媒介之所以成為媒介的前提[6],可為理解和檢視數字出版業提供關系的、過程的和網絡的分析視角。VR2.0階段的“PIE”特性與可供性進行耦合,進一步實現VRM在數字出版生態中的互動關系,并在生產、社交和移動社交可供性[5]上延伸出VRM生產可供性、社交可供性和移動可供性。
(1)VRM的生產可供性
VRM的生產可供性指制作VR內容時所需要的設備、軟件和資源等方面的供應能力和技術條件。其中,演變性指通過AI技術提高VR設備的自適應性和自我學習能力,從而更好地適應不同的用戶需求和環境條件,同時在生產流程中通過智能化的數據分析和管理,實現生產效率和品質的提升。在參與性方面,AI通過提供更真實的存在感和自主性增強用戶身臨其境的感覺,激發用戶參與創作的積極性和熱情。在互通性方面,AI可以將VR設備和周圍環境、其他設備及網絡連接起來,實現萬物互聯,從而使得用戶可以更方便地獲取相關信息并進行交流和分享。
(2)VRM的社交可供性
VRM的社交可供性指VR技術帶來的社交互動體驗:在演變性方面,可實現更智能化和自適應的社交體驗,如通過智能推薦系統和匹配算法,將用戶更好地連接到與自己興趣愛好相似的其他用戶,從而實現更真實自然的社交體驗;在參與性方面,可激發用戶的社交參與度和積極性,如通過對話生成技術和情感計算技術等,使虛擬角色產生語言上的自主性、更強的情感感知和回應能力,能與用戶更自然地對話和互動,從而實現更真實的人際交往體驗;在互通性方面,通過物聯網和傳感器技術,將社交活動與其他VR應用和服務連接起來,使得VR用戶可與現實世界進行互動,實現更便捷、多樣化的社交和內容共享。
(3)VRM的移動可供性
VRM的移動可供性指VR技術可以隨時隨地使用,不再局限于固定的設備和場所。演變性表現為在VRM中更適應用戶不同的移動場景。如AI可以根據用戶所在的位置、移動方向等,自動調整VR設備的顯示方式、顯示內容等。參與性指通過智能化的動態變化、互動和反饋,使用戶更深入地融入VR場景,增強用戶的參與感。用戶可通過移動設備控制虛擬現實場景中的角色或物體,感受更切合現實的VR互動體驗。互通性指VR設備可與其他智能設備進行無縫連接和互動。當用戶在移動場景中需要與其他智能設備進行協作時,AI可以通過聯網功能實現VR設備與其他設備之間的數據交換和互通。
綜上,VRM生產可供性、社交可供性和移動可供性與VR1.0階段的特征相互關聯,它們在VR2.0階段將得到更深入的拓展和耦合。這一過程中,AI技術扮演了關鍵的角色,通過提供更豐富的存在感和強大的自主性增強用戶的參與性、互通性、演變性,進一步提高了VRM的適用性和可塑性,推動數字出版向更成熟和智能化的方向發展。基于此,本研究構建了VRM內容生產的可供性模型,對VR內容的生成、發布、傳播和共享進行剖析,以進一步提升VRM生成內容的質量和實用性,為數字出版的可持續發展注入全新的動力。
二、生產可供性:多元主體協同敘事
VRM的生產可供性通過集結不同主體的力量和資源,打破傳統媒介的邊界,創造多樣化、個性化、富有創意的內容,滿足用戶不斷增強的參與性、互通性和演變性需求。這不僅促使內容生產主體發生角色關系的轉變,同時也對資源要素的適應性和可用性提出了新的要求。
1.主體從“互動者”轉向“智能化創作”
VRM技術的演進和智能技術的發展,使得讀者和作者身份逐漸模糊,呈現多向度的創作和閱讀形式。創作者和用戶都能對文本進行補充、改寫和續寫,作品的傳播也不再是單向的,每個信息接受者都可以成為潛在的創作者。同時,不同的用戶故事卷入程度和可靠性判斷,也會引發用戶與作者敘事的多樣化反應,從而推動創新的激發、鏈接和重組[13]。
當下,社會網絡可以成為個體智慧的補充[14]。在VR領域,電影化敘事(cinematic virtual reality,簡稱CVR)通過借助計算機人工智能程序、算法、工具等,讓用戶在VR環境中實時與敘事角色進行人機交互。在這個過程中,虛擬敘事角色同時扮演了認知代理(cognitive agent)、情感代理(emotional agent)、虛擬代理(virtual agent)和故事管理者(story manager)等多重身份,并肩負敘述故事、管理故事、表演故事和用戶交互等多種功能[15]。正如《技術中的身體》中提出的“第三維度”的身體概念——身體成為媒介的一部分,通過調動肢體、感官完成跨時空的“身體在場”。人機身體成為一個行動單位,而“主動式參與”加深了對內容的認知和理解。這意味著當這些角色與觀眾互動時,AI系統要能夠判斷用戶目前遇到什么問題,以及他們需要什么信息,才能夠充分理解故事進展并繼續跟進主線。AI系統會從系統數據庫中提取相關信息,并指示相關角色盡可能以自然的方式將這些信息融入當前對話中,幫助觀眾無縫地理解和參與到故事敘述中,極大地發揮了智能系統和虛擬敘事角色的聯動作用。這種智能化人機交互式創作,為VR的數字出版內容提供了更加互動的創作形式,實現了數字出版內容創作的創新和讀者體驗的提升。
2.資源從“在地化”轉向“全球在地化”
在全球化深入發展的歷史語境下,網絡媒介將地方文化從現實空間向虛擬空間拓展,實現了“在場”與“非在場”的動態相連與時空重組[16],通過結合使用者賦予權限、跨界融合以及媒介技術演進的特性,促使VRM內容生產空間形成互生互塑與深度融合的生產格局,進一步推動VRM內容生產資源從“在地化”向“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轉變。
在VRM內容生產中,用戶可以融入敘事,成為故事場景的一部分。用戶在參與過程中全身心沉浸其中,實現了心理活動、身體行為、情感甚至是過往生活經驗的整合。如游戲《原神》作為一款開放世界冒險游戲,玩家需要扮演一個名為“旅行者”的神秘角色,在游歷七國的探索和冒險過程中,將跨文化傳播與本土化運營相結合,助力該款游戲的“全球在地化”。數字內容開發者和制作者可借鑒這種理念,在考慮本地市場的同時,充分考慮全球市場的文化和政治背景,為實現數字出版內容的全球化和本地化,在內容資源的調配和適用性上要進行跨界、跨業、跨域整合,以實現數字出版內容的“全球在地化”認同[17]。
三、社交可供性:圈層化交互性體驗
VRM的社交可供性可以通過VR社交網絡的連接性,讓用戶更深入地參與內容生產,創造出更具個性化和互動性的內容,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用戶共創。
1.媒介社交化與影響力圈層
新型技術支撐的社交媒體正在形成一種“影響力圈層”,它不是指向社會學意義上的“圈子”倫理或“熟人社會”的群體架構,而是基于網絡性,甚至伴有不同程度匿名性、準虛擬性的交互關系[18]。技術的快速進步為VRM內容生成提供了重要支撐,如3D建模技術、AI 技術、全息成像技術等,可以促進粉絲與VR環境中的人物進行互動交流,建立強關系,在一定程度上實現對特定群體的精準傳播,使得圍繞VRM生成內容形成的用戶圈向圈層化趨勢演進[19]。
敘事主體的重塑需要媒介技術的可供性支撐。VR裝置作為一種媒介,是實現用戶與虛擬時空的人、物和情境進行交互的重要工具。在VR內容的創作過程中,用戶不斷通過動作、聲音或表情等身體自然行為來與虛擬環境進行非接觸交互[20];同時借助手柄、傳感器等設備參與內容創作,從而實現了個人與虛擬環境的融合,成為VR內容生產的重要組成部分。
VR空間的再造為也創作者提供了多維平臺,用戶可以在空間中敘事、在場景中創作。如2021年的元宇宙虛擬世界社交應用Horizon worlds,以VRM技術為支撐,允許用戶通過動作、聲音和表情等身體自然行為與虛擬環境進行交互。用戶不僅可以通過手柄、傳感器等設備參與VR內容創作,還可通過修改腳本搭建新的場景深度進行交互,創造出獨特的情境空間。該應用還打造免費的素材庫,讓用戶參與編寫程序代碼,進而創造出新的虛擬物品或空間。未來,虛擬社交游戲和VRM技術可為數字出版提供一個多維的創作交流平臺和全新的傳播途徑。
2.全員媒體共建的沉浸模式
沉浸式媒體模式指通過虛擬世界進行社交互動和傳遞內容。在VR2.0基礎設施不斷完善的前提下,沉浸式媒體模式成為社交媒體的未來,被動的敘事媒體已經逐漸被“故事情節”所取代,虛擬世界正在提供比無休止、無意識的滾動社交媒體更高的價值。
隨著VR技術基礎設施的不斷發展,沉浸式媒體已經成為一種具有參與度和互動性的媒介形式,構建了傳受全面融合的沉浸模式。這種模式強化了媒介的社交功能,使得傳播與接受的過程更加緊密相連,成為一個創造與交流的過程。在虛擬世界中,人們可以通過沉浸式媒體建立更緊密的讀者社群(社交網絡),促進內容創作者、技術服務商、出版社和平臺服務商之間的互動交流。為此,數字出版可以通過與VR社交游戲結合來獲得新的傳播渠道和增長空間。
當前,VR社交游戲已經成為“Alpha一代”和“Z世代”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玩家可以在VR游戲中與朋友交流、創建內容,定制視頻和滿足個性化需求。加入數字出版物元素后,用戶還可以在游戲中閱讀、分享和評論數字內容。同時,游戲制造商也可以與數字出版相關品牌進行聯合推廣,提高品牌曝光度和用戶黏性。已有部分傳統媒體公司開始積極探索VR社交游戲的新媒體特性,如VR科技公司“盜夢空間”(Inception)與德國出版社企鵝蘭登書屋(Penguin Random House)授權推出的AR體驗應用程序“Bookful”,利用AR技術和VR技術為讀者帶來更生動的閱讀體驗,已有較好的實踐基礎。
四、移動可供性:多模態立體式傳播
多模態立體式傳播已經成為數字化時代不可或缺的一部分,VRM的移動可供性可以促進其更廣泛地傳播和應用,通過提供更豐富、生動、互動的內容使用戶更深入地參與其中,滿足不同的需求和偏好,從而提升信息傳遞和互動體驗效果。
1.多模態數據互通與內容生產創新
“具身關系的概念表明主體借助技術來獲得感知,并將技術獲得的感知轉化為人的認知,從而構成人與世界的生存關系。在具身關系中,技術處在中介的位置。”[21]移動的可供性主要基于媒介技術打造協同交互式敘事情境,并通過相關設備為用戶身體介入場景提供可能。用戶的視覺、聽覺、觸覺等各種感官,通過和計算機感應接口的連接,可隨時隨地以語音、文字、圖形、動作等方式進行輸入和輸出,實現與計算機或虛擬世界之間的信息交流。VR2.0時代的互通性使得虛擬和真實環境可以進行信息交換和有效整合,從而構建“技術+場景”的多模態內容生產形式。如今,AI影像生產技術已成為多模態內容生產的關鍵技術力量,涉及AI內容生成、AI虛擬場景搭建、AI數字商業等領域,推動了傳統視覺內容生產流程創新性變革,實現了視覺內容生產的批量化、自動化、智能化。
數字出版業可在此基礎上,構建出數字化出版物、場景化在線體驗、數字圖書館、數字客服、數字工廠、數字營銷以及虛擬社區等全鏈內容的可視化、交互化生產模式,進一步降低數字出版內容制作的時間和成本,實現價值輸送和交互融合。如在數字出版中引用AIGC等功能,不僅可以基于圖像渲染、立體幾何重建和深度理解、高效還原真實環境,解決圖像畸變失真等問題,還可通過語音輸入在真實環境中快速創建各種虛擬物體。
2.無邊界融合重構立體式傳播體系
可移動特性不僅是一種對媒介融合和出版融合發展的回應[22],同時也是對人們媒介參與性、演變性和互通性需求的滿足。智能技術的出現打破了傳統媒介的邊界,促成了“無邊界融合”[23]。基于信息生態系統的核心要素,從主體、技術和信息三個維度可構建一個以用戶為主體、以數字平臺為載體、以智能技術為支撐、以創意文化為內容的新型立體式傳播體系。該體系可以跨越終端界限、超越時空限制,滿足用戶隨時、隨地、隨需、隨意進行數字出版內容創作、感知和傳播的需求。
智媒時代,基于AI技術的VR和AR等應用可以生成涵蓋視覺、聽覺的三維動態交互世界,觸覺、視覺、聽覺之間的界限甚至更多維感官之間的界限將被超越,這對數字出版行業來說尤為重要。在數字出版中,敘事主體可借助AI輔助VRM內容生成,通過MR、VR、XR等技術讓文字內容轉變為活動的視覺圖像展現在用戶眼前。用戶借助 AR眼鏡、VR頭盔等設備,可與虛擬環境、真實環境進行協同交互。虛擬環境與真實環境之間的實時數據傳輸,使用戶可在真實環境中感受來自虛擬環境的一切模擬或幻想的事物,從而增強使用的趣味性。
在媒介技術的驅動下,用戶對媒介的多功能性、移動性、交互性需求明顯增強,人與技術之間的邊界變得越來越模糊,身體成為技術的“定位場所”,人也變成可配置的“物”。由于用戶活動可以脫離特定的時空與情境,從而使傳播場景得到了極大擴容,并且日趨虛擬化、個性化和移動化。因此,在數字出版中,VRM內容生產需要開發、挖掘面向不同信息類型的多種場景,借助大數據算法推薦等技術獲取不同場景的高維數據,進而生產、推薦多樣的、適配不同場景的關聯性信息,以適應不同用戶狀態、需求和身份的差異。
五、未來數字出版的發展進路
虛擬現實媒介的創新應用推動了出版業內容生產的變革,有助于我們從生產、社交和移動等維度探索數字出版的未來發展進路。
1.開啟眾智生產,擴展多樣化內容生態
眾智生產指通過互聯網等信息技術手段,將某些特定的任務或活動向廣大用戶群體開放,讓其自由參與、貢獻智慧或資源的過程。未來的數字出版可以采用眾智生產模式,在VRM的出版環境中運用人工智能、大數據、區塊鏈、物聯網、云計算等技術,與用戶協同創作和共建多樣化內容生態。在此模式下,數字出版商可以通過多種方式來生成和呈現內容,即通過人工智能生成內容(AIGC)、專業生成內容(PGC)、用戶生成內容(UGC)等方式生成內容,并利用VRM進行內容呈現,如將其呈現為虛擬現實場景、虛擬現實游戲等形式。但在此過程中,數字出版商需根據不同內容類型和呈現方式進行適當的選擇和調整。
同時,基于AI大模型、深度合成等技術,VRM還可實現文本、圖像、視頻的自動生成,豐富數字出版的內容生產生態。例如,VR2.0的創作通常采用批量生產的方式,利用AI生成技術實現根據“任何文本”提示生成新的圖像,提供創作素材,進一步促進用戶參與創作。NFT就是其中常見的一種虛擬電子作品形態,也是數字出版物的一種新形態。NFT不僅可以用來做所有權證書,還可以作為現實世界資產的數字孿生體,使獨一無二的內容資產變得“可計算”,即可搜索、可審計和可核實,以極低的信任成本在數字出版環境中進行交易和傳播,使現實世界對應的實物產品和服務以通用、可互操作的格式在“可編程商業”中流通。由此可見,眾智化的VRM生成內容不僅推動Web 2.0向Web 3.0過渡,還進一步推動數字出版向可編程出版方向邁進。
2.引入社交元素,形成社交化用戶生態
社交網絡平臺和社交媒體內容可以為數字出版提供用戶群體和市場需求,利用VR技術打造新型的社交媒體內容和互動方式,吸引更多用戶參與其中,增強用戶黏性和品牌忠誠度,構建良好的用戶生態。
以智能算法為內核打造個性化功能,可以借助大數據、云計算等技術對用戶數據進行采集,深入分析用戶需求和掌握用戶喜好,提供更符合用戶群體特點的產品和服務,并在此基礎上重新整合,讓服務更精準。例如,通過對用戶行為數據的深度分析,為用戶提供不同的推薦服務,以滿足他們的個性化需求,并通過社區協作的方式形成用戶生態群簇,讓用戶沉浸于自己感興趣的內容之中,進一步增強用戶體驗和社交可供性的情感連接。
為此,數字出版機構應積極探索跨界合作,如與科技公司、影視公司等合作共同開發VR內容,推進數字出版的發展。如Baobab Studios內容創作公司推出的“Momoguro”以太坊NFT,就是引入社交元素的一種詮釋。總之,數字出版在未來的發展中需要注重社交化用戶生態的構建和優化,引入VRM技術提高數字出版物的品質和用戶體驗,為數字出版業的發展注入新的動力。
3.優化終端體驗,構建綜合型場景生態
數字出版面臨消費場景的多樣化和終端設備的碎片化趨勢,因此,需要在優化終端體驗的同時,構建適應不同場景需求的綜合型生態系統。其中,復合場景是數字出版發展的重要方向之一,主要指現實世界與虛擬世界相交融合,為用戶提供VRM敘事內容共創與閱讀體驗創新的復合型應用場景[24],從而創造出更豐富的閱讀和共創體驗。
隨著移動設備的發展,我們正進入后移動時代。在VRM內容生成方面,數字出版商要注重數字出版物的移動可供性和跨平臺兼容性,確保數字出版物在不同設備和場景下都能提供優質的用戶體驗。為此,數字出版物應該具有良好的可擴展性和響應性,能夠自適應不同屏幕、網絡環境和設備配置。同時,數字出版商還要探索更豐富的交互方式和內容呈現形式,積極利用新的應用場景和技術手段,開發適應可穿戴設備等新型終端設備的應用程序,拓展虛擬世界的規模和用戶群。因此,優化終端體驗、構建綜合型場景生態,已成為數字出版業務發展的必然趨勢,數字出版商需要注重用戶需求和場景變化,加強技術創新和產品研發,推動數字內容的多元化和協同創新,以滿足用戶對不同場景下數字內容的需求。
|參考文獻|
[1]史安斌. 作為傳播媒介的虛擬現實技術:理論溯源與現實反思[J]. 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16(24):27-37.
[2]徐麗芳,田崢崢,何倩. 虛擬現實媒介研究綜述[J]. 出版科學,2022(6):77-89.
[3]沈珉. VR內容生產研究:具身的視角[J]. 出版科學,2023(1):91-99.
[4]GIBSON J. J. The ecological approach to visual perception: classic edition[M]. New York:Psychology press,2014.
[5]潘忠黨,劉于思. 以何為“新”?“新媒體”話語中的權力陷阱與研究者的理論自省:潘忠黨教授訪談錄[J]. 新聞與傳播評論,2017(1):2-19.
[6]胡翼青,馬新瑤. 作為媒介性的可供性:基于媒介本體論的考察[J]. 新聞記者,2022(1):66-76.
[7]孫凝翔,韓松. “可供性”:譯名之辯與范式/概念之變[J]. 國際新聞界,2020(9):122-141.
[8]常江,田浩. 生態革命:可供性與“數字新聞”的再定義[J]. 南京社會科學,2021(5):109-117+127.
[9]趙宇佳,姜進章. VR數字出版:技術可供性視角下出版業的轉向[J]. 編輯之友,2021(3):64-72.
[10]周逵. 虛擬現實的媒介建構:一種媒介技術史的視角[J]. 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13(8):29-33.
[11]HEIM M. The metaphysics of virtual reality[M].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n Demand,1993.
[12]CIPRESSO P, GIGLIOLI I A C, RAYA M A, et al.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virtual and augmented reality research: a network and cluster analysis of the literature[J]. Frontiers in psychology,2018:2086.
[13]段鵬,李芊芊. 敘事·主體·空間:虛擬現實技術下沉浸媒介傳播機制與效果探究[J]. 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19(4):89-95.
[14]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詹姆斯·富勒. 大連接:社會網絡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對人類現實行為的影響[M]. 簡學,譯. 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7 .
[15] 周雯,徐小棠. 沉浸感與360度全景視域:VR全景敘事探究[J]. 當代電影,2021(8):58-164.
[16]郭永平,賈璐璐. 全球在地化到地方全球化:互聯網時代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與傳承[J]. 云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3(2):125-133.
[17]余洋洋,巫達. 全球化與在地化[J]. 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4):17-23.
[18]徐翔. 社交媒體傳播中的“影響力圈層”效應:基于媒體樣本的實證挖掘與分析[J]. 同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3):48-58+109.
[19]喻國明,滕文強. 發力情感價值:論虛擬偶像的“破圈”機制:基于可供性視角下的情感三層次理論分析[J]. 新聞與寫作,2021(4):63-67.
[20]楊青,周書華. 國外“虛擬現實技術發展及演化趨勢”研究綜述[M]. 自然辯證法通訊,2021
(3):100.
[21]顧亞奇,王立銳. 可供性視角下虛擬現實藝術的實踐與思考[J]. 美術研究,2022(2):109-113.
[22]王軍. 媒介可供性視角下出版知識服務產品的設計邏輯及其應用策略[J]. 出版發行研究,2020(10):55-61.
[23]陳虹,楊啟飛. 無邊界融合:可供性視角下的智能傳播模式創新[J]. 新聞界,2020(7):33-40.
[24]劉毅,曾佳欣,姜曉源. 媒介可供性視角下數字閱讀平臺數智化轉型路徑研究[J]. 中國出版,2023(4):44-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