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數據要素市場化中“產權”的特殊性(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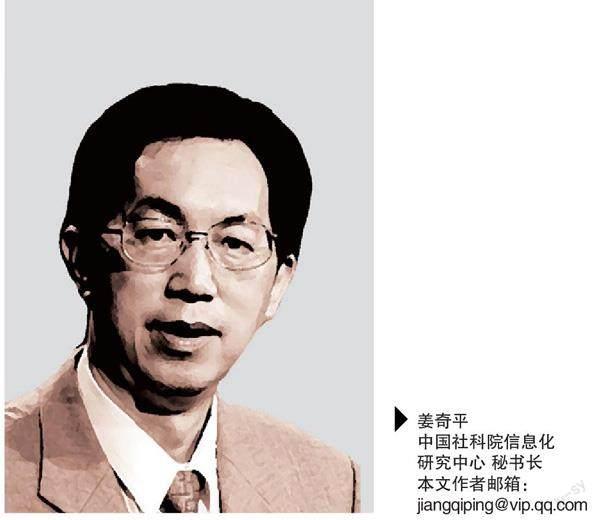
把數據要素市場化中的基本政策問題進行大的分類,一類屬于市場問題,主要是單邊市場與雙邊市場關系問題;一類屬于產權問題,主要是所有權與使用權的關系問題。本文著重談談后一個問題。
一、問題由來:與市場問題相聯系的數據要素市場化獨有產權問題
產權問題與市場問題是聯系著的。一般來說,“所有權-使用權”兩權合一是單邊市場(如貴陽大數據交易所,由實體基礎設施、買賣雙方與等價交換規則構成)隱含的前提,兩權分離(三權分置是其中使用權再分離形成)是雙邊市場(由商業基礎設施、平臺方,應用方即買賣雙邊,及合作分成合約構成)隱含的前提。
這種分類的緣由在于:第一,單邊市場中買賣雙方的數據要素商品交換,需要同時轉移所有權與使用權,是按歸屬(擁有、所有)收費;而在雙邊市場中,平臺與買賣雙邊之間數據要素交換,只轉移使用權,不轉移所有權,是按使用(效果)收費。第二,把產品形態的數據要素作為中間產品(資產),把服務形態的數據要素作為最終產品(商品),兩權分離便于對數據要素進行資產定價,而不只是商品定價。
商品交換既轉移所有權,也轉移使用權。但是數據要素還有另一面,就是在雙邊市場中,它是作為生產資料這一生產要素來進行“交換”的,但只交換使用權,而不交換所有權。例如,平臺與網商進行數據要素(虛擬店鋪與柜臺)交換,要素的所有權歸平臺不變,但(可帶來剩余的)使用權卻轉移給網商,網商按市場化原則有償共享數據要素使用權。由此帶來所有權和使用權兩權分離問題。
在政策討論中,遇到過有專家對兩權分離產生疑惑,質問兩權分離是什么意思的情況。其實不是不知道所有權與使用權的兩權分離本身(因為在農村改革中也出現過),而是不知道在數據要素問題上為什么要提兩權分離(包括三權分置)。
實際上,專家在這里真正的疑惑產生于,他心目中只有貴陽大數據交易所這種類型的市場(即先買賣、后使用的單邊市場,交換完成后才使用,而使用不另外付費),而雙邊市場在使用中才完成交換,按使用效果付費。只不過因為雙邊市場存在于網絡空間中,沒有集市或上交所那樣的一個有長寬高的空間場所,因此許多專家否定它是市場。但否定雙邊市場也是市場是沒有道理的。先得證明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雙邊市場理論(梯若爾)是一個錯誤,這可能超過了一般人的能力范圍。只能認為這些人對市場化的前沿理論理解得不夠深入。
二、理解雙邊市場的第一個產權要點:共享使用與用益物權是什么關系?
正是因為不理解雙邊市場,才產生了第一種誤解,以為兩權分離所涉及的數據要素有償共享使用(即在雙邊市場使用環節交換數據要素),不過是用益物權。以為沒有必要專門提共享使用,只要提(沒有雙邊市場也可存在的)用益物權就行了。這為獨尊單邊市場、排斥雙邊市場提供了一個不可靠論據。
先說使用權共享與用益物權的唯一相通處:數據要素市場化中兩權分離中的使用權,涉及非所有者對于所有者生產要素的使用權,這是一種對他人所有的財產加以使用(利用)并從中獲得收益的權利。從這種意義上來說,它與用益權處于同一產權類別之中。在這里,“用益”這個詞是使用與收益的合稱。
但除此之外,現有用益物權概念無法套到數據要素市場化行為上,主要有以下原因:
1.數據要素市場化中的產權需結合市場交換、使用競爭這個大背景來理解
用益物權不是法律概念(幾乎沒有什么法律使用過這一概念),而只是法理概念。它的學理在于表達對所有權進行限制,在法律中提及的都只是這種限制的具體樣式,如地上權。單邊市場的交換,要建立在所有權轉移基礎上。用益物權對所有權的限制,實際可以視為是對市場交換的一種權利限制,也就是說,用益物權所涉及權利是排除在所有權交換之外的。例如土地買賣可以不涉及地上權交易。在單邊市場中,財產的用益物權(如地上權)已被“扣除”在所有權之外了,因此在交換之前已被排除。
以單邊市場模式進行數據要素交換現存問題是,對數據要素直接定價,等于以所有(即擁有)的價值定價,而非以使用的價值定價。導致在所有權轉移中,把數據要素的用益權(注意不是用益物權)“打包”白送。而數據要素的價值,不同于商品的價值,只有在使用中才能真正確定,這導致數據要素使用帶來的溢價受“壓榨”(周其仁概念),從場內逃向場外。
與用益物權相反,有償共享數據生產要素,要求把使用權共享當作交換的條件,把所共享的使用權,當作交換的內容。這體現了數據要素的價值不在擁有而在使用的理念。交換的本質在于引入使用權的市場競爭,使要素充分自由流動并創造新價值。因此它恰恰不是要把用益權排除于交換之外,而是要把它納入交換,才能體現其完整產權。如果在雙邊市場中對用益權(對他人所有的財產加以使用并從中獲得收益的權利)也像單邊市場那樣加以排除,雙邊市場本身也就不存在了。
2.從定限物權向數據要素通用權利擴展:服務形態的生產資料的用益權
不把用益物權當作與兩權并列概念討論的第二個原因,在于它不像所有權與使用權存在于所有類型財產之中,這包括兩個方面:
其一,用益物權是一種限定適用范圍的權利(“定限物權”)。例如,根據各國法律不同,用益物權的實務,僅限處理地上權(如德國的所有權人地上權)、永佃權、地役權等少數特定用途的權利,主要是與土地有關的使用權。在關于用益物權的討論中,甚至連工業生產資料(實物生產資料)的相關權利都較少涉及。
而數字經濟學所要討論的數字生產資料共享相關的使用權,是整個一類資產(作為通用性資產的數據要素)的一般權利。如果一定要將有償共享數字生產資料納入用益物權研究,需要極大地拓展這個概念,把它從僅適用農業生產資料(土地),拓展到適用數字生產資料。由此需要重新定義用益權概念,將用益物權僅當作這種廣義用益權的子集。
其二,現有用益物權的定限對象僅限于不動產,而一般不用于動產。而數字經濟中生產資料存在服務形態的生產資料這種特殊財產分類,它不屬于物權——實物財產權的范圍。首先需要擴展財產,特別是生產資料的定義范圍,將數據要素納入進來。李江帆認為:“社會生產資料不僅包括實物生產資料,而且包括服務生產資料”,“服務產品直接構成第一、二、三產業的生產要素”。以服務方式存在的數字生產資料,主要是生產性服務業所提供的軟生產要素。包括技術、通用性資產、數據等資源。對它們的所謂用益物權,顯然要去掉“物”字。
其次要把現有用益權定義中的“排他性權利”這個表述去掉。現有表述是這樣的:“用益物權是非所有權人對他人之物所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的排他性權利”(王利明.物權法研究[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7:129)。但網商(非所有權人)對他人之物(平臺虛擬網店)的使用是非排他性的。共享就是非排他性使用的權利。
使用上的“非排他性”這一點決定了現代產權制度(工業經濟兩權合一)與 “更現代”產權制度(數字經濟兩權分離)的重要不同。后者模式是“先使用,后定價”;改變了前者的“先定價,后使用”。產權設計意圖是化解數字經濟難以避免的高風險:先利用非排他性使用來“廣種”,再對3%-6%的使用效果良好者收費來“薄收”,省卻了甄別誰使用有效,誰使用無效的交易費用,從而為數據資產的產權提供在模糊(不確定性)中動態明晰(確定)的界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