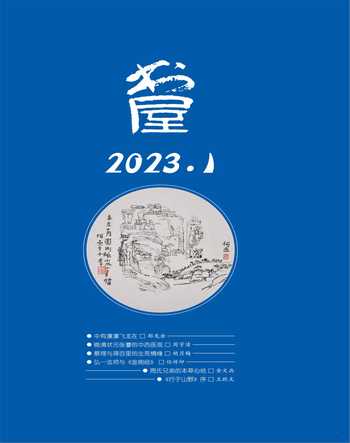四方同此水中天
劉朝華
無數關于郁龍余老師的記憶片段、對老師學術著作的閱讀心得,一次次想寫出,又一次次中斷擱下。對我來說,要深入郁師的文本并不容易,要進入他的思想世界更是艱難。郁師精通印地語,在中印文化交流研究上有多方面的卓越貢獻:刊發論文過百篇,編撰論著三十余部,其犖犖大端有《東方文學史》《中國印度文學比較》《中國印度詩學比較》《梵典與華章:印度作家與中國文化》《中外文學交流史:中國-印度卷》《印度文化論》《季羨林評傳》《中國外國文學研究的學術歷程·印度文學研究的學術歷程》等,鉤沉抉隱,賦新思于舊史,凝聚了郁師最主要的學術精華;《譚云山》《黃道婆》等文學作品,則借前賢人事,別道情志心曲,深意存焉。盡管老師的文字洗練平實,卻具有樸素的包容性和無限的伸展性。他善用譬喻,但其重要論斷卻進本退末、直斷不疑,若學問沒有生根,對其思想脈絡沒把握,其實不太能領會當中的機緣道理。
段晴老師曾在梵文課上說,言語和書寫都要慎重恭敬,印度古人認為,一出口一落筆,它就成了“咒”,具有影響生命的能量。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出版的《明清之際中國和西方國家的文化交流——中國中外關系史學會第六次學術討論會論文集》收錄郁龍余老師對我國古代官方外事機構的介紹,其中有小文題為《四方館》,郁師引用《隋書·百官志下》的記載證明隋煬帝時已設置四方館接待四方外國和少數民族來賓。我莫名感覺“四方”好像由此成了郁師的一個生命空間密碼,郁師最珍重的四方:西,自然是他畢生研究的印度;東,既是他的出生地中國,也是故鄉東方明珠上海;北是北京,也是北京大學,他學術生涯生根發芽的地方;南是深圳,也是深圳大學,他教于斯、成就于斯的一方熱土。
郁龍余老師于1946年4月3日出生在上海浦東的三林鎮,是家中長子。父親陳祥剛是南京燕子磯人,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流落上海成為難童,先被普益習藝所收容,后被周姓人家收養,送到上海學裁縫。新中國成立后,陳祥剛在上海第五服裝廠帶著徒弟完成了中國服裝行業的好幾樣技術革新而成為“工人革新家”,兩次獲評“上海市先進工作者”。外公1935年去世,外婆1940年去世,母親郁如心十四歲就獨當門戶,莊敬自強,是上海毛紡廠受人尊敬的標兵。郁老師說,父母本是苦命人,“為了養活兄妹六人,父母吃盡了千辛萬苦,但是他們從來不說苦……父母的教誨,歸結為一句話,就是爭氣”。因父母進城工作難得回家,郁老師十歲起就當家拉扯五個弟妹,把日子過得井井有條。早歲生活的艱辛從沒有扭曲、傷害到郁師的精氣神,反而培育了他的擔當、勤儉、智慧、豁達、堅韌和每臨大事有靜氣的涵養。
郁老師斷斷續續花了二十年在廢舊講義紙背寫成歷史小說《黃道婆》,周思明老師以《超越苦難生命的傳奇》一文高度評價了這部小說。在我看來郁師所塑造的黃道婆及其他勞動者形象,于苦難中不屈不撓,常懷悲憫之心,樂于助人……分明閃現著郁師對父輩和故園的追懷。小說的確超越了苦難,其底色分明是人間最值得依偎的親情、慈悲和團結互助,是黃浦江“會跳到鍋臺”的大烏鱧,是貼在墻上蟹螯骨殼做成的“蝴蝶”,是屋后三林塘港新漲的春水、甜嫩的蘆粟,是秋來籬外野菊花的芬芳。
1965年夏天,郁龍余老師從三林中學畢業,在語文老師陳一冰和班主任周文良老師的鼓勵下考入北京大學東方語言文學系,攻讀印地語。當時東語系主任是季羨林先生,而印地語專業的師資在南亞學系的三大專業中最強,除了研究室主任金克木先生、副主任徐曉陽老師,還有彭正篤、殷洪元、劉安武、劉國楠、金鼎漢、馬孟剛、張德福、劉寶珍等老師,1965年印地語專業剛畢業留校的王樹英老師和1966屆畢業的王益香老師分別負責政治思想和業務工作。郁龍余老師在北大學習期間被選為班長,然而入學第二年“文化大革命”爆發,他剛讀了一年大學就被卷入洪流,驟然失去了步步跟隨名師深入學習的條件。在此期間,郁師以堅韌的毅力自學了印度語言文學、中國文學和文學理論。1970年,郁龍余老師畢業后留校任教,在印地語專業教書工作了十四年。
在厚厚的《季羨林評傳》中,郁龍余老師歷歷述往,寫下了季羨林先生對他的學術指引和幫扶,流露出真摯而深厚的師生情誼。多年來,郁龍余老師效師而行,季先生的言傳身教已融入他的學術研究和生活中,甚至已“日用而不知”了。
跟隨郁老師時間最長的楊曉霞師姐寫道:“老師生活簡樸,從不講究吃穿,過著幾乎印度的苦行者一樣的生活。有時,我們想請老師一起聚餐,老師總說沒有必要,到學校食堂打個盒飯就可以了。除了校外學者交流來訪,或同門到深,老師很少出外應酬。”與季羨林先生如出一轍。
郁師的中印史學研究,最擅長也最具特點的是以人志史。中印兩國學者間的相互往來、著作的相互翻譯、思想的相互啟發,體現了中印文化同音共律、廣師求益的特質。郁龍余老師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起就有意識地認真思考中印交流的成果和其中有影響力的關鍵性歷史人物,通過對成果的理解并與其他史料相激發,把握一個時代的基本面貌。記人記言作為歷史結構單元本是中國史書的特點,郁老師通過記錄、整理、研究和書寫兩國學者的思想,逐步將之納入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框架,最終上升為記載中印現代文化交流史的最重要方法。這源自季羨林先生的一次小小的勉勵和期許:
“文革”后期,季羨林逐步獲得了“解放”。有一天,我在外文樓遇見他。他叫我到他辦公室。其實,這是一間空辦公室,除了蒙滿灰塵的辦公桌椅、書架之外,什么也沒有。我替他擦拭桌椅,又幫他把所有抽屜里的擦鼻涕紙清理掉……靠東墻的書架上有一摞書,我幫他整理了一下,又把書架擦了個干凈。這時,他對我說:“這些書送給你,都拿走。”……在這一摞書中,有一本印度中印學會出版的《觀光祖國詩及其他》,作者是譚云山。翻開,扉頁上有他的題贈:
敬贈季教授羨林先生指教? 譚云山一九五九年十月廿二日? 北京
我問:“這譚云山是什么人?”季羨林說:“這個人很了不起,是泰戈爾的朋友和學生,這本書,你可以好好讀一讀。”
季先生肯定沒料到,他送給郁師的這本小冊子是一粒小種子,在郁師的努力下,三十多年后開花結果。2008年,第一座“譚云山中印友誼館”在深圳大學落成,接受、收藏了譚中先生及其家人捐贈的譚云山的全部文獻,而館名,則是季羨林先生親手所題。
季先生對郁師的另一個重要學術影響也未有人提及,我認為那就是季先生早年跟郁師說的“一個字也能寫一部書”,這后來也成為郁師學術研究的重要方法:通過識別一個個重要學術概念,厘清概念與概念間的特殊連接方式,再展開體系的營造與思想的進路,最后由小及大,揭橥中印文化交流豐沛磅礴的歷史原貌。
1983年,教育部批準設立深圳大學,請清華、北大和人大支持。1984年,為了爭取一家團聚,郁龍余老師帶著二十六箱書和結婚時東語系老師們送的一口鍋離開燕園,來到草創中的深圳大學,由此開啟在南中國的印度學建設歷程。由北至南,需要于無路處辟路的堅韌,但離開燕園是“困于心,衡于慮”后的決斷。我曾反復研讀郁師跟季先生辭行的一幕:
我在一個晚上,從紅四樓(備齋)宿舍來到十三公寓季先生家。本來不長的路,變得漫長起來。平常輕松而隨意的敲門,變得猶豫和沉重起來。進了門,向季先生說明辭行之意。他一言不發,不說好,也不說不好。我請他寫封推薦信,他說:“那邊那么復雜,怎么寫?”沉默,空氣像凝固了一樣。他搓搓手望了我一眼,不知說什么好,眼中充滿不舍、無奈和擔心。我覺得再沉默下去不好,就說:“我在那里有了著落,再回來看你。”說著就告辭出門。季先生像往常一樣,將我送到樓門口。我一步一回頭地請他回屋,可是他一直站在那里望著我。我走到石橋邊快要拐彎了,回頭一看,他還在樓門口燈光下看著我。我心頭涌上一股熱流,我知道印地語專業招了好幾屆學生,正是用人之際。我也知道,我丟掉搞了十九年的專業,到了深大改行會遇到多大的困難!那個夏天的晚上,季先生在自家樓門口昏黃的燈光下,頭頂上一些趨光的蟲子在飛舞著,他久久地望著我遠去,直到我看不到他。
從1984年至2005年,在深圳大學任教治學時期是郁龍余老師學術道路的第二個階段,也是其學術思想發展的關鍵時期。在這清貧寂寞的學術拓荒時期,郁龍余老師受到樂黛云、湯一介老師的莫大鼓舞,此后轉向了中西印比較文學研究和東方文論研究。這一階段的學術成果如《中印文學關系源流》和《中西文化異同論》《中國印度文學比較》《中國印度詩學比較》是“兩面一體”的,雖然都討論中國文化與外來文化的異同關系,但實際討論的是中國文化的根性和中國學派的本質。例如,郁師曾基于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保護,嚴厲批評著名學術大家沒有歷史傳承自覺和“知識產權意識”,將中國傳統理論概念借翻譯之名套到西方概念上,從而造成對中國學術的極大損害。
2005年7月,深圳大學發文,正式成立深圳大學印度研究中心,聘任季羨林為顧問,劉安武、孫培均、黃寶生為名譽主任,郁龍余為主任。當我將深圳大學校長章必功教授簽署的聘書送到季先生手上時,他喜悅之情溢于言表。此時的季先生,聲名如日中天,根本不缺榮譽。他喜悅的是看到學生做對了一件大事。
可以說,如果沒有一個眼界開闊、自立自強的學術使命擔當人篳路藍縷,沒有幾代中印研究學人的守望相助,深圳大學印度研究中心是不可能成功創建的。從籌備多年的艱難起步,到一次又一次獲得高級別的肯定與嘉獎,每一項成績的取得都得益于創建者的不懈努力和國家的強大支持。郁龍余老師帶領深圳大學印度研究中心團隊不斷拓展思維空間、完善思路、豐富著述,利用學術聯結及社會交往,深入印度學術界,廣泛收集第一手資料,解讀中印文化關系的深層次問題,對印度文明的根源進行學術溯源,熱切為解決中印關系問題提供有建設性的對策意見,并著書立說,形成獨特的中印地緣文明話語體系,國內外學者紛紛以受中心邀請到深圳講學為榮。在郁龍余老師三十多年堅守與精耕細作下,一個扎根中印實際、自覺摒除西方話語崇拜迷障、具有靈活學術對話機制的中國印度學術研究通道終于水到渠成,深圳大學印度研究中心成為中外學界高度認可的印度學研究、中印文化關系研究的重鎮。中心的印度學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印度學研究版圖,向世界展現了學術中國、思想中國、文化中國。
2016年12月1日,時任印度總統普拉納布·慕克吉在新德里總統府隆重召開頒獎大會,將第二屆“杰出印度學家”獎授予郁龍余教授。“杰出印度學家”獎由印度文化關系委員會設立,授予在研究及教授印度哲學、思想、歷史、藝術、文化、語言、文學等方面取得卓越貢獻的海外著名印度學家。這是世界第二位、中國第一位學者獲得此項殊榮。印度國寶學者、印度文化關系委員會主席金德爾教授,在頒獎典禮上致辭說:“郁教授充實了中印兩國之間偉大的價值交流活動。在這些價值中,心靈是一束神圣的亮光。他令我們想起了手持蓮花、觀照世界的大慈大悲的觀音菩薩。慈悲使世界美好,如同晨曦之于白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