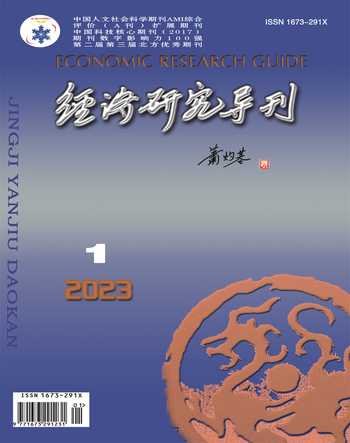“一帶一路”背景下我國移動支付國際化發展探析
崔曉瑞 梁鑫
摘? ?要: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和全球化進程的不斷推進,促使移動支付的需求飛速增長,進而推動我國移動支付的國際化發展。在“一帶一路”背景下,我國與沿線各國的金融合作日益深化,同時對外投資額不斷增加、出境游客量大幅增長等諸多因素為我國移動支付拓展海外市場提供了新機遇。因此,結合我國移動支付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發展現狀,探究其國際化發展的動因及阻礙,提出具體的發展思路和建議有助于增強我國移動支付的國際競爭力,進一步提升我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金融合作效率。
關鍵詞:移動支付;國際化;“一帶一路”
中圖分類號:F830.49? ? ? ?文獻標志碼:A? ? ? 文章編號:1673-291X(2023)01-0060-03
隨著互聯網技術和跨境電商的飛速發展,全球非現金交易規模不斷擴大,進而加快了我國移動支付的全球化步伐。目前,我國移動支付用戶數量和交易規模已遠超美國、英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穩居世界榜首。從服務境外游中國人,逐步拓展到服務當地市場,我國移動支付企業積極將技術、產品、模式、人才帶向全世界,掀起了全球從卡基支付向賬基支付轉型升級的浪潮[1]。
“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加速了人民幣國際化進程,進一步深化了我國與沿線各國的區域金融合作,為我國移動支付的國際化發展創造了機遇,同時我國技術方面的成功經驗為沿線金融欠發達國家帶來了移動支付快速發展的契機。
一、移動支付基本概念
作為一種新型的支付體系,移動支付將互聯網、移動終端和金融機構聯系起來,通過手機等電子產品進行貨幣支付結算。
移動支付打破了時空的限制,用戶無須使用現金、銀行卡等傳統支付工具,使用智能手機便可以隨時隨地進行支付,不必局限于面對面交易。而且移動支付的服務范圍廣泛,包括網絡購物、生活繳費等,為用戶的生活提供了極大的便利。
目前,移動支付技術的發展主要包括三種模式:一是“生物識別”支付,主要通過面容、聲紋、虹膜、指靜脈等方式進行身份驗證,也可通過步伐姿勢、手勢舉止等無意識行為完成身份精確識別;二是“無感交互”支付,不再依托具體載體,而是利用弱信用驗證技術將用戶的強弱ID關聯,進而完成用戶識別和資金轉移,促進用戶場景化應用發展;三是“泛終端”支付,在萬物互聯的時代,任何物體都可作為終端,因此可通過物聯網技術將資金賬戶與任意物體的ID相連接,能夠真正實現“萬物皆可支付”。
二、我國移動支付發展現狀
(一)國內
諸如人工智能、云計算、大數據、物聯網等新技術推動我國移動支付極速發展,相關產業鏈日趨成熟。《2019年全球消費者洞察力調查》顯示,中國是目前世界上移動支付使用規模最大的國家,交易比例高達86%。中國人民銀行發布的《2020年支付體系運行總體情況》顯示,2020年銀行共處理移動支付業務1 232.20億筆,交易金額高達432.16萬億元,同比增長24.50%。
借助技術的革新和市場規模的擴張,我國移動支付通過不斷的創新打造了獨特的支付應用場景,參與主體逐漸從前端的研究開發、市場布局和客戶服務等轉向移動端,帶動了包括共享經濟在內的多個新興產業。相較于歐美國家,中國并未形成使用信用卡消費的習慣,這一差異助力我國消費者迅速完成了短期內現金支付到移動支付的轉變,進一步促使我國移動支付的迅速崛起,成為遠超海外競爭對手的全球性領先產業[2]。
(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
“一帶一路”倡議加速了我國移動支付融入境外市場的進程,目前我國主要移動支付平臺在海外市場擴張勢頭正足。2019年9月公布的數據顯示,支付寶海外用戶超過3億,消費者可使用支付寶在56個國家和地區進行線上交易;截至2020年1月,微信支付業務已成功接入60個國家和地區,能進行16個幣種的直接換算,同時利用微信小程序等產品與境外商戶合作;2020年11月的公開數據顯示,共有179個國家和地區支持使用銀聯卡,其中有61個國家和地區提供銀聯移動支付服務,14個國家和地區開通了約90個銀聯標準電子錢包。
借助“一帶一路”建設發展契機,我國移動支付企業正逐步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輸出先進技術及發展經驗,為沿線部分金融欠發達國家和地區帶來了在移動支付領域趕超歐美等國的可能性,目前有些國家已順利進入互聯網金融時代。為成功融入境外市場,支付寶聚焦當地支付市場特征,實施“本地伙伴+技術賦能”戰略,通過技術輸出在包括印度、泰國、菲律賓在內的9個國家打造本土化“支付寶”,因地制宜地構造出適合當地消費者的支付平臺[3]。
在移動支付方面,“一帶一路”沿線各國雖然起步較晚,但已開始逐漸重視這一技術的發展:新加坡提出了“智慧國家2025”十年計劃,以高新技術發展助力移動支付的進步;馬來西亞借鑒中國發展經驗,蓄力推進無現金社會建設[4];印度大力推行電子錢包支付,在短期內成功實現普及率翻番。但與國內市場相比,我國移動支付在海外仍有巨大的發展空間,有望進一步通過境外市場的拓展,快速輸出我國創新技術和支付標準[5]。
三、我國移動支付國際化發展動因
(一)政策支持
2013年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強調深化區域合作與創新,構建多元化金融主體和新型交易方式以拓展區域資金融通,進一步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習近平總書記在2017年7月召開的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中明確指出,應推進“一帶一路”建設金融創新,做好相關制度設計。在2018年11月舉辦的中新(重慶)戰略性互聯互通示范項目金融峰會中,中國銀保監會副主席黃洪強調,促進金融互聯互通是“一帶一路”的重中之重。
另一方面,央行出臺《人民銀行非銀行機構網絡支付管理辦法》等一系列網絡支付監管法規,監管政策壓力降低了我國移動支付企業的盈利水平,壓縮了國內發展空間,迫使其加快了進軍海外的步伐。
(二)國內競爭激烈
我國已逐漸放寬市場準入限制,境外各移動支付巨頭大批涌入,使原本銀聯、螞蟻金服、騰訊三家獨大的國內支付市場競爭愈加激烈。中國移動支付市場日益飽和,集中度不斷攀升,各大平臺發展增速逐漸放緩,盈利水平慢慢降低,未來發展空間日益狹窄,種種壓力將促使支付企業另謀出路,通過國際化戰略拓展國際市場空間。
(三)跨境支付需求增長
統計數據顯示,我國已成為出境游客最多、境外消費最高的國家,“出國熱”同時帶領我國移動支付“走出國門”,應用場景從傳統的餐飲購物逐漸延伸至醫療、退稅等日常生活各個領域。中國人民銀行公開數據顯示,2020年,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處理業務共220.49萬筆,交易金額45.27萬億元,同比分別增長17.02%和33.44%。“一帶一路”建設的深入推進使得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到國外去工作和生活,出境游客及海外華人華僑的移動支付需求日益增長,從而形成了龐大的移動支付市場空間,進一步帶動我國移動支付行業發展。
四、我國移動支付國際化發展的阻礙
(一)政治環境經濟形勢存在不確定性
一方面,“一帶一路”途經多個東西方文明交匯地區,部分地區長期處于政權更迭狀態,極易爆發內戰或邊境沖突[6]。例如,由于位處歐亞大陸地緣政治中心,烏克蘭成為了美俄兩國爭奪的焦點;嚴重的民族宗教矛盾使伊朗、以色列等國家關系緊繃。國家間的微小矛盾極易演變成危險的武裝沖突,導致我國移動支付在這部分地區的發展面臨著嚴峻挑戰。
另外,沿線部分國家正處于政治經濟轉型的過程中,可能存在國內政治經濟不穩定的情況。在這種形勢下,當地政府可能認為我國移動支付企業會對其國家安全造成一定程度的威脅,從而會阻礙我國支付企業進入其金融市場。
(二)基礎設施建設不完善
目前,我國4G網絡覆蓋人口已超99%,超過95%的行政村已接通了光纖寬帶。相比之下,絕大部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仍處于發展中階段,總體實力較弱,在金融相關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積極性不高,且資金投入不足,總體支付體系現代化程度較低,相應的配套體系不健全,移動支付產業仍需進一步探索,例如約半數巴基斯坦人無法獲得基礎性金融服務;馬來西亞直到2018年才正式出臺電子支付相關法律法規。相關基礎設施的欠缺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整體移動支付產業的發展,同時給我國移動支付順利進入當地市場帶來了較大的困難。
(三)金融監管阻礙市場拓展
對于一個國家來說,支付體系是其最為重要的金融基礎設施之一,我國移動支付企業在境外面臨著更為嚴格的監管制度和約束環境,加大了獲取支付牌照的難度[7]。而且目前沿線各國并未實行統一的安全認證方式,制定一致的標準及合作機制還需各國相關部門間的進一步溝通。此外,我國移動支付企業在進軍海外過程中極有可能被他國視為威脅,受到不正當競爭、威脅國家安全等指控,局面更為復雜困難。
同時,“一帶一路”沿線各國金融政策復雜,我國移動支付在入駐境外市場時要遵守包括國內國外多項法律法規,需與不同監管部門進行交涉,根據目標市場具體情況對戰略規劃進行調整,在保證技術安全、保障用戶權益的同時滿足當地市場指標。
(四)消費文化差異顯著
大部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仍保留著使用現金和銀行卡支付的消費習慣,市場格局較為穩定[8]。新加坡消費者認為現金是國家價值的象征,且具有一定的匿名性質,因此仍堅持使用現金支付;約95%的菲律賓消費者沒有信用卡,通常選擇支票或現金支付。因此,即使順利通過了當地政府許可,取得了當地支付牌照,根深蒂固的消費者認知仍制約著我國移動支付企業進入當地市場的進程,使其處于滲透率低、普及程度受限的局面。
五、我國移動支付國際化發展思路及建議
(一)推進基礎設施建設
“一帶一路”沿線是我國“走出去”戰略的重點發展區域,發展移動支付的前提是實現信息網絡的互聯互通。云計算技術能夠將傳統的硬件設施高度虛擬化,把科學技術以服務的形式呈現出來,最大程度降低了對實體硬件設施的資金投入。因此,我國移動支付企業應加大對云計算、大數據等互聯網基礎設施的投入,推動產業創新,促進國內外資源共享,在境外市場營造有利于支付業務發展的環境,助力沿線國家經濟的數字化轉型。
(二)加強金融監管合作
我國應進一步探索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建立信息共享平臺和互信互認機制的可行性,完善跨境電商、信用、消費者權益保護等領域的政策法規。同時我國移動支付企業要嚴格遵守沿線國家的法律法規,我國金融監管部門應加強與他國相應支付監管部門的政策溝通,擴大共識,從而推動產業鏈、資金鏈的深度融合,實現合作共贏。
(三)洞悉消費市場導向
應著重培養當地市場消費者的消費習慣,提高用戶認同度。我國移動支付企業可以采取體驗式營銷和口碑評論等方法實行移動社交營銷戰略,與當地主流平臺開展合作,提供移動支付場景入口。通過聯合營銷推廣吸引當地消費者,使其切實感受到我國移動支付的安全便捷,逐步提高我國移動支付的知名度和影響力,同時結合當地特色,進一步開拓市場。
參考文獻:
[1]? ?吳芍希.未來移動支付產業發展環境分析[J].現代商貿工業,2021,(13):12-13.
[2]? ?孫剛.境內外移動支付發展差異比較[J].中國信用卡,2020,(9):70-72.
[3]? ?關守科,Li wanchao.國際比較視角下的中國移動支付發展研究[J].金融發展評論,2019,(7):8-13.
[4]? ?肖翔,姜鈺羨,程鉞.“一帶一路”建設金融合作的效率評估研究[J].區域金融研究,2019,(5):5-12.
[5]? ?方萍.中國移動支付在國際貿易中的應用研究[J].產業創新研究,2018,(11):72-74.
[6]? ?王運昌,楊柳.基于“海上絲綢之路”視角的東盟跨境電商發展研究[J].中國集體經濟,2018,(20):106-107.
[7]? ?劉鵬,侯瑋迪,張鳳.中國移動支付國際化動因與面臨的挑戰[J].對外經貿實務,2018,(5):57-60.
[8]? ?王玉玉.“一帶一路”戰略背景下跨境電商發展相關問題研究[J].全國商情(經濟理論研究),2015,(12):27-28.
[責任編輯? ?文? ?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