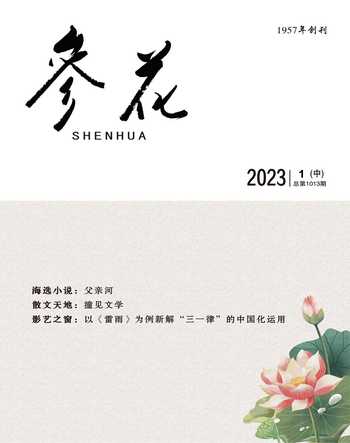淺析《自流井》中的方言運用與藝術特色
一、引言
作為一部獨具地域鄉土色彩的小說,《自流井》在語言上大量使用方言口語,具有濃郁的自貢地域特色,這與小說的題材、風格以及作者的語言觀密切相關。作者通過方言來展示當地的風俗習慣,勾勒出一幅具有濃郁地方特色的鹽都生活圖景。方言口語的使用不僅展現了鹽都人直率耿直、樂觀幽默的性格特征,更揭示了鹽都人在困境中仍能保持堅韌達觀的文化心理。本文旨在從方言出發,探究小說《自流井》的藝術特色,從而研究方言寫作對于文學創作的意義。
二、從方言看自流井人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
方言被稱為是人類文化歷史的活化石,在小說《自流井》中,作者使用了大量的方言詞匯,不僅增加了小說的地域特色,更展現了自流井人的生活方式。作者不僅在人物對話中使用方言俗語,一些職業稱謂、娛樂方式仍舊保留了方言中的叫法。自流井,是自貢的一個地名,因出產井鹽而聞名。因此,當地人多以鹽為生,他們大多參與了井鹽的生產活動。小說中,自流井的鹽業發達,鹽場的工人種類劃分得格外細,有司機、拭篾匠、山匠、管事、大幫車、牛牌、生火、輥子匠、白水挑夫、鹽水挑夫、燒鹽匠、桶子匠、篼山匠、打更匠、井上雜工、灶上雜工、筧上雜工、筧山匠、車水匠、巡視匠等。他們都通過自己的體力勞動生存,因此,也叫作“下力人”。雖然作者在自序中說他對當地人民的生活不是很熟悉,因此,只能書寫自己家族的人與事。但實際上,作者在書寫家族故事時,仍不時地關注基層鹽工的生活,并對他們的生存困境報以深刻的同情和鼓勵。
“看棚”是指在柑子林中,搭一草棚,派人看守,叫作看棚。小說中的李老幺本是柑子林的“看棚”,但由于生活壓力,放棄了土地,成了一名鹽工。李老幺原本還種著兩塊地,又是柑子林的“看棚”,但仍舊解決不了溫飽問題。因此,不得已,李老幺只能放棄土地而成為一名鹽工。鹽工的生活雖然不會有溫飽問題,但身為農民,對土地有一種天然的眷戀之情。“少種田地少吃虧。鄉下熬不過只好朝井上跑,實在說井上哪里住得慣呢?滿天是煙塵,遍地是鬧聲,鼻子里塞滿了鹽崗氣,時時刻刻直想家——想我那間茅草房,想我那片土和田,想我那座柑子林,三少,柑子林最叫我舍不得!”這里,作者以獨特的視角,描寫了鹽井生活和鹽井周邊的農村生活,筆下的鹽工是最平凡的勞動人民,他們拿著最微薄的收入,做著無比艱辛的工作,卻依然積極樂觀。除了對鹽工飽含深切的同情以外,作者也揭示了勞動人民對土地最樸實的熱愛。
除了關注與鹽密切相關的職業以外,作者在描寫鹽商家族的生活時,其中還穿插著對當地各種職業的介紹。例如“么師”指茶房,“棒客”“棒老二”指土匪,“女煙槍”指以給人燒煙為職業的女人,“丘二”指雇傭性質的掌柜、管賬之流,往往掌控著生產經營大權,“大班”指轎夫,“雙飛燕”指兩個大班等。這些特殊的方言稱謂,既體現了自貢方言的生機與活力,又展現了當地獨特的生存方式。
同時,小說中還經常提到“擺龍門陣”,方言指聊天。“龍門”是指在巴蜀地區,人們在院壩門口建造的一個類似前廳的建筑,往往用來休息或聚會。傳統鄉村禮俗社會在日常生產生活上是一個開放系統,鄰人常常串門聊天。而“龍門”則成為家人和村鄰聚集、交流、休閑、說笑的共享性空間。“擺龍門陣”不僅是自流井人休閑的日常生活方式,還展現了人們對日常休閑的重視。除了“擺龍門陣”、喝茶、抽煙以外,自流井人還喜歡打牌。而玩牌的種類則更是豐富多樣,比如“六胡兒”“斗十四”等。這些方言詞匯為人們描繪出一幅獨有的巴蜀日常生活畫卷,也反映了自流井人在困境中樂觀、知足常樂的生存觀念與人生態度。
三、從方言看鹽都的民俗與民情
《自流井》是一部描寫四川鹽場生活的小說,具有獨特的地域文化色彩,“是一篇很好的風土記”。王余杞在小說中紀實性地呈現了鹽場的風貌,真實地記錄了二十世紀初,四川鹽業生產的一些基本情況,是四川井鹽歷史真實而形象的寫照。作者得益于他出生于鹽業世家,對于自流井井鹽產銷方面的情形相當熟悉。加上作者為了使讀者充分地了解井鹽產業,還“搜集得許多不可多得的珍貴資料”。《自流井》不僅是一部活的近代自貢鹽場的興衰史,更是一部民俗文化史。“人都愛著他的故鄉,我自然是熱愛著自流井,每因為愛之深,望之切,責備求全,在所不免。”(《自流井·校后記》)作者將他對故鄉的眷念滲透在文學創作中,飽含深情地描寫了自流井的民俗風情。大量方言詞匯的使用更增添了民俗生活的地域特色,使小說獨具鄉土氣息與地方文化韻味。
小說中,自流井以鹽為生,因此,圍繞鹽有各種獨特的生活習俗。例如每家鹽井與鹽灶都分別供著井神與烘神,如運氣不好,一口井可能使井主傾家蕩產,迪三爺后來便是這樣敗家的。不同井灶的地域分布較為分散,鹽井的主人們乘著碧綠的藤小轎,飛一般的進出于他們擁有的井灶間。此外,為了躲避戰亂,大鹽商還會修建穩固的村寨,如幼宜奶奶所住的大安寨便是這樣。而這種堡壘似的住地,在自流井并不罕見。另外,還有祭祀、宗祠月會、新年正月夜里的燈會游藝等自貢當地的生活習俗。每一種特色風俗背后,無不充滿著濃郁的地方色彩和鄉土情愫,使人能夠領略到自流井當年的情狀和韻味。
在這些風俗中,還包含著人們的生活習慣,從這些生活習慣中,人們還可以看到當地人的價值觀念。例如過年要吹“過山號”,方言指年節中的一種竹制玩具,聲音如號。在大年初一拜年時,“大小一群都團聚在大門外吹‘過山號,‘嗚嘟嘟,嗚嘟啷嘟……”端午節要吃粽子、鹽蛋、雄黃酒,而門上掛的菖蒲和艾葉,散發出略帶苦澀的川南風俗的異香。盛夏時節,去水塘浮“狗扒搔”、浮“仰天推”、踩“假水”、栽“汩斗”,更是把少年的情趣和故鄉的山水交融一體了。其中最具自貢特色的,要數元宵燈會:“等到一般浪潮洶涌過去,人流讓開,才走來一對對的燈火:頭里一定是一對大紗燈,然后是四對或五對圓的,然后又是方的小紗燈,每個紗燈上都寫著朱紅扁字,標明某姓某某堂。母親對于這些堂名是熟悉的,她告訴他這是哪一家,是家門或者是親戚,是某房的某一輩……一大半是熟人,因此也就更有意思。紗燈之后應該是亮筒子,近年卻加添了馬燈,也是成對走著。緊接著亮筒子馬燈的便是一撥鑼鼓:打小鼓的走在中間,四圍的人都望著他的‘點子;那人將兩根竹芊子,一齊用力在鼓心打出一聲‘巴!急速伸出右手的竹芊在鼓面上一倒立,跟著便是一段急驟的樂節……”
從這段描寫中可以看出,燈會不僅可以欣賞到各種花樣的燈,展現自貢人民制燈工藝的精湛,還能從中看出自貢熱鬧的節日盛況以及豐富的娛樂生活。鼓聲、鑼聲與燈光、人流交織在一起,則形成了自流井獨具特色的富庶場面。從這些獨具地域特色的風俗民情中,看到的不僅是民間的文化底蘊,更是民俗文化背后自貢人的世界觀與生活態度。
另外,作者在家族故事的講述中,穿插著各種民俗節令以及民間儀式,在集體生活的展開中揭示寧靜、恒久的地方生活秩序。在民俗生活的細節刻畫上,作者用近乎白描的手法,側重呈現民俗本身的特點,展現了一幅飽含地方特色的日常生活圖景。然而作者的意圖并不是簡單地描寫當地的風俗,而是旨在挖掘民俗背后的民情,通過風俗畫面的描寫展現背后人與人之間的交往、生活等,從而揭示人性的真實。
四、從方言看民間文化心理
“方言是一種地域文化最外在的標記,深刻地體現了某一地域群體的成員體察世界,表達情緒感受以及群體間進行交流的方式,沉淀著這一群體的文化傳統、生活習俗、人情世故等人文因素,也敏感地折射著群體成員現時的社會心態、文化觀點和生活方式的變化。”方言不僅是地域化的表達方式,更是文化心理的傳達方式。《自流井》中所描述的鄉間普通民眾的生存現實,是十分樸實卻又有血有肉的,他們的語言真摯、率性,表達著最自然的情感,始終對生活抱著一種堅韌達觀的態度。同時,王余杞還通過方言土語揭露了人性的另一面,作者最成功之處,就在于通過方言將這種真實而又豐富的民間生存圖景呈現出來。
自流井的人們雖生活在灰暗中,但他們卻始終熱愛生活,對人生抱有一種樂觀豁達的態度。前文說到自流井的人們在艱難的生活之余有各種休閑娛樂的方式,這是他們熱愛生活的一種表現。除此之外,從他們的方言中也能看出其幽默、樂觀的性格。“刷壇子”“扮燈”都是開玩笑的意思,這些方言詞匯在小說中出現了很多次,從中可以看出當地群眾幽默、風趣的一面,他們面對生活的苦痛往往能一笑置之,不計較得失,因此,能笑對生活。作七公道出了人生的真理:“天公是最平等的:不分貧富,都一樣地有年過,快樂幾天,有錢的不用說咧;就是窮人,多少也可以得點喜錢,吃幾頓‘油大,酒醉飯飽,歡歡喜喜地耍上一場。”“油大”是肉類葷腥的意思。人們辛苦奔波了一年,而一頓肉就能撫平生活的苦痛。當然,這只是暫時的,這是他們面對生活壓力的一種紓解方式,同時,也是一種生存的智慧,從中可以真實感受到普通民眾堅韌、豁達的生活態度。
此外,在小說中,自流井地區的大家族內部,往往有著嚴格的等級秩序,人們按照字輩劃分等級,高的字輩往往受人尊重,但隨著發展,經濟能力也逐漸成為一個人身份地位的象征,如“字輩雖然矮,私家卻有錢的角色也不寂寞,那會使得年老的老輩子也要放下身份,有意無意地舔肥兩句”。“舔肥”的意思是捧拍,也就是拍馬屁的意思。“形勢明明地擺在這里,所以越窮的越急,而且越關心家務,都想‘趁渾水打蝦扒地在這時候摸弄幾文。”“趁渾水打蝦扒”同趁火打劫,也即渾水摸魚。在這里,方言的使用使這種以經濟能力作為等級劃分標準的現象,展現得極為形象與生動。
小說中還出現了許多戲謔的方言詞,比如說人愚笨,就有“頇”“木”等詞。其中也有自嘲的意味。在自貢方言中,常常以動物來喻指人,從而達到貶低人的效果,比如“龜兒子”“貓兒毛脾氣”等。這些方言體現了當地人直率的一面,同時,也是他們潑辣豪爽的性格體現。正是這些飽含情感的方言塑造了人們耿直率性的性格,建構了在井鹽文化影響下的文化心理。
總而言之,《自流井》不僅承載著一時一地的社會風貌及其文化信息,還承載當時當地的生活經驗與情感表達。作者以紀實性的筆觸對自貢的民俗風情、社會現實加以描摹與刻畫,第一次集中反映出自流井這一鹽都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社會原貌。作者沉浸在鹽文化中憑吊、思考,在鹽文化與自貢方言的互滲中,揭示文化與人情的密切聯系,給新文學帶來了新的文化元素與風貌。
五、結語
王余杞以自身的體驗與調查,書寫身邊熟悉的人與事,為人們展現了獨具特色的地方風俗,以一個家族的興衰觀照了整個自流井的歷史,被認為是“家族史”與“地方志”的融合。方言土語的使用,更加凸顯了小說的地方文化特色與民間色彩,展現了當地的日常生活與民俗文化,更多地揭示了自流井特有的生命體驗。
參考文獻:
[1]毛一波.王余杞與自流井[J].文史雜志,1990(06):30-32.
[2]李怡.現代四川文學的巴蜀文化闡釋[M].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
[3]汪如東.漢語方言修辭學[M].上海:學林出版社,2004.
[4]顏同林,譚琳妃.小說《自流井》與鹽文化[J].中華文化論壇,2008(01):64-68.
[5]陳裕容.王余杞代表作《自流井》與鹽文化[C]//.鹽文化研究論叢(第三輯).,2008:227-235.
[6]王余,李樹民,王小平,等.著.鹽香風韻:井鹽文化與鹽都作家研究[M].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16.
[7]王余杞.王余杞文集(上)[M].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2016.
[8]王浩.自貢方言研究與社會應用[M].成都:西南交通大學出版社,2016.
[9]秦洪平.現代四川小說中的井鹽文化初探[C]//.中國鹽文化(第12輯).,2019:93-100.
(作者簡介:彭艷玲,女,碩士研究生在讀,西華師范大學,研究方向:中國現當代文學)
(責任編輯 葛星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