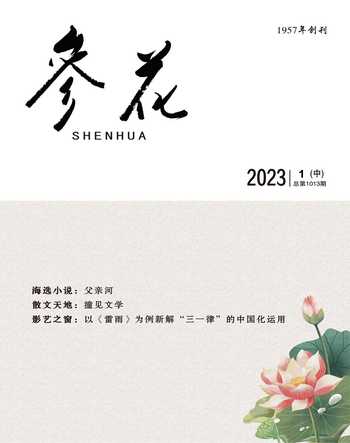新世紀詩歌思想中的傳統元素探析
一、引言
新世紀詩歌在近年來的發展中不斷生發新的創作空間,具體表現為創作活力的提升與創作技巧的靈活多變。隨著新媒體的發展,詩歌發表的門檻不斷降低,每個人都能找到適合自己的渠道進行詩歌創作,由此生成的多元化詩歌格局,展現了新世紀詩歌發展欣欣向榮的局面。我國詩歌在走向國際的過程中,需要以中國化面貌面向世人,為此,詩人開始回歸對中國傳統思想的關注,希望在汲取優秀傳統文化的過程中重建詩歌創作的精神家園。
近年來,更多的詩人開始將中國優秀傳統思想融入自己的詩學理念中,向古代先哲致敬的同時,實現了詩人安身立命的責任使命,展現出一場新世紀詩人用自己的力量與中華傳統思想對話的文化盛宴。向古典美學與傳統元素回歸,通過減緩節奏,營造感覺結構,新世紀詩歌在傳統與現代并行的道路上探索前行,不斷尋找自身發展的新的可能。中國傳統思想滋潤著每一位中國人的內心,在新世紀詩歌中引入植根于血脈的傳統思想,可使詩歌體現出古老而深遠的哲學理念。本文旨在分析新世紀詩歌思想在傳統元素使用下的文本成果,通過與優秀傳統文化結合,觀測新世紀詩歌如何在實際創作中回應傳統思想。
二、新世紀詩歌回歸傳統的可能
自新文化運動以來,現代漢語詩歌不斷探索自身的成長道路。為了找回古典詩歌的內在神韻與思想傳統,為了將象征著中華民族的審美范式傳承下來,新月派在吸收西方詩學的基礎上借用古典意象入詩,在現代漢語詩歌中融入傳統元素。當代詩歌需要在展現中華理想和氣節的同時,彰顯中華民族的思想底蘊。新世紀以來,越來越多的詩人意識到詩歌創作回歸傳統的重要性,他們通過自身的創作,感悟到古典與現代的連接,成為新世紀詩歌創作實踐的自覺。
新世紀詩歌創作兼收并蓄,橫向學習西方現代主義詩學理念,縱向接通古典詩歌傳統,“傳統與現代永遠在建構中……二者的博弈推動著審美文化的嬗變”。 時代精神仍需要通過詩歌傳遞,先進文化的提升、民族精神的繼承和發展促進了新世紀詩歌創作向著更遠的方向前行。當前要結合優秀的傳統思想,保持東方情懷,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新世紀詩歌創作不斷創新融合,推動文化精神和價值觀的傳承,讓新世紀詩歌散發更獨特的迷人光彩。詩人要在話語實踐中實現傳統與現代精神的相互感應,在傳承傳統思想的同時立足當下,在傳統與現代的平衡中順利實現詩歌的轉型,達到新世紀詩歌新的發展基點。一些詩人在宏大的歷史敘事之下賦予詩歌以古典與現代的完美結合,用詩人的個人體驗展望歷史建構下詩歌未來的出路。
三、“道法自然”——道家思想中的生態智慧
自20世紀50年代起,西方后現代主義文學在尋求精神出路時,不斷向東方文化傳統學習借鑒,英國學者李約瑟曾說:“古代中國人在整個自然界尋求秩序與和諧,并將之視為一切人類關系的理想。”新世紀以來,我國傳統文化中的生態智慧依然體現在當代漢語詩歌中。在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上,新世紀的許多詩人開始回顧老子的道法自然觀,融于天人合一、物我兩忘的境界,祈求能夠在新的困境與悖謬中尋得完美的生命形態。新世紀詩歌中展現出順應萬物的自然而然,以“出世”的狀態,從根本上肯定天人合一的狀態。
道家精神賦予新世紀詩人以和諧的眼光看待現代化進程中人與自然的關系,對推進當代中國文化自覺有著重要意義。一些對自然界的無度破壞是道家文化極力排斥的。面對自然與生存的危機,有人向現代化進程中破壞自然的行為提出反抗;有人力圖尋找一份來自內心的寧靜。在詩人于堅眼中,道家敬畏自然的理念被一些人無情破壞,在《哀滇池》中,于堅表現出對水體污染的焦慮:
“冶煉廠的微風 把一群群水葫蘆
……
一片混雜著魚腥味的閃光……鍍鉻的玻璃
圣湖 我的回憶中沒有水產 只有腐爛的形容詞”
于堅感嘆著回憶里的美好,在現實面前不斷反思現代化進程中人類對自然的破壞,表現出對自然生靈的呵護之情。給大地喘息的空間,以敬畏的心態觀照自然,在人與自然和諧相處中保持詩意的棲居,于堅用憂思寄托了農耕文明下道法自然的美好愿景,作為守望者堅守著大地的傳統,生命的傳統。華海的“筆架山組詩”和“靜福山系列”堪稱當代生態詩歌的經典篇章,是對天人合一的傳統道家思想的現代演繹。華海在《起風》一詩中的吟詠,像是回歸故里,詩人似乎觸摸到了人和大自然之間的同一脈搏。華海的詩歌結合了我國古典山水田園詩歌的傳統,正是道家思想中“天人合一”觀念的體現。詩人遵循道家思想,真正將自己投放至大自然中,感受來自天地萬物的生命節律,為現下精神方面提供一系列具有詩意的創作。
道家思想使當代人對如何把握與自然的關系有了新的認識,尊重自然、善待大自然才是人類應有的態度。在道家思想中,天人合一的至高境界便是萬物齊一,于堅、華海等詩人承繼道家精神,看待自然的眼光自覺清醒,以敬畏之心反思當下的破壞行為,借助道家的智慧喚醒人心,重建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
四、“自性氣韻”——禪宗思想中的內在本源
新世紀以來,部分詩歌在西化傾向的過程中逐步失去詩歌內在的氣韻,因而詩人們從中國傳統思想中吸取靈感,將禪宗靜悟人生的真諦運用到詩歌創作中,找尋自己的文化認同和精神歸屬。禪宗思想在佛教與老莊思想的融合中誕生,“詩禪合一”使唐宋詩詞空而有靈,提升了詩歌的審美境界。詩歌中的“氣韻”與自然意象的內在和諧,在傳統文化的交融中不斷生發新的美學范式。
楊鍵將這種思想融入日常生活中,用具有禪宗思想的詩學方式記錄著當下社會的自然與民俗。楊鍵的詩歌包含著對萬物消亡之思考,使讀者感受到冷艷孤絕之美,在自然天成的氣韻中呈現禪宗傳統中溫和典雅、帶著天地間悲憫的味道,如《恩情》:
“順從它們吧
你的手,你的嘴,你的聽覺
你的心
在這一切里面寂滅
在這一切里面延續下去”
楊鍵洞悉人世,在充滿禪意的詩句中流露出對傳統精神的繼承,他的詩歌對于其人本身而言就是一種實現,是其從個人體驗出發構建出的鄉土中國、禪宗文化、新世紀詩歌有機結合的完美實現。充盈著古典美學帶來的底蘊,現代文明的進步沖擊著中國舊有的秩序,使心靈中保持“空性”越發重要。
泉子有著江南才子溫婉如玉的心靈,他的心境在沁潤之下變得越發清澈透明,如《當你的心滿盈時》:
“當你的心滿盈時
你看見的花草樹木
遠山與濃云
都散發著
一層淡淡的光暈”
可以看到泉子在禪思中得來的智慧,在寫作中完成了對世俗的超越。泉子在詩歌里更多的是展現內心思考的過程,這與禪宗的“頓悟”一脈相承。泉子的詩歌帶有飄逸的藝術風格,用靈巧精妙的情思彰顯空靈氣韻,能夠帶給讀者無限遐想。在生活節奏較快的當下,停下腳步,充盈內心顯得無比珍貴。泉子將“慢”寫進詩歌,將自然事物與靜思禪意統一,實現自我與內心的交流,意在展現清幽孤寂、空靈悠遠的意境。中國古代禪宗思想以意味無窮和富于理趣的內容一直深受詩人喜愛,當代詩學批評的理論研究離不開禪學精神與當代話語的緊密關聯。新世紀詩歌也在不斷尋找發展方向,當新世紀詩歌發展到直指核心尋找事物之本質,沖破修辭的束縛而窺見詩歌發展的內在可能時,就會讓世界看到耀眼的東方詩學之美。
五、“民為邦本”——儒家思想中的仁愛意識
儒家文化講求仁愛,關注人生價值,探究生命意義,新世紀詩歌創作中體現的仁愛理念,正是實現個人小我與家國大業結合過程中,通過優秀傳統思想獲取經驗的有利因素,與古代儒家“齊家”“修身”理念相契合。儒家思想中關懷民生、心系社會的責任感正是詩人們進行創作實踐的需要。當困難降臨時,人們需要情感宣泄的通道,詩歌便是其中最便捷、最迅速的一種載體。困難面前,最能見證家國情懷,詩人本著時代賦予的使命感,實現對傳統文化中高尚精神的對接。
葛詩謙在《清明》一詩中,帶著這份源自傳統精神中對家國情懷的理解,用悲憫之心向英雄致敬。
“風,怎么使勁也拽不動
一泓泉懸在眼睛和鼻翼之間
沒向上滾,也沒往下涌
……”
“秦時明月不復見/楚韻離騷猶在耳”,荊楚大地上彰顯的民族精神,在新世紀詩歌中重現,是用詩歌留在這個時代的回響。鄭仁東采用古體詩的創作技巧,向古典詩歌致敬,詩歌內容感天憫人,體現出作者心系蒼生的大義胸襟,具有儒家精神中的氣度,展現詩歌回歸傳統過程中憂患意識與當下時代的緊密結合。一批心系地震災區的詩人曾拿起紙筆展現個人的關注,為抗震救災增添一份鼓舞。《星星詩刊》連載的詩選致敬了在抗震救災中艱苦付出的英雄。
“不屈不撓的意志
舍己救人
鑄就華夏兒子的鐵骨錚錚
遍地英雄鑄就重建家園的壯美詩篇”
在藍帆的《大渡河英雄重現》中,詩人由特警上演懸空飛翔的場景,聯想到那一時期英雄架起生命通道的感人歷史。當代詩人合著心中真摯的情感,從具有擔當意識的社會人視角出發,書寫著屬于時代的歷史。新世紀詩歌通過文字展現人民生活,在凝望人性中到達心靈深處,顯現出儒家思想“民為邦本”的意識。“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文藝當以人民為中心,新世紀詩歌以文字觸碰大眾,用詩歌吶喊大眾的真實內心,用詩歌表現時空的張力。當生活經驗通過詩性轉化表達出來,人們能夠在當下的創作中感受到富有詩意的生活氣息,盡管新世紀詩歌已經顯示出不同于20世紀新的審美傾向,詩人的擔當精神仍然要遵循詩歌“興觀群怨”的功能機制與現實關懷的結合。新世紀詩歌與人民現實生活的結合若彰顯了儒家思想的“仁”與知識分子的“義”,才能更好地在創作過程中活用表現技巧,構造別具匠心的詩意空間。
六、結語
新世紀詩歌在一路摸索前進,在回歸傳統的同時,不忘對現代化進程進行反思,試圖在重構精神家園的同時守住文化本心。詩人勇于探索傳統思想中積極的部分,在“道法自然”“自性氣韻”“民為邦本”分別為代表的傳統思想與社會實際結合。傳統與現代的結合是時代的必然,要將詩歌的根深深植根于這片肥沃的傳統土壤中吸取養分。新世紀詩歌的創作還在繼續,當前有許多詩人在現代詩歌回歸傳統方面做出了努力,經得起時間打磨的優秀詩歌也日漸被人們關注,詩人應該防止自己落入守舊的窠臼中,而無法將目光放遠。
正如吳興華所說:“我們現在寫詩并不是個人娛樂的事,而是將來整個一個傳統的奠基石。”當今,我國的詩歌創作迎來了黃金時代,我國優秀的詩人懷著對古典詩歌文化的熱忱,清醒地審視傳承了數千年的華夏精神,以期汲取積淀下來的優秀傳統精髓,努力開拓新世紀詩歌發展的新方向。新世紀詩歌思想蘊含著傳統文學與民族記憶,在新的時代下展現出獨特的文學價值。思想的傳承超越了時空距離,為當下展現了文學責任,傳統精神流淌在中華民族每一代人的生命和血液里,構成了傳統與現代交融的先決條件。新世紀詩歌始終割舍不下與傳統元素的關系,傳統思想為新世紀詩歌的創作提供了時用時新的精神特質。堅守詩歌陣地,重鑄民族自信,實現傳統文化與現代生活方式結合的各種可能,守住心中的傳統精神,是新世紀詩人回歸傳統的必經之路。
參考文獻:
[1]劉波.新世紀詩歌書寫與傳統之關系[J].北方論叢,2014(04):45-49.
[2]韓東.韓東散文[M].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8:155.
[3]潘吉星,主編.李約瑟文集[M].沈陽:遼寧科學技術出版社,1986:338.
[4]汪樹東.傳統生態智慧與當代中國詩歌——以于堅、華海與吉狄馬加為例[J].中國文學批評,2020(04):113-121+157-158.
(作者簡介:劉珈含,女,碩士研究生,哈爾濱師范大學,研究方向:中國現當代文學)
(責任編輯 王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