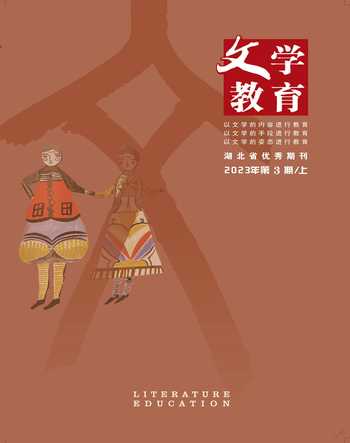新批評下鮑勃·迪倫《密西西比》文本分析
徐敏

2016年,美國當代著名民謠、搖滾藝術家鮑勃·迪倫因其“在偉大的美國歌曲傳統中開創了新的詩意表達”[1]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以此為界,國內對他的研究,可分為兩個階段。前一階段,主要介紹他的藝術創作、人物生平。后一階段,有關他的研究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一、獲獎事件[2];二、“詩人身份”及其形象構建[3];三、創作與時代的關系[4];四、作品的藝術性[5]。顯然,前三個方面側重于“外部研究”,后一方面雖是針對迪倫作品的研究,但主要從探討大眾文化與精英藝術的關系入手。國外對迪倫的研究關注到以下幾點:一、歌詞中的文學、哲學乃至宗教淵源[6];二、歌詞中特定主題的呈現[7];三、迪倫對歌詞形式與音樂結構的創造[8]。此外,還有恩杜卡·奧蒂奧諾與喬什·托斯編選的論文集《多聲部的鮑勃·迪倫:音樂,表演,文學》[9],從跨學科角度探索迪倫音樂與文學作品產生的美學與文化影響。相較國內,以英語為母語的國家地區顯然更注重對迪倫歌詞作品的研究。
既然迪倫是以“開創了新的詩性表達”獲獎,那么我們理應關注他歌詞中的詩性表達。英文“lyric”一詞源于古希臘語,原指有里爾琴(lyre)伴奏的吟誦詩,后兼具“抒情詩”與“歌詞”之意,詩、歌本為一體。而英美新批評的詩歌理論正為解讀迪倫的歌詞提供了一條可供參考的道路。縱觀國內外學界,少有學者從新批評的角度分析迪倫的歌詞藝術。主要原因如下:首先,在獲獎之前,迪倫被視為歌手而非詩人,評論界傾向于從音樂而非文學的角度研究他。其次,迪倫的歌曲傳唱度很高,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深受美國民眾喜愛,其歌詞顯然不屬于傳統意義上的精英文學。而新批評作為誕生于學院的理論派別,多以精英文學為研究對象。如今,迪倫摘得了諾獎桂冠,足見學界認可了他的詩人身份與文學成就。他的歌詞不僅是街頭巷尾傳誦著的時代記憶,更成為主題嚴肅、內涵深刻的文學作品。因此,運用英美新批評的理論方法去分析迪倫的歌詞,有助于實現對其作品的價值重估。盡管自上世紀70年代后,新批評逐漸讓位于其它流派,但它的影響卻經久不衰。有關“張力”的論說便是其中之一。1937年,艾倫·退特從兩個邏輯術語“外延”(extension)與“內涵”(intension)中提煉出了“張力”(tension)一詞。之后梵·奧康納等人在此基礎上進行擴展,張力逐漸發展為“詩歌內部各矛盾因素對立統一現象的總稱”[10]。新批評派提出的兩個重要概念:悖論(paradox)——“表面上荒謬而實際上真實的陳述”[11];復義(ambiguity)——“不論如何細微,只要它能使同一句話有可能引起不同的反應”[12],均可看作詩歌產生張力的條件。迪倫歌詞中的詩性,很大程度上亦來源于此。
《密西西比》(“Mississippi”)[13]收錄于鮑勃·迪倫2001年發行的專輯《“愛與偷”》(“Love and Theft”)。在《滾石》雜志評選的“2000年代最偉大的100首歌曲”中,它位列第17,被視為一首“漂泊者的戀歌”(a drifters love song)[14]。歌詞以第一人稱敘事,共分三節,分別敘述“我”與羅茜重逢、“我”與羅茜產生分歧卻執意追尋她、“我”沉船淹溺的經過,每節均以“只有一件事我犯了大錯/在密西西比整日蹉跎”(Only one thing I did wrong/ Stayed in Mississippi a day too long)結尾。筆者將按照文本順序,結合敘述內容逐一分析《密西西比》中蘊含的張力、悖論、復義和隱喻,從多層面解讀其藝術特色。
一.與羅茜重逢:回歸故里
在歌詞第一節中,敘述者率先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即一個從鄉村混跡到城市、再由城市返至家鄉的漂泊者,由此奠定了歌曲沉重的基調。而后出現了本詩中極富張力的一句——“天空火焰彌漫,痛苦傾盆倒落”(Sky full of fire,pain pourin down)。它既是景物描寫又是心理描寫,用短短七個單詞描繪了一幅末日般的可怖景象。“pain”無論從寫法還是從讀音上都能使人聯想到“rain”,“pour down”也常用來形容傾盆大雨。在此,迪倫不是直接將“pain”比喻成“rain”,雖也有隱喻成分,但更多的是利用單詞的讀音和字形,乃至整體語境來引人遐想。同樣,人們還會想到,“rain”來自于“sky”,由水構成;然而“sky”中又彌漫著“fire”,與水不容。這便構成了一種悖論情景。它與古典修辭格意義上的悖論有所不同,并非從文字本身就能看出其前后矛盾之處,而類似于布魯克斯在評價華茲華斯的《西敏寺橋上作》時所提出的那種“悖論”[15]。在華茲華斯眼中,大自然是奇美的、富有生命力的,倫敦城則相反,是人造的、機械的、腐朽的。可當親眼見證晨光灑落在倫敦城上的美景時,詩人驚異不已,原來死氣沉沉的大都市也能變得如大自然般鮮活美麗。他真誠地將這種驚奇之感呈現在詩歌中,由此,表面尋常之物變得不平常,日常事物顯現出新奇的魅力,作為死物的城市獲得了新生,“悖論”就這樣產生了。迪倫的這句歌詞亦是如此。漫天火焰本是不存在的,“我”卻能夠看到,因為“我”的內心充滿了痛苦;這痛苦伴隨著天空中的火焰傾瀉而下,如同雨水一般,卻沒能澆滅熊熊烈火。于是,“我”的痛苦被具象化了,它既是火也是水,它既灼人又冰冷,它既存在又不存在;正如華茲華斯的“驚奇”被具象化了,化作了一座不同于往日的、沐浴在晨光中的、“活著”的倫敦城。開篇第一句歌詞既勾勒出了一幅形神秘、恐怖的畫面,又傳達出一種主觀上極端痛苦的感受,同時又合情合理。
隨后,主人公陷入愛河,他的“思維和表達能力都那么高超”,卻總是說不清他的愛人,“真是莫名其妙”。由此可以生發出兩種解讀:或許是他被愛情沖昏了頭腦,變得糊涂;又或許是他的愛人太過復雜,捉摸不透。新批評派將復義視作詩歌語言特殊魅力之所在,正體現于此。即便《密西西比》的歌詞帶有一定敘事性,但詩歌對語言精煉程度的要求乃至對字數和格律的限制,與小說等敘事類作品相較,往往不可同日而語,因此一句歌詞更可生發出多種含義。“只有一件事我犯了大錯/待在密西西比整日蹉跎”,“你我的日子都有限度”,而“我”卻還在密西西比浪費了許多時日。這不僅是敘述者對自己蹉跎歲月的悔恨,更為深層豐富的含義將在后文中呈現。
二.追逐羅茜:重溫舊夢
歌詞第二節以“啊,魔鬼進了街巷,騾子進了廄舍”開頭,寫“我”與羅茜的情變。“騾子進了廄舍”(mules in the stall)在俚語中有“被戴了綠帽”的意思,正與前半句中表現出的不安情感相對應。曾對“我”許下誓言的、夢中出現在“我”身邊的羅茜最終背叛了“我”。她“很抱歉”,“我一樣抱歉”。“我”或許是抱歉自己“無法化解”這些事;或許是抱歉自己“在密西西比整日蹉跎”,“從來都一無所有”。“昨晚我還認識你,今晚我卻不懂”也與第一節中“卻根本說不清你真是莫名其妙”相呼應,表達出一種今非昔比、物是人非的哀愁:愛情變質了,羅茜也隨著這份愛情的消逝變成了陌生人。而“有人會向你伸出援手有人卻無動于衷”一句似乎與前后文關聯不大,細讀來卻貼切地體現出“我”心境——在這一意識流式的描寫中,“你”并非指羅茜,而是指“我”,我們可以將它理解成這是“我”面臨失去羅茜、心懷痛意時喃喃自語的一句話。不論他人是“伸出援手”還是“無動于衷”,都無益于改善這對戀人現在的境況。前文中已提到歌詞的每小節都以“只有一件事我犯了大錯/待在密西西比整日蹉跎”結尾,實際上它是對一首未命名歌曲歌詞的挪用。原句是“It aint but the one thing I done wrong/ I stayed in Mississippi just a day too long”,這首歌在20世紀初的密西西比州立監獄流傳甚廣。密西西比州作為美國種族歧視較為嚴重的州,監獄里多為黑人囚犯。囚犯們常被安排到帕奇曼農場(Parchman farm)參加勞動,在此過程中他們集體創作了一些歌曲。這些歌曲被民俗音樂學家艾倫·洛馬克斯(Alan Lomax)記錄下來,得以流傳。而其中正有一曲名為“Roise”。Roise也被視為理想的黑人女性形象。正是這樣的“典故”,更使得《密西西比》從整體上產生了復義。我們可以把它當做一首漂泊者的戀歌:主人公四處游歷,最終與羅茜相戀,他為自己曾蹉跎歲月而懊悔不已,也為羅茜的不忠傷透了心。
但這首歌詞的意義并不僅僅限于戀人之間的情感糾葛。聯系專輯名為極具種族政治意味的“愛與偷”,它源自美國文化史家埃里克·洛特的著作《愛與偷:黑面歌舞團和美國工人階級》[16],指主流文化一面歧視黑人,一面又通過戲仿和挪用來“偷竊”黑人的歌舞和文化,實際表達了一種深愛。我們推斷主人公應是一名黑人,由于犯罪(或遭受歧視)被關進了密西西比監獄。他希望愛人羅茜能夠等待自己回家,可羅茜背叛了他。當兩人再度團聚時,試圖重溫舊夢,卻早已不復當年。羅茜心懷歉疚,而他“一樣抱歉”。結合黑人在美國歷史上所遭受的不公,主人公的特殊身份、服刑的不幸經歷和愛情的失敗,在這首歌曲更顯得沉重和悲哀。歌詞“我要一直看著你直到我雙目失明”,讓人體會到強烈的哀怨之情與悲劇式的宿命感。
三.沉船淹溺:美好已逝
盡管如此,“我”仍試圖挽回羅茜。在歌曲第三節中,“我”踏上了尋找和挽留羅茜的旅程:“啊我追隨南天星來到這里/我渡過大河只為了和你在一起/啊我的船已碎成碎片然后轉眼沉底/我在毒藥中淹溺,沒有未來,沒有過去/但我的心卻不知疲憊,它輕盈它自由”。《密西西比》的美妙很大程度上在于它的復義,這一特點在本節尤為突出。“我”已經死亡,軀體在毒藥中溺斃下沉,無所謂將來,更不必說過去,往日之事已不可追,來日無論能否再追尋到“我”的羅茜,也都釋然了。“但我的心卻不知疲憊”,它不會隨著“我”的肉身一同消逝,而終將走向雋永,失去重量,伴著“我”的靈魂一并上升。“人人都在奔忙,即使早已到了地方”,這話顯然帶有悖論色彩。既然“到了地方”,怎么還會“奔忙”呢?但這不就是地獄中人“人來人往”的荒誕景象嗎?“我”呼喚羅茜與“我”同行,即和“我”一起走向死亡,引誘她開始一段有趣的生活。淹溺在毒藥中的“我”渾身濕透,衣料緊貼在身上;但因為“我”的心已自由,便不感到緊逼。于是“我”請求羅茜的“行善”以得到“幸運”。“行善”是指什么?還是死亡。在這里,最壓抑的不是死亡本身,而是“我”表達死亡的方式。“我”沒有一句話是直接表達的,而是請求她與“我”同行、向“我”行善。“我”乞求羅茜給“我”她的手,那么“我”必然也向她伸出了“我”的手;將此與第二節中“有人會向你伸出援手有人卻無動于衷”結合來看,這里的“我”仿佛在說,“我”給了你“我”的手,那么請“你”接受吧,因為愿意向別人伸出手的人已經不多了;假如“你”也愿意向“我”伸出“你”的手,“我”必然會十分感激。或許羅茜沒有牽“我”的手,于是“空虛無窮無盡”,“我”深陷于“涼透的泥土”之中。盡管“我”“隨時可以回頭”,但“不能從原路往回走”,這逝去的愛情正如“我”在密西西比浪費了的時光般,早已無法挽回。或許羅茜牽了“我”的手,但這可怖的結局也并沒能拯救喪失的激情。至此看來,這首戀歌已然成為了一首帶有濃厚悲劇色彩的“挽歌”。
當然,我們也可以對第三節作另一種理解。也許“我”并沒有死。“我”的心“不知疲憊”,“輕盈自由”,是因為“我”見到了羅茜,愛情使它重煥光彩。“我”的身體漸漸下沉,但已“不像把自己困在一個角落那樣緊逼”,“我”輕松了,甚至握住了羅茜的手,期待她說出那句她是愿意屬于我的。然而就在此刻,無窮無盡的空虛吞并了“我”。因為“我”忽然意識到,盡管我們可以回憶過去的美好,但卻無法真正回到過去那段美好的時光,對重現往日的渴望實則不過是一種逃避現實的虛妄。照此看來,這首歌仍是一首愛情的挽歌。主人公在經歷了愛人的背叛后選擇了原諒,只可惜美好已逝,青春不再。
在《密西西比》中,我們可以聽到在種族壓迫的宏大背景下緩緩道來的個體的悲劇。同時,一種被新批評派稱之為“非同質性的刺激物所招致出現的緊張力”幾乎貫穿了整首歌曲:張力存在于“天空”和“火焰”的對立之間,存在于“痛苦”與“傾盆大雨”的隱喻之間,存在于“達到目的地的人們依然在奔忙”的悖論之間,存在于“我”與“羅茜”結局的不確定性之間,甚至,也存在于歌詞的斷句、音韻的協和之間。
參考文獻
[1]https://www.bbc.co.uk/news/enterta
inment-arts-3764362(2022年7月30日)
[2]馬漢廣:《文學的事件化——從鮑勃·迪倫獲諾獎說起》,《外國文學動態研究》2017年第1期,第19-28頁。
[3]顧悅:《論鮑勃·迪倫的詩人身份》,《當代外國文學》2019年第1期,第110-116頁。
[4]李保杰:《矛盾中前行:鮑勃·迪倫的創作與時代》,《外國文學》2017年第6期,第67-77頁。
[5]陶鋒,周璇:《大眾文化還是精英藝術:論鮑勃·迪倫作品的藝術性》,《當代文壇》2017年第3期,第25-30頁。
[6]Strunk, Thomas E. “Achilles in the Alleyway: Bob Dylan and Classical Poetry and Myth.” Arion: A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the Classics,vol.17,no.1,Trustees of Bost-
on University,2009,119–36.
[7]Davies,Paul.“‘Theres No Success like Failure: From Rags to Riches in the Lyrics of Bob Dylan.”The Yearbook of English Studies,vol.20,Modern Humanities Research Association,1990,162-81.
[8]Hartman, Charles O. “Dylans Bridges.”New Literary History,vol. 46,no.4,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15,737-57.
[9]N.Otiono,J.Toth, eds, Polyvocal Bob Dylan:Music, Performance,Literature,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9.
[10][11][12][15]趙毅衡編:《“新批評”文集》,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1年,第120、353、343、354-375頁。
[13]鮑勃·迪倫:《密西西比》,選自《鮑勃迪倫詩歌集:“愛與偷”》,羅池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10-14頁。
[14]https://www.rollingstone.com/mus
ic/muic-lists/100-best-songs-of-the-2000s-153056/.(2022年7月30日)
[16]Lott,Eric. Love and theft:bl
ackface minstrelsy and the American working clas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
(作者單位: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
鮑勃·迪倫,原名羅伯特·艾倫·齊默曼。美國搖滾、民謠藝術家。鮑勃在高中的時候就組建了自己的樂隊。1959年高中畢業后,就讀于明尼蘇達大學。在讀大學期間,對民謠產生興趣,開始在學校附近的民謠圈子演出,并首度以鮑勃·迪倫作藝名。1961年簽約哥倫比亞唱片公司。1962年推出處女專輯名為《鮑勃·迪倫》。1963年起,瓊·貝茲邀請迪倫與她一起巡回演出。2016年,鮑勃·迪倫獲得諾貝爾文學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