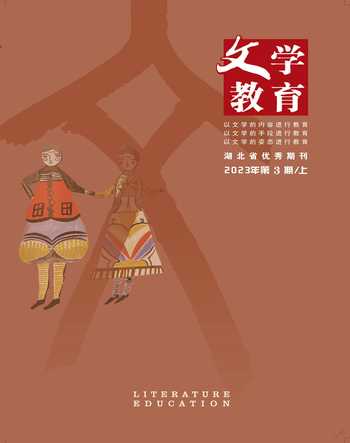論張煒《古船》的歷史意蘊
路佳
內容摘要:張煒的《古船》被一些批評家們認為“被低估了的作品”,其書寫洼貍鎮的鎮史窺見整個民族史的同時,還對家族意識的何去何從做出探索。《古船》圍繞著80年的改革展開書寫,其中歷史的片段以情境回顧的閃回與重復敘事模式,再現了50年代到80年代的家族歷史;圍繞隋家、趙家、李家的族權斗爭展開家族敘事;站在文明進步的出發點,《古船》中的主人公們都面臨著家族意識的衰落與個人主體意識的發掘。
關鍵詞:《古船》 家族敘事 歷史回顧 家族意識
20世紀80年代,可謂是家族小說創作的高發期,《古船》就作為其中之一,它的發表引發了學術界的關注。對《古船》的探索,直至現如今還是學術界的熱門。究其緣由,《古船》不僅作為具有民族隱喻意味的家庭小說,更是文明變遷的歷史寫照,正如曹文書言:“<古船>繼承了中國現代家族小說以‘家喻‘國, 以家族的歷史變遷書寫時代興衰演變的敘事傳統, 客觀真實地敘述了作為傳統鄉土中國象征的洼貍鎮上三個家族的興衰史, 聚焦于洼貍鎮的‘浮華世家如何一步一步走向敗落和解體。”[1]家族的敗落在更深層是對中國傳統以家族為單位的組織生活方式的消解與個體意識的興起。
一.歷史回顧:歷史情境再現的閃回與重復
《古船》深刻地反映上世紀七八十年的改革下,農民的生活變化。與此同時,張煒不局限于書寫八十年代改革風貌,而是將敘事時間延伸到六七十年代再到五十年代。站在敘事學角度上解讀《古船》是把握其中關于歷史書寫的關鍵。對歷史的回顧,張煒采用了一種閃回與重復的敘事模式。閃回敘事,既能保證所敘述事件與讀者的距離大大縮短,又能對整個文本脈絡起到補充作用;而重復敘事則是對具體事件與意象的深層把握。
歷史回顧之一:閃回敘事中的苦難史。中華民族對歷史的深刻把握大多數是站在對往日苦難的記憶獲得的。《古船》中的歷史回顧,承繼傳統歷史敘述以苦難與反思的兩大命題。作為見證隋家父輩“輝煌”與“自歿”的隋抱樸,對隋抱樸回憶的閃回敘事是苦難史回顧的主體內容。文本以隋抱樸視角首次閃回隋家第二代磨坊主隋迎之的自歿事件,新的社會制度確立以及舊的生產方式的清理,使得隋迎之這個手工磨坊主卸“磨”歸田,解散所有的豆腐磨坊以求罪贖后自歿身亡。中年抱樸因身份歷史問題,導致妻子被連累病死,種種苦難內化為隋抱樸的精神內核。經歷苦難洗刷后,心理及其扭曲的抱樸沉醉在老磨坊,他反思“人”的苦難及解脫途徑作為“自救”的法門,日夜在《共產黨宣言》中尋求出路。張煒對于隋抱樸個人扭曲的生活方式(甘愿在老磨屋度過漫長歲月)的溯源,就是通過一次次文本外部閃回的歷史記憶情景的回顧中彰顯出來的。這里最有趣的是,相當一部分局部閃回是通過人物回憶展開,在很多程度上卻超越了人物的視角局限。并且文本里許多章節是整體性的閃回敘述,整體事件的閃回敘述方式對文本造成一種時空的錯亂,這就造成文本時間的絕對靜止與空間的相對化。在更深層意義上,時空的錯亂除了造成敘事的張力之外,更是對具體情境下人物經歷的深層次挖掘。
歷史回顧之二:重復敘事中的情景再現。重復敘事屬于文本中敘事頻率的范疇,所謂重復敘事就是:“這種重復旨在通過多次敘述以造成時間的多樣性和風格的豐富性,增加閱讀的難度,調動讀者參與的積極性。”[2]張煒在《古船》中將重復敘事運用的出神入化。首先,對于隨大虎犧牲的描述。“老隋家,死人了”,第一次敘述是隋不召與隋見素的敘述;第二次敘述“老隋家又死人了!”的敘述語境是出現在洼貍鎮上許多人的謠言之中,緊接著直接閃回到隨大虎參軍到軍中違反紀律到犧牲的情節中;第三次敘述是出現在隋不召與李知常的聊天中穿插隨大虎戰場上的經歷。三次對隋大虎犧牲的愈加詳細的描寫,將隨大虎這個在敘事時空之外的隨家人的犧牲逐次精細化敘述出來。其次,對于茴子之死的重復敘述。以抱樸的回憶為主要敘述視角,第一次敘述茴子之死僅簡單的敘述了她死后的狀況:“她死在了落滿黑炭的土炕上,目不忍睹”[3];第二次敘述場景是在隋抱樸與隋見素的抒發擠壓二十多年的秘密時,坦露了茴子是吃毒藥自殺的;第三次在整體閃回敘述“土改”歷史中,深刻的還原了茴子自殺后受辱的慘狀。通過三次由簡到繁、迂回的重復敘述,茴子之死被完全展現出來了,歷史的面貌最終透過一層層的疊加敘述展露出真面目。
第二種重復敘事:意象重復的隱喻意味。縱觀文本有營造了幾個具有文化隱喻性的意象:古船、蘆清河,這些意象起到了一種深刻的象征意味。古船是最古老且在文本中幾次出現的意象,而且它也作為整個文本中對歷史文明的象征意象,古船第一次出現:“到后來誰都聞到血腥味了,啊啊嗚嗚地想退遠一點。高空里,那只大鷹還在盤旋,有時像定住了一樣,紋絲不動”[4],“血水”、“大鷹”具有明顯的民族文明象征效用,如果視古船為民族歷經磨難的歷史原貌,那么它吐出來的血水就象征著文明奮斗史中無辜的生命,大鷹象征著它昔日的光輝與榮耀。自此之后,古船這一意象就被隋不召不斷重復,隋不召總是將自己成為“鄭和的弟子”,他的身上確實繼承了古代航海文明的冒險精神,而古船這一意象也成為民族精神在歲月滄桑變化中的永恒存在。蘆清河也是作家常常關照的對象,文本伊始就以蘆清河的擱淺為敘述的開始,蘆清河的擱淺象征著一種古代家族文明的沒落,而后來蘆清河下發現的地下河流也證明了現代社會與古代文明的斷裂。
二.家族敘事:權力驅使下的家族發展道路
家族作為中國傳統社會的中不可避免地組成要素,中國傳統小說大多是以家族為基本書寫對象,張煒在《古船》中以族權斗爭為主要線索展開對洼貍鎮的書寫。這是因為,上世紀50—80年代甚至以后,中國農村雖然一直走在擺脫封建主義的束縛的道路上,但是封建家族的觀念與家族權力的龐大仍然占據社會主流。于是,很多書寫同時期的作品都以家族為一條明線展開書寫的,而《古船》獨特之處就在于,它將三個家族之間的經濟與政治的壓倒性關系關照文本,并且以前瞻性的眼光看待家族斗爭背后的文明衰落的現象。政治權力與經濟權力斗爭構成了隋家、趙家、李家三個家族書寫主要方面,揭示新的一代在權力斗爭中各自人生的道路。
如果說家庭敘事是《古船》文本結構的重要一環,隱含在文本中的家庭敘事后的驅使力就是三個家族內部權力的此起彼伏。五十年代以前,老隋家是掌握洼貍鎮的經濟權力的家族,隋家之人一代代的以粉絲制作為生,這不僅是隋氏家族的“底氣”所在,更是洼貍鎮引以為傲的經濟支撐。在掌握經濟權力的同時,隋氏家族后代因品行與德行之高成為洼貍鎮有名的鄉紳。時代的變化賦予家族發展更大的不穩定性,民族國家的建立后,新的政治權利扎根在洼貍鎮,隋迎之預先感受到時代變化的彷徨,于是將所有的工廠散盡,僅留下最后一個老磨屋。在政治改革的時代背景下,政治權力超越并且碾壓經濟因素,以趙家“長老”趙炳為代表的革命力量成為鎮中的權利主宰者。趙炳年少家貧,這就決定了他在今后政治出身清白;由于接受了幾年的私塾教育,他熟知中國傳統文化,作為封建知識分子;最重要的是,他在三族中輩分最高,輩分決定了處理村鎮事務的話語權。政治改革使以趙炳為代表的趙家超越以經濟權力為代表的隋家,隋家開始走向了沒落。在政治權力壓倒性戰勝經濟權力后,最令吊詭的事實是,中國大地上仍舊活躍著趙炳這樣的封建宗族家長,宗法制度仍舊在鄉間田野里深深扎根。
80年代政策的變化又將兩個家族的對立推向了新的一代,改革開放后對粉絲工廠實行承包責任制。在此之前,趙家儼然演變成了洼貍鎮政治權威的代表。在“四爺爺”趙炳的帶領下,趙多多先后在土改與文革時期擔任民兵首領,他是農村地痞流氓的代表。在特殊時期,他燒殺搶掠、無惡不作,先后對隋迎之的妻子茴子進行攻擊。他因誓死保衛趙炳而成為趙炳的得力干將。他是被趙炳這個集封建宗法權力與政治權力于一身的大家長默許的粉絲工廠接班人,趙多多對粉絲工廠的掌權,象征著趙家對隋家族權復仇的完全勝利。同時,隋見素作為隋家次子,他不像抱樸一樣年少時經歷諸多磨難,他的骨子力刻著奪回粉絲工廠的使命。在爭奪粉絲工廠經濟權力失敗后,隋見素踏入城市,后來被人所騙又返鄉。最終,粉絲工廠經歷趙多多的摻假的丑聞后終于落敗,隋抱樸不得不走出“老磨屋”的修行,著手經營粉絲工廠。洼貍鎮內部族權斗爭以趙家與隋家為主,李家作為權利邊緣化姓氏群體。
縱觀《古船》對于三個家族的敘述,權力驅使的家族間的斗爭構成了家族書寫的主要部分。自五十年代再到八九十年代,隋見素、隋抱樸、隋含章、趙多多、趙炳等人物依托家族仇恨展開權力爭奪。不難看出,封建勢力尤其是以封建家族為代表的勢力,籠罩在整個洼貍鎮,甚至是中國。對以趙炳這種表面上作為先進無產階級,背后作為隱含的封建家長的封建勢力的鞭撻,也構成了張煒《古船》的主題。以家族為單位的集體文明,最終要在時代的發展中逐漸消解,取而代之的是個人主體的意識的崛起。
三.意識嬗變:家族意識衰落與主體性發掘
評論界的許多作家稱張煒的《古船》是家族小說的典范,這毋庸置疑,家族敘事確實在文本的結構中占據重要的地位。筆者認為,家族敘事背后深層次來講,是張煒站在80年代時代先鋒對中國傳統的家族意識衰落的時代預言,小說中的人物是出生于建國之后,成長于改革的道路上,他們一方面從小接受的是農村的封建觀念的熏陶;另一方面,面對80年代祖國經濟體制的變化,他們有的敢于順應時代潮流,有的沉浸在舊的思想體制下匍匐前行。但是,無論當他們或是迎難而上或是保守堅韌,時代的破浪總會卷席著他們向前走,家族主義終會被以個人為主體的文明取代。
《古船》中每個人物都是家族的一員,無論他們在家族發展中發揮什么作用,人物與家族的關系,如同樹根之于樹冠,他們因家族被賦予社會地位與待遇,又因家族榮譽使得他們捆綁在一起,隋抱樸、隋見素、隋含章就是如此。隋家作為沒落的家族,隋式家族的兒女們都是被出身限制的單身者。雖然隋抱樸擁有過轉瞬即逝的婚姻,但在妻子桂桂死后一直單身。隋抱樸作為長子,他從小歷經磨難,隋抱樸的家庭意識體現在他的贖罪意識與追尋解脫的個人命題上,他時刻拿著死去的父母妻子與四十三人的苦難為原罪的同時,苦讀《共產黨宣言》找尋救贖自我及他人的方法。隋抱樸的感情經歷被他的苦難經歷與贖罪心理束縛,桂桂因病而死后,他愛上了小葵,最終小葵被趙炳嫁給李家,隋抱樸在李兆路出門時與小葵結合,在贖罪意識捆綁他的個人意識,最終小葵另嫁他人。而隋見素作為精力充沛的年輕小伙子,他是隋家“復仇”的代表。他厭惡哥哥抱樸的封閉與木訥,對趙多多奪去粉絲工廠懷恨在心。家族復仇意識是他行為的邏輯準則,為了阻止粉絲工廠的在趙多多手里發展,他勒令李知常不許他發明機器;為了證明老隋家人的能耐,他只身走向城市;最后,他甚至為了奪權失敗離開家鄉。隋見素的家族意識是與他個人的復仇意識捆綁的,這種族權與欲望的含混性也是隋見素個人意識發掘的起點。隋含章一直未嫁,年少的她在文革時期被趙炳拯救,迫于趙炳的淫威委身于他。趙炳于隋含章的占有是帶有報復性質的,而隋含章為了家族人員的安危受迫不得已認趙炳做干爹,家族意識是隋含章犧牲自我的根源。深厚的家族意識構成了隋家兄妹命運的牽絆,他們時時刻刻圍繞著家族利益行動,“幾乎可以這樣認為,《古船》中所有人、事的悲歡離合都能夠在其中找到屬于家族觀念的動因。”[5]盡管如此,最終他們還是走向了個人化道路。
以隋家兄妹為代表的農村社會新的一代,他們雖然努力的維持家族內部利益所得與穩定,但是面臨時代的變革與現代化道路的演進,最終以隋家為代表的古老中國的家族文明終被個人主體文明取代。無奈之下,隋抱樸接管了被趙多多經營慘淡的粉絲工廠,走出了困他十多年的“老磨屋”,成為粉絲工廠的總經理。隋抱樸的“出仕”行為象征著他內心自我封閉的結束與家族贖罪意識的解脫,以及個人意識的覺醒。隋見素幾次流連于城鄉之間,由于病情回歸故土。絕癥使他遠離家庭,居住于大夫家中靜養,“靜養”是對這個與世俗權力斗爭的年輕人的懲罰,也是他反思自我的開始。文中個人意識覺醒最明顯且激進的就是隋含章,她幾次想刺殺趙炳,但被趙炳“無賴的自責”擊退。隋含章最終拿起刀柄刺向趙炳,舍棄背負在她身上沉重的保衛家庭責任,實現了真正的個人自縊性質的解放。家族的沉重枷鎖困住的三兄妹最終都不得不舍棄家庭單位的組織生活方式,走向自我的解放道路與個人的回歸。以家族意識主導的組織生活方式最終被這些充滿現代意識的先進青年打破,新的個人主體意識開始逐漸在田野大地上覺醒。這是時代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是歷史演變的過程之不可避免的文明發展趨向。
張煒以現代意識觀照農村進化歷程,更重要的是《古船》以現代性思索歷史與民族文明,正如陳思和先生所說的:“以現代意識來觀照歷史,使讀者從歷史圖像中激發起現代人的啟示和聯想——對時間維度真正的超越,讓歷史與現實在同一個空間中發生交匯”[6]。時間已經證明了張煒的《古船》作為上世紀80年代不可忽視的家族小說典范,《古船》必將成為文學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
參考文獻
[1]曹書文.《古船》:當代家族敘事的經典文本[J].河南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05):188-191.2007.
[2]胡亞敏.敘事學(文學理論批評建設叢書)[M].華中師大出版社,2004:87.
[3][4]張煒.古船[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2:53;51.
[5]吳俊.原罪的懺悔,人性的迷狂——《古船》人物論[J].當代作家評論,1987(02):79-86.1987.
[6]陳思和.批評與想象[M].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160-161.
(作者單位:天水師范學院文學與文化傳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