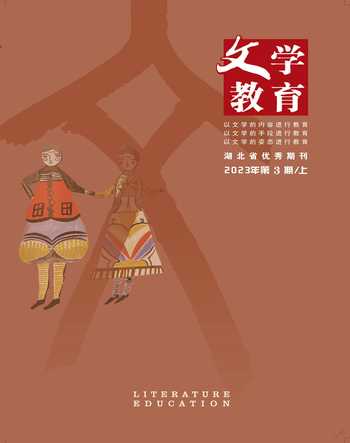《鑄劍》中的王權政治與知識分子家國理念
王萬軍
內容摘要:復仇是文學作品的經典母題。魯迅作為一個新式知識分子,作為繼往開來的一代人,他的《鑄劍》沿襲了這一主題,敘寫了一出復仇故事。并通過復仇這一主題構建了作者自己的王權政治與知識分子家國理念。王權政治通過“劍”這一形象得以闡釋;家國理念通過“江湖”與“廟堂”之關系進行深入。在王權政治與家國理念的糾纏中復仇完成,復仇的主題也實現了升華。鑄劍鑄地是文化之劍,是失掉的民族精神。復仇復的不是眉間尺的私仇,而是宏大敘事下現代人的反抗。
關鍵詞:魯迅 《鑄劍》 王權政治 家國理念
與愛情一樣,復仇也是文學中一大永恒的母題,從上古神話中的精衛填海、刑天舞干戚、共工怒觸不周山,到詩經時代的《秦風?無衣》,一直到魯迅的《鑄劍》,這一傳統既是作家的自主選擇,也是中國文學的傳承。同時,《鑄劍》中顯現出來作家的人生信條——以徹底的懷疑態度面對世界,在冰冷的外表下掩蓋著火一樣的熱情,并去審視所有可能導向徒勞與虛無的行為,避免虛無主義深淵,同時熱情似火,色貌如冰,又暗含俠義。一方面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發出反抗絕望的吶喊,另一方面又像江湖兒女快意恩仇;一方面實踐的是家國理念,另一方面反抗的是王權政治。這便是他在《鑄劍》中傳遞給我們地得。而所有的意蘊都建立在復仇主題之下,因此對復仇的開掘具有重要意義。
新時期以來,業界對《鑄劍》情有獨鐘;不獨批評界,創作圈內的莫言、殘雪等作家也十分鐘愛《鑄劍》。他們圍繞復仇情節和復仇精神進行的廣泛的探討,不過復仇背后還顯現出魯迅對于時局、政治、王權與民間的看法,這是此前的研究所忽略地。因此本文旨在探討復仇背后流露出的這些因素。
一.劍背后的王權政治
魯迅的《鑄劍》選擇了劍這一武器,有何深意呢?在《故事新編》的《序言》里魯迅認為自己的這部短篇小說集的創作方式是“只取一點因由,隨意點染”[1]354,很明顯他在選擇《三王墓》的同時也選取了古代劍文化。劍,古代兵器之一,乃是兵中王者,十八般武器之首,亦有“百兵之君”的美稱。后來隨著劍的形象逐漸泛化,它成為士大夫階級的象征,因此古典詩詞中的劍這一意象的使用數不勝數。同時劍還有俠文化的含義,荊軻刺秦時使用的是匕首,金庸小說《笑傲江湖》里豪俠令狐沖憑借一套獨孤九劍獨步天下。在千百年來的文化演變中劍已經成為一個多元化的文化意象。劍:權力、俠義、君子皆可代表。因此他鑄了這把劍,表達了一個知識分子的王權政治,同時也熔鑄了自己的秉性——“橫眉冷對千夫指,我以我血薦軒轅”的性格。
就文本而言,魯迅提到了兩把劍,分別是大王手中的雌劍與眉間尺手中的雄劍。
(一)雌劍
大王手中的雌劍代表的是無上王權。從制度層面講,王權在古代并非沒有制衡的力量,相權是唯一一個可以和王權制衡的存在,皇帝并沒有無上的權力任意罷免宰相,二者分別負責治理權與決策權,這不僅大大降低了皇帝的負擔,也不失為對政治清明的制度期待[1]。但是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因此從實際層面出發,即使制度天衣無縫,執行的依舊是人,況且中國古代多是“人治”大于“法治”。這一情況自明以降尤為嚴重,明人在取代了宋室的江山后并沒有沿襲宋人的政治經驗,最大的敗筆就是朱元璋廢除了宰相制度,大權獨攬,自明以降中國古代的中央集權制度也達到了頂峰。因此王權在古代一直難于約束。
眉間尺的父親對于大王來說是功臣,他為大王打造了絕世好劍,這把劍既是兵器又是權力。當它作兵器講時,眉間尺的父親則對應是鑄造這把兵器之人——鐵匠;當它作為權力的象征講時,眉間尺的父親便是擁王上臺的那一群人。這一群人使王坐擁了天下,因此當眉間尺的父親為大王鑄造好劍時,也是大王江山穩固之時,這時舊日的生死之交,被懷疑為覬覦自己王位的潛在者,因此,“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殺功臣,歷朝歷代都是如此,正如魯迅在自己雜文《現代史》中隱喻的那樣,歷朝歷代統治者就像變戲法的人一樣在蕓蕓看客前欲蓋彌彰。眉間尺的父親也成為第一個祀劍之人。
權力一旦沒有制衡的力量,就會變本加厲,毫無節制。這無上權力背后的空虛,以及百無聊賴的膨脹過程在文中有鮮活的體現:(1)“游山并不能使國王覺得有趣;加上了路上將有刺客的密報,更使他掃興而還。那夜他很生氣,說是連第九個妃子的頭發,也沒有昨天那樣的黑得好看了。”[2]442盛大權力后的空虛早在游山開始就已顯現,游山結束是異化的終結——權力對人性的異化。《易》曰“天地氤氳,萬物化生”,莊子云:“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辛稼軒說:“我見青山多嫵媚”,古來多少風流客,傾盡才思歌詠山河,而此刻的王卻覺得無趣,王的游山像極了馬二先生游西湖,一個因被權力異化,空虛中生出無趣,一個被科舉異化,木訥得只剩迂腐。他們不能被天地大美感動,屬于人性的那一點光輝已經消逝干凈,甚至作為一段生命,其生命本質的靈性也消失了。他們呈現出物化、奴隸化的狀態。空虛的發泄途徑是毫無緣由的宣泄沒由來的憤怒。妃子的頭發是否沒有昨天黑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有了發泄的借口。于是王的空虛轉化成了憤怒。(2)“午后,國王一起身,就又有些不高興,待到用過午膳,簡直現出怒容來。”“‘唉唉!無聊!他打一個大呵欠之后,高聲說。上自王后,下至弄臣,看見這情形,都不覺手足無措。”[2]443易怒、暴躁、毫無根據,這個人失去了生命的意義,無盡的空虛,憤怒把他引向空虛的深淵。理智的殿堂隨風而逝,這架權力的機器遂開始作威作福——“彼用百頭顱,千頭顱兮用萬頭顱!”[2]445他決定殺人,非這樣殘酷事情不能刺激他麻木的神經。(3)“‘奏來!王暴躁的說。他見那個家伙簡單,以為他會玩什么好把戲。”[2]444首先,作為王他不能禮賢下士;其次,拋卻他王的身份不談,陌生人社會交往的基礎法則是禮貌待人。這兩項他都不占,他為何敢暴躁的說,因為,他是王,他有“槍”,他環視四維意識到自己是唯一的王、是天,自己的話就是天命,人不能違天命,小民更不敢有違天命,他在憤怒的同時又在享受著權力的樂趣,這是權力帶來的附加值。
(二)雄劍
眉間尺手中的雄劍,也是權力的代表,只是這是另一股力量,如果說大王的雌劍代表的居廟堂之高者的權力,那么眉間尺的的雌劍就是天下處江湖之遠的民間力量。與雌劍不一樣,眉間尺的雄劍有一個進化過程,或者可以說是覺醒過程。在覺醒前他是眉間尺手中的蘆柴,眉間尺用其戲弄那只老鼠,小說中詳細寫到了他對待老鼠的情景:老鼠被他因憎惡一會兒按在水底,一會兒又因為生出憐憫被撈起來,救上來后又覺得它面目可憎,將它抖在水甕,用蘆柴直搗其頭,一番折騰后老鼠不再動彈,他又生出惻隱之心,折斷蘆柴把它夾起來。他掌控了它的生死,它像草芥一樣匍匐在他面前,左突右沖,逃不脫囚籠。這是民智未開時的原始暴力,他和王上手中的雌劍無異。他主宰了老鼠的生死就像大王主宰小民的生死一樣。因此這時的他若果復仇,則等同于阿Q式的革命[3]。就像禪宗講的頓悟一樣,“迷則千百劫,悟則剎那間”,當母親告訴眉間尺這一晴空霹靂后,他頓悟了。然而革命必然流血,他犧牲在半途,但他的意志由黑衣人接替,并且更為強大,更堅不可摧,就像黑衣人歌謠唱的——“我用一頭顱兮而無萬夫”[2]445。因此盡管殘雪評論認為眉間尺與黑衣人是同一人[4],但還是有諸多文本證據顯示二人應當是兩個獨立的不同的個體,只是擁有相同的信念。
1911年11月4日,革命黨人活捉了浙江巡撫增韞,杭州宣布光復。這個消息很快傳到了紹興。正在紹興府中學堂教書的周樹人這一年正好30歲,此時他還沒有啟用魯迅的筆名,他尤其興奮,在《越鐸出世辭》里以“國土恒恒,則首舉義旗于鄂。諸公響應,濤起風從,華夏故物,光復大半,東南大府,亦赫然歸其主人”的句子,禮贊了這次革命。紹興光復時,他甚至佩戴著祖父的腰刀去迎接光復。魯迅曾給自己取號“戛劍生”。他崇敬有俠士氣的人,例如秋瑾這樣的俠女,尤其敬佩。可見魯迅本身的俠義精神也使得他引入劍這一文化元素。
此外對“劍”這一形象的引入,使得它與《鑄劍》這一題目互文。他愿意做文明的執劍人,正如于堅所言“必須有人唱挽歌 ?否則文明沒有深度”。劍,是文化,鑄劍鑄的就是文化,是失掉的民族精神。希冀愚弱的國民能夠奮發起來,拿好手中的“劍”,而不是徘徊于“坐穩奴隸”與“想做奴隸而不可得”的時代。“愿中國青年都擺脫冷氣,只是向上走,不必聽自暴自棄者流的話。能做事的做事,能發聲的發聲。有一分熱,發一分光。就令螢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發一點光,不必等候炬火。”[5]340
二.復仇與知識分子家國理想
魯迅在抄了幾年古碑后,遇上了錢玄同,產生了經典的鐵屋之辯,看似魯迅被錢玄同“說服”,寫作了《狂人日記》,可是在魯迅自己的思想中“虛無”、“必無”這樣的觀點仍是占據主導地位,注定他與樂觀的《新青年》同仁不一樣。
他并不渴望“將來的黃金世界”在這一點上,魯迅與托爾斯泰的《論末世》中的觀點相通。在這里托爾斯泰將作家、藝術家與帝王、總統、爵爺們劃入了同一個維護所謂“文明”的陣營,也就是文化守成者的陣營,西川認為這觸及了一個大問題:文明——不是人類學、考古學意義上的那個意涵廣闊的文明概念——是一種富含品味、記憶、不愁吃不愁穿、講究層次的生活方式,是一種特權,你需要跳起來才能夠到;但在某些時刻,甚至某些相當長的時間段,它拒絕你的靠近,尤其當你是一個跳不起來的人時。[6]很長一段時間,民間都是被文明排斥在外的。而魯迅早在《故鄉》中就呈現出一種農民情節[7],顯示了作者自己對農民的哀矜,農民正是民間的代表。對于權力意識形態不曾抵達過的民間,那些未經美化的角落,一切現有的道德文明還沒有完全滲透,生命在這里野蠻生長。它看起來是那么不盡如人意,那么落后蠻荒,但是現在有的一切文明竟都是從這里生發開來的。魯迅在新文學伊始便注意到了對民間的思考,鄉土小說便是在他的影響下發展起來的創作。《朝花夕拾》中對民俗文化的記憶,甚至《吶喊》《彷徨》中對民間的批判,這背后都反映出作者對民間的重視。
《鑄劍》創作于1926年,這是《故事新編》中的早期作品,此時沒有發生國民黨對共產黨的大屠殺,他內心的虛無或許并不多,內心的“死火”,還沒有掉進冰冷的深谷,只需要一點觸發,他仍然敢像浮士德一樣去搏擊長空,仍然有敢于入世的膽量。例如,他在《影的告別》中寫道:“我將向黑暗里彷徨于無地”、“我獨自遠行,不但沒有你,并且再沒有別的影在黑暗里。只有我被黑暗沉沒,那世界全屬于我自己。”[2]170他愿意獨自掮起閘門,解脫眾生,自己走向黑暗,同它戰斗,仿佛若佛陀、基督、釋迦一樣,世間的苦難,他要一概擔當。甚至后來的女師大慘案發生當天還寫下過“墨寫的謊說,決掩不住血寫的事實。血債必須用同物償還。[2]217”這樣有戰斗性的文字。可見魯迅絕不是一個投降主義、機會主義,他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和古代許多文人士大夫一樣有著自己的入世理想,或許不在于“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但誰又能說沒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民”的心愿呢。
在《影的告別》中魯迅刻畫了一個渾身漆黑的影的形象,而在《鑄劍》中他又塑造了一個渾身漆黑的黑衣人形象,“影”是魯迅的自喻,那么毋容置疑,黑衣人身上我們仍然能看見魯迅的側影。就像丸尾常喜談論的一樣,魯迅把自己的身影投射到這個黑衣人身上,于是自己是的矛盾心理也能通過其雙重身份看出來。[8]黑衣人,純黑;影,純黑。魯迅以黑為其色彩:黑,萬色之宗,將萬物隱去,同時又包含了萬物的駁雜。古老的中國哲學中便只有黑白二色。而黑衣人眉間的一輪“燐火”更是“死火”,是魯迅甩不脫的“鬼氣”,在宴之敖者眼中閃爍。因此,他必然踏上復仇之旅,這注定是一個先覺者,同樣注定的還有先覺者們的宿命。七天后,合城街道上,看客熙攘,百姓跪拜著國王的“大出喪”,“幾個義民很忠憤,咽著淚,怕那兩個大逆不道的逆賊的靈魂,此時也和國王一樣享受祭禮”[2]451,“義民們”看見的是復仇者享受著和國王一樣的祭禮,看不見的的是“一夫則無兮愛乎嗚呼”[2]442。“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暴君的暴政,時常還不能饜足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欲望。”[5]384現在一個復仇的人犧牲了,卻遺給了大眾無比的愛和幸福。合城夕陽里,“眾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你則“含道獨往,棄智遺身”。這就是魯迅的復仇觀。恰似“影”獨自邁向無底深淵,殊不知“所謂無底深淵,下去,也是前程萬里”。[9]小說的主題是復仇,但復的不是眉間尺的私仇,而是宏大敘事下的現代人的反抗。這樣的復仇充滿俠的形象,近乎與墨家的俠,是愛與溫存,像“士為知己者死”,挺身而出,像《理水》中的大禹。
歷朝歷代,權力對知識總是占有絕對的優勢,沒有“青劍”的知識者墮入歷史的煉獄。知識分子企圖參與歷史文化建構,參與江山社稷,出則憂其君,入則憂其民,然而卻被權力劃定了活動界限。知識理性的缺席,導致歷史的蒙昧和野蠻,就像《塵埃落定》中的麥琪土司家族,盡管他們曾今繁榮,可是他們割了翁波意西的舌頭,所以塵埃落定以后,“遂無人問津”,也無法問津。權力圈禁了泱泱之口,幾千年了,依舊如魯迅的《近代史》一樣,如加西亞馬爾克斯筆下的馬孔多居民一樣,“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盡顯貧瘠與荒涼。于是魯迅創造了這樣一個以劍為武器的復仇故事,顯示了一個知識分子的家國理念:結尾處,三個頭顱難分彼此,頭顱即腦袋,腦袋即思想,三個頭顱不分彼此,則是三種思想的相互糾纏與制衡,即以大王為代表的廟堂,以黑衣人為代表的知識分子,以眉間尺為代表的民間,三種力量相互影響,相互影響制衡,最終達到一個三角形的穩定結構。
參考文獻
[1]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8年10月
[2]魯迅全集[M].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11月
[3]李之凡.生存還是死亡——論《鑄劍》中老鼠的虐殺[J].《安徽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2年12月
[4]殘雪.藝術復仇——讀《鑄劍》[J].書屋,1999年1月
[5]魯迅全集[M].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11月
[6]西川.大河拐大彎:一種探求可能性的詩歌思想[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7月
[7]楊梅.試論魯迅作品中的農民情節[J].成才之路,2010年1月
[8]沈子渝.從《鑄劍》再看魯迅之“復仇”與“鬼氣”[J].《青年文學家》,2018年5月
[9]木心.云雀叫了一整天[M].廣西: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9月
(作者單位:貴州財經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