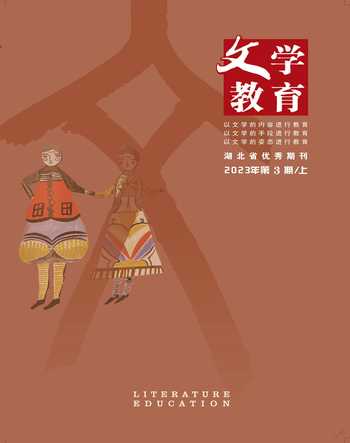老舍《月牙兒》中概念式人物“月牙兒”研究
孫嘉欣
內容摘要:概念式人物是一種沒有具體形象、偏向印象式的人物。老舍通過自敘傳的形式,塑造了概念式人物“月牙兒”,并賦予“月牙兒” 這個概念式人物復雜的內涵。概念式人物“月牙兒”在言和意中建立起意象式的中介,賦予《月牙兒》的主人公更加悠長的意蘊。
關鍵詞:老舍 《月牙兒》 概念式人物 內涵
《月牙兒》是現代著名作家老舍的早期作品,也是他短篇小說的代表作。在《月牙兒》中,故事發生的時代背景是民國時期。民國時期,雖然封建社會的政治體制已經崩潰,但是,并沒有建立起一套有利于社會發展、有利于民生發展、符合中國國情的政治體制。再加上多年的軍閥混戰,大量農民失去了土地,流入城市,成為生活毫無保障的城市貧民。其中,那些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女性,更是處于一種近乎絕望的處境。經過“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的沖擊,雖然西方“民主、自由、科學”的觀念已經傳入了中國,“女權運動”、“婦女解放”的口號,也已經在社會上有了一些影響,個別家庭條件較好的婦女,也有了到學校上學的機會,成為所謂的“新式”女性。但是,不少有識之士都清醒地意識到,所謂“解放”之后的婦女們,依然是沒有出路的,她們中的大多數,甚至連最基本的生存權利都沒有,能夠獨立生活的機會也是非常渺茫。之所以會如此,從思想觀念的層面來看,整個社會對婦女的歧視沒有從根本上發生改變,婦女的社會地位也沒有得到實質性的提升;從政治制度的層面里看,民國時期的社會,也沒有為婦女的生存和發展提供更多的機會,即便是她們最基本的就業機會也是極少的。所以,所謂的“婦女解放”,實際上只是一句空口號而已。關于這個問題,魯迅在他的小說《傷逝》中,也進行過深刻的思考。《傷逝》的女主人公子君,受到婦女解放和新式愛情等新思想的影響,為了追求新式愛情而離家出走,離開了她賴以生存的所謂的舊家庭,后來,她又被丈夫涓生拋棄,最終在生活貧困與他人的輕蔑、譏笑和冷眼中孤寂地死去。所以,魯迅在《娜拉走后怎樣》一文中,尖銳地指出:“娜拉或者也只有兩條路:不是墮落,就是回來……還有一條,就是餓死……”由此,我又聯想到春秋時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軍事家管仲,在《管子·牧民》中所說的兩句話:“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這兩句話實在是至理名言,道出了千古不變的真理。所以,民生問題,特別是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女性的生存和發展問題,不論在哪個時代,都是一個頭等重要的大問題,需要引起社會各界人士的高度重視。
在老舍的小說《月牙兒》中,“月牙兒”這個意象是文章的情感線索,也是女主人公的化身,同時也是女主人公命運沉浮的象征。與遼闊清冷的夜空相比,月牙顯得那么的渺小;與無邊無際的黑暗相比,月牙的光也顯得那么的微弱,隨時都有可能被無邊的黑暗吞沒。所以,“月牙兒”其實象征著當時大多數處在社會最底層的女性們,所面臨的幾乎近于絕望的處境和命運。本文將從概念式人物“月牙兒”的形成、“月牙兒”的內涵、“月牙兒”式人物的意義等幾個方面,全面展示女主公的生存狀況和絕望處境,深入剖析《月牙兒》的思想內涵,體味作者對民國時期女性悲劇命運以及女性未來出路的深刻思考。
一.概念式人物“月牙兒”的形成
《月牙兒》以自敘傳的方式講述了一個女學生,為生活所逼迫逐漸淪落為暗娼的故事,我們觀察故事的主人公,可以發現,我們不知其姓名、不知其具體相貌、不知其家住何方,不能產生一個具體的形象。作者在塑造人物的過程中,采用較為主觀的自敘傳的形式,散文詩化的語言,描繪出一個脆弱而倔強的女性在命運中掙扎的剪影,但是,我們卻不能窺見這個剪影的細節。有學者這樣評價,“女主人公自身不甘淪落的奮斗掙扎歷程和她所處的令她不斷淪落的客觀處境,不僅無助于作家把她塑造成一個豐滿鮮活、個性獨具的形象,反而在某種意義上似乎更指向了一種寬泛的共性的表達。”[1]因此,這種沒有具體形象,偏向印象式的人物我將其稱為概念式人物。
概念式人物在中國傳統文學中早已存在,也在外國文學中出現過,可謂是歷史悠久。概念式人物通常伴隨著意象出現。比如“香草美人”的意象,最早出現在屈原的作品中。屈原在他的代表作《離騷》中,經常以“香草美人”自喻。后來,在中國古代文學作品中,“香草美人”逐漸抽象化,象征著那些有著高尚的品行修養,德才兼備、潔身自好、不與世俗同流合污的文人、君子。再比如,我們常說的“于連式”人物,則用以代指那些毫無道德修養和道德追求,但是又野心勃勃的青年。在作品經典化之后,原作中的人物的某一特質得到強化,并用一概念命名,使這一概念與這一人物特質產生強烈的聯系,由此誕生出一種典型人物,這便是本文所指的概念式人物。
因此,《月牙兒》中的主人公這種擺脫具體化,偏向于共性的塑造方式,使“月牙兒”成為了一個概念式人物。月牙兒這個意象可以說是文章的情感線索,它是主人公的化身。下面,我用表格梳理了故事情節發展中,月牙兒情狀和人物情感的對應變化,來具體研究作者是如何通過“月牙兒”來塑造人物,表達文章的主旨。
二.“月牙兒”的內涵
內涵1
看見月牙兒的時機:七歲,爸爸去世。
月牙兒的情狀(原文):帶著寒氣;酸苦;一點點一點點微弱的淺金光兒照著我的淚。
感情:孤獨,命運的悲苦。
內涵2
看見月牙兒的時機:被當鋪老板拒絕,家中無物可當。
月牙兒的情狀(原文):月牙兒照著我的眼淚;老這么斜斜著。
感情:對無法逃脫的貧苦的命運的恐懼和悲傷。
內涵3
看見月牙兒的時機:媽媽洗衣服養家。
月牙兒的情狀(原文):越可憐媽媽,便越愛這個月牙兒,在夏天更可愛,老有那么點涼氣,像一條冰似的。我愛它地上那點小影子。
感情:“我”和月牙兒同病相憐,找到了唯一的知音;苦中作樂。
內涵4
看見月牙兒的時機:母親再婚,要離開住慣了的家。
月牙兒的情狀(原文):天上又掛著月牙兒。
感情:我有點怕,又有點希望。不希望重蹈覆轍,又對未來的美好抱有幻想。
內涵5
看見月牙兒的時機:“我”不愿意做暗娼來“幫助”媽媽掙錢,母親又嫁人我和母親分道揚鑣。
月牙兒的情狀(原文):月牙兒這回沒出來,這回只有黑暗;連個影子也沒有。
感情:“我”不恨媽媽了,一切都是因為這張嘴,是糧食的問題。我意識到生存才是讓人被迫放棄尊嚴的罪魁禍首。
內涵6
看見月牙兒的時機:“我”被胖校長收留。
月牙兒的情狀(原文):我又老沒有看月牙兒了;心就好像在月光下的蝙蝠,雖然是在光的下面,可是自己是黑的。
感情:“我”明白人的唯一價值在于有用,才能換取生存資料,“我”變成只關心自己的利己者。“我”對于外表的美驕傲又害怕,害怕自己的美變成別人眼中的有價值的商品而被消費被蹂躪;月牙兒也是“我”的自尊與希望的象征,“我”不敢看月牙兒是因為害怕面對這個內心逐漸冷酷消沉的自己。
內涵7
看見月牙兒的時機:“我”理解了媽媽,媽媽所走的路是唯一的,開始出去找事兒做。
月牙兒的情狀(原文):那個月牙兒清亮而溫柔把一些軟光輕輕送到柳枝上;月的微光把這圈雪照成一半白亮,顯出難以想到的純凈,這個月牙兒是希望的開始。
感情:“我”開始與自己的命運和解,想探求一種新的生活,月牙兒代表希望。
內涵8
看見月牙兒的時機:“我”與青年“戀愛”。
月牙兒的情狀(原文):他的笑唇在我的臉上,從他的頭發上我看著那也在微笑的月牙兒。
感情:月牙兒被雪掩住,也是自己失去獨立人格,變成他人附屬的意思。
內涵9
看見月牙兒的時機:青年的妻子找到了“我”,懇求“我”離開他。
月牙兒的情狀(原文):一點云便能把月牙兒遮住。
感情:月牙兒象征著被所謂甜蜜粉飾著的實為交易的愛情,是脆弱的,也象征著我的命運再次陷入黑暗。
內涵10
看見月牙兒的時機:“我”去當了女招待。
月牙兒的情狀(原文):我的希望是初月的光,一會兒就要消失。
感情:“我”再次意識到女性的命運和結局,女性不僅僅是男人的玩物,更上趕著當男人的玩物,而這卻是較好的局面,畢竟自食其力。
內涵11
看見月牙兒的時機:媽媽來投奔“我”,媽媽還愛“我”,但并不勸我不做暗娼。媽媽不擇手段地要錢。
月牙兒的情狀(原文):(月牙兒沒有出現)“女子的職業是世襲的,是專門的!”“我已愛不了自己,我愛別人干什么呢?
感情:“我”變得渾渾噩噩,成為了第二個媽媽,行尸走肉地活著。
內涵12
看見月牙兒的時機:“我”被關進感化院。
月牙兒的情狀(原文):我又看見了我的好朋友,月牙兒!多久沒見著它了。“它使人堅信人類沒有起色”。
感情:“我”已經完全絕望,但在絕望的盡頭我審視自己,看到了月牙兒。
通過梳理我們發現,“月牙兒”這個意象是復雜的,它不是一個突出主人公某方面特質的意象。它本身的情感是復雜的,與主人公之間也存在著多方面的對應關系。
首先,月牙所代表的情感有兩方面的偏向:冷和暖。
一方面,月牙兒是冷的,光是微弱的,是能夠被云輕易遮住的。在“我”面臨人生變故的時候,總是能看到月牙兒。爸爸去世、媽媽養家糊口時、新爸離開時,在略感幸福的時候,住進新爸家的時候,反而會忽視月牙兒。月牙兒就象征著“我”和“我”悲苦的命運:月牙兒是細瘦的,幸福是脆弱的;月牙兒的光是冷的,象征著命運悲涼的底色。
另一方面,月牙兒也是暖的,是希望的象征。在“我”絕望的時候,月牙兒會消失:“我”與媽媽分道揚鑣時、“我”與青年的“戀愛”幻滅時、我看透了世界的弱肉強食當了女招待當了暗娼時,月牙兒都沒有出現。雖然月牙兒脆弱,但是,與另一個脆弱的自己相對時,感到凄苦的同時也會得到一點慰藉,只有心灰意冷、毫無依靠時,才是月牙兒消失之時。
其次,月牙兒體現了一種命運的循環和必然。在《駱駝祥子》中,作者通過三起三落來表現個人主義的抗爭是無法擺脫命運的漩渦,在《月牙兒》當中,也通過兩代人命運的重疊來體現女性在舊時代的悲劇命運。月相本就有周期循環的特征,月牙兒的形態又是相對穩定的,由此來表現“我的媽媽是我的影子”——身份世襲宿命論[2]。“女子的職業是世襲的,是專門的!”[3]當主人公喊出這句話時,命運的軌跡悄然既定。
第三,月牙兒不僅僅是人物命運的象征,同樣也是人格的象征。在文章的前后有著鮮明的對比,之前,面臨人生變故時,“我”總喜歡看看月牙兒,這是一種既落寞又心懷希望的看,然而當“我”成為女招待、淪為暗娼后,月牙兒就再也沒有出現。
在這個變化中,“我”的人生觀發生了三方面的改變:其一,是對命運的認識。我明白了“肚子餓是最大的真理”[4],理解了媽媽的選擇,接受了成為第二個媽媽的命運;其二,是對男女關系的認識。當我與青年所謂的“戀愛”幻滅后,“我”明白了女人不過是男人的玩物,而男女之間的本質不過是交易關系,所謂愛情不過是“他是利用我的無知,暢快自己。”[5]男女關系不過是物物交換,女子付出自由和肉體,換取寄居,因此,曾經“我”所視若珍寶的自尊、自食其力,不過是笑話。文中說“我上了市”[6],在那個時代,只有女人真正自愿接受被物化成商品,女人才能換取自己的價值。其三,是對整個社會的認識。在三十年代小說中,娼妓話題的敘事文學得到了發展,有學者研究,當時南京政府視娼妓問題僅為道德問題,采用簡單易行的“取締”辦法,造成“禁者自禁,娼者自娼”的局面,多數以“易幟主義”變成私娼。面對禁娼弊端,政府曾考慮“馳禁”辦法,但遭到女權運動之強烈抵制。而禁娼運動也促進了20世紀30年代“娼妓敘事”的相對繁榮。[7]在文章的末尾,“我”被關進了感化院,實際就是被下了獄。女子在這里唯一的出路不是被“感化”,而是被賤賣,視賤賣為拯救女性。“我”按照我唯一能走的路變成了暗娼,然而,“我”卻被社會當成了渣滓,被政客當成了偽造政績的工具,被男人當成了物品。因此,末尾說月牙兒“使人堅信人類沒有起色”,這是對整個社會的絕望,代表著一種整體性否定。在這三方面改變的過程中,月牙兒不見了,曾經“我”自尊、獨立的人格不見了,“我”淪為行尸走肉,再無生與死的意識。
三.“月牙兒”式人物的意義
我們之所以會感覺“月牙兒”這個概念式人物具有抽象性,正是因為這個概念所包含的意象是復雜的。它符合言——象——意的傳統,語言是有所局限的,當某種情感無法直接表達時,我們通常用意象為中介,使人能夠體會言外之意,同樣,當某個人物具有復雜性、缺乏具體形象、偏向抽象時,我們也可以使用某一概念,來指代這一人物,而這一概念可以被無盡闡釋。就像“月牙兒”包蘊了那個時代千千萬萬處在社會最底層的女性的命運,包蘊著她們與命運和社會的抗爭,對命運和社會的絕望。我想這便是概念式人物產生的原因,它使人物擁有更加強大的生命力,賦予了人物一種雋永悠長的魅力。
注 釋
[1]王春林;王曉俞.《月牙兒》:女性敘事話語與中國文人心態的曲折表達[J].文藝理論研究,1996,(03):60-66.
[2]范亦毫.論《月牙兒》及其在老舍創作史中的地位[J].文學評論,1984,(04):45-53.
[3]老舍.月牙兒[J].國聞周報,1935,(14):4
[4]老舍.月牙兒[J].國聞周報,1935,(14):1
[5]老舍.月牙兒[J].國聞周報,1935,(14):1
[6]老舍.月牙兒[J].國聞周報,1935,(14):1.
[7]王燁;尹琴.廢娼運動與“娼妓敘事”的現實諷喻——淺議20世紀30年代有關“娼妓”話題的文學敘事[J].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06):20-27.
(作者單位:內蒙古大學歷史與旅游文化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