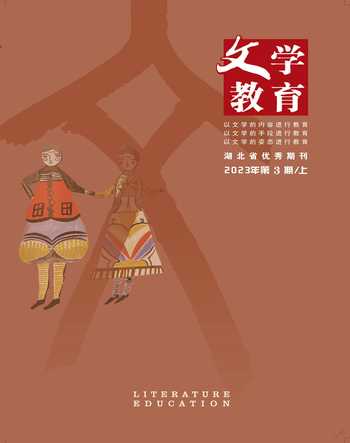蕭紅小說中的斷裂與并置敘事
王佳偉 夏雨
內容摘要:作為文壇洛神,蕭紅憑借其獨特的文體風格和文學理想,在文學史上獨樹一幟。蕭紅的小說打破了傳統的敘事模式,在文本中時常會出現明顯的斷裂和并置,通過鮮明的敘事技巧展現了東北黑土地農民的真實生存狀態,這種特殊的敘事功能也導致了其與傳統的文學批評相悖的審美風格和誤讀。本文試通過蕭紅《生死場》與《呼蘭河傳》的部分內容,來分析蕭紅文學創作中運用的斷裂和并置的敘事功能,進而探討蕭紅獨特的敘事風格和內在情感糾葛,從而更好地展示出蕭紅小說悖于傳統和審美范疇的異質性,分析作者暗含于文學中的對于傳統與現代、都市與鄉村、啟蒙與民間的內在思考,以及形而上的生命體驗。
關鍵詞:蕭紅小說 敘事功能 斷裂 并置 反思
在傳統小說創作中,時間與空間是一部小說的主要構成因素。俄羅斯文藝理論家巴赫金提出了“時空體”這一概念,其特征表現為“時間在這里濃縮、凝聚,變成藝術上可見的東西;空間則趨向緊張,被卷入時間、情節、歷史的運動之中。時間的標志要展現在空間里,而空間則要通過時間來衡量。”[1]傳統小說采取的是“縱剖式”的敘述結構。而蕭紅的異質性則在于她突破了傳統文學視角和審美風格的限制,這與她的文學理想和獨特的人生經歷,是分不開的。
蕭紅在回望自己的短暫一生時,故鄉傾注了她畢生的情感。出身于東北小城的蕭紅,自身帶有鮮明的鄉土文化烙印,無論是《生死場》還是《呼蘭河傳》,對于叛逃到都市的蕭紅來說都是對故鄉的一次回望與反思。童年的后花園和祖父,都是蕭紅不斷重溫、不斷追尋的精神之鄉。可相比于短暫的流露出對故鄉的溫情,蕭紅大部分情況下都在細數故鄉的愚昧和麻木,字里行間流露出的,都是對故鄉的批判和憤懣之情。
“歸鄉者終未歸鄉。”她出身于東北小城,卻向往都市,一生都未能與鄉土取得和解,矛盾與糾葛使她在文章中一面對故鄉報以真摯赤誠的愛,一面卻流露出激烈地仇視與痛恨,陰暗、絕望的筆觸下埋藏的是無法釋懷的舊痛。這不僅僅是源于故鄉農村無可救藥的蒙昧本身,更應歸結到支撐蕭紅本人文學理想的都市目光,以及她在都市漂泊中遭受的苦難與絕望上。也就是說,伴隨著蕭紅歸鄉悲涼的背后,既有蕭紅終生都未能淡化的對東北黑土地的舊痛,也必然包含著她不惜一切奔向都市后所新增的創傷。因此,蕭紅小說創作中出現的對傳統敘事的顛覆,其審美風格的異質性和情感的叛逆性,都與她本人的獨特人生經歷是息息相關的。
一.小說中的斷裂功能
(一)文本時間的斷裂
學者摩羅認為《生死場》是一個“斷裂的文本”。[2]在小說里,敘事的時間長度跨越了十年,但蕭紅卻只用了六個季節的更替,用不到一年半的時間進行了概括,這就是一種時間的斷裂。蕭紅在開篇九章運用了純客觀敘事的手法,不動聲色地展示著生長在這片土地上的農人的精神麻木和心靈的死寂。小說開頭向我們展示了一幅夏季農人收獲忙碌的場景,他們為了生計不斷奔波,卻因此而陷入了循環往復的掙扎之中。夏去秋來,小說繼而著力續寫了深秋意象,自然界顯示出了它周期性的衰亡,遲暮的日落、蕭瑟的禿樹,農人們也因此被置于凄涼和蕭條之境。秋去冬來,雪白的天地間仿佛都沉寂了下來,也預示著農民們被籠罩在死亡的陰影之下,標志著生命力的喪失。仔細看這部小說,蕭紅是有時間安排的,但彼此之間卻不構成情節和人物上的繼承和聯系,“全篇顯得是一些散漫的素描,感不到向著中心的發展。”[3]因此這里的時間線索實際上更像一根線,串起了這一個個場景。
另一部代表作《呼蘭河傳》,小說以故鄉呼蘭河城為描寫和回憶的對象,分為七章。“在一定范圍內,事故中的時間如果在向度上屬于‘過去便常常會賦予文本一種感傷的色彩。”[4]蕭紅用悲涼的語言,將呼蘭河城置于不同的季節時令之下,展開了全景式的描寫。“春夏秋冬,一年四季來回循環地走,那是自古也就這樣的了。風霜雨雪,受得住的就過去了,受不住的,就尋求著自然的結果。那自然的結果不大好,把一個人默默地一聲不響地就拉著離開了這人間的世界了。”[5]在蕭紅的筆下,故鄉是沒有時間概念的,只有一年四季的輪回,像一幅幅日常生活的畫卷,被并置地排列出來。這些故事雖然發生在“我”的童年,但具體的時間卻是模糊不清的,更像是“我”的一個個童年記憶的碎片,抓住了其中的幾塊進行了延展。這種文本的時間斷裂,是小說的一大特色。
(二)生命人性的斷裂
過去-現在-未來本是傳統小說中常用常見的時間線索,但在《生死場》中,蕭紅切掉了過去和未來。“十年前村中的山,山下的小河,而今依舊似十年前,河水靜靜地在流,山坡隨著季節而更換衣裳;大片的村莊生死輪回著和十年前一樣。”[6]在蕭紅筆下,時間是相對靜止的,是一個循環軌道,它不回憶過去,也不預示未來,只作為現實的無限重復。她關注著人的普遍性的封建思想和精神愚昧,從而產生了殘忍而無奈的判斷: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老一輩農民,已經陷入了忙著生,忙著死的生存困境。他們深入泥淖,無力改變困境、走向遠方,從而告別過去。他們更沒有對幸福的憧憬,只能在年復一年的混沌中茫然地徘徊,看不到未來,從而重復著無謂的循環。我把這稱為蕭紅小說中第二個“時間斷裂”。
在《呼蘭河傳》中,時間的發展與個體生命的成長形成了強烈的反差,廣義上的時間是不斷前進、不斷發展的,但生長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們,他們的生命卻逐漸喪失了前進的心力,只是不斷在生命的圓軌上循環往復,重復著生命的悲劇。蕭紅用仇恨憤怒的眼睛,掃視著民間發生的一幕幕喪失人性的情境:老板娘因為迷信風水,殘忍地驅趕了馮歪嘴一家三口。王大姐未婚生子,面對著人們的非議、譴責和生育的痛苦,最后不幸的死去。看客們圍觀小團圓媳婦,興奮地看著她的嚎叫和恐懼,痛苦和死亡,享受著別人的痛苦對自己麻木靈魂的刺激。在這些場景之上,蕭紅抽著煙,坐在病床上,神色滿是憤怒與悲涼:“滿天星光,滿屋月亮,人生何如,為什么這么悲涼。”每個人的不幸都在不斷地發生,又被黑土地所掩埋,不斷地被遺忘。這是生命層次上的斷裂,是人性的斷裂。
生命是不斷向前、不斷消耗的,可人在生命不斷被壓縮、不斷被剝奪的情況下,會本能的為了繼續生存而去反抗。蕭紅筆下的這群被歷史和現實所拋棄、淡忘的農民,麻木愚昧地掙扎生存著,可在文章的后半部分,他們也迎來了新生的希望;長期以來被壓迫、被禁錮的人性,在無法墮落于更黑暗的情況下迎來了反彈。日本人來了,“愛國軍”從門前走過,有些人自發地跟了上去,可他們并不完全是因為愛國,也沒有心思去愛國。戰爭侵略并不是在瞬間讓這些人升起了強烈的愛國情感和守衛鄉土的信念,而是因為日本人來了,他們已經很糟糕的生活變得更加糟糕,他們活不下去了,于是他們站起來去反抗,去尋找生存下去的機會。蕭紅并沒有刻意去拔高什么,她只是在不斷強化這些人的生存信念,肯定他們的生存法則,從而在希望即將消亡的時候,讓時間有了打破循環的契機,讓生命走向光明未來的機會。這與蕭紅的寫作風格是一致的,盡管她的文字充滿了哀婉凄涼之情,卻又內含著明麗和英武之氣,有著強烈的反抗精神。
二.小說中的并置功能
(一)生與死的空間并置
德國文藝理論家萊辛說:“空間屬于畫家的領域。”[7]蕭紅正是一位出色的畫家,她受弗蘭克的空間敘事學的影響,通過空間并置的手法展現了故鄉黑土地的全景,表現了農民們在“生”與“死”中所表現出的生存的掙扎和生命的糾葛之上。通過空間并置,用一幅幅散漫卻觸目驚心的畫面,將人物、景色皆投入其中,呈現出了東北故鄉每個人的生存狀態,更能透視人性,體現人的生存悲劇。生死場的十年變遷,也是通過空間的對比并置呈現的,這些畫面都依附于一個囊括一切場景的空間中,每個畫面互相組合,使小說的整體框架得以建構。她通過時間斷裂的手法,將人們置于時間的圓軌之內,表現其蒙昧的靈魂和停滯的生命力。他們就像牲畜一樣地生存著,稀里糊涂的繁殖,然后等待自然的死亡。
基于此,蕭紅采取了“丑化”的小說筆法。在她筆下,少有那些水靈的人物,也極少精致漂亮的事情,反而到處充斥著一些庸碌、惡俗和悲慘。如《麥場》里的麻面婆,“眼睛大得那樣可怕,比起牛的眼睛來更大”;“那樣,麻面婆是一只母熊了,母熊帶著草類進洞”。金枝與愛人在菜圃上偷情后被發現,被鄰里鄉親罵為不要臉、不守婦道。王婆麻木冷漠地講述著自己孩子的死:“我把她丟到草堆上,血盡是向草堆上流呀!……我也親眼看過小狗被車輪軋死,我什么都看過。”為了加深讀者與她的情感共鳴,她甚至刻意對不夠“丑”的人加以丑化,讓她們代表這片土地上苦苦掙扎的眾生,象征著被歷史和現實所拋棄的生命。在那種躁動的、讓靈魂永遠無法安寧的世界,她們展現出的一切可悲可恨,所有的掙扎與迷茫,變得深入骨髓卻無關緊要。此時的蕭紅,是作為一名文學家,一名叛逃出鄉土的女性而存在。她將目光凝聚在這些橫掃后無法輕易察覺到的情狀,引導著人們將目光聚焦在這些丑和惡之上,一個畫面接著一個畫面,情感沖擊強烈,令人不由心生悲憫之情。繼承了魯迅“戰士”思想的蕭紅,傾注了自己無數的悲痛與憤恨,來嘲諷這人間悲苦。
(二)啟蒙與民間的視角并置
對啟蒙主義者而言,他們常聚焦于以中國民間為主的封建宗法制文化和倫理道德,將之視為愚昧和落后的象征,并施以啟蒙的眼光。這種自上而下的俯瞰,飽含悲憫與批判之情的態度是其基本特征。而與之相對應的,以民間視角為主的作家大多是來自鄉土社會,他們的生命之基、文化之根都來源于故鄉,因此被賦予了不同的文化視野。這一類的作家,大多出身于民間底層,他們將目光穿過了掙扎在生存與死亡的人們所展現出的愚昧和荒誕,而更多關注于在極其閉塞、腐朽、嚴苛的環境下,中國的傳統民間社會是如何存活的,并進行自我反思:千百年來始終維系這種生存力量的源泉在哪里?這種看似粗糙、惡劣的野性,是否有其歷史必然性與合理性?
在《生死場》中,蕭紅用典型的啟蒙主義式的語言來剖析家鄉的頑疾,繼承了左翼文學的批判性。金枝懷孕時痛苦地摘下柿子進行發泄,經歷過生育痛苦的母親卻無法做到感同身受,反而生氣地踢了她一腳,讓蕭紅不由生出感慨:“農家無論是菜棵,或是一株茅草也要超過人的價值。”可有別于啟蒙文學的是,蕭紅放棄了悲憫。蕭紅寫了一群不像人的人,人性的野蠻與殘酷仿佛與生俱來,可她并沒有因此否定這些人的存在意義和權利,而是站在與他們平等的立場上,去認可他們的生命力和作為人的尊嚴。蕭紅用十分嚴肅的態度描寫了麻面婆在柴堆里找羊的場面,盡管麻面婆愚蠢笨拙的還不如一只羊,可她一直在努力做好這件事,因為她也渴望得到別人的認同和稱贊,她也想驕傲的被別人注視,去實現自己作為人的價值。還有趙三、二里半等人,他們不愿當亡國奴,他們打聽“人民革命軍”在哪,他們要把國旗插在自己的墳頂……這些猥瑣低賤的人,也有作為男人頂天立地的豪氣與尊嚴。由此可見,蕭紅是站在了與啟蒙者完全不同的立場上來觀察故鄉的。從故鄉叛逃又回望故鄉的蕭紅,她自身帶有的傳統性和民間性,使她將情感毫無保留地投入到這片土地,不由自主的對底層人民產生認同感,導致她終究無法脫離故鄉,完全冷眼旁觀這世間悲苦。
三.反思
然而,一心回望鄉土的蕭紅,在追逐生命的歷程中,似乎也無法將都市作為其最終的歸宿。蕭紅的一生,是從故鄉到都市的不斷逃離、不斷漂泊中度過的,這使得她究其一生都在不斷追尋的啟蒙與文明,也最終成為了終生未完成的夢。由此我們可以看出,蕭紅彌漫于字里行間中的創痛和憤懣,并不僅是故鄉帶給她的,更是其一生流離漂泊的寫照。正是這種鄉土傳統與都市現實之間無法調和的矛盾,以及蕭紅身處二者之間卻永遠無法找尋歸宿的悲劇,導致了其所展示的、處于矛盾和割裂中的都市與鄉土,始終處于一種被分離和遮蔽的狀態:故鄉無根可尋,都市未曾反思。
然而,盡管蕭紅的都市經歷只帶給了她無盡的痛苦與悲劇,致使她所認同的生命追求出現了偏差,但毫無疑問,相比于東北黑土地蒙昧的生死場和呼蘭河,冷漠的都市依然還是成為了她苦苦掙扎的寄托,這里包容著她生命的信仰。而不可避免的,蕭紅在這段追夢過程中所受到的打擊與痛苦,也將作為歷時性的存在,一種刻骨銘心的記憶成為其生命歷程的寫照,一種獨屬于她個人的生命體驗,從而推動了其文學創作風格的大成。
蕭紅文學敘事的獨特性,通過斷裂與并置的敘事功能使得小說最終呈現出一種開放式的結構,它使作者能夠以自如的筆觸,摒棄線索、情節、結構的束縛,把對民間底層人性的窺視、地域文化的自省、寫作技巧的創新同時呈現出來,從而形成了完整的文學世界。《生死場》和《呼蘭河傳》作為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體現了蕭紅鮮明的創作個性。它真實地再現了特殊時代的風土人情和民族心理,也呼應了那個極度渴望前途與光明的時代要求。貫穿于小說中的矛盾情感,對于傳統與現代、都市與鄉村、啟蒙與民間的內在思考,以及形而上的生命體驗,使得她的小說總能給人一種震撼感,一種錯落有致、參差的美。
參考文獻
[1]巴赫金.小說理論[M].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274-275.
[2]摩羅.《生死場》的文本斷裂及蕭紅的文學貢獻[J].社會科學論壇(石家莊),2003(10):41.
[3]胡風.生死場讀后記[A].蕭紅全集[C].哈爾濱.哈爾濱出版社,1991.147.
[4]徐岱.小說敘事學[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253-254.
[5]蕭紅.呼蘭河傳[M].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79.2
[6]蕭紅.生死場[A].蕭紅文集[C].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5
[7]萊辛.拉奧孔[M].朱光潛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18.
(作者單位:伊犁師范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學院。夏雨為本文通訊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