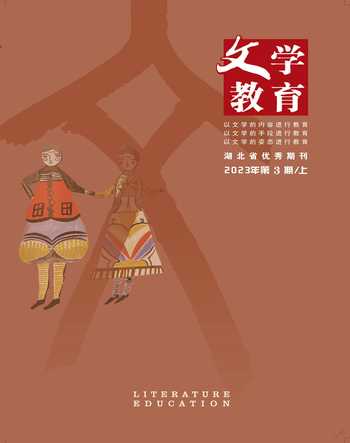艾略特《荒原》的美學解讀
吳天威
內容摘要:《荒原》開啟了英語詩歌新方向,確立了艾略特作為英美現代派詩歌一代大師的地位。《荒原》語言創意與思想深度深刻影響現代西方文學,詩中充滿宗教色彩、死亡意象、怪誕與丑、反傳統、反諷與無奈、非個人、非理性特點的詩歌表達獨具美學符號。
關鍵詞:艾略特 《荒原》 美學 詩歌
《荒原》是艾略特創作中期重要代表作,在西方現代詩歌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荒原》的題辭開頭就引用了希臘神話西比爾的典故。寫到,“因為我在古米親眼看見西比爾吊在籠子里。孩子們問她:你要什么,西比爾?她回答道:我要死。”[1]它奠定了整首長詩的基調,點明“死亡與救贖”的主導意象貫穿全詩。在詩人筆下,通過“尋找圣杯”的傳說故事進行立意,表現出輕賤猥瑣的“人間地獄”,同時不停地呈現了當代西方城市中墮落和行跡齷齪的醉生夢死的人物形象。毫不客氣的說,這就是一個荒謬的世界,沒有崇拜與次序,僅有的是生活的空虛和精神的絕望。
《荒原》被譽為西方現代文學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作品,其寫作手法營造出一種撲朔迷離的美感;它兼具的美學功能傳達出的人類終極關懷,還原了一戰后的歐洲生活現狀,寫出20世紀歐美乃至全社會的本質。艾略特說過,當代詩歌之所以變得越來越艱澀,其根源是由于受到了復雜多變的時代與社會的限制。比如在《荒原》的結構上不難看出,交叉點較多,頭緒繁雜,是多層面對社會現狀的揭露、還原與表達。多數研究者從詩原文上理解的同時,也對各環節的交叉點進行了不同程度的整理和思考。
筆者認為,《荒原》在詩的結構上錯綜復雜,恰是詩人具有高深的詩技,詩歌寫作的嚴謹,對所反映社會頹廢現狀的勇敢負責,這本身也是一種美的態度。而從詩的結構和內容上看,《荒原》不僅表達的是對一戰后歐洲精神生活缺失現狀的反抗。當然,本長詩的之所以能在詩歌史長河中留下來,經歷各種不同的評論和聲音的錘煉,經久不衰的確立了自身的重要地位。它的成功之處是多維度的。首先體現在它結構下藝術特征的獨到與創新,古今神話傳奇穿插,宗教救贖的深厚信仰;其次是死亡意象的抽象復雜和深刻,怪誕與丑的表現形式和審美取向;最后是它反傳統的表達方式和詩歌中非個人化情感消解;它們形成了艾略特詩歌獨具美學符號的風格及特色。
一.《荒原》呈現的美學特征
1.《荒原》的結構和意象系統
西方較為著名的人類學家杰西·魏士登的《從祭儀到神話》和人類學家、宗教史學家弗雷澤的《金枝》為《荒原》提供了象征結構的整體框架和意象語言。在弗雷澤筆下,他把繁殖神基本上人格化了,神靈富有戲劇性的經歷會影響萬物的生長,比如四季不定性的變化及植物的盛衰;而且神的健康指數也會直接影響到人類季節的豐收及大地的景象。比如,神一旦復活,荒原就開始復回生機,大地也將茂盛起來,反之冬季或旱季瞬時到來,大地將是荒蕪。魏士登有關尋找圣杯的神話傳說也與《荒原》息息相關。《荒原》在現代詩歌題材的表面結構下,隱含著與經典的尋找圣杯平行發展對應的神話結構。詩人以尋找圣杯的傳說為契機,使得典故框架與死亡意象碎連成一個整體,形成一個外在的結構脈絡。而整個詩篇的內在層面是隱喻式的勾畫出一個毫無生氣的“死亡、地獄式”意象,構成《荒原》一詩的意象系統。
《荒原》分為5章。第1章“死亡葬儀”的標題出自英國教會出葬儀式,點明了死亡氣息貫穿整個章節。如“四月是最殘忍的一個月”,便采用時間記憶與欲望煎熬了出葬的人群,呈現了貴族瑪麗懷念過去的靜美歲月而今卻是遙不可及。四月中,冬天昏暗的黃色云霧中,倫敦橋上流過的人們,死亡早就在這荒涼的環境里不斷地毀滅了他們。“它發芽了嗎?/今年會開花嗎?[2]”最后幾句一連串的提出疑問,表達了對精神復活的渴求。第2章 “對弈”引征莎士比亞、維吉爾、彌爾頓和奧維德的作品,把過去的昌盛生活與當前生活頹廢形成一個對照。借此分解出西歐現代社會中人們濫情聲色、如同僵尸的悲哀境地。它分為兩個場景。前一個場景一直在不斷地叩問“風在干什么?我該做些什么?”這是個人人生意義喪失的表現,后一個場景尾行借用《哈姆萊特》中奧菲利亞在告別生活時所說的瘋話,映射現代女性的不瘋猶瘋的頹廢生活,兩位不同時代、不同地位的女性代表不同階層社會普遍的墮落風氣,雖生猶死。第3章開頭便描寫了泰晤士運河的古昔,生活在倫敦的人們不同程度的頹廢無聊生活,“仙女們已經走了。”河上不再有四處飄蕩的空瓶子、面包薄紙、綢手帕、紙皮匣子、香煙頭。在這里留下的只是所有一切都走了的空無景象。再加上我在萊芒湖畔的飲泣,白骨,老鼠,冬夜,煤氣廠,沉舟和父親的死,唯有孩子們在教堂里的歌聲能稀釋一切。“他立即進攻;/探險的雙手沒遇到阻礙”[3]。女打字員和猥瑣男青年有欲無愛的交合。在這樣的精神荒原面前,唯有宗教能解救這卑微不堪的生活,點化迷惑的人生,拋棄世俗雜念,過上有意義的圣潔的生活。 “燒啊燒啊燒啊燒啊……”,說明火在此具有了兩種不同的含義:即是情欲之火、也是讓人再生的凈化之火。這暗示著人類若是要解救精神的缺失,務必依靠佛陀的凈火的冶煉。
“水里的死亡”,“水”也指殘酷、泛濫的情欲,第4章中女相士“紙牌算命”得出的預言腓尼基人死亡的命運在這里得到了應驗。弗萊巴斯死了已兩星期,他的骨被海的潮流剔凈,又在暗指欲望和金錢的漩渦中再次且重復沉下去,人們在茫茫海洋中依然會縱情聲色下去,人們的死是必然結果,即現代人的死亡無法避免。第5章表達了吠陀經里的說教,同時采用三個“客觀對應物”來描繪荒原的部分景象。首先山滿口吐不出一滴水的因由是耶穌的死去。“在紫色暮色中開裂、/重建又爆炸/傾塌著的城樓”[4],東歐和俄國革命,戰爭帶給城市深重的破壞。人們在一陣陣絕望、無奈和恐慌中期盼著烏黑的云降下雨來。因為荒原上長期缺乏著水,人們對水的尋找因極其艱難而變得痛苦和困惑。這里的水被賦予了再生的含義。最后漁夫在岸上垂釣的地方,其背后皆是一整片干旱的、荒蕪的大地,尋找圣杯的武士走進的教堂也是空的。荒原能否恢復生機?人能否獲得拯救?一切都未知。“我們給了些什么?/我的朋友,熱血震動著我的心……/”[5]接下來詩歌的尾聲,是在賦予宗教色彩的雷霆“同情,克制,平安”的告誡聲中走向結束,但這告誡并不是絕對肯定。足見詩人并沒有對宗教寄予著絕對的、全部的希望,而是在結尾中保持了對“雷霆的話”一份沉甸甸的懷疑和憂慮。
2.《荒原》的藝術特征
本長詩的藝術特征首先表現在對蒙太奇剪接手法和拼貼技法運用自如上,詩人把古今神話傳奇、宗教典故原本并不相關的片段或意象,神奇地聯接成一體,可謂穿越時間、空間的界限,把古今熔進一爐,形成了《荒原》的整體意象。其次是大量采用豐富復雜的象征,比如貴族瑪麗、女相士及荒唐的麗兒與女伴等的經歷寫照代表出現實而荒誕的生活。接著詩歌中的語言復雜多變,深奧難解,對現實西歐現狀有著深刻、透徹的解剖。最后是《荒原》每個章節片段死亡意象新奇怪誕,水與火的交融,死去與救贖,充滿了宗教色彩,達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效果。讓人深省,救贖意義深遠。
(1)救贖意識的宗教色彩
《荒原》這部作品以圣杯傳說為框架,即為了給漁王治病騎士們走向尋找圣杯的漫長征途,這樣的框架結構表現了《荒原》濃厚的宗教色彩。同時,構成本詩原始宗教色彩的證據之一的還有受弗雷澤“金枝”對繁殖神崇拜故事的影響。此外,《荒原》中印度教、佛教因素非常明顯,詩歌中每章都帶著極其強烈的宗教式暗示。比如第1章中女相士預言人們死亡的命運、第2章“火”最后的燃燒等,引用了宗教典籍中的某一個只言片語,要么以象征、暗示等手法來間接的闡述詩人以宗教救贖現實荒原的思想。類似的手法比比皆是,例如詩句片段:“一堆破爛的偶像,承受著太陽的鞭打”、“你早起的影子,在你后面邁步”、“這些孩子們的聲音,在教堂里歌唱!”等等。詩人力圖用宗教復興來挽救西方文明,其社會理想便是宗教救世。
艾略特信仰英國天主教,是一位虔誠的天主教徒,在政治上是保皇派,在文學上是古典主義者。《荒原》全篇主要以“死亡”為主題,詩中彌散著死亡的煙霧,第1章節描寫到的,“并無實體的城”的景象,以及暮色下的可愛的泰晤士,人們在那里依然重復著精神已死的艱難困頓的生活。接著,艾略特運用神話傳說死而復生的故事間接鑲嵌入詩句中加以列舉。“我沒想到死亡毀壞了這許多人。”倫敦這座城市人們在墮落中沉淪下去,無可救藥的生存狀態,最后在城市上空煙霧的背后,作者點明了一個明確的方向,那就是讓死的死去,我們才有希望重生。“腓尼基人弗萊巴斯,死了已兩星期,/回顧一下弗萊巴斯,他曾經是和你一樣漂亮、高大的——(水里的死亡)。[6]”再轉到第5章,“恒河水位下降了,那些疲軟的葉子/在等著雨來”[7],在死亡的氛圍中,水又化成了大地的拯救者,人們在整片焦急中期盼著水的到來。《荒原》一直把重建人們的信仰為主題,在救贖意識上強調基督教的重要性。人類所處的精神荒原狀態缺少的是生命之水,缺少心靈的信仰,人類只有在古老的神話和文明中才能尋找到智慧和愛的精神。
艾略特在《荒原》一詩中,首先是天主教、佛教、希臘神話、東方生殖崇拜、漁王神話等等合起來構成了艾略特的詩歌隱喻。如在第3章中最后一段的“主啊你把我救拔出來”,是對前面無愛性行為的荒誕及生活中沒有生氣的死亡燃燒的呼喚拯救。艾略特在第3章節的召喚及第5章節雷霆的勸誡中極力地表達了這樣一個問題,認為歐洲現代社會歷經了一戰的洗禮后,進入了一場喪失信仰、缺乏理性、沒有秩序的精神文化危機之中,人們只有重建基督教信仰維度才能扭轉這一危機或加以拯救。
(2)死亡意象和象征主義
艾略特在詩歌中的宗教色彩一系列主張,正如之前提及到的,是由死亡意象、象征、暗示等手法來完成。這在《荒原》詩的語言中,能夠進一步找到。比如《荒原》這個現代主義詩歌的里程碑之作,在標題上也存在著深刻的暗喻。艾略特在《荒原》遠古神話的框架結構內形象地構造了現代的荒原和荒原人,“荒原”即是現代歐洲社會的象征,“荒原人”是現代歐洲人的象征。(我,帖瑞西士,都早就忍受過了,……/他摸著去路,發現樓梯上沒有燈……/(“火誡”)[8]。詩人選取了病態的、卑微的意象,詩歌中基本上不間斷地充斥著死亡與孤獨、頹廢野蠻的氣氛,整個就是干涸的世界。這些意象揭露了生活在現代歐洲城市的人們的精神荒原感、虛無和消失。
接著,艾略特對象征主義的發揚創新表現在象征意義不再局限于單個的意象體,而是由一組意象重盛或并置創造出一個整體,該整體所暗示的象征意義正是人類共通的經驗,一致的情感。如,詩歌中的“荒野”、“水”、“火”、神話原型以及人的軀體動作,這一系列意象都被賦予了象征意義。詩中大量運用了時空交錯、順序倒置等手法,如第1章女相士預言了人們的命運,在第4章“水里的死亡”中得到了驗證。第1章倫敦“一群人魚貫地流過倫敦橋,人是那么多,”的死亡景象,與第3章“火誡”對泰晤士河及萊芒湖畔周圍人們的死氣沉沉的生活相照應。這種對應把神話人物與現實人物交織在了一起,時間上使昨天、今天、明天相并存,泰晤士河、萊茵河等景象相重疊,其現代性顯示無疑。
此外《荒原》既繼承了玄學派詩歌對選取意象主題的求新立異,又賦予意象以深層次的象征意義。在《荒原》中,比如:“另外一個把眼睛藏在翅膀背后/使七枝光燭臺的火焰加高一倍”[9],玄學派詩歌善用的比喻修辭已經上升為象征,將比喻蘊含在象征之中,又如:荒原就象征著西方現代人的精神荒蕪。
(3)怪誕與丑的審美取向
《荒原》死亡意象中,也不乏藝術的怪誕與丑之美。如:“荒地上長著丁香”、“你頭發濕漉”、“只有老鼠的腳在那踢來踢去”、“你是活的還是死的?”“凝視的人像探出身來”等詩句勾畫的場景都是沮喪的、又丑又怪誕。當然,藝術的怪涎美作為審美對象在文學藝術史上的地位久久不能被正式予以承認,其美的形態難以歸人美學的正道,但艾略特則大膽創新,把這一手法貫穿于《荒原》全詩之中,來作為其詩歌藝術的間離、諷刺、荒誕和夢幻手段,發揮其怪誕的審美功能。《荒原》在構思、場景、人物、結構等方面大做文章,使該詩處在表面上互不相干而內部則緊密相連的各種因素的沖突中,營造出一種強烈的、沖擊力十足的非正常表面現象,給讀者以感官刺激或情感的震動,進而產生審美效應的審美價值。
在第2章“對弈”中,“老鼠窩里”的偷情是一處特別怪誕場景,作者把這一骯臟的場所安排成偷情男女交合的地方,表達了詩人的倫理審美觀念,用這一怪誕手法完成了藝術形式美向倫理審美的過渡。總之,這種“不規則美”所形成的“非對稱性”的哲學思路,從不同的側面服務于全詩的主題,其表現形式多樣,審美功能各異。古典藝術的“意味”是比較和諧、嚴整、它以優美的形態為主,使人感到比較愉快、舒服。當然,崇高和悲劇包含著丑,但大部分還難以擺脫古典和諧的束縛。現代藝術由古典規則的完整性走向模糊性、多義、非完整,由訴諸感情的感染走向訴諸非感念的領會,由美向丑,又可以由丑向美。
《荒原》中最能體現“以丑為美”的是對于倫敦城的景物勾勒。并無實體的城/在冬日破曉時的黃霧下,/……/在死水里垂釣。/[10]傳統詩人避而遠之的客觀事物,例如“黃霧”、“死水”、“白骨”、“老鼠”、等常常會令人感到厭惡、恐怖、絕望對于傳統詩歌做法的拒斥,使他能夠打破傳統作法。詩人在《荒原》中的這種寫法承擔了一定的社會責任,那就是試圖幫助人們更加充分、明晰地認識到自身所處困境,從而能夠在認識的基礎上噴發出活力找回拯救心靈的動力和激情。詩人在極丑抒寫中同時蘊含了對精神信仰、對真善美的渴望與追求。
(4)“反傳統”的詩歌新格局
英美詩歌史中,成績突出的詩人并不少,且不論十五世紀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就近代來講,雪萊、拜倫、惠特曼等一批又一批詩壇巨人,均有不朽的詩作。但詩人卻能夠以其特有的方式,突破了傳統意義上的詩歌美學追求,繼往開來的為現代詩歌創作開辟了一條新的道路。詩人艾略特運用各種零碎的片段表現了現代城市的支離破碎,“我用這些碎片撐住了我的廢墟。”
艾略特在《荒原》長詩中,反傳統的精神是多面的,首先表現在他詩歌創作中的對浪漫主義方法的否定。其次是他在寫作過程中不斷地通過自身體驗突破了西方自十九世紀以來長久不變而且具有非常深厚影響的傳統的浪漫主義創作手法,形成了自己的獨特寫作風格和藝術。最后艾略特尤其十分反對詩歌的直抒胸臆和語言上的華麗辭藻、堆砌,他在《荒原》的寫作上,通過了自己對詩歌史的研究和詩歌創作的實踐,形成了自己的美學符號,其中一方面表現在他對歷史傳統、宗教傳統、道德傳統,特別是文學傳統的重新界定上。
比如:樹葉留下的最后手指/……/走了,也沒有留下地址。/在萊芒湖畔我坐下來飲泣……/(“火誡”)[11]。以往的詩篇,特別是傳統的英美浪漫主義詩作,歌頌的多為自然之美,或在處理悲劇性及邪惡主題時使用意象而給讀者帶來愉悅感的作品。艾略特處理類似題材時反其道而行之,例如在“火誡”一章泰晤士河的描寫就充滿了冷色調。詩人另辟蹊徑,所描寫的痛苦沒有任何詩情畫意,近百年來建立起的詩與美、偷悅和理想的聯系被徹底打破了。
(5)“非個人化”的情感消解
《荒原》詩歌中的宗教色彩、死亡意象、反傳統與怪誕,都是肩負著反映現實社會精神敗落現狀,要拯救人們的精神信仰的潛在的責任。艾略特不僅在詩歌中的表現是非個人的,而且在詩歌中對社會情感的處理上也是非個人化的。比如在第1章“死者葬儀”開頭寫到:“四月是最殘忍的一個月,荒地上/……/枯干的球根提供少許生命。[12]”這一段詩人以“殘忍的四月”凝合了沉重的情感和思緒,讓這個讓人陌生的、非正常的自然圖景直接被指向了客觀對應物,使得讀者或詩人本身能夠客觀對應地從內心深處強烈感受到殘忍的現實環境。這里雖然沒有詩人直白的情感宣泄,但是通過詩歌中描繪殘酷的客觀對應物后,我們馬上能夠察覺出了詩人深藏的荒原景象和死亡意象,感受出詩人構造荒原圖景冷色調的語意。這種讓人意外的寫法和疼痛的陌生情景,達到一種讓廣大讀者震驚的效果,使我們能夠立刻沉入《荒原》所營造的藝術世界當中去。
在第1章“死者葬儀”的中間段開始揭示了西方文明衰退的必然趨勢,既有歷史的透視,又有現實的觀照。例如:那古舊的壁爐架上展現著一幅/……/她還在叫喚著,世界也還在追逐著,/“唧唧”唱給臟耳朵聽。/[13]詩人通過“古舊的壁爐”引進了窗外的“田野景物”。“翡綠眉”“夜鶯”“沙漠”“臟耳朵”等意象,赤裸裸反應了不正常的兩性關系,而非詩人個人的情緒寫照。詩并不是放縱感情,而是避卻感情;詩不是在表達個性,而是避卻個性。這是長詩《荒原》的重要特征。
“非個人化”特征最后在艾略特論文《傳統與個人才能》(1917)中得出結論:“一個藝術家的前進是不斷的犧牲自己,不斷的消滅自己的個性。”把個人變成歷史的載體,在《荒原》詩歌中我們看到的也是他超越個性化的人身,他避免了傳統浪漫詩歌中抒發主觀理想的熱衷,語言上消解了個性色彩,凸顯詩歌的“歷史批評”以及美學層面的藝術性,具有超越時代的美學意義。
二.《荒原》的美學意義
審美作為人把握世界的特殊方式,是人在感性與理性的統一中,按照“美的規律”來把握現實的一種自由的創造性實踐。確切地說,審美在我們的生活中無處不在,它是一種有價值活動。《荒原》的美學思想,從廣闊的現實角度上來講,首先表現在詩人崇高的社會責任感上。在人類歷史上其實比戰爭破壞更讓人心疼、更無辜、更為嚴重的是對整個文明社會的毀滅,其中包括古老建筑、文明的生活狀態等。尤其是宗教信仰的喪失,更是讓身處環境毀滅的人們在水深火熱的現實面前,所有一切都變得無處依靠,包括偉大的靈魂。這就好比荒原這種殘酷、讓人絕望的環境。而荒原最缺的水在這里實則是人們靈魂里的水。艾略特客觀冷靜地展示了一個精神絕望的、思想空虛的、黑暗與痛苦交織的、無所適從的時代,所以《荒原》長詩是不屬于一個人的,而是已經升格到反映整個現代歐洲的城市的一切頹敗,它屬于整個一戰后的世界。
二十世紀以來西方尤其是一戰以后,人們的信仰普遍的喪失了,自然資源走向匱乏和工業化、商業化不斷地改變人們的觀念、甚至慢慢扭曲了人性。人類的物質進步帶來了精神的徹底迷失,以及走向了所謂“性開放”的時代。《荒原》對這樣的文明缺失有效提出了疑問和反思,加上詩中各章節片段“死亡、地獄式”的象征意象的交錯重疊,不僅豐富了詩歌的厚度和內涵,而且使詩歌主題繁復多變。《荒原》的審美張力還表現在其詩歌含蓄凝練上,也就是在簡潔明了的詩句中蘊含著詩人深邃的哲理思想。此外,詩歌中始終帶有堅持宗教神學立場的氣息,詩人這樣似乎是力圖挽救文學的世俗化,甚至在詩中暗藏著號召人們可以通過宗教神學的框架重建文學的價值。
德國現代哲學家斯賓格勒在《西方的沒落》中有過這樣的預言:歐洲文化在現代社會中必將走向精神的荒原;艾略特《荒原》長詩,也剛好是對斯賓格勒的一次回應。偉大的詩歌在于表達人們內心真實的感受,當這種詩歌結合了對人類的終極關懷之美時,加上藝術的載體(而全非技巧)那么它會變得更加的完美。無疑,《荒原》之美也就更加的偉大。
《荒原》開創了英語詩歌的新紀元,使英語詩從舊的美學信條中解脫出來,為探尋新的藝術規律樹起一塊豐碑。詩歌同任何一種文學形式一樣,無處不在體現著詩人對美的追求,也是詩人對現代詩歌美學孜孜不倦追求的結果。瑞恰茲說:“在艾略特手里,典故是一種技巧,《荒原》在內涵上相當于一部史詩,沒有這種技巧,就得由12本著作來表達。”艾略特以其特有的方式,打破傳統詩歌的美學追求,在現代詩歌的美學思想上力圖創新,精益求精,并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語言藝術和創作風格。艾略特在《荒原》中一直消解“非個人化”論的情感抒發,詩中“非個人化”的消滅,“反傳統”的審美角度使得詩歌本身更兼具社會責任感,非個性化特征中的生命體驗使我們永不停止思索生命的意義和價值。
《荒原》具有經久不衰的影響力。艾略特在詩歌表達與取材上對審美與傳統的疏離,在廣闊的語境中,“反傳統”意識表現十分強烈,詩中也表現出的怪誕與從丑之美的角度揭示了人類生存困惑。詩人在意象延伸與象征手法上均有獨到的審美取向。意象和象征在詩歌中的立意新異,主客體之間的隱喻把握極其深入到位。其次是怪誕的大膽與沖擊,擺脫了傳統意義上的束縛,反其道而行之的手段,通過對丑的事物描摹,描寫的場景大部分都是充滿著蕭條、腐朽、虛偽和骯臟,然而這些正是詩人通過詩歌所要揭露的真實現象。《荒原》的成就在于其敏銳地捕捉到了西方世界的舊文明和傳統的價值觀念衰敗的精神所在。反應了歐洲一戰后現代社會現狀,抒發了深刻思想感受。
同時,文學標準不能與宗教尺度割裂,艾略特本身信仰基督教,亦是“宗教上的英國天主教徒”,《荒原》詩中的宗教情愫與救贖意識也使得詩歌意義得到了最大的延伸與拓展。詩歌將生命的沉淪,超越及救贖反復穿插,在悲觀絕望中孕育希望,將死亡作為一種對生命的超脫,將信仰作為最終的救贖。綜上一系列創新得出結論,《荒原》具有重要的詩歌美學意義。
參考文獻:
[1][英]艾略特.傳統與個人才能[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年.
[2][英]艾.阿.瑞恰茲.楊自伍譯.文學批評原理[M].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2年.
[3]胡鐵生.美國文學論稿[M].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8期,第48-55頁.
[4]徐文貴.《荒原》:互文性研究[D].華中師范大學.2004年.
[5]梁冬華.艾略特“傳統”詩學觀探究[D].廣西師范大學.2004年.
[6]閆柯菲.艾略特《荒原》的總體象征藝術研究[D].黑龍江大學.2010年.
[7]李新.試論艾略特詩歌的意識內蘊[J].山東社會科學.1993年,第2期,第64頁.
[8]張劍.T.S.艾略特內心深處的《荒原》[J].當代外國文學.1996年,第1期,第147-148頁.
[9]胡鐵生.論《荒原》的美學思想[J].外國文學研究.1996年,第02期,第27頁.
[10]黃宗英.艾略特《荒原》中的動物話語[J].英美文學研究論叢.2001年,第 1期.
[11]王若蘭.遠古神話框架里的現代生活——淺析《荒原》的復雜性[J].文教資料.2009年.
[12]梁冬華.從《荒原》看T.S.艾略特的"非個人化"創作[J].觀曲靖師范學院學報.2009年,第4期,第28頁.
[13]張劍.艾略特與印度:《荒原》和《四個四重奏》中的佛教、印度教思想[J].外國文學.2010年,第1期,第39頁.
[14]喬明文.沉淪.超越及救贖——解讀艾略特《荒原》中的生命美學[J].時代文學.2011年,第2期,第156頁.
[15]姚艷梅.探析T.S.艾略特荒原之多元融合[J].名作欣賞.2011年,第03期,第104頁.
[16]陳本益.艾略特“非個人”論的美學意義[J].東南大學學報.2012年,5月,第3期,第105-107頁.
[17]吳振寅.《荒原》的美學體驗[J].芒種.2012年,第11期,第102頁.
[18]王娟.曹景凱.艾略特《荒原》中審美與傳統的疏離[J].長城.詩苑縱橫.2013年,第2期,第101頁.
[19]江群,張敬.反諷性典故和特·斯·艾略特的“傳統觀”[J].阜陽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4期.
[20]羅俏鵑,趙娜.艾略特主要詩歌中的意象觀擅變[J].語言教育.2013年,第5期,第83頁.
[21]閆柯菲.艾略特《荒原》的宗教救贖觀及藝術特色[J].北京科技大學學報.2013年,第12期,第30-32頁.
[22]王敏.《荒原》中死亡與復活主題的研究[J].語文建設.2013年,第35期.
[23]劉丹.TS艾略特詩學理論對20世紀中國現代詩歌的影響[J].文化縱橫.2014年,第10期,第73頁.
注 釋
[1]查良錚.穆旦譯文集 英國現代詩選[M].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378頁.
[2]徐志摩著.中國最美的詩歌世界最美的詩歌經典集下[M].江蘇美術出版社.2014年,第351頁.
[3](德)歌德等著.羅益民選編.外國長詩經典10篇[M].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第553頁.
[4]趙蘿蕤等譯.世界詩苑英華艾略特卷[M].山東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80頁.
[5][英]T.S.艾略特著,趙蘿蕤,張子清等譯.荒原——T.S.艾略特詩選[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第68頁.
[6][英]T.S.艾略特著,趙蘿蕤,張子清等譯.荒原——T.S.艾略特詩選[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
[7][英]T.S.艾略特著,趙蘿蕤,張子清等譯.荒原——T.S.艾略特詩選[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
[8]趙蘿蕤等譯.世界詩苑英華艾略特卷[M].山東大學出版社.1997年.
[9]趙蘿蕤等譯.世界詩苑英華艾略特卷[M]山東大學出版社.1997年.
[10]陸明.閆冰編著.外國文學名著導讀[M].清華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237頁.
[11]柳東林著.哲思黜退 禪意盎然 現代西方文學的禪化述要[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
[12]徐志摩著.中國最美的詩歌世界最美的詩歌經典集下[M].江蘇美術出版社2014年.
[13]趙蘿蕤等譯.世界詩苑英華艾略特卷[M].山東大學出版社.1997年.
(作者單位:貴州省荔波縣荔波高級中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