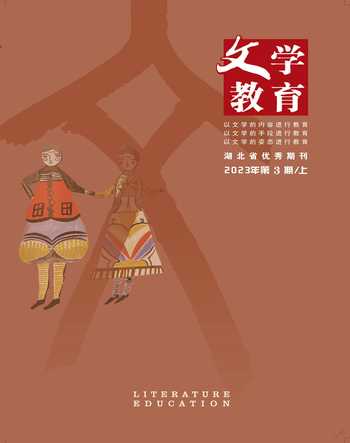海涅《巴赫拉赫的拉比》的互文性解讀
應(yīng)彬琛
內(nèi)容摘要:《巴赫拉赫的拉比》是德國浪漫派晚期改宗猶太作家海因里希·海涅的斷片之一。本文借助新歷史主義研究方法,對文本與歷史進(jìn)行互文性解讀:一方面追尋文本的歷史線索,明確故事發(fā)生時(shí)間及背景,從而進(jìn)一步揭示因缺乏史實(shí)記載而被歷史掩蓋的部分西班牙馬蘭諾人的心聲;另一方面,探尋15世紀(jì)末的西班牙猶太人與19世紀(jì)的德國猶太人的相似之處,由此窺見包括海涅在內(nèi)的19世紀(jì)猶太知識分子面臨的身份認(rèn)同危機(jī)。
關(guān)鍵詞:新歷史主義 《巴赫拉赫的拉比》 海涅 互文性
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1797-1856)是19世紀(jì)上半葉德國著名詩人及作家,憑借其杰出的詩歌、游記和文藝評論文章,成為德國文學(xué)史上繼歌德之后的又一顆璀璨明珠。但因其特殊的改宗猶太人身份與敏感的政治傾向,海涅始終不為當(dāng)時(shí)的德國知識學(xué)界正視,甚至不斷被邊緣化、污名化,其本人后半生也一直流亡法國巴黎,并最終客死他鄉(xiāng)。當(dāng)時(shí)只有少數(shù)德意志知識分子愿意與他交好并欣賞其文學(xué)才華,如首次在《美學(xué)征討》中提出“青年德意志”流派的“三月革命前時(shí)期”作家維恩巴格、女詩人霍恩豪森、猶太女作家拉赫爾·法恩哈根的丈夫卡爾·奧古斯特·法恩哈根,后者更是與海涅終生保持緊密的書信往來。
海涅于1824年夏天著手小說《巴赫拉赫的拉比》的創(chuàng)作,遺憾的是,這部小說在他1826年完成第三章的一部分之后便無疾而終。《巴赫拉赫的拉比》可以說是海涅由浪漫派晚期作家轉(zhuǎn)型為當(dāng)時(shí)官方認(rèn)定的“青年德意志”派作家[1]的過渡時(shí)期作品,雖然這份斷片只有短短三章,但海涅卻在書中詳細(xì)描繪了15世紀(jì)末期德意志地區(qū)猶太人的真實(shí)生活,給后人留下了寶貴的研究歐洲(主要是德國和西班牙)猶太文化的文本素材。
本文運(yùn)用新歷史主義研究視角分析文本。新歷史主義興起于20世紀(jì)70年代末、80年代初,這一概念由美國文學(xué)批評家斯蒂芬·格林布萊特提出,首次出現(xiàn)在《文類》的專刊導(dǎo)言。新歷史主義是聚合歷史、意識形態(tài)、權(quán)力話語的核心表述,挑戰(zhàn)舊歷史主義和形式主義,實(shí)現(xiàn)文學(xué)的“歷史轉(zhuǎn)向”:一方面,歷史事實(shí)通過經(jīng)權(quán)力挑選和抹除而保存下來的“文本”得以表述,使得文學(xué)文本有可能成為反映歷史鏡像的特殊載體,“所有的文本實(shí)際上都是社會文獻(xiàn),它們反映著且更重要的是回應(yīng)著當(dāng)時(shí)的社會歷史狀況”[2];另一方面,文本并非是一個(gè)超歷史的審美課題,而是特定時(shí)代的歷史、階級、權(quán)力以及文化等語境的產(chǎn)物。因此,只有將兩者結(jié)合比較,通過分析文本的歷史性盡可能還原最真實(shí)的歷史,通過分析歷史的文本性找到歷史中被虛構(gòu)或被抹除的成分,才能更大程度上貼近真相,文學(xué)文本對于歷史的反映價(jià)值也得以體現(xiàn)。本文旨在對文本與歷史進(jìn)行互文性解讀,再現(xiàn)中世紀(jì)末期、文藝復(fù)興初期的德意志地區(qū)猶太人與西班牙猶太人的生存狀況,重視19世紀(jì)德國猶太知識分子的身份認(rèn)同焦慮問題,并探究海涅對于德國猶太人義無反顧走上同化道路而發(fā)出的隱晦預(yù)警信號。
一.文本的歷史性:中世紀(jì)末期的德意志地區(qū)與西班牙
海涅并未在文中直接交代《巴赫拉赫的拉比》故事發(fā)生的時(shí)間及歷史背景,但是通過對文本的解讀,不難看出小說描繪的是一幅中世紀(jì)末期德意志地區(qū)猶太人的生活圖景。
首先,小說開頭兩段主要按照時(shí)間順序,簡明扼要地介紹了巴赫拉赫的建城史,以及中世紀(jì)以來屢見不鮮的大規(guī)模迫害猶太人運(yùn)動。萊茵河邊的巴赫拉赫城位于德國西南部,毗鄰美因茨和法蘭克福。小城的歷史最早可追溯到古羅馬時(shí)期,4世紀(jì)末羅馬帝國衰落后,巴赫拉赫“經(jīng)歷了風(fēng)云變幻的諸多朝代”(461)[3],最終由霍恩施陶芬家族接管,1254年之后又成為了威特斯巴赫家族的統(tǒng)治領(lǐng)域。從古羅馬時(shí)期開始便有猶太人居住在此,但因宗教、經(jīng)濟(jì)、政治等多方面因素,占統(tǒng)治地位的貴族、神職人員等團(tuán)體對猶太民族的迫害從未停止,不止針對巴赫拉赫的猶太人,在法蘭克福、在德意志其他地區(qū)、甚至在整個(gè)歐洲地區(qū),猶太人都經(jīng)常面臨莫須有的指責(zé)。十字軍東征時(shí)期(1096-1291),天主教徒打著收復(fù)圣地的旗號首次大規(guī)模迫害猶太人;14世紀(jì)中葉前后,猶太人又為鼠疫的蔓延肆虐承擔(dān)罪責(zé);“另外一種對他們的指責(zé),從過去很早的時(shí)代就開始,經(jīng)整個(gè)中世紀(jì)一直延續(xù)到上世紀(jì)初”(462),即發(fā)生在1287年的圣維爾納的故事,“但是自那以后的兩個(gè)世紀(jì)里,他們(猶太人)就幸免于這種來自平民憤怒的襲擊,盡管他們期間仍然受到各種敵視和威嚇”(463)。因此前文提到的“上世紀(jì)初”便指向海涅所處時(shí)代的上世紀(jì),即18世紀(jì)初,而“自那以后”更是可以將故事背景縮小到1487年前后。
其次,文中個(gè)別詞匯具有濃重的中世紀(jì)色彩,或是暗含了人物的身份指向。第三章出現(xiàn)了“Frauenhaus”[4]一詞,其現(xiàn)代含義確實(shí)為女子收容所或婦女之家[5],在此處卻不盡然,譯為“妓院”更為妥當(dāng)。文中以色列餐館的老板娘施納帕-艾勒提起她那次在阿姆斯特丹的倒霉遭遇,就用“無恥的”來形容被“老奸巨猾的車夫”騙往的“Frauenhaus(妓院)”。阿姆斯特丹一直以來都是一座水陸四通八達(dá)的海港城市,中世紀(jì)晚期城市的發(fā)展及轉(zhuǎn)型又必然伴隨著商業(yè)賣淫的興起[6],因此施納帕-艾勒才會“嚇得差點(diǎn)暈了過去”,她在那里“哪怕只有一小會兒敢于閉上眼睛,就真的會暈倒”(501),也正是因?yàn)榇嬖谶@樣的歷史污點(diǎn),風(fēng)評差勁卻極力想自證清白的施納帕-艾勒,才會在與他人交流時(shí)無數(shù)次強(qiáng)調(diào)她的道德原則[7]。此外,斷片第二章還提到了“馬克西米利安國王”(477),德國歷史上共有兩位馬克西米利安國王,即馬克西米利安一世(1459-1519)和馬克西米利安二世(1527-1576)。考慮到文本語境中豐富的中世紀(jì)元素,以及文藝復(fù)興之風(fēng)、宗教改革之風(fēng)尚未吹進(jìn)普通民眾內(nèi)心的事實(shí)(如神職人員仍舊在暗中控制人們的精神思想[8]),并參考其他譯者給出的注釋[9],可得知文中的“馬克西米利安國王”指的就是馬克西米利安一世;而德語中的“國王”和“皇帝”具有不同的人物身份象征,馬克西米利于1486年4月9日在亞琛大教堂加冕為德意志國王,直到1508年2月4日,經(jīng)教皇尤里烏斯二世批準(zhǔn),他才在意大利特倫托大教堂被授予神圣羅馬帝國皇帝的稱號。由此可進(jìn)一步縮小故事發(fā)生時(shí)間,即馬克西利安一世作為德意志人民的國王之時(shí)(1486-1508)。
最后,西班牙是整篇小說的重要底色,比如海涅在描寫主人公亞伯拉罕時(shí),提到了這位拉比年輕時(shí)赴西班牙求學(xué)的經(jīng)歷,他與“那些當(dāng)時(shí)有著極高修養(yǎng)的西班牙猶太人”(464,下同)一起學(xué)習(xí)了七年。福柯指出:“它(作品)可以在本文中辨讀本文所要掩飾同時(shí)又要表現(xiàn)的某種東西的記錄……(話語單位的)不連續(xù)性不僅僅是所有構(gòu)成歷史地質(zhì)上斷層的重大事件之一,而且存在于陳述的簡單事實(shí)中。”[10]因此,無論是從主人公去西班牙求學(xué)的選擇上看,還是從巴赫拉赫的猶太人對西班牙猶太人的固有認(rèn)知中看,西班牙在文本語境中無疑具有話語場中心地位,這種深入日常話語中的對西班牙的提及,甚至不為巴赫拉赫猶太人所意識。由此可知,中世紀(jì)德意志地區(qū)的發(fā)展明顯落后于西班牙,當(dāng)巴赫拉赫猶太人仍舊保持中世紀(jì)的習(xí)慣、對猶太教心懷虔誠時(shí),“獨(dú)立思考的思維方式”已深入西班牙猶太人的頭腦中,而另一方面,巴赫拉赫的猶太人又對“模仿基督教習(xí)俗”、甚至改宗的西班牙猶太人感到鄙夷和不恥,這恰好印證了15世紀(jì)末的德意志地區(qū)和西班牙的歷史。
15世紀(jì)末、16世紀(jì)初的德意志地區(qū)雖然社會經(jīng)濟(jì)較前已有很大進(jìn)步,但封建生產(chǎn)方式仍占其統(tǒng)治地位,與此同時(shí),西班牙卻早已萌發(fā)資本主義萌芽、接受哲學(xué)思辨之風(fēng)、點(diǎn)亮啟蒙理性之火,并利用地理優(yōu)勢逐漸成為海上殖民霸主,最終通過擴(kuò)張、聯(lián)姻等途徑,一躍成為16世紀(jì)歐洲最強(qiáng)大的國家。因其地理環(huán)境,西班牙自羅馬帝國衰落以來先后經(jīng)歷了蠻族統(tǒng)治、阿拉伯人統(tǒng)治和基督徒—穆斯林共治的時(shí)代,“伊比利亞半島是整個(gè)拉丁基督世界對抗穆斯林的前沿戰(zhàn)場”[11],直到12世紀(jì),北方基督教王國和南方穆斯林統(tǒng)治依舊是西班牙的矛盾中心。而處于矛盾中心之外的少數(shù)族群——西班牙猶太人因此得利:無論是羅馬帝國時(shí)期還是阿拉伯人統(tǒng)治時(shí)期,統(tǒng)治者都對猶太人采取了宗教寬容政策,8世紀(jì)的西班牙南部猶太人甚至可以做到宮廷級別的官吏以及軍事統(tǒng)帥;10世紀(jì)至11世紀(jì),北非穆斯林定都塞維利亞,強(qiáng)力推行宗教統(tǒng)一政策,但北方基督教王國出于各種利益考慮,向猶太人拋出橄欖枝,猶太人就此北遷,猶太精英族群成為基督徒的國務(wù)活動家、顧問和醫(yī)生。相比于夾縫中生存的其他國家猶太人,西班牙猶太人似乎備受上帝恩寵,但這份恩寵從13世紀(jì)末開始逐漸被收回。此時(shí)的基督教王國已站穩(wěn)腳跟,不再需要猶太人的支持,在宗教統(tǒng)一的方向上,猶太人更是成為他們的眼中釘,因此他們對猶太人的寬容政策逐漸收緊,盡管很多猶太限令并未徹底落實(shí)。1391年,在西班牙發(fā)生了猶太歷史上唯一一次大規(guī)模改宗現(xiàn)象;1492年,西班牙徹底驅(qū)逐猶太人,很多猶太人(包括改宗猶太人)為了生存而選擇離開西班牙。
誘發(fā)這兩大歷史事件的因素復(fù)雜且多樣,但可以肯定的是,不像巴赫拉赫猶太人,“來自外部的仇恨越是威逼他們……他們對上帝的虔誠和敬畏也越加深沉,越加根深蒂固”(463),西班牙猶太人經(jīng)歷過的磨難相對較少,對上帝的信仰遠(yuǎn)不如德意志地區(qū)的猶太人忠誠,一旦面臨生存危機(jī)就有極大可能接受洗禮,盡管這一選擇很大程度上出于被迫,盡管他們只是表面上皈依了基督教,暗地里仍信仰猶太教。這類改宗猶太人被稱為馬蘭諾,如斷片中的西班牙改宗猶太人伊薩克就符合馬蘭諾人的部分特質(zhì),本文也將在第二節(jié)中詳細(xì)分析這一重要人物。根據(jù)伊薩克在故事中的表現(xiàn),文本背景符合15世紀(jì)末西班牙歷史現(xiàn)狀,且更有可能發(fā)生在1492年針對所有猶太人的驅(qū)逐事件之前。
二.歷史的文本性:超脫時(shí)代的人物——伊薩克
斷片第三章中出現(xiàn)了一個(gè)重要人物——西班牙騎士唐·伊薩克,他可以說是西班牙歷史經(jīng)過沉淀后的鮮活縮影,并與“符合上帝要求的生活方式的典范”(464,下同)——主人公亞伯拉罕形成了鮮明對照。巴赫拉赫的猶太人因他們的拉比亞伯拉罕赴西班牙求學(xué)七年而隱約聽聞過一些不敬上帝的傳言,但拉比從西班牙回來后“哪怕最細(xì)小最不起眼的猶太教教規(guī)習(xí)俗”也兢兢業(yè)業(yè)地身體力行,謠言不攻而破;與此相反,唐·伊薩克不僅視基督教禮儀習(xí)俗為無物,也有意與猶太教劃清界限,他甚至算不上是一個(gè)西班牙馬蘭諾人,更像是一個(gè)無信仰者,他通過味覺和嗅覺喚起血脈中與猶太教之間割不斷的聯(lián)系,猶太美食是他扎在以色列土壤上的根,無論如何他都無法抹去身上的猶太印記。
然而,伊薩克的行為舉止就其所處時(shí)代而言未免過于大膽放肆。伊薩克在法蘭克福猶太區(qū)的集市上公開承認(rèn)自己是個(gè)異教徒,[12]這很可能令其引火上身,因?yàn)樗漠惗怂枷朐诋?dāng)時(shí)為猶太教所不容,也為基督教所不容。歷史上,15世紀(jì)的猶太知識學(xué)界將14世紀(jì)末猶太人大規(guī)模改宗的原因歸咎為哲學(xué),猶太哲學(xué)家們面對刀劍順勢而為,選擇了受洗而非殉教,從而引導(dǎo)了大量普通猶太人皈依基督教;西班牙在1492年徹底驅(qū)逐猶太人之后,大量猶太人逃離西班牙或是接受基督教洗禮。可以確信的是,在馬蘭諾中存在一些持有異端思想的哲學(xué)家,但至今并未發(fā)現(xiàn)存有相關(guān)著作,因?yàn)檫@些異端思想一旦泄露,他們將失去過安穩(wěn)日子的機(jī)會,改宗也就失去了意義。[13]因此,伊薩克的言行與當(dāng)時(shí)的社會規(guī)則產(chǎn)生強(qiáng)烈沖突,這一文學(xué)人物在某種程度上具有超越時(shí)代的意義;另一方面,這種引人注意的矛盾感又恰好反映了那段被掩藏卻真實(shí)存在的歷史,借伊薩克之口揭示了部分西班牙馬蘭諾人的真實(shí)心聲:即使受禮,也依舊扎根于猶太教的土壤。
新歷史主義批評家認(rèn)為,“由于每個(gè)文本都有一個(gè)實(shí)際的作者,他(她)的行為與觀念就既反映了作者本人也反映了作者所在社會的關(guān)切,并構(gòu)成文本本身的必要元素”[14],因此“超前”的伊薩克可以說帶有海涅本人的影子,而海涅卻沒有他筆下的虛構(gòu)人物那么灑脫。《巴赫拉赫的拉比》開始創(chuàng)作于1824年,且1822年至1824年是海涅集中創(chuàng)作猶太題材作品時(shí)期,直到1825年迫于現(xiàn)實(shí)壓力而改宗后,他才逐漸放棄這一題材。顯然,海涅對猶太教的情感并不淡薄,他試圖通過文學(xué)手段記錄猶太民族的處境、表達(dá)猶太民族的訴求;同時(shí),他皈依基督教更多也是基于現(xiàn)實(shí)利益考慮而非信仰,盡管他想借此做一名律師的目的最終并沒有達(dá)成,且對改宗一事深感后悔,他就像是一個(gè)既想堅(jiān)定猶太教信仰并從中找到歸屬感,又因現(xiàn)實(shí)處境而不得不公開割斷猶太情結(jié)的矛盾體。
但海涅面臨的身份認(rèn)同焦慮并非代表個(gè)人,而是十九世紀(jì)德國猶太知識分子共同面臨的問題,掩藏在兩個(gè)重要人物——亞伯拉罕和伊薩克身上的這段時(shí)期的歷史以文學(xué)形式被書寫下來,此過程甚至不為海涅本人所意識。與十五世紀(jì)西班牙相似的是,啟蒙思想終于在十八、十九世紀(jì)的德國廣泛傳播,將德意志民族從落后的中世紀(jì)神圣羅馬帝國的觀念中解放出來,但德國同時(shí)面臨社會轉(zhuǎn)型,在啟蒙運(yùn)動、法國大革命和拿破侖稱帝等多重影響下,危機(jī)顯得更為復(fù)雜尖銳。十九世紀(jì),德國民族與種族思想逐漸覺醒,猶太知識分子融入德國社會的傳統(tǒng)方式(即改宗)日漸失效,而傾慕啟蒙思想的德國猶太知識分子又不愿遵循正統(tǒng)猶太教的生活方式,他們認(rèn)為猶太教與包括基督教在內(nèi)的其他宗教一樣,是被理性排除出社會發(fā)展過程的事物。與此同時(shí),生長在德國的部分猶太知識分子堅(jiān)定認(rèn)同自己是德國社會的一份子,并渴望在政治文化舞臺上發(fā)揮才能,但德國社會上的種族主義歧視愈演愈烈,拿破侖擊潰普魯士后又對猶太民族采取寬容政策,從中獲益的德國猶太人遭到德意志民族的嫉恨。面對這些社會現(xiàn)象及矛盾,大多數(shù)猶太知識分子為保障和實(shí)現(xiàn)自身訴求而選擇了逃避,然而無論怎樣同化、皈依,往往都只是他們的一廂情愿,與德意志民族建立共同的信仰與民族精神并不能通過簡單的皈依來實(shí)現(xiàn)。[15]處于社會思潮變化中的德國猶太知識分子理應(yīng)具有更敏銳地洞察能力,但對此的錯(cuò)誤判斷和選擇使他們并未發(fā)揮適當(dāng)?shù)念A(yù)警作用,這也為近現(xiàn)代史上德國猶太人的慘劇埋下禍根。
站在十九世紀(jì)歷史洪流中的海涅不會不知道1492年的西班牙究竟發(fā)生何事,也不會不知道當(dāng)時(shí)的改宗猶太人最終還是面臨流離失所的命運(yùn),也許他在二十年代仍心存僥幸,但伊薩克這一超脫時(shí)代背景的小說人物已在時(shí)刻提醒著他猶太人將會面臨的災(zāi)難,無論是在西班牙還是在德國。也許海涅抹去故事時(shí)間及背景的做法,正是想向所有義無反顧走上同化道路的德國猶太人發(fā)出隱晦的警示信號,只是這一信號確實(shí)過于微弱,甚至沒有人能夠注意到。
1826年后,海涅再未動筆續(xù)寫《巴赫拉赫的拉比》,或許是因?yàn)榱魍錾盍钏麩o暇顧及小說創(chuàng)作,或許是因?yàn)樗扔诂F(xiàn)實(shí)利益皈依基督教的做法使他再也無法面對筆下虔誠的主人公拉比,或許是浪漫派作家寫斷片的偏好使然,又或許是因?yàn)樾≌f的獻(xiàn)予者勞伯的“背叛”[16]。但無論如何,《巴赫拉赫的拉比》給予后人足夠大的闡釋空間。正如本文借助新歷史主義研究方法,分析了文本的歷史性和歷史的文本性,一方面撥開故事背景之迷霧,明確了故事發(fā)生時(shí)間為15世紀(jì)末,并借助文本載體挖掘出了一些未被記載下來的歷史痕跡;另一方面又通過作者海涅與筆下人物的隱匿對話,發(fā)現(xiàn)了處于不同時(shí)空卻有著相似命運(yùn)的猶太人群體,由此窺見十九世紀(jì)猶太知識分子面臨身份認(rèn)同危機(jī)的根源之一,即猶太知識分子的“失格”。
由此可見,文學(xué)文本與歷史語境之間確實(shí)存在著互動和張力,文學(xué)文本不可避免地被歷史語境形塑,與此同時(shí),歷史畫卷也因文學(xué)文本而變得更加清晰。
注 釋
[1]“……法蘭克福的聯(lián)邦議會于1835年12月10日通過決議,全面禁止(包括海涅在內(nèi)的5位)青年德意志作家的作品……雖然聯(lián)邦議會禁止青年德意志作家的決議中把海涅的名字列在第一位,但是,按照傳統(tǒng)慣例,“青年德意志”卻不包括被視為青年德意志之父的海涅和伯爾納。”摘自任衛(wèi)東、劉慧儒、范大燦(2007):德國文學(xué)史(第3卷)。北京:譯林出版社,第322頁+第326頁。
[2]查理斯·E·布萊斯勒,趙勇、李莎、培杰等譯(2014):文學(xué)批評:理論與實(shí)踐導(dǎo)論(第五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第237頁。
[3]本文引用《巴赫拉赫的拉比》均出自:《海涅合集(第一卷)》(Heinrich Heine: Der Rabbi von Bacherach. In Klaus Briegleb (Hg.):Heinrich Heine Smtliche Schriften,Band 1. München 1975.)
[4]DWDS就“Frauenhaus”一詞列舉出三種詞義。(https://www.dwds.de/wb/Frauenhaus,2021年9月27日訪問。)
[5]趙譯為“女子寄宿所”,并給出注釋:“為收容遭到家庭暴力傷害的女人而設(shè)的女子庇護(hù)所”。參見海因里希·海涅,趙蓉恒譯(2015):佛羅倫薩之夜:巴赫拉赫的拉比。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第61頁。
[6]參見Christian Zarend: Bordelle.Frauenhaus und Prostitution im spten Mittelalter und in der frühen Neuzeit.München 2006.S.2.
[7]參見Heine,S.500-501.引文如下:“美德比美貌更有價(jià)值(Tugend ist mehr wert als Schnheit)”,“為了我的美德(Meiner Tugend wegen)”等。
[8]參見Heine,S.461.引文如下:“神職人員在暗處控制人們的精神思想(Die Geistlichkeit herrschte im Dunkeln durch die Verdunkelung des Geistes)。”
[9]潘譯文中注釋如下:“馬克西米連(1459-1519),德國國王,自1493年起被選為德國皇帝。”參見海因里希·海涅,潘子立譯(2003):巴赫拉赫的拉比。載于:海涅全集(第7卷·散文作品),章國鋒、胡其鼎編,潘子立、趙蓉恒等譯。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第149頁。
[10]米歇爾·福柯,謝強(qiáng)、馬月譯(2003):知識考古學(xué)。北京:三聯(lián)書店,第24頁+第29頁。
[11]王玖玖:中世紀(jì)盛期西班牙猶太人與基督徒的族群融合。載于:《中山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科學(xué)版)》2018年第58期。第93頁。
[12]參見Heine,S.498.引文如下:“是的,我是一個(gè)異教徒…(Ja,Ich bin ein Heide…)”
[13]參見王彥:論哲學(xué)與14世紀(jì)末猶太人改宗基督教的關(guān)系。載于:《山東大學(xué)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版》2011年。第127頁。
[14]布萊斯勒,文學(xué)批評:理論與實(shí)踐導(dǎo)論(第五版)。第240頁-第241頁。
[15]王雪:19世紀(jì)德國猶太知識分子身份認(rèn)同問題研究。載于:《北方論叢》2013年。第109頁-第110頁。
[16]“表現(xiàn)得最沒有骨氣的大概要算勞伯……海涅曾戲稱他為‘只能死在競技場上的斗劍士……(但到)1836年初,他(勞伯)又寫道,他已經(jīng)變成另外一個(gè)人了,他覺得文學(xué)不再是政治愿望的表現(xiàn)了。他要對目前的文學(xué)(青年德意志派的文學(xué))進(jìn)行斗爭。”摘自任衛(wèi)東等,德國文學(xué)史(第3卷),第323頁。
(作者單位:西南交通大學(xu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