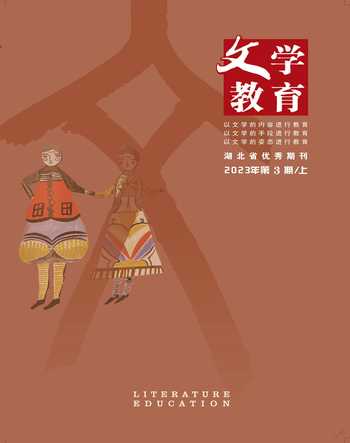《巴塞爾姆的白雪公主》的焦慮書寫
周嫣瑜 楊紀平
內容摘要:《巴塞爾姆的白雪公主》是對經典格林童話的顛覆性改寫,它將英雄人物平庸化,構建了一個現代版的“黑”童話故事。運用蘇珊·蘭瑟提出的敘事聲音酷兒化來解讀小說文本,不難發(fā)現巴塞爾姆將七個小矮人及整個文本創(chuàng)作過程都“酷兒化”,從作者意圖來看,這是巴塞爾姆對女權運動浪潮下的男性生存狀況、消費文化泛濫下的文學發(fā)展狀況的擔憂。
關鍵詞:唐納德·巴塞爾姆 《白雪公主》 蘇珊·蘭瑟 酷兒化敘事聲音
作為一部典型的后現代主義作品,《巴塞爾姆的白雪公主》是對經典格林童話《白雪公主與七個小矮人》的顛覆性改寫。唐納德·巴塞爾姆將白雪公主、王子和小矮人們經典的身份標簽撕除,將他們降格為妓女、乞丐和流氓[1]。原先柏拉圖式的世界坍塌了,白雪公主與七個男人同居于紐約的破舊公寓,她期盼著王子的到來,卻等來一個“青蛙王子”。本文基于蘇珊·蘭瑟的酷兒化敘事理論,用敘事聲音作為透鏡來探索《巴塞爾姆的白雪公主》中含蓄型的、雙性別化的以及解構敘述規(guī)則的酷兒敘事聲音,挖掘出潛藏于文本中的“酷兒”形象。七個現代侏儒通過選擇性的贅敘和省敘,掩蓋了他們的異化情感和身份;其次,他們捆綁式的集體型發(fā)聲,加之白雪公主的獨白干擾,形成了一個雌雄莫辨的跨性別的敘事聲音,再次對其“酷兒”身份進行隱喻,在呈現男性異化情感的背后,是巴塞爾姆對男性生存狀況的擔憂;此外,作者將整個文本創(chuàng)作也“酷兒化”,通過解構敘事規(guī)則和經典人物形象,巴塞爾姆創(chuàng)造了全新的文學形式,傳達了對文學未來發(fā)展的焦慮。
一.含蓄型酷兒敘述聲音:欲蓋彌彰的酷兒群體
作為女性主義敘事學的奠基人,蘇珊·蘭瑟試圖走向一種更酷兒、更女性主義、更兼容的敘事學。在《敘事聲音酷兒化》中,她探究了在什么情況下敘事聲音可以被認為是“酷兒化”了的,以及酷兒化的敘事聲音可以給文本帶來怎樣的效果。基于此,她提出了三種酷兒化的敘事聲音,概括來說就是:(1)酷兒敘述者的聲音;(2)模糊或顛覆性別的聲音;(3)解構敘述規(guī)則的聲音。作為后現代主義文本,若要把握《巴塞爾姆的白雪公主》中人物的行為動機和事件的因果關系,就不得不挖掘其中的“影子情節(jié)”(negative plotting),即事件的重要意義來自于它們在文本引發(fā)的(但不一定直接表達出來的)的對立面[2]。
小說的大部分內容是由“我”(小矮人中的一個)或“我們”(七個或數個小矮人)敘述的,讀者藉此窺見了他們空虛糜爛的生活。然而正如蘭瑟對頗具主觀性的敘述聲音表示質疑一般,筆者認為小矮人這一邊緣化群體的發(fā)聲是不可靠的,表面上,他們的話題聚焦于女性,實際上,這是為了掩蓋他們之間的異化情感。他們主觀而巧妙地對一些內容詳細闡述,而對另一些可能會暴露其異化身份的內容刻意回避。
女性是他們贅述的話題。故事開篇,小矮人們就對白雪公主的身體進行了直白的描述:“她是一個黑發(fā)美人,高個子。身上長著許多美人痣:胸上一顆,肚子上一顆,膝蓋上一顆,腳踝上一顆,臀部上一顆,脖子后面一顆。它們全長在左邊,從上到下,幾乎能列成一排......”、“她的頭發(fā)黑如烏木,皮膚潔白如雪”。他們還常在工作之余偷窺其他女性:“從上面看,她們向靶子,梅花色的頭事靶心,波狀的海軍藍的裙子是粗粗的圓圈。在前面晃動的白腿或黑腿,仿佛是有人在靶子上方揮動著手臂叫喊。[3]”女性似乎成為了一道視覺景觀,對于異性身體大膽而熱烈的敘述貫穿整部作品,是小矮人們津津樂道的話題。
他們談論女性,但從不投入情感,并且作為兄弟親密無間的他們,對同性的情感和身體避而不談。全篇對男性身體唯一敘述是針對克萊爾(小矮人之一)的:“透過克萊姆透明的免燙尼龍襯衫,端詳著他的胸部......他也是那種許多西部男孩都有的凹胸,好像小時候被一頭母牛壓過似的[4]”。巴塞爾姆沒有透露該敘述者是誰,實際上這也無關緊要,因為他必定是剩下六個中的一個或幾個。此時的觀察是“透視性”的,且不難發(fā)現敘述者對于克萊姆的身體是贊嘆的。在描述克萊姆身體的段落內,敘述者多次圍繞克萊姆的“襯衫”展開討論:“只穿著一件襯衫”、“克萊姆一邊燙著襯衫”、“克萊姆把熨斗放回桶里。襯衫現在好看了,非常好看”。在描述了克萊姆宜人的身體后,敘述者又用將其物化為具體的商品,此時的身體變成了一種符號,暗示的正是對其消費和占有的欲望。
除了男性之外,浴室這一重要的場所也是他們刻意省敘的對象。白雪公主與小矮人之間的伴侶關系顯而易見,而七個小矮人與白雪公主共處浴室的這一事實,實際上也暗示著潛在的酷兒書寫,即伴侶關系不僅存在小矮人與白雪公主之間,也存在七個小矮人之間。在這里,“浴室”充當的是“櫥柜”(closet)的角色。小矮人們正是在浴室這個對外隱蔽、對內敞露的領域里進行著酷兒式凝視,讓一切私密性都無處可藏。浴室這一意象也是對他們生存處境的隱喻——“公共浴室”是無處不在的規(guī)訓工具,它對于人們的身體、精神的獨特性視而不見,誘惑著人們在喧鬧的世俗中狂歡[5]。
通過贅敘和省敘的巧妙結合,小矮人們實現了在情節(jié)層面上無法公開的酷兒關系。在他們的敘述中,一方面是其津津樂道的內容——女性身體,一方面是其刻意避諱的話題——浴室和同性身體。這兩種敘述巧思的結合,構成了對其酷兒身份的掩蓋。
二.雙性別化的酷兒敘述聲音:雌雄莫辨的敘事主體
如果說含蓄型酷兒敘述者試圖掩蓋的是其“酷兒”身份,那么雙性別化的酷兒敘述聲音則是對“酷兒”身份和性別身份的雙重掩蓋,它通常表現為故事敘述者的非性別化或雙性別化的酷兒敘述。這種敘事聲音是對身份類別的抵制,它存在于或者創(chuàng)造了一個超越性別的世界,這個世界拒絕傳統(tǒng)的男性和女性的范疇和傳統(tǒng)的等級制度。巴塞爾姆構建的后現代童話文本就穿插著亦男亦女的敘述聲音。
七個現代版小矮人是一組集體敘述者,他們的言行幾乎都是以“我們”的名義進行的,代表的是七個人作為一個捆綁式團體的發(fā)聲:“除了刷洗樓房,我們還制造嬰兒食品”、“我們不曉得白雪公主在那里是否幸福。可是,她要是不幸福,我們也無能為力”。他們的抱團式發(fā)言開發(fā)了一種“集體型敘述聲音”(communal voice),這種敘述聲音可以同時包含男性和女性角色,或者性別未被指定的角色,從而創(chuàng)造出一種具有包容性或者性別酷兒化的集體聲音[6]。正如蘇珊·S·蘭瑟所言,“我們-敘述者”的性別定位往往是開放性的,留待讀者去確定,七個侏儒的成組發(fā)言恰好模糊了他們作為個體時的“酷兒”形象;反過來,小矮人們這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發(fā)聲也是其缺乏男性氣質的表現,這種概括性的聲音將七個侏儒在思想和行動上進行了統(tǒng)一,因為他們沒有個性特征,或者說他們作為個體的特征根本不足以鑒別他們的男性身份,所以他們互相捆綁,離不開彼此,是一群被邊緣化了的“酷兒”。
除了言語行為的集體敘述之外,七個侏儒的工作也是捆綁式的。從事服務小孩、刷洗樓房這類被傳統(tǒng)認為是女性范疇內的工作,大大地削弱了他們的男性氣質。他們不去追尋剛硬的、工業(yè)化的男性工作,卻屈居于柔弱的、合作式的女性化工作。究其原因,可以歸為他們困囿于“男性氣質危機”之中,這些精神侏儒知道自己無法勝任男性角色,便退而求其次選擇了相對容易、不需要承擔過多社會職責的“酷兒”身份。他們在一個男人幫的交際社會中,漸漸迷失了作為個體的獨特性,唯有在“浴室”中才能與彼此真正的坦誠相待。
如果說小矮人們作為酷兒敘事者隱性揭示了自己的“酷兒”身份,那么白雪公主的敘述則讓他們的性別身份昭然若揭。白雪以自我直言的方式抒發(fā)女性聲音,對小矮人的敘述進行干擾。白雪是一位處于覺醒狀態(tài)的女權主義者,她雖充當著七個男人的“家庭主附”(horsewife),卻早已厭倦了這種生活。她對這個受男性控制的物質世界感到憤怒:“啊。但愿我能一把抓住那個把電器連接也稱作男女相合的人!他以為自己精于世故......所以不要跑過來指控我不嚴肅。女人也許不嚴肅,但至少她們不是傻瓜![7]”她也數次直白地控訴道:“他們七個人加起來,大約只約等于兩個真正的男人”;她還多次為自己的“不完整”感到焦慮,說自己是一個“缺了一部分的”存在——在傳統(tǒng)看來,沒有男人的女人是不完整的,而白雪公主與七個男性同居卻依舊聲稱自己“不完整”,這七個侏儒無法擔任男性角色的事實也就不言而喻了;至于白雪公主抱怨“早已厭煩了伺候這些男人”,與其說是厭煩了伺候小矮人,不如說是厭煩了充當他們真實身份的“遮羞布”。通過這種直抒胸臆的抱怨和控訴,白雪樹立了作為女性的權威。
除此之外,白雪還將身體作為自我表達的武器,通過無聲的言語抒發(fā)對新生活的渴望。譬如,她不再繼續(xù)穿著小矮人喜愛的緊身褲,而改穿寬松肥大的直筒褲。這一行為惹得小矮人的不滿,卻是白雪邁向反抗的第一步,表明她不再將自己置于“被凝視”的地位,不愿為博得他們的愛憐而裝扮自己的身體,而是將長長的黑發(fā)掛出窗外,讓庸俗之輩大吃一驚,讓自己的性生活恢復活力。女性的頭發(fā)一直被視為“性”的意象,是刻畫女性之美必不可少的部分。白雪的頭發(fā)是她吸引王子的重要手段,也是她抒發(fā)女性聲音的獨特渠道。從白雪無聲的身體敘事中,讀者再次聽見了她構建女性權威的愿望。
七個小矮人的集體型敘述,加之白雪公主的女性主義敘述,構建了一個雙性別化的酷兒敘述聲音。小矮人欲將其“酷兒”的個體身份淹沒于群體之中,因此他們捆綁著言、捆綁著行,這是他們展現話語同謀的重要手段;白雪公主則不安現狀,利用她的身體和言語打亂了小矮人構建的男性話語世界,也讓讀者聽到了她的話外之音和對七個“被閹割的”侏儒的控訴。事實上,敘述聲音的模糊性是對敘述者性別和性別傾向的隱喻,七個小矮人占據的正是一個曖昧不清的身份定位。而造成這一男性群體“酷兒化”的原因,或許可以溯源到小說創(chuàng)作的時代背景。20世界60年代的美國正是女權運動澎湃之際,以白雪公主為代表的女性開始覺醒,不愿再屈居于屋檐之下,渴望解放語言和自己的身體;而以小矮人為代表的男性在這一時期則經歷著一場“男性氣質危機”(crisis of masculinity)[8],面對“屋中天使”突如其來的反抗,他們困惑了,迷茫了,驚愕了,最終退縮了。身為男性作家,巴塞爾姆將“酷兒”這一形象歸之于男性人物,重點關注他們的生存困境,是期望讀者能反思兩性二元對立的主流思想。男性絕對主導或女性絕對主導都不是平衡的狀態(tài),只有兩性平等才能讓社會健康地運轉。
三.解構敘述規(guī)則的聲音:顛覆傳統(tǒng)的文本構建
在《敘事聲音酷兒化》中,蘇珊·蘭瑟總結闡釋了“酷兒”的多義性,提出了作為動詞的“酷兒”(to queer)表示跨越性別規(guī)范、或解構二元對立的性別規(guī)范、或解構所有既定規(guī)范。而酷兒理論學者大衛(wèi)· 哈爾柏林(David Halperin)也認為可以把“酷兒”定義為“一切與規(guī)范、合法、主導相悖的東西。它沒有一個固定的指涉物,它是一種沒有本質的身份。因此‘酷兒相對于規(guī)范劃分出的不是一個實在的事物,而是一種立場”[9]。此外,珍妮弗·多伊爾(Jennifer Doyle)在《酷兒墻紙》(Queer wallpaper) 中也指出“酷兒特質”不僅體現在性別范疇內,也是一種從事藝術的方式與態(tài)度[10]。
從蘭瑟對“酷兒”一詞的動詞性闡釋和酷兒理論家擁護“酷兒”一詞所包含的不確定性可以看出,酷兒敘事并不局限于同性戀研究,是一個有待發(fā)揮的領域。在《巴塞爾姆的白雪公主》中,“酷兒”不僅作為人物個體存在于文本中,而且也以動詞性質的寫作行為統(tǒng)領著整個文本。具體來說,此時的“酷兒”指代小說中所有打破傳統(tǒng)寫作規(guī)范、解構文本穩(wěn)定性的行為,在這些顛覆性改寫中,以碎片化敘事和人物降格這兩種(行為)“酷兒”最為突出,藉此,《巴塞爾姆的白雪公主》闡發(fā)了第三種酷兒敘事聲音——解構敘事規(guī)則的聲音。
巴塞爾姆為讀者準備了一個語言的盛宴,小說中充滿了各種文字游戲[11]。文本充斥著許多中斷的、任意的、無關緊要的列舉,形成了碎片化敘事,打破了傳統(tǒng)流暢的敘述規(guī)范。在談及白雪公主的教育背景時,巴塞爾姆不厭其煩地列舉了白雪在比弗學院的學習內容:“然后,她學習了《英國浪漫主義詩人II》:雪萊、拜倫、濟慈。然后,她學習了《心理學理論基礎》:思維、意識、無意識思維、人格、自我......然后,她學習了——”[12]如此枯燥的枚舉讓學校教育也失去了意義。同樣,在白雪公主期盼王子的到來時,她在心中念叨:“哪位王子會來?會是安德烈王子?伊戈爾王子?阿爾夫王子?阿方索王子?馬爾科姆王子......”[13]如果給予足夠的空間,想必這份“王子清單”會無窮盡地延續(xù)下去。無意義的碎片堆積堵住了讀者找尋意義的出路,如果擯棄了文本可讀性和意義深度,文學是否就降解成了一堆“辭藻垃圾山”?對于巴塞爾姆碎片化的敘事實踐,杰羅姆·克林科維茨(Jerome Klinkowitz)作出了如下的評論:“在一個新的世界里,舊的價值觀念必須用新的形式來表達。對于無理性的、無條理的時代巴塞爾姆的形式使想象力的價值復活了”[14]。在揶揄文學經典商品化的過程中,巴塞爾姆也展示了他對此無可奈何地屈從的一面。
其次,《巴塞爾姆的白雪公主》對經典童話中的人物形象進行了降格處理,公主與王子流落人間,分別淪為了妓女和偷窺狂,善良敦厚的小矮人也出落成一群躁郁的精神侏儒,于是,經典格林童話被降格為“黑”童話故事。白雪公主是一位畢業(yè)于比弗學院(Beaver College)的學生,“Beaver”一詞在英語俚語中有“女陰”之意[15],暗示了白雪的潛在身份。畢業(yè)后,白雪與七個男人同居于一間破爛公寓,充當他們的“家庭主附”——“家庭主附”(horsewife)是對“家庭主婦”(housewife)的滑稽模仿,涵蓋了“主婦”和“蕩婦”的雙層含義。此外,小說還通過“頭發(fā)”這一意象來鞏固白雪公主的妓女形象。頭發(fā)在女性形象的塑造中起著不可或缺的作用,是評判女性之美的重要標準。白雪的頭發(fā)也是她性獵奇的手段之一,她通過將長發(fā)掛出窗外來吸引王子的到來,可悲的是,這個時代根本沒有人敢自詡“王子”,爬上窗來與“公主”相會。童話里英勇的王子也被降格為一個無業(yè)游民——保羅。除了擁有貴族血統(tǒng),保羅與傳統(tǒng)王子的形象大相徑庭,他整日無所事事,在修道院里廝混度日,最后出落成一個觀淫癖。同樣地,敦厚的小矮人也不復存在,巴塞爾姆把他們滑稽模仿為真正的精神侏儒,一群在焦慮中度日、在偏離常規(guī)的道路上一意孤行的“酷兒”群體。他們從事著刷洗樓房和生產嬰兒產品的工作,因為缺乏男性氣概而陷入“男性焦慮”中,在咒怨中度日。誠如白雪公主所言:“他們七個人加起來,大約只約等于兩個真正的男人”。經典人物歷經輪回投胎到了巴塞爾姆的筆下,成為了不值一提的底層人物,所有的人物濾鏡都破碎了,理想的童話世界坍塌了,后現代社會無法承載傳統(tǒng)英雄人物的價值觀,也無法續(xù)寫“王子與公主從此以后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的美好結局。當經典化了的《白雪公主》被當作垃圾而撿拾回來,翻新后再次使用時,其實也就意味著經典的塌陷[16]。
通過解構敘事規(guī)則和經典人物形象,《巴塞爾姆的白雪公主》展示了另一種“酷兒”形象——解構敘述規(guī)則、顛覆傳統(tǒng)的寫作行為,這一意義上的“酷兒”是動詞性質的。通過解構傳統(tǒng)童話的敘事,巴塞爾姆構建了一個“有毛病的”后現代社會,給讀者帶來了震驚的閱讀體驗。而在新奇的敘事形式背后,隱含著巴塞爾姆對于文學創(chuàng)作的焦慮。如果傳統(tǒng)文學已然無法吸引大眾的目光,那么反傳統(tǒng)的敘事是否就能在浮躁的、瞬息萬變的現代社會中爭得一席之地?又或者,任何“新奇”的文學形式都終將淪為一現的曇花?在這種情況下,作家又當何去何從,是堅持經典、延續(xù)傳統(tǒng),還是甘為商販,販賣“新奇”嘩眾取寵?新的文學形式究竟是作家嘗試的一種挽救,還是一種自甘墮落?巴塞爾姆塑造了一個全新的文學創(chuàng)作的“酷兒”形象,在給讀者提供文字游戲的同時,也闡發(fā)了他身為作家的迷惘與焦慮。
總的來說,《巴塞爾姆的白雪公主》是一部全新形式的男性群像小說。從小說呈現來看,巴塞爾姆的確是酷兒化敘事的高手;從作者意圖來看,巴塞爾姆把對時代的焦慮融入了創(chuàng)作。在塑造異化了的男性形象時,巴塞爾姆也在思考:如火如荼的女權運動發(fā)展至今,男性是否也在這一過程中迷失了方向呢?他們是選擇像保羅那樣為了維護自己的形象被迫“英勇”赴死呢?還是像小矮人那樣拘囿于異化情感,躲避男性職責,只能在隱蔽的浴室里狂歡呢?亦或是像頭頭比爾那樣,試圖掙脫集體意志的壓抑,尋找痛苦的根源,卻因無法找到答案而陷入精神困境?無論選擇哪一條道路,他們的結局都不甚理想。作為一個男性作家,巴塞爾姆不乏對男性群體的關注以及對男性未來生存狀況的擔憂。而作為后現代主義小說家,巴塞爾姆借助碎片化敘事和人物降格處理瓦解了瑪麗蘇童話,給讀者帶來了新奇的閱讀體驗。一方面,這是巴塞爾姆對文學商品化的質疑與嘲弄;另一方面,他也試圖通過新的文學試驗來拯救日漸式微的文學經典。在消費文化泛濫的后現代社會,不僅讀者迷茫了,連作家也迷茫了。
參考文獻
[1]許晶.巴塞爾姆《白雪公主》的敘事策略及其效果[J].河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48(06):152.
[2]蘇珊·S·蘭瑟,胡安江,唐偉勝.我們到了沒——“交叉路口”的女性主義敘事學的未來[J].外國語文,2010,26(03):4.
[3][4][7][12]唐納德·巴塞爾姆.巴塞爾姆的白雪公主[M].南海出版公司,2015.
[5]殷孟霞.無處逃身的公共浴池——米蘭·昆德拉作品“公共浴池”意象探析[J].大眾文藝,2017(02):28.
[6]Susan S.Lanser.Queering Narrative Voice[J].Textual Practice,2018:6.
[8]Wood S E.Masculinity and Cold War Fairy Tales: Eudora Welty,Vladimir Nabokov,Donald Barthelme, and Ross Macdonald[D]. The University of Mississippi,2021.
[9]都嵐嵐.酷兒理論等于同性戀研究嗎?[J].文藝理論研究,2015,35(06):190.
[10]郭夢丹.后現代思想語境下的酷兒藝術概念探析[J].世界美術,2022(01):67.
[11]劉輝.從《白雪公主》看巴塞爾姆解構文本意義的策略及意圖[J].當代外國文學,2007(04):39.
[14]程錫麟.“碎片是我信任的唯一形式”——談唐納德·巴塞爾姆的創(chuàng)作[J].外國文學,2001(03):15.
[15]巴塞爾姆《白雪公主》的敘事策略及其效果[J].河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48(06):155.
[16]巴塞爾姆《白雪公主》的敘事策略及其效果[J].河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48(06):154.
(作者單位:北京郵電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