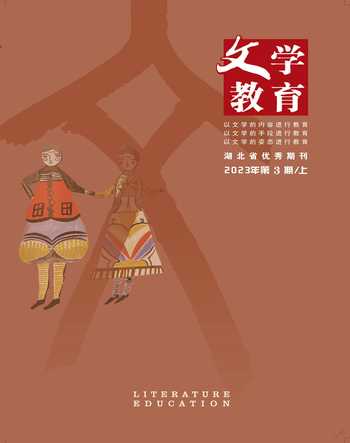錢希言《獪園》鬼怪故事的空間敘事
李俊杰
內(nèi)容摘要:《獪園》中的鬼怪故事展現(xiàn)出了極富藝術特色的空間形態(tài),物理性空間為故事人物的活動提供了廣闊的舞臺,具體的空間意象連接了現(xiàn)實世界與神秘世界,實現(xiàn)了多種空間的轉(zhuǎn)換;心理空間展現(xiàn)了人物細膩而豐富的情感世界,也曲折表達了民眾的思想態(tài)度;社會空間的構(gòu)擬一方面以現(xiàn)實生活為基礎構(gòu)建出冥界的社會空間,另一方面通過現(xiàn)實生活的片段展現(xiàn)市井生活的面貌。三種空間形態(tài)相互作用,共同推動敘事的進程,構(gòu)建出了一個詭譎奇幻的藝術空間。
關鍵詞:錢希言 《獪園》 空間敘事 空間類型 文化心理
有明一代的志怪小說并不十分發(fā)達,直到明代后期才出現(xiàn)專門的志怪小說,明代作家錢希言的《獪園》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錢希言原先字象先,后來因避祖諱而改字簡棲,江南常熟人,年少時家里遇難后在吳縣避難,被人們稱為“山人”[1]2。《獪園》中涉及神仙方士、佛道名家、奇鬼精怪,更有寺塔古跡、冥府禮制、民間風俗、奇聞異物等等,內(nèi)容豐富,覆蓋范圍較廣。其中的鬼怪故事有著鮮明而獨特的敘事風格,最突出的是對敘事空間的把握與運用,多種空間類型在故事中不僅發(fā)揮著重要的敘事功能,也營造出別樣的藝術境界。
古人很早就產(chǎn)生了時空觀念,也認識到了時間與空間的共存與統(tǒng)一。本文中所說的“空間”并不完全等于“環(huán)境”或“場景”,它“包括了作品中靜態(tài)的空間風貌和動態(tài)的空間轉(zhuǎn)換,還包含了潛藏在小說中的各種空間現(xiàn)象背后的民眾的空間意識和空間觀念”[2]176,更包含了民眾在空間中投射的文化觀念和社會心理。本文將從物理空間、心理空間和社會空間三個方面入手分析《獪園》鬼怪故事的空間敘事特征,并勾畫出民眾的心理狀態(tài)與思想觀念。
一.《獪園》中鬼怪故事的物理空間
空間和時間被視為小說敘事也包括其他領域的敘事必不可少的結(jié)構(gòu)要素和故事的存在形式,空間因素和時間因素對于故事場景的塑造有著極為重要的作用。古代小說的“空間”,主要是指小說當中包含著人物與故事的地域片段。古代小說空間的地域內(nèi)容是承載人物活動的處所,它規(guī)定了人物活動和故事發(fā)生的空間范圍,是小說中一切矛盾和事件的地理落腳點。這種地理落腳點是真實可感、實實在在的,是一種物理性的空間意象,《獪園》中鬼怪故事的物理性空間具體表現(xiàn)在三個意象:一是郊外的墳地;二是水邊與橋;三是家宅。空間不僅僅交代了故事發(fā)生的地理位置,更隱藏著深層次的文化含義,時間與空間的相互作用更能夠幫助推動整個敘事的進程。
(一)郊外的墳地
古代施行夜禁制度,夜禁制度的施行使得黑夜活動和郊外活動都具有了反常規(guī)的性質(zhì)。夜禁制度是指古代統(tǒng)治者管理臣民作息,對夜間活動實施管控的社會制度。夜禁制度為黑夜活動和郊外活動賦予了反常規(guī)的性質(zhì),黑夜活動和郊外活動很容易陷入無序的、不受控的狀態(tài),民眾在這種失控的狀態(tài)中自然而然產(chǎn)生恐懼,相應地就會將那些難以理解的、無法解釋的現(xiàn)象歸結(jié)于鬼魅作祟。
古人認為“肉體的死亡并不意味著生命的終結(jié),而是生命形式的轉(zhuǎn)化”[3],人死后將以新的形態(tài)存在著,并前往另一個世界開始新的生活。墳墓是死去的人與現(xiàn)世的人之間唯一可以溝通并產(chǎn)生聯(lián)系的紐帶,是活著的人能夠真切接觸和感受到的。墳墓的外形特征在朦朧的夜色下很容易使人聯(lián)想到人的形態(tài),更容易將內(nèi)心的恐懼外化成鬼魅的出沒。以《鬼產(chǎn)收生》一篇為例,講述的是吳江縣八尺鎮(zhèn)的接生婆,晚上有人請她去接生,待接生回來時已天亮,回望接生的地方卻什么都看不見,“但有雙墳拱木”,自己身上沾滿青泥,“摸袖皆得紙錢”[1]443。夜間朦朧模糊,對冢墓幻象有遮蔽作用,從而為人鬼交往提供了合適的場景,以房屋形態(tài)出現(xiàn)的冢墓在夜色的遮蔽下不容易被識別出原貌,這就使得不明實情的凡人貿(mào)然誤入,而到天色微明的時候,視野開闊后回望夜間的房屋就會發(fā)現(xiàn)只是墳冢。
郊外的墳地屬于故事場景中的空間因素,朦朧模糊的黑夜屬于故事場景中的時間因素,物理性的空間借助于特殊的時間營造出獨特的敘事效果,古代的社會制度為郊外活動賦予了反常規(guī)的效果,墳地因為其特殊的連接紐帶的身份被披上了神秘恐怖的外衣,因此,郊外的墳地這一物理性空間就蘊含了深刻的文化內(nèi)涵和復雜的社會心理,這一物理性空間巧妙融合在鬼怪故事中就營造出獨特的敘事效果。
(二)水與橋
水邊遇鬼是《獪園》“奇鬼”一卷中最為常見的例子,與水相關的空間常常與鬼產(chǎn)生聯(lián)系,可見,水在民眾的觀念里有著十分重要的內(nèi)涵。“水鬼是民間傳說中常見的鬼怪,他們或是意外溺水而死,或是在水中自殺,他們無法投胎轉(zhuǎn)世只能游蕩在水底,只能等待合適的時機引誘活人并將其拉入水中溺死,以此來尋找自己的替死鬼,而后自己才能轉(zhuǎn)世投胎。”[4]144-155水中的鬼和岸上的人形成了一種鮮明的對立,人居住的空間是從下至上延伸的,是人們熟悉的能夠掌握的領域,而水鬼居住的空間是“從上至下延伸的”[5],對人而言是完全陌生的未知的且無法掌控的領域。與人無法在水中施展力量相反,鬼的形態(tài)變化萬千,他們無論是水中還是岸上都能夠施展力量,而身處水邊于人而言是極其危險的。以水為界構(gòu)成兩種境界的分隔,《鬼產(chǎn)收生》中渡過河就從人間來到了鬼的生活區(qū)域,水將兩種領域區(qū)隔開來,一邊是熟悉的人間,另一邊則是陌生而充滿危險的冥界。有水流的空間構(gòu)成了《獪園》中鬼故事的重要敘事場景,這一物理性空間蘊含著豐富的心理與情感。
橋與水是不可分割的,橋構(gòu)成的獨特空間與水一樣有著重要的敘事作用。《百歲骷髏》一文,沈流勛走在路上聽見有人呼喚他的姓名,四顧無人只看到沙岸邊有一具枯骨,便將枯骨踢下水溝,唾之而去。幾天后準備乘船入城,遇見一位白衣老翁,就是那具百歲骷髏所變,沈流勛苦苦哀求以得原諒,老人便相約一起向西行,主人公沈流勛過橋后進入了冥府,看見冥府“大闕廣殿,煥然丹碧”,橋的一端有鬼“披枷帶鎖如死囚狀”,而后被已故婦人“推墮于橋下”,“歘然驚寤”,便回到了現(xiàn)實世界。橋在這里不僅僅是實體的用于過河的橋,更是聯(lián)系陽界與冥界的虛擬的橋梁,橋的一端連接著冥界,一端連接著現(xiàn)實世界。周星在《境界與象征:橋和民俗》一書中指出:“橋及其周圍地區(qū)即橋場,在空間上具有境界的特殊性,這是因為河是境界,橋也是境界。從平面上說,河構(gòu)成了境界的分隔,橋構(gòu)成了境界的聯(lián)系。橋場境界的基本意義在于它是兩個不同世界及其象征或意識間的媒介、通路和中轉(zhuǎn)之所。”[6]174-175橋象征著從一種狀態(tài)、情境向另一種狀態(tài)、情境的過渡與轉(zhuǎn)換,橋的兩端都隱藏著未知的危險,而橋下深不可測的水域更是人們恐懼的來源之一,所以,無論是作為分隔陰陽的水還是作為聯(lián)系陰陽的橋,都成為奇鬼故事中獨特的敘事空間。
(三)家宅
《獪園》中有大量精怪故事發(fā)生于家宅,龍迪勇在《空間敘事學》中就指出“家宅”在敘事作品中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無疑,在各式各樣的建筑物中,住宅由于與人的關系最為密切,所以常常成為敘事者用來表征人物形象的‘空間意象……只有‘家才是構(gòu)成我們個性的物質(zhì)性的空間框架。”[7]266-267在“家宅現(xiàn)精怪”的故事中,有兩個典型的特征:一是精怪種類繁多,萬物可化為精怪;二是精怪出現(xiàn)的不確定性,事先無法預判。這就為家宅這一空間賦予了神秘性和危險性,人日常居住的空間本應該是安全的、具有保護性的,可精怪的出現(xiàn)使得這一空間變得不再安全,精怪出現(xiàn)的不可預知性更是加深了民眾對于家宅的不安與恐懼。此外,原本的家宅是封閉性的,人的生活區(qū)域只局限在一個有限的空間內(nèi),而精怪的出現(xiàn)打破了這一格局。
《蠶化為美女》一文中,寡婦王氏以貞潔著稱,古代婦人貞潔的代價便是與世俗的情欲隔絕,她的生活是完全封閉在家宅里面的,而她養(yǎng)的蠶化為了樣貌端正的美女并凌空而去,這就打破了原先封閉的格局,隨后寡婦也消失了。可以理解為蠶其實是寡婦真實的內(nèi)心寫照,長期被孤獨而封閉的生活壓抑著,她渴望著個性的釋放與情感的抒發(fā)。民眾將精怪的出現(xiàn)放置于“家宅”這一特殊的空間,首先流露出民眾萬物有靈的自然觀,認為身邊的一切事物都可以幻化為有生命有意識的精怪,其次是隱晦曲折地表達了民眾對于世俗常規(guī)的突破,表達了自己想要打破生活桎梏的樸素愿望。
二.《獪園》中鬼怪故事的心理空間
與物理性空間相對的是心理空間,心理空間在某種程度上就是心理狀態(tài)的反映和折射,因其內(nèi)在性而顯得神秘和深不可測,具有精神性的特征。這里所說的心理空間指的就是主體心理在現(xiàn)實空間的基礎上通過想象創(chuàng)造出來的想象性空間,想象性空間可能是特定的心理空間情境類型,也可能是隱喻性的心理空間場景。《獪園》中鬼怪故事的心理空間具體表現(xiàn)在兩個方面:一是奇幻的夢境;二是奇特的幻想。
(一)奇幻的夢境
夢境是典型的心理空間,相比于現(xiàn)實空間的有限性,夢境是無限延展的空間,對于人的精神和意志來說是自由的。《獪園》的鬼怪故事中也巧妙運用了夢境這一心理空間,如“奇鬼”一卷中的《竹林冤鬼》一篇,故事講述的是處州的侍御獻可年少時在除夕夜那天夢見自己在大石橋附近的竹林遇見兩位白衣婦人拿著訟牒跪求洗刷冤屈,十年后,侍御路過一處地方就如十年前的夢境一樣,兩位白衣婦人從竹林中走出來陳述自己的冤屈并呈遞訟牒,訟牒中記錄的她們死去的時間恰好是在十年前的那個除夕夜,后來在侍御的幫助下為她們澄清了當年的案件,也洗刷了冤屈。夢境屬于超現(xiàn)實的心理空間,在“替鬼洗冤”的情節(jié)模式中穿插進了“冤鬼托夢”的情節(jié)單元,敘事空間就得以延伸——從現(xiàn)實世界延伸至心理世界,作者也有了更多自我發(fā)揮的余地。夢境是完全虛擬的空間,不會給人帶來任何實質(zhì)性的傷害,冤鬼入夢且用十年的時間等來自己沉冤得雪,這種情節(jié)模式安排冤鬼故事也恰恰反映了作者對于社會不公的批判,現(xiàn)實中訴求無門而只能求助于虛幻的夢境更是對社會現(xiàn)實的強烈諷刺,民眾講述冤鬼故事更多的是表達自己對社會公平的渴望。
(二)奇特的幻想
古人認為肉體的死亡并不意味著生命的終結(jié),而是會以一種嶄新的形態(tài)存在——鬼,在萬物有靈的自然觀的影響下,人生活的世界中的任何事物都能夠幻化為一種有生命的、有意識的精靈存在于世界中,于是出現(xiàn)了各種生物和各種器物幻化而成的精怪。在古人的認知與信仰中,這些都是真切存在的,可事實上這些是想象的、精神的、意念的、心理的產(chǎn)物,是一種非現(xiàn)實性的存在。《獪園》的鬼怪故事大多表現(xiàn)為幻想性空間的發(fā)揮,如《討替鬼五》一篇,水鬼與土神的對話被描寫得真切可感:
有某處一土神廟,廟祝夜聞鬼聲。鬼告土神曰:“明日有替代人矣。”廟祝次日候於河濱,將拯溺者。見一少年濯足於河,無恙而返。其夜又聞土神問鬼曰:“何不捉替去?”鬼曰:“其母老,殺之則母必相從以死,某不忍其母子俱亡也。明日有婦人來替代矣。”
又明日,復往候之,果見一婦人過橋,忽暴風起,吹其襆墮水中。婦詣河邊撈取,又不及溺。是夜復聞鬼答土神言曰:“此婦有雙胎在腹,一舉手而戕三命,吾豈忍哉!終當更伺良便耳。”則又明日之半夜,聞有鼓樂騎從之聲,喧填而至。土神告其鬼曰:“上帝憫爾一念之善,敕爾為此地社神,今與某共事地方矣。”[1]414
鬼與神的對話不可能在現(xiàn)實世界發(fā)生,或是作者想象性的發(fā)揮,或是民眾將人的對話想象為鬼神的對話,無論是哪一種情況,都表現(xiàn)為一種幻想性的空間。想象性的心理空間具有明顯的超越性,它們在本質(zhì)上是對客觀物理空間尺度的突破,將主體的主觀情感融入其中從而使文藝文本呈現(xiàn)出超現(xiàn)實的審美感受。故事通過對延展性的心理空間的展現(xiàn),流露的不僅僅是故事主人公的心理世界,更是曲折表達了民眾對行善的渴求。
三.《獪園》中鬼怪故事的社會空間
《獪園》鬼怪故事中除了上文中論述的物理空間和心理空間外,還涉及到社會空間的敘事。社會空間更多的是映射現(xiàn)實社會生活的一面鏡子,《獪園》的鬼怪故事中通過若干社會畫面的展演構(gòu)建出了現(xiàn)實生活的容貌,其中的社會空間主要表現(xiàn)在:一是冥界生活的想象,二是市井生活的勾畫。
(一)冥界
冥界本就屬于人們虛擬的社會空間,與現(xiàn)實的社會空間是截然對立的。可通過現(xiàn)實世界的人從口中講述冥界的生活就可以發(fā)現(xiàn),兩者在社會內(nèi)容上有相似相通的地方。《獪園》“冥跡”一卷,作者通過凡人的視角講述冥府的陳設布置,詳細介紹冥府的官職設計,其中《陸文裕游地獄》一篇:
隱隱望見城郭宮室,俄而至大城,……兩吏便掖之而行。行如霧中,足不踐地。見兩傍皆市井,居民往來貿(mào)易,一同人間。有頃,忽達大王殿前。宮闕左右,侍從威儀,見如王者。凡經(jīng)數(shù)重門,乃是大王所居之處。……王聞文裕至,整簪冕,降階盡禮,傳呼甚嚴。[1]271
簡短百余字,通過陸文裕的視角將冥府的景象展露無疑,講述故事的人及寫作故事的人斷沒有真實地進入過冥府,但是民眾將現(xiàn)實的生活投射到冥界,充分發(fā)揮想象創(chuàng)造出一個完全不存在的世界,而在他們心中這些都是真真實實存在著的。在藝術創(chuàng)作中,人們可以創(chuàng)造出一個想象的鬼并不斷加以豐富,使其不僅具有與人不同的外表,而且在性格、嗜好等方面都具有鮮明的個性特征,此外,還有了“各種鬼名、上下隸屬關系、活動場所等”[8]3。冥界的居民也能夠“往來貿(mào)易”,冥府的宮殿也如王室的宮殿一般——“侍從威儀”,無論是冥界的生活還是冥府的場景設置和人員安排都與現(xiàn)實世界沒有太多差別,民眾將生活經(jīng)驗融入到故事的創(chuàng)作和講述中,可以很明顯地看出來,故事一經(jīng)創(chuàng)作出來就深深烙印了民眾日常生活的痕跡。冥府大殿的恢弘、冥府侍從的威儀、冥界百姓的日常生活等都屬于冥界這一虛擬的社會空間的若干社會生活畫面,通過將現(xiàn)實生活投映并對冥界生活展開想象,就將這些社會生活畫面組合在一起構(gòu)成了冥界這一獨特的敘事空間。這一空間在民眾的想象中是危險的、恐怖的,但是融入了現(xiàn)實生活的片段之后就消解了這種危險與恐怖,而使得整個空間變得真實可感。
(二)市井
市井生活空間在《獪園》的鬼怪故事中展現(xiàn)得并不完整,但是能夠通過故事中碎片化的社會生活畫面勾勒出特殊歷史時期的民眾的生活面貌與心理狀態(tài)。《獪園》“妖孽”卷中有《宅魘》三篇,講述的都是主人公新來到某個地方居住就被妖物纏身,后找來看風水的人一看,或是“發(fā)其屋東頭第七椽下,鑿出以裸形婦人,熾火焚之,出血如縷”,或是“忽見梁上墮下小木偶人,高三寸許,形甚丑獰可憎”[1]476-478,《宅魘》三篇中的主人公都是被巫蠱之術所累,更有《妖術》四篇講述的都是書生修習妖術,從這些故事的片段中得以窺見當時社會上有妖術的傳言,家宅中的房梁上隱藏著巫蠱、文弱的書生卻要修習妖術為害人間,家宅與書生本屬于安全的、不具有威脅性的存在,可在故事中呈現(xiàn)出來的卻是截然相反的,家宅的選址需要靠風水道士的指點,家宅的房梁需要專業(yè)人員雕刻,書生沒有取得功名就只能尋求他法以謀生,這就造成了家宅與書生的不穩(wěn)定性與不安全性。從這種對妖術的描述中就能夠還原當時市民生活空間中彌漫著的恐慌與不安,故事不是從施行妖術的人的角度講述,而是從受害者的角度講述出來,這更多的可能是一種恐懼的投射。這里所展現(xiàn)的市井生活空間指的更多的是市民生活的心理狀態(tài),而不局限于生活的畫面。在社會空間中,不同的生命體驗和不同的價值觀念得以交流碰撞,也正是在這個社會空間中,傳統(tǒng)文化、倫理道德、宗教意識、地域風俗、人情世故等得以展現(xiàn),更是通過這一社會空間構(gòu)建出一個充滿奇幻色彩的鬼怪空間、文化空間,這種文化空間就成為了現(xiàn)實空間的一部分。
四.《獪園》中鬼怪故事的思想內(nèi)涵
故事中的各種空間類型為人物活動提供了舞臺,民眾借助于故事的講述、借助于故事中人物的行為活動傳達的是民眾集體的心理觀念和情感態(tài)度。《獪園》的鬼怪故事中隱含的思想觀念主要表現(xiàn)在一下兩個方面:
一是萬物有靈的自然觀。古人相信鬼怪精靈都是真實地在他們生活中存在著的,《獪園》中塑造了眾多形態(tài)多變、性格迥異的奇鬼形象,也構(gòu)思出了各種生物和物品幻化出的精靈。人們信奉魂魄是獨立的,他們認為魂魄可以通過入夢的方式與人類交流,于是故事中就常常出現(xiàn)托夢的情節(jié),魂魄獨立的觀念便是萬物有靈觀的體現(xiàn)。《獪園》中的精靈種類眾多,大自然中存在的動植物、日常生活中各種器物都可以幻化為精靈,它們都有著超自然的力量,如《宅魘》和《妖術》中就有人借助于精靈的力量來施行妖術以謀取利益,他們將崇敬轉(zhuǎn)化為信仰。對鬼魂的畏懼、魂魄獨立的觀念和對精怪的信仰都是萬物有靈的自然觀的體現(xiàn)。
二是因果報應的命運觀。“宋元明時期,佛教在中國已經(jīng)進入世俗化、民間化發(fā)展的重要時期”[9]23,佛教融入到民間,與民眾的生活緊密相連,也深深地影響到民眾的思想觀念和行為模式,《獪園》中故事大都鮮明地表現(xiàn)了佛教的果報思想,表達了民眾因果報應的命運觀。道教作為中國土生土長的宗教在民眾思想信仰和傳統(tǒng)文化中有著扎實的根基,同時隨著佛教在中國的傳播,也吸收了佛教的思想。佛教與道家密切相關,共同影響著民眾的日常生活和思想信仰。《獪園》中的鬼故事最能展現(xiàn)因果報應的觀念,故事的核心情節(jié)一般都是作惡多端的人被鬼魅纏身進而自食惡果得到報應。宗教思想與文學創(chuàng)作有著密切的關系,作者通過故事的創(chuàng)作或編寫傳達民間信仰的同時,也意在通過故事的傳播起到教化的目的,這不僅僅是作者對于社會民風的期待,更是民眾自身對于宗教思想的認可。
靜態(tài)的空間面貌和動態(tài)的空間轉(zhuǎn)換都潛藏著民眾的空間意識和空間觀念,作者將各種空間的類型融入進敘事中,同時那些碎片化的社會生活畫面又構(gòu)建出各種真實而又奇幻的空間。如果說靜止的空間意象為人物提供了生活的基本物質(zhì)空間和情感與回憶的支撐點,空間意象的運動則為人物行動的位移提供了可能,有力推動了敘事進程的發(fā)展。水域形成了人界與冥界的區(qū)隔,同時水與橋也形成了現(xiàn)實世界與神秘世界的聯(lián)系,人處于這一物理性的空間就可能實現(xiàn)從現(xiàn)實世界到神秘世界的移動,進而通過人物視角的變化實現(xiàn)從物理性空間到冥界的轉(zhuǎn)換。民眾和作者在講述故事和構(gòu)思故事的過程中,通過奇特的想象與聯(lián)想將夢境與幻想巧妙地融入進敘事中,同時也將現(xiàn)實生活畫面投射到想象中,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心理空間和社會空間。一方面,這些空間為故事中人物的活動提供了舞臺;另一方面,這些空間具有的特殊的文化含義為人物的行為和動機提供了背景,也賦予了深刻的文化含義,其表露的是作者的情感態(tài)度和民眾的社會心理。
參考文獻
[1](明)錢希言.獪園[M].文物出版社,2014.
[2]黃霖,李桂奎,韓曉,鄧百意著. 中國古代小說敘事三維論[M].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07.
[3]李虹.死與重生:漢代墓葬信仰研究[D].山東大學,2011.
[4]文彥生選編.中國鬼話[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1.03.
[5]楊正興.新溝村“水猴子”傳說象征內(nèi)涵探析[D].安徽大學,2019.
[6]周星.境界與象征橋和民俗[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10.
[7]龍迪勇.空間敘事學[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5.08.
[8]徐華龍等編著.鬼話連篇[M].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96.05.
[9]姜良存.三言二拍與佛道關系之研究[M].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14.11[10]
基金資助:廣西研究生教育創(chuàng)新計劃項目(XYCSR2021024)“廣西盤古文化符號的生產(chǎn)與傳承”.
(作者單位:廣西師范大學文學院/新聞與傳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