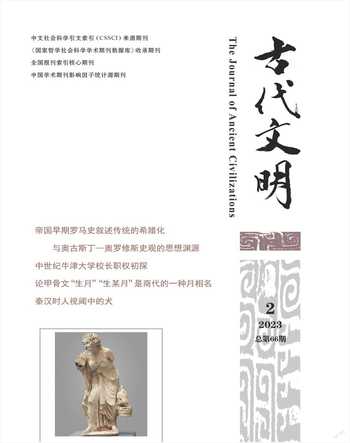論甲骨文“生月”“生某月”是商代的一種月相名



關鍵詞:商代;甲骨文;生月;生某月;月相名
DOI: 10.16758/j.cnki.1004-9371.2023.02.008
關于周代月相名及其紀時形式方面的材料,古代典籍記載和訓詁解釋頗為豐富,歷來學者對此十分重視。20世紀以降,中國現代考古學形成并迅速發展,考古出土、新發現了大量兩周青銅器,古文字和青銅器銘文的研究有了較大發展;同時,歷史年代學和現代天文學的理論方法和技術也在日益更新。在以往研究基礎上,許多學者將新發現材料與古代文獻相結合,對照、考訂與補證,并將新的理論方法和技術應用于周代月相名及其紀時研究中,取得了豐碩成果,使這一古老課題有了突破性的進展。相比之下,盡管殷墟甲骨文自19世紀末發現以來研究成果令人矚目,但是,在關于商代是否存在月相名以及所涉及紀時形式等方面,卻較少有學者問津,這顯然是商代史研究中的薄弱環節。而商代是否存在月相名的問題是極其重要的,探究此問題對于商代史研究無疑具有重大意義,是深入研究商代紀時、歷法、年代學和商代文化現象的一個關鍵點。殷商甲骨卜辭中有“生月”“生某月”之稱,且用于紀時,很可能與月相名有關,可成為探究商代月相名問題的一個重要突破口。
一、舊釋諸說
殷商甲骨卜辭常見“生月”和“生某月”之語,研究者釋說不一。“生月”,起初王國維讀為“之月”,并釋“猶言是月”。當時也有學者將“生月”之“生”誤釋為“之”,讀“生月”為“之月”。此釋曾被早期甲骨文研究者所接受。陳夢家糾正了王國維等釋“之月”“是月”之誤,釋“生月”為“下月”,后來學者多從其說,并將此釋義延伸,認為“生”有“來”義,如徐中舒主編的《甲骨文字典》認為:“生月,即下月之義,與茲月對言,生幾月猶來幾月。”但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釋》指出其不足,認識到“生月”釋“來月”是不可取的:“訓生為來,后世文獻中無用此義者,其說亦未足以厭人意也。”趙誠則認為“生月”表未來時,但確切意思不清楚,同時指出將“生月”釋為“下一月”證據不足,尚不能作定論。后來他又在《甲骨文字補釋》中將“生月”釋為“本月”。蔡哲茂《卜辭生字再探》一文綜理前釋諸說,認為“生月”應表示“來月”,并據古人有關月亮盈虧、死生的觀念補充陳氏等以“生月”訓“下一月”、訓“來月”的理由。蔡先生注意到古代文獻所載月亮盈虧、死生觀念與卜辭“生月”的關聯,“生月”是月光再生的一個月。這顯然較以往研究更深入了一層。常玉芝贊同此說,且認為殷人靠觀察月相確定月首、月長,以月光生出之日,即新月初見之日為一個月的開始。這一觀點對于商代歷法研究和探討紀月、月相問題具有重要意義。
通觀各家釋說,大致分為兩類:一是訓“來”“下一(個)”;一是訓“之/茲(是)”或“本”。此外還有諸多相關釋論(不一一備舉),觀點大致屬于這兩大類,只是具體解釋有所不同。
近二十多年來,關于“生月”“生某月”研究,正式出版刊布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鄧飛的《商代甲金文時間范疇研究》涉及“生月”“生某月”的格式,其“生”的含義仍從前說釋“來”,并無新釋。偶有學者提出“生月”“生某月”屬商代月相,但其釋論甚為不足,未能令人信服。除此之外,一直未有更具價值或令人信服的釋說產生。然而,遍查甲骨卜辭中“生”“生月”“生某月”用法,可知無論是將此“生”釋“來”“下一個”,還是釋“茲(是)”“本”,均不能通徹各條卜辭句義,仍有疑惑、不妥之處。
甲骨文“生月”“生某月”至今也未能得出合理、有可信依據的解釋。而此語在卜辭中頻繁出現,正確理解其時間含義和用法至關重要,這是進一步探究殷商的紀時體系和文化現象的一個重要問題。在全面考察、分析卜辭“生月”“生某月”用法和相關文獻材料的基礎上,本文提出新釋,以期學界同仁指正。
二、“生”無“今”“來”之義
在甲骨卜辭中,“生”直接與時間名詞“月”或“某月”組合時,其義與“今”“來”有別。
“今”“來”與時間名詞組合,起限定、修飾時間名詞的作用。“今”可與“月”或“某月”組成“今月”“今某月”格式 。“來”與“月”也可組成“來月”格式,不過“來月”在目前已發現甲骨文中出現很少,而多見于先秦傳世文獻。“今”“來”也可與時間名詞“日”組合,構成“今日”“今日+干支”格式 ,“來日”“來日+干支”“來+干支”格式。例如:
(1)甲辰卜,亙貞:今三月光乎(呼)來。(《合集》94)
(2)乙未卜:王入今月。(《合集》20038)
(3)貞:今日壬申其雨。之日允雨。(《合集》12939正)
(4)□子卜……母……來四月。(《合集》21093)
(5)乙未卜,爭貞:來辛亥雈匚于且(祖)辛。(《合集》190)
(6)于來日丁亥又(侑)歲伊……(《合集》32795)
“今”又可用于“今夕”,如典賓卜辭《合集》3297反有“今夕其雨,翌辛[丑]不[雨]。”出組卜辭《合集》24769有“今夕雨,至于戊戌雨。戊戌允夕雨。”
“今”還可與“春”“秋”“歲”“旬”直接組合,表示此、今時。“來”也可與“春”“秋”“歲”直接組合,表示“下一個”或“將來”的意思。此外,“今”“來”二詞可一起與時間詞“歲”組合,如“今來歲受年。”(《合集》9653正、9655)“今來歲我不其受年?”(《合集》9654)等例,“今來歲”是今歲和來歲的省稱,表示“今歲和來歲(都)……”。“今”“來”一起與干支日組合,如“今來乙酉”(《合集》4917),是今乙酉來乙酉的省稱,表示“今乙酉和來乙酉(都)……”,其格式為“今來干支1”。但卜辭從無“今干支1來干支2”一類說法,此為語病。
除“今”“來”之外,還有“茲”用于“月”前,表示此月、本月,如無名組卜辭《屯南》345“茲月”。“茲”也用于“夕”前,表示此夕,無名組卜辭《屯南》2300、黃組卜辭《合集》38165有“茲夕”。
再看“生”。“生”直接與時間名詞組合時,專用于“月”或“某月”前,即“生月”或“生某月”,而無“生+日”和“生+干支日”的直接組合用法,也不用于“春”“秋”“歲”“旬”“翌”等時間名詞前。卜辭僅見“生今日”一例,但其句殘缺,難以判斷“生”的確切用法——此例“生”,即使表示時間用法,也并不與“日”直接連接,則“生今日”組合更說明其既無“來”義,也無“今”義。顯然,“生”與時間詞語組合,其用法與表示時間的“來”“今”一類詞明顯不同。
卜辭中有“今”與“生月”“生某月”組合之例。如師賓間卜辭“今生一月”(《合集》6673)、典賓卜辭“今生三月”(《合集》5845)和“今生月”(《合集》15240),這幾例骨片有殘斷或磨泐不清,僅見單句或些許只言片語,尚不能明確其中“生”字是否表示“來”義。而以下卜辭中“生”是否表示“來”義是可以分析出來的:


卜辭中亦有“來”與“生某月”組合,《合集》11562正“貞:來生二月……今……”,但因骨片殘缺,辭句不全,故有他釋,然則,即使該辭不釋為“來生二月”,根據殷商卜辭中“生”專用于時間名詞“月”前而不用于“春”“秋”“歲”“旬”“翌”前,其意思和用法顯然不同于“今”和“來”。可推斷出卜辭“生月”“生某月”之稱是具有特定時間涵義的一種專門用法。
從“今”“來”與“生月”“生某月”組合之例來看,此“生”字既無“今”“茲”“本”之義,也不宜釋為“來”。甲骨卜辭中時間名詞“月”前“生”的用法和意思有別于“今”“來”,并無“本/茲”“來”(下一個)之義。同時,在古代典籍文獻語言及字書、韻書中,“生”均無表示“今”“本/茲”或“來”的含義和用法。
通觀殷商甲骨卜辭,“生”與“數字+月”組合涉及紀月,每個月份均有“生月”——換言之“生月”“生某月”與每月都密切相關,必有其特定含義,應當就是商代的一種月相名稱。下面具體探討這一問題。
三、商代月相名問題與“生月”含義
(一)月相名于傳世文獻和西周金文習見,如“初吉”“哉生霸”“既望”“旁死霸”“既死霸”“朏”等。據傳世文獻、金文和周原甲骨文資料,現已見西周月相名有9種。“某月(月份數)+某月相名+干支日辰”組合,是西周至春秋時期的主要紀時格式,也是周人特有的紀時方式,自成體系。
春秋至戰國時期推步歷法形成,這種月份、干支日辰與月相名緊密結合的紀時形式已顯多余,逐漸淡出紀時體系。但是,這些月相名并未從歷史視野中消失,有的作為月相詞語遺存后世,有的在后世的紀時中仍然被沿用。而關于月相名內容和解釋則常見于古代文獻的記載和訓詁材料中。
(二)由于傳世文獻和金文明確記載有周代月相名(或月相詞語)及其與干支日辰結合的紀時形式,因此,歷來學者一直注重考論和解釋周代月相名問題,而很少探查商代是否有月相名。那么,殷商王朝是否已有月相名呢?

周原甲骨卜辭與殷商甲骨卜辭在字體、用語、行款、鉆鑿形態等方面有明顯區別,顯示出周族卜辭的特色。2月相名“既吉”“既魄”“既死□(魄)”未見于殷商卜辭和商代金文,而與西周金文、典籍文獻中的月相名相吻合,可見在商末或殷周之際周族已經形成了自己的月相名體系。
周初青銅器銘文中出現一些月相名:如西周早期前段成王世的保尊銘(《集成》6003)、保卣銘(《集成》5415)有“在二月既望”,西周早期前段的師衛壺銘(《銘圖》12403)有“唯九月既生霸”, “既望”和“既生霸”均與月份數組合為紀時格式。由于目前發現的周初武王世器銘極少,尚未見其銘文記有月相名的紀時格式。但在西周早期前段器銘中,確實有月相名用于紀時,現已發現的康王世的器銘數量多于武王、成王時期,而用于紀時的月相名隨之增多,有“初吉”“月吉”“既望”“生霸”“既生霸”“既死霸”等。對于周初器銘來說,考察月相名的出現及其紀時形式無疑受到了器銘發現、出土等情況的限制,但不能因此否定武王、成王時期已使用多種月相名的可能性。從周原甲骨卜辭來看,文王至成王時期顯然確已使用了多種月相名。
另外《易》爻辭中亦有月相名,如《易·小畜》爻辭有“月幾望”一語,顯然指月相。以往許多學者認為《易》經爻辭大約產生于商末,是周族筮卦產物,這是可信的。
結合周原甲骨卜辭來看,有些月相名最遲至商代末期已經出現,亦即商末時期的周族方國已經使用多種月相名。很難想象這些月相名是西周初年突然創制的,這是不合常理的,其形成應該有一個較長的過程。
(三)從上古文獻記載看,華夏先民很早已采用觀象授時制歷。《尚書·堯典》曰:“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民) 時。”又曰:“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盡管《堯典》內容摻雜后世追記和改動成分,但所謂“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和以閏月定時成歲(按:西周以前尚無四季之稱),仍然可信。華夏先民通過觀察日月星辰的運行、位置和天象變化而制歷,殷商時期還處于觀象授時的歷史階段。張培瑜等學者據甲骨卜辭、金文和古文獻資料證明了殷商歷法的月確是太陰月(按月相周期確定的月),月的長度是根據觀察月相的循環周期定出來的。常玉芝詳查卜辭資料也認為,殷歷是以太陰紀月、太陽紀年的陰陽合歷,是依靠觀察天象制定的不精確的陰陽歷。這種陰陽合歷,以太陰紀月則需要通過置閏月調整歲時和節氣,殷商甲骨卜辭中有“十三月”“十四月”,顯然采取了年終置閏。不僅如此,以太陰紀月還意味著需要觀察月相變化以確定月數周期,并結合月相變化而定歷日。
馮時通過對偃師二里頭考古材料分析,論證夏商時代陰陽合歷的可能性,據考古發現而為《堯典》涉及的古歷體系提供了印證材料;同時,又從考古學角度揭示了《堯典》古歷體系與甲骨文所反映的商代晚期歷法系統之間明顯存在某種繼承關系。總體來看,古代的陰陽合歷是一種以朔望月與太陽年并行為基礎的歷法,雖然殷商王朝行使的是尚不精確的陰陽合歷,但其以太陰紀月必然是觀察月相變化周期的結果。換言之,殷商時期以太陰紀月不可能不注意觀察月相變化,亦不可能忽視每月份中月相與日序的關系。月相觀念很早已形成,與之相應,也應該有一定的月相名稱較早產生。

《尚書·太甲》曰:“惟三祀,十有二月朔。”其中“朔”為月相名,傳世《尚書》遺存商代各篇被后世言辭、詞語篡改,或為后世追述,故其所記商代太甲時稱月相“朔”是不可信的。藪內清、張培瑜、常玉芝等學者否定了董作賓關于殷歷之月以朔日為首的觀點,而認為殷歷以新月初見(朏)為月首。張培瑜將甲骨文、金文與《詩·小雅·十月之交》《尚書·召誥》等資料對照,證明了至少在周初還是以新月初見(“朏”)作為月首的,殷商取朔為月首的情況是不可能的。他說,由于當時無法觀測或推步朔日,因此殷商歷月是實際觀測月亮確定的,月首以“朏”始,因為新月是可以直接觀測的。常玉芝據古文獻資料和考古證據也認為,殷商時期殷人尚不能觀測到“朔”,仍不能推算出朔日,其歷月以新月初見為月首。

殷商甲骨文和金文中均未見與西周那種“某月+某月相名+干支日辰”完全一樣的紀時格式,一方面,大概由于殷商對月相的觀測和劃分較為粗略,不及后來西周那樣精細,另一方面,在月相名稱和紀時形式方面,殷商與周族雖然有一定相同之處,但也存在許多差異。換言之,學術界通常熟知的西周月相名,在殷商時代多數尚未產生,有的名稱即使已產生,或未用于紀時,或不同于西周的月相名。
“某月+某月相名”和“[唯][王某年]某月+某月相名+干支日辰”是西周的主要紀時形式,其月相名稱自成體系。而在殷商晚期,周族已將月相名用于紀時,周是商朝的一個方國,兩者文化習俗既有區別又有交往、聯系,雖然在月相名的使用、紀時方面存在一定差別,但對于月相的稱名應該也有某些相似之處——或者說,商朝已使用了一定的月相名,只是與周族月相名體系并不完全相同,且在紀時格式上亦有差別。
四、卜辭的用法與傳世文獻的印證
(一)現在進一步來分析“生月”“生某月”。
據殷商甲骨卜辭看,“生”不用于“春”“秋”“歲”
“旬”以及干支日等時間名詞前,也不直接與“日”
組合,而僅與時間名詞“月”組合,形成“生月”“生月+干支日”和“生某月”(生+數字+月)3種格式:
1.“生月”式,如:
(1)癸酉卜,亙貞:生月多雨。(《合集》8648正)
(2)辛巳卜:叀生月伐尸方。八月。(《合集》33038)

(7)癸丑卜:生月毓。(《合補》6860)
“生月”時常寫作合文,見《合集》20074、33038、33068、33916、34120、34489、41302等辭,又有析書。卜辭中紀時月份“數字+月”也常作合文,與析書并存。甲骨文合文由兩字或三字刻寫在一起,在行款上只占一個字的位置,1而非單字(合體字),這是一種以文字組合刻寫形式表示的固定詞語用法,通常用來表示特定稱名的詞以及習語、某些詞語的固定組合關系,如先公、先王稱謂、人名、地名、某月份、數量和單位等,卜辭中合文或與析書形式并存。顯然,卜辭中“生月”合文表示一種時間的固定用法。
又如,前舉《合集》21729一組卜辭有“今生月”,從各辭句中癸卯日與甲辰日均在同年七月的日期關系,可分析出此“今生月”也應在此七月之中,即屬于此七月中某種性質的日期,而且稱“生月”應與“月”的某種性質密切相關。
2.“生月+干支日”式:

很明顯,“生月+干支日”是一種表示時間的組合格式,用于紀日,與西周早期金文“[唯]某月+某月相名+干支日”格式中的“某月相名+干支日”組合結構相近,但西周時期各類文獻不見“生月”“生某月”之稱,卻有月相名“生霸”(如西周早期榮仲鼎銘有“生霸吉庚寅”2)。“生月+干支日”與“某月相名+干支日”近似,“生月”與“生霸”近似,“生月”應該就是殷商使用的一種月相名,此“生”字與月相名“生霸”之“生”同義。
3.“生某月”(生+數字+月)式,如:
(1)癸未卜,爭貞:生一月帝其弘令雷。(《合集》14128正)
(2)庚寅卜:今生一月方其亦有告。(《合集》6673)

(5)婦好不[于]生四月娩。(《合集》13947正)
(6)貞:生五月?至。(《合集》10613正)

(8)戊寅卜,爭貞:王于生七月入于商。(《合集》1666)

(12)壬寅卜:生十月雨。(《合集》6719)
(13)戊[戌卜],王貞:生十一月帝雨。二旬?六日……(《合集》21081)
(14)……生十二月……(《合補》13218)
(15)癸酉卜,亙貞:生十三月婦好來。(《合集》2653)
卜辭中“生+數字+月”組合格式固定,“生”在一月至十三月前均有出現(例(14)為殘片,但仍可辨明“生十二月”)。這種現象,一方面表明“生月”之稱并非某一月的專名(即月名),另一方面說明此“生”與每個月份均有直接的、密不可分的關系——為何有這種現象?卜辭“生+數字+月”組合格式與西周“某月(數字+月)+某月相名”組合形式頗為近似,同時,結合“生月”固定用法和“生月+干支日”紀時格式來看,“生月”和“生某月”顯然與一種月相有關,其用意只能從月相名與每月份的關系中得到解釋。
另外,甲骨卜辭還有疑似“月生”之稱:

圖一: 《合補》9759,《懷特》S0770



圖二:《合集》17055正,《合集》17056,《合集》17057
表一: “黽”字、偏旁“黽”的古文字字形沿革



“月死黽(冥)”是月光消失、死卻狀態,雖然殷人尚不能觀測或推步朔日,但是,通過直觀地觀測月相是可以看到“月死冥”狀態的。“月死冥”之后數日,當又見新月始生,殷人將其定為一個月的開始。商代對于月相階段劃分較為粗略,只是一個大致狀況而已。
(三)進一步考察,殷商甲骨卜辭中的“生月”“生某月”“(某)月死冥”,以及疑似“月生”之稱,與古代文獻中“月生”“生月”“月死”“死月”等詞語相吻合。
《黃帝內經·素問》之《刺腰痛篇》有“以月生死為痏數”唐代王冰補注曰:“以月生死為瘠數者,月初向圓為月生,月半向空為月死,死月刺少,生月刺多。”古人尚不知日月天體運行為宇宙物理的自然規律,而將月光盈虧變化看作月有生死,似生命之生死一般,此種觀念自古有之,月光盈虧變化習稱“月生”“月死”。戰國時期的《鹖冠子·王缺》云:“月信生信死,終則有始。”又《孫子·虛實篇》謂:“日有長短,月有生死。”此語又見出土文獻《銀雀山漢墓竹簡一》67:“……日有短長,月有死生。”馬王堆漢墓出土帛書《黃帝四經·經法》亦有:“月信生信死,進退有常,數之稽也。”古代文獻記載月光盈虧的“月生”“月死”現象,即指月相變化。例如《禮記·禮運》云:“和而后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生月”或“月生”概念則多見于古代的律歷和訓詁中。《漢書·律歷志》:“所謂陽歷者,先朔月生;陰歷者,朔而后月乃生。”《釋名·釋天》:“朔,蘇也,月死復蘇生也。”等等,均為其例。
另,前舉醫書典籍《黃帝內經·素問》提到“以月生死為痏數”以及王冰所注“月初向圓為月生,月半向空為月死,死月刺少,生月刺多。”其中“月生”是指某一月內月初向圓的月相時段,即“生月”;“月死”是月半向空的月相時段,即“死月”。這表明了古人認知中所謂“月生”“月死”的變化觀念其實也就是一種月相變化觀念,并將月相稱之為“生月”“死月”。
“生月”和“死月”之稱以及月有生死的觀念一直延續于后世,例如,唐代《開元占經》引《荊州占》云:“月升(生)七日而弦。”南宋楊萬里《誠齋集》云:“月迫而并焉則月之光不勝日,是以魄而缺烏有所謂死月。”明代徐光啟等撰《新法筭書》學筭小辨記有:“(月)轉西馳兩道違行,是生月孛。孛者,悖也,月轉至是則違。”明代陳言所著《楊敬齋針灸全書》講到中醫針灸時仍承襲古法“以月生死為期”,并云:“……月望巳前謂之生,月望巳后謂之死……”其所言月初生至月望巳前(月望之日夜半巳時前)為月之“生”,月望巳后(月望日夜半巳時以后)至月晦之日為月死。古人將月光盈虧變化看作月有生死,這是一種普遍的觀念,并以月生、月死為月相變化之稱,即“生月”和“死月”,殷商時代觀念亦唯如此。
(四)殷商時代應該已有月相觀念,已發現的殷商甲骨卜辭中有“?”(霸)字,其造字本義為月相之魄。商代雖有表示月相的“?”(霸)字,但或是由于其確未用于紀時形式,或是由于受出土甲骨文、金文材料等內容限制,因而尚未見“?”(霸)的紀時用法。此外,殷商卜辭也未見“初吉”“生霸(魄)”“望”一類月相詞語。值得注意的是,卜辭中出現的“生月”與西周月相名“生霸”頗為近似,又與《尚書·武成》中“哉生明”之“生明”極其相近,此“生”字應該與月相名“生霸”和“生明”之“生”同義。另《古文苑》中班婕妤《搗素賦》有“皎若明魄之生崖”章樵注曰:“明魄,月也。”可見漢代人有時也將“月”稱“明魄”,故“生月”也應有“生明”或“生魄”之義。

約晚商或商周之際,周族已有“初吉”“生霸(魄)”“死霸(魄)”“既望”等多個月相名稱,形成了周族的月相名體系,而與殷商相區別。至西周時期,紀時方式是月份與月相名、干支日辰的結合,以觀測月相為基礎,按月光的盈虧,即“生霸(魄)”“死霸(魄)”“望”等情況,將每月精細劃為幾段,形成“初吉”“朏”“既生霸”“旁生霸”“哉生霸”“既望”“既死霸”“旁死霸”等月相名稱。傳世文獻和金文所見周代月相名是與月份、干支日辰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形成了系統的紀時形式,也就是說月相名主要是作為紀時格式的一項要素出現的,其文獻記載相當明確,而且傳世典籍和訓詁材料對此也有諸多解釋和研究。所以,歷代學者對月相名的認知,主要來自周代月相名體系以及古文獻、后世訓詁資料對其記載和解釋。
至于商代曾使用過的月相名稱,與周代月相名雖有部分相似處,兩者體系卻不同。商代使用的月相名至西周時期有些被廢棄,但從客觀上來看,其名稱或詞語在周秦及以后時期并未完全消失,而是部分地遺存于后世文獻中,如前舉《黃帝內經·素問》《漢書·律歷志》《釋名》等即是。不過,這些文獻中關于月相生死的詞語“生月”“月生”“月死”等,僅見表示月相變化現象,未見其用于紀時的記載;同時,更由于古文獻未見記載、釋論商代月相名一類的內容,且商代金文中亦未見月相名;再者,商代月相名與周代月相名及其紀時形式是不同的體系。由于這些情況,人們受到典籍記載、訓詁解釋以及認知習慣、傳統思路等因素的影響,通常不會著意探究商代紀時月相名問題。殷商甲骨卜辭所見“生月”“月生”“月死黽(冥)”正與傳世文獻相合,特別是卜辭中“生月”“生某月”用于紀時形式,顯然是商代的一種月相名。總之,傳世文獻中的“生月”“死月”等詞語顯現出商代月相名稱遺存于后世的一些痕跡。
以上釋論了甲骨卜辭中“生月”“生某月”是商代的一種月相名。下面進一步討論月相名“生月”“生某月”涉及的主要問題。
五、月相名“生月”“生某月”用法涉及的主要問題
商代月相名“生月”“生某月”表示每月中的日期,涉及兩個方面的主要問題:一是“生月”“生某月”作為一種月相名稱有何特性,“生月”與“生某月”之稱的關系如何,以及“生月”“生某月”與“月生”的不同之處;二是殷商卜辭中“生月”“生某月”所表示的日期,是每月中的定點日期還是多日時段。
(一)“生某月”(“生+數字+月”式)與“生月”之稱的使用特性,以及兩者的關系,可以從同版、同組甲骨卜辭和內容相近的卜辭中進行分析:
(1) a.貞:帝其及今十三月令雷。
b.帝其于生一月令雷。(《合集》14127正)
這組卜辭貞問帝是今十三月“令雷”抑或是生一月“令雷”。雖然是選貞卜辭,但可以分析其中的時間關系:生一月緊接于十三月結束之后,“于生一月”與其銜接的具體月份數“及今十三月”相對而稱,即使不出現干支日,而前后兩月份銜接也可表明月份間的日期關系——“生一月”應是十三月結束后至一月月魄(光)漸生向圓的日期。
(2)辛巳卜:叀生九月伐方。八月。(《合補》10524)

圖三:《合補》10524, 《合集》33038
此為師類卜辭,記錄了在八月辛巳日卜問生九月伐方之事,“生九月”與“八月”相對而稱,是八月結束后緊接進入九月的日期,可知是月相魄生向圓之時,故稱“生九月”。與之內容頗為近似的師歷間類卜辭《合集》33038:
(3)辛巳卜:叀生月伐尸方。八月。
此“生月”應即“生九月”。例(2)“生九月”與例(3)“生月”兩者月相日期都在九月,有義同之處,只是用法上略有所分別——“生九月”側重標出該生月的月份數,而“生月”則對此并不強調。
“生某月”(或“今生某月”)與某一具體月份數相對而稱,特別是在同組卜辭中還有“生某月”與某具體月份數是同月份的情況,通過分析兩者關系可以看出“生某月”是這一月份(同月份)中的日期。例如,師歷間類卜辭《合集》33069:

在丁酉日卜問“今生十月”之事,其后第二日為己亥日,卜問則稱“今十月”,相隔一日在十月稱均“今”,“今生十月”仍屬“今十月”。可見,“今生十月”與“今十月”在同一個十月,只是“今生十月”側重生月日期而特稱“今生十月”,是該十月前段的特定日期,即十月月相魄生向圓的日期。
師類小字卜辭《合集》20797為同版一組,占卜的是同一件事:
(5)a.戊午[卜],貞:子……子不……一月。
b.生一月不。
該組卜辭的兩句卜問均在一月份,從中可以看出“一月”與“生一月”的關系。b辭稱用“生一月”,指的是一月份的生月時間,既可明確是具體月份“一月”,又能明確是該月份中的生月時期。“生某月”與同組卜辭中出現的月份數還有隔月的情況,如典賓卜辭《合集》4070正:

a辭的丁丑日在六月,b辭的丙辰日距丁丑日有39天,那么丙辰日應在七月,可以看出干支日序所在月份與“生八月”的關系。這組卜辭出現紀時隔月的情況,則生月更需要用“生+數字+月”格式表示,用以指明此生月所在的確切月份,即在八月,而不是在七月。
從分析甲骨卜辭可知,所謂“生某月”當指具體某一月份中月光初生向月圓的月相日期,側重于確定生月所在的具體月份數。由此,卜辭中所見一年各月份均有“生某月”之稱便不難理解。“生某月”之稱與占卜時所在月份的關系有3種情況:一是在同一月份;二是在不同的月份,生某月在進行占卜之月的下一月;三是在不同月份,生某月不在進行占卜之月的下一月,而是隔一月或數月。
而“生月”,既可與某一具體月份數相對而稱,也可用于不出現月份數時,并不側重具體月份數。“生月”用于不出現具體月份數的卜辭中時,從各干支日的間隔日期可分析出“生月”在某月中的日期。例如,師類小字卜辭《合集》20470:
(7)丙午卜,其生(月)雨。癸丑允雨。
此句所在的一組卜辭中未出現具體月份數,稱“生月”是對于丙午日所在月份而言的。該卜辭雖未出現月份數,但從干支日的間隔日期長短看,丙午至癸丑間隔7天。丙午日應為某月下旬之日,其后7天癸丑日即在“生月”,是某月結束緊接其后月份上旬的日期,也就是月光漸生的日期。“生月”還可與“今月”對舉出現,例如,師歷間類卜辭《合集》20038:
(8)a.乙未卜:王入今月。
b.乙未卜:王于生月入。
又如《花東》159:

“今月六日”后二字殘缺不清,該卜辭所記為癸未日卜問之事,癸未日在“今月”,其第六日之后則進入“生月”,癸未日應是“今月”下旬某日。
從月相名稱的使用特性來看,“生月”具有泛稱的性質,用于泛指某月月魄漸生向圓的日期,而且“生月”可與“今月”對稱。顯然,稱“生月”用于表示占卜時所在月份下一月的生月,不用于上述隔月的情況,亦即占卜相鄰月份之事,在相鄰月份關系明確的情況下使用“生月”。“生某月”(生+數字+月)則強調某一具體月份數的生月日期,既可用于當月和鄰月,也可用于隔月,特別是同組卜辭中,占卜隔月的生月之事,則要用“生某月”指明生月所在的確切月份。
辨明“生月”“生某月”之稱的月相含義及其使用特性,對于確定同組卜辭中月份間的關系是至關重要的。值得注意的是,當一組卜辭中出現“今生月”或“今生某月”時,而這組卜辭中又出現某月份(“數字+月”或“今+數字+某月”),那么基于對“生月”“生某月”的月相含義、特性的認識,可以判斷此月份與“今生月”(或“今生某月”)在同一月。此外,認識到“生月”“生某月”的月相含義和特性,還有助于還原殘缺的卜辭內容。例如,斷片殘缺的一組典賓卜辭《合集》13740:

該組卜辭中,a 辭句在“今生”與“月”之間有斷片殘缺。f 辭記為“五月”,“卜”前的干支日期雖殘缺不清,但從各辭句義關系看,丙辰日、戊午日相隔二日,f 辭與丙辰日、戊午日所卜之事聯系緊密,所卜為同一組事,其占卜日期與丙辰日、戊午日應該相距很近,當均在五月。據生月的月相含義和干支日序關系,今生月應當在此五月之中,則“今生□月”可補釋為“今生[五]月”。“今生[五]月”與前舉《合集》33069辭“今生十月”相類。
以上辨析了“生月”與“生某月”含義、用法的差別。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月相名“生月”“生某月”的含義、用法與“月生”并不相同:卜辭中的“生月”“生某月”表示某月中月魄漸生向圓日期的時間概念,均為偏正結構的詞,并用于紀時;而“月生”雖然是用作月相名稱的詞語,但只表示月魄生出的現象(一種月相),未見其用于紀時,如前舉傳世文獻中所說“月生”一語表達的即是月魄生出的現象,是主謂結構的動詞性詞組。故月相名“生月”“生某月”的含義、用法并不等同于“月生”一語。
(二)“生月”“生某月”表示的月相日期問題。在殷商時代,“生月”“生某月”這種月相名稱所表示的月相時間是怎樣的?究竟是某月月光初生向月圓的多日時段,還是這段日期間固定的某一天?若要認清這一問題,需要考察、辨析某生月所涉及的前后日序關系,以及某生月與其銜接月份之間的日期情況,且應將這兩方面結合起來進行考察。
首先,觀察卜辭中“生月”后系某一干支日的情況,如:

(3)丙午卜,其生(月)雨。癸丑允雨。(《合集》20470)

表二: 甲骨卜辭中月相名稱“生月”“生某月”及相關詞語的使用功能和特性

這種情況類似西周“某月+某月相名+干支日”格式。殷商卜辭則多見“某月+干支日”格式,觀察如下卜辭:
(4)壬辰卜,五月癸巳雨,乙巳亦雨。(《合集》20943)
此例與上舉例(3)同是師類小字卜辭,“五月癸巳……乙巳……”均指五月中的某一日,這與“生月……癸丑”指生月中的某一日是一個道理。例(3)是說在丙午日貞卜生月會下雨,癸丑這日果真有雨。此例卜問的是生月下雨,而與之對應的驗辭是癸丑這一日果真下雨,但并不意味著此生月僅指癸丑這一日,癸丑是生月中的一日,癸丑日下雨允驗,也表明生月有雨是允驗的,這并不矛盾。類似情況還有:
(1)辛酉卜:今二月雨。七日戊辰雨。(《合集》12509)

師歷間卜辭《合集》12509辭,卜問今二月雨,第七日的戊辰這一天下雨,戊辰日是二月中的一日,此與癸丑日為生月中一日的道理相同。師歷間卜辭《合集》20514辭“二月丙子”則是月份系干支日格式。
分析同一組卜辭中生月與相關各日的關系可以看出,“生月”顯然并非僅指某一固定之日。例如,《合補》10559(即《懷特》1575)的一組卜辭:


圖四:《合集》20470 , 《合補》10559
此例甲午日至辛丑日8天,月相變化階段7、8天,從月望之日時經8天,又為下一月的新月出現,辛丑日至乙巳日5天,月相已生魄。此甲午日至辛丑日相隔8天,甲午日至乙巳日相隔11天,甲午日應在此“生月”之前月的下旬,與辛丑日、乙巳日屬于不同之月,故對于乙巳日所在之月稱“生月”。而此辛丑日與乙巳日應在同一月,相對于上月甲午日來說是“生月”,故在辛丑日卜乙巳,不稱“生月”。
據卜辭中各干支日之間的周期關系,可知“生月”是每月月生明魄之日期,同時辛丑日與乙巳日皆在此“生月”之中,亦可知此“生月”月相并非僅指特定某一日,而是月中的多日時段。
其次,可以從各月份之間的關系分析“生某月”的日期情況。例如,卜辭中有“今某月”,又有“今+生某月”,兩者所指時間有區別:
(1)今一月……(《合集》14132正)
(2)今生一月……(《合集》6673)
(3)生一月……(《合集》14128正)
辭例中雖然都是“一月”,其所指有區別。但是兩者亦有共同之處:均以月份數紀時,“今一月”指現在(此)整個的一月份,而“今生一月”是此一月份月光初生至月望前的時段日期。
前文所舉《合集》21729一組卜辭:a 辭癸卯日與 e 辭、f 辭的甲辰日都在七月,e 辭“今生月”稱“今”必與該“七月”同月,兩者相對而稱均指月份時段,但其專稱“今生月”,看來又與“七月”之稱有分別。顯然稱“今生月”是指該七月中的“生月”時段日期。
再觀察同組卜辭中“生月”與其銜接月份之間的日期情況:


(6)a.弗及今三月?(有)史(事)。
b.乙亥卜,生四月妹?(有)史(事)。
c.乙亥卜,?(有)史(事)。(《合集》20348)
例(4)“茲月至生月”與例(5)“及茲月”“于生月”的用法相類,表示在茲月、至于生月時段。而例(5)“茲月”和“生月”相對舉而言,用法相同,“及茲月”泛指到這一月份的時段日期,“于生月”則泛指在下一月份“生月”的時段日期。類似情況如例(6)a 辭,從“今三月有事”來看,是指三月時段日期有事,b 辭“生四月妹有事”與其對舉,“生四月”與“今三月”表示的日期均為多日時段。
從卜辭紀月時間關系來看,“生月”“生某月”應為某月份中的多日時段,即指每月月首之日新月初生向月圓的月相日期,“生月”與干支日結合時,則指“生月”這一時段中的某一日。
六、余論
商代月相名,除“生月”“生某月”之外還應該有其他,“月死冥”亦為月相之一,另外,殷商甲骨文中有“?”(霸)字,這說明商代人們對月霸(魄)有明確的認識。由于受發現材料所限,目前尚不能確定商代的其他月相名,需要發現更多材料,對商代月相名體系作深入考察和探究。
“生月”“生某月”是殷商卜辭中經常出現的一種月相名,對其使用情況可從兩方面理解:
一方面,“生月”“生某月”表示特定的月相名稱含義,而許多學者將其釋為“來”義(下一個),究其原因在于:甲骨卜辭經常在某月占卜其來月的“生月”(或“生某月”)月相日期的某事情況,“生月”(或“生某月”)是指月光漸生的月相日期,從月份關系看,“生月”日期多為進行占卜之月的下一月(或來月),由于這種情況,“生月”很容易被理解為“來月”。由此可以解釋為何“生月”“生某月”是一種月相名,卻似乎有“下月”或“來月”的意思。
另一方面,商代應該還有其他月相名,但甲骨卜辭僅常見“生月”“生某月”,這與殷人尚白觀念應該有關系,更與占卜、祭祀往往為重要之事有關。“生月”即月生白之相,亦即月魄。《尚書·康誥》陸德明釋文引馬云:“魄,朏也。謂月三日始生兆朏,名曰魄。”又《法言·五百》有“月未望則載魄于西”李軌注曰:“魄,光也。”按這種解釋月魄即指月光。“魄”與“白”音義關系十分密切,月魄即月白,月有光亮的部分即是月白。《左傳·昭公七年》云:“人生始化曰魄”孔穎達引據《孝經說》:“魄者,白也,白,明白。”《白虎通·情性》謂:“魄者,白也。”“魄”與“白”音近義通。自漢代以降,有些學者認為月魄指月望之后月缺無光之處,后持此說者不乏其人。然而從先秦文獻“魄”字用法來看,其音義與“白”相通,“魄”指月之有光、月明有白的部位。
又《禮記·檀弓》謂:“殷人尚白。”《周禮·春官·司常》鄭玄注:“白,殷之正色也。”殷人崇尚白色,以其為正色,祭祀、占卜以及重要象征物皆以白色為崇尚之色。殷人崇尚白色有種種表現。《禮記·明堂位》云:“殷之大白”,此謂殷人于旗幟崇尚白色;又云:“殷白牡”,此謂殷人于犧牲崇尚白色。另外,有的學者認為“殷人尚白”極可能是以白色象征魂魄,殷人認為魂魄為色白。月之色白,象“魄”之色,“生魄”者即生白也,這是殷人尚白的一種表現。《說文》釋霸字云:“月始生魄然也。”即謂始生之月其色淺白如魄之色(魄然)。這不無道理,正與殷人尚鬼神的觀念吻合。
殷人尚白,對于月相亦如此。“生月”即生月之白,生月之明,與《尚書·武成》所謂“哉生明”之“生明”同。“生月”是每月月光初生至月望這段日期,即月初白向圓的日期。卜辭多見占卜“生月”“生某月”之事,在殷人觀念中“生月”是每月中很重要的一段日期,這與殷人尚白的觀念是一致的——殷人在祭祀、占卜中當更注重尚白之物,“生月”即月白之色,故而殷人十分重視占卜“生月”月相時段的事情和現象。按此思路,則殷商卜辭常見“生月”“生某月”月相名也就容易理解了。另外,卜辭有卜問“生”、于生月祭之例,見《屯南》1089等卜辭,殷人重視占卜“生月”之事,除尚白觀念外,還應該與“生”的生出義所涉及的生育、生長等認知觀念有聯系。
總之,探究商代月相名“生月”“生某月”及其紀時問題,對于商代史研究具有重大意義,是進一步研究商代歷法、年代學和商代文化觀念的一個關鍵點。
[作者王曉鵬(1969年—),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山東,濟南,250100]
[收稿日期:2022年11月28日]
(責任編輯:謝乃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