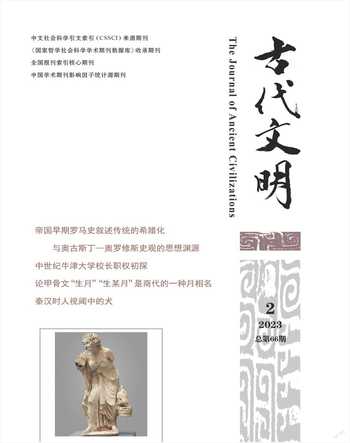秦及漢初外戚的政治平衡作用
關鍵詞:外戚;政治平衡;秦始皇;呂后;沙丘政變
DOI: 10.16758/j.cnki.1004-9371.2023.02.010
一般認為,外戚登上政治舞臺并形成較強勢力,是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發展日漸成熟的結果。盡管外戚自秦漢時期開始在中國歷史上多有消極影響,但亦有其積極貢獻,不能一概而論。秦及漢初作為外戚勢力滋長的關鍵階段,一向受到學界重視。以往學者對秦及漢初外戚的研究,主要是從制度等層面揭示外戚擅權的原因,另有部分研究側重關注具有代表性的外戚人物;而從政治史的角度出發,將外戚置于一個比較長的時段,以充分考察其在政治格局中的作用與影響的研究則相對少見。值得注意的是,當君主對統治擁有絕對掌控力時,外戚其實可以成為維持政治平衡的重要力量。縱觀秦及漢初的政治格局演生,不難發現外戚在長達百余年的時間里持續發揮著作用,并產生了不容忽視的影響。一個很少為學者提及卻又令人頗感意外的現象是,這一時期外戚勢力的興衰軌跡與政權發展的大致走向時常出現重合,其原因值得深入探索。本文就此略作分析,不當之處,祈請方家不吝賜教。
一、秦國外戚維持政治平衡的貢獻
外戚政治作為中國歷史上一種特殊的政治文化現象,始于戰國中后期的秦國。盡管關于秦國外戚,時人范雎曾有“妒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的負面評價,1 但正如《史記·外戚世家》開篇所說——“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2秦國外戚對秦的發展壯大實際也發揮了一定積極作用,尤其是在平定叛亂和維系政權平穩交接方面有其值得稱道之處。
(一)秦國外戚平定叛亂的功績
從秦昭襄王即位到秦始皇統一六國,秦國發生過三次性質嚴重的內亂,即季君之亂、成蟜之亂和嫪毐之亂。其中在平定季君之亂和嫪毐之亂方面,我們可以看到外戚勢力發揮的積極作用。
季君之亂因秦武王死后的王位繼承權而起。由于秦武王沒有子嗣,他死后出現了激烈的權力斗爭,最終武王的異母弟公子稷繼位,是為秦昭襄王。公子稷之所以得立,離不開外戚的助力。史載“昭襄母楚人,姓羋氏,號宣太后”,“宣太后二弟:其異父長弟曰穰侯,姓魏氏,名冉;同父弟曰羋戎,為華陽君。而昭王同母弟曰高陵君、涇陽君”。在宣太后的親族中,最具才干的是魏冉。他“自惠王、武王時任職用事”,在“武王卒,諸弟爭立”的情況下將本不占優勢的公子稷扶上王位。昭襄王二年(前305),“庶長壯與大臣、諸侯、公子為逆”,發動反對昭襄王的政變,又遭魏冉強力鎮壓:“誅季君之亂,而逐武王后出之魏,昭王諸兄弟不善者皆滅之,威振秦國。”
至于嫪毐之亂,則因嫪毐與帝太后私亂生子之事暴露而起。《史記·秦始皇本紀》詳細記錄了叛亂經過:
九年,彗星見,或竟天。攻魏垣、蒲陽。四月,上宿雍。己酉,王冠,帶劍。長信侯毐作亂而覺,矯王御璽及太后璽以發縣卒及衛卒、官騎、戎翟君公、舍人,將欲攻蘄年宮為亂。王知之,令相國昌平君、昌文君發卒攻毐。戰咸陽,斬首數百,皆拜爵,及宦者皆在戰中,亦拜爵一級。毐等敗走。
嫪毐反叛前受命先發制人的昌平君和昌文君,不像魏冉那樣聲名顯赫,《史記索隱》著重就昌平君作了解說:“昌平君,楚之公子,立以為相,后徙于郢,項燕立為荊王,史失其名。昌文君名亦不知也。”另外,在《索隱》對《春申君列傳》的注釋中,亦可見有關昌平君身世的記載:“楚捍有母弟猶,猶有庶兄負芻及昌平君。”針對《索隱》提出的昌平君乃楚考烈王熊完之子的說法,清人梁玉繩在《史記志疑》中曾予以批駁,認為“昌平君之稱,考烈王子,未見確據”,
但他并沒有否認昌平君作為楚公子的身份。考慮到安國君嬴柱系宣太后之孫,其正妻華陽夫人是楚人,根據楚、秦之間長期的聯姻關系判斷,出嫁秦王子的華陽夫人理應來自楚國王室。因此,無論昌平君是不是楚考烈之子,他與華陽夫人都應有血緣關系,他的外戚身份當無疑問。再加上昌平君平定嫪毐之亂時,華陽夫人早已升格為華陽太后,地位尊隆自不待言,此時昌平君(及昌文君)用事,甚至擔任秦相,正是其以外戚身份掌權的證明。否則怎么會平白無故地讓出身楚國王族的昌平君,在危急關頭擔負平定叛亂的重任呢?
由上可見,在兩次動亂中,起到平息事態、保持秦國政治穩定作用的是外戚魏冉和昌平君。就叛亂的發動者而言,公子壯和嫪毐都有很強的個人實力。公子壯能夠任庶長之職,“僭立而號曰季君”,說明他有領兵作戰才能,并且在秦國朝野中具有一定威望;嫪毐在作亂前也處于權勢的巔峰:“封為長信侯。予之山陽地,令毐居之。宮室車馬衣服苑囿馳獵恣毐,事無小大皆決于毐。又以河西太原郡更為毐國。”“嫪毐家僮數千人,諸客求宦為嫪毐舍人千余人。”正因為如此,二者起兵反叛時得以聯合其他多股勢力,造成更大威脅。公子壯發動政變得到大臣、諸侯、公子支持,甚至武王生母惠文后也參與其中;嫪毐的同黨亦多有在秦行政中樞任職者,如衛尉竭、內史肆、佐弋竭、中大夫齊等。可見魏冉和昌平君的對手絕非泛泛之輩,這更凸顯了他們迅速平息動亂的重要功績,即保證了當政者不被顛覆,能夠持續穩定地推行其統治,并且令秦國免于陷入內部紛爭的動蕩局面。當然也必須看到,魏冉和昌平君等秦國外戚之所以能夠順利地平定叛亂,實際憑借的是最高統治者的支持,沒有最高統治者授予的實權,一切便無從談起——我們不能忽視這一基本前提,更不能對秦國外戚的權勢作過高估計。
(二)秦國外戚維系政權平穩交接的作用
事實上,即便沒有發生動亂,外戚在戰國后期秦國最高權力的交接中也起到關鍵作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莫過于華陽夫人——正是她說服安國君將子楚立為太子,并加以大力扶持,從而奠定了從秦孝文王到莊襄王,再從莊襄王至于秦王政的權力交接次序。《史記·呂不韋列傳》:
華陽夫人以為然,承太子閑,從容言子楚質于趙者絕賢,來往者皆稱譽之。乃因涕泣曰:“妾幸得充后宮,不幸無子,愿得子楚立以為適嗣,以托妾身。”安國君許之,乃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為適嗣。安國君及夫人因厚饋遺子楚,而請呂不韋傅之,子楚以此名譽益盛于諸侯。
兼及孝文王即位僅3天便撒手人寰,莊襄王在位也不到3年,故而可以想見的是,在華陽夫人由王后升級為太后的過程中,她還會憑借其權勢地位為秦國王位交接的順利進行提供保證。這從“孝文王元年,赦罪人,修先王功臣,褒厚親戚”,“莊襄王元年,大赦罪人,修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而布惠于民”的記載中便可看出一絲端倪。不管是孝文王“褒厚親戚”,還是莊襄王“施德厚骨肉”,以華陽夫人為代表的外戚勢力都能從中享受到好處。可以說這是外戚與王權的一種相互確認,即外戚為王位交接提供保證,新王掌握權力以后又第一時間對外戚的地位給予肯定。同時在這里也不難發現,“先王功臣”與“親戚”的重要程度相當。一方面,秦國的發展并不單純依賴功臣或親戚(其中主要應理解為外戚,當時秦國的宗室力量過于孱弱),二者皆有其相應貢獻;另一方面,功臣與外戚也存在相互制約的關系。比如當宣太后和魏冉為首的外戚勢力過分膨脹之時,范雎這樣日益受到重用的“功臣”就向秦昭襄王進言:
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單,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
昭襄王于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于關外”。而當嫪毐勢力登峰造極、威脅王權時,受命對他加兵鎮壓的又是外戚昌平君。這也證明秦王政繼位以后,功臣和外戚并為引重的傳統依然延續,最高統治集團通過掌握功臣與外戚間的平衡關系,確保政權在自己的控制下穩健運轉。
毋庸置疑,秦國外戚也有其明顯弊端。前引范雎“聞秦之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之語,便足證秦國外戚的權勢顯赫,這對秦王的最高權威無疑構成了一定程度的挑戰。但總體而言,不論是平定叛亂、保證最高權力順利交接,抑或是與功臣之間既共同為秦國效力又彼此制約的關系,都充分顯示出外戚在維持秦國政權穩定方面的積極作用,令秦國在內部出現問題時得以涉險過關。這也提示我們,秦國外戚看似手握大權,但實際上他們基本處于一種可控的狀態,不會從根本上威脅秦王的統治。誠如孫家洲先生所說:
在出重手整肅魏冉和范雎之前,秦昭王都曾經以賦予高度信任、授予足夠實權的方式,讓他們自以為大得君寵,因而竭力輔政,有效地制造了君王與輔政重臣之間和衷共濟的政治表象。秦昭王對魏冉的四度拜相,就是這樣的籠絡式手段,而力挺范雎“公報私仇”,更是這一統治手法的高明運作。嚴峻的制度制約,輔之以靈活的處理手法,造就了秦國的君臣關系既有“尊君卑臣”的規范,又有和衷共濟的氛圍,避免了出現“權臣”竊弄國柄而出現權力斗爭,招致政局動蕩的局面。
因此,秦國外戚不僅在某些關鍵時刻能夠發揮維持政治穩定的重要作用,而且始終沒有形成尾大不掉之勢。
二、秦朝外戚式微對政治平衡的影響
外戚作為戰國中后期秦國維持政治平衡的重要力量,在昌平君和昌文君之后便從人們的視線淡出,從此銷聲匿跡,史書中竟找不到秦朝外戚的相關記錄。《史記·外戚世家》稱“秦以前尚略矣,其詳靡得而記焉”,以資料匱乏為由將漢以前的后妃、外戚一筆帶過,便是明證。這不得不說是令人驚訝的,也是值得深入思考的。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狀況?我們認為,此系以秦始皇為首的秦國統治階層權衡之后的結果,除了防止外戚擅權,主要原因有三。
其一,這應與秦在消滅六國、建立大一統帝國的新格局下,對外戚勢力進行強力打壓有關。秦統一后外戚的母國已不復存在,如果說在戰國時代,母國多少還能為外戚的活動發揮支撐作用,那么等到六國覆滅以后,這方面的作用也喪失殆盡了。外戚勢力的繼續存在反而會變成一種潛在的顛覆秦帝國的威脅。昌平君反秦就是例證。盡管如前所述,昌平君曾平息嫪毐之亂并擔任秦相,但他在秦滅楚的關鍵時刻背秦向楚,“反秦于淮南”,選擇為了楚國而對抗秦國。這必然會極大影響秦始皇對外戚的態度,他很有可能將外戚一并視作六國殘余勢力。眾所周知,在滅六國的過程中,秦人“墮名城,殺豪俊”,多有摧抑六國殘余勢力之舉。如滅趙后將趙王遷驅至房陵,坑殺與秦王母家有仇怨者,遷趙國豪強貴族于葭萌;滅魏后處死投降的魏王假;滅齊后遷齊王建于共;等等。此外,里耶秦簡、岳麓書院藏秦簡中均有“從人”簡。所謂“從人”,也就是主張合縱抗秦之人。楊振紅先生指出:
“從”意為“合從”“從親”,專指關東六國締結盟約,聯合抗秦。《岳麓秦簡(伍)》013-018簡表明,至晚在公元前228年秦滅趙以后便興起從人獄,故趙將軍樂突及其親屬、舍人均被列為從人,在全國范圍內進行通緝。從人獄波及全國、歷時長久。
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秦始皇對與山東六國聯系緊密的外戚也曾嚴厲打擊,以杜絕六國勢力復辟的可能性。其中,戰國后期屢屢成為秦國政治中優勢力量、表現強勢的楚國系外戚,應當是秦始皇重點打擊的對象。昌平君反秦前被放逐便顯露出了此種跡象。
其二,秦始皇的獨斷專行遠遠超過他的父輩和祖輩。一方面,秦始皇事無巨細皆要親自裁決,正如侯生和盧生所說:“始皇為人,天性剛戾自用,起諸侯,并天下,意得欲從,以為自古莫及已……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于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貪于權勢至如此,未可為求仙藥。”可想而知,外戚勢力對秦始皇的統治而言不是必須的。另一方面,秦始皇對帝國的行政體制也頗為自信,特別是在推行郡縣制方面表現出很大的決心,故而除了扶蘇和胡亥,秦始皇幾乎沒有給其他子女以任何參與政治的機會。盡管丞相王綰曾公開建議立諸子為諸侯王,鎮撫東方;博士淳于越也進言:“臣聞殷周之王千余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但秦始皇不為所動。這不僅使秦“內亡骨肉本根之輔,外亡尺土藩翼之衛”,而且令本就受到打壓的外戚勢力毫無抬頭機會。
其三,史書中關于秦始皇后宮的記載可能被有意刪除了。這一推測同樣基于從秦國到秦帝國的轉變,以及秦對故六國的警惕防備。秦始皇統一六國后,毫不掩飾他對山東六國的鄙薄。在其巡游所立刻石的文辭中,六國君主的殘忍無道和皇帝的輝煌功業總是形成鮮明對照:“六國回辟,貪戾無厭,虐殺不已。皇帝哀眾,遂發討師,奮揚武德。義誅信行,威燀旁達,莫不賓服。烹滅強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極。普施明法,經緯天下,永為儀則。”此外,還有不少在故秦地犯過錯、政績差或者身體欠佳的官吏,源源不斷地被派往“新地”擔任官吏。可見秦始皇既心懷強烈的優越感,又難掩其作為征服者的傲慢。在此種情況下,秦帝國皇室在血緣上與六國的聯系就變得敏感起來。要讓不屑與“六王”為伍的秦始皇承認,他的子女身上其實也流淌著六國血脈,大概是很不情愿的,這也與刻辭中描述的秦與六國勢不兩立、高下分明的情況有較大出入。又兼藤田勝久和李開元先生提出,秦始皇長子扶蘇的生母或出自楚國王室。考慮到秦滅六國,楚國的反抗最為頑強持久,楚亡后楚地流傳的讖言“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及“東南有天子氣”,亦集中反映了楚人對秦的仇視。再加上故楚國幅員遼闊,東南的江淮地區距離秦統治中心比較遙遠,是秦統治相對薄弱之處,是以類似扶蘇為楚王女所生的信息,更需加以隱瞞,不便明確寫在史書中。也許正是綜合考慮過后,為避免對統治產生消極影響,秦始皇下令刪除了史書中有關其后宮的內容。
總而言之,在秦統一六國的歷史背景下,外戚勢力的潛在威脅是秦的統治者無法忽視的。為了杜絕統治集團出現從內部被打破的可能性,確保對六國故地統治的穩定,秦始皇采取了堅決打壓外戚勢力的舉措。也就是說,他寧愿舍棄外戚在維持政治平衡方面發揮的作用,也要鏟草除根,不留后患。秦二世胡亥即位之初所下詔書便多少印證了這一點:
天下失始皇帝,皆遽恐悲哀甚,朕奉遺詔。今宗廟吏(事)及箸(書)以明至治大功德者具矣,律令當除定者畢矣,以元年與黔首更始,盡為解除故罪,令皆已下矣。朕將自撫天下。吏、黔首,其具(俱)行事,毋以繇(徭)賦擾黔首,毋以細物苛劾縣吏。亟布。
同樣是登基伊始,前揭孝文王“褒厚親戚”、莊襄王“施德厚骨肉”,即使是秦始皇本人,也“委國事太后及大臣”,而年紀輕輕的二世皇帝卻在如此重要的詔書中對宗室親戚只字不提。這恐怕絕非偶然或疏忽,而很有可能是對先前秦始皇的某種既定路線的繼承和貫徹。
我們認為,外戚式微造成的負面影響已遠遠超出秦始皇的預想,在一定程度上也改變了秦朝的政治格局——最顯著的影響莫過于在趙高和李斯篡改秦始皇遺詔,殺害扶蘇、擁立胡亥時,朝野中缺少了重要的制約力量。這使趙高和李斯在發動政變前少了許多顧慮。趙高說:“今上崩,未有知者也。所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實也確實如此。手中并無軍權的謀逆者,在政變過程中竟沒有遇到多少阻力,僅憑一封璽書就將扶蘇置于死地,這不禁令人想起同樣“矯王御璽及太后璽”為亂,卻被昌平君、昌文君挫敗的嫪毐。只可惜趙高和李斯謀逆時,已經不存在能夠有效制約他們的外戚勢力了。實際上,縱然沙丘政變是場政治陰謀而非明目張膽地起兵造反,也并非沒有可疑之處。比如蒙恬就曾提醒扶蘇:“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將三十萬眾守邊,公子為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即自殺,安知其非詐?”甚至趙高自己也承認:“夫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故而假如扶蘇身后有支持他的外戚勢力存在,趙高、李斯矯詔前或許就要仔細權衡一下輕重,他們逼迫扶蘇就范也不可能只是憑借一封璽書這么簡單了。以趙、李二人的實力而言,即便成功一時,也很難保證胡亥可以順利登上皇位并掌權。總之,盡管沙丘政變的發生可能與許多因素有關,但外戚勢力在該事件中的缺席及其影響仍然值得關注。
進一步而言,即便對秦二世的統治來說,外戚勢力式微也是相當不利的。秦二世對同父的兄弟姐妹大開殺戒,說明其統治地位并不穩固,參照秦昭襄王的先例,爭取外戚勢力的支持本是實現政治平衡、鞏固統治的有效途徑之一。然而,揆諸史實,我們卻看不到任何外戚的身影。秦二世從始至終倚仗的都是趙高等人,直到最后身死其手,似乎都別無選擇。
三、漢初呂氏外戚的勃興與政治平衡
伴隨著秦漢交接,還有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前揭秦為鞏固新興大一統帝國采取了嚴厲打擊外戚勢力的舉措,可同樣是在大一統的格局下,為什么繼起的漢帝國卻很快出現呂氏外戚干政的情況?就其根本而言,我們認為這應與漢吸取秦亡的歷史經驗和教訓,重新回歸戰國后期秦國奉行的功臣與親戚并為引重的路線有關。《漢書·諸侯王表》:“漢興之初,海內新定,同姓寡少,懲戒亡秦孤立之敗,于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余邑,尊王子弟,大啟九國。”在漢初形成的內倚功臣、外封同姓諸侯王的政治局面中,呂氏外戚因為具有開國功臣和宗室外親的雙重身份而居于十分特殊的地位,這也為其勢力的滋長提供了便利。
一方面,呂氏家族在漢朝奪取天下的過程中貢獻頗多。
首先,呂后本人就是漢的功臣。劉邦起初亡匿“芒、碭山澤巖石之間”,正是呂后投合“東南有天子氣”,稱“季所居上常有云氣,故從往常得季”,為劉邦在政治上的興起制造輿論;“佐高祖定天下”后,呂后又親自參與對異姓諸侯王的誅殺,“所誅大臣多呂后力”。
其次,呂后的親族亦不乏因功封侯者。呂后的兄長周呂侯呂澤,便是漢高祖麾下的得力戰將。《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記載呂澤“以呂后兄初起以客從,入漢,為侯。還定三秦,將兵先入碭。漢王之解彭城,往從之,復發兵佐高祖定天下,功侯”。可見呂澤不但戰功顯赫,為漢定鼎天下發揮過關鍵作用,而且手握重兵,甚至其行動還享有相當獨立性。呂后的另一位兄長呂釋之,也因“擊三秦”“奉衛呂宣王、太上皇”得封建成侯。至于呂后的妹夫舞陽侯樊噲,更是劉邦集團無可置疑的核心成員之一。
由于同屬功臣集團的緣故,呂氏外戚與許多朝廷重臣的關系密切。譬如在太子劉盈的廢立之爭中,呂氏外戚就得到張良、周昌等人的支持。功臣集團之所以力主立劉盈為太子,其中一個原因便是呂氏外戚并非攀龍附鳳之徒,而是有實打實的功勞的。他們深知日后呂后在超拔自己親族地位的同時,多少也會照顧到其他功臣的利益。是以當呂氏外戚邁開擴張勢力的腳步時,功臣集團的反對力度是很微弱的,甚至還有人報以逢迎的態度。故此,也才會出現“大臣請立酈侯呂臺為呂王,太后許之”,呂后隨即下詔“差次列侯功以定朝位,藏于高廟,世世勿絕,嗣子各襲其位”的情況。這既是呂氏外戚與功臣集團的利益置換,也是一種心照不宣的默契。
另一方面,呂氏外戚對平衡守內的功臣和居外的同姓諸侯王也有重要價值。
漢初功臣集團在政治和經濟上擁有強大勢力:“有其功者上致之王,次為列侯,下乃食邑。而重臣之親,或為列侯,皆令自置吏,得賦斂,女子公主。為列侯食邑者,皆配之印,賜大第室。”盡管漢高祖在位期間消滅了絕大多數異姓諸侯王,并代之以同姓諸侯王,但是功臣集團的力量仍然十分壯盛。據《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除去宗室和外戚,漢高祖時因功封侯者多達137人。考慮到宗室力量的分布并不集中,單純依靠東方的同姓諸侯王可能導致中央出現內部空虛的漏洞,而沙丘政變已經證明,對權臣不加制約是極其危險的——呂氏外戚的作用由此得以凸顯。《漢書·高帝紀》記錄漢高祖離世前,呂后曾問及其身后的安排:
“陛下百歲后,蕭相國即死,令誰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余,然難以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
可見在確定未來主政大臣人選及執政次序的問題上,呂后是得到漢高祖授意的。漢高祖一來期望呂后與功臣和衷共濟,二來將用人的最高權力交予呂后,亦表明他欲通過呂后約束功臣,起到“安劉氏”的作用。趙翼云:“孝惠既立,政由母氏,其所用曹參、王陵、陳平、周勃等,無一非高帝注意安劉之人。”呂后順利踐行漢高祖意旨的背后,實際體現了她對功臣精確有效的控制。雖然漢高祖逝世后,呂后曾與審食其密謀“諸將與帝為編戶民,今北面為臣,此常怏怏,今乃事少主,非盡族是,天下不安”,但我們認為,這只是呂后因為即將獨當大局,前途叵測,一時恐懼的情緒流露。
次及漢惠帝駕崩,由于其太子的來歷不明,呂后自覺地位受到威脅。為了維持朝中力量的均勢,尤其是制衡功臣集團,呂后遂廣立諸呂為王侯。侍中張辟強曾向丞相陳平建言:“帝毋壯子,太后畏君等。君今請拜呂臺、呂產、呂祿為將,將兵居南北軍,及諸呂皆入宮,居中用事,如此則太后心安,君等幸得脫禍矣。”是知呂后最大的心腹之患正是功臣集團,而賦予諸呂權力,令之“居中用事”,能夠有效緩解呂后的憂慮,呂氏諸王無一之國也正是因應于此。自高后元年(前187)四月封呂臺為呂王,至高后八年封呂通為燕王,呂后共封立呂氏七人為王、九人為侯,包括“追尊父呂公為呂宣王,兄周呂侯為悼武王”。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具律》更是明確記錄了優待呂氏子弟的法律條文:“呂宣王內孫、外孫、內耳孫玄孫,諸侯王子、內孫耳孫,徹侯子、內孫有罪,如上造、上造妻以上。”《史記·外戚世家》這樣總結當時的局面:“及孝惠帝崩,天下初定未久,繼嗣不明。于是貴外家,王諸呂以為輔,而以呂祿女為少帝后,欲連固根本牢甚。”呂思勉先生也說:“內任外戚,外封建宗室,此漢初之治法也。”有鑒于此,我們不能簡單地認為“王諸呂”僅僅就是為了呂氏一家之私,酈寄所說的“呂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諸侯皆以為宜”,其實也不盡為虛言。在當時特定的背景下,因為呂后的存在,呂氏與漢家的利益在某種程度上是具有一致性的,“王諸呂”確實為鞏固漢的統治發揮了一定功用,這一點不能輕易否定。
總之,呂氏外戚既憑借其功勞躋身漢的開國功臣行列,與一眾漢的股肱之臣關系密切,又因宗室外親的身份,而有機會在制約功臣集團的過程中進一步提升其地位。再加上“為人剛毅”的呂后長期執掌大局,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漢初呂氏外戚的勃興。
不過,應該看到的是,呂氏外戚的權勢與西漢中后期及東漢的外戚不可同日而語,即便他們侵奪了部分功臣和宗室的利益,也難以徹底壟斷漢初的朝政。有學者指出,呂氏外戚擺脫不了劉姓皇權的附庸地位,“他們的勢力僅僅局限于中央統治的上層,而在地方上是沒有根基的,因而呂氏集團自始至終沒有能夠形成足以駕馭整個局勢的力量”。呂后雖然在“擅廢帝更立,又比殺三趙王”等事上恣意而為,但治國理政不敢稍離漢高祖時期的既定路線。呂后統治期間,漢的兩大支柱力量——功臣和宗室的地位未曾受到根本性動搖。固然呂后稱制后,呂氏外戚勢力膨脹,令其雙重身份屬性逐漸褪色,自外于功臣和宗室集團,儼然成為左右帝國的第三股勢力,但呂氏外戚實際并不具備同功臣和宗室集團抗衡的實力。《史記·荊燕世家》載齊人田生語:“今呂氏雅故本推轂高帝就天下,功至大,又親戚太后之重。太后春秋長,諸呂弱,太后欲立呂產為呂王,王代。太后又重發之,恐大臣不聽。”故呂后一死,破壞平衡的呂氏外戚立即被功臣和宗室集團聯手消滅,便完全不可避免了。
四、結語
綜上所陳,自秦昭襄王即位到秦始皇統治前期,憑借最高統治者的強有力支持,外戚在平定叛亂、保證權力順利交接以及制約權臣方面發揮著持續性作用。但秦統一后,這樣一種歷史傳統被人為地打斷。雖然經過認真剖析,可以發現當中有其迫不得已的原因,但外戚的式微依然給秦帝國造成不利影響,即導致了政治上的失衡和危機來臨時應變能力的欠缺。從宏觀的圖景來看,盡管歷史在秦統一后進入了嶄新階段,但新興的大一統帝國與戰國之間依然有太多聯系,可謂打斷骨頭連著筋,強行割裂便難免有得必有失。抑制外戚勢力既體現了帝國為走出戰國時代所做的努力,也成為趙高和李斯在沙丘陰謀得逞的原因之一。
迄于漢初,統治者吸取秦短祚而亡的歷史教訓,重新回歸戰國后期秦國奉行的功臣與親戚并重的路線。由于兼具開國功臣和宗室外戚的雙重身份,呂氏外戚在呂后稱制期間盛極一時。然而,外戚勢力的過度膨脹同樣威脅統治穩定。當呂氏外戚從平衡功臣和宗室集團的力量轉變為均勢局面的破壞者時,也就不可避免地給國家帶來禍患。盡管諸呂之亂最終得到平息,但呂氏開啟的先聲,為有漢一代層出不窮的外戚專政埋下了伏筆。
縱觀秦及漢初外戚勢力的消長,不論頓衰,還是驟興,背后皆存在種種人為因素的推動。最初的設計總是好的,但道路走到盡頭往往事與愿違,不是自斷雙臂,便是節外生枝。在政治格局的不斷演生中,外戚勢力的此起彼伏,都是早期帝制時代的統治集團不得不進行實驗的結果——這多少也有助于解釋兩漢以后外戚活躍程度逐漸下降的原因。
[作者張夢晗(1988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學報》史學編輯,北京,102488]
[收稿日期:2022年11月13日]
(責任編輯:王彥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