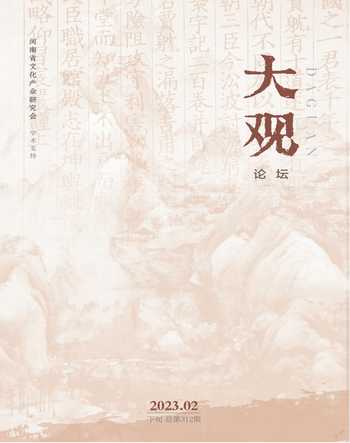細木鑲嵌工藝的歷史探微與當代展望
王玖
摘 要:細木鑲嵌的木畫技藝是中國木質家具史上極為重要的工藝門類,代表了唐代木作在細木作工藝史中的巔峰。以正倉院的唐代木畫器物為例,系統探究傳統細木鑲嵌工藝的歷史發展與革新,進而思索傳統工藝與現代藝術設計的融合,旨在探討細木鑲嵌工藝與當代生活美學的關聯與途徑。
關鍵詞:細木鑲嵌工藝;正倉院;木畫器物;傳統工藝
一、正倉院的木畫器物
正倉院珍藏的數件唐代木畫器物,尤為震撼。這些現存傳世的唐代器物綻放出的高超鑲嵌技藝讓人過目難忘。木畫器物與其他寶鈿鑲嵌器物不同的是,它們基本全部采用不同木材拼接鑲嵌而成,依靠木質色彩和紋理的拼合,形成不同圖案,并形成純平面的裝飾效果。《正倉院考古記白川集》中談到,“中尚署每年二月二日,即進木畫紫檀尺。法以紫檀或桑木為地,雜嵌染色象牙、黃楊木、鹿角等,巧現人物鳥獸花草及各種圖案,窮極瑰麗,或尤勝于螺鈿”。可見,屬于細木鑲嵌的木畫技藝,乃是中國木質家具史上極為重要的工藝門類,代表了唐代木作在細木作工藝史中的巔峰。
正倉院北倉四弦四柱紫檀木畫槽琵琶共5把,其中一把的木畫風格尤為特殊。長梨琴身,其形制為西亞之風,琴面為桑木制,中間部分采用魏晉南北朝時期流行的密陀繪方式,繪制高山流水人物圖。琴的背面裝飾也極其精彩,整體紫檀封底,表面裝飾均勻排列著圓形花紋、四邊花菱紋和六邊花形紋,平鋪在整個琴背,整體風格極其現代化。其雍容華貴的背后是令人嘆為觀止的細木凹槽填嵌技術。
自魏晉以來,西域的貿易往來中,硬木的代表——紫檀被大眾所了解,艷麗而富有變化的堅硬表面成為尊貴奢華的象征,大眾的審美情趣也從欣賞傳統木胎髹漆轉向了欣賞天然木質的優雅質感和紋路。但當時,硬木數量極其有限,能夠加工硬木的技術也屈指可數,且稍大尺寸的紫檀木原料往往芯材空洞,可以被拿來做封面板材的料鳳毛麟角,更多是以表面貼皮或者拼接的方式來制作大面積的器物表面。正倉院中倉所珍藏的木畫箱珍品是滿拼平鑲工藝的代表,由檳榔木、紫檀、黃楊木、桑木、漬紋木等以菱形或龜甲形片狀拼合而成,像是將自然編碼打亂重新組合,營造出強烈的視覺沖擊。
千年以前的木畫工藝不僅能讓大眾領略到大唐藝術的自由絢爛,同時也能為我們今天的時尚審美提供不竭的營養。營造新審美的背后不僅僅是將這些傳統紋樣直接復制到當代設計語言中去,更應該站在歷史的角度,深挖傳統脈絡,總結技藝語言的發展。
二、細木鑲嵌工藝的起源與發展
細木鑲嵌是一種古老的木工技藝,兩河流域的蘇美爾文明和古埃及的馬賽克鑲嵌藝術是它的鼻祖。公元前3000年,人們從古埃及法老圖坦卡蒙陵墓中陪葬的木箱中發現最早使用切削過的烏木與黃楊木塊進行拼接鑲嵌的工藝,之后這一工藝在古希臘時期的小亞細亞地區開始流行。這種工藝擺脫以往受木料的紋理和形體雕刻的限制,單獨依靠不同木色獲得精致華麗和自由多變的表現力。細木鑲嵌一般分為鑲嵌、鑲貼與拼鑲,是將木質裝飾件嵌入木制品或鑲貼在木制品表面、將不同木料進行拼合成型的三種相近的工藝。一般情況下,其統稱為鑲嵌。
古羅馬時期,大量不同色澤的木料通過地中海貿易開始匯聚,在制作工藝上也逐漸成熟,旋切、徑切、弦切、端面橫切與斜切等不同的切割方式呈現出不一樣的木質紋路,豐富的木元素滿足了工匠們不斷推陳出新的圖案設計需求,細木鑲嵌獲得了飛速發展。從中世紀到文藝復興時期,細木鑲嵌工藝一直在意大利南部活躍,其裝飾風格轉向寫實再現,以木質飾面作為畫布的衍生,表現出了真實的明暗變化與空間效果。
歐洲細木鑲嵌技術的真正成熟是在15—16世紀,一種類似阿拉伯風格的復雜鑲嵌工藝得到法國皇室的推崇,這種極為精細的雕刻工藝和運用深淺搭配產生夸張明暗對比的圖案風格很快風靡歐洲。深色的烏木邊框結合胡桃木和橡木中間色調,搭配黃楊木和漂染過后的淺色木料組合成極富空間深度的視覺奇觀,圖案生動,色域極廣,鑲嵌的木料往往需要上千片,最后配以玳瑁、貝母、銅件、鎏金進行高光點綴,富麗堂皇、極盡奢華,形成了今天的歐洲古典家具風格。
工業革命后,大量新型材料和工藝的出現加上大眾消費審美發生轉變,再加上名貴硬木的稀缺和20世紀《華盛頓公約》制定之后環保主義盛行,細木鑲嵌工藝走向了繁華的盛世。目前在歐洲,僅有數家門店利用新興技術和可持續發展的經營理念延續著這門古老技藝。
三、東亞細木鑲嵌工藝的淵源與革新
古老絲綢之路打開了東西方交流的大門,魏晉時期就出現了西域傳來的薄木貼皮技藝,直到唐代,開放自由的時局推動越來越多西域文化進入中原,同時也帶來了大量珍貴硬木。一種包含貼皮技藝和包鑲技術的木畫技藝在唐代盛行,不同于唐代的華麗,宋代相關技藝更有一種貼近自然、和諧優美的意境。特有的文人氣質也將木材中天然連貫的色澤紋路打造為富有氣韻的山水長卷,從而形成了獨有的木器審美情懷。這種傳統審美的轉變致使細木鑲嵌工藝逐漸式微,文人和工匠的追求也從表面的裝飾轉向注重結構美學的榫卯工藝,開啟了獨具中國特色的家具裝飾體系。
在今天很少能看到唐之后細木鑲嵌的珍品,但是日本的組子細工、寄木細工以其他方式延續著這股唐代遺風。箱根寄木細工憑借該地區自然資源,以當地的樹木為例,黃色的有苦樹、漆樹,白色的有水木、西南衛矛,綠色的有日本厚樸,灰色的有連香樹。除了連香樹外,還有櫸樹、榆樹之類樹種,大致呈現灰色,其他還有褐色的樟樹等。這些天然木色在日本被歸為9大色系,分別為白色系、淡黃色系、黃色系、紅色系、茶色系、褐色系、綠色系、灰色系、黑色系。近百種木色和紋理的集合就似一處取之不盡的視覺寶藏。與以往的細木鑲嵌工藝不同的是,寄木細工的工藝集中于馬賽克式元素的“拼”,一般采用規整的幾何形態的徑切條狀木料,按照事先準備的圖案,進行有序的拼接,形成單元組件,然后再將各個組件集合在一起,最后用木刨手工將拼好的多彩大木塊完整地刨出似紙一樣的彩紋木皮。由于木料硬度和紋理不同,裝飾面多為木料的橫截面,所以刨的環節極考驗匠人的技藝和手感。刨下來的木皮被粘貼在木質器物的表面。拼色的樣式一般以連續的直線幾何紋樣為主,顏色以漸變和復雜夸張的明暗對比為主。這種方法制成的產品在之后被稱為“指物”,其特點是刨削獲得的飾面木皮數量繁多,非常耐用。之后寄木細工又出現“挽物”一類,即直接使用拼接好的彩色木料,通過車床將直線拼接的裝飾條紋飾融入曼妙的曲線。
四、細木鑲嵌工藝發展的當代展望
每個歷史時代的造物都會有其不同的社會需求與審美傾向,但對傳統工藝的追問就像是永恒的話題。無論是在工業革命之后的莫里斯提倡的“工藝美術運動”,自然主義美學超越機器生產所帶來的視覺桎梏,還是在20世紀30年代開始的日本民藝運動,都是使手工藝重新回歸,并與工業設計結合,尋找器物生命的靈魂。今天,人們在更快節奏的生活與虛擬化的社會空間中,高頻率地接受圖像化的信息轟炸,越來越缺少能夠將內心沉淀下來的物,而傳統工藝所蘊藏的匠心成了這個時代的心靈滋養品,所以重提民藝是當代設計中的重要指向。當然,純粹回歸傳統并不代表傳統就符合今天的審美和社會需要,相關人員應在追問的過程中,不斷去探討當代藝術設計與傳統工藝之間的巧妙結合。細木鑲嵌自古以來不斷散發的魅力來源于木質材料賦予它的自然屬性——質地溫和的觸感、獨特色澤紋理的觀感,工藝方式賦予它的審美屬性——千變萬化的組合方式,制作過程賦予它的靈魂屬性——細膩的心靈對話。這些魅力并沒有僅留存在博物館,而是持續為當代設計供給營養,不斷地回歸生活。
(一)傳統工藝的技藝升華
對于極致的追求,是工藝的生命,也是匠人精神的真諦。傳統方式的細木鑲嵌在今天依然可以不斷挑戰極限,極盡精微地細膩刻畫,這也是工藝進步的重要展現。百達翡麗的時尚鐘表設計將細木鑲嵌的傳統工藝運用在表盤的制作中,用漫長與精細的制作襯托時間的永恒。工匠們從上百種色澤的天然木料中,根據每塊圖案挑選色澤紋理接近的木皮,手工切割后,在最完美的色塊中進行最挑剔的選擇,然后將上百枚極小的木片進行粘貼拼接、加固、干燥、打磨上蠟,方寸之間乾坤無限、極致奢華。
(二)新技術下的工藝再生
細木鑲嵌中的材料加工方式在今天早已更新換代。新的數控技術已將最為考驗技藝的切割開槽變得方便快捷,目前常用的技術為激光雕刻,其切割精度可達到0.05 mm,但是切割邊緣會有細微灼燒黑邊。一般情況下,采用濕紙張貼在木料表面,再進行激光切割,可減少黑邊。近年來,國內原創品牌端木良錦的細木鑲嵌便采用這種方式復原了正倉院紫檀木畫槽琵琶的工藝,將消失上千年的唐代繁華濃縮在當代器物設計中,引起轟動。新技術并不能全然替代手工,因為工藝的再生復蘇不僅僅是尋找超越時空的美感,更重要的是工藝背后的人文情懷與對工藝重歸生活的向往與尊重。
(三)傳統工藝的當代設計轉譯
轉譯是一種不依據原文語言,而根據其他語言進行的翻譯。“傳統工藝”這個原有詞匯在當代縱橫交錯的設計理念中不斷被鎖定、解構、再創造。細木鑲嵌工藝也被不斷重新編碼轉譯,不斷擴展出跨界的可能。日本寄木細工中的拼木貼皮工藝擴展方式非常廣泛,運用特殊的膠合技術,將華麗的木皮貼在皮質箱包之上,一改以往方正規矩的呈現,這種載體的轉譯可為大眾帶來嶄新的感受。寄木細工的“挽物”工藝在今天也大放異彩,Take-G創作出幻想中的機器人形象,這些雕塑化的形象并不是完全根據平面圖案進行木質拼接,而是根據立體的結構進行定位組合,通過3—5種的木色變化服務于形體的需要,使傳統的工藝突然搖身一變,塑造了極具親和力的科幻玩具。可以說,這個制作工藝方式的“轉譯”相當成功。
(四)細木鑲嵌工藝與當代藝術觀念的結合
自古以來,工藝與藝術都是相輔相成。工藝的進步能夠推進藝術的發展,但是工藝的屬性始終無法逾越人類情感和觀念的表達。工藝在藝術范疇始終被視為材料語言的修煉,而藝術觀念的革新賦予工藝時代意義。今天的日常塑造今日的藝術觀念,當代的藝術觀念重新書寫傳統工藝的魅力。中國臺灣藝術家韓旭東的像素化木雕作品就是將細木鑲嵌工藝與當代木雕結合的典范。木色的拼接并沒有單純按照圖案和顏色進行有序的分布,而是變成大小均衡的方塊組合在一起,構成無序的造型,然后再進行具象雕刻,呈現出一種數碼化的人物形態。拼接工藝背后的藝術觀念蘊含著碎片化的生活與當代人虛幻與孤獨心靈的描述。中國藝術家陳彧凡的作品中經常出現傳統木工技藝,在《衍生物》這件作品中,他將各種顏色的木材按照規整條形下料,在方形畫面中不斷隨機拼接搭建,將細木鑲嵌的工藝解構,賦予抽象的意境,讓拼變成一種風景的再生,隨緣的組合與拼接的內容無關,而更在意拼的過程——一種自然生長的感受。
五、結語
傳統細木鑲嵌工藝像其他優秀的傳統工藝一樣,也許會在某個時代銷聲匿跡,又會在某個時代如雨后春筍一般,持續發展。這一切和時代的生活樣本密切相關,當一項技藝越來越少地進入社會日常生活,它的式微和消亡幾乎是必然的。在今天,越來越多的設計師、藝術家應一改視傳統工藝為枷鎖和負擔的思維,縱情深入這些傳統工藝的研究。民藝和匠人文化正成為時代的強音,正是在這個關鍵時候,如何復興傳統工藝,做出符合時代審美潮流的回應就成為重要問題。簡單的復制已沒有曾經的語境,過度的承載反而會將傳統工藝架在高臺,相關人員應融會貫通地運用當代設計思路與觀念,擺脫浮于表面的單純創意,堅持深入工藝制作一線,切實研習傳統工藝,這樣興許才能提煉出傳統工藝的魅力與自我獨特的當代感知。傳統工藝正從“外在的傳統形態”走向“內在的傳統精神”,為當代器物創作注入靈魂和營養。
參考文獻:
[1]傅蕓子.正倉院考古記白川集[M].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
[2]鑲嵌、鑲貼與拼鑲[J].家具與室內裝飾,1996(1):4-6.
[3]喜多俊之.給設計以靈魂:當現代設計遇見傳統工藝[M].郭菀琪,譯.北京:電子工業出版社,2012.
[4]民藝再造:傳統手工藝遇見當代藝術[J].工業設計,2018(1):155.
作者單位:
四川美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