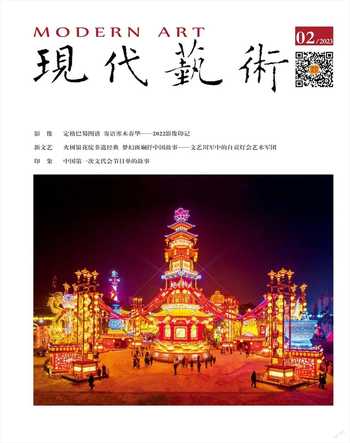以影像交織 顯別具一格
劉詩琪
《萬里歸途》憑借超高的制作能力給觀眾帶來了一場視聽盛宴:硝煙四起的異國他鄉、安危難保的海外僑胞、交流不便的語言障礙、防不勝防的彈藥偷襲、政權更迭的混亂局勢、縱橫交替的鏡頭運動、復雜多變的場面調度、明暗交替的光影構圖、起承轉合的情節變化,體現出影片的張弛有度和豪邁氣勢。
戰爭的的自反性
戰爭不僅是一個政治行為,而且是一個真正的、政治的工具,是政治交往的一個延續,是以其他手段進行的政治交往。《萬里歸途》這部電影則是將鏡頭聚焦于在戰爭中受到侵害的普通民眾:在槍林彈雨中生死未卜的駐外員工、在面對國家政治沖突時手足無措的百姓、被當做種族沖突矛頭的小女孩、強忍著丈夫犧牲的傷痛仍顧全大局的女領導,這一幕幕鮮活的眾生相讓觀眾意識到戰爭對于作為個體的人的災難性,葛瑞琳曾經說過:戰爭是邪惡的,應該被停止;在戰爭進行時,則應該盡己所能,減輕它造成的損害。([英]A.C.葛瑞林.《戰爭的本質》.吳奕俊譯.海南出版社,2020年版.163.)《萬里歸途》通過激烈的戰斗場面最大限度地還原了人若螻蟻、命若塵埃的百姓遭遇:章寧的犧牲讓宗大偉再一次意識到戰爭的殘酷和無情,他質問當地外交官:我的原則就是帶領我們的人民回家,難道我有錯嗎?這種自反性敘事無時無刻不質問著一元論的價值追問:如果我們不終結戰爭,戰爭將終結我們。
童話《一千零一夜》中有一篇《航海家辛巴達》,片中被收養的努米亞小女孩多次吟誦,這篇童話故事的情節發展和電影的情節走向交相輝映,形成一種互文。“人們相互攙扶著,凝望漆黑的海面”對應著在烈日炎炎的戈壁荒漠中徒步的被困人員;機智勇敢的辛巴達隱喻外交官宗大偉,他鋼鐵般的意志、臨危不亂的心態、機智聰慧的頭腦和挺身而出的責任感暗含著英雄的孤光。電影的情節隨著童話故事的敘事而鋪展開去,荒沙大漠中包裹著一個勇敢追夢的浪漫童話,也預示著人們對結束戰爭的美好期待。《萬里歸途》用獨特的視聽語言批判了戰爭的殘酷,表達了對和平的向往。
關注個體敘事的主旋律
主旋律電影是黨和國家進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途徑,也是傳播主流意識形態的重要藝術手段。作為弘揚國家主流價值觀與意識形態的重要工具,主旋律電影還是反映特定國家政治格局、經濟樣態、民族文化的大眾傳播媒介,也與提升國民思想道德素養起到密不可分的關系。
比之于突出激烈戰爭場面的電影,《萬里歸途》的敘事沒有僅停留在宏大的家國敘事,而是專注于在困難面前作為個體的人的主觀能動性及具體的人對于其家庭的重要存在意義。該片通過不同家庭的悲歡聚散寓意華夏兒女建設祖國的崢嶸歲月,使其與觀眾之間形成有效的情感共鳴、喚醒中華兒女的家國情懷與民族記憶。該片以外交官的撤僑工作為主要切入點,將鏡頭聚焦在外交官、中資企業管理者等個體身上,宗大偉經歷了失去隊友的悲痛、被同事誤解的無奈、在反叛軍頭領穆夫塔前的怯懦、無法陪伴妻子與新生兒的愧疚,但他仍不忘外交官這一職業所賦予的使命,在關鍵時刻扭轉時局帶領人們走出荒漠;沒有經過專業訓練的實習外交官成朗從青澀懵懂到顧全大局,從魯莽地與同事頂撞到勇敢地扛起攝像機拯救一支隊伍,他在這個過程中完成了一次個人價值觀的重塑;外企領導白婳在得知丈夫章寧去世后強忍悲痛整理情緒,在整個團隊缺失領隊人心惶惶時站出來作主心骨,在拯救阿拉伯養女與失去自己性命的抉擇時刻挺身而出,彰顯女性外柔內剛的人格魅力。
近年來,國家高度重視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更加自覺地用文化引領風尚、教育人民、服務社會、推動發展。2022年10月1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二十大報告中指出:“增強文化自信,圍繞舉旗幟、聚民心、育新人、興文化、展形象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發展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激發全民族文化創新創造活力,增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精神力量。”《萬里歸途》就是以謳歌人性的光輝、弘揚國家的核心價值觀為基調,體現時代的精神風貌和主流思想,采用多種創作方式,傳播人間真、善、美的電影。這類電影大多以真實可信的中國故事、紅色經典塑造國家形象,以表達集體主義精神等國家主流意識形態的故事為藍本,旨在生產能打動人心、喚起國族意識的中國故事和中國人物,正面或側面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凸顯中國氣派、中國風度和中國形象(何天洋.后現代語境下主旋律電影意識形態敘事策略的變化及成因分析.貴州大學.2007.)。與以往動用國家機器進行軍事撤僑的宏大場面不同,該片較為關注作為普通個體的人,注重刻畫人物內心的情感變化,在展現中國氣派、中國風度的同時高舉人道主義旗幟。
有血有肉的英雄人物
英雄主義是人類社會由野蠻向文明演進的過程中逐漸形成的帶有集體主義色彩的精神價值觀,不僅具有強烈的歷史感、時代感和人格震撼力,同時具有鮮明的民族和國家特色。英雄往往具備堅如磐石的崇高信仰、堅韌不拔的革命精神、平等博愛的人道主義和英勇頑強的戰斗作風;在更本質的維度上,英雄的偉大在于其內心深處永不屈服的生命意志和勇往直前的精神信念。英雄締造著民族歷史、凝聚著時代理想、塑造著祖國形象、象征著國家權威。主旋律電影因其道德性、政治性、傳統性和主導性,其本身系統性和權威性的藝術形態、話語權的闡釋等都與英雄形象類型符號息息相關(范佳佳,劉磊.主旋律電影英雄形象符號化建構的嬗變與發展.《傳媒》,2022年第18期)。在中國傳統主旋律電影的英雄人物設計中,主人公常被打造成不食人間煙火的、完美無缺的高大形象(如勞模、英雄、榜樣等),無疑是對英雄人物的狹隘理解,使得文藝與真實漸行漸遠。
進入新世紀以后,主旋律電影重新明確自身的市場定位,在塑造鮮明的愛國主義、英雄主義、集體主義、理想主義等主流價值之外,更關注作為人的個體敘事與情感表達。有學者認為,個體生命的自由,一方面表現為個體的行為能夠充分地表達自己,另一方面也表現為個體在社會現實中的生存規律。不再刻意回避英雄身上的缺點,而是把它當做一個完整的個體來寫,這不僅符合藝術創作的規律,更能塑造出一個有血有肉、完整立體的英雄形象,英雄的生成空間也在“別現代”這一特殊的社會形態中不斷拓展。《萬里歸途》中的外交官宗大偉出場時的角色設定是一個玩世不恭、性格暴躁、油嘴滑舌的人物形象,面對外交職業的危險性和不確定性,他有明哲保身的退縮與猶豫,也有緊要危機關頭的怯懦與糾結,而章寧的殉職讓他意識到外交官盡職履責的使命感,讓他看到了戰火紛飛的國家中百姓流離失所的現狀,看到了努米亞共和國政權的不穩定和西方殖民主義導致穆夫塔叛亂奪權,這更堅定了他要與白婳一起帶領被困僑胞踏上歸國征途的決心,映照出他具有強烈的家國情懷、社會責任感與職業使命感的英雄弧光。同時,影片并沒有突出單個孤膽英雄的英勇事跡,而是采用英雄群像的方式來構建故事框架,初出茅廬的外交新人成朗與宗大偉相互扶持、共同成長,最后在緊要關頭用一架沒有電的相機震懾住了穆夫塔等恐怖分子,外柔內剛、堅毅果敢的白婳強忍失去親人的痛苦承擔起撤僑的重擔與使命。這部影片十分注重刻畫英雄豐富的內心世界,使得英雄人物更加貼近生活實際也更具感染力。宗大偉在執行外派任務的過程中有兒女情長的牽掛與羈絆,有生死抉擇的膽怯與懦弱,有脾氣暴躁的失控狀態,也有面對朋友之死無法釋懷的于心有愧,但這仍不掩他作為一個英雄在關鍵時刻挺身而出的孤光,他既感受到刻不容緩的鏗鏘使命,又有舍小家而顧大局的心酸之處,由此一個完整立體、有血有肉的英雄人物形象便被刻畫得入木三分——英雄不是遙不可及的超人,而是每一個具體的普通人。
鏡頭調度下的視聽盛宴
《萬里歸途》的開頭運用了一系列簡短有力的畫面轉化,流離失所的百姓、治安失控的居民區、水泄不通的街道、斷壁殘垣的樓房、千瘡百孔的城市、嚴防死守的軍隊、眉頭緊鎖的外交官、被扣押在大使館的異國人民……短鏡頭組接營造了一種緊迫感。這些交替出現的畫面不在一個時間線卻在同一結構體系之中,聲音和畫面交錯出現與觀眾在觀影時的視覺轉移及產生的心理活動相一致,簡略的敘事給人觸目驚心的視覺沖擊,不僅能在短時間內交代努米亞共和國人民的生活現狀,更能給觀眾一種身臨其境的帶入感。安德烈·巴贊指出:段落鏡頭、景深鏡頭和搖拍等綜合性的語言比傳統的分析性的分鏡頭更接近現實主義,同時更智慧,因為它以某種方式讓觀眾通過暗含的關系參與影片表意的過程中([法]安德烈·巴贊.《奧遜·威爾斯論評》.陳梅譯.中國電影出版社,1986年版)。運動鏡頭和手持鏡頭是制造緊張感的重要手段,不僅映照了努米亞共和國風云變化的政治格局和戰火紛飛的壓抑氛圍,也將焦慮不安、緊張惶恐的人物心理帶到銀幕上,攝影充分運用了搖、移、跟等運動鏡頭,拍攝出猝不及防的偷襲場面、四散流亡的無辜民眾、緊急救援的醫療隊伍、與大使館保持聯系的外交人員等,一系列快速切換的戰爭環境和緊張的敘事節奏相輔相成,讓觀眾完全沉浸在這一敘事場景中,感受電影的流動感、急促感、緊張感與刺激感。另外,電影使用大量的景深鏡頭來展現敘事的空間感。如宗大偉找到白婳那場戲,攝像機的機位與被攝主體相隔一個長長的走廊,觀眾可以體會到被拉長的空間縱深感與畫面的信息增量;在宗大偉找到白婳帶領的被困隊伍后,鏡頭跟蹤著宗大偉進行移動的同時巧妙運用景深鏡頭對焦交談的雙方,使用長焦距鏡頭使遙遠的對象在畫面上產生近景的感覺,這樣的鏡頭語言將宗大偉的欲言又止、白婳的隱忍悲痛帶到觀影者的面前,為整體的情節增加了敘事的張力。
“從似真性這一點來說,電影藝術稱得上是一種全方位的感性刺激和身心享受”(陳旭光.《藝術的本體與維度》.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351.),所以通過鏡頭調度、音效景別、鏡頭組接、色彩、結構等藝術手段與技巧讓受眾增強觀影的體驗極為重要。《萬里歸途》憑借超高的制作能力給觀眾帶來了一場視聽盛宴:硝煙四起的異國他鄉、安危難保的海外僑胞、交流不便的語言障礙、防不勝防的彈藥偷襲、政權更迭的混亂局勢、縱橫交替的鏡頭運動、復雜多變的場面調度、明暗交替的光影構圖、起承轉合的情節變化,體現出影片的張弛有度和豪邁氣勢。為了真實還原事件發生地的光線狀態,導演饒曉志回憶道:演員一般要在太陽最為毒辣的正午進行彩排,并在日薄西山之時全力拍攝,在與太陽的追逐角力過程中完成一次光線上的“萬里歸途”;為了再現事件發生的真實環境,劇組歷時4個月搭建出濃縮阿拉伯國家顯著特征的具體場景,并輾轉寧夏、新疆等地的沙漠、戈壁拍攝人跡罕至的荒涼之地——“工程最繁忙的時候動用了差不多一千多人的美術置景組,但是建筑就有七十多處,除大的城市建筑外,細節到集市上售賣的小商品包裝、地方飄過的報紙碎屑內容也都屬于努米亞共和國”。《萬里歸途》中氣勢恢宏的戰爭場面、一比一還原的真實場景和IMAX特制拍攝,為受眾提供了一場身臨其境、酣暢淋漓的視覺享受之旅。
口碑高漲的觀眾反饋
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中說:一個國家的文化軟實力,從根本上說取決于其核心價值觀的生命力、凝聚力和感召力,“真正優秀的影視藝術作品,深深地感染并打動了無數不同國家、不同民族的幾代人,對他們的人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主旋律電影在創作過程中要牢記將多種藝術表現形式中注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創作目標,將文藝宣傳、思政教育、引導輿論和服務群眾等關鍵要素相結合,尊重人民首創精神、尊重人民主體地位,做到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增強全國各族人民的文化自信,以此來滿足人民日益多樣化的精神需求;同時,主旋律電影也應當在不斷吸納多樣的受眾審美興趣與多元的文化過程中實現自身的豐富與發展,自覺承擔起塑造國家正面形象的社會責任,平衡主流意識形態與商業需求,在繁榮社會主義文化市場的同時實現經濟效益與文化效益的有機統一。
丹尼斯·麥奎爾曾指出受眾可以被界定為一個具備特定的經濟特征的、媒介服務和產品實際與潛在消費者的集合體([英]丹尼斯·麥奎爾.《受眾分析》.劉燕南,李穎,楊振榮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針對這類特殊群體的研究,則應將受眾構成、受眾與傳播者和傳播內容的關系、受眾忠誠度、受眾注意和反饋的質量、卷入程度和持久性納入考量,受眾本身作為電影市場的目標對象,自然是電影生產流程中不可忽視的主要群體。在流量為王的時代,未來即將發生的,或者是當下正在主流媒體平臺上演的,是一場注意力的爭奪戰。在一個注意力極度稀缺的時代,主旋律電影要在眾多電影市場中贏得受眾的青睞,要在兼顧電影的藝術性、商業性與文藝性的同時打通其與受眾之間的鴻溝。有學者提倡將主旋律片與商業片這兩個割裂的概念進行彌合,“在將過去的研究中總結過的主旋律的娛樂化和娛樂片的主旋律化用一種更符合產業規律、市場規律的方式重新整合與界定”(史東明、尹鴻.主流價值、商業訴求、電影產業——關于主流商業大片的對話.《當代電影》.2010年第1期)。面對觀眾流失的殘酷現實,許多主旋律電影逐漸改變以往刻板空洞的說教套路以及高高在上的宏大敘述模式,而是開始嘗試融合商業類型片的敘述法則和娛樂元素,拉近與普通觀眾的距離,將觀眾重新吸引進電影院,從而能在市場上有所作為。可以說,只有不斷摸索出技術、藝術、大眾性與時代性的最大公約數,才能給主旋律電影賦予源源不斷的動力。
新媒體的即時性與雙向互動性決定了觀眾不僅是信息的接受者,更是信息的發布者,社交媒體平臺憑借其高效的互動性、言論的自由性、擴面的傳播范圍、對海量信息的容納性和低廉的傳播成本形成了新媒體時代的傳播口碑,主動承擔推廣任務的受眾也成為電影口碑營銷的主要驅動因素。上映前,搶奪用戶注意力并留下記憶點與討論點為后期口碑發酵提供突破口,通過話題活動促進受眾增長觀影興趣,并由此引發深層次的內容表達。在《萬里歸途》的首映典禮上,一位曾在剛果共和國大使館擔任一等秘書辦公室主任的外交人員在觀影后落淚哽咽,另外一位坐標阿富汗的中國外交領事工作者也在其官方微博平臺寫下觀影感受:“飛機進入中國領空,萬家燈火托起京城……當硝煙散盡,繁華再現,往日那些喧囂煙火和擁堵吵鬧,其實就是我們最值得珍惜的歲月靜好,也是我們雖隔萬里卻苦苦尋求的家的方向。”
總體看來,《萬里歸途》好評度高、受關注度持久、話題量豐富。截至電影上映的兩個月后,該電影已在微博獲得9.2分的高分評價。在貓眼專業版的數據抓取中可以看到:《萬里歸途》超過《長津湖》 《姜子牙》 《我和我的家鄉》《我和我的祖國》等電影,位列內地影史國慶節總場次榜的第一位。該片在全球上映一個月后票房突破15億,收獲貓眼、淘票票雙平臺9.6分,豆瓣7.4分的高評分,在豆瓣平臺收獲11萬條以上短評,截至11月中旬,該話題在抖音的播放量已高達38.8億。愿如《萬里歸途》這樣的具有創新意識,既叫好又叫座的主旋律電影能更多地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