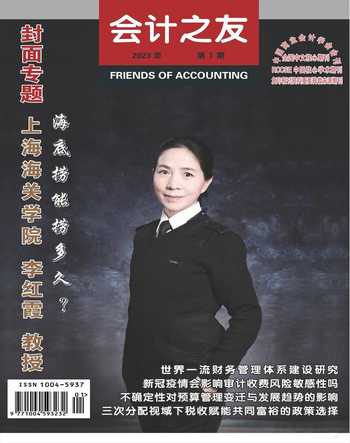新三板創新層企業股權融資效率研究
湯新華 湯伊鈴



【摘 要】 深化新三板改革是完善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的重要內容,對促進科技與資本融合具有重要意義。為探究新三板分層后,創新層企業的股權融資效率是否有所提高,選取2017年定向增發的新三板創新層企業為研究樣本,運用因子分析法、數據包絡分析法及DEA-mlamquist模型,研究其在2016—2020年定向增發前后的效率變化。研究結果顯示:新三板在分層后,創新層少數企業的融資效率略有提升,但大部分仍處于非有效狀態,股權融資效率并沒有因此而提高。最后根據指標的松弛變量,從投入冗余和產出不足兩個方面分析創新層企業股權融資效率低下的原因并提出相關建議。文章的創新之處在于:在選取研究樣本時,剔除了多次融資對效率的影響;使用因子分析法將多個原始指標做降維處理,并將提取出的公因子作為研究的產出指標,這樣可以更全面地反映出掛牌企業的融資效率。
【關鍵詞】 新三板; 創新層; 股權融資效率; 因子分析法; 數據包絡分析法; Malmquist指數模型; 定向增發
【中圖分類號】 F275.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4-5937(2023)01-0037-10
一、引言
新三板市場于2013年底正式接受全國中小企業掛牌申請,為無法順利上市的眾多中小型企業創造了融資機會和途徑,提供了發展空間,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當前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新三板市場雖然起步晚,但受到了許多投資者及證券公司的追捧,該板塊的規模不斷擴大,掛牌公司的數量也在一直增加,故新三板市場在北京證券交易所設立之前成為了全國第三大證券交易所。由于在新三板掛牌的門檻相比其他板塊要低,市場上的企業魚目混珠,投資者往往無法辨別優質的企業,于是自2016年6月起,新三板開始采用分層制度,將市場分為創新層和基礎層,具有資格的企業進入創新層,將未達到標準的企業納入基礎層,對其交易、發行以及信息披露等方面都進行差異化安排和管理,這樣有利于引導掛牌企業實行投融資精準對接。
二、文獻回顧
目前,國內外已有諸多學者對融資效率問題進行了研究。通過查閱文獻不難發現,西方學者側重于研究融資結構與融資效率之間的關系,而國內的學者則更擅長通過實證分析對企業的融資效率進行研究。
Fama(1970)就有效市場理論定義了三種水平的市場效率,從此開辟了西方市場效率的研究。隨后,Jensen和Meckling(1972)的代理理論以及Leland(1977)的優序融資理論相繼提出,有助于融資結構理論的進步與完善。Hogan et al.[1]通過實證分析發現,相對于債務融資,科技型企業更加愿意選擇股權融資,而且不同的融資決策將導致不同的融資效率。Suyanto et al.[2]曾運用DEA-Malmquist指數模型對不同行業的效率變化進行實證分析。
國內對融資效率的研究較為豐富,數據包絡分析法、熵值法和因子分析法等都可以實現對企業融資效率的研究,其中,數據包絡分析法是國內學者最常用的方法,由于該方法無需構建特定的函數,故相比于其他方法更具客觀性與真實性。王重潤等[3]運用數據包絡分析法研究企業在2013—2015年的融資效率,得出多數企業處于融資非有效狀態的結論。楊國佐等[4]采用同樣方法研究597家掛牌企業2012—2014年的融資效率。林妍等[5]運用數據包絡分析法中的BCC模型分析并研究科技企業的融資效率。王偉等[6]運用DEA模型通過橫向對比與縱向對比對湖北省科技型掛牌企業進行比較分析。曾雄旺等[7]也運用此模型研究政府補助對融資效率的影響。在DEA模型的基礎上,學者研究出了DEA-Malmquist動態指數模型,相比于前者,該模型可以實現企業效率變化的動態分析。肖雅等[8]運用DEA模型對新三板高新技術企業2014—2016年的融資效率進行靜態分析,同時使用了Malmquist模型對其進行進一步的動態分析,研究其融資效率的變化趨勢。吳陽芬等[9]將DEA模型與Malmquist指數模型相結合,對新三板的中小型企業實行了靜態評估和動態分析。桂嘉偉等[10]運用三階段DEA模型以及Malmquist指數模型對248家樣本企業2015—2017年的融資效率進行研究,并提出財務風險與融資效率之間的關系。杜麗[11]同樣運用三番式數據包絡分析法對新三板企業的融資效率進行研究,結果表明企業在分層實施后效率有所提升,但總體融資效率水平還是差強人意。王文寅等[12]和曹翠珍等[13]也使用了Malmquist指數模型分別對物流企業和商業銀行的融資效率進行動態分析。
縱觀現有的研究成果,既有的文獻已對新三板掛牌企業的融資效率進行了研究,但在研究范圍和指標選取這兩個方面,仍存在需要深入探索和分析的地方:從研究范圍來看,大部分文獻未考慮市場分層對企業的影響,將不同層次的企業一同進行研究,且較多學者在研究時,未剔除多次融資對效率的影響,這樣無法真實地體現出分層后的融資效率;從指標選取來看,大部分學者在選取DEA模型的投入產出指標時,僅選擇幾個具有代表性的指標,這樣未必能全面地反映融資效率。
三、新三板分層對企業融資效率的影響
(一)激勵企業提升自身實力
分層制度實施后,不同層次的掛牌企業會被進行區別管理,達標的優質企業進入創新層,未達標的企業則留在基礎層,實現了一定程度上的優勝劣汰,進入創新層的企業在信息披露方面更加規范、全面,所以創新層的掛牌企業更受投資者的青睞,融資相對容易,這樣擴大了不同層次的企業流動性的差異,對基礎層的企業起到了激勵和引導的作用,形成了無形的高效競爭機制,有利于帶動企業提高自身的經營能力和內部管理水平,從而提升融資效率。
(二)增強該板塊市場活躍度
新三板企業入市門檻低、信息披露不規范,投資者因害怕風險而不敢投資,市場活躍度低。實行市場分層制度后,優質的掛牌企業可以脫穎而出,這降低了投資者進行信息收集及處理的各種成本,為其決策提供了價值參考標準,進而激發了投資者投資交易的積極性,市場上定增次數、交易金額和交易次數都有了明顯的提升,增強了新三板市場的活躍度,從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部分企業融資渠道窄、融資成本高等問題,融資規模和效率也會隨之提升。
四、研究設計
(一)研究思路
將因子分析法和數據包絡分析法(DEA)相結合,利用因子分析法將產出指標進行降維,然后運用DEA模型分別計算出新三板創新層的掛牌企業2016年(融資前一年)、2017年(融資當年)、2018年(融資后第一年)、2019年(融資后第二年)和2020年(融資后第三年)的效率,并運用DAE-Malmquist指數模型從動態的角度分析企業融資前后的效率變化。
(二)樣本選取及數據來源
新三板企業籌資的方式有定向增發、股權質押及發行債券等,其中定向增發是掛牌公司常用的融資方式,因為與其他融資方式相比,實行定向增發獲得的資金規模較大,且融資要求也低,企業更易獲得資金,因此本研究僅考慮定向增發這種融資方式。
由于掛牌企業在經過市場嚴格規范的分層篩選后,創新層企業可從掛牌公司中脫穎而出,相比較于基礎層,這些企業更容易獲得投資市場的青睞,更易籌集資金,所以在此背景下,選取在市場分層后第一年,即2017年,進行定向增發的創新層掛牌企業為樣本,由于市場分層時間為2016年年中,為真實地體現分層后的效率,故選擇2017年的企業為樣本,研究其股權融資效率,并為了確保研究結果的準確性,做了如下篩選:(1)剔除進行多次融資的公司,即在2016年、2018年、2019年和2020年進行過融資的公司,以消除多次融資對效率的影響。(2)剔除金融類公司,基于金融類公司脫離了實體經濟,而且相比較于其他類型的企業,現金流較大,所以其財務指標與其他行業的財務指標不可比。(3)剔除ST類公司,由于該類企業的運營狀況不佳,財務指標異常,不具備普遍性,所以將其剔除,避免影響研究結果。(4)剔除財報數據缺失的公司。
經過篩選,最終選取新三板創新層的134家掛牌公司為研究樣本。研究所使用的所有原始數據均來自全國中小企業股份轉讓系統網站、Wind數據庫和同花順網站。
(三)實證分析
1.因子分析法
(1)選取指標
在使用數據包絡模型以及Malmquist指數模型對企業的融資效率進行研究時,選取的指標不同,產生的結論也可能會隨之不同,所以指標的選取會對最終的研究評價結果產生重要的影響。選取何種指標才能使相關研究結果更為準確,目前學術界尚未達成統一標準。故為了準確體現企業的融資效率,在選取投入指標時,參考了其他學者的研究成果,并綜合考慮數據收集可行性等問題,選取了四個指標為DEA模型的投入指標,分別為:X1(資產總額),該指標可體現企業的融資規模,因為不管企業使用哪種融資方式,其總資產都會隨著融資擴大;X2(資產負債率),該指標可體現企業的融資結構與融資能力;X3(營業成本),該指標可以體現企業融資后資金的使用情況及效率;X4(財務費用),該指標是指企業為獲得生產經營所需要的資金而產生的開支,體現了融資的成本。在選擇評價企業融資效率的產出指標時,應該考慮其對資金的使用效率、市場表現、發展能力和清償能力等方面,因此參考了前人的研究結果,為了體現企業的盈利能力、償債能力、成長能力和營運能力,選取了以下指標作為DEA模型的產出指標,見表1。
(2)因子分析適宜性檢驗
利用SPSS 26.0軟件對產出指標進行KMO檢驗和巴特利特球型檢驗,KMO檢驗的統計量為0.638(>0.6),巴特利球形檢驗的顯著性水平為0.000(<0.05),說明原始變量間存在較強的相關性,選取的產出指標適合做因子分析。
(3)提取公因子
降維后共篩選出4個主成分,累計方差貢獻率達83.806%,說明這4個因子可以解釋大部分原始變量,經過分析,本文將提取出的4個主成分分別命名為:Y1(盈利因子)、Y2(償債因子)、Y3(成長因子)、Y4(營運因子)。
(4)因子得分
通過成分得分系數矩陣,建立4個因子的因子得分函數,計算出4個因子的得分,得分系數矩陣如表2。
2.數據包絡分析法
數據包絡分析法,即DEA模型,它是由線性規劃以及數據模型共同構建而成。該方法分為兩個模型,分別是CCR模型和BCC模型。
由于BCC模型不僅可以測定企業的綜合效率,還能實現純技術效率以及規模效率的測量,且該模型是基于規模報酬可變的假設,克服了CCR模型的缺陷,故選擇BCC模型研究企業的融資效率。
DEA模型的評價步驟:
(1)對該模型的投入、產出指標以及評價對象進行確定。上文已提及,該模型選取的投入指標為:X1(資產總額)、X2(資產負債率)、X3(營業成本)、X4(財務費用);選取的產出指標經降維,最終提取四個公因子為:Y1(盈利因子)、Y2(償債因子)、Y3(成長因子)、Y4(營運因子);評價對象為在2017年進行定向增發融資的134家新三板創新層掛牌公司。
(2)預處理數據。該模型要求所有數據非負,故需對數據進行無量綱化處理。對所有數據進行如下處理:
X?觹=0.1+0.9(X—Xmin)/(Xmax—Xmin),X∈N
Y?觹=0.1+0.9(Y—Ymin)/(Ymax—Ymin),Y∈N
其中,X為投入指標進行處理前的原始數據,Xmax、Xmin分別是該組樣本的最大值和最小值。Y是產出指標進行數據處理前的原始數據,Ymax、Ymin分別是該組樣本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經過統一處理后,所有數據均達到了非負性的要求。
(3)建立BCC模型進行檢測,本文借助DEAP 2.1軟件進行測算,分析結果如下:
①效率分布
由表3可知,進行定向增發之前,創新層的掛牌企業中有14家(占總體10.45%)達到綜合效率有效的水平,即綜合效率值為1,這些企業也同時實現了純技術和規模有效,其松弛變量的值均為0,說明其投入和產出達到了最佳比例,即投入實現了最小化,沒有冗余的現象,產出也實現了最大化,不存在短缺的情況,但這些企業僅占少數。進行定增后,達到融資有效的企業更少,2017年、2018年綜合效率為1的企業分別有13家(占總體9.70%)、12家(占總體8.96%),這歸因于處在(0.5,0.8)這個區間的企業數量有所增加,說明融資后部分企業的效率降低了。至2019年,處于有效狀態的企業數量略有回升,有14家,約占10%左右,但綜合效率值大于0.8的企業在減少,說明許多企業都從有效或弱有效狀態中脫離,向較無效的方向發展,大部分的企業效率在降低。2020年,融資有效的企業持續增加至17家(占總體12.69%),處在(0.5,0.8)這個區間的企業也在增加,說明至2020年企業整體的融資效率有所上升。雖然這些企業沒有達到最佳融資狀態,但在一定程度上有合理地規劃利用籌集的資金,距離最優狀態不遠。總體來看,企業在融資后的初期效率是較低的,處于有效狀態的企業持續減少,尤其在2018年,不僅達到有效狀態的企業最少,融資效率低于0.5的企業也是五年中最多的。至2020年,效率低下的情況有所改善,部分企業的效率有所提升,但即便如此,大部分企業還是處于無效狀態。由此可見,實行定向增發后,大部分企業的效率并沒有得到改善,且融資前后均有超過85%的企業沒有達到有效狀態,整個創新層融資效率存在較大的提升空間。
達到純技術效率有效的企業,2016—2018年期間逐年減少,數量占比由61.94%降至48.50%,說明這段時期新三板企業的經營管理能力和技術水平在不斷降低,這可能與當時宏觀的經濟環境有關,近年來國內經濟持續放緩,市場需求有所下降,市場需求不足就直接削弱了許多中小型企業研發的積極性,導致企業缺乏核心競爭力,所以企業應該加強技術創新,提高其自主研發能力;與此同時企業還應改善其管理模式和治理結構,因為新三板的企業大多為中小型民營企業,股權主要掌握在出資人手中,企業的所有者和經營者為同一人,在管理層次較少的情況下,企業難以實現高效的內部控制和管理,不利于純技術效率的提升。2018年之后達到純技術效率有效的企業有所增加,2020年增加至81家,占總體的60.45%,與2016年的情況相近持平。2016—2020年,達到純技術效率有效但規模效率無效的企業分別有69、57、53、61和64家,每年都超過總數約40%,說明創新層有不少企業存在這種狀況:合理地使用籌集的資金,也達到了產出最大化,且公司內部管理有效,但之所以無法實現綜合效率有效,其原因是企業的規模和投入產出并不相符,所以這一類企業可以通過調整規模提高綜合效率。純技術效率體現的是一家公司的管理能力和技術水平,2016—2020年這段觀察期內,雖然純技術效率有效的企業數量有所降低,但處在效率較低位置的樣本企業數量不多,每年均有超過90%的企業其效率值大于0.8,說明絕大部分企業的純技術效率都處在較高的水平,這也符合新三板創新層企業的定位,新三板大多為高成長的科技創新型企業,其研發投入較高,所以技術水平普遍不會太低。總體來看,創新層達到純技術效率有效的企業略有減少,融資后只有大約一半的企業處于有效狀態,可見大部分企業的管理能力和技術水平仍存在一定的不足,有待進一步完善和提高。
實現規模效率有效的企業占比不大,2016—2020年,達到有效的企業分別有14、13、12、14和18家,總體變化不大,規模效率表示的是企業當前規模對融資效率的影響,說明這些企業投融資都與公司規模基本匹配。融資后,有超過50%的企業規模效率值均大于0.8,說明有近一半的企業處于較有效狀態,對于這部分企業而言,其規模效率雖接近前沿面,但仍未達到最優經濟效益的合理規模,可能是由于其投入并未達到最小化,與公司規模不匹配,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可能是新三板融資門檻低,企業更易獲得資金,所以大多數掛牌公司往往沒有按照實際投資需求確定籌資的數額,在融資過程中存在一定的盲目性,這樣容易造成資金閑置、使用效率低等問題,企業可適當地縮小融資規模以提升其效率。
②效率均值
由表4可知,創新層掛牌企業在2016—2020年綜合效率的均值分別為0.846、0.763、0.796、0.802和0.879,相比于融資前,效率有所降低,且2017年和2018年的效率值低于0.8,可見在融資后的初期,創新層樣本企業融資效率水平處在較低的位置,2018年后效率值開始回升,至2020年超過了融資前的水平,但每年均未達到1,說明整體來看融資是處于非有效狀態。在觀察期內,純技術效率的變化呈U型,先下降后上升,每年的效率值均大于0.9,但距有效的水平還有一定距離,純技術效率雖沒有明顯的波動,但相比于融資之前都有所下降,尤其是在2018年,效率值跌落低谷,該年的規模效率有所提高,說明2018年綜合效率的略微提升是由于規模效率的帶動。在這五年期間,規模效率均值分別為0.885、0.807、0.852、0.847和0.926,波動較大,2017年規模效率降低至0.807,五年中最低,下降幅度大于純技術效率的降低幅度,該年綜合效率值也跌落至0.8以下,從綜合效率的構成來看,說明2017年企業融資效率低下主要是受到了規模效率的制約。總體看來,大部分企業的投入資金并沒有在最大程度上被利用,企業想要提升融資效率,不僅應該從純技術效率方面入手,還要兼顧規模效率,通過改進技術、調整規模等方式改善融資效率不理想的情況。
③規模報酬分布
由表5可知,規模報酬遞增企業的數量總體沒有較大變化,前四年徘徊在120家左右,2020年略有降低,但每年均有超過80%的企業處于規模報酬遞增的狀態,說明大部分企業都處在早期的發展階段,急需規模擴張,這似乎也符合新三板大多數掛牌企業的共同特點,這些企業往往需要通過融資的方式進行相關的研究開發或維持經營活動,以實現企業迅速發展,融資可能無法滿足其發展需要,所以這些企業可以通過兼并重組或再次融資等方法,進一步擴大公司規模以提升效率。融資后,處于規模報酬遞減的企業先是增加后減少,至2020年又有所增加,這些企業的產出增加值小于投入值,可能是由于此類企業一味追求生產規模和市場占有率,導致其沒有對籌集的資金進行及時有效的協調,所以這些企業應該適當地去其產能,壓縮公司的規模。總體來看,融資后,創新層企業的規模報酬分布沒有出現較大的變動,處于規模報酬不變的企業略有增加,但每年占比僅約10%左右,這表明,只有少數企業處在有序的狀態,大部分企業規模還是處于不足或飽和的階段。
3.DEA-Malmquist模型
Malmquist模型用于評價技術效率變動(Effch)、技術進步變動(Techch)和全要素變動(Tfpch)間的關系,若評價對象的規模報酬處于可變狀態,則可將技術效率變動進一步分解為純技術效率變化(Pech)和規模效率(Sech)。具體的關系式如下:
Tfpch=Effch×Techch=Pech×Sech×Techch
在研究新三板融資效率的過程中,只使用DEA模型,靜態地比較企業不同年份的指標和效率,并不能深入分析企業融資前后效率的變化情況,所以還需使用DEA-Malmquist指數模型對2016—2019年企業融資效率的變化過程進行進一步動態分析。借助DEAP 2.1軟件,效率值的具體測算結果如表6。
由表6可知,從均值上看,2016—2020年,全要素生產率的均值為1.106,說明在這段時期內,創新層掛牌企業的融資效率整體是提升的,增幅為10.6%。將全要素生產率分解后,可知技術進步變化值為1.096,增幅為9.6%,這意味著生產前沿面向著高水平的方向略微進行了移動,即整體的技術水平在提升;再看技術效率值為1.009,也大于1,但增幅不大,整體平均僅提升了0.9%,說明企業與前沿面之間的距離縮小了,由三者的關系可知,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是由技術效率和技術進步共同貢獻所致,但技術進步的上升幅度大于技術效率,故效率的提升主要是由于技術進步的帶動。技術效率的變化取決于純技術效率和規模效率的變動,將技術效率分解可知,純技術效率值小于1,下降幅度為0.3%,說明2016—2020年這段時期內,企業整體的管理能力在降低,且在技術創新方面沒有取得突破性的進展;規模效率值為1.011,大于1,說明規模效率提升了1.1%,由此可見,技術效率的提升是由規模效率的提高引起的,在這過程中純技術效率拖了后腿,但規模效率的提升足以彌補純技術效率的下降,所以技術效率并沒有隨之降低。
從縱向上看,在四個環比觀測期內,全要素生產率的變化呈先下降后上升的趨勢。在第一個觀測期內,全要素生產率大于1,技術進步值為1.221,也大于1,說明在第一個觀測期內,技術進步是全要素生產率提升的關鍵原因;技術效率值為0.895,小于1,說明在該期間內,融資機制不夠完善,風險管理也沒有到位,這段時間股市過熱,帶動了許多企業進行投資,使其資金使用效率低下,進而影響到融資效率,這意味著融資機制對融資效率的影響起著重要作用。在第二個環比觀測期內,全要素生產率為0.843,相比第一個觀測期有明顯降低,這很大程度上是源于技術進步的制約,說明這段期間內企業技術在衰退;技術效率值為1.044,大于1,表示技術效率的提升無法去除技術進步下降的影響,將技術效率分解后可知,該指標的上升得益于規模效率的提升。在第三個觀測期內,全要素生產率開始回升,甚至高于第一個觀測期的數值,分解該指標可知,技術效率值與技術進步值均大于1,說明技術效率和技術進步均有所提升,技術進步提升的幅度大于技術效率,說明效率的提升主要是由技術進步作用所致。在最后一個觀測期內,全要素生產率持續上升至1.301,且四個分解因素的值均大于1,說明全要素生產率的良好表現是受到了技術效率值和技術進步值共同的影響。
(四)結果分析
總體來看,新三板創新層掛牌企業2017年定向增發融資的整體效率并不高。雖然在融資后,部分企業的效率有所上升,但還是有將近90%的企業處于無效狀態,說明籌集到的資金并沒有進行充分的利用,企業可以采取調整規模、改良技術或改善內部管理等方式提高融資效率。從規模報酬分布上看,整體變動不大,大部分企業還是處在規模報酬遞增或遞減的狀態,說明創新層的大部分企業都沒有通過融資改善其生產規模,未能達到最佳狀態。從Malmquist指數動態分析來看,融資效率自2018年后略有上升。
五、融資非有效分析
為了對樣本企業股權融資效率低下的原因進行具體分析,由此借助DEAP2.1軟件計算出了各投入產出數據的松弛變量。若投入與產出的松弛變量都是0,則表示該企業投入已達到了最小,無冗余,產出也實現了最大化,無短缺;若輸入指標的松弛變量不為0,則說明投入存在冗余,公司需要減少投入以此提高效率。若輸出指標的松弛變量不為0,則說明產出沒有最大化,存在短缺,企業應該提高產出進而提升效率。對該模型的投入和產出指標的松弛變量的統計分析見表7。
(一) 投入指標分析
由表7可知,從投入的角度看,資產總額和營業成本冗余的比例較低,財務費用的冗余程度在融資后有所改善,存在資產負債率冗余的企業一直較多,比重超過70%,表明企業資產負債結構不合理是導致融資效率低下的主要因素。企業應理性、充分地研究各個時期的融資需求,科學合理地設置債權融資比例、股權融資比例和長短期融資比例,在保證公司造血功能、留存收益提取不斷上升的同時,提升內源融資的比例,備足自主操控資金,以此面對突發的狀況,通過采取多樣化的籌資方法來降低融資風險,形成多樣化的資本結構,降低資產負債率。
(二) 產出指標分析
由表7可知,從產出角度分析,成長因子產出不足的企業較少,大部分企業在成長能力方面都表現不錯。盈利因子和營運因子產出短缺的比例不是很高,但程度不穩定,波動較大,說明企業在盈利能力和營運能力兩方面不是很穩定。盈利能力不穩定,其一是由于新三板的掛牌標準低,對入市的公司沒有盈利方面的要求,所以掛牌企業的盈利能力參差不齊;其二,新三板的企業主要是科創型企業,研發投入較高,研發的過程漫長,公司無法立即將資金轉化成自身利潤。營運能力不足,一方面是由于新三板掛牌的主要為中小型民營企業,其資金的運營效率較低,所以導致經營存在不穩定性;另一方面,企業融資后其業務總量,公司規模都有所增長,從而使其總資產周轉速度放緩,所以公司需要通過提升其資產周轉的能力,完善其供應鏈和存貨管理,合理編制生產計劃,使企業的生產運營管理體系更加完備,逐漸增強企業的營運能力。另外,償債因子產出短缺的程度很嚴重,比例高達80%左右,說明大部分企業償債能力都較弱,在面臨短期或長期債務時不能及時付現進行償還,這也是阻礙企業提升融資效率的重要原因,所以,這一類的公司都需要努力提升各項資產的質量,以提高其變現能力,同時,也應該科學合理地舉債,選用恰當的舉債方法,并制訂合理、有效的還款規劃,降低財務風險。
六、研究結論與相關建議
(一)研究結論
通過運用數據包絡模型、Malmquist指數模型等對新三板創新層企業的股權融資效率進行研究并分析融資非有效的原因,研究結論如下:
1.企業進行定向增發后,部分企業的綜合效率有所上升,但大部分企業仍處于無效狀態,整體融資效率不高,這歸因于純技術效率和規模效率的低下。
2.處于規模報酬不變的企業較少,大部分還是處在規模報酬遞增或遞減的狀態,說明大部分企業未能通過融資改善其生產規模,且無法將其生產規模控制在合理的范圍內。
3.Malmquist指數動態分析來看,融資效率整體上呈略微上升的趨勢。
(二)相關建議
基于以上結論,從企業自身和市場政策兩個角度提出如下建議:
1.企業自身
(1)合理使用資金,制訂詳細計劃
新三板掛牌的公司多數為初創型企業,缺乏科學的決策機制,投融資時隨意性較大,在投資前未對投資項目的可行性進行理性、深入的分析,投資存在一定程度的盲目性,導致沒有將籌集的資金進行有效使用。所以企業在投資前應調查并評估投資項目的可行性,制訂合理、詳細的資金使用計劃;投資時專注于主要領域,避免盲目多元化;同時引入資金績效評估機制,減少大股東的“圈錢”行為,并健全企業內部相關的管理制度,進一步提升資金的綜合使用效率。
(2)調整企業生產,保持最優規模
新三板創新層有超過80%的企業處在規模報酬遞增的狀態,上述公司應該采取再融資或兼并重組等方法,來進一步擴張公司規模以提升股權融資效率;對于處在規模報酬遞減狀態的公司,壓縮規模、去產能是其發展的主要任務,可采取股權回購、分立、出售等方法,壓縮公司的規模,以提升股權融資的效率;已達到規模經濟的上市企業,可以選擇內涵式發展,合理配置公司內的存量資本,以此提升經營效率。總而言之,企業應該結合自身發展情況,理性地決定公司是否需要實施融資,并對新募集資金的運用做出合理、細致的計劃,及時調整并合理控制公司的規模,使企業規模保持最佳狀態以提升其融資效率。
(3)加大研發投入,掌握核心技術
新三板的創新層企業大部分是科技創新型企業,擁有先進的技術是其發展的動力,是其立足之本。純技術效率的低下限制了融資效率的提升,說明這些企業缺乏核心競爭力,技術更新緩慢,無法形成企業發展和競爭優勢。因此,企業應培養或引進相關研究領域的創新技術型人才,引入股票期權、限制性股票或知識產權入股等人才激勵制度;加大研發投入,重視技術創新,參考借鑒其他企業先進的技術成果,并根據自身情況進行整合、改進以及創新,形成特有的先進核心技術。
2.市場政策
(1)完善信息披露制度
市場透明度低,信息披露不完整,會導致信息不對稱,從而引發資源錯配等問題。相比于其他投資板塊,新三板市場不僅對企業掛牌的門檻要求低,對其財報信息披露的規范要求也較為寬松,這使新三板企業在信息披露的完備性、及時性等方面都存在諸多不足,財報質量參差不齊,從而導致投資者無法做出合理的投資決策,或對該板塊失去信心不敢參與,最終出現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所以市場需要提高該板塊公司信息披露的要求,提升信息披露的質量,使優質的企業脫穎而出,降低投資者的決策成本,促使資金盡可能地流向高效的企業,利用高效良性的市場競爭機制促使企業提高融資效率。
(2)完善轉板、退市機制
進入新三板掛牌的標準較低,導致新三板的企業水平不盡相同,沒有健全的轉板、退市制度,會使連年虧損的企業沒有及時推出,優質的企業無法進入創新層。所以各層次都要制定進入和維持的標準,沒有達到進入標準的企業,不允許其掛牌,沒有達到維持標準的企業,可進行降層處理或進行退市緩沖,給予企業一定的壓力,使其規范管理模式,激勵其不斷發展,促進新三板市場良性循環;通過市場的篩選引導投資者做出正確的投資決策,保護投資人的利益,提高市場的吸引力、活躍度。
【參考文獻】
[1] TERESA HOGAN,ELAINE HUTSON.Capital structure in new technology-based firms:evidence from the Irish software sector[J].Global Finance Journal,2004,15(3):369-387.
[2] SUYANTO,Ruhul A,SALIM.Sources Of productivity gains from FDI in Indonesia:is it efficiency improvement or technological progress?[J].The Developing Economies,2010,48(4):450-472.
[3] 王重潤,王贊.“新三板”掛牌企業融資效率分析[J].上海金融,2016(11):70-75.
[4] 楊國佐,張峰,陳紫怡.新三板掛牌公司融資效率實證分析[J].財經理論與實踐,2017,38(2):48-53.
[5] 林妍,劉霞.多層次資本市場支持科技企業融資效率研究——基于京津冀的比較視角[J].會計之友,2019(20):101-106.
[6] 王偉,董登新.科技型中小企業新三板市場融資效率分析——基于湖北省企業面板數據的實證研究[J].證券市場導報,2020(2):45-51.
[7] 曾雄旺,唐學思,李志勝.農業上市公司融資效率及政府補助的影響效應[J].會計之友,2021(23):58-63.
[8] 肖雅,郭曉順.新三板高新技術企業股權融資效率評價[J].財會月刊,2018(11):57-61.
[9] 吳陽芬,曾繁華.我國新三板中小企業融資效率測度研究[J].湖北社會科學,2019(1):69-77.
[10] 桂嘉偉,吳群琪.新三板科技服務企業融資效率與財務風險研究[J].科技進步與對策,2019,36(12):115-124.
[11] 杜麗.市場分層視角下新三板公司融資效率分析[J].財會通訊,2020(12):147-151.
[12] 王文寅,劉佳.多維視閾下物流企業融資效率比較研究[J].會計之友,2021(6):73-80.
[13] 曹翠珍,杜威.我國發行優先股的上市商業銀行融資效率分析[J].會計之友,2021(6):81-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