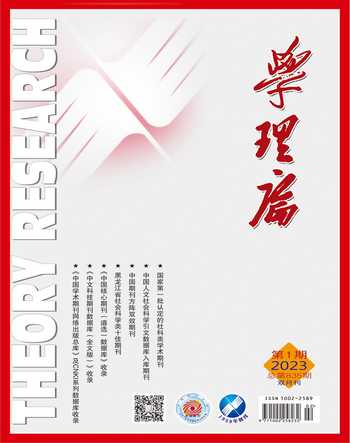全球生產網絡與金融化相統一的政治經濟學分析
摘 要:二戰后尤其是冷戰結束以來,新自由主義思潮引發了生產集中趨勢的退化,使得全球生產網絡和金融化相統一的孿生關系逐漸演化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這枚“硬幣”的“一體兩面”。二者的對立統一,已成為全球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主要矛盾。這一矛盾的上升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充分利用商品、貨幣和資本形式的必然結果,而二者相統一的實現是以全球范圍內技術變革、勞動組織變遷以及從全球到地方的社會空間范圍內生產網絡吸納小生產方式為路徑的。進一步地,這一現實矛盾的運動引發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危機和蛻變,給出了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為主導的社會形態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可能。
關鍵詞:全球生產網絡;金融化;新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變革;社會主義
中圖分類號:F034 ? 文獻標志碼:A ? 文章編號:1002-2589(2023)01-0075-06
21世紀以來,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為主導的全球政治經濟波譎云詭:一方面,經由全球生產網絡的蔓延,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滑坡,導致全球范圍內的金融海嘯與經濟衰退,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生命力遭到質疑[1];另一方面,全球新冠疫情大流行的沖擊,引發美國股市的崩潰和全球生產網絡的失靈,放大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治理無力,給全球經濟治理帶來新挑戰[2]。可見,全球生產網絡和金融化的統一,構成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內在矛盾充分發展,進而引發危機和蛻變的現實路徑。這也正是基于二戰后乃至冷戰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演化的歷史邏輯而出現的。
20世紀后半葉,新自由主義思潮指導下國家壟斷資本的私有化,使資本主義國家權力與生產組織逐步脫鉤。作為金融資本的銀行資本在國家權力控制下執行產業資本職能[3],銀行資本轉化為金融化資本,并不再返回生產過程的趨勢正逐步走強。產業資本與銀行資本也再度分離,形成訴求相反的利益集團,進一步剝離了國家權力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控制力。資本主義進入最高階段的帝國主義后,其充分發展的集中趨勢反而停滯了。因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開始統一于全球生產網絡的產業資本擴張與金融化的剝奪性積累的結合,中心國家的金融化滲透與向外圍擴張的生產網絡構建,成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這“一枚硬幣”的“兩個面”,引導著世界經濟的演化并對國際政治經濟格局產生深刻影響。
現有文獻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全球擴張和金融化相結合的研究較多,并形成以下三種觀點。第一,全球金融化論[4]。強調金融化作為一種獨立的趨勢,以其自身更為劇烈的價值增值特性向全球擴張,并通過全球生產網絡等具體形式將全球范圍內的生產行為進一步結合,進而促進全球化金融化市場的一體化。第二,全球價值鏈論[5]。強調以中間品貿易和服務貿易興起為代表的全球使用價值生產的新現象,推動了全球經濟一體化,而金融活動作為服務貿易的子類型,從屬并嵌入于全球價值鏈的動態。第三,新帝國主義論[6]。強調全球生產網絡與金融化,共同作為工具,使新帝國主義國家對全球范圍的外圍國家進行控制,并展開價值剝削形成積累。實際上,金融化與全球生產網絡都作為相對成熟的分析范式,各自亦有翔實的理論傳承。金融化研究在個人生活[7]、企業運營[8]與社會運行[9]等層面逐步遞進,全球生產網絡研究也是從經典國際分工[10]到新國際勞動分工[11],再從全球商品鏈[12]到全球價值鏈[5]的理論研究逐步深入。這都將為全球生產網絡與金融化相統一的研究提供充分借鑒。雖然現有研究已現雛形,但也存在著不足。其一,多數研究聚焦在二者相統一現象;其二,對機制的分析較為零散和單薄,且過于工具主義與功能主義;其三,對社會空間范圍的生產方式分析不足,對技術基礎和勞動過程表現的生產方式的聯系分析有待深化。
由此,本文將嘗試在給出全球生產網絡與金融化相統一的理論邏輯后,從生產方式的三重含義[13]出發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變革視角的全球生產網絡和金融化相統一的實現機制加以闡釋,并力圖以其矛盾運動揭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現狀與前途。
一、全球生產網絡與金融化相統一的資本演化動力
全球生產網絡和金融化相統一,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充分利用的商品、貨幣和資本形式各自內在蘊含的矛盾運動而自然演化的結果。
第一,勞動力商品是使用價值和價值的矛盾體[14]。勞動力是商品的特殊形式,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特有的商品形式。勞動者通過出賣勞動力獲得工資以彌補勞動力價值,而資本家獲得勞動力的使用價值,即能夠與資本家的生產資料相結合生產出勞動力價值的同時還能夠產出一個剩余[14]。一方面,勞動者獲得勞動力的價值以求維持其勞動力的再生產,而勞動力商品價值作為歷史的、道德的范疇[14],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具有不同的內容,隨著資本積累與經濟社會演化而具有豐富的趨勢;另一方面,資本家具有不斷控制勞動者充分利用其使用價值以獲得更多剩余的傾向,通過改進技術以生產相對剩余價值引發必要勞動時間縮短而使工資率下降,同時通過勞工套利剝奪本身可能屬于工資部分的價值[15],進而引發勞動力商品價值的轉化形式工資的下降趨勢。從這一矛盾出發,一方面,勞動者力圖實現工資的增值保值,而讓渡一部分貨幣工資的使用權使其進入金融市場,并通過消費信貸手段以獲得更多的勞動力再生產的消費基金[16],使金融資本向金融化資本的轉化具有更豐富的貨幣基礎;另一方面,中心國家的勞動者,自發結成工會以抵制資本的勞動過程控制并向資本家議價以力圖促進工資的合理化。勞資矛盾的加劇,成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向外圍國家擴張的重要動力[11]。資本尋求更具勞動力優勢的生產區位,向外圍地區產業轉移和資本輸出,資本主義的全球生產網絡開始出現。
第二,貨幣是價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矛盾體[17]。貨幣從金屬貨幣到信用貨幣演化,乃至過渡到數字貨幣后拋棄其實體形式,始終具有價值尺度與流通手段兩大基本職能。金屬貨幣作為一般等價物是為滿足交易需要而成為流通手段,其實物形式金屬同時也是其價值的錨定物,而具有穩定的價值尺度。然而,隨著流通擴張的需要,信用貨幣與主權貨幣成為資本主義商品和資本流通主要載體。一方面,信用貨幣乃至主權貨幣的價值錨定物不能夠維持貨幣品質[18],資本主義國家過度使用貨幣政策潤滑擴張流通手段以刺激經濟的常態化,使得超量發行主權貨幣而通貨膨脹成為趨勢,其價值尺度就因流通需要而不穩定;另一方面,價值尺度的穩定,需要維持貨幣的品質和價值,需要在貨幣流通、貨幣資本流通和借貸資本流通的過程中維持貨幣總量的穩定,但這難以滿足資本積累與經濟社會演化的需要。從這一矛盾出發,一方面,作為貨幣持有者的勞動者和資本家都力圖實現其貨幣品質的穩定,金融手段的套期保值成為重要路徑,使得部分參與金融活動的貨幣持有者的貨幣價值和品質得到維護,金融活躍而金融化得到推進;另一方面,中心國家的貨幣、貨幣資本和借貸資本流通的供給出于積累需要而超量增發,以其國際貨幣權力向更廣闊的地理空間流動[19],成為其具體形態轉化為世界貨幣的重要動力,生產過程實現的資本積累就有了全球擴張的趨勢,可能使其流通手段職能與貨幣供給充分匹配,有助于維持貨幣價值穩定。
第三,資本是價值增值與平均利潤率下降趨勢的矛盾體[20]。資本是一種過程[17],價值增值是其唯一目的,而平均利潤率下降規律限制了價值增值的物質上限。資本通過使用一切手段增值,進而實現積累以擴大再生產,促進其新一輪價值增值。但在剝削率相對穩定的前提下,資本出于技術控制的需要引發有機構成提高導致平均利潤率下降,限制了價值增殖過程。一方面,價值增值是資本及其人格化的資本家的天然使命[14],另一方面,平均利潤率下降趨勢的自然規律引發資本價值增殖受到限制,資本的天然使命和自然規律存在矛盾,由此資本就成為價值增值和平均利潤率下降趨勢的矛盾統一。從這一矛盾出發,一方面,中心國家的勞資矛盾和生產條件變化使資本的價值增殖遇到平均利潤率下降的瓶頸,生產過程向勞資關系更緩和與生產條件優越的地區轉進[21],進而尋求高效的價值增值與更大的利潤空間;另一方面,處于發達國家的資本生產過程已不再是最優的增值手段,而利用從發達國家興起的金融市場的收入再分配,則有助于部分資本繼續瓜分剩余價值乃至勞動力價值[22],既有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和勞動力參與金融市場以求投機增值的部分,也包括外圍國家在資本的生產過程帶來的工業化所游離出的新價值。
所以,商品、貨幣和資本形式的利用雖成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取得歷史成就的關鍵,但這三種形式的內在矛盾也決定了全球生產網絡和金融化的結合性充分展開。那么,現實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實踐中,全球生產網絡和金融化相統一的經濟事實與理論表現將是如何,生產方式如何得以成為解釋全球生產網絡和金融化相統一的實現機制,本文將嘗試予以考察。
二、全球生產網絡與金融化相統一的生產方式路徑
根據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分析,生產方式是在勞動資料起決定作用的物質技術條件基礎上[21],以勞動過程中勞動者利用生產資料的組織形式[23]為核心,在社會空間范圍內利用生產條件[24]的方式方法。即生產方式包含技術、勞動過程和社會空間三重含義[25]。二戰后尤其是冷戰以來至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變革,就是由技術革新的推動,帶動勞動力市場的彈性化和自由化[26],促使更多小生產方式被納入全球生產網絡[27],加速攫取金融利潤的歷史進程[22]。
第一,世界范圍內廣泛的通信、交通運輸和能源利用技術的革新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變革提供內生動力,成為全球生產網絡和金融化相統一的物質技術條件。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演化史就是一部技術爆發史。二戰后的資本主義“黃金時期”為技術創新提供了研發環境,也為消化二戰期間躍進的軍事技術轉化為生產力提供土壤[28]。至今,經歷了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洗禮,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主導的技術基礎,從電氣化走向數字化和信息化。其一,能源利用上,電氣時代使生產力的控制較蒸汽時代更精確,電流的微調實現了標準化與大規模生產[29],第三次科技革命使電力的生產從原始的水力火力來源,過渡到對核能、風能和太陽能等新能源,能源的轉化和利用效率提升,得以拓展大規模生產的邊界,也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繼續變革創造了特殊生產條件。數字化平臺條件下,以比特幣等虛擬數字貨幣為代表的新型金融化錨定物概念也相伴而生[30]。其二,通信技術上,第三次科技革命和較長的大范圍和平時期,使得世界范圍內的海底光纜和通信衛星網絡的構建成為現實,數字信號的電話通信以及互聯網技術的廣泛應用,縮短了全球資本生產和流通過程的時間和距離,有助于流通費用降低和流通時間縮短,為全球金融市場無縫對接的瞬時交易提供現實工具。其三,交通運輸上,管道運輸成為能源傳輸的主流,鐵路運輸的密度和強度增加,港口和空港的大規模建設為海洋和航空運輸提供一般生產條件[25],國際遠洋運輸的速度和容量提升,航空運輸的廣泛應用,使得國際多式聯運成為更高效的國際商品流通機制,以國際商品大宗交易為現實交易基礎的期貨市場也就逐漸繁榮,成為國際金融市場的重要補充。
新物質技術基礎的逐步確立,提升了資本和勞動的機動性[31],以計算機為核心的系統工程機器體系成為占主導地位的勞動資料形式,也為資本主義勞動過程內部的勞動組織變革提供新契機。
第二,世界范圍內的勞動力市場自由化和國際產業后備軍的形成,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變革提供勞動組織基礎,為全球生產網絡和金融化提供統一的勞動條件。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演化史就是一部勞動過程控制史。科學管理的泰勒制[32]在美國的確立為生產方式演化提供新方向,以去技能化控制的科學管理為精神的流水線福特主義催生大規模生產[33],與二戰后較穩定的經濟環境相配合。直至今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勞動過程控制不斷強化,導致勞動力市場不斷彈性化和自由化[26]。一方面,從以美國為代表的中心國家勞動力市場看,工會組織力量使工人暫時具備和資本議價的能力,勞動過程控制遇到瓶頸,資本憑借其沉淀在固定資本中分解勞動過程的技術,向外圍轉移尋求更為廉價和易控制的勞動力即國際產業后備軍[11],中心國家的勞動力面臨失業風險,失去資本的勞動力結成的工會組織也失去存在必要。資本以其在技術上的機動性,通過全球勞動者的間接競爭消解了工人的對抗,工人階級松散為原子化個人,參與勞動過程的形式逐步彈性化。勞動力再生產出現瓶頸,使其通過儲蓄基金的金融化[34],參與金融投機為其簡單生存尋求新的消費基金再分配。另一方面,從外圍國家的國際產業后備軍看,分布在全球的小生產勞動者,以靈活的形式參與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勞動過程中,以傳統雇傭形式參與生產過程,卻以“召之即來揮之即去”的彈性化形式就業,甚至成為“幽靈勞動”[35],與中心國家的自由化勞動力同等競爭,卻面臨更低的勞動待遇,也同樣面臨被迫從屬于金融化的命運。
勞動力市場的自由化與雇傭的彈性化,豐富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變革的價值基礎,進一步深化了勞動力商品化和產業后備軍擴張的邏輯,為更為廣闊的社會空間范圍內的生產方式變革提供張力。
第三,世界范圍內的地方生產網絡,對小生產方式的吸收及其全球生產網絡的嵌入,為全球生產網絡和金融化提供統一的社會空間條件。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演化史就是一部資本的空間拓荒史。對外貿易和世界市場為資本攫取更多剩余價值提供蓄水池[36],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也通過全球生產網絡,利用地方生產網絡在競爭機制中摧毀并收納小生產,確立其世界范圍內的統治。一方面,從全球生產網絡塑造并牽動地方生產網絡,資本擴展并依托生產者和購買者驅動的全球生產網絡,憑借其機動性尋求全球范圍內最優的生產區位,其間必然要考慮地方性制度、法律、文化、傳統等社會條件對可行技術和勞動過程的影響[27],形成參與國際分工的具體生產方式,從而推動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變革的道路安排,形成當地特色的地方生產網絡[21]。然而,地方生產網絡內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融資需求日益緊迫,對建立與全球金融市場相聯結的金融化機制安排起到推波助瀾作用。另一方面,從地方生產網絡摧毀并吸收小生產方式看,不同地方生產網絡內對生產條件要求差別很大,但存在具有最優生產條件的資本[37]。掌握不同條件的資本在競爭和淘汰中分化,一些僅要求取得低于平均利潤率乃至成本價格就得以維持其再生產的資本經過競爭篩選,其存活下來的部分雖能維持生存但積累較為單薄,增殖能力弱而規模始終較小,成為與其他資本進行競爭和議價的過程中處于劣勢的“小型資本”[38],而經過競爭淘汰而游離出的資本恢復貨幣形式則可能進入金融市場而參與金融化的進程。
全球生產網絡對地方生產網絡的塑造進而引發小生產方式分化,在更廣闊的社會范圍內拓展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生存的空間,為其在全球范圍內確立其統治提供社會基礎。
然而,只要民族國家的地方性經濟體存在,地方生產網絡的嵌入就將與全球生產網絡保持距離。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對小生產方式的摧毀與吸收的傳導機制就會不暢,資本發揮作用的空間就存在限度[13]。與國家權力天然保持距離,也正是新自由主義的鮮明屬性[39],資本權力就很難克服這一限度。但全球生產網絡與金融化的相統一,作為當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一體兩面”的主要矛盾,伴隨著外部沖擊其運動將為生產方式的演化帶來新的前途。
三、全球生產網絡與金融化相統一的現實矛盾運動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演化變革是當前世界經濟的主要矛盾,而全球生產網絡和金融化是這一矛盾的兩個主要方面。前者體現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社會屬性或公共屬性,使大面積的小生產方式消失而帶來陣痛,也有助于在全球范圍內創造更高的勞動生產力;后者則體現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私人屬性,雖能活躍經濟并融通資本,但放任了資本的無序擴張并可能使危機的爆發更為激烈。二者共同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走向終點指出路徑,也為當代資本主義經濟的演化多樣性提供依據。
其一,金融化克服全球生產網絡,將引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系統性危機。
根據馬克思的分析,生產過程中的活勞動創造價值,為資本的擴張帶來積累[28]。金融化作為資本實現剝奪式積累的收入再分配的典型形式,使資本自覺游離出生產(勞動)過程。金融化的個別資本增值顯得相對輕易,免去了經營和管理生產過程壓力與流通過程實現剩余價值的風險,加之一般利潤率下降趨勢,在個別資本尤其是“小型資本”層面,金融化也具有克服生產的天然傾向。金融化的無序擴張與金融化資本的增加,使得金融化的經濟系統內價值增值流入的合意速度未必能通過依附于實體經濟的生產(勞動)過程得到保障,則金融利潤率走低,終會因某一債務鏈條的斷裂導致整個金融化的經濟系統崩潰即金融爆炸[40]。同時,金融系統的價值增殖流入難以為繼,也多因外部系統的劇烈沖擊,暴露金融化經濟系統的整體脆弱性,危機和崩潰的頻發并經全球生產網絡傳導引發金融海嘯,這可能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出現新的變革調整,甚至局部消亡。
金融化克服全球生產網絡以及外部沖擊下發生危機的表現,以金融危機和新冠疫情流行下的經濟治理無力為代表。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源于債務鏈條的斷裂,美國憑借其處于全球生產網絡中的核心地位與國際貨幣權力,通過量化寬松向外圍地區以虹吸增殖價值的形式輸出金融化,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全球擴張形成的生產網絡成為金融化收入再分配的工具。幾次量化寬松的信用貨幣放水,將亞太眾多地區的房地價抬高[41],日常生活的金融化甚囂塵上[7],同時以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為代表的半中心和半外圍地區受到金融化滲透的趨勢更加凸顯。2020年新冠疫情蔓延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更是一時癱瘓。根據《國防生產法》,雖然美國總統有權緊急要求私營企業生產國防產品并控制經銷,但此前美國政府希望通用汽車公司能生產幾萬臺呼吸機救急,但企業認為成本太高,談判居然破裂[42]。抗疫物資的生產能力陷入無力使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疫情國的同時,美國股市更是史無前例地十天之內熔斷四次,約3萬億美元作為虛擬資本的流通手段而消失。產業資本家的損失也因此尤其突出,法國奢侈品巨頭路易·威登集團總裁貝爾納·阿爾諾(Bernard Arnault)在3月12日夜晚損失最多95億美元,第一季度個人損失高達370億美元;硅谷鋼鐵巨頭特斯拉首席執行官埃隆·馬斯克(ElonMusk)的凈資產在3月16日減少約40億美元,此前一個月內更是累計損失超過120億美元[43],若非在國家權力強制下關閉了紐約證券交易所來抑制金融滑坡,美國金融化引發的經濟衰退將更激烈,去生產過程的中心國家將陷入更深的經濟治理危機。外部沖擊下,金融化克服全球生產網絡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危機,也將可能引發資本家階級本身的進一步分化、解體與集中。
其二,全球生產網絡克服金融化,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將繼續充分發展,孕育帶有社會主義因素的新特征。
根據馬克思的分析,資本也力圖無限制地發展生產力[17],而全球生產網絡則帶來可能。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全球擴張,不光為其生產過程提供充足的國際產業后備軍,還得以積累更多可供資本更新的物質資料。資本被限制往金融化領域流動就可能固定在生產過程中,生產便得以繼續擴張以力圖無限制地發展生產力,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變革儲存新的能量。在半中心半外圍地帶,全球生產網絡克服金融化,會促進工人階級在機器體系的裝備下節約更多的勞動時間,資本的社會屬性克服私人屬性就能夠使剩余勞動時間更多地向工人階級的自由時間轉化,使工人可能自由而全面地發展[44]。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克服新自由主義占主導地位的生產網絡,強化了國家承擔社會職能的能力[24],資本的剩余得以可能社會共享[25],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就得以潛在孕育帶有社會主義因素的新特征。
全球生產網絡克服金融化,以瑞典等社會民主主義國家財富差距與收入差距的分化,以及不發達社會主義國家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歷史成就的繼承為主要代表。一方面,瑞典作為北歐社會民主主義國家的重要代表,自外于兩次世界大戰,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自由而充分發展的典型。其內部財富分配不均,2019年瑞典的財富基尼系數高達0.867,然而其收入分配較公平,雖然初次分配基尼系數高達0.5左右,但收入分配基尼系數僅0.3左右,其內部收入再分配調整起到了均衡分配的作用[45],憑借其高稅收和福利對其來自全球的剩余價值進行本國范圍內更為公平化的再分配,同時醫療、教育等少數關乎社會福利的領域則由公有經濟控制。瑞典金融業風險控制能力亦不低,主要銀行的不良貸款率常年保持在1%左右[46],致使其不至于金融化地出現收入的二次集中以及收入與財富再分配狀態的趨同,回避了金融化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充分發展的負面影響。另一方面,改革開放后的中國,在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前提下,充分利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成就,參與全球生產網絡的同時并提升對外直接投資在經濟中的地位。隨著利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深入與充分,中國的平臺經濟出現壟斷以及金融化的可能,制造業企業也出現從事金融活動的趨勢[47]。但隨著資本無序擴張監管的強化,所謂“脫實向虛”趨勢得到遏制。在資本的社會屬性克服私人屬性的斗爭方面成就突出,也較好地抵制了以美國為核心的中心國家輸出金融化壓力的系統性風險。
四、結語與展望
本文基于生產方式變革的視角,考察了全球生產網絡與金融化相統一的資本演化動力、生產方式路徑和現實矛盾運動。全球生產網絡和金融化相統一的孿生關系是利用商品、貨幣和資本等具體形式的邏輯結果,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變革是全球生產網絡和金融化相統一的實現機制,并且二者的統一推動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演化與走向歷史終點。展望未來,本文認為:
一方面,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占主導的社會形態向社會主義的過渡路徑是多樣化的。資本主義的充分發展實現向社會主義的過渡,為此,其國家政權將不斷通過改革緩和其內在矛盾。生產集中趨勢不斷將生產力推向更高水平,同時不斷揚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私人屬性并終以帶有社會主義因素的道路安排逐漸取代,最終引發社會形態的更迭,這一量變的緩慢過程指明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走向歷史終點的必然。資本主義的生產集中邁向帝國主義以充分發展的道路上,其矛盾激化引發動蕩可能會引發革命,而確立社會主義的社會形態。但實現具有本國特色的發達社會主義,要充分利用資本的生產方式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積極功用,以達致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充分演化的等同效果,以最終確立社會主義。雖然實現社會主義的過程存在差異,但卻殊途同歸。
另一方面,金融化與全球生產網絡相統一的孿生關系將作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主要矛盾始終伴隨。然而,全球生產網絡存在地理和民族國家的阻隔,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終將無法吸納小生產方式而走向終點;金融化給生產(勞動)過程的平均利潤率下降趨勢提供了新的出路,相對延緩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在矛盾爆發的時限,但通過金融系統的空轉帶來的風險擴張,無法避免新帝國主義矛盾危機的爆發。在全球生產網絡與金融化相統一的矛盾運動中,無論二者哪一方最終克服對方,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走向終點都具有必然性。
參考文獻:
[1]Bresser-Pereira L C.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and a new capitalism[J]. Journal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 2010, 32(4): 499-534.
[2]Mavroudeas S.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the COVID-19 pandemic[J]. International Critical Thought, 2020, 10(4): 559-565.
[3]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44.
[4]Stockhammer E. Financialization and the global economy[J]. Political Economy Research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2010, 242(40): 1-17.
[5]Kano L. Global value chain governance: A relational perspective[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18, 49(6): 684-705.
[6]Yu B. Neo-imperialism, the final stage of imperialism[J]. International Critical Thought, 2020, 10(4): 495-518.
[7]Martin R. Financialization of daily life[M].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02.
[8]Davis G F, Kim S. Financialization of the economy[J].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15, 41(1): 203-221.
[9]Krippner G R. The financialization of the American economy[J]. Socio-economic review, 2005, 3(2): 173-208.
[10]Terzea E R. The concep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main classic theories[J]. SEA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Science, 2016, 4(11): 243-246.
[11]Frbel F, Heinrichs J, Kreye O. The 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ur[J].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1978, 17(1): 123-142.
[12]Gibbon P. Upgrading primary production: A global commodity chain approach[J]. World development, 2001, 29(2): 345-363.
[13]Harvey D. The limits to capital[M]. Verso books, 2018.
[14]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5]Pottier C. Offshore production and global labor arbitrage: a new era of capitalism[G]//Radical Economics and Labour. Routledge, 2009: 169-182.
[16]Kumm K. The subsistence fund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labor power[J]. Problems in Economics, 1984, 26(12): 44-53.
[17]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草稿) [G]//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8]Aschheim J, Tavlas G S. Nominal anchors for monetary policy: a doctrinal analysis[J]. PSL Quarterly Review, 1994, 47(191).
[19]Hardie I, Maxfield S. Atlas constrained: the US external balance sheet and international monetary power[J].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016, 23(4): 583-613.
[20]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1]李直,劉越.馬克思主義視角下的當代國際分工理論:缺失、復歸與融合[J].政治經濟學評論,2022,13(5):166-187.
[22]Lapavitsas C, Levina I. Financial profit: Profit from production and profit upon alienation[R]. 2010.
[23]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1861-1863年草稿)[G]//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24]恩格斯.反杜林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25]劉越,王小軍.生產條件的躍遷與生產方式的演化:邁向共同富裕的政治經濟學分析[J].青海社會科學,2022(3):97-106,116.
[26]Brodsky M M. Labor market flexibility: a changing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J]. Monthly Lab. Rev., 1994, 117: 53.
[27]Coe N M, Dicken P, Hess M.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realizing the potential[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08, 8(3): 271-295.
[28]David F N. Forces of production: A social history of industrial automation[M]. Routledge, 2017.
[29]Tsigkas A. Open lean electricity supply communities[J]. Energy systems, 2011, 2(3): 407-422.
[30]Wang W, Li X, Zhao H. DCAF: Dynamic cross-chain anchoring framework using smart contracts[J]. The Computer Journal, 2022, 65(8): 2164-2182.
[31]大衛·哈維.資本的限度[M].北京:中信出版集團,2017:373.
[32]Taylor F W. The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M]. Harper & brothers, 1919.
[33]Williams K, Haslam C, Williams J. Ford versus ‘Fordism: The beginning of mass production[J]. Work, Employment and Society, 1992, 6(4): 517-555.
[34]Langley P. Uncertain subjects of Anglo-American financialization[J]. Cultural critique, 2007 (65): 67-91.
[35]Gray M L, Suri S. Ghost work: How to stop Silicon Valley from building a new global underclass[M]. Eamon Dolan Books, 2019.
[36]Foley D K. Rethinking financial capitalism and the “information” economy[J].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2013, 45(3): 257-268.
[37]Shaikh A. Capitalism: Competition, conflict, crise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265.
[38]Starosta G. Global commodity chains and the Marxian law of value[J]. Antipode, 2010, 42(2): 433-465.
[39]Guazzone L. The Arab state and neo-liberal globalization: The restructuring of state power in the Middle East[M]. Garnet Publishing Ltd, 2009.
[40]Magdoff H, Sweezy P M. Stagnation and the financial explosion[M]. Aakar Books, 2008.
[41]Hudson M. US‘quantitative easingis fracturing the global economy[J]. Bard College Levy Economics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2010 (639).
[42]特朗普動用《國防生產法》要求通用汽車公司生產呼吸機[N/OL].(2021-07-31)[2022-09-14].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20-03/28/c_1125779610.htm.
[43]全球首富貝索斯一天損失70億美元,過去1個月身價減少180億美元[N/OL].(2021-07-31)[2022-09-14].https://new.qq.com/omn/TEC20200/TEC2020031002017900.html.
[44]馬克思.德意志意識形態(節選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119.
[45]高建昆,陳海若.瑞典財富與收入的不平等擴大趨勢及成因分析[J].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20(4):131-139.
[46]閻維潔.瑞典經濟發展模式及啟示[J].宏觀經濟管理,2019(8):75-79,85.
[47]Fang F. A study of financial risks of listed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in China[J]. Journal of financial risk management, 2016, 5(4): 229-2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