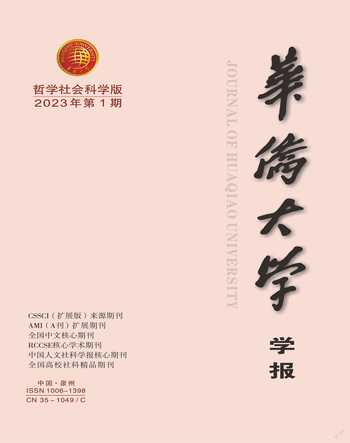國際因素考量與中共歷史決議書寫
摘 要:
中共起草《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并非源自外發性的國際肇因,但國際社會對中國政治局勢的擔憂、對重大歷史問題評價的猜忌、對所謂社會主義革命失敗的指責以及對肯定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期冀,為起草工作既提供著由外而內的異域視角,亦提示著由此及彼的闡證路徑。中共及時回應關切、鄭重表達立場、反復闡證觀點,飽含著對評價建國以來重大歷史問題相關原則、方法、觀點的深刻思考,同時也有效推動了對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實事求是和恰如其分地評價“文化大革命”,以及毛澤東的功過等三大核心論題的“論證、闡述和概括”。中共此舉,既有助于總結經驗、統一思想、團結一致向前看,更有利于建構新時期黨和國家的嶄新形象,為助益于成功書寫黨的第二個重大歷史決議,以及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局面奠定重要政治基礎。
關鍵詞:中國共產黨;國際因素;《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歷史書寫
作者簡介:許沖,華南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法學博士,主要研究方向: 中共黨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E-mail:zsuxuchong@163.com; 廣東 廣州 510631)。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中國共產黨創建史的百年記憶建構研究”(22ADJ004)
中圖分類號:A811;J0-0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398(2023)01-0005-13
2021年是《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下稱《決議》)正式通過40周年,對于中共而言,這是黨的百年歷史上第二次以中央名義就重大歷史問題作出決議。在《決議》起草過程中,中共“放眼四面八方,既看到了國內國外,也看到了黨內黨外”,并在歷經起草、修改、討論、完善以及中央會議審議通過的繁復過程后,成就了一份兼具“科學權威(符合實際)和組織權威(中央通過)的經典文獻”【龔育之:《黨史札記》一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43、196頁。】。遺憾的是,目前學術界的相關研究,雖從文件起草過程、黨的歷史經驗總結、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關系、對黨史和國史研究的推進等維度進行了有益探索,【相關成果主要包括陳東林:《論<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國史研究的奠基和指導作用》,《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10年第9期;沙健孫:《科學地研究和宣傳黨的歷史——紀念<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通過30周年》,《當代中國史研究》2011年第4期;黃一兵:《理論工作務虛會與<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起草》,《中共黨史研究》2013年第4期;宋月紅:《起草黨的第二個歷史決議的思想史料整理與研究》,《中共黨史研究》2014年第4期;李曉培:《<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湖南大學,博士論文,2017年;李捷:《總結過去、開辟未來的經典之作——重溫<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湘潭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1期;夏春濤:《從百年黨史看兩個“歷史決議”的偉大意義》,《毛澤東研究》2021年第3期。】但多側重于歷史史實的線性爬梳和經驗總結方法的抽象歸納,較少系統研辨來自“四面八方”的文件起草影響因素,特別是對其中著墨不多卻考量再三的國際因素考察更是尚付闕如。眾所周知,起草《決議》涉及對黨的重大歷史問題的評價與闡釋,“不只是個理論問題,尤其是個政治問題,是國際國內的很大的政治問題”【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684頁。】。究其要義,“對待毛澤東同志、對待毛澤東思想的態度,不單是中國的問題,也是世界性的問題;不單是我們這一代人的問題,也是關系到子孫后代的問題”【《胡耀邦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09頁。】。這就意味著,缺少國際因素考量的《決議》起草論題及其相關研究,恐將是難以想象,甚至是無法理解的。有鑒于此,本文就該論題作一簡要探討。
一 關切與考量:《決議》起草的多重外部語境
作為一個將“要放到歷史里面去的一個文件”【《鄧小平文選》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09頁。】,對于《決議》是否寫入國際問題,在起草之初就是個“比較麻煩的問題”:一方面,國際問題直接涉及外交工作以及對某些國內問題的書寫;另一方面,在寫法上即便從正面寫,最后也有可能是吃力不討好。【《胡喬木傳》編寫組編:《胡喬木談中共黨史(修訂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54頁。】在開始《決議》起草之前,為說明建國三十周年慶祝大會講話的起草情況,胡喬木就曾轉述鄧小平對國際問題寫作的類似擔憂:國際上重視中國對國際問題的講法,不講以為我們不關心,少講容易使人不滿,講了還有可能被人利用。【《胡喬木傳》編寫組編:《胡喬木談中共黨史(修訂本)》,第52頁。】為此,胡喬木提醒《決議》起草小組的成員:“不要涉及國際問題,我們答復不了。但國內問題包括我們的對外政策一定要講清楚。”【《胡喬木傳》編寫組編:《胡喬木談中共黨史(修訂本)》,第64頁。】也就是說,在《決議》中即便能夠對國際問題秉筆直書,也恐將面臨進退失據的尷尬境地。但不容忽視的是,《決議》雖然可以回避對國際問題的直接評議,但就所涉歷史、理論以及現實問題來看,它既不可能規避國際因素的影響,也不可能漠視國際社會的關切,更不可能舍棄對外政策的考量。基于此,所謂《決議》起草中必須考量的國際因素,并非針對具體的國際議題做出評價而論,卻是源自國際社會對個中所涉重大論題的復雜認知和多重關切,以及中共根據內政外交需要所須因應的國際訴求和所應考量的政策方案。
基于上述研判,并綜合檢視撥亂反正時期國際上的涉中輿論,首先被納入《決議》起草考量范圍的域外關切,乃是對中國政治局勢的擔憂。在歷經“文化大革命”十年內亂后,國際社會對中國問題的核心擔憂,毫無疑問是能否保持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事實上,這并非完全是出于政治同情或者國際友誼,而是基于自身利益的多重考量。從《決議》起草前后的中國政策背景看,隨著撥亂反正的推進,黨和國家的工作中心不僅逐漸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而且還作出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因此,能否確保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和政治氛圍,就成為國際國內普遍關注的焦點:從內部來講,“安定團結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必要政治條件”;從外部來看,“國際上也十分注意我們國內局勢是不是能夠保持穩定。引進新技術,利用外資,你穩定了,人家才敢和你打交道”【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思想年譜(1975—1997)》,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第92頁。】。日本團體在討論對華投資風險時,就曾發出兩種聲音:一是中國政局穩固,可放心投資;二是以段祺瑞政府時期對華貸款無法收回為鑒戒,現實地擔心“四人幫”會卷土重來。【《胡喬木傳》編寫組編:《胡喬木談中共黨史(修訂本)》,第51頁。】因此,為切實貫徹對外開放政策,中共務須直面國際社會的兩大關切:一是中國是否具有引進技術和資金的償付能力,二是中國的政策是否具有連續性暨穩定性。【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卷,第495頁。】與此同時,黨內高層人事變動是否會造成權力斗爭的外部印象【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卷,第455頁。】,對經濟政策的“調整”是否意味著“收縮”【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思想年譜(1975—1997)》,第123頁。】或“后退”【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754頁。】,以及動議起草中的《決議》能否最終通過等種種擔憂【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卷,第472頁。】,也均影響著國際社會對中國局勢的研判。
可見,安定團結因素確系中共起草《決議》時務須傾聽的“域外之音”,但它背后還潛藏著國際社會的“弦外之意”,也即是對評價中國重大歷史問題的猜疑。作為安定團結問題的重要肇因,它隨即成為國際關切的第二個焦點。整體考量撥亂反正時期中共政治運行的邏輯,基本政治操作是先批判林彪和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再起草、修改、審議和通過《決議》,最后以此為基礎召開黨的十二大。其實,此舉不僅是為了確認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是犯了錯誤,而“四人幫”等是在犯罪【《鄧小平關于正確評價毛澤東和起草歷史問題決議的談話選載》,《黨的文獻》2011年第3期。】,更在于劃清毛澤東思想與毛澤東晚年錯誤的界限,借以統一思想和集中全黨力量進行四個現代化建設。然而,中共精心擘畫的政治操作,實際并未得到國際社會的完全認可。只因在具體的政治實踐中,無論是為天安門事件和劉少奇同志平反,還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論與實踐,抑或推行旨在消除個人崇拜的政治舉措(在全國范圍內拆除毛主席塑像和掛像)等,無不在國際社會引發種種猜疑。單就鄧小平在《決議》起草階段慮及之處,既有國際上“對毛主席的評價可不可以像對斯大林評價那樣三七開” 的直接質問【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卷,第435頁。】,也有對中國在搞“非毛化”的各種非議【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卷,第474頁。 】,還有所謂“赫魯曉夫時代又殺回”中國的胡亂猜測,甚至連港臺報刊也大肆鼓噪“大陸批毛,勢在必行”。對于國際社會的縱聲喧嘩,鄧小平嚴正地指出:“國際上很關心”對毛澤東功過以及“文化大革命”的評價,不但存有全面否定和全面肯定毛主席的兩種聲音,【《鄧小平關于正確評價毛澤東和起草歷史問題決議的談話選載》,《黨的文獻》2011年第3期。】而且“各方面的朋友都在注意我們怎么說”【《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91頁。】。這就意味著,即便中共不打算起草《決議》,也必須以“慎重”和“實事求是”的態度來因應國際社會的猜疑【《鄧小平關于正確評價毛澤東和起草歷史問題決議的談話選載》,《黨的文獻》2011年第3期。】。
從本質上看,上述猜疑實屬于歷史向度的現實關切,更多折射出國際社會對中國現實政策和政治走向的一種擔憂,但這不代表他們對建國以來的歷史和理論問題就毫無疑惑。其中,因對“文化大革命”的多重誤讀而催生的所謂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失敗論,也隨即構成國際社會的第三重關切。胡喬木曾說,“文化大革命”的歷史在世界歷史上是“千年不遇”的【《胡喬木傳》編寫組編:《胡喬木談中共黨史(修訂本)》,第94頁。】。對此,國際上特別是一些左派小黨及其知識分子的認知與中共多有分歧,并因政治理念沖突而屢加責問中方。在起草《決議》期間,胡喬木反復告誡起草小組成員:國際上對“文化大革命”既有“擁護”和“贊頌”的,也有“同情”和“惋惜”的,還有因其所謂以失敗告終心生“失望”和“迷茫”的;具體來說,他們或是認為“文化大革命”使中國繼續保持了“革命”的勢頭和勁頭,是全世界共產黨奪取政權后唯一在搞社會主義的(其他政黨都在搞經濟建設),或是強調毛澤東借“文化大革命”提出了“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的現實政治問題并力圖加以解決,既推動了“社會主義社會革命化”,又“鏟除了官僚階層”,所以是個具有“好的方面”和“好的理想”的“勇敢的嘗試”【《胡喬木傳》編寫組編:《胡喬木談中共黨史(修訂本)》,第59、76、80、135、137、84頁。】。及至中共提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著力推進改革開放和四個現代化建設時,原先因由國際反修和防修而集中在“文化大革命”旗幟下的左派小黨及其知識分子們,不僅質疑“中國是否走到跟蘇聯一樣的道路去”,甚至還指責“中國已經叛變了”社會主義革命;而當中國徹底打倒“四人幫”,他們又再度指責世界工人運動的前途因此破滅了。【《胡喬木傳》編寫組編:《胡喬木談中共黨史(修訂本)》,第61—62頁。】客觀而言,國際社會的諸種誤解與責問,與中共過往的政治宣傳和毛澤東的崇高威信也不無關系。【《胡喬木傳》編寫組編:《胡喬木談中共黨史(修訂本)》,第62頁。】所以,中共確有責任借起草《決議》為契機,從歷史、理論和實踐上做出正面的回應與解釋,并藉此給予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以“現實的”和“理想的”力量【《胡喬木傳》編寫組編:《胡喬木談中共黨史(修訂本)》,第63頁。】。
與此相對,第三世界國家對中國問題的核心關切,與歐洲左派小黨及其知識分子的責問可謂大相徑庭,而是特別表現出對肯定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殷切期待。究其緣由,這與第三世界國家的民族獨立和解放運動不無關系。其實,早在動議起草《決議》前,對如何闡釋毛澤東思想和中國革命經驗的國際價值,胡喬木就曾主張不要“自說自話”,因為“世界上除少數幾個黨以外,已掌握政權的國家的黨沒有一個接受我們關于毛澤東思想的過分的提法”【《胡喬木傳》編寫組編:《胡喬木談中共黨史(修訂本)》,第45—46頁。】。所以,這個問題本來就是應由各國、各黨根據自身實際和實踐加以評價的。事實也確實如此。坦桑尼亞總統尼雷爾就曾告訴鄧小平他不贊成“文化大革命”,所以能夠接受中共對其展開批評,但強調“毛澤東思想無論如何不能丟掉”;津巴布韋總統穆加貝也指出:自己雖然對“文化大革命”知之甚少,但津巴布韋獲得獨立主要是靠毛澤東思想,是易懂、管用且符合實際的《毛澤東選集》第一至四卷的內容指導著津巴布韋獲得勝利,因此他特別關心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的評價問題,認為毛主席是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的領袖,并希望中共在任何時候都不要丟掉毛澤東思想。【《鄧力群文集》第1卷,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年,第545—546頁。】與此相對,國際上還有不少人對“文化大革命”報以同情,也不贊成過分批評和否定毛澤東。比如,埃及理論家就曾提出既不要把毛主席說得太壞,也不要把“文化大革命”說得太壞。顯然,此中的期冀明顯缺乏對“文化大革命”的性質“不是革命而是個內亂”的清醒認識,但它也會同前述關切代表著國際社會的一種聲音:在評價毛澤東的問題上,無論是“錯誤講過分”,還是“評價不恰當”,均“有相當一部分人不能接受”【《胡喬木傳》編寫組編:《胡喬木談中共黨史(修訂本)》,第137—138頁。】。
除上述四種關切外,在部分國際人士中還存有社會主義經濟不存在客觀規律、“文化大革命”中實現了社會主義、毛澤東主義就是毛澤東的晚期思想等理論誤讀【《胡喬木傳》編寫組編:《胡喬木談中共黨史(修訂本)》,第67、80、83、140頁。】。凡此種種,也均被納入《決議》起草的考量范圍。不僅如此,這些表面看似互有差異的外部關切,并非是單向度的存在,內在里均有著高度互聯的復雜關系。如鄧小平所言,外國人對其他事情沒有興趣,主要看中國安定與否,但實現安定團結的首要前提是看中共能否“堅決地維護毛主席這面偉大旗幟”,而這本身就是個“很重要的國際影響問題”【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卷,第493、445頁。】;特別是,論及“國際上很關心”的“文化大革命”評價問題,其實也“涉及到毛主席的問題”【《鄧小平關于正確評價毛澤東和起草歷史問題決議的談話選載》,《黨的文獻》2011年第3期。】。可見,基于由外而內的視閾來審度國際關切中的重大議題,其實與中共起草《決議》的“中心意思”是基本相符的,單就個中差異看,也僅是國際社會未能從“建國三十年來歷史”以及“基本的總結”的維度來提問而已;但不管以何種方式來提問,均須中共作出及時回應和合理解釋,只因這不僅是服從中央戰略部署的“大局”和符合黨、國家以及人民利益的要求,而且還能夠讓國際社會對中國放心。【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卷,第610、495頁。】
二 回應與擘畫:《決議》起草的現實政治考量
如何因應國內國外和黨內黨外的共同關切,中共原本有著不同的考量。相比較而言,鑒于國際社會特別是在外交層面對中國問題的熱切關注,中共務須作出及時回應,甚至予以鄭重表態。事實上,這與鄧小平最初的構想大有不同(待時機和條件成熟后再系統總結建國以來的重大歷史問題),但不容忽視的是,中共高層在涉外場域的回應與表態,實際蘊含著解答和評價建國以來重大歷史問題的原則、思路、方法甚至核心觀點。至中央正式動議起草《決議》,國際關切與中共高應間的思想共振也并未停止,而是循著滿足國內國外和黨內黨外對《決議》“最核心、最根本的問題”施以論證、闡述和概括的綜合要求【《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96頁。】,繼續提供著由外而內的廣闊視野,以及提示著由表及里的論證路徑【《胡喬木傳》編寫組編:《胡喬木談中共黨史(修訂本)》,第92頁。】。
在動議起草《決議》前,面對國際社會甚囂塵上的“非毛化”議論,鄧小平就曾一方面向美國作家羅伯特堅稱“黨中央、中國人民永遠不會干赫魯曉夫那樣的事”,另一方面又歷史地肯定“沒有毛澤東主席就沒有新中國”,直言中共將沿用毛澤東本人所提倡的“把馬列主義的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以及“反對本本主義”的思想方法來對待毛澤東思想,據以“完整地、準確地掌握和運用毛澤東思想”,解決“毛主席在世時不可能提出”的問題【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卷,第438頁。】。而在做出上述表達的同一天晚上,鄧小平還向中央工作會議各組召集人重申:毛主席的偉大功勛不可磨滅,缺點錯誤也不能回避,對他的評價絕不可以像赫魯曉夫對待斯大林那樣。【《胡喬木傳》編寫組編:《胡喬木談中共黨史(修訂本)》,第95頁。】不僅如此,隨后在會見美國時代出版公司代表時,鄧小平再次就所謂“非毛化”問題鄭重表態:不論現在還是以后,毛澤東思想仍舊是黨的指導思想,不應苛求偉大人物沒有缺點和錯誤,當前根據現實提出毛主席生前沒有條件提出的問題并加以解決是完全應該的,這并不是什么“非毛化”,而是按照毛主席、周總理生前確定的原則和繪制的藍圖來建設國家與實行對外政策。【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卷,第474頁。】至于國際上高度關注的安定團結等問題,鄧小平也對到訪的日本公明黨委員長再度強調:中共是“按照毛主席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方針”來撥亂反正,據以創造良好政治氣氛和安定團結政治局面,一心一意搞好四個現代化建設。【《胡喬木傳》編寫組編:《胡喬木談中共黨史(修訂本)》,第97頁。】借助頻繁的外事活動,鄧小平直接回應了國際關切,同時也逐步明確了中共對待黨的重大歷史問題的基本態度、原則和方針,這就為擇機起草《決議》做了必要準備。
至1979年10月下旬,中央正式動議起草《決議》,鄧小平提出可以國慶三十周年講話為綱要,并作進一步的具體化和深化。【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卷,第574頁。】客觀而言,盡管該講話在發表后曾引發國內外的積極評價【《鄧力群文集》第1卷,第269頁。】,實際上它仍不足以給建國三十年的歷史和“文化大革命”等重大問題做出全面和具體的總結。對此,胡喬木最初設想是先確定“究竟要寫幾個什么問題”,然后再研究整體寫法和對國際問題的說法,進而專注于對重大事件發生背景的分析,以及對發生問題作理論上的評論【《胡喬木傳》編寫組編:《胡喬木談中共黨史(修訂本)》,第54—55頁。】;至于所謂的核心問題,他在同《決議》起草小組成員談話時指出:基于“文化大革命”錯誤的嚴重性和堅持毛澤東思想的重要性,必須闡明前者發生的原因和后者的本質內涵以及現實價值。【《胡喬木傳》編寫組編:《胡喬木談中共黨史(修訂本)》,第54—56頁。】如若不然,中共既難以消解國際上對“文化大革命”的多重誤讀,也可能因為缺少對中共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科學理論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的權威表達,而使人誤解黨的性質已經發生了改變【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卷,第600頁。】。基于上述考量,《決議》起草小組擬定了寫作提綱,但鄧小平在看后卻指示:應采用集中寫法對重要問題做出論斷,針對黨內黨外和國內國外都很關心的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評價問題,著重寫清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和形成的過程,對其主要內容特別是今后還要繼續貫徹執行的內容,要用比較概括的語言寫出來,同時實事求是地分析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錯誤。【《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91—292頁。】由此,從胡喬木的“最初設想”到鄧小平的三點“中心意思”,中央逐步厘定《決議》寫作的核心論題。它既涵蓋了建國以來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重點、難點和焦點問題,也囊括了國際社會所“關心”“議論”和“注意”最多的問題,從本質意義上看,這兩者實際具有著明顯的論題一致性。
藉由上述鋪墊,《決議》的起草工作有序推進,鄧小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在與起草小組保持即時溝通的同時,仍不忘借助外事活動繼續申明中共對重大歷史問題的立場、態度與觀點。在1980年4月至5月間,鄧小平先是向起草小組建議《決議》起草的“整個設計”應包括前言、建國以來十七年、“文化大革命”、毛澤東思想和結語等五個部分,后是再度強調論證、闡述和概括“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的問題,已成為黨內黨外和國內國外的迫切要求。【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卷,第291—292頁。】緊接著,面對歐美以及非洲各界人士的關切,鄧小平再度對外重申:一方面,中國現行的政策是遵循毛主席制定的政策的,也是在恢復毛澤東思想的本來面目【《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619頁。】,毛主席的偉大之處是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另一方面,應重視研究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概括中國建國三十年來的經驗,其中的關鍵,是不要離開現實和超越階段采取“左”的辦法,以及堅持有利于發展生產力的原則【《胡喬木傳》編寫組編:《胡喬木談中共黨史(修訂本)》,第154—155頁。】。鄧小平的如此回應,已不止“向客人介紹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教訓”,實際蘊含著對同期《決議》起草“難題”的具體思考與破解。究其緣由,也正如鄧小平在外事活動中所言,不管是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問題,還是世界的社會主義運動實踐,僅從好聽的“名字”或“名稱”出發,既難以揭示社會主義的本質,更不可能客觀評價毛澤東同志和毛澤東思想。【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卷,第629頁。】
客觀而言,藉由起草《決議》系統總結經驗和解釋歷史原委,絕非直接回應國際關切和評論歷史功過那般簡單,也更非撰寫黨政報告或節慶紀念講話所能比擬。胡喬木曾言,《決議》若不能答復“文化大革命”為何發生之類的重大論題,這“就等于不作”;即便從中得出了經驗教訓,也將是一場“空論”【《胡喬木傳》編寫組編:《胡喬木談中共黨史(修訂本)》,第94頁。】。由此可見《決議》起草工作之不易。所以,當鄧小平看到《決議》初稿時,直言它“沒有很好體現原先的設想”,即沒有抓住闡明“毛澤東思想是什么和毛澤東正確的東西是什么”這個寫作“重點”【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卷,第694頁。】,自然也就無法解釋毛澤東為什么會在“文化大革命”中犯錯。不妨設想,如果連《決議》起草者自身都不能將毛澤東晚年思想上和行動上的錯誤同毛澤東思想加以區別與對照,那么國內外各界人士又如何能形成對“文化大革命”及其發動者的客觀評價,進而正面回應社會主義革命在蘇聯之后的中國是否已經失敗的質問呢?這就意味著,中共對上述問題務須做出更權威、更科學和更客觀的評價。因此,當面對意大利記者法拉奇有關天安門城樓是否繼續懸掛毛主席像的敏感提問時,鄧小平不僅給予了肯定答復,而且借機再度聲明:客觀評價毛主席一生的功過,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中共繼續堅持的毛澤東思想,是毛主席一生中正確的部分,它在過去引導中國取得革命勝利,現在和將來還應是黨和國家的寶貴財富;對毛主席后期的錯誤,中共將實事求是地加以評價。【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卷,第665—666頁。】藉此涉外場域,特別是面向媒體人士的“慎重”表態,看似在直面歷史問題和回應國際關切,但它已遠超從常規意義厘定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評價基調,確是在本質意義上標定了《決議》行文運思的政治邏輯甚至最終結論。可以說,如此因應也并非僅為回答法拉奇的一時提問,隨著鄧小平本著“真正實事求是”的原則向竹入義勝再度重申上述觀點【《鄧小平關于正確評價毛澤東和起草歷史問題決議的談話選載》,《黨的文獻》2011年第3期。】,他業已向黨內和國內徹底闡明了“寫不寫、怎么寫”毛澤東同志的功過和評價毛澤東思想這兩個“國際國內的很大的政治問題”【《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98—299頁。】。
鄧小平向法拉奇和竹入義勝所表達的立場和觀點,對完成《決議》的起草工作,特別是評價毛澤東的功過是非和毛澤東思想的重大論題而言,實際具有著標志性的政治意涵。由此,《決議》起草小組的基本工作就應是以“寫好這個問題”為前提,“實事求是地分清建國以來黨的歷史上的是和非、對和錯,包括個人的功過”【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卷,第721頁。】。對鄧小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來說,由此亦可以理直氣壯地回應國際社會:建國三十年來“成績不少,雖然也犯了一些錯誤,但不是一片漆黑”【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卷,第700頁。】,“我們沒有搞‘非毛化,我們堅持毛澤東思想”【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卷,第709頁。】,中國的對外政策不會改變,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也有保障。甚至于,還可以繼續借外事活動向亞歐等國的共產黨領導人“重新”定義毛澤東思想的“概念”:它就“是把馬列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根據中國的實際,運用馬列主義原理,尋求自己革命的道路,包括方式”【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卷,第692頁。】;抑或,它是在中國共產黨建黨以后、尤其是在遵義會議后逐漸形成的,隨后經由黨的七大肯定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和中國革命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是對中國革命經驗的總結,而且“對世界也有貢獻”【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卷,第734頁。】。
言及至此,可以確證鄧小平所言不虛,“世界上有好多議論都是一種不了解中國實際情況的猜測”,而藉由外事活動中的直接回應來助力《決議》的起草工作,其價值遠不止于解疑釋惑或增進互信,更在于對外消除誤解、建構形象和樹立信心,對內省察問題、啟迪思路和總結經驗。更何況,循此由外而內的政治邏輯來消解中共的歷史難題,不僅有助于“教育我們的人民和后代,也教育我們自己”,而且更有益于拓寬中共《決議》起草工作的國際視野【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卷,第709頁。】。在此基點上,《決議》起草工作的核心內容,就應當以客觀的論據為基礎,系統論證國際關切與國內矚目的重大論題的真實性,據以做好對毛澤東思想和中國革命建設經驗的系統闡述,以及形成對毛澤東功過是非和“文化大革命”的歷史性評價。
三 論證與闡述:《決議》起草的核心論題求解
藉由前述梳辨可見,中共在起草《決議》過程中務須論證并闡述清楚三大基本論題:一是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二是實事求是和恰如其分地評價“文化大革命”,三是客觀評價毛澤東的功過。【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卷,第750頁。】能否對此做出合乎歷史與邏輯的論證,特別是在理論上予以闡明和解釋,將不止影響對國際關切的深度回應,更關系《決議》能否最終出臺以及發揮類似《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作用,起到總結經驗、統一思想、團結一致向前看的作用。可見,在撥亂反正期間做好此項工作,將是綜合考驗中共歷史自覺、政治智慧和科學精神的重大政治工程。
如前所述,起草《決議》雖不同于撰寫歷史文本,卻也同樣是從歷史結果出發的,需要對相關論題做回溯式研究和前瞻性敘事。從政治歷史思維和論證技術路線看,鄧小平在開始起草前就已認識到“歷史問題只能搞粗,不能搞細”,既應堅持“有錯必糾”的原則,還應秉持服從大局和“向前看”的思路【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卷,第445、451頁。】。進入正式起草階段后,胡喬木與鄧力群進一步主張“要講歷史,要講理論”,不能陷入具體的歷史事件之中而“只見樹木,不見森林”;換言之,可以采用“回顧歷史的形式”來講清問題,但無需把每個“問題說得很詳盡具體”,重點是“在原則上把問題講得更透”【《胡喬木傳》編寫組編:《胡喬木談中共黨史(修訂本)》,第61—62頁。】。所以,在起草《決議》過程中,具有前提性的宏觀歷史評述問題應當率先敲定,這也是鄧小平向起草小組反復明確的。具體而論,就是延安時期是毛澤東思想“比較完整地形成”階段【《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92頁。】,新中國成立后的十七年有曲折也有錯誤,但基本方面是對的,毛澤東在由社會主義革命轉入建設階段后,也有好的文章和好的思想【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卷,第614頁。】。若單就后者而言,前七年取得了公認的成績,社會主義改造獲得成功,雖然部分工作急了一些,但確是毛澤東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重大貢獻;后十年也應當肯定,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發展,中間雖有曲折甚至犯過錯誤,但成績是主要的;至于“文化大革命”,無疑“是嚴重的、全局性的錯誤”,而在此期間也有健康的方面【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卷,第721頁。】。仔細考量可見,鄧小平對建國以來歷史的階段性判定與整體性評述,實際已經涵蓋了對《決議》“整個設計”的全部內容。同時,胡喬木作為具體領導起草工作的負責人,也逐段分析了建國以來的歷史,還對“文化大革命”的發生原因和發展演變過程,毛澤東思想產生、發展和形成條件等重大論題,或從國內國際兩個維度進行社會歷史分析,或將其置于國際共運史、中共黨史甚至資產階級革命史的維度加以比鑒和判定,這就為“客觀的,信實的,公允的,全面的”論證和闡釋前述論題提供了歷史依據。【《胡喬木傳》編寫組編:《胡喬木談中共黨史(修訂本)》,第148頁。】
若就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的論證與闡述看,在《決議》起草工作開始前,鄧小平對此已經多有論述,既將其視作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團結的旗幟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旗幟,亦強調它關系到安定團結和具有重要的國際影響,全黨應從黨的思想路線和政治路線的高度予以重視。【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卷,第435、493、537頁。】在與陳云的討論中,二人均強調毛澤東思想不僅絕對不能丟掉,而且在起草《決議》時“這項工作要做細。蘇聯丟了(黨的指導思想),結果吃了虧”。【韓泰倫主編:《紅墻檔案》第3卷,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333頁。】至起草工作正式開始,他再度強調應從“原則”的高度上加以“覺悟”和“認識”,只因此論題乃是中國共產黨、中華民族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利益所在”【轉自程中原:《在歷史轉折過程中鄧小平怎樣堅持毛澤東思想》,《淮陰師范學院學報》1999年第3期。】。比較而言,前后兩個階段論析的政治意指是基本相同的,但后者更為嚴謹和明確。在涉及具體內容的論證和闡述方面,鄧小平強調應以“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為根本,據以在《決議》中“正確評價毛澤東思想,科學地確立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卷,第614頁。】。與此同時,胡喬木也歷數黨的歷史上對毛澤東思想概念的“解釋的變化”,先是主張不采取“過分的提法”,后是強調要抓住“毛澤東思想的實質”【《胡喬木傳》編寫組編:《胡喬木談中共黨史(修訂本)》,第46、56頁。】。如此論證思路,彰顯出歷史與邏輯相統一的辯證要求,但它距離從理論上闡釋清楚如何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還遠遠不夠。其中,對“毛澤東晚年思想”的界定就是個難題,鄧小平在與胡耀邦等人討論后,基于嚴肅歷史和理論表述的考量,商定將其改為“毛澤東晚年的錯誤”【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卷,第646頁。】。但即便如此,《決議》初稿也未能完全實現對毛澤東思想的“充分地表達”,自然也就無法為恢復、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的歷史書寫和理論表達“提供一個基礎”【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卷,第649頁。】。
有鑒于此,同時也為深度因應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中的理論誤讀,胡喬木提出要把毛主席晚年的錯誤同毛澤東思想加以區別,對前者進行理論的和實踐的批判,對后者加以肯定。【《胡喬木傳》編寫組編:《胡喬木談中共黨史(修訂本)》,第84頁。】考慮到毛澤東思想在國際上已然形成“兩種形象”,他強調要繼承和發展中國革命為世界展現新的光明前景和提供新的前途的形象。【《胡喬木傳》編寫組編:《胡喬木談中共黨史(修訂本)》,第90頁。】基于此,從國際社會歷史背景(特別是共產國際的影響)出發,闡明毛澤東思想產生的背景和條件,從國際社會混同毛澤東主義即毛澤東同志的晚期思想出發,闡明中共并不是堅持毛澤東主義,“而是堅持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與中國的實際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胡喬木傳》編寫組編:《胡喬木談中共黨史(修訂本)》,第105—106、126—127、140頁。】,對樹立和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無疑具有內外雙重價值。如此界定毛澤東思想的意涵,與前述鄧小平的涉外回應如出一轍。不僅如此,再至羅馬尼亞政府總理維爾德茨到訪,他又將對前述論題的闡析升格為“確立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進一步區別于毛澤東后期所犯的錯誤【《鄧小平關于正確評價毛澤東和起草歷史問題決議的談話選載》,《黨的文獻》2011年第3期。】。
言及至此,本論題看似已得到縝密而又嚴肅的論證和闡述,但事實并非如此,只因它還缺少一個“全面的根據”和整體的“分析”作為歷史支撐和理論依據。對此,陳云關于“增加回顧建國以前二十八年歷史的段落”的重要建議,無疑為從黨的整個歷史(特別是毛澤東在這六十年中重要關頭所作出的貢獻和成績)出發,評定“毛澤東同志的功績是第一位的”,“毛澤東思想指引我們取得了勝利”,奠定了更令人信服的基礎,由此“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也就有了根據【《陳云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4頁。】。而與此同時,胡耀邦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講話,也從毛澤東思想的歷史發生、經驗根據、內容體系、思想地位、文本呈現以及理論發展等維度出發,系統闡釋了“如何看待毛澤東思想”的六個方面內容。【主要內容包括:一是要認識到毛澤東思想是歷史的形成的和為全黨所公認的;二是要肯定毛澤東思想既是中國革命勝利的科學總結,又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寶庫;三是要看到毛澤東思想是毛澤東同志通過中 國革命長期的、艱難曲折的實踐逐漸形成的;四是認識到毛澤東思想是有科學體系并應當加以總結好的;五是毛澤東思想主要表現在《毛澤東選集》、黨的文件和黨內同志的重要著作上;六是毛澤東思想是需要繼續發展的。參見《胡耀邦文選》,第213—216頁。】上述兩個層面,無疑從文本結構和理論內容上補足了《決議》草案存在的缺失,這就為更加完整地和準確地把握、堅持和運用毛澤東思想,特別是完成對樹立和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相關論題的論證與闡釋工作,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進一步而言,困擾前述論題論證和闡述的核心因素,確系毛澤東晚年在思想上和實踐上所犯的錯誤,以及由此在國內國外和黨內黨外引發的認知沖突和理論緊張。其中,如何評價“文化大革命”的論題尤為典型,鄧小平在《決議》起草工作開始前既主張應“科學地歷史地來看”,又強調“不能勉強”和“不必匆忙”去解決【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卷,第451、435頁。】,足見該論題的敏感性和復雜性。至《決議》起草工作開始,胡喬木也將其作為需要重點破解的難題,強調要講清楚犯錯的原因,若從國際層面上來看,主要是反霸權主義斗爭范圍擴大化影響至國內斗爭加劇,以及受到馬克思列寧主義一些不明確的被誤解的論點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傳統的影響所致。【《胡喬木傳》編寫組編:《胡喬木談中共黨史(修訂本)》,第57、148頁。】不僅如此,鑒于前述國際社會的復雜情緒和錯誤認知,他還強調要從理論上闡釋清楚它與所謂反修正主義道路、繼續實現社會主義革命的關聯,借以讓全世界追求進步的人們認識到“文化大革命”是搞錯了,中共不僅沒有拋棄自己的理想,而且更不會走上蘇聯的道路。【《胡喬木傳》編寫組編:《胡喬木談中共黨史(修訂本)》,第61—63頁。】胡喬木還認為,論證和闡述本論題還應做時段上和性質上的判別,中共八大至“文化大革命”這段只應講“錯誤”,在此之后的階段才發展成為“路線錯誤”,犯下了在任何條件下都不允許重犯的錯誤,它不但在任何意義上都不能稱之為“革命”,而且需要永遠銘記其深刻教訓。【《胡喬木傳》編寫組編:《胡喬木談中共黨史(修訂本)》,第76頁。】
基于上述鋪墊,1980年8月胡喬木又兩次就本論題發表講話和談話:首先是作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場內亂的性質判定,確認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是其全面發動的標志,對此毛澤東和黨中央都負有責任,但毛澤東在基本維持解放軍、國務院和黨的統一等方面是有功勞的;其次是闡明“文化大革命”的發動既缺少經濟和政治基礎,也沒有找到革命對象、依靠力量和提出革命綱領,不但在理論上不能自圓其說,而且在實踐上沒有指出前途;再次是說明“文化大革命”的發生肇因,其中社會主義發展經驗不足、規律認識不清,毛主席個人權威達到極點,以及國內和國際社會歷史背景等均應考量。【《胡喬木傳》編寫組編:《胡喬木談中共黨史(修訂本)》,第117—127頁。】胡喬木的上述論析得到了鄧小平的贊同。【《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02頁。】并且,鄧小平本人也通過對比新中國成立后十七年歷史中的錯誤,再度確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是嚴重的、全局性的;通過對整個歷史事件的“實質分析”,開啟了黨內“原則上不再用路線斗爭的提法”的先例;通過肯定“文化大革命”期間仍存有健康的方面(如外事工作取得很大成績和粉碎了“四人幫”等),否定所謂“黨不存在了”的說法。【《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02、308、304頁。】基于如此論證和闡述,有助于達成對“文化大革命”的科學地和歷史地評價,而其中秉持的既“實事求是”又“恰如其分”的評價指針,也成為評價毛澤東同志功過的基本遵循。【《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08頁。】
如前所述,鄧小平在直接回應國際關切時,實已確立評價毛澤東的基調、思路甚至是核心觀點。在起草《決議》過程中,鄧小平、陳云、胡喬木等人也從多個維度對此展開了論證和闡述:一是著重說明“正確評價毛主席的各個方面”的重要性【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卷,第725頁。】,強調這不僅是針對其個人,而且是關乎黨的整個歷史及其評價,千萬不能“像赫魯曉夫評價斯大林那樣一棍子打死”【中央文獻研究室科研部圖書館編:《陳云人生紀實》下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11年,第774頁。】;二是充分肯定毛澤東的功績,強調作為黨和國家的主要締造者【《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44頁。】,毛澤東最偉大的功績是根據中國實際提出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方針,以及通過長期武裝斗爭奪取全國革命勝利,所以在任何時候都不能損害他在中國革命史上的光輝形象【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卷,第692頁。】;三是客觀判定毛澤東所犯錯誤的事實及原因,認定他在新中國成立后十七年中確實存有失誤,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錯誤,但這是一個偉大的革命家和馬克思主義者犯的錯誤,原因包括違反毛澤東思想、封建主義殘余影響以及其他復雜的國內國際社會背景【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卷,第725、742、719頁。】,盡管他自己曾覺察并力圖改正,無奈對情況作出了錯誤估計和采取了錯誤的方法,最終給黨和國家造成嚴重危害【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卷,第650頁。 】;四是綜合評價毛澤東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認定其晚年確有錯誤,但他的一生對中國人民和中國革命作出了偉大貢獻,【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卷,第713、751頁;】在毫不含糊地批評其錯誤時,不應過分損害或把所有錯誤都歸咎于其個人或個人品質,黨中央和集體層面上也應承擔一些責任【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卷,第684頁。】。
在做出上述論證與闡述的過程中,鄧小平反復強調:“不管怎么寫,還是要把毛澤東同志的功過,把毛澤東思想的內容,把毛澤東思想對我們當前及今后工作的指導作用寫清楚”【《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00頁。】,“目的還是要堅持毛澤東思想”,“把毛澤東同志已經提出、但是沒有做的事情做起來,把他反對錯了的改正過來,把他沒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卷,第725、709頁。】,特別是要藉由《決議》的公布把過去的問題做個了結,不再糾纏,一心一意向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目標努力【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卷,第684頁。】。針對毛澤東犯錯及其責任承擔問題,陳云特別強調要著重從破壞民主集中制方面的錯誤加以界定,從毛主席和黨中央兩個主體維度判定主要責任與集體責任,甚至地方領導人也應擔負一定責任。【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云年譜(19051995)》下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260頁。】統觀中央對上述三大論題的系統“論證”和權威“闡述”,著實有助于達成“對歷史問題作出實事求是的恰如其分的”評價目標,這就為《決議》進一步“概括”和總結歷史經驗夯實了政治的、歷史的和理論的基礎。
四 概括與總結:《決議》文本的政治歷史書寫
在起草《決議》整個過程中,鄧小平和胡喬木等人多次強調:“要避免敘述性的寫法”,既要寫得集中,又要對重要問題要加以論斷【《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91頁。】;不僅要做到“寓繁于簡”,而且要將史實與理論互相穿插【《胡喬木傳》編寫組編:《胡喬木談中共黨史(修訂本)》,第67頁。】。如此要求,既是源自對建國以來的歷史是一個“復雜的整體”的認識【《胡喬木傳》編寫組編:《胡喬木談中共黨史(修訂本)》,第92頁。】,也是基于“總結經驗,統一思想,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政治訴求。循此路徑,《決議》成稿既有對三大論題的科學概括,亦有對國際關切的最終因應,同時也融入了黨對歷史問題國際成因的客觀考量。
最后通過的《決議》主要由八個部分組成,第一部分以“總分總”的結構回顧和總結了建國以前的革命歷史,并從五個層面概括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原因和意義,意在立足黨的六十年歷史發展進程的整體性維度,彰顯毛澤東的歷史功績和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第二至第六部分采用同樣的敘事結構,先總結建國以來的十項成就,后概述其間存有的認識偏差和實踐錯誤,再分階段總結社會主義改造的必要性與意義,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十年中的成就、經驗與失誤,“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觀點、錯誤性質、發展階段和產生原因,直至確認十一屆三中全會作為“偉大轉折”的深遠意義。其中,對建國后的前兩個歷史階段而言,《決議》借助歷史貢獻與重大失誤的對比來確認毛澤東的功勞大于失誤,以及說明毛澤東思想處于繼續發展當中;在“文化大革命”的專章總結中,既提出要把毛澤東思想同毛澤東晚年所犯的錯誤區別開來,又作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的政治定性。以此為基礎,第七個部分先是立足毛澤東對黨和人民軍隊的建立與發展,對中華民族的解放事業、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和社會主義事業的不朽功勛來肯定其歷史地位,后是從歷時性維度界定“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是被實踐證明了的關于中國革命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進而概括出毛澤東思想的六個方面內容以及三個方面的“活的靈魂”。《決議》的第八部分重申概括建國三十二年經驗的目的,即以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為基礎,把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的意志和力量集中到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偉大目標上來,此乃建國以來正反兩方面的十項經驗基本總結的客觀要求。【《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21年,第55—121頁。 】
正如胡喬木所言,黨要通過《決議》的起草和發布,在社會主義的旗幟下說明社會主義的理想和原則,說明社會主義的革命不僅沒有結束,我們還要給予革命的口號一些新的明確的內容。【《胡喬木傳》編寫組編:《胡喬木談中共黨史(修訂本)》,第85頁。】《決議》作出的上述論證、闡釋和概括,已完全不止于對外回應國際關切或對內解疑釋惑,而實際具有著深刻的政治發展意涵,一是具有推進撥亂反正的社會政治功能,二是具有推動繼往開來的社會發展價值。這是中共秉持著“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的辯證唯物主義的根本立場【《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第67頁。】,繼作出《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之后,從總結經濟文化落后的東方大國如何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經驗,轉向進一步總結革命勝利后如何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經驗的政治自覺。從《決議》發表的社會政治效應看,對內說服了眾多黨內人士和起草過程中持不同意見的人,并把黨對重大歷史問題的評論真正說到了普通干部和群眾的心底【《鄧力群文集》第1卷,第553—554頁。】,對外也引發了國際社會的廣泛好評,美國人曾高度肯定這是一個非常出色的文件,就像“動得非常干凈的外科手術”,不僅思路很清楚,而且事實闡述得也很明白【《胡喬木傳》編寫組編:《胡喬木談中共黨史(修訂本)》,第204頁。】。基于此,當鄧小平在《決議》通過后向國際人士“重申在經濟調整期間,中國對外開放的政策不變”,或者向港臺人士闡明不對歷史問題作出實事求是的恰如其分的分析就無法統一思想和統一認識,以及向布熱津斯基強調十一屆六中全會的召開足以證明中國政策的連續性時【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卷,第754、759、760—761頁。】,前述國際關切無疑得到了進一步的權威性解答。
言及至此,或可做一個基本小結:盡管起草《決議》并非是源自外發性的國際肇因,但來自國際社會的擔憂、猜忌、指責和期冀,確為中共開展政治歷史的自我省察提供了特定的思想場域。就其對解答內生性社會政治歷史問題的價值來看,它或已完全不止于提供一種他者視角,而是切實推動著中共將自身重大歷史問題置于20世紀的世界歷史時空,進而從單向度的消解歷史問題走向更為深刻的世界社會主義變革的現代性思考。從歷史問題到現實政策,從領袖人物到重大事件,從政治理論到社會理想,這些觸及黨內黨外和國內國外敏感神經的重大論題,在任何時候都需中共歷史地和科學地面對,不只是因為它們具有重大的國際國內影響,更在于高度關乎中國共產黨人的政治理性與革命信仰。
International Consideration and the CPCs Historical Resolution
in Historiography focus on the Resolution on Several Historical Issues
of the Party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XU Chong
Abstract: The drafting of the Resolution on Several Historical Issues of the Party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id not originate from an external international cause, but the concer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bout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n China, the suspicion of the evaluation of major historical issues, the accusation of the so-called failure of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 as well as expectation for affirming Mao Zedong and Mao Zedong Thought not only provide a foreign perspective for the drafting work from outside to inside, but also suggest an interpretation path relating to the CPC from one to the other. The CPC responding to the concerns timely, expressing its position solemnly and repeatedly elaborating its views were full of profound thinking on the principles, methods and viewpoints related to the evaluation of major historical issue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t the same time, it effectively promoted the “demonstration, elaboration and generalization” of three core topics, namely, holding high the great banner of Mao Zedong Thought, practically and properly evaluating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Mao Zedongs merits and demerits. This action of the CPC is not only conducive to summing up experience, unifying thoughts, and looking forward together, but also conducive to building a new image of the Party and the country in the new era, which lays an important poli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successful writing of the second significant resolution of the Party, and creating a new situation for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Keywords: the CPC; international cause; the Resolution on Several Historical Issues of the Party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istoriography
【責任編輯:龔桂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