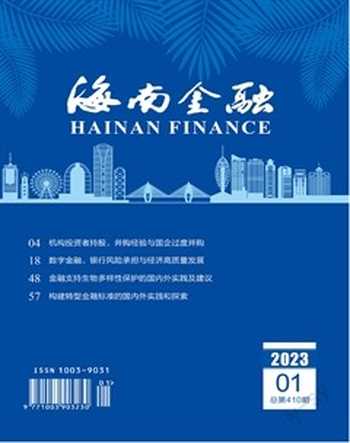機構投資者持股、并購經驗與國企過度并購
王言



摘? ?要:基于目前國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推動下并購正在加速的現實背景,機構投資者作為混改的重要引入對象,對國企并購行為的影響越來越明顯。本文以2015—2021年滬深A股國企并購事件為樣本,實證檢驗了機構投資者持股對國企過度并購行為的影響。研究表明:機構投資者持股對國企過度并購行為具有顯著抑制作用。機制檢驗表明:機構投資者持股主要是通過其過往并購經驗對國企過度并購行為產生治理作用。進一步研究表明:機構投資者持股在高市場化程度地區對國企過度并購行為的抑制作用更強。
關鍵詞:機構投資者持股;并購經驗;國有企業;過度并購行為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23.01.001
中圖分類號:F273.1;F832.51? ? ? ?文獻標識碼:A? ? ?文章編號:1003-9031(2023)01-0004-14
一、引言
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國企改革”成為一個高頻詞匯,隨著頂層設計方案的出臺,國企改革逐步駛入快車道。以混合所有制改革為主要手段的國企改革措施主要是通過并購重組來實現國有資本和社會資本交叉融合的目的,因此,并購重組成為實現國企資源優化配置的重要手段和關鍵環節。同花順iFinD數據顯示,截至2022年8月,A股國有上市公司發生并購事件734起,同比增長43.08%,涉及央企上市公司的并購事件為216起,占比約29.43%,同比增長80%。經過近幾年實踐發現,國企在如此大規模并購交易背景下,很多企業超出自身能力范圍盲目進行并購而導致并購效果不佳,存在大量過度并購行為。因此,研究國企合理并購規模在現階段是十分必要的。
影響國企并購行為的因素,從內部因素來講,與西方發達國家不同,我國國企并購重組往往不是以股東財富最大化為目標,而是以產業績效的提高為直接動因,這就有可能導致帶有盲目性的大規模并購事件發生,很多并購事件缺乏科學嚴格的論證。此外,國企的所有權人缺位,可能導致國企管理層相比民營企業因缺乏股東監管而在并購問題上過度自信。從外部因素來講,制度因素是外部環境因素的關鍵,不斷影響國企的并購行為,國家主導的并購制度政策制訂推動了國企并購的浪潮。因此,受到內外部環境因素的影響,國企可能不能很好的把控并購規模,一定程度表現為過度并購。
機構投資者股東治理是繼公司內部治理后的一項新的外部治理機制,是對既有治理機制的補充,主要包括基金、QFII、券商、保險、社保基金、銀行、信托等。主要通過提交股東議案、私下協商、積極行使投票權以及股東訴訟四種方式參與公司治理。每種方式的成本不同,機構投資者會根據事件的嚴重程度選擇不同的治理方式,甚至會提起訴訟。《上市公司治理準則》已經明確機構投資者股東公司治理作用,在當前國企大規模并購的情況下,機構投資者持股能否對過度并購這一問題發揮有益的治理效應?哪些因素會對機構投資者持股與國企過度并購行為的關系產生影響?本文分析了中國滬深A股國企是否存在過度并購行為,實證檢驗了機構投資者持股能否抑制國企過度并購行為,驗證了機構投資者股東對公司治理的重要作用。研究發現,機構投資者主要是通過股東并購經驗對國企過度并購行為產生治理作用,此外,企業所在市場化程度高低在機構投資者抑制國企過度并購時具有顯著差異性,市場化程度高的地區抑制作用更強。為引入機構投資者股東治理及引入方式提供的了實證證據和參考建議。
二、文獻綜述與研究假設
目前國內外學者對于過度并購行為研究較少,機構投資者參與企業過度并購行為研究則更是沒有。現有文獻大多集中在機構投資者對企業并購目標選擇、并購信息以及并購績效的影響等方面來研究。在并購目標選擇方面,機構投資者選擇完全控制,從而增加了并購成為大型跨境交易的可能性,機構持股集中度和外資機構持股增加了跨境并購的可能性(Andriosopoulos & Yang,2015)。但也有研究認為,由于機構投資者持股具有流動性,企業具有并購傾向是機構投資者進行投資的原因,機構投資者更傾向于投資將要進行并購業務的公司(Anderson & Huang,2017)。在并購信息方面,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較高、調研活動較為頻繁的企業,不管是并購信息獲取,還是并購信息處理,在抑制并購信息不對稱方面都具有較強的優勢(黃順武等,2015;陳詣之和潘敏,2020)。在并購績效方面,機構投資者有利于國內和跨國并購績效的提升(王治皓等,2020;張志平和鞠傳寶,2021),且境內長期機構投資者相比境外機構投資者對跨國并購績效的提升作用更明顯(凌志雄和陶詩慧,2016)。
根據委托代理和信息不對稱理論,高管層是企業的直接經營者,掌握著公司經營的一手信息,所有者將經營權委托給高管,導致獲取信息具有一定滯后性。高管層可以利用此機會,借助信息優勢,通過發動并購獲取短期效益,長期可能不利于公司發展和股權利益。因此,企業過度并購亦是高管層代理問題所產生的。尤其是針對國企普遍存在“內部人控制”現象,大股東虛化缺位和小股東搭便車導致對國企經理人缺乏長期激勵且手段單一,以及對知識型員工普遍存在著激勵方式滯后等問題,嚴重時可還導致盈余管理等問題出現(呂微和唐偉,2012;金曉燕,2016;廖紅偉和楊良平,2017;潘星宇和沈藝峰,2021)。根據上述分析,機構投資者對公司治理效率和并購績效具有正向影響,那么能否抑制國企過度并購行為則變得十分具有研究價值,這不僅能補充和拓展機構投資者治理效應文獻,還可以豐富符合中國國企過度并購問題中機構投資者治理作用的相關結論,為國企是否堅定引入機構投資者股東提供實證證據,因此提出H1:機構投資者持股與國企過度并購行為呈負相關。
根據學者對并購經驗的解釋,并購經驗大體可以定義為:企業由以前的并購活動學習積累的知識。根據學習遷移理論,這些經驗教訓和技能會深深地嵌入相關個人的腦海中,為執行一些任務或行動的組織的常規途徑奠定了基礎。當企業擁有豐富的自身并購經驗時,企業會總結發展自身的經驗教訓以便提高以后并購的成功率,而缺乏相關并購經驗的企業則會想方設法獲取。現有文獻研究并購經驗主要是從并購方過往的并購經驗視角進行研究,Bruton 等(1994)檢查了跨行業的樣本,財務困境和非財務困境并購,發現在財務困境時候并購,并購經驗對績效的感知測量是正效應。吳建祖和陳麗玲(2017)以A股滬深并購事件為基礎,實證研究發現高管并購經驗有利于提升海外并購績效。孟陽(2020)以我國制造業企業為樣本,研究發現高管并購經驗促使企業發動更多的并購并提升了并購成功率和并購績效。劉博文和任颋(2020)通過問卷調查的方式,研究了生產制造企業跨國并購經驗的作用,研究發現跨國并購經驗有利于人才的獲取。趙君麗和童非(2020)以我國海外并購事件為樣本,研究發現海外并購經驗有利于降低由地區差異性而導致的企業海外并購劣勢。孫燁等(2021)將并購經驗分為成功并購經驗和失敗并購經驗,成功的并購經驗對并購績效的提升作用更大。目前有關并購經驗研究中,從機構投資者視角出發具有創新性。有學者研究發現,機構投資者持股可以提高投資效率(尚航標等,2022;馮曉晴和文雯,2022)。如果說機構投資者可以通過持股對公司投資行為產生正向影響,那么機構投資者股東同樣可以通過以往并購經驗有助于企業并購行為的優化。故而提出H2:機構投資者股東可以通過并購經驗對國企過度并購行為產生抑制作用。
三、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擇和數據來源
本文研究國企并購問題,國企混改從2015年拉開序幕,故而,選取2015—2021年滬深A股并購事件。根據交易信息表篩選并購樣本數據原則按如下順序:并購標的為股權且為買方并購,剔除置換、剝離等廣義并購形式;首次公告日實際控制人為國務院國資委、地方國資委或其他具有政府機構性質的行政機關、事業單位、國企等研究對象,不包括國有股東為第一大股東但無實際控制人的上市公司的并購交易①;剔除未成功、終止的并購樣本;由于金融企業財務結構與實體企業具有較大差異,剔除金融企業(以2012年證監會行業標準為準);因為本文使用變化量和滯后量,剔除上市年份不足以及被特別處理(ST)的樣本;剔除其他關鍵研究數據不全或缺失的樣本;相關并購研究均剔除小并購樣本,因為轉讓股權比例較小或交易金額較小的并購對主并方影響很小,本文同樣剔除持股比例和交易金額較小樣本(5%或100萬元以下);對并購事件進行逐個分析,合并一攬子交易以及收購方購買同一控制下企業并購等情況。
本文數據主要來源于國泰安(CSMAR)、同花順iFinD以及Wind數據庫,同時,手工收集整理了機構投資者股東并購經驗數據,主要方法為,根據實證分析篩選出的國企過度并購樣本,逐一查找并購事件中主并方十大股東中機構投資者股東前三年(三年以前的學習經驗通常被認為對現在影響較小)在所有滬深A股上市公司并購中的主并方十大股東持股情況,如果存在除過度并購樣本中相同的機構投資者之前持股上市公司發生了并購,視為有并購經驗,反之則為沒有并購經驗。所有連續變量Winsorize縮尾(1%和99%),樣本不變。
(二)變量定義與模型構建
1.變量定義
被解釋變量:過度并購(I(O))。姜軍(2010)認為,企業在自身發展和競爭過程中客觀上存在著企業邊界不斷擴展的內在要求,合理的并購規模是由企業在發展過程中所累積的一系列內部條件支撐的,在一定內外部條件激發下表現出來的對外投資形式。如果由企業內外條件所決定的并購規模是合理的,或者是可預期的,則這一并購行為是由一系列企業內外部因素決定或影響的。那么則稱不能由企業內外部條件解釋的、超過預期并購規模的部分定義為過度并購(差值小于零為并購不足,不在本文研究范圍)。過度并購的度量是實證研究的難點。關于過度并購程度應該如何度量,一直沒有作出理論闡述,也沒有直接的數理模型可供借鑒。本文認為,影響企業并購規模的內外部因素有很多,根據這些因素預期企業并購規模具有較高的科學性,為合理并購規模。結合Richardson(2006)預期過度投資模型和姜軍(2010)過度并購的影響因素研究,建立了預期并購規模度量模型(1)①:
其中,因變量E(I)i,t表示i上市公司t年度的并購規模,自變量為i上市公司第t-1年末的托賓Q值(Q)、財務杠桿(LEVERAGE)、貨幣資金(CASH)、內部投資(CAPEXP)、銷售額(SALES)以及公司治理因素(GOVERNANCE),并控制行業因素(INDUSTRY)和年度因素(YEAR)。具體的,Q表示企業的投資機會、成長機會、估值水平、管理能力、企業價值等諸多含義;LEVERAGE表示負債水平;CASH包括現金、銀行存款和交易性金融資產;CAPEXP包括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產等支付的現金;SALES是企業規模的替代變量;GOVERNANCE包括董事會規模(BOARDSIZE,用年末人數度量)、領導層結構的二職分離虛擬變量(DUALITY,二職分離為1,其余為0)、獨立董事比例(PROPORTION)、股權結構前5名股東集中度(HHi5)、董事會活躍程度(BOARDMEETING,用每年會議次數度量)5個指標。INDUSTRY為行業虛擬變量,按照2012年最新版中國證監會行業劃分標準,本文通過前述篩選步驟最終確定的并購樣本所涉行業共有17類。YEAR包括2015—2021年6個虛擬變量,發生并購的年份取1,否則取0。?著是i上市公司t年度的并購規模殘值,通過模型(1)可以判斷過度并購水平,模型的殘差值即為非效率并購水平,若殘差為正值,則為過度并購,殘差值越大,過度并購程度越高。?茁為回歸系數,?琢是常數量。
解釋變量: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INVESTOR)。由于本文需要研究機構投資者股東并購經驗的治理作用,根據數據可得性,選取前十大股東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同時,并購事件在一年內的任何時點都是可能發生的,機構投資者交易又比較頻繁,為盡量避免內生性問題,本文采用并購首次公告日前最近年度末的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作為代理變量。
中介變量:機構投資者股東并購經驗(I_EXPERIENCE)。借鑒孫燁等(2021)的研究,采取二元虛擬變量,找出過度并購樣本主并方前十大股東中機構投資者股東在并購首次公告日前三年內具有一次以上和沒有并購經驗的情況,再根據每個過度并購樣本中機構投資者的劃分,將至少有一家機構投資者股東具有并購經驗的情況記為1,沒有一家機構投資者股東具有并購經驗的情況記為0。
控制變量。與前文研究預期并購規模影響因素模型構建不同,在主檢驗部分本文借鑒已有研究(蔚美樂和岳寶宏,2020;宋思淼和梁雯,2021,潘紅波和楊海霞,2022)揭示的可能對公司并購規模產生影響的主要因素,選取包括公司財務特征、公司治理特征以及其他控制變量。
2.模型構建
設計模型(2)檢驗H1:
I(O)i,t=C0+?茁1*INVESTORi,t-1+?茁2~11?撞CONTROLSi,t-1+?撞INDUSTRY+?撞YEAR+?著i,t? (2)
借鑒溫忠麟等(2004)檢驗中介效應方法,設計模型(3)—(4)檢驗H2:
I_EXPERIENCEi,t-1~t-3=C0+?茁1*INVESTORi,t-1+?茁2~11?撞CONTROLSi,t-1+?撞INDUSTRY+?撞YEAR+?著i,t? ? (3)
I(O)i,t=C0+?茁1*INVESTORi,t-1+?茁2*I_EXPERIENCEi,t-1~t-3+?茁3~12?撞CONTROLSi,t-1+?撞INDUSTRY+?撞YEAR+?著i,t (4)
其中,i代表企業,t為時間;I(O)為i公司t年發生的過度并購;INVESTOR分別表示i公司機構投資者t-1年末持股比例;I_EXPERIENCE為i公司機構投資者股東t-1至t-3年的并購經驗;CONTROLS為上述提到的影響過度并購的控制變量,同時,公司財務、治理特征變量以及公司規模均取滯后一期值,盡量緩解反向因果可能導致的內生性問題;?茁1~11為變量對應估計系數;INDUSTRY為行業虛擬變量,以2012年證監會行業標準為準,本文所涉行業共有13類;YEAR包括2015—2021年6個虛擬變量,發生并購的年份取1,否則取0;C0和?著分別表示常數項和隨機誤差項。
四、實證結果分析及穩健性檢驗
(一)描述性統計分析
運用Stata 15.1進行變量描述性統計(見表2)。通過對國企并購事件樣本篩選和過度并購計算,最終得到418個過度并購樣本,過度并購標準差為1.695,表明過度并購現象比較嚴重且強弱差異較大。機構投資者股東并購經驗中位數為1,且均值大于或等于0.5,表明機構投資者股東大多數都參與過公司并購,形成了本文假設的基礎。此外,國企“一股獨大”特征明顯,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均值達42.580%,說明將大股東持股比例作為控制變量加入模型具有一定現實意義。
(二)相關性統計分析
表3相關性分析顯示,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較小(都小于0.65),說明變量選取合理且可均納入模型。
(三)基礎檢驗結果與分析
根據研究設計,本文首先對模型(2)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INVESTOR)與國企過度并購行為(I(O))進行了回歸。表4(1)—(2)列分別檢驗了在不加入控制變量和加入控制變量下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INVESTOR)與國企過度并購行為(I(O))的關系。發現機構投資者持股對國企過度并購行為的估計系數在5%的水平下顯著為負,說明機構投資者持股對國企過度并購行為具有顯著抑制作用。原因是機構投資者整體交易頻繁,不容易受到來自國企體制等多方面的干預,更加市場化,積極參與了國企并購且發揮了治理效果,假設H1得到驗證。此外,由控制變量回歸結果可知,首先,公司的資產規模(SIZE)和賬面價值比(MB)回歸系數都在1%的水平下呈現出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即上市公司資產規模越大,市值越高,越容易發生過度并購。這可能是因為資產規模越大,市值越高的公司,往往聲譽好,實力強,相對中小型企業而言進行并購的規模大和頻率高,在這種情況下導致超額并購的概率會大大增加。其次,董事會規模(BOARDSIZE)、獨立董事比例(INDEP)以及經營活動現金流量回報率(OCF)至少在10%的水平下呈正相關關系,這是因為企業經營活動現金流量越多,所擁有的資金越多,越容易發生過度并購。由于本文選取國企并購樣本所導致,我國國企國有出資人具有絕對控制權,中小股東和獨立董事往往聽之任之,沒能充分發揮監督作用。但通過引入機構投資者股東,充分體現其他社會資本股東的利益,建立現代公司治理體制,可有力解決這一問題。
(四)內生性檢驗
本文可能存在一定內生性問題:一方面,不是因為其持股了企業后才并購,而是因為獲得了公司要并購的信息才投資,為緩解反向因果可能存在的內生性問題,保證結論穩健性,引入Heckman兩階段自選擇修正方法(Heckman,1979)檢驗內生性問題。第一階段建立影響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變化因素模型。總結前人研究成果,選擇的影響因素包括上市公司的財務數據類別中四個變量(總資產對數值SIZE、資產負債率LEV、每股收益EPS、每股經營性現金凈流量OCF)、交易數據類別中三個變量(貝塔系數BETA、市凈率P/BV、換手率TURN)、公司治理數據類別中一個變量(實際控制人持股比例CONTROL),同時引入會計信息披露質量(審計意見RANK)一個虛擬變量。模型中為截距項,?茁為各變量對應的估計系數,INDUSTRY和YEAR為行業和年份虛擬變量,?著為隨機擾動項。因變量為并購發生前兩年到前一年內機構投資者持股數是否發生變化(CHANGE),發生變化取1,不變取0①。
通過模型計算出逆米爾斯比率(IMR),并將其作為控制變量加入模型(2)式機構投資者持股數變化組中,進行第二階段回歸,分別檢驗在不加入控制變量和加入控制變量下控制逆米爾斯比率(IMR)時的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INVESTOR)與國企過度并購行為(I(O))的關系,為了節省篇幅,控制變量的結果不再列示。通過表5檢驗結果可知,逆米爾斯比率均不顯著,則說明最開始的回歸方程并不具有樣本自選擇問題,而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的回歸系數在5%的水平上負向顯著,與前述檢驗結果一致。說明在控制樣本自選擇問題之后,研究結論依然成立。
五、機制作用分析
根據研究設計,對模型(2)—(4)進行回歸,回歸結果見表6。列(1)為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INVESTOR)與國企過度并購行為(I(O))的回歸結果,表明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INVESTOR)對國企過度并購行為(I(O))具有顯著負向影響,具備下一步檢驗基礎;列(2)為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INVESTOR)與機構投資者股東并購經驗(I_EXPERIENCE)的回歸結果,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的估計系數在1%的水平下保持顯著為正,表明機構投資者持股有利于增強機構投資者股東并購經驗,具備下一步檢驗基礎;列(3)為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INVESTOR)、機構投資者股東并購經驗(I_EXPERIENCE)與國企過度并購行為(I(O))的回歸結果,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和機構投資者股東并購經驗的估計系數分別在10%和1%的水平下保持顯著為負,說明機構投資者股東并購經驗在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與國企過度并購行為之間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機構投資者股東通過持股,可以獲得更多并購經驗,從而導致了對國企過度并購行為的抑制作用,假設H2得到驗證。
六、拓展性分析
機構投資者股東是否參與國企并購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外部地區的治理環境,由于中國各地區自然條件和經濟基礎的不同,市場化程度存在較為明顯的差異。已有研究發現,區域地理距離對機構投資者投資意愿具有顯著影響,與其他地區相比,機構投資者更愿意持股東部地區的上市公司(宋玉等,2012)。那么市場化程度是否會顯著影響機構投資者股東參與抑制國企過度并購行為呢?為了檢驗上述觀點,故而提出市場化程度能夠強化機構投資者持股對國企過度并購行為的抑制作用。為了檢驗,本文設計了模型(6),具體如下:
模型(6)考察了與機構投資者股東并購經驗內生變量相對應的市場化程度(MARKET)這一外生變量對機構投資者持股與國企過度并購行為關系的影響作用。有關市場化程度的度量,如果主并方所在城市為東部地區,則取值為1,如果主并方所在城市為中西部和東北部地區,則取值為0①,其他變量定義與前述研究一致。模型回歸結果列示于表7,從結果來看,在不加入控制變量和加入控制變量下,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與國企過度并購行為至少在10%的水平上呈顯著負相關關系,和前述結論一致。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與市場化程度交乘項的回歸系數至少在5%的水平上顯著為負,表明隨著地區市場化程度的提高,機構投資者持股對抑制國企過度并購行為的作用越強。
七、研究結論及啟示
(一)研究結論
本文以2015—2021年滬深A股除金融行業以外的國企并購事件為研究樣本,對并購事件中過度并購進行了的界定,最終得到418個過度并購樣本。通過引入中介變量機構投資者股東并購經驗,探討了機構投資者持股對國企過度并購行為的影響及其機理。研究發現: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越高,對國企過度并購行為影響越大,即抑制國企過度并購效果越好,說明機構投資者對國企起到了較為積極的治理作用,利用Heckman兩階段自選擇修正方法進行了內生性檢驗。進一步的,增加機構投資者股東有無相關并購經驗的中介變量,發現機構投資者可以通過持股獲得更多并購經驗,從而對國企過度并購行為產生抑制作用。引入市場化程度調節變量,結果表明,隨著地區市場化程度的提高,機構投資者持股對抑制國企過度并購行為的作用越強。
(二)啟示
本文的研究結論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第一,發現了機構投資者持股提高國企并購績效的一個內在機理因素,即抑制國企過度并購行為。這就為理論界機構投資者與并購績效的相關研究提供了參考,堅定了實務界引入機構投資者股東的信心。第二,在國企混合所有制改革股權并購重組實踐中,要更多地引進機構投資者股東,同時,要有針對性的引入有相關并購經驗的機構投資者股東,其可以更好地發揮積極的監督與決策作用,完善國企的公司治理。第三,為了使機構投資者加強抑制國企過度并購行為,發揮機構投資者治理作用,國家應進一步加快地區經濟發展,提高偏遠地區市場化程度。■
(責任編輯:夏凡)
參考文獻:
[1]Anderson C W,Huang J.Institutional Investment in IPOs and Post-IPO M&A Activity[J].Journal of Empirical Finance,2017,41:1-18.
[2]Andriosopoulos, D,Yang S.The impact of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on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in the united kingdom[J].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2015,50(1):547-561.
[3]Bruton G D,Oviatt B M,White M A.Performance of Acquisitions of Distressed Firms[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94,37(4):972-989.
[4]Cheng C S A,Huang H H,Li Y,et al.Institutional Monitoring Through Shareholder Litigation[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10,95(3):356-383.
[5]Gillan S L,Starks L T.Corporate Governance Proposals and Shareholder Activism: the Role of Institutional Investors[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0,57(2):275-305.
[6]Heckman J J.Sample Selection Bias as a Specification Error [J]. Econometrica,1979,47(1):153-161.
[7]Hellman N.Can We Expect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to Improve Corporate Governance?[J].Scandinavian Journal of Management,2005,21(3):293-327.
[8]Richardson S.Over-investment of Free Cash Flow[J].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2006,11(2-3):159-189.
[9]Thomas R S.The Evolving Role of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in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Corporate Litigation[J].Vanderbilt Law Review,2008,61(2):299-313.
[10]陳詣之,潘敏.機構投資者調研與并購績效——基于信息不對稱視角的研究[J].經濟管理,2022,44(4):175-192.
[11]馮曉晴,文雯.國有機構投資者持股能提升企業投資效率嗎?[J].經濟管理,2022,44(1):65-84.
[12]黃順武,王夢瑩,昌望.機構投資者的信息優勢研究——來自上市公司重大股權收購的證據[J].證券市場導報,2015(8):45-51.
[13]姜軍. 機構投資者的治理效應——基于過度并購視角[D].北京:中國人民大學,2010.
[14]金曉燕.政府規制、公司治理與國企高管薪酬約束機制研究[J].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2):59-63.
[15]廖紅偉,楊良平.國有企業經理人薪酬激勵機制深化改革研究[J].財經問題研究,2017(1):108-114.
[16]凌志雄,陶詩慧.機構投資者異質性、公司治理和跨國并購績效——基于代理成本視角[J].財會月刊,2016(6):27-31.
[17]劉博文,任颋.跨境并購經驗對優質人才獲取的影響——來自雙方戰略共識的調節作用[J].技術經濟與管理研究,2020(2):55-59.
[18]呂微,唐偉.國有企業知識型員工激勵機制研究[J].經濟問題,2012(12):57-60.
[19]孟陽.高管并購經驗與企業并購研究——基于并購數量與質量雙重視角[J].技術經濟與管理研究,2020(5):53-59.
[20]潘紅波,楊海霞.競爭者融資約束對企業并購行為的影響研究[J].中國工業經濟,2022(7):159-177.
[21]潘星宇,沈藝峰.股權激勵、企業并購與利潤管理[J].經濟管理,2021,43(10):99-118.
[22]尚航標,宋學瑞,王智林.監督與紓困!機構投資者持股與企業投資效率的關系研究[J].技術經濟,2022,41(3):128-138.
[23]宋思淼,梁雯.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影響企業并購決策嗎——基于能力與意愿角度的分析[J].金融經濟學研究,2021,36(1):108-121.
[24]宋玉,沈吉,范敏虹.上市公司的地理特征影響機構投資者的持股決策嗎?——來自中國證券市場的經驗證據[J].會計研究,2012(7):72-79.
[25]蘇杭,方樂.投資者保護機構股東代表訴訟機制研究[J].金融監管研究,2021(6):53-69.
[26]孫燁,侯力赫,劉金橋.累積經驗與并購績效:從成功和失敗中學習[J].財經論叢,2021(8):69-80.
[27]王治皓,廖科智,齊岳.內部控制、機構投資者與上市公司海外并購績效[J].華東經濟管理,2020,34(10):120-128.
[28]蔚美樂,岳寶宏.跨國并購中對賭協議設計的案例研究——以東方國信的并購交易為例[J].海南金融,2020(3):62-67.
[29]吳超鵬,吳世農,鄭方鑣.管理者行為與連續并購績效的理論與實證研究[J].管理世界,2008(7):126-133.
[30]吳建祖,陳麗玲.高管團隊并購經驗與企業海外并購績效:高管團隊薪酬差距的調節作用[J].管理工程學報,2017,31(4):8-14.
[31]張志平,鞠傳寶.基于多維控制權視角的異質機構投資者治理效應研究——源自中國A股并購市場的經驗證據[J].東岳論叢,2021,42(8):110-125.
[32]張子學.機構投資者投票顧問的引入與規制[J].中國政法大學學報,2022(4):150-166.
[33]趙君麗,童非.并購經驗、企業性質與海外并購的外來者劣勢[J].世界經濟研究,2020(2):7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