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讀記
長安
孩子越長越大,童書也越積越多,次子小學一畢業就處理掉了一大批。不過,總有那么一些舍不得的,也總覺得應該留下點什么,于是試著寫下這篇札記。邊讀邊寫,仿佛又回到了親子共讀的金色長河,亦仿佛重溫了一遍童年。
鼠目有情,鼠眼有光
賊眉鼠眼,鼠目寸光,碩鼠碩鼠,無食我黍,老鼠過街……人類社會里鼠類的形象實在有些不上臺面。然而小孩眼里萬物有光,人類鼠類,皆我族類。周氏兄弟成年后均念念不忘兒時看過的“老鼠娶親”的年畫,魯迅回憶說“那時的想看‘老鼠成親的儀式,卻極其神往”(《狗·貓·鼠》),還養過一只能為他舔食墨汁的小隱鼠。
《鼴鼠的故事》是捷克藝術家茲德內克·米勒(Zdeněk Miler)自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起在將近半個世紀的時間里創作的系列動畫片及繪本,由波希米亞走向世界,早已是兒童故事的經典。土里來土里去的鼴鼠到了米勒筆下纖塵不染,大眼睛溫和靈動。《鼴鼠幫兔子找媽媽》里,與媽媽走散的小兔子痛哭失聲,哭醒了在地下睡得正香的鼴鼠。剛會說話的長子讀到這頁便拿起書來,讓我抱著那書,說,兔子要媽媽啊,你抱抱它吧。《鼴鼠與老鷹》里鼴鼠自洪水中救出老鷹寶寶,一手把它養大,母性十足。《鼴鼠與電視》講了個電視“中毒”的故事。小動物們有了電視就像得了寶貝,鼴鼠看累了回去睡覺了,大耳鼠、兔子和刺猬它們則看得夜以繼日、雨雪無阻,直看到藤蔓纏身、動彈不得。后來鼴鼠鋸開藤蔓解救了它們,還推來一車啞鈴讓大家鍛煉身體。《鼴鼠當醫生》里大耳鼠病了,鼴鼠從歐洲跑到非洲,又跑到大洋洲、北極洲和北美洲,滿世界給大耳鼠找藥。一路上鼴鼠曾經掉到獅子頭上,也曾被鯊魚吞進肚里,還見識過會吃蟲的豬籠草、聞一下就讓人失去知覺的毒花……世上無奇不有,鼴鼠有驚無險。最后鼴鼠還是回到了故鄉,在老橡樹下采到了藥。《鼴鼠的故事》溫情脈脈、從容舒緩,也流露出了波希米亞人樂天知命、與世無爭的天性。

卡夫卡發表于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小說《地洞》的主人公就是個鼠類(大約是只鼴鼠,卡夫卡在致友人信中提到過自己像只打地洞的鼴鼠),首鼠兩端,孤立絕望,患得患失,惶惶不可終日。半個世紀后,赫拉巴爾寫了一本《過于喧囂的孤獨》,書里的老鼠成了精般參與到廢紙打包工漢嘉的生活當中,見證了他在地獄里尋覓天堂的另類人生。《鼴鼠的故事》中,創作于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鼴鼠在城市》《鼴鼠的夢》仿佛與這些文字一脈相承,陰翳多陽光少,更像是給大人看的。《鼴鼠在城市》里森林被砍伐光了,鼴鼠與伙伴們不得不體驗了一把鋼筋水泥的城市生活,到最后還是義無反顧離開城市,奔向遠方。《鼴鼠的夢》講述一個大人夢見沒電沒水沒汽油了,天寒地凍,鼴鼠幫他生火取暖,春天到了,他與動物們過著原始的生活……醒來發覺是個夢,長出一口氣。等他來到加油站卻發現真的沒油了,而夢里的錘子亦出現在現實中,令他混亂且沮喪。生活中的荒誕與喪失多了,童書亦不免染上灰色。《鼴鼠的夢》只有動畫沒有繪本,或許也是由于太過灰暗了。

波希米亞鼴鼠橫空出世,無親無故,無牽無掛,巖村和朗筆下的“14只老鼠”系列繪本則講述了一個老鼠大家庭的故事,里面有爺爺奶奶爸爸媽媽,還有六個男孩四個女孩。巖村三十六歲離開東京遷到櫪木縣益子町,隱居雜木林中,亦耕亦讀亦畫,也給了他的孩子們一個野生的童年。“14只老鼠”系列繪本從一九八三年畫到二○○七年,皆創作于大自然中,細膩不留白,本本精彩。《14只老鼠大搬家》《14只老鼠的晚餐》……都是左右合起來成一大頁,嚴絲合縫,構圖精妙,每大頁下面又都有一行字,問那個睡懶覺的是誰,那個戴著漂亮帽子的是誰,那個差點兒坐了個屁墩兒的是誰……兩三歲的小孩很快就能找到答案,開心得手舞足蹈。“古里與古拉”系列繪本亦以老鼠為主人公,作者中川李枝子接受采訪時說:“想做一個讓孩子們吃驚的大蛋糕,就得用一個大雞蛋……為了顯得雞蛋大,古里與古拉就設定成了小小的‘野老鼠。”(《嚇人的大蛋糕》,《朝日新聞》2021年5月4日)這對雙胞胎野老鼠深得幼兒喜愛,開了“古里與古拉”系列的先河。
鼠目有情,鼠眼有光。
成長,歷險
人的成長或許是個漫長的過程,或許緣于一個事件,或許就是一瞬間,刻骨銘心,成長小說亦自成一類。張愛玲在一九六三年六月二十三日致友人信中談及將自己的英文小說《易經》改譯成中文,說《易經》“并不比他們的那些幼年心理小說更‘長氣,變成中文卻從心底里代讀者感到厭倦”(《紙短情長:張愛玲往來書信集1》)。“他們的”可用“英語世界的”或“西洋的”來置換,私信里張愛玲一向將他們與我們分得清清楚楚。弗朗西絲·霍奇森·伯內特(Frances Hodgson Burnett)的《秘密花園》氤氳綿長,乃張愛玲所謂“長氣”的成長故事,我耐心給次子讀過一遍。花園內外的孩子慢慢成長,脾氣壞的瑪麗變溫和了,體格弱的柯林變強壯了,故事也就結束了。
相比《秘密花園》,詹姆斯·馬修·巴利(James Matthew Barrie)的《彼得·潘》似乎是個反例,主人公永遠長不大。次子年幼時愛玩彼得·潘游戲,與鄰家女孩互稱彼得與溫迪,把我家小院當作夢幻島,占島為王。彼得·潘長不大也不肯長大,以致有心理學家以“彼得·潘綜合征”形容拒絕成長的男性。彼得·潘故事之所以深得人心,實在也因為道出了許多人—有大人也有孩子—的心聲或曰潛意識。安托萬·德·圣埃克絮佩里(Antoine de Saint-Exupéry)的《小王子》幽邃曲折,經得住各路闡釋,或者亦可讀成《彼得·潘》的進化版,永遠定格在少年模樣的小王子就像個憂郁內斂的升華版彼得·潘。只在自己的小星球見過一朵玫瑰花的小王子來到地球上的花園里,發現了五千朵同樣的玫瑰花,沮喪又崩潰,像所有在情感中迷路的人一樣。后來狐貍告訴他“重要的東西眼睛是看不見的”“你珍惜你的玫瑰,因為你在她身上花了時間”,而且,“你要對你的玫瑰負責”。這些話小王子聽懂了,也聽怕了。責任是道義的而非審美的,也是他難以承受的。飛行員作家圣埃克絮佩里心里揣著他的小王子,本能地抗拒乏味的成人世界,痛苦地徘徊于家國責任與自在人生之間。人世多困擾,他只想往天上跑,超齡開不了飛機就以身殉夢。不肯長大、拒斥社會性、回避責任,在普通人便是有人格缺陷,而藝術家則或大都有些彼得·潘情結,無論男女。張愛玲至死都在改寫《小團圓》,從小說改成散文,不厭其煩地重溫那些悠長的童年往事。村上春樹廣受歡迎,或許也是由于他內心長住著一個青春期男孩。作家大都擅長寫自己,寫孩子也是寫自己,寫給孩子也是寫給自己,童年變成年,人還是那個人。我也曾試著給孩子們讀點描寫當代成長故事的中文繪本,比如,黃蓓佳撰文的《會跳舞的搖搖》,大概內容有些偏嚴肅了,他們讀了好像也沒有什么代入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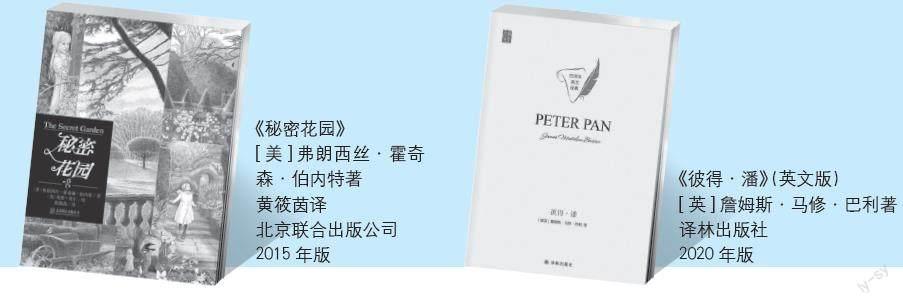
成長,隨之而來的就是遇險、冒險、探險、歷險。無人島、海盜船、喧囂鬧市、深山老林,撒向世間都是險。女孩子必看(?)的灰姑娘、睡美人、白雪公主……似乎都可省略,男孩們更愛讀那些未必經典但匪夷所思的書,像薩姆·塔普林(Sam Taplin)“可怕的體驗”系列繪本中的《千萬別當海盜》。鄰家女孩來我家玩有時也帶上小妹妹,那小妹妹有一次穿了長裙扮演公主,忽然就伏在沙發上哭了起來,過會兒又笑出了聲,解釋道:“公主都是得哭的啊!”公主都得哭,童話女主角差不多個個窩窩囊囊受苦受難,最后又幾乎都與王子成婚,過上了“幸福生活”,除了那個生猛的小紅帽和那個傷殘的小美人魚。童話里隱藏著重重疊疊的古老密碼,有這些童話做底子,女孩子就更難面對成長過程中的諸多課題—獨立與依賴、自尊自愛與自我犧牲、自我認同與社會認同……她只會更惶惑更混亂。沒生女兒,暗自松了口氣。
孩子們喜歡歷險故事,我自己小時候卻很少讀這類書,于是母子共讀,皆有興致,尤其是在歐亞之間倒時差的時候,迷迷糊糊讀著打發時間,亦夢亦醒,夢里不知身是客,醒來再讀歷險行。比利時漫畫家埃爾熱(Hergé,本名Georges Prosper Remi)的《丁丁歷險記》信息量大又細致謹嚴,經得起大人孩子一讀再讀。娃娃臉記者丁丁走南闖北,滿世界轉悠,周遭總有些密探、特務或壞人,殺機四伏,最后總是正義戰勝邪惡。《714航班》《金鰲蟹》《奧托卡王的權杖》……驚險,神秘,詼諧,背景是光怪陸離的域外風光。若是在這域外風光里看到老上海鴉片館……翻開《藍蓮花》,撲面而來的是舊時代的中國氣息,里面有細密的寫實,還有個中國少年小張。故事背后亦有佳話。同為一九○七年出生的埃爾熱與中國雕塑家張充仁相識于一九三四年,彼時埃爾熱筆下的丁丁已去過蘇聯、剛果、美洲和埃及,下個目標便是中國。在張充仁的大力幫助下,埃爾熱終于完成了《藍蓮花》。謙和儒雅、心懷文化自信的張充仁讓埃爾熱知道了一個馬可·波羅紀行文字之外的中國,也改變了他對世界、對繪畫的看法。一九三五年張充仁回國后兩人便失去了聯系,埃爾熱多方打探張充仁的消息,還于一九五八年至一九五九年創作了《丁丁在西藏》,書里那個讓丁丁晝思夜想的小張寄托著埃爾熱對張充仁的殷切思念。分別四十六年后,兩位老人終于在布魯塞爾機場重逢,相擁而泣。
原汁原味的、有滋有味的,生活
小孩有小孩的認同,大人中意的小孩未必感興趣,小孩喜歡的大人可能覺得莫名其妙,長幼咸宜的便彌足珍貴。那些不實用、非教訓、無目的又“有那無意思之意思”(周作人《兒童的書》)的童書,就像原汁原味、有滋有味的生活,讓人回味。
《小王子》故事里商人告訴小王子每周吃一粒止渴丸就不會渴,能省下五十三分鐘,小王子就想用這五十三分鐘走到有泉水的地方。我問長子,如果是你呢?他說要去飛機場看飛機。彼得·史比爾(Peter Spier)的繪本《好無聊啊》開頭便是兩兄弟百無聊賴癱坐床上,閑得五脊六獸。被母親訓斥后,他們就到儲藏室找出了螺旋槳,又拆掉汽車引擎,找來家里的木桶、梯子、床單……物盡其用,做了一架飛機,還真就開著飛起來了。家里一團糟,父母斥責他們膽大妄為,暗地里也贊嘆孩子們的天才創意。閃光的無聊日子,無聊的閃光日子,喜愛飛機的長子看得很投入。埃爾文·莫澤爾(Erwin Moser)創作的《會走路的樹》繪本故事集里,有兩個躺平享福的故事,長子亦喜歡。《會溜冰的床》描繪刺猬兩口子拆下溜冰鞋上的馬蹄鐵裝到床腳下,又用掃帚支起床單做成冰上船帆,躺在床上溜冰。《樹上的床》里小灰熊把床挪到了樹上,晚上又把兩個蜜罐子掛上樹冠,還點了個燈籠。一只只彩蝶翩翩飛來,小灰熊和朋友小考拉躺在床上,享受這個夢幻世界。
在克利斯提昂·約里波瓦(Chrisian Jolibois)撰文的繪本《我去找回太陽》里,我看到了嫉妒與背叛,努力與機遇,親情與成長,次子更感興趣的則是老佩羅對太陽的解釋:“太陽其實是天上的一個巨大無比的蛋黃……當我們看不到它的時候……那是它已經煮熟了!”次子剛上幼兒園時訂了每月一冊的繪本,十月那本是古川裕子創作的《出來吧,地瓜》。書到的那天幼兒園老師剛領孩子們到田里挖過地瓜,大家烤著吃,還各帶了一包粘著濕潤黑土的地瓜回家。睡前讀那繪本,螞蚱、螞蟻、蝴蝶、花大姐們喊著“地瓜地瓜等等啊,我們出發啦”,浩浩蕩蕩去挖地瓜。鼴鼠一家,老鼠一家……都來幫忙,終于挖出巨無霸大地瓜。動物們吃得正歡,次子已沉沉入夢,夢里可聞得到甜甜的焦香?
童書里有十四只老鼠融融泄泄、三世同堂,亦有孤獨、衰老與死亡。蘇茜·摩根斯坦(Susie Morgenstern)撰文的《一個老女人的故事》日譯本名為《巴黎老奶奶的故事》,譯者為著名女藝人兼作家岸惠子。巴黎老奶奶是個猶太移民,不得不離開自己的國家。孩子們在戰爭中四散逃亡的慘痛經歷是她心中永遠的陰影,“她知道,就是得到全世界的甜美糖果,也絕不會減輕心中的傷痛”。老婦人腿腳不便、牙口不靈、眼神不濟,上街購物、做飯吃飯、拿鑰匙開門都是大事難事,還健忘,整天找東西。老婦對鏡自語:“皺紋,皺紋,皺紋,可愛的皺紋啊。我的臉上刻著,四分之三個世紀里品嘗到的,人生的苦樂。”夜里,往事走馬燈般旋轉不停,老婦嘆息著吞下一粒安眠藥。這本書讓當時六十八歲的岸惠子心有戚戚,打破了不做翻譯的戒條。《后記》中岸惠子說:“依然夢想著旅行與冒險的我對衰老亦有所覺悟,但也相信自己還有使不完的勁兒。”岸惠子如今九十高齡,經常寫作到凌晨三點,中午才起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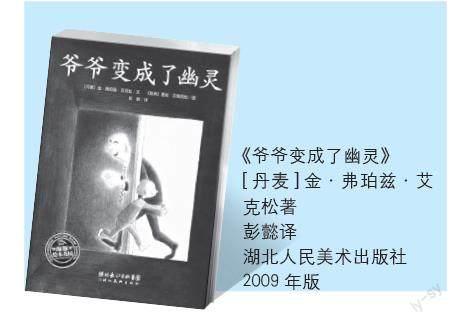
金·弗珀茲·艾克松(Kim Fupz Aakeson)撰文的繪本《爺爺變成了幽靈》描繪了死亡與告別。爺爺突發心臟病離世,艾里克哭得死去活來,學也不上了。夜里爺爺變成幽靈穿墻而來,自己也忘了來做什么。祖孫倆出門散步,來到爺爺家,一同回憶從前的溫馨時光。爺爺明白了,自己回來就是為了跟艾里克說再見。有了這番儀式,艾里克終于定下心來,又去上學了。長子幼時共讀這本書,讀得難過,好多年沒再碰。其間孩子們的外祖父去世,祖父去世,外祖母去世,一樁樁的生離死別。如今再讀,仿佛已跨過幾重山水,悵惘中亦有了那么幾分釋然。
童年時光澌澌流走,記憶的繪本里印刻著離奇的、夢幻的、甜蜜的、悲傷的……原汁原味的、有滋有味的生活。
渡? 河
小時候好像沒讀過什么像樣的童書,仿佛從小人書一下子就跳到了大部頭的三國水滸紅樓,親子共讀也像補課。回望共讀的日子,其實統共也沒多少年,眨一眨眼就過去了,只是當初,似乎每天都漫長。臨睡讀繪本,有時比孩子還困,尤其是冬天,半感冒狀態,白天教書,晚上聲音喑啞,實在有些對不起夢幻童話。孩子睡了還得放下大灰狼小紅帽,重拾孔乙己祥林嫂,糾結于為師為母的角色轉換。
長子幼時也看小人書,一大盒三十六本《西游記》全都一起讀過。隔了幾年,世間越發聲光化電、五色迷目,電視更加高清,繪本也進化得有聲音有味道,有小洞洞或鑲著小鏡子……小人書蒼蒼白白,像童書標本,亦像上個世紀的化石,次子不感興趣。我心有不甘,母子游沖繩時就只給他帶了幾本《西游記》小人書,讓他別無選擇。每晚床頭燈下大講西游,大鬧天宮,盤絲洞,三借芭蕉扇,三打白骨精……次子聽得也津津有味。但黑白小人書終歸敵不過斑斕五色,敵不過高清聲光化電,回東京后次子就又不碰小人書了。至少,西游沖繩,次子還記得個猴哥。
百年前周作人談到兒童圖畫書時曾說“中國現在的畫,失了古人的神韻,又并沒有新的技工”(《兒童的書》),百年后面對林林總總的童書,還是困惑。碰到色彩俗艷、圖畫死板的就糾結,遇到措辭不切、譯筆不暢的則邊看邊改,邊潤色邊講。魯迅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四日致蕭軍蕭紅信中談到了童話《表》的翻譯,自云“想不用難字,話也就比較的容易懂,不料竟比古文還難,每天弄到半夜,睡了還做亂夢”。魯迅尚且如此,童書之難譯亦可想而知。《爺爺變成了幽靈》的日文譯本雋永耐讀,其譯者菱木晃子在接受“好書好日”網站采訪時一再說,“翻譯繪本得有詩心”。詩意難覓,詩心難尋。培育想象力及語感的黃金時期,不讀好書或許還不如不讀為好,玩泥巴也許更重要。困惑,困惑,摸石頭過河。
困惑中,糾結里,魔幻歲月不再,金色河流遠去。

